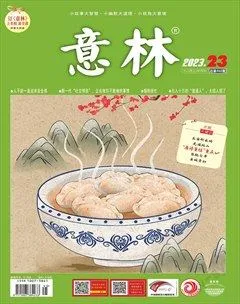學生和我一起過中秋節
劉年貴
十八歲那年,我中師畢業,被分配到一所邊遠山村小學教書。
學校在村子最東邊,掛在半山腰,周圍被梯田和菜園包圍著。就是取水和撿拾柴火,也須走上三四里羊腸小道,生活極為不便。
開學已有半月余,適逢中秋節放假,鄰村的校長和同事都回家過節,我因路途遙遠,再加上交通不便,早在開學之初,就寫信告知家中父母:“中秋節不回家。”傍晚時分,村子里傳來此起彼伏的爆竹聲,那是村民在過節團聚。而我置身操場,面對著空空的校園,倍覺清冷。就在剛才,我還拿出早上從集市買來的魚肉,準備做成幾道佳肴,然后擺上月餅和美酒,來個“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月下獨酌。可是我一看到冷冰冰的廚房,黑洞洞的灶門(當時還是土灶臺做飯),想著往日里幾位老師一起做飯的熱鬧場景,想起溫馨的家,不覺悲從中來,于是沖出了廚房,一個人在操場上傷心地抽泣起來。畢竟,我也還是個孩子,我想家呀!

正當我停止哭泣擦拭眼淚時,耳邊突然傳來:“老師,中秋節快樂!”我循聲望去,對面圍墻上探出幾個小黑頭,隨即他們翻身跳下圍墻來到我身邊,接著向外一招手,又有幾個小家伙從校門走進來。領頭的那個高個子男生說:“老師還沒吃飯,走——咱給老師做飯去。”原來這些小家伙在暗中觀察我!領頭的男生話音剛落,他們沖進廚房,燒火、淘米、煮飯、切菜、炒菜有條不紊地忙碌著。這些小家伙都是一至四年級學生(當時村小學只有一至四年級,五、六年級須到鎮上中心小學就讀),我教他們語文,他們連課文須默寫的生字甚至“a、o、e”都不會寫,為此沒少挨我批評,不過我也經常用毛巾擦拭他們的黑手和大花臉,為了感謝我,他們利用空余時間主動給我抬水及撿拾柴火——別看他們人小,可干活是好手。
看著他們有說有笑地做飯,我心情有所好轉,也加入他們行列。不一會兒,飯菜做好了,我們端到操場上,大家席地而坐,邊吃邊談笑。吃罷晚飯,他們搶著收拾碗筷清洗餐具,又一起圍在操場給我唱歌講故事,這些機靈鬼!知道我一個人很寂寞,特來陪我過中秋節的。我們的“表演節目”引來更多的人,尤其是那些村民,得知我留在學校過中秋節,紛紛拿出家中的月餅及剛收獲的梨子和板栗。人越聚越多,整個操場幾乎擠滿了人。大家圍成一圈,村民和小孩紛紛上前表演節目,或是唱歌,或是說相聲、講故事,或是當場耍起了武術拳腳,一時間校園上空歡呼聲、喊好聲和巴掌聲一浪高過一浪。在那個年代,整個小山村都沒有一臺電視機,村民不能觀看“中秋晚會”,于是來個現場版“村中秋晚會”。大伙興致很高,當節目至高潮,一致要求我也來個節目,于是我走到圈子中央唱了首《難忘今宵》,我的唱功,贏得了經久不息的掌聲。
不覺間,已是月上中天。那輪滿月似乎也帶著微笑,在深情地凝望著我們呢。
沒承想,離開父母的第一個中秋節是跟孩子們一起過的。也是那個中秋節,堅定了我要留守農村執教的信念。沒想到,我這一堅守就是整整二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