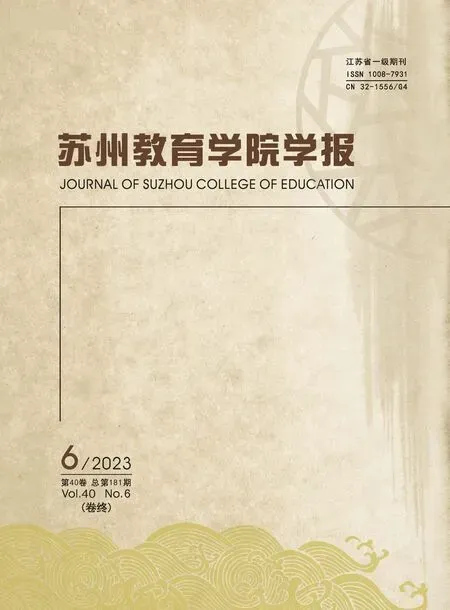文學史重構與文體升降
——周作人批判清季文論發微
白新宇
(北京師范大學 文學院,北京 100875)
以1904 年在《女子世界》發表《說死生》為開端,周作人正式介入清季文壇,受林譯小說與梁啟超政論文的影響,其文學趣味與思想主張大體不出晚清趨新之士開辟的論域。1906 年周作人隨兄長魯迅東渡日本后,思想為之一變,在把握西方近代文明根柢的同時超克時賢施于自身的影響,尤其是1908 年的《論文章之意義暨其使命因及中國近時論文之失》[1](以下簡稱《論文章》)一文,立與破相結合,厘清文學的定義,探析文學的使命,在新文學觀念燭照下對清季流行文論展開批判。
周作人的文學觀有兩個重心,分別為學問(Learning)與審美(Esthetic)。他以古今中西的思想為縱橫坐標,對清季文論的批判即對兩個重心之一畸形發展的批判。在具體實踐中,周作人放過偏倚審美的傾向,矛頭主要指向納學術于文學中的泛文學觀以及將文學系于政教治化的功利化理解,圍繞清季文論的文學概念界定、文學史書寫、小說論展開,批判對象包括林傳甲、陶曾佑、金松岑、梁啟超、羅辀重、陸紹明、林紓、吳趼人、沈敦和等。本文細致梳理周作人批判對象的基本情況、批判邏輯的曲折展開,關注“代溝當中所存在的同一性”[2]問題,重新勘探文學理解范式的轉變軌轍。
一、“文學”作為“美術”之一部
周作人批評清季文論的言論集中體現在《論文章》第21—26 段,其中的第21—23 段批評的是,長期以來被認為是中國人自著的首部文學史—林傳甲的《中國文學史》[3],以及陶曾佑的《中國文學之概觀》[4]、金松岑的《文學上之美術觀》[5]。周作人指出,金文從標題上看顛倒了“文學”與“美術”的從屬關系,林著“言必宗圣”[1]108,陶文“耿介于程器”[1]109,未明了文學之意義,墮入儒教思想專制的窠臼。周作人深明“一國文明之消長,以種業為因”[6],當下文學觀往往由千年以上觀念漸積而成,因此周作人上溯至孔子,認為孔子刪詩“束思想于一縛”,文藝淪為“潤色鴻業、宣布皇猷”的工具,[1]107《文心雕龍》亦不免于此,其章節安排以《原道》為開端,繼之以《徵圣》《宗經》,在《序志》中交代寫作此書旨在敷贊圣旨。在周作人看來,劉勰同樣墮入弼教輔政的傳統,“于博學明辨之中”流露出“一種教徒氣”[7],降及后世,文章的意義愈晦,地位愈卑。應該指出,周作人對《文心雕龍》的指摘是有選擇性的誤讀,《原道》所本之“道”首先是“自然之道”,是本于垂象鋪形的天地之道,不同于韓愈《原道》建構的排斥佛老的儒家“道統”,劉勰尊孔宗經而不妨其禮佛,但周作人去歷史化的批判為重新界定文學、重構中國文學史的圖景提供了契機。
周作人沒有讀過金松岑《文學上之美術觀》原文,因而所費筆墨最少,但其論旨關聯諸種批評的理論出發點—文學是“美術”之一門。《文學上之美術觀》初刊于1907 年《國粹學報》,作者金一即金松岑(1873—1947),他是晚清“女權革命”的積極提倡者[8],著有研討婦女問題的著作《女界鐘》(1903)及小說《孽海花》前6 回,是周作人留日前發表文章的主要陣地《女子世界》雜志的支持者,在《〈女子世界〉發刊詞》中金一號召“振興女學,提倡女權”以鑄造“新國民”[9]。周作人翻譯的柯南·道爾短篇小說《荒磯》(The Man from Archangel)與金一的文章在《女子世界》同期發表,周作人的《好花枝》與金一的《〈女子世界〉發刊詞》開篇皆以花喻女子,周作人應該了解金一并非閉塞守舊之輩,卻在沒有讀過金一文章的情況下貿然批判,此舉更宜視為周作人對留日前文學思想的自我反思與自我清理,從而完成對晚清流行之文學論的超克。
周作人批判金文的原因在于,從標題上看,金松岑“以文學觀美術”,“文章可屬之美術而不能以統美術”[1]106。不同于當下僅指視覺藝術的“美術”概念,周氏兄弟在日本接受的用來對譯英文“art”或“fine art”的“美術”概念的包羅范圍更加廣泛,在周作人那里“美術”包括“土木金石繪畫音樂以及文章”[1]91,魯迅亦謂“文章為美術之一”[10]73,植根于審美活動的“美術”包含“文學”①周氏兄弟的“美術”觀可追溯到法國學者巴托的《歸結為單一原則的美的藝術》(1746),參見張勇:《魯迅早期思想中的“美術”觀念探源—從〈儗播布美術意見書〉的材源談起》,《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7 年第3 期,第116—127 頁。黑格爾《美學》第三卷“各門藝術的體系”,包含建筑、雕刻、繪畫、音樂、詩等,參見黑格爾著、朱光潛譯:《美學》,商務印書館2020年出版。。其實金松岑并未如周作人所說“以文學觀美術”,但也沒有單純在“art”這一名詞意義上使用“美術”。金文中的“美術”時而作“藝術手法”解,時而作“審美感覺”解,含義夾纏不清,文中的“美術”一詞自始至終未體現出有別于“文學”并包含“文學”的現代內涵。[5]金文主旨在于論述“文章以碑銘為宗”,而“詩歌以樂府為盛”,[5]論據出自《文心雕龍》的《銘箴》《誄碑》篇和鄭樵《通志·樂略》,思想資源基本囿于傳統文論。即使周作人讀了《文學上之美術觀》原文,金松岑表彰主要用來“勒石贊勛”[11]214的碑銘亦難以被反感“希勒石圖形之熱中者”[1]100的周作人所接納。
另一篇被周作人猛烈批判的文章是陶曾佑的《中國文學之概觀》,該文發表于《著作林》1908 年第13 期②《著作林》不著出版時間,上海圖書館編《中國近代期刊篇目匯錄》第二卷(中)根據該刊第17 期出版廣告時間為戊申六月(約1908 年7 月),按“月刊一冊,望日發行”推斷該刊創刊于丁未年(1907)二月,第13 期出版時間應為戊申二月望日。,作者陶曾佑生平不詳,僅知其為“甌閩”人。長期以來,研究者將陶曾佑與陶祐曾混淆為同一人①需要說明的是,大量文論選集與研究文章誤將“陶曾佑”與“陶祐曾”混淆,陶曾佑在《著作林》發表過《中國文學之概觀》(第13 期)、《論文學之勢力及其關系》(第14 期),后一篇署名“甌閩 陶曾佑”;另一位湖南安化人陶祐曾在《游戲世界》第10 期發表《論小說之勢力及其影響》。陶祐曾生平資料及著作參見郭延禮:《近代小說家和小說理論家陶祐曾》,收錄于《中西文化碰撞與近代文學》,山東教育出版社1999 年出版,第509—524 頁。舒蕪編的《中國近代文論選》將上述三篇文章誤認為都是“陶曾佑”所作,徐中玉編的《中國近代文學大系·文學理論集》將上述三篇文章誤認為都是“陶祐曾”所作,大量研究文章亦輾轉延訛。。《中國文學之概觀》是一篇極簡版中國文學史,陶曾佑不無夸張地認為文學優于其他學科,從包羲創八卦談起,簡要勾勒戰國至清歷代文學變遷情況。周作人的批評從陶氏的文學觀入手,指摘“其言文章,初既并諸一切文書”[1]106,即陶氏將八卦、文字、河圖洛書一并闌入文學,“繼復分為二物”[1]106,指的是陶氏區分文學為“正體之文”與“變體之文”,“有益于一般事實者即為正體之文,有損于普通組織者即屬變體之文也”[4],這種正、變之分大體脫胎于《詩大序》以時代治亂區分“正風正雅”與“變風變雅”,正、變的評判標準轉換為文學的現實功效。周作人所言,“后復言維新之士,心醉東西洋之文學,襲取其唾余,轉相則效,彼國極粗淺之一名一詞,無不驚為至寶”[1]106,指的是陶曾佑在文章結尾處告誡同胞,“慎毋數典忘祖,徒歡迎晰種之唾余,舍己蕓人,盡捐棄神州之特質”,召喚“力挽文瀾,保存國學……競爭文界,排擊文魔”。[4]陶曾佑在《論文學之勢力及其關系》中也有類似表述,他批評近世青年“競尚西文,侈談東籍”,“于祖國固有之文明,排斥不遺余力”[12]。衰世文人面對西潮強勢襲來而捍衛國粹,稱對手為“文魔”,暴露其思想的局限性。
周作人批評陶文之失在于“耿介于程器”。“耿介于程器”語出《文心雕龍·序志》,指的是劉勰在《程器》篇評騭文學家的道德品質與識見,周作人以“耿介于程器”概括陶文之失,說明他看出陶氏立論多本于《文心雕龍》且愈發趨于苛刻無情。現代文學觀念傾向于將文學作品視為獨立的藝術品,藝術品的文學品格與創作主體的道德品質無涉,然而在文學未獲得本體性的時代,作家道德成為衡量文學價值的第一標準。陶曾佑根據《文心雕龍》“宋發巧談,實始淫麗”[11]135及“自宋玉景差,夸飾始盛”[11]608,認為宋玉、景差之徒“理想雖甚微,然詞華之茂,固擅一時矣”[4],周作人顛倒陶文語序,突出陶曾佑對宋玉、景差“理想甚微”的批判性面相。陶曾佑依據《程器》所歷數的“文士之疵”批評班固、揚雄、司馬相如等人“文有余而行不逮,華有余而實不存”[4]。與此針鋒相對,周作人反顧《文心雕龍》,從中提取批評陶曾佑的思想資源。劉勰對德行有疵累的文士、將相并非一味譴責,而是懷著同情與理解,王戎以平吳之功封安豐侯,賣官鬻爵,同樣名列竹林七賢,更何況司馬相如、杜篤、丁儀、路粹這樣的貧寒之士,欲有所作為而夤緣攀附亦可理解,自非上哲,難以求備,隨意臧否古人不過是勢利的幫兇。周作人引《全唐詩話》卷四所載溫庭筠因得罪宣宗,以“德行無取”為口實被謫方城尉的故事,暗示陶曾佑的立論同乎此類深文周納的苛評。在周作人后來的寫作生涯中,他格外重視觸犯禮教的文士,正面闡發孔融、李贄、馮夢龍、王思任、金圣嘆的價值,重構理想的文學史圖景,梁簡文帝“立身先須謹重,文章且須放蕩”[13]作為對“程器”的反撥受到周作人的青睞,他從此言看出簡文帝“對于文藝有了解”“知道生活的道理”[14],符合文與人分離的現代文學觀念。具有獨立品格的文學自有其檢驗高下的標準—趣味(taste),趣味的高下是杰出作品的試金石。
從陶氏僅存的兩篇文章來看,他并非不知世事之輩,而是較為廣泛地吸收晚清新知,對文壇新人佳作如數家珍。論劇舉汪笑儂,論詩舉黃公度、蔣觀云,論譯學舉林紓、嚴復、馬君武,論文則舉章太炎、梁啟超、劉師培、柳亞子,論小說則舉陳冷血①原刊本“陳冷血”誤作“許冷血”。、包天笑、李伯元、喋血生,可見其閱讀范圍之廣。文章使用“巴科民族”“天演場”等詞語表明陶曾佑受到中國人種西來說及進化論等新思潮的沖擊,他認識到元代詞曲發達“正語言文字合一之漸也”,小說發達“開俗語入文之漸也”。[4]陶曾佑沒有像林傳甲那樣痛斥戲曲小說,不歧視俚俗文辭,表現出其通達開明之處;他認為“文學為群治之萌芽”,表彰斯巴達“尚武精神”,認為中國經學“詳于私德,略于公益”,[12]顯然受到梁啟超《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系》和《新民說》之《論尚武》《論公德》中認為中國道德“偏于私德,而公德殆闕如”[15]的啟發。陶曾佑回溯晚明文學曾慨嘆諸才士留“悲愴之影于吾漢族歷史之中”[4],似悵恨于漢族所失權柄,但他似乎并不支持革命派的活動,從《中國文學之概觀》開篇引用蔣觀云《盧騷》詩,改“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16]為“文字收功日,全球改革潮”可見一斑。在周作人未提及的部分,陶曾佑還是一位身處聲光化電等“質學”熱潮卻崇尚靈虛的文學之人,他從“立國之特別精神”[4]、“國魂”[12]的高度界定文學的地位,這與《論文章》的開篇相似,二人并非沒有可以溝通之處。但他在“摛文必在緯軍國”[11]720傳統觀念的影響下,篤信文學的價值是“載道明德,紀政察民”[12],推崇王陽明開化人群的簡易文章,魏晉玄學由于無益于載道明德而見黜,使他注定無法跨入現代文學觀念的大門。總體而言,陶曾佑是一位受新潮影響,有意趨新,但根柢仍舊的過渡時代的人物,周作人對他的批判則是文學觀更迭嬗變的微觀表征。
二、文學史圖景的重構
周作人批評林傳甲《中國文學史》用力最猛。長期以來,林傳甲的《中國文學史》被視為理想文學史的反面鏡鑒,20 世紀90 年代以降,夏曉虹、戴燕、陳國球、陳廣宏等學者揭示出林著與《奏定大學堂章程》(以下簡稱《章程》)的關聯,評價漸趨客觀。林氏《中國文學史》②筆者閱讀的《早期北大文學史講義三種》所收《中國文學史》據1910 年武林謀新室的校正本(1914 年第6 版)影印,與1908 年周作人讀到的版本不同,核查發現周作人所引文字與1910 年版微異。如“后漢列文苑者二十二人”,1910 年版作“后漢列文苑有二十有二人”;“乃歸于漢人之竄入”,1910 年版作“乃歸罪漢人之竄入”;“而民間無學不識者流”,1910 年版作“而民間無學不識者”,類此均無關宏旨。內容駁雜,結構編排按照《章程》中文學科大學中國文學門的具體要求,全書16 篇的篇名與中國文學門科目一“文學研究法”的“研究文學之要義”的前16 項要求一致[17]355,第1 篇“古文籀文小篆八分草書隸書北朝書唐以后正書”參照《章程》經學科大學補助課“說文學”的講習法[17]345,第2 篇“古今音韻之變遷”參照中國文學門“音韻學”講習法[17]356,批評今文學家“黜周王魯”[3]114也與《章程》規定講《公羊春秋》應避免“借經術以禍天下之害”[17]343桴鼓相應。但林傳甲并未全盤接受《章程》的要求,作為趨新的開明之士,他在尊孔的前提下悄然提升諸子的思想價值,主張以經世致用的眼光讀諸子之書,正面掊擊《章程》中“文學家于周秦諸子當論其文,非宗其學術”[17]357的觀點。通讀林氏《中國文學史》,可知他對清代學術及日文典籍頗為了解,書中所提和、漢文籍甚夥,③林傳甲《中國文學史》提及與征引日文書目如下:落合直文《言海》、武島又次郎《修辭學》、兒島獻吉郎《漢文典》、遠藤隆吉《中國哲學史》、小宮山綏介《孫子講義》、大田才次郎《莊子講義》、笹川種郎《支那文學史》、古城貞吉《支那文學史》、中根淑《支那文學史要》、坂本健一《日本風俗史》。眼界較為寬廣。然而林著的官方屬性與致用追求恰恰與周作人建構的文學本體觀有所沖突。此時,周作人已讀到泰納的《英國文學史》、圣茲伯利的《英文學小史》,認識到文學具有反叛政治教化的獨立屬性,文學作品并非個人想象力與心智的戛戛獨造之作,而是當代精神與行止的復寫,文學與歷史事件互相闡釋[18],研討文學史“必與其史實相緣”[1]107,周作人歷史化的考察路徑將恒久不變的政教桎梏相對化,為文學史的重構創造了可能性。
林傳甲及其依托的《章程》依然拘囿于視文學與政治教化合一的傳統觀念,是統治者意識形態與趨新知識官僚認知形態的綜合,褒貶揚抑間暗含著有意變革而心存抵拒的復雜心態,變革之心投射在書中,即以實用程度排列諸子之文價值,欲于四部之外設外部,抵拒之心體現為尊孔、批評行文貪用東瀛新名詞等。無論何種情況,文學皆不具獨立價值,脫離政教羈勒的詞章遭到撻伐。周作人對林著的摘批集中于其第4、6、7、9、10、12、14 篇,其中第4 篇“古以治化為文今以詞章為文關于世運之升降”勾勒治化與詞章由合至分的歷程,“治化之文”即以文字書面形式呈現的君主治理教化的方策,“詞章”指向脫離政教的情感抒發,如商紂、六朝的衰世正是詞章泛濫之世,六朝文的價值因無關風教而遭到貶抑,講求詞藻的文學成為亂國的原因,“竭云約之才,締成梁武之篡謀”[3]192,“咀嚼聲偶”[3]75之才無益于世,徐陵、庾信不過“古之夸人”[3]193。周作人批評這種不離治化的文學觀,召喚的正是后來被稱為“文學的自覺”的本體觀念。
周作人激烈批孔,置文學于經學之上,消弭經書的神圣性,將經書當作文章研治,1921年他論述《圣經》研究的文學路徑基本延續這種思路展開。此時周作人牛刀小試,批評林氏在《中國文學史》第9 篇第15 章“屈子離騷經文體之奇奧”為《楚辭》爭取子部地位的做法。《楚辭》在《隋書·經籍志》隸于集部,《四庫提要》沿襲,林傳甲認為《楚辭》不列于經部是由于未經孔子刪定,但可列入子部,“為諸子中有韻之文”[3]142,與老莊及賈誼《新書》并列。林氏為《楚辭》爭子部地位反映出四部分類法背后的價值等級差異,尊經而賤集,故林氏會不滿于《楚辭》“儕于后人碌碌之文集”[3]142。然而升《楚辭》于子部的做法正陷入傳統文類等級制的陷阱,反而湮沒《楚辭》作為“無韻之詩”的價值。周作人認為《離騷》與《國風》及后世詩賦、傳奇、歌曲同歸詩類,即前文所說的根于至情的“言志”之聲,周作人從審美角度出發,有選擇性地重塑《離騷》的形象,認為《文心雕龍·辨騷》“文辭麗雅,為詞賦之宗”[11]46的評價更準確地道出了《離騷》的價值。如果進一步聯系魯迅在《摩羅詩力說》中賦予屈原“放言無憚”“孤偉自死”[10]71的品格,可知林氏與周氏兄弟文學思想的溝壑。當林傳甲依照四部分類法的等級結構為屈原鳴不平時,周氏兄弟已用現代文學觀念重新審視屈原的文學創作,周作人強調《楚辭》的文辭本身的審美價值,魯迅則將屈原與爭天拒俗的摩羅詩人作比較,他們是以“世界文學”的宏闊背景作為參照。在現代文學觀念的燭照下,重構中國文學史圖景的沖動與嘗試已隱含在文章之中。
周作人在批評林傳甲時順帶不點名地批評了沈敦和,文中“近有人論科學與道德之關系者曰:‘人之大患,在欲發達其思想。’”[1]112一句,出自清末民初頗具影響力的社會活動家沈敦和的演說文章。1906 年11 月17 日下午5 點[19],沈敦和在美國傳教士李佳白倡辦的尚賢堂發表演說《論道德心與科學之關系宜亟謀德育以防人民日即于非行》①此文最初刊登于1906 年11 月19 日的《申報》與《新聞報》,《申報》標題作《論道德心與科學之關系宜亟謀德育以防人民日即于非行(尚賢堂來稿代論)》,《新聞報》標題作《論道德心與科學之關系(來稿)》;1906 年12 月1 日再次刊發于《寰球中國學生報》第1 卷第3 期,標題作《論道德心與科學之關系》;1907 年1 月1 日《通學報》第2 卷第16 期發表楊味西筆述的版本,題為《道德心與科學之關系》;1907 年11 月23 日《北華捷報》報道沈敦和演講,英文報道結尾部分交代李佳白對沈敦和演講內容的肯定,李佳白認為如今的中國人更需要goodness(道德)而非enlightenment(啟蒙),這段信息為中文報道所無;1908 年3 月2 日《廣益叢報》第161 號再次刊登,標題作《論道德心與科學之關系宜亟謀德育以防人民日即于非行》。《通學報》的版本與其他各版文字有較大差異,并且沒有周作人提到的“今日之大病何在乎?曰在人人欲發達其思想”這句話,可知周作人看到的不是這一版。,他說道:“今日之大病何在乎?曰在人人欲發達其思想,奉歐美權利之說為泰斗,而視吾固有之道德若弁髦。”[20]沈敦和亦非不知世事之輩,他曾留學英國,為中國慈善、教育及婦女解放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在演說中,沈敦和承認中國“自秦以來,進化停頓”,但科學應限定在倫理道德的框架中,將科學作為“強國保重”的工具,而非損人利己的兇器。沈敦和的焦灼主要針對西方科學技術逾越了中國儒家倫理的規范,導致科學為不道德者利用作惡,但他開出的救時弊之方帶有一定保守性—“崇尚經訓”,從四書五經中搜集覺世勵民的內容,“編輯古人之嘉言懿行,為修身課本”[20],以經訓為圭臬申斥“人人欲發達其思想,奉歐美權利之說為泰斗”,無異于為清朝的專制統治提供了意識形態基礎;譴責國人“步俄之虛無黨”,矛頭指向頻頻進行暗殺活動的革命黨人同樣佐證這一點。沈敦和譴責虛無黨,恰與為虛無主義正名的周作人產生了沖突[21],自然引起被排滿思想吸引、堅信“必與政府相敵,此必然之勢”[22]的周作人的不滿,這也是周作人在批評林傳甲時聯想到沈敦和之言論的原因。此外,沈敦和在演說結尾提倡“利人主義”,“使知非利人則自利必不能完全”,[20]與嚴復認同的“開明自營”,“非明道則無以計功,非正誼則無以謀利”[23]相通,為興辦實業、追尋富強提供意識形態基礎,而周作人直斥夾纏儒教思想的富強之說將強化禁錮人心的實利觀念,希望以“靈虛之物”為濟渡中國的方舟,這也是沈敦和言論為周作人所惡的另一原因。
三、文體升降中小說的位置
在中國文學現代化的進程中,文學擺脫政教倫理的規范而獨立出來,部分實用性文體被摒棄于文學畛域之外,不同文體的地位有所升降,小說由邊緣走向中心,由“君子弗為”的“小道”躍居“文學之最上乘”[24]。面對小說在清季的崛起,趨新之士從借助小說開啟民智的角度加以肯定,推波助瀾,清政府的文教官僚視小說為“洪水猛獸”,禁扼排詆。周作人針對晚清關于小說的諸種言說,摧陷廓清,從小說本體與小說功用的角度為小說尋找恰切的位置。
周作人對晚清言論場中“不以小說為文章”[1]110的觀點加以批判,納小說于文章/文學與藝術之中。周作人拈出兩種關于小說的對立觀點,其一是陶曾佑《中國文學之概觀》對當下文學的高度評價,他認為今世文學的內容與外表均達到“極點”,近代文豪可“傲睨東西”[4];其二是林傳甲《中國文學史》第14 篇“唐宋至今文體·元人文體為詞曲說部所紊”對說部文體的撻伐,林傳甲認為元代文格日卑源于說部、詞曲的興盛,對笹川種郎的文學史述及湯顯祖、金圣嘆進行攻擊,不滿于近來翻譯小說的興盛,希望將小說查禁焚燒[3]209-210。一則褒舉,一則貶抑,在周作人看來皆荒謬不經。陶曾佑的觀點在當時并不普遍,周作人在此也沒有過多糾纏,而是強調借鏡他國以反觀中國當下文學的蕪陋,重申文學趣味需尚美而非卑瑣。
林傳甲的小說觀代表了仕宦清廷的文教官僚的小說觀念,雖日益見棄于開明之士,但在官方仍占統治地位。小說、戲曲在元、明、清三代長期面臨專制朝廷的禁毀,官員雖私下傳閱小說以為談資,但明面上的禁扼之勢有增無減。張之洞曾參與草擬《章程》,其早年撰寫的《輶軒語》告誡學子戒“自命為才子名士”,斥金圣嘆為“俗陋人”;[25]其《書目答問》小說家部分列舉的書目以“雅核可信”為標準[26]。學堂教育以實用文寫作為主,若有學生閱讀小說將受到嚴厲懲罰,作為學堂講義的林氏《中國文學史》對小說的態度自然合于矩矱。
周作人對林氏《中國文學史》的批駁分為三步:第一步,暗引太田善男《文學概論》的說法,將小說歸入“純文章”中“讀式詩”一類,肯定小說與戲曲的文學屬性,未來梳理中國文學史必不可遺落小說。第二步,批評林氏攻訐“譯新小說以誨淫盜”[3]210的說法,認為小說與教誨無涉。周作人在南京時讀到政治小說《經國美談》,感到“不能引人入勝”[27],對承載政治理念的小說表達不滿,至東渡泛覽諸國文學史,正面抨擊中國“文章與教訓漫無畛畦”[28]之弊。所謂“教訓”包括正、反兩面,主張禁毀小說者看到的是“誨淫盜”,主張以小說“新民”者看到的是“誨道德”,兩面統歸于一體,在周作人看來,二者皆未將小說當作獨立的文學范疇。淫盜之罪產生于現實世界,產生于人類食色之本性[29],文學的價值之一即“闡釋人情”[1]103,不能顛倒現實罪惡與文學書寫的發生順序。第三步,周作人指出林氏“戮其人而火其書”[3]210的思想專制本質,這一釜底抽薪的批判彰顯其排滿革命的政治追求,點明清廷專制是阻礙小說發達的根本障礙。周作人在1907 年發表的《防淫奇策》已將批評的矛頭指向清政府頒布的《學堂禁律》[30],針對林傳甲的批駁是此類批判的持續與深化①《學堂禁律》共12 條,第6 條“各學堂學生不準私自購閱稗官小說、謬報逆書,凡非科學應用之參考書,均不準攜帶入室”,正是周作人批判的內容。《學堂禁律》的頒布與1907 年9 月30 日清廷諭令張之洞管理學部有關,張之洞管理學部以尊孔為宗旨,約束學生的思想、行為,因此,張之洞也是周作人的潛在批判對象。。周作人論文藝主張寬容,認為文藝的生命是自由,尋覓文化事件背后的政治力量,這是其思維方式中持久穩定的特點。
在批判否定小說價值的保守觀點、肯定小說的文學屬性之后,周作人開始批評趨新人士對小說的功利化理解。官方對小說的詆諆與查禁反襯出小說在民間的廣受歡迎,趨新之士紛紛從“開民智”的角度推崇小說,針對褒舉小說言議的批判更能顯示周作人文學思想的深度。
周作人認為小說的作用在于通過“托意寫誠”以“移人情”[1]113,“非主誨示”[1]114,以小說寓教訓的改良之士與禁毀小說的清廷同樣無視小說作為藝術的審美自足性。利用小說、戲曲教誨百姓的想法并非始于晚清[31],但晚清時局危阽促使士人格外重視小說轉移人心、風俗之效②1897 年,嚴復、夏曾佑刊載于天津《國聞報》的《本館附印說部緣起》將小說視為“正史之根”,希望借助小說“使民開化”,參見陳平原、夏曉虹:《二十世紀中國小說理論資料:第1 卷(1897—1916)》,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 年出版,第1—12 頁。,梁啟超的《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系》標舉小說治化之功并產生深遠影響,這一點周作人已指出。周作人著重從混亂的小說分類角度批評晚清小說論,這是因為在實用者眼中,作為工具的小說需要按照它所承載的內容來劃分部類,小說不過是包在所載內容外面的有“趣味”的糖衣,以內容或題材劃分小說門類是功利思維的體現。
利用小說教誨國民這一啟蒙行為在晚清小說家吳趼人這里成為一門生意,啟蒙抱負與盈利目的難以分割。1906 年,《月月小說》創刊,旨在以小說增進國民智識以獲得立憲資格。編者吳趼人發愿“撰譯歷史小說,以為教科之助”[32],周作人批評這種觀點顛倒了歷史小說中歷史材料與小說藝術的位置。《月月小說》第3 號登載了羅辀重的《〈月月小說〉敘》與陸紹明的《〈月月小說〉發刊詞》,前者視小說為樹立國民自治心的誘餌,試圖在清廷“預備立憲”的氛圍中證明小說的價值[33],后者在五經與諸子中尋覓小說源頭[34],將小說的價值建立在傳統學問之上。周作人拈出羅文中“夫立憲之國,期于人人有自治心,何以使心能自治,則惟投其心之所喜而治之”[33]一句,指出此論斷不過是將小說視作規范人心的“臥碑”,即束縛思想的禁律,與文學發揚神思的批判精神相悖逆,而陸紹明無視小說作為文學/藝術之一門類的屬性,出于現實訴求“發明”并不實存的小說傳統,乖離之處自不可免。
此外,周作人又將批評的矛頭指向曾對他的小說閱讀興趣產生重要影響的林紓。1906 年,林紓與曾宗鞏(版權頁作魏易)合作翻譯了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記》前兩部,命名為《海外軒渠錄》出版。周作人抵日不久讀到泰納的《英國文學史》,從中了解到斯威夫特的文學成就及其反諷藝術所蘊蓄的政治悲憤①周作人文中“法人泰納(Taine)作《英國文章史》,極稱異其人,方之火中宮闕,愈見其美”一句來自泰納《英國文學史》第2 卷第55 章的最后一句:we say that a palace is beautiful even when it is on fire. Artists will add: especially when it is on fire。,認為以“軒渠錄”(笑話集)作譯名背離小說本旨,令讀者視之為“滑稽小說”,在歡笑中忘卻背后的沉痛。不過從林紓序文中可知,他雖然混淆了作者與主人公/敘述者的區別,但還是敏銳地把握到怪誕故事背后的政治孤憤,點明斯威夫特寫作此書“侘傺孤憤,托為奇想,以諷宗國”[35],將葛利佛與孤憤投江的屈原相類比,以“軒渠”命名不能說明林紓對此書完全隔膜不通。
周作人接著提到林譯“實業小說”《愛國二童子傳》,此書以14 歲的恩忒與7 歲的舒利亞兄弟從羅亨乃(Lorraine,通譯洛林)潛行至法國本土并在全境浪游的故事為線索,勾連起法國各地區的自然景觀、風土物產、名人事跡,兩兄弟在漫游途中遍歷人事而逐漸成長,愛國信念愈發堅固。林紓翻譯此書寄托著他的救世思想,寫下長篇《達旨》,勸勉國民重視農、工、商、醫等實業,不要一味選擇學習法政,鼓動青年學生“愛國之志氣”[36]。此番論調招致不滿于實業救國論的周作人的強烈批評,周作人為追求小說的純文學品質嚴格排斥任何施加于文學的功利訴求。與此形成對比的是,青年胡適讀到《愛國二童子傳》后熱情洋溢地推崇此書有助于激發國民自治、發展實業、愛國以及崇拜英雄的思想[37],摘錄書中格言警句,在將小說作為承載啟蒙思想的工具這一層面上,胡適尚處在梁啟超的影響下。
林譯哈葛德“言情小說”廣受讀者歡迎,而書中間或逾越禮教綱常的情愛故事又觸犯了衛道士的禁律,譬如《迦茵小傳》的全譯本便因為出現迦茵“有妊”的情節招致批評[38]。林紓在《〈洪罕女郎傳〉序》中引《楞嚴經》中摩登伽女的故事,說明若有讀者讀言情小說心旌搖蕩,責任在于自身“遺失本妙”,與譯者無涉,暗含為翻譯言情小說辯護之意。[39]在所有被周作人批評的人中,林紓對小說的理解其實與周作人有相當接近之處,林紓了解“西人歸古文于美術”[40],宣稱“蓋政教兩事,與文章無屬”[41],為文章爭取獨立于政教的合法性,在晚清實屬難得的創辟之論②林紓在《畏廬續集·書黃生札記后》中所說的“美術”指向對“古文”的“鍛煉之法”,涉及“練字之法”等修辭手法,在“積理”的基礎上寫出“有聲之文”,宏潤而不流于油滑。參見江中柱編:《林紓集》第 1 冊,福建人民出版社2020 年出版,第116 頁。。然而禮教的熏習使林紓為其小說中人物溢出禮教框架的行止,以及翻譯過程中突破嚴苛的古文修辭禁律而感到焦慮。1907 年,林紓與魏易合譯了《雙孝子噀血酬恩記》,他在《評語》中將書中人物的行動邏輯歸結為“孝”,罵詈虛無黨人為“蠢物”,以孝子“仇虛無黨人”為“平亂”,表彰此書是西方挽救人心不古的“倫理小說”。[42]周作人此前讀到克魯泡特金的《自敘傳》(巴金譯為《我底自傳》),克魯泡特金區分被世人混為一談的虛無主義(Nihilist)與恐怖主義(Terrorism)的說法為周作人編譯紹述,克魯泡特金概括虛無主義者的獨特之處在于“絕對的真誠”[43],不拘于世俗陳規,周作人欣賞虛無主義作為“求誠之學”滌除虛偽的價值,對林紓謾罵虛無黨的言論痛下針砭。
最后,周作人否定了晚清廣受讀者歡迎的偵探小說、冒險小說的價值,認為這兩類小說皆屬于“文章之下乘”[1]114,國人嗜讀此類作品反映國民“趣味”的幼稚。周作人追求文學作品的高尚趣味,通俗小說不會因其受眾面廣、語言淺近而得到周作人的青睞。周作人批判輔益群治的功利化小說觀并不意味著他不懷抱寄寓于文學的理想,他視“文章改革”為“中國切要之圖”[1]115,希望以西方近代人道主義與自由精神振蕩儒教拘束下為實利蠱惑的國民精神,批判清季文論旨在更有效地以人道的思想、尚美的藝術形式,潛移默化地改變國人的心靈,避免倒向純粹娛樂化的境地。周作人批評僅供娛樂的文學讀物,隱含著“五四”時期抨擊黑幕小說、舊戲的理據與激情。
通行的文學史敘述往往將晚清至“五四”時期文學觀的嬗變理解為從傳統到現代、從舊到新的過程,在二元對立的模式中把握現代文學觀念的建構。梁實秋在1926 年批評現代文學之浪漫趨勢時,提出文學無新舊之分,只有中外可辨。①梁實秋認為中國文學受外國影響最緊要處即在外國文學觀念之輸入中國,從“文以載道”轉變為把文學當作藝術。參見梁實秋:《現代中國文學之浪漫的趨勢》,《晨報副刊》1926 年3 月25 日。通過細致梳理周作人對清季文論的批判,可以看出周作人由于身處東京,可以便捷地直取西潮之前沿;而為周作人所批判者,大多身居國內,陷入特定的政治經濟的結構網絡中,西學知識多由轉販而得,只能在傳統內部零敲碎打。以觀空者觀時,對于被批判者懷有同情與理解,對于周作人的批判意圖體會亦更加深刻。《論文章》并非一份凝滯的文學方案,而是召喚性的開放文本,批評清季文論是思想革命、心靈解放的重要環節,痛衰亡而思改,存希望于方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