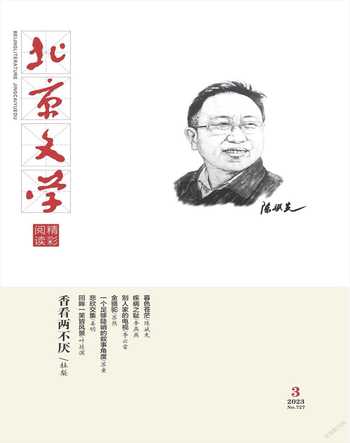故鄉(xiāng)的表情
熊紅久
下一場雪是如此地艱難,不禁讓播下冬麥的農民先是無奈地輕拂出芽的嫩苗,而后惆悵地仰視鉛灰色的天空。冬至的時令似乎與氣候所應對的景象大相徑庭。林木都早早褪去了枯葉,惶恐地擁擠在瑟瑟寒風里,街上的行人用圍巾和棉襖,將自己的外形和體溫維護在冬季所應有的狀態(tài)之內,而作為印證冬天最權威的雪,卻遲遲沒有落下。就像夜晚來臨時,人們褪去了身上的衣飾,鉆進厚厚的棉被,而睡意卻沒有到來一樣。使得形勢與內容相互脫離,雪讓這個冬天變得更像一個逃課的學生。
直到離新年還剩最后的兩天了,雪才期期艾艾地擠上了日歷的末班車,把自己運抵博爾塔拉大地,讓一個邊城的冬季,做回了自己。起先是散散漫漫似有似無,像趕早市的人們,三三兩兩;后來像上班的人流,逐漸縝密;最后簡直成了銀行破產前的擠兌,蜂擁而至,前赴后繼。整整三個小時,白色潮水淹沒了整個世界,連瞳孔都蓄滿了白色。
作為博爾塔拉州府所在地的博樂市,最寬闊的那條北京路,陡然間也開始忙碌起來。原本趾高氣揚、呼嘯而過的汽車,一下子老態(tài)龍鐘了,首尾相接,禮讓三先,好像這場雪里,蘊含了素質教育的內容。人們的舉止文雅、彬彬有禮。在岔口和彎道處,交警揮動著落滿雪花的手臂,讓城市的血液,順暢流動。
就像巴黎的埃菲爾鐵塔,紐約的自由女神像一樣,作為一個城市顯著的標志,北京橋是小城最具特色的名片。盡管橋的長度不足百米,橋下只流淌著一條窄窄的小河,卻是小城最具地標意義的存在,對博樂人而言,北京橋是情感最可靠的確認。兩個陌生人在外相遇,一談到博樂,一談到北京橋,雙手自然就會緊握在一起。一座橋,同時擺渡了兩個人的鄉(xiāng)愁。北京橋,用一個小小的橋名,就把祖國的首都與邊陲的小城連接起來,這種皈依的情感,讓這座小橋贏得了不少引以為豪的聲譽。即使隆冬時節(jié),北京橋依然成為風雪中的一道風景。夜幕降臨時,橋頭的幾十盞彩燈,投射出橘黃的暖色,頭飾一樣讓整條馬路霍然間妖嬈起來。
從天而降的雪讓博爾塔拉對冬天的注釋形象生動。其實,這纖塵不染的純潔,把自己降落到草原和被草原擁圍的城市,是對圣潔生命最高的禮贊,就像秀女選對了下嫁的人家。沒有污濁,沒有嘈雜,沒有破敗不堪的殘垣斷壁,沒有藏污納垢的泥塘濁潭,雪完全保持著原有的色澤和晶瑩,個性鮮明地走下凡塵,給這個世界披上婚紗。而此時的草原,早在完成了草木一秋的輪回之后,敞開了寬闊的胸懷,期待著被一種純凈和寧靜,悄然覆蓋。即使整個冬季過后,這里的雪依然會用潔白來逼視人類的雙眼,讓你產生昏眩,這種潔凈來自天空、大地和整座城市的呵護。沒有林立的煙囪給藍天書寫濃墨,沒有刺鼻的污水給大地注入危機,這讓博爾塔拉的山水和人們都置身于清澈透明的境遇中。
很多的水面凝結成冰層,博爾塔拉河卻沖破了寒冷的禁錮,讓自己流動的思想穿行在白色的世界里,途經濱河公園時,瘦身蜿蜒的粼粼波光,泊下一灣碧水,在干枯的水草和蘆葦?shù)沫h(huán)衛(wèi)下,構筑起一道水鳥嬉戲的樂園。天鵝是被白色修飾的精靈,游弋在霧氣升騰的水波之上,十幾只擁圍在一起,遠遠望去,水面竟浮動著一蓬蓬絨雪。忽而離開水面,在岸邊依次排開,成為長高的雪堆;或扇動翅膀,抖落水珠;或緩步走動,巡視家園。粉紅的鵝掌在平鋪直敘的宣紙上,小楷出許多意境幽遠的詩句,一幅幅田園水墨,裝裱了冬季。那群黃野鴨總也改不了輕浮的個性,在水里躥來躥去,你爭我奪。兩相比較,高下自明。天鵝的高尚,會讓你內心的情愫充滿愛意,原本簡單的白色在目光里變得豐富而靈動起來。尤其是赤冠和紅嘴,在光的折射下,成為醒目的感嘆,彰顯著生命的貴氣。天鵝,是自然頒發(fā)給這座城市最有溫度的獎牌。
從一個縣城跨越到另一個縣城,會有上百公里的間隔,這是遼闊新疆所特有的舒展和節(jié)奏。中間的區(qū)域,都會被田野和草場所填充。而此時,收割后的田野被皚皚白雪占據(jù)著,只有一些長短不一的秫秸稈,費力地刺破顏色,像一只只黧黑的溫度計,測量寒潮的深淺。更遠處是起伏的山坡,坡上一排排筆直的白楊,被寒風盤剝得只剩下了枝干。阿拉套山作為強大的背景,橫亙在博爾塔拉的北方,這個從天山伸出的健碩的臂膀,將兩萬多平方公里的綠洲,攬在懷里。田野的后面是遼闊的草場,一叢叢順著流水的自然溝壑逶迤而生的野生沙棘刺,讓整個曠野顯得錯落有致,每叢沙棘的上面,都落著厚厚的雪,像胖廚師頂著的白帽,帽子下面橘紅色的沙棘果,給整個曠野描了一道唇線。經歷過一年的風吹雨打,果子緊緊攥在枝干上,把自己的一生交給對方。這些果實成為野兔和呱呱雞最好的糧食。因此,驅車走在平坦的原野上,你會很輕易地發(fā)現(xiàn),不時有驚慌的野兔箭一樣把自己從刺叢里射出,而后落入遠處的另一叢植物中。或發(fā)現(xiàn)一群呱呱雞從覓食的深雪里探出頭來,在你離它四五米時,才魚貫而出,擺動頻率極快的短腿,迅速逃離你的視線,沉穩(wěn)嫻熟,像在游戲。
這是一種司空見慣的場景,博爾塔拉廣袤的原野,成為野生動物生活的勝地。冬季深厚的積雪,將干草深埋其中,一些體型較小的動物黃羊、鵝喉羚等都會從阿拉套山上走下來,小心翼翼靠近人類,尋找食物。起初,只在冰雪較淺的郊外,感受到了人類的無害,膽子漸大,慢慢靠近道路兩邊的綠化帶。在通往阿拉山口口岸的博——阿公路兩邊,稍加留意就能發(fā)現(xiàn),有大量的鵝喉羚在低頭吃草,那些草是林業(yè)部門特意采購的干苜蓿,有專門的飼養(yǎng)人員定時投放,幫助這些野生動物安全越冬。這些動物第一次距離人類這么近,二三十米之外,就可以旁若無人地徑自覓食。以往艱難的日子,變得舒心而安定起來。
這個時候,喧鬧了整個夏季的賽里木湖,也徹底沉靜下來。昔日湖濱的碧綠蒼翠和姹紫嫣紅早已隱匿在白雪之下,氈房、炊煙和牧人的琴聲被駱駝馱向了遙遠的冬草場,在湖中穿梭繁忙的游艇和絡繹不絕的游客也都淡出了這個季節(jié),這使得賽里木湖一下子有了離索寡居的況味。就像人生度過了青壯年,不再有透支生命的壓力,不再有激烈沖突的矛盾,冬天的草原讓一切榮華富貴都成為過眼云煙,沒有了欲望,才變得從容。賽里木湖會慢慢結冰,先是從湖的東岸開始,再一點點往西延伸,冬至過后,冰完全鎖住了湖面,昔日碧波蕩漾的湖水,終于凝固了心中的波瀾,變成了一面藍色的鏡子,或許只有這458平方公里的大鏡子,才能照出賽里木草原的曠古和遼遠。
我觀看過在賽里木湖的冬捕,水產養(yǎng)殖站的員工們,用尖利的冰鎬間隔五六米鑿一個半米見方的窟窿,用竹竿把網(wǎng)順著一個個窟窿串起來,張網(wǎng)以待。那些憋屈許久的魚,終于找到了透氣的窗口,歡呼雀躍、奔走相告,卻未料已陷入生命的騙局之中。看著冰面上活蹦亂跳的高白鮭,我總會涌出些許幫兇的愧疚。
博爾塔拉的冬季,像是被許多音符聯(lián)袂起來的合弦,需要用心去細細品味的。此時最好的去處是坐進溫暖的氈房里,桌前排列開醇香的馬奶酒,身后是一柄悠揚的馬頭琴,一條潔白的哈達,一曲蒙古長調,便是草原最高亢的和聲。有奶酒的滋養(yǎng),有哈達的佑護,這個冬天的醉意,就有了幾分粗獷和雄渾。任何人都可以從蒙古包里踉蹌而出,草原足夠大,可以承載你腳步所有想去的方向;天空足夠高,可以裝下你心中所有想唱出的情愁。
對于博樂人而言,生活是絕不可以缺少美酒的,就像居住在牧區(qū)的牧民絕不可以缺少奶茶一樣。以酒會友、以酒交心、以酒迎客、以酒送賓。在博樂人的心目中,舉杯就像握手一樣自然而真誠,喝酒就像解渴一樣痛快而酣暢。很難想象,沒有酒,人與人如何交往?不舉杯,心與心豈能溝通?
在博樂,飲酒只是歡樂的序幕,三巡之后的載歌載舞,才是歡樂的開始。這些來自五湖四海的人們,把不同的風俗倒進一口鍋里,熬出了酒歌草原的味道和認同。無論哪個民族,只要有酒,就必然會有歌,必然會有隨著歌聲伴舞的人,快樂變成了一種可聽可視的形體語言,讓粗獷和豪邁回蕩在小小的空間里。在酒和歌的召喚下,人的戒備消除了,以往的隔閡溶解了,陌生的情感增溫了,一曲終罷,舉杯過頭,便已是尊崇之極。
其實用“飲”來形容博樂人喝酒,是有些詞不達意的,與生俱來的秉性使得他們舉杯必空其樽,無論腔腹能否一次性容納那么多的灼烈,都得面對斟滿了的金碗、銀碗、牛角杯。所以,第一次到博樂的朋友,三杯酒的儀式剛剛開始,大多都被恫嚇得半醉了。沒有足夠的酒量,是撐不起草原生活的尊嚴的。奇怪的是,自稱酒量不行的人,只要不停地唱歌跳舞,就不會醉倒,就像落水的人,只要不停地劃動腿腳,就不會沉溺一樣。敬酒獻歌,成為外地人對博樂,津津樂道的風景。
如果認真考究的話,對酒當歌是有歷史淵源的,早在兩千多年前,曹公北征烏桓,勝利班師,途經碣石山登高望海時,就發(fā)出過“對酒當歌,人生幾何”“何以解憂,唯有杜康”的慨嘆。而博樂人只是將詩文里的情緒,結合自身的地域,進行了貼切的表達。這些悠揚的歌聲和嘹亮的嗓音,被廣袤的博爾塔拉草原所滋養(yǎng),每個人胸腔里,都住著一個干凈的草原,博大的氣度和空曠的意境,讓私心雜念無處藏身。
歌聲在博樂人的酒桌上就像連綿不絕的山脈,你不知道如何會有這么多舒緩而悠揚的蒙古長調,詼諧而機智的哈薩克小曲,你的耳音一新再新。尤其是尊貴的客人,把酒歌畢,再將一條潔白的哈達恭謹?shù)鼐传I在你胸前,再不勝酒力的推辭,也難以啟齒,就像大海無法拒絕潮汐的洶涌那般,你已無法拒絕捧在面前的這滿滿一碗祝福,唯一能做的便是,接過,且一飲而盡。
如果恰好在度假村的蒙古氈房里宴賓的話,那更得歌聲繚繞了。大家席“地”而坐,所謂的“地”其實是鋪了厚氈的木板,就像在草地上那樣,縱酒放歌。醉了不離臺桌,倒下可睡;醒來舉杯再戰(zhàn),此消我漲。歡樂和歌聲擁擠在氈房里,可以通宵達旦;豪邁與真誠書寫在眉宇間,當然樂此不疲。
沒有見過比博樂人在酒桌子上更輕松的了,這種輕松當然來自他們對生活的豁達與熱愛。只要去發(fā)現(xiàn),其實生活中有許多事情,是值得我們開心的。比如讀到了一篇好文章;比如你的感冒治愈了;比如孩子期末考出了好成績;甚至臨睡前想想,又過了充實的一天,這些都是開心的理由。生命的歷程,不可能總是大起大落,要學會享受每一件細微的收獲。生活從不缺少陽光,缺少的是走出室外。從這個意義上說,生活在博樂,的確是一件幸事。
其實,生活的快樂與幸福遠不是用經濟價值和物質尺度來衡量的,平凡的世界,給了我們平靜的生活,發(fā)現(xiàn)美好遠比等待奇跡,要充實得多。
快樂一杯酒,幸福一首歌。
???此時,我走在博樂大街上,走在陽春四月的清明里,就像走在一條懷舊的錄像帶上,原本很多散漫漂浮的情緒,漸次歸寂于一條思路之上。這讓我很快就感覺到了一種叫作溫暖的物質,通過目光所波及區(qū)域的光合作用,在身體里慢慢升騰。這或許就是所謂的故鄉(xiāng)帶給我的精神依戀吧。它約定了我們內心的走向。如果一個思念是一束光的話,那么故鄉(xiāng)應該呈放射狀的,多少游子,從四面八方投過來能量,作用于同一個家園。
已經有很多年沒有步行一條街道了,大多的時間,來去匆匆,身邊的事物都是一晃而過,快的節(jié)奏,讓我們忽略掉了許多寶貴的細節(jié)。
觀察的想法一旦形成,我的步履便有了一種閱讀的分量。一些沉淀在歲月深處的畫面,被記憶打撈出來,沖刷掉泥沙,竟然熠熠生輝。對號入座的故事,把很多情節(jié)散落在這座我生活了三十年的城市,散落在每一條路的枝干上。開始想它們的時候,我覺得,那些凋敝已久的往事,抖落掉灰塵,排列有序地站在路邊,桃花一樣地,開了。
腳下是筆直的北京路,也是初始工作時,上下班每天必經的一條道。我甚至閉上眼睛,都可以挨個叫出從宿舍到單位這兩公里間街道兩側所有店鋪的名字。有著古典八角樓建筑風格的益文齋工藝美術店、門口擺滿了自行車的興鵬五金商行、櫥窗掛著巨幅婚紗照的海燕照相館、門兩邊外墻上掛滿了色彩鮮艷服裝的海潮服飾、躺在長椅上在陽光下打盹的方圓印章店店主……這些店鋪的門楣上,都端端正正地舉著一幅牌匾,我每天騎車路過,都要側頭看他們。起初是辨認,時間久了變成了端詳,到后來僅用余光就可以飛落匾上,那簡直已經是用心撫摸了。我時常可以感受到與一幅幅牌匾的對視和交流,它們比我更早地佇立在路口,等待著四目匯合。有時我也會走進店里,隨意欣賞擺放在柜臺里琳瑯滿目的商品,以表達對牌匾的敬意,這是我和牌匾之間的秘密。當然,去得最多的是“一心書屋”和“藍天花卉”了。書是我常常要閱讀的必需品,稍有閑錢便跨進書店,隨性選購。即使囊中羞澀,也并不妨礙在書架前捧書閱讀。而花店,則是那里彌散的芬芳味道和疊花掩映中俯身插花的芬芳姑娘。到現(xiàn)在也不知曉她的名字。但這并不妨礙我把她和花仙子毗連在一起,成為情感懵懂時夢境的主角。時常摒棄惶恐,躑躅良久,才裝作植物愛好者,踱進門檻,尋找一些有關花的科普知識。當終于鼓足勇氣,在某個該買玫瑰花的節(jié)日里,準備走進花店,挑選一支最大的送給她時,店老板才告訴我,她表妹回內地定親去了。
時間久了,這些店鋪便和我的生活有了聯(lián)絡,就像一條條輸血管扎進了我的身體里,它們有了溫度,是從我的血脈里分流出去的一些熱量,附著在了街道和這些店鋪的身上。每當見到一些早已熟知的牌匾被換下來,我都會心生悲哀,總有親朋罹難的酸楚,它們以自己獨有的生命方式,告別了我和這座城市。
我還認識街道兩旁筆直的天山楊和茂盛的白蠟木。很多次,我蹣跚出喜來登飯莊門口,只需往前跨七步,就可以依靠到一株10年樹齡的天山楊上,它當時筆直而高聳,完全可以支撐住一個醉意深重嘔吐不止130斤重的酒鬼的。我還曾于某夜,依偎一株白蠟樹身旁小解,醉醺中連小樹一起扎進了腰帶,還埋怨有人拽著自己,不讓回到酒桌。幾經拉扯,傷及樹皮深處。這株行將枯萎的幼苗,終于熬過了歲月,把自己艱難長大,還帶著星夜被腰帶劃傷的印痕,慢慢搞過了我的頭頂。每行至此,都要駐足仰望,內心啞然。這些被我熟知的故事和樹的年輪一起被季節(jié)一圈一圈收藏了,我知道,其中的一圈,就記錄著我的秘密。
每一盞路燈和昏黑下發(fā)出的光線,是我熟悉的,它們橘紅而柔媚。闌珊之夜,騎車從燈下經過,影子會被第一盞燈推在前面,越拉越長,再被第二盞燈慢慢壓縮,行至燈下,已被壓成一張餅,再猛然彈開,然后又被第三盞燈重新壓縮。我就在伸縮之間,走完全程。現(xiàn)在想來,這種影子下的游戲,竟似模仿現(xiàn)實中的人生。
穿過友誼路的紅綠燈,就聽見了德德瑪悠揚的草原牧歌,這是從八音齋發(fā)出的旋律,店主悠閑地靠坐在門口的沙發(fā)上,雙眼微瞇半似欣賞音樂,半似關注行人。陽光斜照下來,讓他橫貫右側半邊臉原本暗紅的傷疤,顯得鮮艷了許多。他是我初中同學的姐夫,生意一直做得挺好,在博爾塔拉開了六家音像連鎖店。兩年前花十幾萬買了一輛新車。盛夏傍晚,心血來潮,非要驅車50多里,到五臺去吃一碗雜燴湯,把駕駛新車的歡暢心情,抒發(fā)成了對交通法規(guī)的漠視,結果,翻入邊溝,新車報廢,妻子斃命,自己也摔得支離破碎,昏迷十余天,終于從鬼門關折回。住了大半年醫(yī)院,以五家連鎖店的轉讓費用,換回了臉上這條不規(guī)則的標志。怕引起傷感,我想扭頭躲過他的視線,卻見他猛然彈起,伸過右手:兄弟,好久沒見了,還在公安局吧!單憑聲音,洪亮中透著熱情,根本感覺不到是從大禍中游離出來的。你咋樣?還好著吧馬哥。我有意回避自己已經轉變的身份。我想通了,人一輩子就那么回事,只剩這一個店了,生活是沒任何問題,我現(xiàn)在真正覺得把每一天活開心,才是最重要的。他笑的時候,右邊面孔的表情是被傷疤分割開來的,這使得他的表達不能上下同步,有了一種參差不齊的雜亂感。老馬,這盒帶子多少錢?我聽見從店鋪子里傳出一個女人尖銳的聲音。老馬沖著我擠了擠眉毛,現(xiàn)在又有人管了,你先忙著。
往前十余步,另一只大喇叭里傳出嘶啞吶喊:好消息!好消息!清倉大血買!每條褲子29元,只需29元,你就能穿出白領品質,貴族氣勢!嘶啞具有鏟車的功效,很快就把德德瑪覆蓋了。
再往前幾十米是買買提抓飯館,門前支一口大海鍋,油晾涼的米粒、金燦燦的黃蘿卜、鮮嫩的羔羊肉,加上幽默的吆喝:哎嗨!剛出鍋的新抓飯,最有力量的黃蘿卜配上沒有結婚的羊羔子,男人吃上一碗,一個晚上不睡覺,女人吃上一碗,一個晚上不讓男人睡覺,兩個人都吃上一碗,一個晚上不讓鄰居睡覺了哎!來來來!大多數(shù)人都會哈哈大笑,即使腳步走了過去,心卻被吆喝抓回了店里。
北京路上有一座橋,叫北京橋,橋東側有六七家擦皮鞋的小攤,老劉一直堅守在這里,無論春夏秋冬。十幾年前,我就尋著他的攤位。位置每天變動,大家輪莊排序,老劉時而龍頭,時而末尾。人從攤位走過,所有的攤主都盯著你的鞋,嘴里急切地喊著:老板!擦鞋!老劉不,沒活時,他叼著一只細細的煙嘴,沖著你的目光微笑,見你望他了,才冒出一句:老板,打個亮撒!既不迫切,又不輕待,濃濃的川味。一只小靠椅,一個小木箱,擺放成了主顧的服務態(tài)勢。他就坐在對面的木箱板上。椅子與他的雙腳的位置,剛好構成了很好的視角,能很輕易看見老劉腳上兩只擦得锃亮的皮鞋,盡管多有廣告的意味,卻插播得非常自然。每次都是,仿佛十幾年從沒落過灰塵。低頭勞作時,能看見他灰白的頭發(fā),我說,劉總,焗一下么。他呵呵笑兩聲,并未停止手里的活計,都六十多歲的人了,焗啥子喲。他的頭隨著身子晃動,我的視線被攪得一片灰白。若是夏天,脫掉鞋子,老劉會從箱子里拿出一個木制的腳踏,上面有許多突出的疙瘩,來回滾動,按摩足穴。冬天他會掏出一只厚厚的手工縫制的棉腳套,讓腳暖暖地蜷縮在里面,右側有一只燒得通紅的小鐵爐,他不時地把手湊上去,把鞋油和自己的手都烘烤一下。給鞋面拋光時,他把鞋子湊近嘴邊,猛哈幾口熱氣。溫度通過白色哈氣傳遞到我的鞋面上,也傳遞到了我的感動里。我不知道這道工序是不是有助于提升擦鞋的質量,但他對鞋的重視,至少提升了我與服務者之間情感的親近。
我站在北京橋頭,沒有見到一個鞋攤,這么好的天氣,這么好的時間,我覺得是有什么事情發(fā)生了,改變了這些人業(yè)已為繼的生活軌跡。剛轉過身準備離開,身后傳來濃濃川音:老板,打個亮。老劉背著箱子,從一間小門面房出來。四處回顧,小心放下箱子。我看了半天像是你,好久沒來了。老劉不知我姓什么,他也從來不問,他記住了每個不同的面孔,那是他記憶里的姓。老劉說,這里干不成了,新來了領導,要打造北京橋這條城中河的景觀,他們都被清理了。他暫時寄居在這個小門面房,下月小門面房也要拆掉了,他也不知道去哪里。在這兒蹲了十幾年了,有感情了。我聽出了老劉嗓音里的傷感,他俯身擦鞋時,頭還是懷舊式地晃著,一片雪白了。
對這條道路的熟知,讓我一直以為,自己才是路的主人,可以隨性改變自己的速度和方向,可以從任何一個角度來丈量馬路。一雙腳來來回回的,把多少鞋印疊加在了路面上。諳熟每一截路段的坑坑洼洼,掌握每一處拐彎、每一個岔口。其實,路一直在測量著我們,測量歲月的深度和生命的高度。我們每天一次來回,都被路做了刻度,但我們不知道,路默默記錄下了我們人生的過程,但不說。直到有一天,一個落魄的男人,重回故鄉(xiāng),走在兒時的路上,正低頭回顧自己的人生,卻看見一輛失控的小車沖向道外,撞在路沿石上,又被彈回,一些碎片,一輛破損的車,一排稍加猶豫繞行而過的車流,路還是過去的路,車已不是原來的車了。男人是否讀懂了,路不去判定,只擺出不變的姿態(tài),包容所有的足跡,承載不同的車輪。
站在千里之外,我時常撫摸中國版圖西北端的這座小城,感恩上蒼,讓她成為我的故鄉(xiāng)。那里有許多同我一樣熱愛這片土地的人們,他們沒有離開,他們讓自己的臉龐長成了土地的樣子,讓自己的胃長出了玉米的樣子,讓自己的眼神長出了奶酒的樣子,讓自己的生命,長成了祖國想要的樣子。我不全認識他們,但我知道,他們都是家鄉(xiāng)那塊土地上,最樸素的表情。因為愛,而生動;因為情,而生輝。
責任編輯?丁莉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