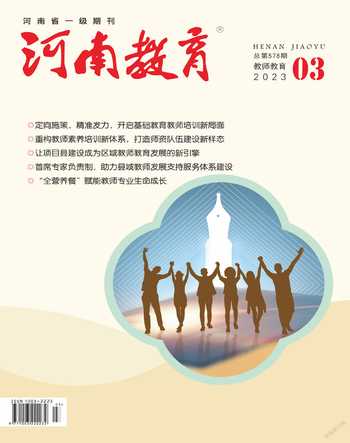教師專業發展的意蘊演變和價值取向
李一鳴 王獻玲
中共中央、國務院在《關于全面深化新時代教師隊伍建設改革的意見》中指出,“把教師工作置于教育事業發展的重點支持戰略領域”。“職業發展”一詞具有“時間性”和“方向性”,即“職業生涯發展”。教師專業發展區別于其他職業生涯發展的核心,是基于教師及社會對“生涯”的理解、態度及相關行動。因此,了解生涯及生涯發展的內涵演進,并以此觀照教師專業發展的意蘊演變和價值取向,對教師的專業化成長具有重要意義。
生涯及生涯發展的內涵演進
隨著時代發展和研究的“精湛化”,“生涯”的含義歷經演變,意蘊也逐漸豐富。職業生涯并非職業行為本身,一方面,生涯可指代職務變動和非職務變動,強調流動和變化;另一方面,生涯亦可被解釋為“職業”,即勞動者在穩定從事的、有報酬的工作崗位上的特定就業狀態,如職業教練,突出了專業性。我們也常把職業(專業)作為個人身份的表達,通過生涯發展,勞動者獲得了對自我身份和價值的確認。
生涯在中國人的概念中,與“生計”“職業”“命運”等詞有相通之處。中國人的集體生涯意識具有“以考試為晉身之階、性別刻板印象、服從權威與循例重俗、命定與自定”等特征。在西方,從Parsons時代開始,career,vocation,occupation等經常被混用,生涯指個人工作經歷的演變順序。
早期的研究受到后續研究的批判,對生涯概念的線性的、垂直的解釋受到挑戰。Super將生涯(career)定義為“貫穿個人在職前、職中和職后生活中所占據的主要職位的順序;包括與工作相關的角色,如學生、雇員和退休者,以及副業、家庭和民事角色”。自此,對生涯的研究進入一個新的階段。Tyler對“個體在自我發展中扮演著重要角色”而非“個體差異”的心理學關注,也深刻影響了學界對“生涯”的概念認知。人們開始意識到生涯與個體生活的其他方面息息相關,性別、社會階層、家庭背景、文化特征等都深刻影響著對職業的界定。生涯不再被認為是既定的,而是由個體建構出來的。而生涯是否一定包含有償的成分也受到一些學者的質疑。Schaeffer(2013)強調,有償工作和職業生涯之間的聯系是資本主義崛起的人為產物,談論無償工作、護理工作,是對資本主義霸權中的社會價值觀的一個重大挑戰。易變生涯、無邊界生涯等概念提出,個體置于生涯、組織和組織環境的中心(M. B. Arthur & Rousseau,1996),生涯并非由外在機構而是由個體所創造的(Littleton,M. B. Arthur & Rousseau,2000)。特別是,在21世紀無邊界生涯中,“身體和心理流動”極為重要(Sullivan and M. B. Arthur,2006)。生涯的概念向著跨文化的、更廣泛的、更具包容性的方向演進,其方向性、終生性、空間性、易變性、流動性、獨特性、現象性、主動性等特征越發凸顯。
生涯發展這一概念最早被Ginzberg, Ginsburg, Axelrad and Herma(1951)提出,他們初期假設其過程在成年早期完成,后來又被修正為“終身的決策過程”,生涯的終生性得到承認。Sears認為“生涯發展是心理的、社會的、教育的、身體的、經濟的和機會因素推動的總和,而這些因素結合在一起也成為了個人的職業生涯”。關于討論個人的其他角色身份、關系和文化等對生涯發展的影響研究更為廣泛,生涯發展逐漸具有了生涯規劃、生涯設計、生涯建設的意蘊。個體需要在復雜變化的環境中,依據自己的經歷,積極主動地擬定策略并向周圍即刻變化的環境做出反應(選擇、決策、適應等)。
教師專業發展的意蘊演變
第11屆國際勞工統計專家會議通過的《國際標準職業分類》將各級各類教師列入“專家、技術人員和有關工作者”類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同年發布了《關于教師地位的建議》報告,提出應該把教師工作視為專門的職業,教師需持續不斷地經過嚴格系統的學習和訓練,獲得并維持專業知識和技能。在標準和報告中,教師的專業發展首要是知識和技能的發展。
目前對教師發展、教師職業(生涯)發展、教師專業發展等概念的理解存在較大差異,概念界定也較為模糊,因此常被互用。基于以上對生涯和生涯發展的理解,筆者將教師生涯發展區別于其他職業生涯發展的核心要素定位于教師的專業發展。
已有研究從不同維度對教師的專業發展進行了解讀。如從政治角度看,專業發展體現在與教師專業發展相關的制度和體系的完善上。從角色定位的角度看,專業發展是從新手教師、熟練新手教師、勝任型教師、業務精干型教師到專家型教師的角色轉變。從教學專長發展過程的角度看,專業發展是接受學習、能力建立、成長與受挫、穩定與停滯、低落與退出的過程。從專業發展的相關內容來看,專業發展是知識技能體系的完善與更新、實踐能力的拓展、思維與道德水平的提升等。專業發展的方式則以外部引領、規約為主導。
生涯定義的更新和生涯發展的新要求對這些線性的專業發展模式提出了挑戰。知識的產生和獲得機制發生變革,知識的功能和價值不斷被審視,其不再是主體對客觀現實進行的機械反映,而是來源于主客體間的相互作用。中國教育學會名譽會長顧明遠指出,教師職業以生命為對象,以教書育人為主要任務,以自己的知識、智慧、人格魅力在和學生共同活動中去影響學生,具有復雜腦力勞動的特點,以及極大的創造性和靈活性、鮮明的示范性、長期性和長效性等。教師角色也從古代的“巫師”角色、控制者角色、現代的灌輸者角色趨向知識層面的引導設計者、組織管理層面的組織協作整合者、主體發展層面的參與研究終身學習者。教師專業發展以教師為中心,以內驅力為主導,在復雜的動態環境中通過終身學習和規劃,實現教師專業技能之知情意行的提升及與外部和自我的和諧。
教師專業發展的價值取向
從19世紀50~70年代的差異性、發展性視角到19世紀80年代的認知學習、社會學習和社會認知視角,再到19世紀90年代的建構主義視角的演進,推動了生涯發展的探究從以“職業”為中心(注重特質差異以匹配職業)到以“人”為中心的關注轉移,從靜態的時間性點狀事件到動態發展過程的關注轉移,從“個體差異”到“個體發展”的關注轉移。基于此,以人為本成為教師專業發展的價值取向,貫穿教師專業發展的內容系統和過程系統。
從工具客體走向真實自我。教師專業發展的終極目的是實現人與外部和自我的和諧。教師并非知識傳遞、技能傳授的手段,也非技術控制的對象,一刀切、自上而下的外在引領和規約為主的教師專業發展線性方式無疑將教師定位于工具客體。教師專業發展是以教師為中心的建構,發展的方式、歷程因真實自我的主動追求獨一無二,內在自覺和自我意識的喚醒、情感認同的達成亦是和諧實現的表征。
關注動態交互,回歸生命歷程。教師專業發展并非處在物理時間的固定序列中,而需要考慮個體生命階段、家庭生命周期、組織動態、自然社會環境的演化與專業發展的交互影響,考慮教師專業發展的動態本質、教師隊伍結構的調整變化、早期教師的可能性流動、女性教師的倫理關懷等。
終身學習,面向未來。成長為專家型教師不是教師專業發展的終極目標。對教師專業發展的考量應放在對專家型教師典型的素質結構和行為特征的追求上,放在特定的、復雜的社會和文化背景下對職業問題及相關問題解決的成效上。終身學習是以自我為主導的學習,不僅僅意味著自我不斷地獲取知識與技能,更意味著將其轉化為有意義的信息再納入自我的先驗知識,從而使自我得到發展。
教師職業生涯的高質量發展是教育事業高質量發展的重要驅動。從生涯發展的視角反思教師專業發展的意蘊演變和價值取向,承認教師在專業發展中的主體地位,轉變刻意追求外在地位提升的態度,增強教師的職業幸福感,破解職業倦怠的難題,才能助力實現教師專業真正的內涵式發展。
(本文系河南省教育科學規劃2023年度重點課題“基于鄉村振興的河南省農村脫貧人口職業發展教育機制研究”的項目成果。課題編號:2023JKZD01)
(責編 韓玉兵 侯心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