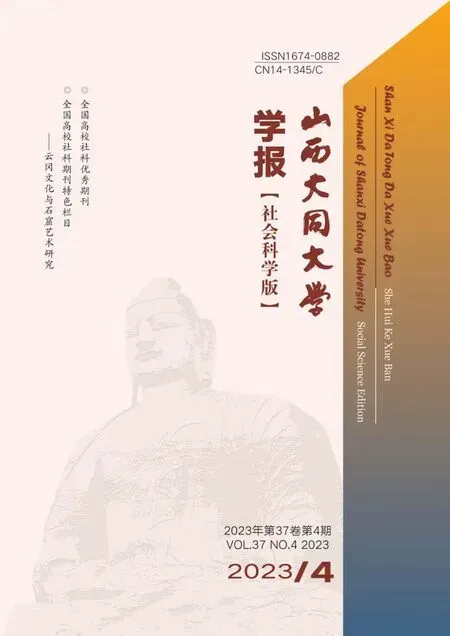由出口商品的變遷看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興衰
許寧寧
(山西大同大學云岡學學院,山西 大同 037009)
海上絲綢之路是古代中國與世界其它地區進行經濟文化交往的重要通道。自西漢開辟以來,絲綢便是由此遠銷海外最主要的中國商品;唐代以后,瓷器又經此運銷海外,并成為中國第二大出口商品。自此近千年間,中國的絲綢和瓷器便一直經由這一通道源源不斷地輸往海外。正是由于以絲綢和瓷器為“物”的代表的古代中國經濟文化高居世界之翹楚,海上絲綢之路才能跨越漫長的歷史持久不衰。
16 世紀,隨著新航路的開辟,葡萄牙人、西班牙人以及稍后的荷蘭人、英國人競相東來,又為古老的海上絲綢之路注入了新的活力。尤其是1567 年“隆慶開關”準販東西二洋以后,長期抑制下的中國民間商業活力噴涌而出。一條條新開辟的航線將中國與世界聯系在了一起。精巧絕倫的中國商品受到了世界各國的廣泛歡迎,而附著于這些商品之上的中國文化也由此傳播到世界各地。伴隨著人與物的頻繁往來,西學東來,東學西漸,承載著東西方經濟文化交往的海上絲綢之路達到了空前鼎盛。然而也正是從這個全球范圍的“大航海時代”開始,西方文明加速發展的引擎已然啟動,而古老的中國文明則越發沉寂。海上絲綢之路由盛轉衰的節點已經悄然來臨。
一、絲織品出口:由盛轉衰的征兆
海絲之路上的第一個變化發生在最重要的絲綢出口領域。“絲綢”一詞原本是由“絲”與“綢”合構而成的復合詞。“絲”指的是制綢的原料生絲,“綢”指的是由生絲制成的絲織品。自古以來的絲綢出口,既包括絲織品這種制成品的出口,也包含生絲這種中間產品的出口。中國的絲織品以其輕柔絢麗著稱于世,一直是異國商人們來華尋求的主要商品;生絲盡管也以其潔白優質聞名遐邇,但長期以來在出口貿易中僅僅是作為絲織品交易的補充。然而當16世紀“絲銀”貿易興起時,“西洋番舶者,市我湖絲諸物,走諸國貿易”,[1](P5438)生絲開始變成海絲之路上的主角,絲織品出口反而退居到次要位置。此后直到海上絲綢之路退出歷史舞臺,生絲都是中國出口海外的大宗商品,完全取代了絲織品在出口貿易中的地位。
發生在絲綢出口領域的這種結構性變化與16世紀全球范圍的社會經濟變遷密切相關。中國生絲出口的興盛,不僅得益于美洲、日本白銀大量開采所帶來的國際購買力激增,更源自這一時期國外對中國生絲的旺盛需求。而這種生絲需求的背后,則是在中國絲織技藝長期外傳影響下國外絲織技術的顯著進步與絲織業的日益成熟。其中,尤以日本和歐洲的絲織業表現得最為典型。
日本絲織業的發展與中日間文化交流緊密結合在一起。據傳中國的蠶絲技藝早在秦代便開始傳入日本。到魏晉時期,自稱秦始皇后裔的弓月君率其部眾將中國的養蠶和機織技術帶到日本,仁德天皇“以百二十七縣秦民,分置諸郡,即使養蠶織絹貢之”,[2](P435)日本絲綢業自此開始發端。5 世紀中葉,雄略天皇又兩次派使者到江南招徠絲織工匠傳授技藝,并下令“宜桑國縣殖桑”,[3](P233)促進了日本絲綢業的進步。到了隋唐時代,隨同遣隋使、遣唐使前來的大批留學生和留學僧在學習中國文物典章的同時,也學習中國的絲織技藝并購買中國精美的絲織品回國仿制,極大帶動了日本絲織業的發展。此后歷經宋、元、明三代,日本絲織業在不斷地汲取中國絲綢技藝的基礎上漸趨成熟,在16世紀后半葉出現了劃時代的勃興。傳統的京都西陣和作為學習中國先進絲織技藝窗口的堺市成為日本絲織業的兩大中心,其“所制金襕、緞子、唐織物、紅梅、綺羅,先代未聞也”。[4](P295)進入17 世紀后,日本的絲織生產由京都西陣向周邊擴展,博多、丹后、桐生、足利、仙臺等地亦紛紛崛起為新的絲織中心。與此同時,日本絲織業開始更加注重本土技藝的發明和推廣,先進的絲織“高機”得到普及,代表日本傳統絲織工具最高水準的“織錦機”也發明了出來。這一切都使日本的絲織技術與生產規模達到了相當高的水準。
與日本相比,歐洲絲織業更顯示出一種獨立發展的特性。由于中國的絲織品并不適合地中海溫暖濕潤的氣候條件,早期羅馬人在購得中國絲綢后往往將其拆成絲線,然后重新織成適合當地需要的輕薄織物,即所謂“又常利得中國絲,解以為胡綾”。[5](P861)當時的絲綢在西方價比黃金,羅馬人為奪取與中國進行絲綢貿易的商道曾數次發動“絲綢戰爭”。直到公元6世紀中葉,在被稱為“絲綢皇帝”的查士丁尼將中國的蠶種和絲織技藝引入君士坦丁堡之后,種桑、養蠶和絲織技術才在小亞和希臘地區傳播開來。7 世紀阿拉伯人征服小亞地區之后,將蠶桑生產推廣到阿拉伯地區,又由摩爾人帶到了西班牙。到10世紀,西班牙的安德盧西亞已發展成為歐洲的絲織中心。12世紀中葉,西西里國王羅杰二世從希臘半島虜回大批絲織工匠,極大刺激了西西里絲織業的發展。不久之后,絲織業沿著意大利半島一路向北擴張。到14至15世紀,意大利已發展成為歐洲新的絲織中心。此后,絲綢生產進一步越過阿爾卑斯山在法國南部安家。在法國王室的大力獎掖下,到17 世紀初法國的絲織業已能與意大利并駕齊驅。17 世紀下半葉,隨著《南特敕令》的廢除,包括許多絲織技工在內的胡格教徒移居英國、德國、瑞士等地,又大大促進了這些地區絲織業的發展。到18 世紀中葉,絲織工廠已在西北歐遍地開花。法國的里昂,英國的倫敦,瑞士的蘇黎世,德國的克雷菲爾德與荷蘭的哈勒姆等地都已成為了歐洲絲織生產的重鎮。[6](P95-96)
隨著日本與歐洲絲織業的日趨成熟,其生產的絲織品質量已能不遜于遠渡重洋而來的中國織物,而其花紋樣式則更適應本地居民的需求。16 世紀,胡宗憲在《籌海圖編》中對日本的絲織品使用情況做過這樣的記載:“蓋彼國自有成式花樣,朝會宴享必自織而后用之,中國絹纻但充里衣而已。”[7](P414)中國絲織品此時在日本已被“自有成式花樣”的本土織物所取代。雖然仍能出口日本,然而也不過是“但充里衣而已”。及至18世紀中葉,隨著日本絲織業的進一步成熟,江戶幕府更制定海舶條例明告華商:“藥材自余物件,惟下品者多帶前來,匹頭等項地素尺寸及闊狹等止不宜者,是之載帶,其于本處乃不中用。……無用之物著令載回。”[8]中國商人運來的絲織品已被視為并不適合日本市場需要的“無用之物”。而在歐洲,為了保護本國絲織業的發展,各國也紛紛頒布法令禁止進口中國絲織品或對其課以重稅。由此,曾為各國商人趨之若鶩的中國絲織品逐漸喪失了國際市場,在國際貿易中的地位也隨著各國絲織業對原料的旺盛需求而被中國生絲所取代了。
生絲出口與絲織品出口雖然都為中國帶來了巨大的經濟利益,但其所蘊含的社會經濟意義卻截然不同。作為制成品出口的絲織品,其背后是中國先進的絲織技藝,是各國對中國絲綢文化的仰慕與追求;作為中間產品出口的生絲,其背后是各國絲織技術的長足進步,是各國絲織業蓬勃發展所帶來的對絲織原料的旺盛需求。運送絲織品的海上絲綢之路,承載的是先進的中國文化,是國際市場的主導;輸送生絲的海上絲綢之路,裝載的是各國經濟發展所需的原料,是國際市場的附庸。由絲織品出口向生絲出口的轉變無疑是一個征兆,預示著中國的經濟文化正在喪失其長期保持的優勢地位,海上絲綢之路在極盛的16世紀已然敲響了走向衰落的警鐘。
二、瓷器出口:盛衰易位的標志
發生在絲綢出口領域的這種結構性變化,只不過是更大范圍內中外經濟文化關系轉變的開始。不久之后,一個更明確的信號又在海上絲綢之路上另一主要商品——中國瓷器的出口貿易中昭顯出來了。與中國絲織品一樣,在瓷器的出口過程中,也伴隨著制瓷技藝的外傳和外國對中國瓷器制作技術的模仿。不過由于瓷器的制作工藝非常復雜,對原料與火候的要求異常嚴苛,因此外國對中國制瓷技藝的學習首先是從相對簡單的陶瓷技藝開始的。
以日本為例。早在唐代,隨遣唐使來中國學習各種手工藝能的日本工匠們便將中國的陶瓷技藝帶到了日本,一些遣唐使還從中國招募工匠到日本試制陶瓷。在留學的日本工匠和渡日的中國工匠共同努力下,日本模仿唐三彩的制法燒出了奈良三彩,使日本陶瓷技術躍升到一個較高的水平。到南宋嘉定年間(1208-1224 年),被尊為日本“陶祖”的藤田三郎又在福建潛心鉆研陶瓷技藝,歸國后成功燒制出被稱為“瀨戶天目”的黑釉陶瓷,大大推動了日本陶瓷業的進步。進入明代以后,隨著景德鎮青花瓷的大量輸入,已具相當陶瓷制作水準的日本工匠們開始真正學習中國的制瓷技術。正德年間(1506-1521年),五良大甫化名“吳祥瑞”在景德鎮刻苦鉆研多年,學會了燒制青花瓷的整套工藝,并將中國的瓷土和釉料帶回日本,在肥前的伊萬里燒制出日本的第一件青花瓷器。五良大甫由此日本人奉為“瓷圣”。“慶長·文祿之役”(1591-1598 年)時,豐臣秀吉又將千余名朝鮮匠人虜回日本。其中一位名叫李參平的制瓷工匠在肥前的有田發現了優質的瓷土礦并在此開窯,開始大規模燒制名為“有田燒”的純白瓷器。及至17 世紀中葉,喜三右衛門又從經常出入長崎的中國商人手中獲得了中國的赤繪調色法,并經反復試驗,用赤繪技術成功燒制出日本的第一件彩繪瓷器。隨后,柿右衛門、色鍋島、古七谷、七寶燒、京燒、清水燒、薩摩燒等獨具日本特色的彩繪瓷器紛紛面世。隨著制瓷業的日益興盛,日本的瓷器生產不但能夠實現自給,而且逐漸具備了出口海外的能力。明末清初厲行海禁之際,供銷海外的中國瓷器幾近絕跡。荷蘭東印度公司從1650年開始將日本的伊萬里瓷和有田燒運銷歐洲,很快盛行一時。此后,運銷歐洲的日本瓷器不斷增加,甚至動搖了中國瓷器在歐洲市場的地位。
相比于日本,中國的瓷器和制瓷技藝很晚才開始傳入歐洲。而在中國瓷器大量輸入之前,大多數西方人日常使用的都是粗糙而厚重的石制、陶制器皿。因此,當16 世紀初葡萄牙帆船首次將精巧的中國瓷器運抵歐洲時,整個歐洲為之傾倒。從國王到普通百姓都將其視為珍寶,以瓷器作為財富和身份的象征。中國瓷器由此成為了那個時代最具吸引力的進口商品。與此同時,歐洲人也開始試制瓷器。但由于無法獲悉中國制瓷的秘密,在很長時期內只能燒制出一些簡單的陶瓷。直到18 世紀初,一位名為殷弘緒的法國傳教士得到康熙皇帝的首肯,得以長駐景德鎮并自由出入當地的大小作坊。他由此深入了解到燒制瓷器的各項工序和技術,并將其寫成報告,與中國的瓷土樣本一道寄回歐洲,直接推動了歐洲制瓷業的誕生。1708 年1 月15 日,被譽為“歐洲瓷器之父”的德國人伯特格爾在實驗室里燒制出歐洲的第一件瓷器。憑借其制瓷技術,著名的邁森瓷器工廠很快建立起來,其生產的白瓷精美多樣,風靡全歐。此時的歐洲正值工業革命前夜,技術傳播與產業擴張的速度比以往任何一個時代都要迅猛。及至18 世紀中葉,歐洲的制瓷中心已從德國邁森擴展到法國。法國的摩利日被譽為“歐洲景德鎮”,其生產的白瓷與塞勒夫生產的軟質瓷小雕像共同引領了18 世紀歐洲的瓷器潮流。稍后不久,被稱為“英國陶瓷之父”的韋奇伍德創辦了他的第一家陶瓷工廠,西班牙、荷蘭、奧地利、意大利等國也相繼開設工廠生產瓷器。到18世紀下半葉,奧地利皇家維也納、意大利卡波迪蒙蒂又成為歐洲新的制瓷中心。
由此,隨著日本制瓷業的日益成熟,中國瓷器在17 世紀中后期逐漸淡出了日本市場;而在歐洲制瓷業的迅速成長中,到18 世紀下半葉中國瓷器又結束了出口歐洲的黃金時期。如果說發生在絲綢出口領域的結構性變化還只是一個不那么明顯的征兆的話,那么瓷器出口的衰落則是一個明確的標志。在工業革命中蒸蒸日上的歐洲自不待言,即便是對于同樣處于傳統社會中的日本,徐光啟在17 世紀初時尚能不無得意地宣稱“彼中百貨取資于我,最多者無若絲,次則磁,最急者無如藥,通國所用,展轉灌輸,即南北并通,不厭多也”,[1](P5442-5443)及至18 世紀中葉,也已被前述的“藥材自余物件,惟下品者多帶前來”所取代,中國經濟文化的領先優勢不復存在。
國際領先地位的喪失從根本上改變了海上絲綢之路的整體貿易格局。那些曾支撐海絲之路千年不衰的、作為古代中國經濟文化“物”的代表的傳統手工制品逐漸失去了昔日的光環,中間產品和原料產品開始成為海絲之路上的主角。由此撐持海上絲綢之路的,不再是先進的經濟文化與技術優勢,而是極易被移植和取代的原產地優勢與價格優勢。當以“優美精良”享譽世界的中國商品被“物美價廉”的中國商品所取代的時候,海上絲綢之路已在衰落的道路上漸行漸遠了。
三、生絲出口:先進落后的分野
導致海絲之路上中國生絲與絲織品出口地位逆轉的“絲銀”貿易在16世紀中葉以后很長一段時期內都是世界上最有利可圖的貿易之一。由于各主要絲織生產國的蠶絲生產水平無法滿足本國蓬勃發展的絲織業需要,從中國進口生絲就成為它們的必然選擇。然而與需要高超的絲織技藝才能織出精美織品的絲織業相比,蠶絲業的移植顯然更為便易。因此在進口中國生絲的同時,各國也分別走上了蠶絲本土化的道路。其中,尤以日本蠶絲業的成長影響最為深遠。
對于日本來說,“絲銀”貿易雖然滿足了絲織生產的需要,但也造成日本白銀的大量外流。尤其是在16 世紀后期到17 世紀早期,穿戴絲織品曾一度成為日本社會各階層的時尚,“以至現在已然形成從中國、馬尼拉販來的全部生絲亦不能滿足他們需求的現狀。”[9](P136)因此“若番舶不通,則無絲可織,每百斤值銀五十兩,取去者其價十倍。”[7](P414)巨大的利潤將各國商人紛紛吸引到中日“絲銀”貿易中來,僅葡萄牙商船在1599至1637年間就將5800萬兩白銀運出長崎。[10](P150)白銀的大量外流嚴重影響了日本經濟的正常運轉,甚至連作為國內貨幣流通的白銀也出現短缺。為了扭轉這一局面,德川幕府在頒布“貞享令”(1685 年)限制貿易規模的同時,更不遺余力地鼓勵農民植桑養蠶。地方各藩府和生絲批發商們也都以各種形式積極參與到發展本土蠶絲業的事業中來。在朝野的共同努力下,植桑養蠶事業迅速在日本各地推廣開來。及至“貞享令”頒布30 年后,日本的主要產絲藩國已增至16個;到了德川時代晚期,大部分農村都已實現了向“農耕為主、桑蠶為輔”的轉變。與此同時,日本的蠶絲技術也取得了長足進步。從德川時代中期起,不僅夏蠶飼育已在日本各地普及,秋蠶飼育也逐漸為農戶所采用,清涼育蠶、溫暖育蠶等養蠶技術日臻完備。[4](P313)在繅絲工序中,傳統的“胴取”法已為“手挽”法、乃至更為先進的“座繅”所取代,生產效率顯著提高。隨著日本蠶絲業的迅猛發展,1737 年以后來日貿易的中國商人已不能用生絲換購日本商品,必須支付相當數量的金銀;[11](P45)而到文化年間(1804—1817 年),日本的生絲產量已比慶長、元和年間(1596—1623 年)增加了八倍之多,[4](P310)徹底擺脫了對中國生絲的依賴。
相對于日本蠶絲業的快速成長,歐洲的生絲生產一直落后于絲織業的發展水平。盡管植桑養蠶已在西班牙、意大利、法國、奧地利等國的農村地區逐漸推行,但其生產的生絲絕大部分僅能自給,無法滿足歐洲蓬勃發展的絲織業需要。加之西屬美洲殖民地墨西哥絲織業的興起,更令歐洲市場上的生絲供應捉襟見肘。于是自16 世紀中葉起,歐洲商人開始利用從美洲開采的白銀大量購買中國生絲。通過經巴達維亞到歐洲與經馬尼拉到墨西哥的兩條航線,中國生絲連綿不絕地運往歐美,歐美白銀源源不斷地流入中國,這就是中國與歐美的“絲銀”貿易。這項貿易延續了三百多年。直至19 世紀中期,中國生絲仍牢牢主導著歐美生絲市場。
然而到19 世紀60 年代,這種一家獨大的局面亦開始被打破。19 世紀中葉,蠶微粒子病的爆發對歐洲蠶絲業造成毀滅性打擊,中國對歐生絲出口由此急劇擴大。然而中國蠶絲業未能把握住這一機遇,其出口質量反而隨著出口數量的劇增日漸下降。人們“或將劣繭和雜草混入,或以濕氣和灑水使生絲增重,或以普通絲、劣質絲混充優質絲……種種投機取巧、蒙混作弊的行為公然行之”,[12](P255-256)嚴重損害了中國生絲的國際聲譽。而與此同時,日本生絲則在“安政開國”(1858 年)后開始涌入國際市場,向中國生絲發起了挑戰。為避免重蹈中國生絲的覆轍,日本在主要的生絲出口港都設立了“生絲檢查所”,對生絲的出口質量嚴格把關,使日本生絲很快在歐洲站穩了腳跟。70 年代后,中日生絲較量的主戰場又從歐洲移至美國。這一時期,隨著歐美絲織業中動力織機的普及,對生絲質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質量低下的中國手工繅絲越來越無法滿足歐美絲織業的發展需要。而日本蠶絲業則通過大規模興建繅絲工廠和改良傳統手工繅絲提高生絲質量,獲得了歐美絲織業的青睞。由此,中日生絲在國際市場上的地位發生了逆轉:當19 世紀60 年代日本生絲在國際市場上嶄露頭角時,其出口量不過是中國生絲的七分之一;而到1882 年日本生絲便已奪取了中國生絲在美國的市場地位;1903 年日本生絲出口量首次超過中國,成為世界第一生絲出口大國;20世紀30年代日本生絲更囊括了國際生絲交易總量的四分之三,[4](P551)徹底取代中國成為了世界“絲業霸主”。
可以說,面對近代化浪潮,應對的快慢直接改變了中日兩國生絲出口的命運。而兩國生絲出口的盛衰,更是近代兩國先進與落后的縮影。眾所周知,生絲是近代日本最重要的出口商品之一,由其創造的外匯為日本近代化建設發揮了無可替代的作用。相比之下,中國生絲出口的沒落尤令人嘆息。如果說絲織品與瓷器出口的衰落是中國經濟文化喪失了世界領先優勢的一個標志的話,那么生絲出口的衰微則標示著中國經濟文化已日益落后于世界前進的步伐。從絲織品到生絲,當中國的絲綢逐漸淡出以“絲綢”命名的海絲之路的時候,海上絲綢之路也即將走向終結。
四、茶葉出口:最后的余暉
在海絲之路上,茶葉是最后一種廣為稱道的中國商品。自1610 年荷蘭商船第一次將中國茶葉運抵歐洲之后,飲茶之風在西方日益盛行,茶葉與咖啡、可可一道被稱為歐洲人最喜歡的三種進口飲料,又伴隨歐洲人的殖民活動傳播到美洲、澳洲和非洲。隨著西方人對飲茶的熱愛與日俱增,自康熙年間起,中國茶葉的出口量迅速增加;到嘉慶、道光年間,茶葉已取代生絲成為中國最大宗的出口商品。由于鴉片戰爭以前中國是世界上唯一出口茶葉的國家,茶葉出口又為中國及海上絲綢之路贏得了“茶葉之國”與“茶葉之路”的贊譽。經營茶葉貿易獲利巨豐,是當時歐洲各國東方貿易公司最重要的盈利手段之一。曾有法國商人說:“茶葉是驅使他們前往中國的主要動力,其他的商品只是為了點綴商品種類”,一位歷史學家甚至宣稱:“茶葉是上帝,在它面前其他東西都可以犧牲”。[13](P72)
茶葉貿易不僅為西方商人帶來巨額利潤,也使中國海上絲綢之路的輝煌得以延續。然而到這一時期,日益強大的西方資本主義已遠不滿足于經營茶葉貿易所獲得的利益。隨著工業化的進展,他們更渴求將茶葉的生產利潤也掌握到自己手中。為此,歐洲人不遺余力地嘗試將中國茶葉引種到他們在南亞和東南亞的殖民地內。
最早試種茶葉的是荷蘭人。早在1827至1833年間,荷蘭東印度公司就曾先后六次派人到中國學習種茶與制茶技藝,并帶回茶師、茶種和器具在爪哇試種茶葉。而真正大規模引種茶葉的是英國人。18世紀末,馬戛爾尼在率領使團訪華時就曾在信中透露:“如果有可能,我想弄幾株優質茶樹的樹苗。多虧廣州新任總督的好意——我與他一起穿越了中國最好的茶葉種植區——我得以觀察和提取優質樣品”。[17](P73)1834年,英國人在印度成立了植茶研究發展委員會,并授命雇員戈登到中國搜集大量武夷茶籽秘密運回加爾各答,并聘請到十幾位四川雅州茶師向印度人傳授種茶、收茶和制茶技藝,由此在印度建立了第一個茶葉生產基地。1838 年,英國東印度公司首次將印度茶葉輸入英國,中國茶葉一家獨大的局面由此被打破。此后,印度的茶葉生產迅猛擴張,到1869 年輸入英國的數量已突破1000 萬磅,約占當年英國茶葉消費總量的10%。1870 年后,英國人又在錫蘭(斯里蘭卡)建立了新的茶葉生產基地。此后數十年間,錫蘭的茶葉產量以驚人的速度增長。1880 年時,錫蘭還僅有茶園13 個,產茶1300 箱;而到1886 年,其茶園已擴張到約900個,占地72萬畝,年產茶葉2.88萬噸。[6](P95)
印度和錫蘭的茶園實行大規模機械化作業,許多茶園還建有鐵路,可以將茶葉直接運抵港口銷往海外,其效率是僅僅將其作為茶農副業的中國茶業無法比擬的。加之此前粗制濫造之風已使中國茶葉的國際聲譽嚴重受損,最終導致中國茶葉的對歐出口在印度茶和錫蘭茶的夾擊下敗下陣來。而在大洋彼岸的美國,曾經在“波士頓傾茶事件”中扮演過關鍵角色的中國茶葉同樣受到以近代工業武裝起來的日本茶的猛烈沖擊,一步步被排擠出美國市場。由此中國茶葉的出口量日漸萎縮,從其頂峰時(1886 年)的13.14 萬噸滑落到1902 至1917 年間的年均9.57 萬噸,再跌落為1918 至1940 年間的年均4.98 萬噸,直至1945 年落入谷底,其出口量僅為0.48 萬噸。[14](P160)短短五十年間,中國茶葉便從獨占國際市場,墜落到無足輕重的地位。
相比于絲織品、瓷器和生絲,中國茶葉的出口興起得最晚,也衰落得最快,表明了中國的前近代手工業在近代資本主義工業大生產面前已全無招架之力。生絲出口與茶葉出口相繼沒落之后,步履蹣跚的中國已無法再向世界提供任何有吸引力的商品。從19 世紀末20 世紀初開始,豆類、棉花、芝麻、植物油、豬鬃、羊毛之類的農產品原料成為了中國出口的大宗商品。曾經作為全球貿易中心的中國,此時已徹底淪為向西方出口農礦產品與工業原料的半殖民地國家,綿延千年之久的海上絲綢之路最終走到了盡頭。
結語
從16世紀后期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大約350年間,中國的海上絲綢之路經歷了由極盛走向極衰的巨大變動。這一變動是漫長的、漸進式的,與中國由一個向世界出口高端制成品的發達國家到一個只能向西方(包括日本)提供初級產品的落后國家的歷史轉變互為表里。正如貢德·弗蘭克所說,當16世紀西方人來到亞洲時,他們根本拿不出有競爭力的商品與中國進行貿易,只能依靠美洲白銀“在亞洲經濟列車上買了一個三等廂座位”;而隨著東西方貿易的展開,不久之后他們便“包租了整整一個車廂”,到19世紀更“取代了亞洲在火車頭的位置”,[15](P36-37)將中國納入到西方資本主義國際體系之中。而在這一歷史轉變中,海上絲綢之路逐漸由原本的中外經濟文化交流之路變成為西方資本主義發展供給養分的“輸血之路”。隨著其性質的根本改變,最終不得不退出了歷史舞臺。
在這場始于16世紀的巨大變動中,經由海上絲綢之路出口的主要中國商品,先是由絲織品、瓷器等手工業制成品變為了生絲、茶葉等中間產品和農副制品,最后又變成了豆類、鐵礦石等初級產品,由高端到低端,呈現出一條明顯的衰變軌跡。而不同商品出口的衰變都有一個共同的模式:中國商品出口-生產技藝外傳-本土商品發展-中國商品替代。在這一模式中,生產技術外傳是導致中國商品出口衰落最為關鍵的因素。中國出口商品由高端向低端的衰變過程,正是西方(以光彩或不光彩的手段)對中國商品制作技藝的學習過程。也正是由于日本和歐洲對中國經濟文化的長期不斷汲取,掌握了中國商品的生產技術,才具備了與中國商品一爭高下的能力,最終將其擠出了國際市場。
日本和歐洲之所以能在傳統產業領域實現對中國生產技術的趕超,更在于中國自身的固步不前。日本人曾評價中國的絲織技術早在漢代便已達到相當高的水準,但在此后的一千多年里幾乎沒有多大改進。正因如此,日本在掌握中國絲織技藝之后才能青出于藍,到了近代反而將其絲織品銷往中國。絲織品如此,瓷器、生絲、茶葉亦是如此。由于自身生產技術的發展停滯,近代以后,那些曾在世界上大放異彩的中國商品非但喪失了國際市場,在國內市場上也開始受到異國“學生”們的挑戰,越發舉步維艱。正是在這種進步與停滯的強烈對比中,海上絲綢之路走到了它的終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