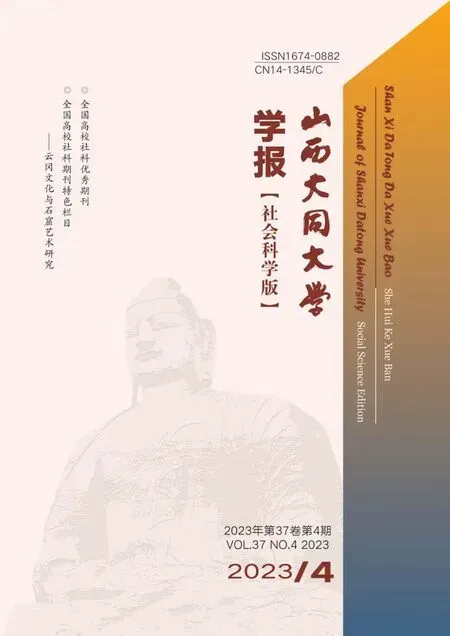近古哲學本體論與郝經的文學批評
侯文宜,王 晉
(山西大學文學院,山西 太原 030006)
對于中國文學批評史,在時序上各史家所采用的表述方法不同。或采用通史之法,按上古、中古、近古分期的;或參照通行的文學史,大體按歷史朝代分期;或一般徑直按年代先后,以文論家批評家的姓名為章目,而不標明分期。其中,應該說郭紹虞先生的《中國文學批評史》最為周備明晰,綜合其1934 年版本和1955年版本來看,既兼顧一般通史、文學史的表述,亦厘清批評史內在觀念的邏輯演變,故這里即采用郭氏上古、中古、近古之分期。所謂上古即指周秦至魏晉南北朝,中古指隋唐至五代,近古則指宋金元以至明清(鴉片戰爭前),而作為元初思想家的郝經,恰身處近古哲學轉型的時代,深刻受到理學本體論思維的浸潤,其思維向度和詩文論明顯地帶上理學的思辨特征,成為具有理論建樹和承啟意義的重要批評家。
一、近古理學之興與哲學的本體論思維及其影響
宋金元時期是中國歷史上一個特殊的、由沖突對峙而走向大一統的過程,又是一個多民族碰撞、融合和多元文化交匯的時期,由此決定了這個時代的社會特點和總體趨勢。盡管戰亂頻仍、朝代更迭、北方民族入主中原,然而有一點卻是一以貫之的,那就是儒學漢法在各個朝代的傳承和軸心作用。無論是女真族主政下的金朝,還是蒙古人主政下的元朝,要想統治中原大地、復建文明秩序,就不得不尊儒學用漢法,即如元代名臣、著名理學家許衡對元世祖忽必烈建言:“北方奄有中夏,必行漢法,乃可長久。故魏、遼、金能用漢法,歷年最多……史冊具載,昭昭可見也。”[1](P265)《金史·文藝傳》載:“世宗、章宗之世,儒風丕變,庠序日盛。當時儒者雖無專門名家之學,然而朝廷典策、鄰國書命,粲然有可觀者矣。”[2](P2713)正是在這樣的歷史邏輯下,自北宋發展起來的理學(又稱“新儒學”)成為宋金元直到明清時期的哲學主潮,并在元代被確立為科舉考試科目而成為官學。
可以說,宋金元時期四百多年,無論朝代變換更迭,整個社會的思想文化主潮是理學或曰新儒學。無疑,在不同時期和不同政權體制下,人們所面臨的社會問題不一樣,其話語形態、思想傾向及其影響力會有不同,但最重要的是其思維方式的變革和廣泛影響。換言之,理學雖然是一種哲學上的儒學轉型,但實際上其意義并不僅限于哲學之學,而是一種思維方法和認識論的轉型。正如著名史學家侯外廬所認為的,宋代思想文化的突出特點是理學的生成,而理學的生成同時也就是哲學的本體化。這一點是學界所公認的,尤其不可低估它對整個中國思想史的影響和理論推進,而這一切都無疑帶上了鮮明的近世色彩,將人們對世間萬象的思考導向了一種形而上的本體向度。
具體說,首先應看到近古哲學思維的本體化、思辨化發展及其方法論特點。
近古中國哲學發展主潮源自北宋崛起的理學,亦稱義理之學,以“二程”、朱熹為代表,強調“理”高于一切。雖然理學派別多樣宗旨各異,但“理本論”卻最大通約地概括了宋元明新儒學的本質特點,即以“理”為宇宙萬物之本源和本體規約。理學的形成無疑有歷史語境和時代的原因,但同時也是中國古代哲學發展的結果,其最大的特點就在于它是以儒學理想為基礎批判佛、道思想而又汲取其本體論思維所建構的新學說,適合了當時社會發展的需要。其實,早在唐中后期,一些名儒已舉起批判佛教的旗幟,面對“三教合一”的無邊彌漫,他們力圖重振儒學的權威,如韓愈作《原道》提出“道統說”,李翱提出“復性說”,這些思想為理學的產生開了端序,但均未達到本體論層面。直到北宋中期的“二程”兄弟程顥、程頤,才提出“理”本體論——天理是宇宙萬物的本原、主張先有理而后有物,如程顥說:“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卻是自家體貼出來。”[3](P424)程頤說:“萬物皆只是一個天理。”[3](P30)正是從“二程”開始,“理”或“天理”被作為哲學的最高范疇使用,亦即被作為世界的本源、本體,它既是指自然的普遍法則,也是指人類社會的當然原則,它適用于自然、社會和一切具體事物,所謂“萬物皆只是一個天理”。由此,帶來宋代哲學的理論化、思辨化特點,并進而成為元、明、清歷代哲學主潮。
對于宋代將儒學本體化的哲學成就,許多學者都有評價,即如侯外廬等所著《宋明理學史》便揭示得非常透徹:
北宋時期州縣學校興起,書院林立,促進了學術思想的發展……劉敞著《七經小傳》,廢棄漢儒專事訓詁名物的傳統,開啟了以己意解經的新學風。
理學是歷史范疇,它是在儒家經學、道教與佛教相結合的基礎上孕育發展起來的。理學是哲學化的儒學,其中滲透了佛教和道教的思辨方法和認識方法……宋明理學達到了思想發展史上的新的水平,它探究的學術理論的廣度和深度,是前所未有的。[4](P7、P20)
的確,在理學的產生和儒學本體化、思辨化的過程中,將中國哲學思維和形而上理論建構推進了一大步。所謂本體化,是指主張“理”是世界的本源和根本規律;所謂思辨化,是指哲學上運用邏輯推導而進行純理論、純概念的思考而得出理論性的結論,也就是將儒家倫理、政治學說提升到哲學思辨的理論高度。眾所周知,一般理論都有形成、發展的過程,思辨哲學的目的“是接過各門科學的結果,然后對這個整體進行反思”,[5](P251)進而通過這種方式,達到一種更為本質的系統的結論。宋儒理學對先秦儒學的發展和重構便凸顯了這一點。這種哲學上的思辨化、理論化趨向,自然而然會影響到人們的思維,從而帶來整個學術上的近古轉型。
其次我們來看這一本體論思維對文學批評的影響。在郭紹虞先生的《中國文學批評史》中,即寫到宋代尤其南宋以降整個中國文學批評史的近古轉型:
我嘗以為一般人之所謂“通”,其意義有三:一是文辭上的通……一是知識上的通……又一是思想上的通。唐人之學重在文辭上的通,所以以為用助字應求其當律令;漢人之學重在知識上的通,所以以為必須通群經而后始能通一經;宋人之學重在思想上的通,所以以為要貫通萬事而無礙。這是思想上的一種進步。文學批評家的思想,也必須能如此有中心、成體系,然后才可以論述,而此種情形,在南宋以后始見發展……為了有此分別,所以本書下卷之所論述,于批評家所提出的文學理論之外,更須涉及其學問思想,這好似贅余而不是贅余……以南宋金元為第一期,是批評家正想建立其思想體系的時期。[6](P3)
這里郭氏看到近古批評史的內在變遷,也就是說,到南宋金元之時,文學批評中開始由自得轉向自我、由對宋詩理論主張的反思開始轉向新的理論建構。最明顯和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南宋時期嚴羽的《滄浪詩話》了。一是其方法論上向形而上學的接近,這就是汲取佛學思辨和本體化思維對詩文本質的認知:“詩有別材,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然非多讀書、多窮理則不能極其至。所謂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詩者,吟詠情性也,盛唐詩人惟在興趣,羚羊掛角,無跡可求。”[7](P23)二是其邏輯化和系統化的論說結構,整體由“詩辯”“詩體”“詩法”“詩評”“考證”五部分構成,如李鐸先生所言“是宋代出現的一部最具嚴密體系的論詩專著”。[8](P116)
與南宋一樣,在北方文學批評中也形成思辨化的理論轉型。雖然與前朝北宋相比,金元之際的文學和文學批評相對沉寂黯淡,“除王若虛、元好問、方回等還以正文風、創詩學自任,寫了一些頗有特色的專著傳世外,其余作家大多不甚重視批評,僅在詩文序跋中興之所至寫些感想心得”,[7](P817)但同樣體現出近古的氣息。特別到了元代,士人的思想是相當自由、活躍的,他們不像宋、明兩代受到科舉和理學的明顯束縛,而表現出多元包容的思辨理性,就像元代文學研究專家查洪德先生在《元代理學“流而為文”與理學文學的兩相浸潤》一文中所說:“元代學術以融合匯通為特色。研究者早已指出,元代理學融會朱陸成為潮流。其實不僅朱陸,舉凡傳統儒學、張載氣學、事功之學以及呂祖謙東萊之學,都為各家吸收,參合變化。在詩文及文學理論界,打通壁壘,轉益多師,表現出與宋人各立門戶的不同取向。進而在文學與理學之間,也呈現融合匯通之勢。這一重要的文化現象,對于元代的學術與文學,產生著巨大的影響,使之表現出與宋、明皆不相同的顯著特點。”[10](P35-39)而就元初來說,正如郭紹虞所說,郝經是排在第一重要的批評家,由于身兼理學家、文學家的雙重身份,使其文學批評典型地呈現出理學文學的兩相浸潤,極富本體思辨色彩。
二、“文道合一”:超越宋儒偏見對文道論的重構
郝經是金元之際學問大家,也是當時著名文學家,《元史》一百五十七卷有傳,今存《陵川集》可窺一斑。《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對其作出如此評價:“其生平大節炳耀古今,而學問文章亦具有根柢。如《太極》《先天》諸圖說、《辨微論》數十篇及論學諸書,皆深切著明,洞見閫奧;《周易》《春秋》諸傳,于經術尤深。故其文雅健雄深,無宋末膚廓之習,其詩亦神思深秀、天骨秀拔,與其師元好問可以雁行。”[11](P1422)由此我們已可知郝經學問之深厚、思想之深銳,清人陶自悅稱其“理性得之江漢趙復,法度得之遺山元好問”雖廣為學界接受,其實遠不止此。他之能夠“獨申己見左右逢源”,還因有著源自程顥的郝氏家學之存養底蘊,以及少時盡讀賈氏、張氏“萬卷樓”藏書,故能貫通經史之學、理學與文學三者,實現對宋儒的超越和批評史上“文道論”的重構。
文道關系歷來就是文學中的一個核心問題,即如劉勰《文心雕龍·原道》所說“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12](P2)二者在社會文化的建構中相輔相成。然而自東漢以降出現了重文輕道或文道分離,故有中唐古文運動和韓愈、柳宗元等提出“文以明道”說。尤其到宋代理學家這里,文道關系成為一個主要問題,理學家追求道學、義理之學,而這些學說無疑有賴于某種形式的表達和呈現,于是“文道”關系再度成為焦點,然而卻出現了兩種極端的“文道論”。一種是周敦頤提出的“文以載道”說,另一種是程頤提出的“作文害道”,自其產生便時遭詬病。前者徹底將文與道分離,把“文”變成了載道的從屬工具;后者則更加走向極端,將“文”看作是有害于體道、傳道的“妨事”。兩種觀點其實都陷入理學本體思維的誤區,但因周、程二人的學術影響力而廣為流行。對處于滅金后元初的社會重建和文化重建來說,文道關系自然成為文人學者同樣面臨的問題,在此情況下,持守重“道”抑“文”,還是可以文道并重?郝經沒有簡單地奉從前人之說,對宋學的反思,對經史文融通的學術觀,讓他終至超越了北宋諸家的說法,并且從哲學本體論思維提出了“文道合一”的理論建構。
這可以說是郝經在文論史上的一個突出貢獻。雖然前人有過類似思想,諸如最早荀子《校儒》中云“圣人也者,道之管也……故《詩》《書》《禮》《樂》之歸是矣”,[13](P133)唐宋古文運動中有柳冕“夫君子之儒,必有其道,有其道必有其文”,或韓愈“修其辭以明其道”、柳宗元“乃知文者以明道”、歐陽修“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蘇軾“吾所為文必與道俱”,但都沒有像郝經這樣上升到哲學本體論上的系統闡論。郝經最大的特點,是把文與道的關系同文與自然的關系合二而一,把“自然”概念和理學家的“太極”觀念引入文道論,提出了“道即文、文即道”的“一體用”說。他在為垂范后世編選的《〈原古錄〉》文選“序”中作出如下的義理闡發:
昊天有至文,圣人有大經,所以昭示道奧,發揮神蘊,經緯天地,潤色皇度,立我人極者也。故自書契以來,載籍所著,莫不以文稱,天曰天文,人曰人文,堯曰文思,舜曰文明,禹曰文命,西伯曰文王,周公曰文公。仲尼之以道自任也,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皆言文而不及道,則道即文也。觀夫揭日月,翳云霓,干星漢,組布綦列,煥乎有文,覆冒磨蕩,庶物出焉,則天之道可知矣。載泰華,振河海,敷原隰,固溪壑,涵負崛岉,穆若有章,發育蕃衍,庶物生焉,則地之道可知矣。家焉而生聚教育,國焉而經理安定,耕鑿疆畛之有限,宮室車服之有數,貴賤親疏之有敘,爵祿上下之有分,典則采物,粲然有法,庶事治焉,則人之道可知矣。非是,則三極之道,莫得而見也,則文即道也。道非文不著,文非道不生,自有天地,即有斯文,所以為道之用而經因以立也。[14](P2180-2184)
在郝經看來,“文”與“道”其實一也,皆為“太極”本然而固有矣。無論天之道、地之道、人之道,其變幻運行,種種情態,即是道也是文,故得出“道即文也,文即道也”的結論。它們二者相輔相成、相依相存并相映相現:“道非文不著,文非道不生。自有天地,即有斯文,所以為道之用,而經因之以立也。”由此郝經實現了“文道合一”的理論確證,并將“文”的價值地位提高到了本體論認識。在這一點上,可以說是對之前文章淵源論的一種超越,得之于宋元理學哲學本體論的支撐。一般關于文章本體,中國歷來有兩種說法:一種如《顏氏家訓》認為文章“原出五經”,即儒家之道是文章的本體;另一種以劉勰《文心雕龍》為代表認為文章本于自然,一切文皆出于自然天成,所謂“夫豈外飾,蓋自然耳”“心生而言立,言立麗文明,自然之道也”。[12](P1)而到郝經這里,全部都統到了一起,這就是理學的一個總概念“太極”。在他看來,道與天地一,文章又與道一,道與天地、文章都是本然而固有的,而其共同之本便是太極。由此,“文”與“道”也就合二為一,其生成、昭示乃至多彩形態,皆為太極本體所出,無論天文、地文、人文,都是“同一理耳”。這樣一種“文道”并生互映的理論,顯然遠遠超出了文道分離或對立之說,實現了對“文道論”的重新構建,開元代文學“文理并重”之先聲。
對于郝經這一理論建樹,以往研究少有關注,往往將唐宋古文運動代表人物言論看作經典,似乎后學不過是重復而已。但郝經所論其實有集大成理論價值,這主要就在于其時近古理學已獲得極大發展而更具歷史空間。作為理學家,郝經能夠從本體論思維角度看文道關系予以究理思辨,而非古文家主要著眼于言辭表達與道的關系;作為文學家,其為南北對峙下元好問北宗文學重要成員,有深厚的文學修養,因而能夠洞察文學本體糾偏宋儒之說。而事實上,其后元代文學的繁榮以至《元史》中首次將文苑傳與儒林傳合一,沒有像其他正史一樣另設《文苑傳》,著實表明郝經“文道合一”的理論影響,較好地解決了中國文學史和文學批評史上的這樁公案。對這一點,在成復旺先生出版的《中國文學理論史》中是看到的,雖然一些用詞帶有當時政治語境色彩,但對于郝經這一理論建樹的本體論價值其實給予了很高評價:“它為封建王朝以道統文、以文濟道提供了最為博大精深的理論根據,因而就成了道學出現之后的封建統治階級的官方文學本體論。這種文學本體論的創立者雖不是郝經,但在他之前還沒有這樣完整而系統的表述。”[15](P557)在1980 年代學術回歸之初能達到這樣的理論眼識,可以說已是相當不易。
三、從“理法之本”到“文自我作”:批評史上極富創見的文法論
處于宋、金向元的歷史交替時代,對于北中國來說,這是一個歷經戰亂亟需重建的時代,以復興斯文為己任是當時許多士人的理想,諸如楊惟中、姚樞、張德輝、元好問、許衡、郝經、劉因、王惲等,都將文化救世作為拯救社會方式。郝經一方面追本傳統賡續正脈,對“文道”關系作出新的梳理建構,另一方面,元初北方多元、自由的氛圍,面對宋金遺風影響和創作中僵化泥法的問題,促使他對文與法的關系作出深入思考,寫下了《答友人論文法書》這篇金元批評史上最富新意銳氣之文。此文分量同樣在于它的義理思辨、理論深度和系統性,就像敏澤《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所言:“主張法當自立,反對泥諸前人等等,這些意見無疑還是包含著合理、精到因素的。”[16](P743)如果沒有近古哲學的轉型,沒有義理思辨的思維邏輯,也就難以產生出這篇為學界公認的批評理論雄文。
該文起因是友人寫來書信“惠問作文法度利病”,從而引發郝經思考,在經過系統思索后他給友人回復了這篇答書。因為是與友人論文法,其中道學色彩就較淡些,應該說是郝經所有文學批評中最能體現文學理論價值的一篇長文。它不是一般地討論“法”之重要還是不重要、“法度利病”各是什么,而是同樣立足于理學哲學本體論,從文法的事理關系上作出了深刻闡論。文中首先承認“為文則故自有法”,但接著便區分了只講表層的文法還是從根本上講文法,提出了“理法”的本體論范疇,并批評了近世“以文為技”的弊端。其曰:
理者法之源,法者理之具,理致夫道,法工夫技,明理法之本也。吾子所謂法度、利病,近世以文為技,與求夫法資于人而作之者也,非古之以理為文,自為之意也。古之為文也,理明義熟,辭以達志爾。若源泉奮地而出,悠然而行,奔注曲折,自成態度,匯于江而注之海,不期于工而自工,無意于法而皆自為法。故古之為文,法在文成之后,辭由理出,文自辭生,法以文著,相因而成也,非與求法而作之也。后世之為文也則不然,先求法度,然后措辭以求理。若抱杼軸,求人之絲枲而織之,經營比次,絡繹接續,以求端緒。未措一辭,鈐制夭閼于胸中,惟恐其不工而無法。故后之為文,法在文成之前,以理從辭,以辭從文,以文從法,一資于人而無我,是以愈工而愈不工,愈有法而愈無法,只為近世之文弗逮乎古矣。[14](P1808)
這里,郝經用形象的比喻闡明了“文”與“法”的關系,即非有意“求夫法、資于人而作之者也”,而是出于“自為之意”的自然而然,可見,其第一的基本觀念如他所說:“夫理,文之本也;法,文之末也”。正因此,郝經像當時幾位有識者王若虛、元好問一樣,批評那種為文“法在文成之前”“一資于人而無我”的歧途,表明了自己對文法關系的認識。
如果僅止于上,郝經對文法問題頂多體現出一個理學家推本究原的本體之辨,但除此之外,他進而引出了另一個層面上的主體問題,即文法的直接造作者。這樣,便有了廣為稱道的“文無定法”“皆自我作”這般盡顯新思維的命題。姑引如下:
文有大法,無定法。觀前人之法而自為之,而自立其法,彼為綺,我為錦,彼為榭,我為觀,彼為舟,我為車,則其法不死,文自新而法無窮矣。近世以來,紛紛焉求人之法以為法,玩物喪志,窺竊模寫之不暇,一失步驟,則以為狂為惑,于是不敢自作,不復見古之文,不復有六經之純粹至善,孔孟之明白正大,左氏之麗縟,莊周之邁往,屈宋之幽婉,無復賈、馬、班、揚、韓、柳、歐、蘇之雄奇高古,清新典雅,精潔恣肆,豪宕之作,總為循規蹈矩決科之程文,卑弱日下,又甚齊梁五季之際矣。嗚呼!文固有法,不必志于法。法當立諸己,不當泥諸人……
故今之為文者,不必求人之法以為法,明夫理而已矣。精窮天下之理,
而造化在我,以是理,為是辭,作是文,成是法,皆自我作,志帥行權,多多益善。[14](P1809-1811)
為什么郝經會提出“文無定法”“皆自我作”呢?這是他思考很久的問題。因為當時法度束縛和泥法問題已成文壇大弊,其師元好問《論詩三十首》中有許多即是針對此的批評,如第二十一首對僵硬模擬的批評:“窘步相仍死不前,唱酬無復見前賢。縱橫正有凌云筆,俯仰隨人亦可憐”。再如第二十八首對江西詩派的批評:“古雅難將子美親,精純全失義山真。論詩寧下涪翁拜,未作江西社里人”。另在元好問《自題〈中州集〉五首》中,又有“北人不拾江西唾,未要曾郎借齒牙”和“詩家亦有長沙帖,莫作宣和閣本看”二首,都是對刻板泥法的尖銳批評。綜觀當時對宋金以來文壇的批評,集中起來主要即三點:其一即上述對蘇、黃無保留地學習和模仿;其二是他們的門戶之見;其三是對江西詩派以學問才學為詩的閉門造車式的創作態度之批評。[17](P71)對此,郝經亦頗有不滿和清醒認識,故在《答友人論文法書》中給予了激烈的批評:“近世以來,紛紛焉求人之法以為法,玩物喪志,窺竊模寫之不暇,一失步驟,則以為狂為惑,于是不敢自作……總為循規蹈矩決科之程文,卑弱日下,又甚齊梁、五季之際矣。嗚呼!”[14](P1810-1811)
郝經此文洋洋數千言,層層闡述理與法、文與法的關系及其利弊,其中有形而上本體論的理論思辨,有自古以來文法史的梳理,還有各時期文章家的案例實證,可以說是對文法論的一次透徹思考,也是一種系統構建,其理論價值無疑是十分突出的。當然,我們也應指出郝經作為一個理學家的歷史局限性,如他所倡“明理法之本也”,即主要是指儒家的倫理綱常之理,所謂“六經理之極,文之至,法之備也……《書》有道德仁義之理,而后有點典謨訓誥之法;《詩》有性情教化之理,而后有風賦比興之法;《春秋》有是非邪正之理,而后有褒貶筆削之法;《禮》有卑高上下之理,然后有隆殺度數之法”。[14](P1808)這里明顯表現出與其所說“法皆自作”的矛盾,不自覺地囿于封建時代下理學對文學的牽制。不過瑕不掩瑜,在其“文有大法而無定法”之說下,畢竟各人對“理”的體認是多樣的,如其所列舉的文法典范——從《左傳》《莊子》《荀子》到屈、宋辭賦,從兩漢的賈誼、劉向、揚雄等人到唐宋韓柳、歐蘇之文,認為其文章“皆以理為辭而文法自具”,其實這已將“理”的范圍擴大到一切宇宙、自然、社會、人情之理:所謂“標識根據,不偏不倚,中天下、準四海以為正;輝光照耀,炳烈粲發,引日星、麗霄漢以為明;造微入妙,探賾索隱,極九地、筑底里以為深;包括綿長,籠罩遐外,塵天地、芥太極以為大……莫非自然以為神。豈規規孑孑,求人之法,而后為之乎?”[14](P1807)如此,則與一般理學家道統之說已區別開來,表現了一個文學家的審美自由,也透露出近世批評的個性意識。故而郭紹虞先生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中對此評價甚高:“此種意思,又成清初魏叔子一流古文家的文論。其論學很像清初的學者,其論文也像清初的文人。這真是一篇很重要的文字。”[6](P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