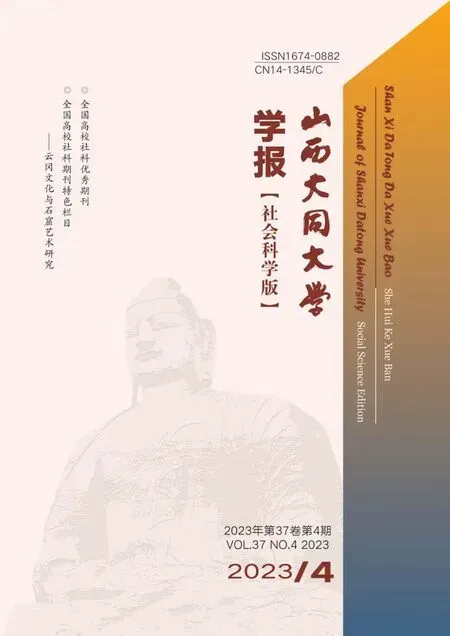試析《東堂老》中的托孤現象
尹 璐,王鵬龍
(1.山西大同大學文學院,山西 大同 037009;2.山西師范大學戲劇與影視學院,山西 太原 030031)
元雜劇對生活難能可貴的真誠,幫助我們了解普通人的七情六欲,這種簡單、真實的記錄將我國戲曲推至輝煌,正如王國維先生所說:“論真正之戲曲,不能不從元雜劇始。”[1](P359)曲盡人情,是元曲在表現情感上根植于社會現實的自然作風。[2](P8)基于對市井深入細致的觀察,塑造出可愛、可親的人物形象。在浩如煙海的元雜劇佳作中,既有反映社會訟獄事件的公案劇,也有反映青年男女之間愛情糾葛的才子佳人劇,還有反映個人與社會之間倫理沖突的人情世態劇。《東堂老》作為秦簡夫代表性的人情世態劇,一直被眾多曲論家贊賞。明人賈仲明在為秦簡夫補作挽詞時,稱贊《東堂老》“壯麗無敵”,[3](P38)明朱權評其詞“如峭壁孤松”,[3](P129)是一篇值得后世品鑒的戲曲佳作。
一、《東堂老》中“托孤”的特點
中國歷史上關于托孤的記述不勝枚舉,但大多都是帝王和大臣之間的托付,如劉備白帝城托孤。而《東堂老》的托孤則是商人和商人之間的托付。秦簡夫將趙國器立托孤文書設置為劇本開場,開篇即點明主線——臨終托孤,其后以浪子揚州奴擺脫劣習逐漸成長為暗線,以東堂老巧計引導揚州奴為明線,明暗交織,經歷多番波折,最終揚州奴浪子回頭。劇目開端東堂老的婉言推辭和劇目結尾東堂老的信義歸產相互呼應,劇中東堂老的竭力引導,根據揚州奴每次所處的實際境地采取不同的引導策略,構思嚴謹。揚州奴由揮霍無度到淪落街頭再到醒悟改正,層層遞進。
(一)以家庭財產為目的 和歷史上托孤現象相比,趙國器的委托是以家產為主要內容,主要目的是實現家庭內部財產的延續。趙國器的托孤,不僅有家產的托付,也有不肖子的托付。作為一名富商,趙國器希望自己打拼的豐厚錢財可以延續下去;作為一位父親,趙國器希望自己的兒子可以光宗耀祖。實際上,《東堂老》中的趙國器擔憂的不僅僅是家產,從更深層次來說,他更擔心的是趙氏家產到自己這一輩無法延續下去,不能維護封建家庭財產繼承權,這和中國人傳統的觀念有關。以家庭倫理為中心的社會文化決定了家庭財產關系,將財產繼承嚴格控制在家庭或家族范圍內。所以這里趙國器的托孤不僅有對兒子揚州奴的恨鐵不成鋼,也有對自己家產無法繼承的遺憾。
劇本一開場,就寫了趙國器憂思過度:“只為生兒性太庸,日夜憂愁”,“戀酒迷花,無數年光景,家業一掃無遺”。[4](P407)家業敗空的憂慮充斥在趙國器的生命最后階段。趙國器殫精竭慮為兒子揚州奴鋪設道路的苦心充分表現出了富商巨賈希望家財能夠輩輩相承的心理,“不肖子”揚州奴如何繼承并發揚家業的擔憂心理充斥了他生命的最后階段。秦簡夫在劇中評價他是“為兒女擔憂鬢已絲,為家財身亡心未亡。”[4](P407)身心俱疲的趙國器離世前仍在為兒子揚州奴謀劃。
《東堂老》中,秦簡夫注意到了家庭財產破敗面臨的兩種危險。[5](P73)一方面來自外在潑皮的覬覦,另一方面出自家庭內部的浪子。“柳隆卿”和“胡子傳”已經成為游手好閑人物的代稱,他們寄生蟲似的生活方式毒蝕著他人的正常生活,腐化著他人的家業。這樣的無賴潑痞在揚州奴“腰纏萬貫”時諂媚巴結,在揚州奴家財散盡時落井下石。揚州奴紈绔子弟的荒唐行徑,在劇作中可窺見一二:“把家私來蕩散了,把妻兒挨凍餓倒。”[4](P413)這種揮霍無度、不勝其任的行為讓東堂老發出“遙望你醉還醒迷還悟夢還覺”[4](P413)的感慨。
但和前一種相比,后一種對家庭財產的破壞性更大更直接。前一種的破壞更像是外部的引誘,外部的力量并不會觸及家庭財產的核心利益。而后一種的破壞是家庭繼承者的自我墮落,對外在誘惑來者不拒,且沉溺其中無法自拔,這樣的繼承者即便有明智長者的苦心指引,也不能挽救岌岌可危的家族產業。直至家庭繼承者自己醒悟,痛徹大悟,走出泥潭,拒絕外在引誘,再加上智者的耐心引導才是挽救家產的最佳方式。《東堂老》劇中記述趙國器托孤,精心塑造東堂老這一藝術形象,并希望通過東堂老完成家庭內部家族財產信托。
公元223 年,劉備在白帝城病重,把兒子劉禪和蜀國政權托付給諸葛亮。無論是劉備的白帝城托孤還是趙國器的臨終托孤,兩者的共同點就是:委托者和受委托者雙方都達成一致意見,委托者是自己信任的下屬或好友,受益人是委托者的后代。作為委托者的劉備和趙國器把自己的孩子分別托付給了諸葛亮和東堂老,受委托者諸葛亮和東堂老也都同意并接受了他們的托付。和趙國器托孤不同,劉備的白帝城托孤是以權力為主要內容,主要目的是實現政權的延續。東堂老是把揚州奴引回正途,重振家業。
(二)以“富而好義”的商人為委托者 歷史上托孤的受委托者一般是托孤大臣,但秦簡夫別出心裁地塑造了東堂老這一藝術人物,并從正面描寫這一商人形象。此前商人形象大多為狡詐、貪婪、自私的負面形象。《東堂老》中東堂老形象的轉變反映出宋元時期商人形象的轉變。“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是趙國器對東堂老的肯定。趙國器和東堂老兩家交情至深,東堂老又具備崇高的聲譽,因而是趙國器托孤的最佳人選。由于缺少法律制度的約束,趙國器的托孤現象屬于道德關系,受委托者的道德品質成為托孤成功與否的關鍵。《論語·泰伯》中曾子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6](P98)可見在儒家思想中,受委托者的基本要求就是“顧命守節”,這是一種道德要求。《東堂老》楔子:“今日請居士來,別無可囑,欲將托孤一事,專靠在居士身上,照顧這不肖,免至流落。”[4](P405)趙國器稱東堂老“居士”,只有擁有崇高的德行和才能,但選擇隱居不踏入仕途的修行之人才能稱為“居士”。由此可見,東堂老的道德品質是極高的。
趙國器把揚州奴托付給東堂老,除了東堂老高尚的道德品質,還因為他知道東堂老有能力也有辦法幫助揚州奴。東堂老幼時讀過經書,深受儒家文化的熏陶,在教育揚州奴時嚴厲也講究方法,東堂老引導揚州奴回歸正途花費了無數心血。撞破揚州奴和腌臜無恥的胡子傳、柳隆卿胡混時,作為威嚴的長者聲色俱厲地戳破這些小人的卑鄙心思,企圖罵醒揚州奴。看到揚州奴夫妻二人淪為乞丐的窘境,又化身慈愛的長輩,語重心長地勸誡過后給揚州奴提供做生意的機會。揚州奴受人蠱惑時是長者對后輩怒其不爭的憤怒,揚州奴經歷磨難幡然醒悟時是長輩對后輩迷途知返的欣慰。東堂老最終誠信歸還家產的舉動是對好友趙國器的守信,托孤文書作為引子,既是趙國器托孤揚州奴的證明,也是揚州奴浪子回頭的證據。同元代其他劇作家一樣,秦簡夫《東堂老》取材也有本事,它來源于宋人方勺筆記小說《泊宅編》記載的張孝基的故事,許昌張孝基受妻子同里富人所托,照顧引導富人獨子,“孝基徐察之,知其能自新,不復有故態,遂以其父所委財產歸之”。[7](P33)《東堂老》中東堂老的形象就是張孝基的延續。
(三)以迷途知返的“浪子”為遺孤 歷史上其他遺孤大多都年齡尚小,需要別人照顧。譬如《趙氏孤兒》里的嬰兒趙武,是尚在襁褓中的嬰兒。而《東堂老》中的“遺孤”揚州奴是“六尺之孤”,他已經成長為可以自食其力的青年男子,父親趙國器在揚州是數一數二的富商,逝世后留給他龐大的家業,揚州奴本可以子承父業,把趙家的生意做得更大,但是交友不慎,誤入歧途,終日和他的酒肉朋友們沉迷享樂,不思進取,肆意揮霍家產。除此之外,歷史上的托孤,因為遺孤是在受托孤者的照顧下長大的,所以一般不會出現交友不慎、誤入歧途的情況。拳拳父母心,殷殷父母情,每個父母都竭盡全力為自己的孩子創造幸福,排除困難。趙國器深知自己的兒子揚州奴本性不壞,只是交友不慎,誤入歧途。臨終之際仍然放心不下他,就把他托付給自己多年的好友李實。而在東堂老的教育引導下,揚州奴經歷一番挫折后,幡然醒悟,迷途知返,最終回歸正途。作為托孤事件的受益者,揚州奴經歷了內外交困的雙重磨難。內部的磨難來自母親的溺愛,缺乏父親的嚴格教導,這樣的成長模式造就了揚州奴揮霍無度的性格。外部的磨難來自損友的誘導。良師東堂老化解了揚州奴內外交困的處境,妻子李翠哥的陪伴也是揚州奴浪子回頭的原因之一,在他早期和渾友相交之際,妻子就極力勸誡,后期淪落街頭也沒有離開揚州奴,一直陪伴他度過最艱難的時刻。如果說良師東堂老是引導揚州奴悔悟歸正的精神力量,那么賢妻李翠哥是支撐他走出困境的精神支柱。良師賢妻的勸化模式引來了揚州奴“浪子回頭金不換”的美滿結局。
二、《東堂老》中托孤現象的成因
作為元雜劇創作家,秦簡夫以其獨特的藝術手法通過《東堂老》反映出歷史上常見的托孤現象,《東堂老》中托孤現象的形成與當時的社會現實和秦簡夫的創作目的有著密切的聯系。
(一)元后期富商家產繼承的社會問題 每個時期的文學必然會和相應時期的經濟發展水平息息相關。游牧民族出身的元代統治者,出于滿足自給自足的生活需求,極力發展經濟,由此我國的城市商業經濟在這一時期得到迅速發展。經商不再被人們所排斥,隨之涌現出大量的富商。與此同時,出現了富商家產不知該如何繼承的社會普遍現象。隋唐以來,揚州憑借水運之利成為我國南北交通樞紐,這為以后揚州的富庶,揚州商業的繁榮都提供了便利的條件。隨著經濟中心的南移,揚州成為著名的商業城市和繁華都市。擁有巨大財富的富賈在城市商業經濟繁榮發展的推動下應運而生。元末,陶宗儀《南村輟耕錄》卷七記載現實生活中揚州富商曹氏瀕死托孤,家庭內部為爭奪家產親情漠然的現象:“劉信甫,揚州人。郡富商曹氏奴。曹瀕死,以孤托之。孤漸長,孤之叔利孤財,妄訴于府。”[8](P91)金錢的巨大誘惑已經將傳統倫理道德的大家庭分崩離析,親情在金錢面前顯得微不足道。家庭財產繼承問題成為現實中的突出問題,引起了雜劇作家的關注。秦簡夫的雜劇《東堂老》就講述了揚州富商趙國器的巨大財富如何繼承的問題。《東堂老》劇中,趙國器不僅“負廓有田千頃”,而且“城中有油磨坊、解典庫”,[4](P405)是揚州出名的大財主。但是,他生前擁有的財富越多,死后財產繼承的問題也就越嚴重。秦簡夫希望通過藝術的手法來解決這一社會問題。
商業經濟越發達,隨之出現的社會問題越復雜。商人們追本逐利的瘋狂在社會上掀起“金錢至上”的社會思潮。面對金錢的巨大誘惑,整個社會都趨向“錢為本”的價值觀,傳統的道德徹底失去約束力,這對儒家思想產生了巨大的沖擊。當商業、道德亂象遍布社會之際便引起作者的關注。當作家們開始關注社會亂象,這種現象又會啟發他們去思考創作,并試圖在劇作中創作出正面形象成為社會生活中的積極力量,激勵在亂象叢生的社會中生活的底層百姓堅守道德。
(二)作者彰顯倫理教化的創作目的 元代末期的雜劇家秦簡夫在雜劇創作史上有突出的地位,元代曲家鐘嗣成在《錄鬼薄》中把秦簡夫列入“方今才人相知者”,并描述他在京都享有名聲。秦簡夫一生著有五部雜劇,分別為《東堂老》《趙禮讓肥》《剪發待賓》《玉溪館》《邢臺記》,現僅存前三種,都是倫理劇作。秦簡夫致力于倫理道德劇的創作和當時的時代背景有極大的關系,秦簡夫所生活的時代正處于元代后期,元朝推崇的儒學政策和當時城市商業的繁華形成了格格不入的局面,市民崛起的商業意識逐漸成為社會主流思潮。整個社會人們的道德水準呈直線下降趨勢。秦簡夫企圖通過作品來對抗這種社會現象,《東堂老》塑造了好逸惡勞的破家子弟“揚州奴”和正直誠實的富商“東堂老”兩個形象,兩者形成鮮明的對比。通過“揚州奴”這一不肖子形象來警示浪子迷途知返,又通過“東堂老”這一正面商人形象來褒揚古人的善行義舉,以達到教育民眾的良好效果。
廖奔、劉彥君的《中國戲曲發展史》認為:“元代由于異族統治,社會風氣混亂,傳統的倫理道德信仰遭受沖擊而傾斜,帶來眾多的社會問題。”[9](P283)于是,劇作家們創作劇目時更多側重以倫理說教為主題。劇作家們取材現實又反哺現實,現實的混亂為文學創作提供土壤,劇作家們的創造又影響現實風氣。秦簡夫借雜劇向人們傳達正面的價值取向,這是劇作家對崩亂社會的反抗,也是對最高層統治者的警醒。
三、《東堂老》中“托孤”的意義
雖然每個朝代的統治者出于鞏固統治的目的大力提倡倫理教化劇,但也應注意到倫理教化劇中傳達出的精神對后世也具有積極的意義,《東堂老》劇目中蘊含的垂范身行的榜樣模范作用,謹慎的交友觀,積極進取的人生觀在當今時代仍具有借鑒意義。
(一)樹立了垂范身行、慎交友的典范《東堂老》的意義之一就體現在長輩對晚輩垂范身行的典范激勵作用。揚州奴的父親趙國器憑借自己早年“做商賈早起晚眠積攢這家業”。趙國器以自己旦出暮歸的行徑試圖感染兒子揚州奴,讓他明白積攢家業的辛酸和艱苦。看到揚州奴結交狂朋渾友的荒唐行徑,趙國器已然預料到敗落家產的危機。好友東堂老受到趙國器的臨終托孤也在生活中引導揚州奴,并以身為范感染揚州奴。東堂老和老友趙國器簽下托孤文書后就對揚州奴進行苦口婆心地勸誡,面對揚州奴的墮落,東堂老憤怒地直言“又不是年紀小,怎生得一樁樁好事不曾學”。[4](P413)東堂老也曾講述自己行商的艱難:“為蠅頭努力去爭……到今來一身殘病,去那虎狼窩不顧殘病”,[4](P413)試圖敲醒揚州奴的墮落。但東堂老在語言上的垂率無法震醒踏入迷途的揚州奴時,他選擇讓揚州奴親身體驗人生悲苦。在揚州奴典賣家產,淪落街頭靠行乞為生的悲慘階段,揚州奴終于舍下臉面去討要做生意的本金。曾經豪擲千金的富家公子哥如今當街叫賣,東堂老看似折辱揚州奴“前街后巷”“自叫”,實則引導他做生意,暗含了對揚州奴轉變的希翼。
劇本末尾東堂老如約把趙家產業全部交還給浪子回頭的揚州奴,可堪守信義、重言諾、忠心地實踐受托的好鄰居。
劇中設置了東堂老和趙國器,浪子揚州奴和柳隆卿、胡子傳兩種交友范式。趙、李二人的友誼以趙國器臨終托孤李實,李實完成趙國器遺愿的雙向圓滿作為結局。揚州奴和柳隆卿、胡子傳的友誼以柳、胡二人誘導揚州奴走上歧途,揚州奴和柳、胡二人分道揚鑣的雙重“悲劇”作為結局。東堂老認為揚州奴是因為“內無老父尊兄道,外無良友嚴師教”[4](P413)雙重缺失才淪落至此,因此東堂老極力讓揚州奴遠離兩個損友,看清他們的真面目。
(二)展現了積極進取、自信勤勉的人生態度 元雜劇出現的商人形象,一般都是譴責他們見利忘義的卑劣行徑,雜劇家竭力揭露商人形象的丑陋。而秦簡夫的《東堂老》則一反傳統,精心塑造了正面商人形象,并展現了東堂老積極的人生態度。劇目否定了貧窮富貴皆由命定的傳統觀念,肯定了個人的主觀能動性。東堂老充分意識到個人的主體作用,表現出了“我命由我不由天”的自信和執著,這從他對后代的教育以及自己的經商生涯中都可以印證。東堂老認為富貴窮達源于人們自己的努力,與天命無關。《東堂老》第二折:“那做買賣的,有一人肯向前,敢當賭,湯風冒雪,忍寒受冷,有一等人怕風怯雨,門也不出”[4](P419)不同的選擇會有不同的結局,所以“怎做得由命不由人”。東堂老相信只要肯吃苦敢冒險,就會發財致富。他極度贊揚那些積極主動做生意的買賣人的態度,人生中只要積極爭取,就會擁有更多的財富和機會。
東堂老的自信勤勉不僅表現在自己的人生態度,也體現在對揚州奴的教育理念上。他毫不避諱自己的商人身份,認為憑借自己汗水和才智賺取的錢財不丟人,把一件事做到極致,就是“人物”。“雖然道貧窮富貴生前定,不徠,咱可便穩坐的安然等?”[4](P419)做生意要靠自己的努力,不要做天上掉餡餅的白日夢。這種積極進取的經營態度,和對商賈辛勤努力的肯定,不僅在重農抑商的傳統觀念中是難能可貴的,在今天的商業經營中也是值得學習的。
結語
《東堂老》的創作,在元代后期雜劇發展史上也是占據突出地位的。元代后期,雜劇創作逐漸脫離社會現實,秦簡夫努力立足現實,筆鋒觸及當時的社會現實,把倫理道德融入自己的雜劇創作中。其劇作不僅反映了當時商人社會地位有所上升的狀況,也體現了醇厚人際關系、教化民眾的社會功能。秦簡夫用自己創作的正面商人形象去挽救中國商業經濟剛剛出現萌芽時道德淪喪的社會亂象,體現了劇作家對時代脈搏的準確把握和對人生價值的深刻思考。
《東堂老》塑造的揚州奴浪子回頭形象成為元代“家長里短”家庭劇的一大文化主題。《東堂老》肯定父母孩子之間的血緣親情,同時也歌頌了朋友之間的信義友情。即秦簡夫《東堂老》不僅塑造了一位正面商人形象,突破以前文學作品中常居于被貶斥的商人形象,也展現了具有時代責任感的雜劇家借戲教化眾人的苦心,還肯定了中華傳統美德在維系家庭穩定和強化社會倫理道德等方面所具有的積極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