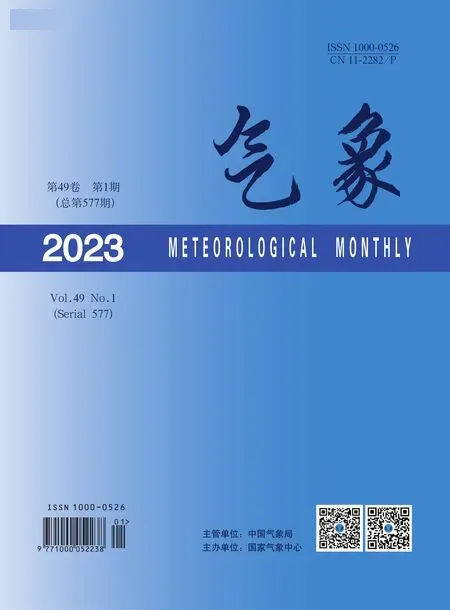一次春季江淮氣旋混合型對流天氣特征及成因分析*
吳 濤 許冠宇 李雙君 魏 凡
武漢中心氣象臺,武漢 430074
提 要: 采用天氣雷達、高空地面觀測、1°×1° NCEP再分析場資料,分析一次春季江淮氣旋形成發展過程中混合型(冰雹、大風、短時強降水)對流天氣特征,初步解釋了不同類型對流天氣形成發展的原因。結果表明:不同類型強對流天氣在時空分布和對流特征上存在差異,其中局地冰雹主要由氣旋形成階段離散對流線產生,帶狀短時強降水由氣旋形成階段人字形對流線上及發展階段S形對流線后部的列車線/鄰接層狀云類中尺度對流系統(MCS)產生,大范圍大風主要由江淮氣旋發展階段S形對流線上尾隨層狀云降水類MCS產生。江淮氣旋是大尺度天氣系統斜壓發展的結果,對流活動使鋒面低層輻合增強,對氣旋形成發展有加強作用。強對流天氣的產生與江淮氣旋動力熱力場有密切關系。氣旋形成階段,西南渦結合山區地形提供了有利于鄂西南大冰雹形成的環境場,暖式切變線以及氣旋發展階段受南支槽影響的冷式切變線,提供有利于風暴列車效應形成的環境場而產生短時強降水;氣旋發展階段,冷式切變線提供有利于后部入流急流形成的環境場而產生大范圍大風。
引 言
江淮氣旋屬于溫帶氣旋的一種,所引發的對流天氣具有多樣性。根據不同的天氣學成因,斯公望(1980)將溫帶氣旋內部具有對流性質的中尺度降水帶分為五種類型:暖鋒型、暖區型、冷鋒型、鋒前冷空氣爆流型及鋒后型。江淮氣旋暖鋒(暖式切變線)附近不穩定性較強時有對流發展,強的鋒生、輻合及正渦度等作用有利于產生大范圍暴雨(張曉紅等,2016;沈陽等,2019)。在西南暖濕急流推動下,暖區暴雨北抬可轉換為暖鋒前暴雨(黃士松等,1976)。因冷暖空氣交匯導致的斜壓鋒生作用,冷鋒附近常形成有組織的線狀對流系統并產生大風、暴雨等強對流天氣(陳永林等,2013;孫繼松等,2014),而斜壓性較弱的江淮氣旋冷鋒在南壓過程中轉為東西走向,風暴移動出現“列車效應”而產生極端降水(張家國等,2018)。近年來鋒前暖區極端降水引起研究人員的重視,由于環境場層結不穩定性強和水汽充足,中尺度對流系統發展活躍易產生極端強降水,其觸發發展機制與地形、邊界層輻合線等關系密切(雷蕾等,2020;黃美金等,2022)。
20世紀以來,天氣雷達大量應用于揭示中尺度對流系統結構及活動規律。趙宇等(2018)探測到冬季江淮氣旋逗點云區中來自不同性質氣團的多條氣旋式旋轉、拉長的中尺度強降水帶。丁治英等(2019)觀測到江淮氣旋暖鋒上由重力波觸發的多條平行對流回波帶。Bluestein and Jain(1985)、Parker and Johnson(2000)、Schumacher and Johnson(2005)、王曉芳和崔春光(2012)、張小玲等(2014)、王玨等(2019)基于中尺度對流性系統(MCS)的雷達觀測事實,根據MCS組織結構及運動特征總結出基本的MCS模態,主要包括尾隨層狀云降水(簡稱TS)類、平行層狀云降水(簡稱PS)類、前導層狀云降水(簡稱LS)類、列車線/鄰接層狀云降水(簡稱TL/AS)類、準靜止/后向建立(簡稱QS/BB)類、渦旋(簡稱VS)類、合并類等。MCS組織結構與風暴相對氣流的垂直分布、中尺度天氣系統、地形等有密切關系,其中TS類MCS與颮線有關(Houze,1997),TL/AS類MCS與靜止鋒有關(Schumacher and Johnson,2005),而渦旋類MCS與中尺度渦旋(氣旋)密切相關(吳濤等,2017;梁建宇和孫建華,2012;易笑園等,2011)。
當前開展江淮氣旋引發暴雨的雷達觀測特征及機制分析較多,而對春季江淮氣旋所引發混合型對流天氣的分析相對較少,江淮氣旋作為斜壓性明顯的α中尺度渦旋系統,在生命史各階段中尺度對流系統演變特征、不同類型對流天氣特點及形成機制還不夠清楚。此外,多數研究成果基于大尺度天氣形勢分析江淮氣旋成因(朱乾根等,2007),而較少分析中尺度對流活動對江淮氣旋的作用,實際上兩者往往是協同發展的,中尺度對流活動所發揮的作用值得重視。
2019年4月8—9日,受江淮氣旋影響,長江中下游及江淮地區經歷了一次較大范圍的短時強降水、冰雹、大風混合型對流天氣過程,然而主要對流天氣出現的時段及對流特征有所不同,開展相關問題的分析很有必要。本文使用新一代天氣雷達、區域自動氣象站資料、高空/地面天氣圖、1°×1°空間分辨率/6 h間隔GFS再分析場,從雷達觀測角度揭示由江淮氣旋形成過程中不同類型對流天氣和MCS形成發展特征,并初步解釋對流天氣成因。
1 強對流天氣特征
分析自動氣象站及災情資料可知,在江淮氣旋形成發展階段,短時強降水(3 h降水量≥50 mm)、對流大風(瞬時極大風速≥17.2 m·s-1,需滿足雷達組合反射率因子≥40 dBz,以下大風均指對流大風)和冰雹(災情信息結合雷達資料,組合反射率因子≥60 dBz)天氣均有出現(圖1a~1c),影響時間近24 h,且各類對流天氣的時空分布存在差異。

圖1 2019年4月8日20時至9日20時逐6 h(a)大風、(b)短時強降水、(c)冰雹位置分布和(d)河南南部Q8233自動氣象站8日21時至9日20時逐小時降水量演變(圖1a中“·、+、-、o”分別表示20—02、02—08、08—14、14—20時大風位置;圖1b中時間標記同圖1a,天氣類型為短時強降水,矩形框R1、R2表示24 h降水量≥100 mm的主要區域;圖1c中時間標記同圖1a,天氣類型為冰雹)Fig.1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a) gale,(b) short-time heavy precipitation,(c) hail every six hours from 20:00 BT 8 to 20:00 BT 9 April 2019 and (d) the hourly rainfall evolution diagram of No.Q8233 automatic weather station in southern Henan from 21:00 BT 8 to 20:00 BT 9 April 2019(“·,+,-,o” in Fig.1a represent gale location in 20:00-02:00 BT, 02:00-08:00 BT, 08:00-14:00 BT,14:00-20:00 BT; time markers in Fig.1b are same as those in Fig.1a, weather type is short-time severe precipitation, and rectangle represents the region with 24 h precipitation ≥100 mm; time markers in Fig.1c are same as those in Fig.1a, severe weather type is hail)
大風主要出現在江淮氣旋發展階段,自西向東影響東長江中下游及江南北部地區,51個區域自動氣象站極大風速超過25 m·s-1,從范圍和強度看,此次大風過程符合我國Derecho事件(陳曉欣等,2022)的特征。此外,主要大風區與短時強降水區不重疊,表明產生大風與短時強降水的對流系統不同。
兩條不同走向的強降水雨帶R1、R2分別出現在江淮氣旋形成及發展階段,其中R1長度明顯大于R2。兩條雨帶上均出現大暴雨,其中R1上局部降水量達150 mm,小時降水強度達40 mm·h-1,連續4個時次的小時降水強度超過20 mm·h-1(圖1d),這在春季江淮地區并不多見。
此外,零散分布的冰雹主要出現在8日夜間鄂西南山區及江漢平原西部地區。
2 中尺度對流系統演變特征
中尺度對流系統是雷暴大風、冰雹、短時強降水天氣的直接制造者。根據雷達觀測的中尺度對流系統形態演變特征分三個階段進行分析,其中不同階段的天氣類型有所不同。
2.1 離散線狀對流階段
8日20時至9日00時,鄂西南至豫南一帶有東北—西南走向的離散線狀對流發展,主要產生局地冰雹、大風天氣。
8日20時,鄂西南山區有局地強風暴發展,向東北方向移動。隨鄂西南風暴進入江漢平原,以及鄂東北一帶風暴發展,多個零散分布的對流風暴構成一條結構松散的線狀對流線(圖2a)向東偏北移動。這種結構的風暴也稱為斷裂線狀MCS(Gallus et al,2008),一般出現在線狀MCS初期階段,其中鄂西南山區局地對流具有強雹暴特征,組合反射率因子達60 dBz,災情調查表明該區域出現直徑超過2 cm的地面降雹且伴有大風。
2.2 人字形對流階段
9日00—08時,離散線狀MCS發展為具有冷暖鋒結構的人字形對流線,其中暖鋒擾動TL/AS類MCS發展旺盛,因對流線沿自身走向移動的列車效應導致短時強降水發展,后期冷鋒擾動TS類MCS發展并產生大風。
00時后,離散對流線南段移出鄂西南后,由東北西南走向轉為近南北走向,而北段對流線走向維持不變, 01時整個對流線呈人字形(圖2b),且風暴單體通過合并相互連接,結構趨于完整。人字形對流常由氣旋擾動產生(易笑園等,2011;梁建宇和孫建華,2012),其中兩條對流線L1、L2分別對應冷、暖鋒式擾動,對流模態特征及天氣不同。對流線L2北側為大片層狀云降水,南側有不斷有45~55 dBz的雷暴新生發展,原地維持近5 h,因對流線沿自身走向移動而產生明顯的列車效應,屬TL/AS類MCS模態,對應短時強降水雨帶R1;而對流線L1快速東移逐漸北收,05時移至鄂東北已發展出弓形回波結構,對流移向幾乎垂直于其走向,屬 TS類MCS模態(圖2c),主要產生大風天氣。
2.3 S形渦旋對流階段
9日08—20時,人字形對流線在江淮地區演變成S形渦旋對流線,其中冷鋒TS類MCS發展,東移南壓影響長江中下游地區,產生大范圍大風、局地短時強降水及冰雹天氣,而暖鋒TL/AS類MCS上列車效應不明顯,強降水減弱。
與人字形回波結構類似, S形渦旋對流由對流線L1、L2共同構成,然氣旋性彎曲結構更明顯,且L1后部弱回波區(缺口)擴大,整個尺度大于人字形回波(圖2d)。這種S形結構對應強度較強的渦旋環流,氣旋后部偏北氣流的侵入導致出現回波缺口(吳濤等,2017)。
冷鋒對流線上不同位置的對流模態不同,導致產生的對流天氣不同。其中冷鋒中北部對流線L1維持TS類MCS模態,快速東移中導致與L2的連接斷開,在長江中下游地區產生大范圍的偏西大風(圖2e)。而這一階段前期,L1后部的對流線呈近東西走向(圖2d),表現出TL/AS類MCS模態特征,對應短時強降水雨帶R2,后期加快南壓,轉換為東北—西南走向的TS類MCS(圖2f),產生大風和局地冰雹。

圖2 2019年4月8日21時至9日16時雷達組合反射率因子演變(三角形表示冰雹,圓圈表示短時強降水,風桿表示大風;圖2d,2e中虛線表示對流線形狀;圖2c中方框表示列車效應區域,箭頭表示對流線移動方向)Fig.2 Evolution of radar composite reflectivity factor from 21:00 BT 8 to 16:00 BT 9 April 2019(Triangles represent hail, circles represent short-time severe precipitation, barbs represent strong wind; dashed lines in Figs.2d, 2e represent convective line pattern; in Fig.2c box represents the area with the train effect, arrow presents the moving direction of convective line)
此外,隨向北的氣旋性運動加強,暖鋒對流線L2由直線型轉為向北凸起的弧狀。由于風暴單體移向不再平行于對流線,列車效應消失,短時強降水逐漸減弱。
2.4 不同類型天氣風暴的垂直結構
分析反射率因子垂直剖面可知,產生不同類型天氣(冰雹、短時強降水、大風)風暴的強度和結構有明顯區別。
從對流發展強度看,離散線狀階段雹暴的強度最強,55 dBz反射率因子的頂部超過-20℃高度(8日20時宜昌探空顯示,-20℃高度約為7.5 km)(圖3a),風暴體顯著傾斜,表明雹暴內部上升運動劇烈,屬超級單體強雹暴(恩施雷達徑向速度圖中有中氣旋特征,圖略)。人字形階段,對流線L2上短時強降水風暴的強度明顯弱于雹暴,呈直立結構,多個風暴單體沿西南—東北方向排列且高度升高(圖3b)。而對流線L1產生大風的弓形回波后部有大片層狀云降水回波(圖3c),是TS類MCS的典型結構特征。值得注意的是,與冰雹、短時強降水相比,沿弓形回波頂點方向的對流發展強度最弱,強回波高度未超過6 km(圖3c),這不同于強烈發展并產生大風的脈沖風暴(俞小鼎等,2006)。

圖3 2019年4月(a)8日21時沿(29.722°N、109.322°E)和(29.440°N、109.761°E)雹暴雷達反射率因子剖面(兩條紅線分別表示0℃、-20℃層高度),(b)9日05時沿(31.799°N、114.863°E)和(32.580°N、116.398°E)短時強降水風暴雷達反射率因子剖面,(c)9日12時沿(31.824°N、119.113°E)和(31.597°N、120.722°E)弓形回波風暴雷達反射率因子剖面Fig.3 Vertical profile of radar reflectivity factor of (a) hail storm along (29.722°N, 109.322°E) to(29.440°N, 109.761°E) at 21:00 BT 8 April (The two red lines respectively represent the height of 0℃, -20℃ level); (b) short-term severe precipitation along (31.799°N, 114.863°E) to (32.580°N, 116.398°E) at 05:00 BT 9 April;(c) bow-echo storm along (31.824°N, 119.113°E) to (31.597°N, 120.722°E) at 12:00 BT 9 April 2019
3 江淮氣旋形成發展成因
3.1 大尺度天氣系統作用
由大尺度天氣形勢分析可知,江淮氣旋形成發展是大氣斜壓發展的結果,與高空槽、西南渦暖倒槽及北方高壓有密切關系。在高空槽東移形勢下,西南渦前側低層暖倒槽切變線發展,與北方高壓結合部有明顯鋒區形成,且高壓底部小股冷空氣侵入暖倒槽,隨高空槽東移,強斜壓性氣旋在倒槽切變線中形成發展。
8日20時,有利于江淮氣旋形成的大尺度形勢場已建立。高空圖上(圖4a,4b),500 hPa南支槽與北支槽接近于同位相疊加,冷平流有利于低槽加深,我國中東部地區受深厚高壓脊控制,脊后西南急流深厚且低層暖平流明顯。925~850 hPa,西南低渦前側暖式切變線控制江淮地區(圖4c),與北方高壓之間的溫度等值線密集,高壓底部小股東北冷空氣侵入暖式切變線西段(圖4d)。地面圖上(圖5a)華北小股冷空氣沿太行山東側侵入暖倒槽。8日夜間,隨南支槽緩慢東移,西南渦暖倒槽切變線發展,同時冷空氣進一步侵入暖倒槽產生氣旋性擾動。

圖4 2019年4月8日20時(a)500 hPa,(b)700 hPa,(c)850 hPa,(d)925 hPa高空天氣圖(棕色等值線表示位勢高度,間距4 dagpm;紅色等值線表示溫度,間距4℃;棕色粗實線表示槽線;雙細線表示切變線;D表示西南渦,G表示北方高壓)Fig.4 (a) 500 hPa,(b) 700 hPa, (c) 850 hPa, (d) 925 hPa synoptic chart at 20:00 BT 8 April 2019 (Brown isolines represent geopotential height with 4 dagpm interval, red isolines represent temperature with 4℃ interval, thick solid brown lines represent high trough, double thin lines represent shear line, D represents southwest vortex and G represents high pressure in North China)
9日08時,南支槽仍位于四川盆地,而北支槽東移至江淮地區,強斜壓性江淮氣旋形成,海平面氣壓場上有1002 hPa的閉合等值線區域形成(圖5b)。

圖5 2019年4月(a)8日20時和(b)9日08時地面圖(等值線表示海平面氣壓,間隔2 hPa;D表示江淮氣旋,G表示北方高壓;帶箭頭線條表示地面氣流)Fig.5 Surface map (a) at 20:00 BT 8 and (b) 08:00 BT 9 April 2019(Isolines represent sea level pressure with 2 hPa interval, D represents the Jianghuai cyclone, G represents high pressure in North China, and line with arrows represent the surface airflow)
從氣旋動力和熱力垂直結構看(圖6),與氣旋相關的渦度大值區主要位于600 hPa以下,且渦度中心和鋒區均向北明顯傾斜,具有典型溫帶氣旋的強斜壓性特征,預示氣旋將發展(熊秋芬等,2016)。在高空槽引導下江淮氣旋發展并向東北移動,14時位于沿海,而西南渦被氣旋后部的冷空氣填充(圖略)。

圖6 2019年4月9日08時沿117°E方向的江淮氣旋渦度(等值線,單位:10-5 s-1)和假相當位溫(填色)垂直剖面Fig.6 Vertical profile of vorticity (isoline, unit: 10-5 s-1) and pseudo-equivalent potential temperature (colored) in Jianghuai cyclone along 117°E at 08:00 BT 9 April 2019
3.2 中尺度對流系統作用
以上分析表明大尺度天氣形勢對江淮氣旋形成發展的根本作用,實際上江淮氣旋是在中尺度對流活動中形成發展的,中尺度對流系統由β中尺度發展至α中尺度,在空間尺度上已具備影響江淮氣旋的能力。以下分析可知,對流活動使鋒面低層輻合增強,對氣旋形成發展有加強作用。
由9日08時合肥雷達組合反射率和8級以上極大風站點分布圖(圖7)可知,S形渦旋對流線L1位于冷鋒后側,具有明顯弓形結構,所產生的大風遠離氣旋后部的冷空氣大風區,可見對流大風產生的陣風鋒與氣旋冷鋒疊加,明顯增強了低層輻合。在圖12雷達徑向速度圖上,對流區域的水平輻合區從近地層伸展至3 km高度,伴有后部入流急流,低層輻合強度可能大于大尺度天氣系統產生的輻合。從9日05、08、12時雷達圖看(圖2),對流線L1上地面大風的范圍隨弓形回波尺度增大而不斷擴大,表明陣風鋒不斷發展,對應這期間江淮氣旋形成發展。由于輻合使氣旋性渦度加強(朱乾根等,2007),因此陣風鋒的輻合有利于江淮氣旋形成發展。

圖7 2019年4月9日08時合肥雷達0.5°仰角基本反射率因子(填色)疊加地面7級以上大風(瞬時極大風≥13.9 m·s-1)(D表示地面氣旋位置,L1、L2分別表示冷鋒、暖鋒對流線)Fig.7 Superposition diagram of the base reflectivity factor (colored) of Hefei Radar at 0.5° elevation and the max wind speed above 13.9 m·s-1 on the ground at 08:00 BT 9 April 2019(D represents the position of the ground cyclone, L1 and L2 represent the convective lines on the cold front and the warm front, respectively)
4 強對流天氣成因
對比中尺度對流系統與江淮氣旋形成發展過程可知,離散線狀、人字形對流出現在江淮氣旋形成階段(8日20時至9日08時),而S形渦旋對流出現在江淮氣旋發展階段(9日08時之后),兩個階段對流產生的主要天氣類型有明顯區別。以下分析可知,這種區別與江淮氣旋的動力熱力特征以及地形有密切關系。
4.1 西南渦結合山區地形提供有利于鄂西南強冰雹形成的環境場
江淮氣旋形成階段初期,西南渦暖倒槽切變線發展,渦前有大范圍偏南急流(圖8),850 hPa暖脊(圖9)且700 hPa暖平流明顯(圖略),有利于在鄂西南地區建立不穩定層結和強垂直風切變。實況探空分析表明,該地區環境場具有一定到中等強度的不穩定能量和強垂直風切變,有利于強風暴形成。由于8日20時恩施附近雷暴發展,相鄰的宜昌實況探空圖(圖8)上,地面溫度26℃,高于當月的日最高氣溫氣候平均值(22℃),850 hPa與500 hPa溫差為26℃,對流有效位能為1387.6 J·kg-1,K指數為36℃,具有中等強度的不穩定能量。雖然夜間地面溫度降低使對流有效位能下降,但低層暖平流仍可維持層結不穩定。并且500 hPa、700 hPa風速分別達20 m·s-1、16 m·s-1,具有強的深層(0~6 km高度)和低層(0~3 km高度)垂直風切變,考慮到鄂西南位于多山地區,實際的垂直風切變應更強。

圖8 2019年4月8日20時宜昌探空圖Fig.8 Sounding chart of Yichang at 20:00 BT 8 April 2019

圖9 2019年4月8日20時雷達組合反射率因子加850 hPa GFS再分析場(等值線表示溫度,間隔2℃,粗虛線表示切變線,藍色填色區表示組合反射率因子超過30 dBz的區域,填色表示地形高度,D表示西南渦)Fig.9 Superposition diagram of radar composite reflectivity factor and 850 hPa GFS reanalysis field at 20:00 BT 8 April 2019(Isolines represent temperature with interval 2℃, thick dashed lines represent shear line, blue colored represents area with composite reflectivity factor exceeding 30 dBz, colored area represents terrain height, and D represents southwest vortex)
從風暴觸發條件看,發展西南渦前側受地形影響的輻合有利于強風暴觸發。20時850 hPa GFS再分析場上(圖9),西南渦前偏南急流出口位于鄂西南山區,風速輻合明顯。顯然,輻合與地形阻擋有密切關系,并且輻合隨西南渦發展而增強,為風暴提供了抬升觸發條件,導致20時后分散風暴在該區域初生發展。
從強冰雹形成環境條件看,鄂西南溫度層結及山區地形有利于強冰雹形成。8日20時宜昌實況探空圖(圖8)中,0℃度層高度約為4.4 km,濕球0℃層高度約為3.6 km,考慮到鄂西南東部山地海拔高度超過1.0 km,實際濕球0℃層距地面高度小于3 km。合適的0℃度和濕球0℃層高度,不僅有利于冰雹粒子在高空增長,并且由于下落融化時間較短,更容易在地面形成強冰雹(俞小鼎等,2006)。從氣候特征看,湖北冰雹主要出現在西部山區,可能與山區濕球0℃層高度低于平原地區有關。
4.2 氣旋形成階段暖式切變線以及發展階段受南支槽影響的冷式切變線提供有利于風暴列車效應形成的環境場而產生短時強降水
從降水環境場條件看,江淮氣旋形成發展階段,暖區低層水汽和層結不穩定有利于產生較高降水強度。夜間暖鋒強降水對流線L2主要位于河南南部,上游地區的武漢探空圖(圖略)中, 850 hPa比濕為11 g·kg-1,略低于江淮地區短時強降水(小時降水強度≥30 mm·h-1)的氣候閾值13 g·kg-1(郝瑩等,2012),K指數為34℃表明大氣層結不穩定,可通過浮力上升運動向風暴供應水汽從而提高降水強度(孫繼松,2017)。9日白天冷鋒對流線L1東移至長江下游,08時安慶探空圖(圖略)中850 hPa比濕為13 g·kg-1,K指數為39℃,水汽和不穩定均有利于短時強降水生成。
江淮氣旋形成階段,925 hPa暖式切變線發展,冷暖空氣交匯有利于對流線L2發展,其中暖式切變線中西段的中低層風場配置有利于對流線L2出現列車效應,是雨帶R1上大暴雨主要成因之一。分析9日02時GFS再分析場和雷達圖(圖10a,10b)可知,發展的925 hPa暖式切變線附近等溫線密集,兩側均有急流配合,且大尺度分析表明地面冷空氣侵入暖倒槽,斜壓發展有利于對流線L2上加強。受冷高壓底部東北氣流阻擋影響,切變線中西段呈西南—東北走向,且該區域上空一致的700 hPa西南急流平行于切變線走向。由于對流線L2沿切變線組織發展,在強西南引導氣流下風暴單體沿對流線移動、整個對流線沿自身走向移動而產生列車效應,這種列車效應在極端降水個例中較多見(茍阿寧等,2019)。而在氣旋發展階段,強烈渦旋運動使925 hPa暖式切變線大部轉為近東西走向,因700 hPa西南引導氣流不再平行于對流線導致列車效應不明顯,且北抬過程中層結不穩定條件變差,短時強降水減弱消失。
江淮氣旋發展階段前期,受南支槽緩慢東移影響,冷式切變線底部的中低層風場配置也有利于冷鋒對流線L1底部出現列車效應,是雨帶R2上大暴雨主要成因之一。分析08—14時925 hPa、700 hPa風場和雷達圖(圖10c,10d)可知,對流線L1底部位于925 hPa冷式切變線后部,呈近東西走向且南壓不明顯,這可能與南支槽緩慢東移有關。由于南支槽位于氣旋后部,槽前西南急流阻擋氣旋后部西北氣流南下,從而使對流線底部不呈近南北走向,并且因700 hPa高空風平行于對流線,造成對流向偏東移動的列車效應。后期隨冷空氣加強南下,對流線L1底部轉為東北—西南走向,列車效應消失。

圖10 2019年4月9日(a,b)02時、(c,d)08時、(e,f)14時雷達組合反射率因子(填色)疊加GFS再分析場(a,c,e)700 hPa,(b,d,f)925 hPa風場(風羽)和溫度場(等值線,間距2℃)(藍色/紅色粗虛線表示冷鋒/暖鋒切變線,方框表示列車效應出現區域,L1、L2表示對流線)Fig.10 Superposition diagram of radar composite reflectivity factor and GFS reanalysis field of wind (barb) and temperature field lisoline with the 2℃ interval at (a, c, e) 700 hPa, (b, d, f) 925 hPa at (a, b) 02:00 BT, (c, d) 08:00 BT and (e, f) 14:00 BT 9 April 2019 (The blue/red thick dotted lines represent the cold front/warm front shear line, and the boxs show the area with the train effect, L1 and L2 represent convective lines)
4.3 氣旋發展階段冷式切變線提供有利于后部入流急流形成的環境場而產生大范圍對流大風
江淮氣旋發展階段,環境場具有一定到中等強度的不穩定能量和強垂直風切變,且中層偏西風急流與對流線的配置有利于后部入流急流(rear inflow jet,RIJ)形成,從而有利于TS類MCS在長江中下游產生大范圍對流大風。
江淮氣旋隨北支槽東移而發展,主要表現為渦旋環流、冷鋒斜壓性加強以及地面降壓,有利于對流線L1組織發展。從9日08—14時低層風場和溫度場變化(圖10f)看,925~700 hPa西南急流加強北抬,而925 hPa氣旋后部偏北氣流轉為西北氣流,氣旋性環流更加閉合,溫度等值線更密集,冷空氣進一步侵入使得冷鋒鋒區向前凸起,表明大氣斜壓性增強。地面圖上,08—14時氣旋中心海平面氣壓下降(圖略)也表明氣旋發展。發展斜壓氣旋的冷鋒有利于大范圍雷暴形成并組織成線狀外形。
從環境場條件看,冷式切變線前側具有一定到中等強度的不穩定能量和強的垂直風切變,有利于風暴發展。9日08—14時NCEP再分析場對流有效位能CAPE圖上(圖11),冷式切變線前側的CAPE呈北低南高分布,大值區主要位于江南地區,且隨午后地面升溫CAPE最大達1650 J·kg-1。需要指出的是,GFS再分析場低估了長江沿線及北岸地區時段(08—14時)的不穩定狀態,將08時南京探空圖中地面溫度訂正為25℃后,CAPE為145 J·kg-1(圖略)。從垂直風切變看,受冷式切變線前側深厚西南急流影響,0~3 km和0~6 km高度垂直風切變達到中等強度以上,有利于強風暴發展。

圖11 2019年4月9日(a)08 時和(b)14時雷達組合反射率因子(填色)疊加GFS再分析場(風桿表示925 hPa風;等值線表示對流有效位能,間距為100 J·kg-1)Fig.11 Superposition diagram of radar composite reflectivity factor (colored) and GFS reanalysis field at (a) 08:00 BT and (b) 14:00 BT 9 April 2019 (Wind barbs represent 925 hPa wind, isolines represent CAPE with the 100 J·kg-1 interval)
從中低層風場配置及對流動力結構看,中層風向垂直于對流線有利于RIJ形成,而RIJ下降對地面大風及線狀對流維持有重要作用。以上風暴演變分析可知長江沿線一帶的大范圍大風由較弱風暴產生,由此提出大風成因問題。從對流大風形成機制看,除下擊暴流外,動量下傳也是地面大風形成的主要原因之一(王秀明等,2012),Fujita(1978)指出RIJ下降到地面導致了大風。分析對流線L1上弓形回波垂直結構(圖12)可知,RIJ在接近風暴過程中高度呈下降趨勢。結合1.5°、0.5°仰角基本徑向速度圖(圖略)可知,從B點到A點,20 m·s-1大值區高度由1.6 km下降至0.5 km,A點徑向速度基本代表了近地層水平風分量。由于風暴發展不高,對流下沉氣流在A點產生的水平輻散風可能不強,因此A點大風可能主要由RIJ通過對流下沉運動下傳至近地層所造成的,這種高水平動量下降至近地面的現象也出現在2009年6月3日河南颮線過程中(王秀明等,2012)。數值模擬和觀測表明后部入流與中尺度過程密切相關(Weisman,1992;Gallus and Johnson,1995;康紅等,2016),然而其強弱與環境場關系密切。從環境風場(圖10c,10e)來看,對流線上方700 hPa為偏西風急流,風向與對流線的夾角較大,尤其在弓形回波區域,風向幾乎垂直于回波線走向,即與RIJ風向接近一致,風向與對流線的這種配置有利于高動量的環境風卷入風暴內部,從而有利于RIJ形成。

圖12 2019年4月9日10:55以常州雷達為中心(261°,131.5 km)至(0°,0 km)連線上的風暴垂直剖面(a)雷達反射率因子,(b)雷達徑向速度(圖中A位置為相對雷達:261°,27.9 km,海拔高度:0.5 km;B位置為相對雷達:261°,94 km,海拔高度:1.6 km)Fig.12 Vertical profile of windstorm on the line from (261°, 131.5 km) to (0°, 0 km) to Changzhou Radar at 10:55 BT 9 April 2019 (a) reflectivity factor, (b) radial velocity(A: location 261°, 27.9 km to radar; sea level height: 0.5 km; B: location 261°, 94 km to radar; sea level height: 1.6 km)
5 結 論
使用天氣雷達、常規高空地面觀測、地面加密觀測、1°×1° NCEP再分析場資料,分析一次春季江淮氣旋形成發展過程中混合型(冰雹、大風、短時強降水)強對流天氣特征,初步解釋了不同類型對流天氣形成發展的可能原因,結論如下:
江淮氣旋引發的大風、短時強降水、冰雹天氣在時空分布和對流特征上存在差異。局地冰雹主要由氣旋形成階段離散對流線產生,帶狀短時強降水由氣旋形成階段人字形對流線及發展階段S形對流線后部的列車線/鄰接層狀云類MCS產生,大范圍大風主要由江淮氣旋發展階段S形對流線上尾隨層狀云降水類MCS產生。三種天氣類型的風暴中,雹暴強度最強,短時強降水風暴強度次之,弓形回波強度最弱。
江淮氣旋是大尺度天氣系統斜壓發展的結果,中尺度對流活動對氣旋形成發展有加強作用。大尺度天氣系統與高空槽、西南渦暖倒槽及北方高壓有密切關系,在高空槽東移形勢下,西南渦前側低層暖倒槽切變線發展,與北方高壓結合部有明顯鋒區形成,且高壓底部小股冷空氣侵入暖倒槽,隨高空槽東移,強斜壓性氣旋在倒槽切變線中形成發展。大尺度天氣系統演變過程伴有中尺度對流系統活動,對流使冷鋒低層輻合增強,對氣旋形成發展有加強作用。
強對流天氣與江淮氣旋動力熱力場有密切關系。離散線狀、人字形對流線主要位于江淮氣旋形成階段,隨江淮氣旋發展演變成S形渦旋對流線。氣旋形成階段,西南渦結合山區地形提供有利于鄂西南強冰雹形成的環境場,暖式切變線以及發展階段受南支槽影響的冷式切變線,提供有利于風暴列車效應形成的環境場從而產生短時強降水;氣旋發展階段冷式切變線,提供有利于后部入流急流形成的環境場而產生大范圍大風。
致謝:感謝武漢中心氣象臺張家國首席預報員對本文分析提出的指導意見,浙江舟山氣象局趙海林提供的部分雷達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