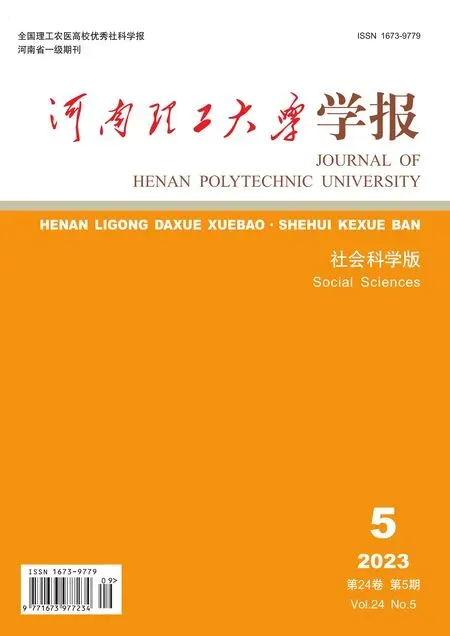論美軍海外軍事基地及人員法律管轄沖突解決模式
羅 恒
(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 政治學院西安校區,陜西 西安 710000)
海外基地部署必然面臨基地、行動部隊及人員法律地位,不同國家法律適用,以及管轄發生沖突的問題,這在美軍部隊長期海外駐軍實踐中多有體現。最直接的表現為駐在國屬地管轄與派遣國屬人管轄間的沖突,如駐日美軍對當地居民實施的暴力犯罪究竟是由美軍軍事法庭還是由駐在國法庭審判?奧本海教授在其著作《國際法》中指出:“作為國際習慣法的一個問題,一個國家的武裝部隊在另一個國家的地位是不確定的。”[1]也就是說,對于武裝部隊及其人員在海外行動時究竟接受派遣國還是駐在國司法管轄并沒有明確、統一的做法。目前,美軍在全球部署超過350個海外軍事基地,與相關駐在國簽訂了超過100余份駐軍地位協定(而無法獲悉)[2]。其在長期軍事基地部署、建設及運行中,依靠本身實力和相關國際法理論就相關問題已形成較為成熟的做法,根據美國與駐在國軍事需求、實力差異圍繞優先管轄、共同管轄時處理等問題形成了不同的管轄分工模式,并隨著國際形勢、駐在國政府和民眾態度的變化進行動態調整,不斷優化與駐在國的管轄分工,維護其軍事利益,兼顧駐在國安全。相關做法和理論具有一定理論研究價值與實踐借鑒意義,也是其他國家解決相關問題的重要參考。
一、問題的提出
海外基地部署于派遣國領域以外,由于各個國家(地區)之間法律制度不盡相同,但各國法律都基于領土主權原則的屬地管轄原則,確立為本國法律適用的基本原則,而一國國民則對本國具有忠誠義務,即便當其位于境外時,也仍受母國法律的約束[3]。軍人作為守護一國安全的特殊公民,其對本國的忠誠義務在范圍上、程度上都會強于普通公民。軍人在海外執行任務時,為保障國家軍事利益的實現,必然需要服從本國軍事指揮人員的命令,而相關命令的基礎則是派遣國法律,進而產生對海外基地及人員的管轄沖突。
(一)根本原因:駐在國領土主權與派遣國軍事需求差異
西方國家在其領域外建立軍事基地的歷史可追溯至古希臘時期,約公元前5世紀,為發展海外商貿、應對波斯入侵和斯巴達爭霸,雅典聯合愛琴海及小亞細亞城邦國家在提洛島上組建了海上軍事同盟——“提洛同盟”。 雅典憑借該軍事同盟在其盟國領土上修建了大量的海外軍事基地,幾乎控制了當時整個愛琴海和地中海,成了名副其實的海上霸主[4]。資本主義萌芽產生后,隨著殖民的擴張,宗主國在被殖民國家建立軍事基地保證其海外軍事力量,實現殖民統治。在舊中國軍事基地擁有治外法權,駐在國法律無法管轄也就無從發生管轄爭議。隨著近代民族國家的產生和興起,二戰后,以《聯合國憲章》為代表的國際法文件確認了國家間主權平等原則,亞非拉等前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獲得民族獨立,新興國家對本國領土主權完整及不受侵犯性訴求使西方國家軍事基地及相關特權面臨前所未有的沖擊,部分新獨立、不結盟國家直接收回部分軍事基地,如第二次中東戰爭結束后,埃及收回了蘇伊士運河所有權,并要求英法駐軍撤軍。但二戰后伴隨著美蘇爭霸“冷戰”的開始及升級,“北約” “華約”組織陣營間面臨的安全、軍事風險客觀存在且不斷升級的背景下,為保證自身及聯盟安全,新的軍事基地部署又重新得以啟動[5]。
如果說在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發展時期西方國家海外基地的部署以武力征服駐在國(地區)為基礎而無須考慮其領土主權的話,那么在二戰后如何協調派遣國需求與駐在國領土主權之間矛盾便成為貫穿基地部署、建設及運用中的重大問題。一方面,對駐在國而言,在法律上,駐在國法律的權威性要求在駐在國領域內沒有法律以外的特權存在。另一方面,派遣國為實現軍事基地效能最大化,滿足基地自身防御、軍事力量前沿部署與運用的最大化,則希望駐在國采取讓渡一定領空、領土、陸地主權,甚至禁止駐在國當地政府與民眾隨意進入軍事基地,并限制因基地部署而引發的民事訴訟,同時對軍事人員在關稅、遵守駐在國當地法律等法律義務上給予一定程度豁免以便部隊獲得最大限度行動自由。可以說,如何認識派遣國設在駐在國軍事基地上的國際法性質,基地內部能不能不適用駐在國法律,或者在多大程度上豁免駐在國法律義務,相關人員在駐在國期間是否享有,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享有駐在國法律屬地管轄豁免是相關法律沖突的直接反映,正是因為駐在國基于領土主權、國家安全及尊嚴的根本原則與派遣國軍事需要存在的矛盾,管轄沖突也就此產生。
(二)直接原因:軍事基地與人員國際法律地位以及駐在國屬地管轄與派遣國屬人管轄上的沖突
既然管轄爭議的本質是派遣國與駐在國在主權問題上的沖突,那么,如何界定軍事基地與人員的國際法律地位,就成為厘清派遣國與駐在國對基地及人員管轄權區分的關鍵所在。在此基礎上,國際主流觀點和做法經歷了從殖民時期“租借地”到近代基于國家主權豁免的“旗國”擬制領土,再到現代“國際地役權”的歷史發展。
在帝國主義殖民時期,軍事基地作為派遣國政府征服駐在國、地區的工具,本身被認為是派遣國主權的一部分,或者強迫租借而形成的主權“讓與”[6]。近代,基于“外國主權者及其財產、外交人員以及外國軍隊人員等在他國領土上享有管轄及執行豁免權”理論,船舶、飛機等被視為派遣國的“浮動領土”,這一理論逐漸擴展至靜態的軍事基地,形成了擬制領土理論,以此為基礎,軍事基地完全適用派遣國本國法律,對軍事基地人員則適用屬人管轄,對基地本身完全豁免管轄就變得理所當然[7]。
二戰后,民族國家對自身主權的重視催生了地役權理論在國際法和軍事基地法律地位上的應用,此理論認為即國家之間根據條約或者協定,為他國利益而對本國領土主權進行的限制和讓渡,這并不改變駐在國對軍事基地的主權,且可根據條約和協定隨時改變。基于此,軍事基地及人員具有一定自治權,其享有的權利來自駐在國的授權,駐在國為維護本國主權和安全,有權對派遣國權利進行限制,對嚴重違反駐在國法律的行為有權予以制止和懲處,甚至終止對派遣國的授權,在發生管轄沖突時,應當由雙方平等協商進行解決。派遣國應當主動維護其國家安全、領土主權完整,以便獲得駐在國及國際社會對軍事基地部署、運行的理解和支持。
如何界定軍事基地的性質是對基地、行動部隊及人員怎樣行使管轄權的基礎。在此基礎上,如何平衡派遣國屬人管轄與駐在國屬地管轄則是關鍵性的問題。基于領土主權完整原則,在任何國家,特別是刑事法領域,屬地管轄是絕對的,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法官Marshall 曾表示:“國家在其領域內之管轄必然是專屬且絕對的。除非國家本身加諸在自己身上外,其領域管轄極不受其他限制。”[8]既然地役權理論已然是現代處理駐軍法律地位問題的通常做法,那么在駐軍地位協定中如何適當限制駐在國屬地管轄權成為刑事管轄安排中的核心問題,即派遣國的法律什么時候可以依據屬人管轄原則對派遣國軍人適用,以及是否可以在軍事基地內實施派遣國本國法律,開展刑事審判甚至刑罰執行等就成為各國駐軍地位協定的核心。
(三)現實原因及表現:國內法與駐在國法律規范之間不一致
每個國家法律原則及規范不盡一致,從實體法看,針對同一行為不同國家之間往往對其法律后果規定不一致甚至完全對立,以《印度尼西亞憲法》為例,其明確規定印度尼西亞國家信仰基礎為至高無上的神道,每一個公民有信仰其自身所信仰宗教的自由[9],該條意味著在印度尼西亞必須信仰一種宗教,這與中國等國家現役軍人不得有宗教信仰的法律規定存在矛盾。可見,如不考慮軍事人員特殊身份及履行國法律義務的實際需求,賦予海外基地及軍事人員部分駐在國法律義務豁免權,而是將軍事基地完全等同于駐在國領土,派遺國軍事人員等同于駐在國領土上的一般公民,則會導致軍事人員在駐在國無法正常履職。另外,軍事基地及人員具有高度敏感性,任何一國當局都不可能輕易將可能掌握本國軍事秘密的人員隨意交由外國偵查、審訊和審判,特別是相關違法行為只在基地內部發生的情況下。這就決定駐在國對派遣國的軍事基地及人員管轄權不能無視派遣國對軍事基地和人員的特殊軍事需求,完全按照屬地管轄原則駐在國進行處理,駐在國必須在管轄問題上向派遣國進行一定讓渡,豁免部分駐在國法律義務,允許軍事基地內部妥當適用派遣國國內法,對軍事人員進行一定程度的駐在國法律義務豁免,否則派遣國軍事人員根本不可能正常履職,軍事基地也不可能發揮應有作用。
(四)相關沖突解決的必要性
管轄沖突的存在實質是派遣國與駐在國領土主權的沖突,其產生了追訴、審判主體的爭議。即相關違法犯罪行為發生時,究竟由派遣國還是駐在國司法機構管轄,如1998年2月3日,美國海軍陸戰隊一架部署在意大利阿維亞諾空軍基地的飛機執行訓練任務時,撞斷了當地一纜車的電纜導致20人死亡。依據《意大利憲法》第112條,刑事案件發生時,檢察官必須立即開展調查并決定是否起訴。但7月13日,法官則依據1951年簽訂的《北大西洋公約締約國關于其軍隊地位的協定》(The NATO Status of Forces Agreement)(以下簡稱《北約部隊協定》),認為美國作為派遣國應行使管轄權而駁回了該案對7名美國軍人的起訴,并指出相關行為屬于職務行為[10]。相關爭議的產生直接引發了派遣國軍事基地及人員地位的爭議,即相關軍事條約是否高于駐在國國內法甚至是憲法,派遣國是否具有優先權或者在何時具有優先權,這一案件中,由意大利抑或美軍軍事法庭進行管轄,在進行追訴、審判時,適用美國《統一軍事法典》抑或意大利本國刑事實體和程序法律就產生了爭議,這為該案的管轄、追訴及審判造成了障礙。
相關問題揭示了解決管轄沖突的必要性,即在面對軍事需要與駐在國主權、派遣國與駐在國管轄爭議時,采取何種標準分配管轄權?相關標準應當包含哪些內容,是否有必要根據危害行為的種類、人員的身份等進行區分等成為國際法和國際軍事法中需要研究的問題。
二、分工管轄模式:《北約部隊地位協定》中管轄權的規定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北約)成立后,在北約國家內部及聯盟外設立了大量的軍事基地,其中僅美國就有超過 2 000 個海外軍事基地和 3 000 個站點[11]。海外軍事基地、駐軍的法律地位必須由國家間條約予以確定,《北約部隊協定》在第七、第八條中分別規定了刑事、民事賠償爭議的管轄原則,被很多西方國家軍事指揮官及學者稱為解決類似管轄爭議的“模板”[12]。該協定關于管轄有以下特點:
(一)相互尊重各成員之間的管轄權
北約組織雖主要由美國發起,但在條文規范上則尊重各國主權,第七條第一款便通過管轄權的一般規定明確了對各成員管轄權的尊重。該款第一項規定“派遣國軍事當局有權在駐在國境內對所有受該國軍事法管轄的人行使派遣國法律賦予其的一切刑事和紀律管轄權”,第二項則規定“駐在國當局對在接受國領土內實施并應受該國法律懲處的罪行,對部隊成員或文職人員及其家屬擁有管轄權”[13]。第一項明確了派遣國當局對所屬部隊及軍事人員的屬人管轄原則,這一點采取了軍事基地是派遣國擬制領土的觀點。第二項規定則尊重了駐在國領土主權,明確了屬地管轄的適用,拋棄了派遣國對軍事基地及人員絕對管轄的治外法權。
條約第七條第三款還設定了締約方均具有管轄權時的情形,即派遣國軍事人員發生僅針對該國財產或安全的犯罪,或僅針對該國軍隊或文職部門的另一名成員,或受撫養人的人身或財產的犯罪,以及因執行公務時的任何作為或不作為引起的罪行,由派遣國軍事當局優先管轄,否則由駐在國當局優先管轄,并明確擁有優先管轄權的一方決定不行使管轄權時,應盡快通知對方當局,體現了締約各方在管轄問題上互相尊重他方在本國領土內軍事基地有限度的自治權,以及在管轄上的協作配合。
(二)以侵犯哪一國安全為主要依據設定刑事案件專屬管轄權
針對屬人管轄與屬地管轄在具體適用上的沖突,在刑事犯罪管轄方面,第七條第二款明確了兩種管轄權,第一種是派遣國的專屬管轄權,即受該國軍事法管轄的人員涉及與派遣國安全有關,且應受派遣國法律處罰,但不受駐在國法律處罰的罪行;第二種是駐在國的專屬管轄權,即派遣國軍事或文職人員及其家屬所犯危害駐在國安全,應受駐在國法律處罰,但不受派遣國國法律處罰有關的罪行。第七條第三款進一步明確相關安全犯罪是指叛國、間諜、竊密等犯罪,并將行為人僅危害派遣國財產或安全的犯罪,或僅針對派遣國的軍事、文職人員或親屬的人身或財產的犯罪以及因執行公務時的任何作為或不作為而引起的犯罪規定為主要由派遣國管轄。可以看出,對于專屬管轄的確定以行為人違反哪一國的法律,危害哪一國的安全為標準。但需要指出的是,盡管條約中充分體現了尊重駐在國基于領土主權的管轄權原則,但實際上,出于美國的強勢地位和北約國家對安全合作的依賴,司法實踐中從未有美軍所屬軍事或文職人員被駐在國當局追訴,普遍的共識是即便外國軍事當局對美軍人員行使管轄權的情況下,駐在國也會將被告移送美軍事法庭接受審判[14]。
對駐在國專屬管轄權對象的分析上,李伯軍教授認為,還存在區分行為人是否為文職人員這一標準,其理由是第七條第二款第一項規定的“受派遣國軍事法管轄人員”,第二項的表述則是“軍事或文職人員及其家屬”。這一看法是存在偏差的,原文中關于派遣國專屬管轄對象表述為“ persons subject to the military law of that State”,第二項關于駐在國專屬管轄對象表述為“members of a force or civilian component and their dependents”,事實上,文職人員亦是一國軍隊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樣受軍事法律管轄。第七條第二款兩項的不同表述必須結合條約全文進行綜合分析,這里不同的表述形式只是為了強調,駐在國管轄權行使對象包括派遣國的所有人員,而非僅僅是具有軍籍的軍事人員,否則第一項關于派遣國專屬管轄權的對象解釋就不包括文職人員,進而得出損害派遣國安全,違反派遣國法律卻不違反駐在國法律的文職人員不能由派遣國專屬管轄,卻可以由駐在國管轄,這顯然是不符合常理的。同時,第七條第二款第二項的表述還可以防止以下情形,即派遣國在軍事基地當地雇傭的,不具有派遣國國籍和軍籍的文職人員在駐在國實施危害駐在國安全的行為,卻不受駐在國和派遣國的懲處。北約部隊多年締約各國行使案件管轄實踐中,也并未以文職人員或軍事人員作為區分管轄的依據,以人的身份區分管轄分工,更多地是依據條約第七條第四款所規定的犯罪人是否為駐在國國民或常住居民,此種情況下一般由駐在國管轄,除非其隸屬于派遣國軍隊,方可由派遣國管轄,但這顯然與其是否為文職人員身份無關,所以第七條第二款不同的表述是為了堵塞法律管轄的漏洞,是法律表述的技術處理,而非以文職人員身份區分管轄。
(三)將民事賠償訴訟管轄權主要交由駐在國行使并規定按照駐在國法律進行裁判
《北約部隊協定》第八條第五款第一項明確規定“對因本國武裝部隊活動引起的索賠,應根據駐在國的法律和條例提出、審議、解決或裁決索賠”,在第七項規定“軍事人員或文職人員不得為執行駐在國對其執行公務而作出的任何判決而提起訴訟”。并在第八條第九款規定“派遣國不得就駐在國法院的民事管轄權要求軍事或文職人員免于接受國法院的管轄”。可見,在因派遣國行動部隊及其人員因職務行為引發的民事賠償訴訟程序上,駐在國當局擁有專屬管轄的權力,在民事訴訟中,《北約部隊協定》維護了駐在國民事法律及民事司法的屬地管轄原則。
(四)明確管轄銜接與司法協作的關系
在同時具有管轄權的情況下,《北約部隊協定》第七條第三款規定了擁有主要權利的國家決定行使管轄權時應盡快通知另一國,第六款明確了派遣國與駐在國相互協助對犯罪進行一切必要的調查,收集和提供證據,扣押、移交與犯罪有關的物品,第八條第六款就民事索賠中規定駐在國對派遣國軍事、文職人員的索賠報告應送交派遣國當局,派遣國當局應毫不拖延地決定是否提供補償金。上述規定有效促成了海外基地在法律適用上可能存在的盲點導致的危害行為無法被懲處這一危險,也促成了派遣國與駐在國在刑事、民事索賠訴訟上的管轄銜接與協作,為保障軍事協作順利開展,整肅部隊紀律、作風創造了法紀基礎。
三、派遣國優先管轄模式:對駐日、駐韓美軍管轄權的分析
二戰、朝鮮戰爭結束后,美軍在日本、韓國部署了大量軍隊,并簽訂了《駐韓美軍地位協定》《日美行政協定》及《日美地位協定》等條約,對駐韓、駐日美軍管轄權做出了規定,相關協定關于管轄權分工的具體內容雖不完全一致,但作為美主導下規定駐軍地位的協定都具備以下特點。
(一)通過協定明文或事實上確立了美軍“治外法權”
在駐日美軍刑事犯罪管轄問題上,1952年簽訂的《日美行政協定》第十七條第二款明確規定,美軍有權對美軍武裝部隊人員、文職人員,及其家屬(除日本籍外)在日本所犯的一切犯法行為行使專屬管轄權,完全排除了日本法律對美軍的適用。在民事賠償上,第十八條第二款明確“各方對于其在日本所有的財產所受損害,如相關損害系由締約他方的武裝人員或文職人員在執行公務中所造成,則對他方放棄一切要求”。否定了日本司法機構針對美軍基地、人員的損害賠償管轄。隨著戰后日本經濟的發展和日本民間反基地斗爭不斷高漲,1960年,日美新的安保條約將駐日美軍地位及管轄問題交由《日美地位協定》決定,《日美地位協定》正式替代《日美行政協定》,該協定28條中規定了“基地的提供與返還”“刑事審判權”及“請求權、民事審判權”等內容,但其不平等性并未有實質性改變。首先,在軍事基地的法律地位上仍然規定了美軍基地及駐日美軍優先地位,第十七條第三款第一項規定美對駐日美軍及親屬為執行公務而作為與不作為導致的犯罪”擁有優先審判權,承認日方擁有對美軍及親屬非因執行公務犯罪的優先審判權[15]。
駐韓美軍基地及人員的法律地位在條約文本上和駐日美軍情況類似。雖然韓國并非二戰戰敗國,但受制于韓國政府因朝韓對立軍事威脅導致的安全需求,以及駐韓美軍的強勢地位注定了駐韓美軍的優先地位。早在1951年簽訂的《韓美行政協定》就明確規定了美軍不經韓方同意有權逮捕有犯法行為的韓國人,并享有處理美國軍人的犯罪權。在美軍基地內即嫌疑人由美軍來處理,在韓境內發生的犯罪行為應美方要求,韓方也應放棄審判權[16]。1966年通過《駐韓美軍地位協定》等條約進一步將相關特權予以固定,成為駐韓美軍在韓國全面介入當地事務,并時常發生嚴重危害韓國地方及民眾安全犯罪的“法律支撐”。有美國國際法專家對此評論道,該協定實際上是韓國讓渡出依據韓國內法管轄駐韓美軍主權的雙邊安排[17]。2001年雙方修改協定后,極少數美軍嚴重刑事犯罪交由韓司法機構進行審理,但美軍都積極主張對相關違法犯罪軍人移送美軍進行管轄。通常情況下除當場被韓方人贓俱獲外,韓國司法機構根本無法在非犯罪現場對美犯罪軍人進行拘捕,更無法在美軍基地內進行調查,這導致大多數案件中的犯罪美軍逍遙法外。如2019年12月一美國軍官夜間外出暴力毆打韓國民眾被韓國警方逮捕后,駐韓美軍司令部公開表示希望將該事件最終處置權移交美軍,后該軍官確實被送回美軍基地[18]。綜上所述,駐韓美軍基地事實上等同于美國海外領土,美軍基地導致的民事損害駐在國管轄權被完全排斥,美軍對所屬人員犯罪管轄上處于絕對的主導地位。
(二)限制駐在國對美軍基地和人員管轄權行使
《日美地位協定》第十七條第三款中,關于兩國優先管轄權的表述,表面上以是否為職務行為及侵犯法益確定管轄,可事實上,美國通過與日本訂立密約形式使日本當局放棄其優先管轄權。根據1997年公開解密的部分資料,美日雙方通過締結密約的形式規定除重大案件外,日方放棄其優先管轄權的行使[19],甚至在1995年沖繩少女被輪奸案中,美軍居然拒絕向日方引渡嫌犯。在民事賠償問題上美軍事基地、行動部隊被完全排除在日司法體系管轄外,因美軍事基地建設、運行中引發的噪音、污水、生化等環境問題以及因演訓任務導致日民眾傷亡、財產損失等爭議時常發生并引發民眾不斷抗議,但日本當地法院卻從未受理并審判針對美軍基地及人員民事賠償訴訟[20]。在駐韓美軍地位上,根據公開披露的《駐韓美軍地位協定》第22條第1至3款,美軍對犯罪行為的優先管轄權不但適用于軍事人員或者文職人員,也適用于軍事、文職人員的親屬。因此,韓國幾乎沒有對駐軍家屬犯罪行為行使過專屬管轄權。
(三)近年來駐在國司法管轄有所擴大
由于駐日、駐韓美軍地位的協定不平等性,加上軍事基地在鬧市、美軍軍紀不嚴等因素,美軍事基地、行動部隊及人員危害駐地環境,實施嚴重犯罪情形引發了駐在國民眾強烈反對。“冷戰”結束后,韓、日對本國安全需求降低,在此背景下,美國不得不與駐在國協商,適當擴大駐在國司法管轄范圍。2001年4月,修訂后的《駐韓美軍地位協定》規定駐韓美軍官兵犯有謀殺、強奸、縱火、毒品走私和其他8種重罪的情況下受到起訴,將被引渡給韓國警方。韓國警方可先行拘留美軍犯罪人員,美軍將在打擊軍人犯罪問題上與韓國進行合作。這實際上明確了韓美雙方在管轄問題上的訴訟程序協作,賦予了駐在國嚴重犯罪的管轄權。駐日美軍地位上,2013年,日美就修改《日美地位協定》中關于駐日美軍士兵及文職人員犯罪的適用規定達成一致。規定將美方審判確定的判決結果、未確定判決、軍隊懲戒處分及不處分的結果告知日政府、受害者及家屬。2016年,日美雙方達成協定,明確美軍“優先審判權”中“受雇于美國政府且為駐日美軍工作的美籍民間人員”的界定,將不具備高度專業技術和知識的人員排除在外,一定程度上減少了美優先審判權的適用對象,擴大日本對相關犯罪司法審判范圍[21]。但顯而易見的是,這并沒有絲毫動搖美在管轄問題上的優先性。
四、駐軍協定共同特點及差異原因
盡管美軍駐北約國家以及駐日、駐韓美軍地位協定關于管轄權的規定存在較多不同之處,但所有的規定都在圍繞如何界定軍事基地性質這一基礎之上,確定刑事、民事損害管轄權等問題。在條約簽訂及后續的發展中都展現出了這樣的共同特點。
(一)派遣國對駐在國領土主權尊重程度都有所提升
二戰后,美蘇爭霸的格局雖然使世界陷入“冷戰”,主要軍事大國紛紛在海外建立軍事基地,但軍事同盟關系以及民族國家意識的覺醒,使得軍事基地完全等同于派遣國殖民地的做法已完全得不到國際法理及輿論的支持,北約國家之間以及部分大國之間基于軍事信任、同盟關系互相派駐軍事力量,通過談判、協商而非武力征服確定軍事基地、駐軍的法律地位并解決管轄等問題。“冷戰”結束后,駐在國安全威脅降低,對于派遣國軍事保護的意愿也有所下降,加之駐在國內反基地運動的興起、推開,駐在國政府有更強烈的動機與派遣國進行協商,限制軍事基地自治權甚至要求取消軍事基地,并加大對派遣國軍隊違法犯罪和民事損害的管轄力度,將直接關系駐在國安全的犯罪納入駐在國本國司法管轄范圍。即使是關于駐韓、駐日美軍地位這些明顯偏向于美方的協定中,其后續修訂也不得不取消最早期對美軍事基地、美軍事人員完全豁免駐在國管轄的規定,在條約文本上承認駐在國對部分案件的管轄權。
(二)通過設定專屬管轄權以平衡派遣國軍事需要與駐在國安全利益
針對危害行為侵犯的對象,不同種類犯罪行為或者民事損害發生的原因,分別為派遣國與駐在國設立專屬管轄權。通常而言,犯罪行為侵害哪一國法益,違反哪一國法律的就由該國進行專屬管轄,反之則由他國管轄。在承認軍事基地、行動部隊一定自治權的前提下,將一般的犯罪行為管轄交由派遣國行使,但嚴重危害駐在國安全和利益的則規定由派遣國進行管轄。對犯罪行為或者民事損害是由職務行為引發的,則主要由派遣國管轄,個人行為則為駐在國進行管轄。專屬管轄權的確立明確了基本的分工原則,平衡了美軍與駐在國關于屬人管轄與屬地管轄之間的需求。
(三)對民事損害爭議管轄多采取靈活性原則
《北約部隊協定》將民事損害賠償爭議一般交由駐在國按照其本國法律進行裁判,駐日、駐韓美軍地位協定則規定了對此類損害賠償的協商補償、集中賠償原則并允許按照駐在國當地標準和法律計算賠償數額。與積極爭奪刑事案件管轄權不同的是,民事管轄行使設定更多處于平衡派遣國因軍事基地部署導致駐在國當地利益受損的考慮,具有鮮明的管轄、法律適用及賠償數額確定上的靈活性。
如前文所述,《北約部隊協定》與駐日、駐韓美軍地位協定相比,存在著顯著的差異,即《北約部隊協定》在形式上體現了軍事盟國之間的平等性,而駐日、駐韓美軍地位協定則顯著的具有不平等性。其直接體現即為《北約部隊協定》中通過相互設定專屬管轄,明確共同管轄時平等的處置方式,而駐日、駐韓美軍的美軍優先管轄設定。對此,有美國學者評價道,相關規定差異實際上體現的是條約締結方是否存在等級制[22]。
二戰后,軍事基地作為完全獨立于駐在國并享有完全自治權的觀點已無法立足,幾乎所有的條約都會宣稱尊重駐在國的領土主權,但實際上,條約本身的“議價權”及實際操作都完全受制于締約方的國家實力和政治情況等諸多因素。從國際政治的角度看,任何國際法都基于國際秩序,現代國際法所依賴的基礎就是二戰后所形成的國際秩序,而國際秩序又直接決定著國家間的價值分配[23]。駐日、駐韓美軍地位協定長期的不平等性體現出日、韓兩國與美國在國家實力上的巨大差異,日本作為二戰戰敗國,在雅爾塔體系下受到更多限制。在冷戰的背景下,華約、北約為代表的東西方世界激烈對抗,韓國、日本也期望通過讓渡本國部分主權換取美國的軍事保護。日本政府對駐日美軍的優先管轄權更是通過不公開的密約被大部分放棄,導致時至今日仍屢禁不止的駐日、駐韓美軍犯罪問題。《北約部隊協定》盡管提供了公平解決管轄權爭議的“模板”,但是實踐中美軍仍然享有超過駐在國法律之上的特權。國際法中主權平等的原則始終未被美軍真正遵守,這應該就是美國主張的所謂“以實力為基礎”在海外基地、行動部隊地位及法律管轄沖突問題上的生動實踐。
五、啟 示
從美國軍事基地部署、運行情況看,單純的派遣國優先模式是不可能得到駐在國支持的,在國際法作用日益增強的今天,也會受到國際社會的反對。而如果將管轄權全部交由駐在國管轄,則顯然會導致對海外基地、人員特殊性的忽視,損害派遣國的軍事利益,所以,單純強調駐在國抑或派遣國優先,甚至完全管轄,顯然是不切實際且有害的,必須在準確把握海外基地國際法地位基礎上合理分配管轄權。
(一)尊重駐在國領土主權,合理設定國際地役權
海外基地的部署必須有助于維護國際秩序和駐在國安全,這是其正當性之所在。國際秩序作為國家依據國際規范采取非暴力方式處理沖突的狀態,由國際規范、主導價值觀和國際制度安排這三個基本要素構成[24]。那么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在部署、運行海外基地上的體現,就是尊重各國主權、領土完整,這一《聯合國憲章》規定的基本規范,倡導主權國家間一律平等,支持、理解各國對于安全的共同需求。在海外基地法律地位上,應當堅持國際地役(《布萊克法律詞典》寫為International regimes)這一理論基礎,即“為保護國際社會整體或者特定國家的權益,由一國或者若干其他國家對某國在部分領土上的主權所加的限制”[25]。即軍事基地是駐在國的領土,而非派遣國的“海外飛地”,只不過為了派遣國軍事需要以及駐在國安全設定了相關限制。
在管轄問題上,即如何合理限制駐在國的屬地管轄權。尊重駐在國主權意味著只有通過協商談判確定海外基地的地位、行動準則等相關條約、制度、法規的安排以最大限度平衡派遣國維護國家安全、利益的需要和駐在國安全需要,才可能使海外基地效能最大限度得以發揮。派遣國與駐在國通過平等協商談判,明確海外基地法律地位是解決部署、運行中行動部隊、人員管轄的先行條件,這其中核心問題就是海外基地自治權及軍事人員部分駐在國法律義務的豁免權,即駐在國需要容忍派遣國自治權情形。海外基地的自治權實際上需要解決的是駐在國法律與派遣國法律在地域適用上的沖突,即什么時候駐在國法律可以對基地內部及行動部隊、人員進行管轄,除此之外均授權基地所屬的軍事或政府當局依照派遣國法律以及其他管理規定進行管理,駐在國不進行干涉。
豁免權通常而言主要針對基地及人員關稅、出入境、基地及周邊海空域限制、駐在國刑事、民事管轄及對象等方面。一方面,需要對豁免人員對象進行界定,可以根據軍事人員身份進行區分,一是絕對豁免管轄對象,這應當按照《維也納外交關系公約》要求,對軍事外交人員、軍事指揮官等予以特別豁免。二是相對豁免管轄原則,即對其他軍隊所屬人員的豁免。三是協議豁免原則,即對軍隊所屬人員的家屬根據談判確定的協議有條件的予以豁免。另一方面,要確定豁免的事由,可參照其他域外國家做法,將行為屬性即是否為職務行為確立為管轄權行使的基礎。
(二)軍隊人員犯罪管轄權:派遣國管轄優先,兼顧駐在國管轄
從各國駐軍協定及通常做法看,軍隊人員實施犯罪行為具有極高的政治、外交敏感性,且刑事案件中通常需要對人員采取強制措施,各國管轄權爭奪的重點即為刑事案件的管轄權。盡管各國協定中的規定不一,但都按照是否為職務行為、犯罪行為種類等設定專屬管轄權。在管轄權分配上,需要明確派遣國國內法屬人管轄優先原則,在此基礎上設定專屬管轄情形。即派遣國所屬部隊人員犯罪行為通常情況下由派遣國司法機關按照派遣國法律行使管轄權,但其個人實施的,嚴重危害駐在國安全、民眾利益且不違反派遣國法律的,以及駐在國政府強烈要求管轄的相關犯罪行為,可考慮交由駐在國司法機關管轄。需要指出的是,相關行為如是在執行職務中或者為執行職務發生的,也不宜交由駐在國司法機構進行管轄,因為職務行為體現的是國家意志,其行為代表的是派遣國。相關因職務行為中的作為或者不作為導致犯罪行為發生的,應當由派遣國與駐在國進行協商賠償等事宜,對行為人的管轄則應當按照自治權的要求由派遣國行使。
(三)民事爭議應以駐在國管轄為主
駐軍地位協定大多將民事爭議的管轄權交由駐在國司法機構按照當地法律進行行使,因相關民事爭議僅涉及損害賠償等問題,并不涉及對軍隊人員的強制措施或其他強制程度較高的調查行為。但相關營地設施作為一國政府的財產具有國際法上豁免權,不應當接受駐在國國內司法機構裁判同樣是共識。前述相關協定在民事賠償的爭議上,大多數針對的主體是從事侵權行為的個人而非軍事基地、行動部隊本身。這意味著該協議的制定必須堅持基地、行動部隊本身不具備接受駐在國司法機構民事訴訟管轄包括被強制執行的原則。發生民事損害需要進行賠償的,可通過協商進行解決。考慮到海外基地的軍事敏感性,原則上派遣國應禁止駐在國地方當局進入基地營區內進行調查取證,確有必要的,可要求駐在國司法機構會同派遣國派駐軍事司法人員協同進行相關調查取證活動。
(四)共同管轄、聯合執法、結果通報等制度是協調管轄沖突的有效手段
對相關犯罪行為及民事損害進行共同管轄、聯合執法目前是較為通行的做法之一,《北約部隊協定》關于共同管轄的規定是關于駐軍地位協定中非常具有創新性的制度,其規定在部分犯罪行為派遣國及駐在國都具備管轄權時通過相關額外的限定來確定優先管轄權[26],該協定確定的標準是犯罪危害的對象、嫌疑人身份等因素。2002年,雙方就《韓美地位協定》達成的修改中,首次明確在對美國軍人罪行進行調查的初期,韓國警方將同美軍開展聯合調查。在調查美軍嫌疑人時,美國政府代表必須在一小時內出席。在美軍嫌疑人被引渡到美國后,如果韓司法機關認為有必要重新傳喚,美方須給予合作,對于犯罪、違紀的美軍處理結果應定期通報韓方,則體現了聯合執法協作及情況通報制度。
可以看出,相關的共同管轄并非是指派遣國與駐在國共同對案件行使審判權,而是在相關案件雙方都具備管轄權時進行的程序上的分工和配合。此種程序的設計有利于最大限度地爭取派遣國的管轄權,同時,尊重駐在國的領土主權。在相關海外基地部署面臨管轄沖突時,可考慮通過程序設計,將涉及駐在國的案件引入共同調查、聯合執法等機制,同時,對處理結果及時通報駐在國,在盡最大可能取得相關案件管轄權的同時,充分體現對駐在國主權、安全的尊重。
(五)通過調整派遣國國內立法協調管轄權沖突
首先,可通過國家立法形式明確海外基地、行動部隊、人員地位問題一般原則。首先要通過海外軍事行動法明確部隊地位一般原則,為談判提供指引、底線支撐。這方面,美國1942年訪問部隊法(The Visiting Forces Act of 1942)對二戰期間在英聯邦國家駐軍地位及相關權利進行了系統性規范,甚至規定可為執行法紀在英國等駐在國執行死刑[27]。美國國防部《外國刑事與民事管轄權》明確指出,美國國防部的政策是在適用的部隊地位協定或其他形式的管轄權允許的范圍內,最大限度地行使美國對國防部人員的管轄權,盡最大可能保護可能受到外國法院刑事審判和外國監獄監禁的國防部人員的權利。如果被捕,在可能的情況下,確保在所有外國司法程序完成之前將這些國防部人員交由美國當局羈押[28]。英國、澳大利亞、加拿大等也通過相關訪問部隊法案,對本國派駐部隊以及外國派遣至本國部隊法律地位、軍事基地周邊管控、軍事合作以及犯罪管轄等問題進行規定。所以,派遣國可通過《海外軍事行動法》等明確海外行動部隊法律地位,明確涉外軍事合作、規范涉外軍事行動。嚴格行動部隊作風紀律,減少違法犯罪行為發生,從根本上減少管轄爭議的發生。
其次,需要明確海外軍事基地造成損害的國家賠償責任。派遣國與駐在國在行政法、民法上可能存在不同的理念、制度,其海外部隊地位協定關于軍事基地、行動部隊及軍事人員在執行職務中造成駐在國及國民人身、財產損失的,通常被認為屬于民事賠償爭議并規定相關訴訟或仲裁程序。但部分派遣國則主張相關行為屬于國家行為,不具備相關民事訴訟的可訴性。對此,派遣國可考慮在相關海外軍事行動法或國家賠償法律中規定相關軍事行為導致的損害由派遣國承擔賠償責任,并在相關駐軍地位協定中排除駐在國司法機構對國家賠償責任的管轄,這既可以減少被駐在國司法機關民事訴訟管轄的可能性,也有助于派遣國爭取主動權,維護派遣國軍隊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