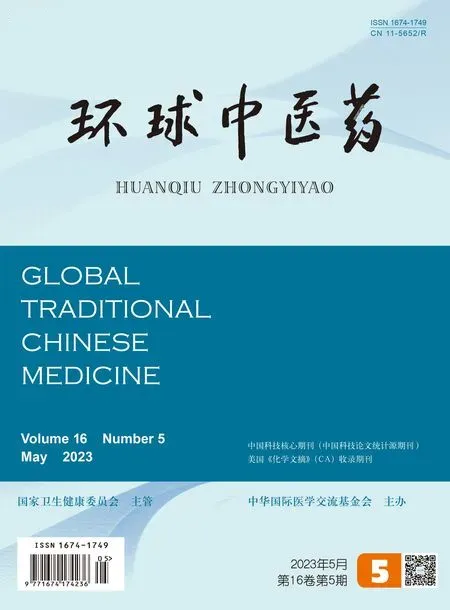淺析傅青主與張錫純診療倒經之異同
陳銀婷 楊燕賢
倒經,亦稱為“逆經”“經行吐衄”,指每逢經行前后,或正值經期,出現周期性的吐血或衄血者。癥狀為每次月經前1~2日,或正值經期,亦可在經凈時,出現吐血或衄血,多伴月經量少,甚則無月經,并且連續2個月經周期以上[1]。現代醫學認為本病與“子宮內膜異位癥”及“代償性月經”密切相關。西醫多采用期待療法、激素療法、止血療法、手術療法等治療手段,但其有療程長、副作用大、易復發等缺點[2]。中醫藥治療倒經具有一定優勢,通過辨證施治,調達臟腑經絡,可達到吐衄血止、月經規律的奇效,且不易復發。
“經行吐衄”一詞最早出現于清代《醫宗金鑒》。清代諸多醫家對此病各有獨特的論述,其中傅青主及張錫純兩位醫家的見解最具有代表性。傅青主,為明末清初著名醫學家,尤精于婦科,其所著《傅青主女科》對近代中醫婦產科學的發展具有深遠的影響;張錫純為清代中西醫匯通派代表人物之一,他對婦產科病的診治有獨特見解,《醫學衷中參西錄》記載的許多治療婦產科疾病的方劑至今仍在臨床上廣泛運用。本文從兩位醫家對本病的病因病機、治療治則及用藥異同進行比較及總結,有利于拓展臨床診療思路,進一步指導臨床工作。
1 病因病機的不同
1.1傅青主認為腎精不足為本,肝郁氣逆為標
傅青主提出倒經病機為“少陰之火急如奔馬,得肝火直沖而上,其勢最捷,反經而為血,亦至便也,正不必肝不藏血,始成吐血之癥”[3]。肝腎乃母子之關系,母病及子,故“肝郁而腎不無繾綣之誼”[3]。他從肝郁氣逆,腎精血虛兩方面闡釋上逆之機。“夫經水出諸腎”[3],腎為經水根本來源,腎水足則經血充足,亦能涵養肝木,氣機條達,月經可按時而下,故腎精不足為本。肝體陰而用陽,肝木失腎水涵養,木郁火生易氣機上逆,腎精血不足易生虛火,腎火借肝氣順勢上沖,血隨火氣升至口鼻出而生吐衄,血不下行而經量少或閉經,故肝郁為標。傅青主認為“反復顛倒,未免太傷腎氣”[3],反復吐衄,肝腎火旺,腎精血虧虛更甚。除外,他還指明“肝木不舒,必下克脾土”[3],肝風火旺,更乘脾土,脾失運化,后天不濟先天,加重腎精血虛損之勢。因此傅青主強調腎虛為本,肝郁為標,同時顧護脾胃,正謂“見肝之病,知肝傳脾,當先實脾”,既要明察病機之根本,也應已病防變,順肝補腎兼健脾,且健脾可加強補腎之力,以達氣順血止衄除之效。
此外傅青主還強調倒經應該與內科吐血相互鑒別。他認為經行吐血是因為臟腑功能失調而致血隨氣逆,內科吐血則與諸經內傷有關。傅青主雖未對倒經進行辨證分型,卻指明應辨清病因再用藥,但若病機均為氣逆所致出血,亦需順氣降逆而止血。
1.2張錫純強調沖氣上逆則生吐衄
張錫純定義沖脈“在女子與血室實為受胎之處”[4],主宰女性生殖功能,故首推從沖脈論治倒經,以沖氣上逆為主要病機。經脈證合參后他對倒經有以下辨證:
1.2.1 胃虛不降,腎失固攝,沖氣上逆 沖脈與陽明胃及少陰腎關系密切,“其脈上隸陽明,下連少陰”[4],故張錫純從胃腎闡述沖氣上逆的病機,一方面,沖脈隸屬陽明,陽明乃多氣多血之經,陽明胃經不僅生化氣血為月經提供物質基礎,同時“胃氣息息下行為順”[4],胃氣下降方可鎮攝沖氣,使氣血循經而行,故“陽明胃虛,其氣化不能下行以鎮安沖氣”[4]則易生倒經;另一方面,少陰與沖脈相連,若少陰腎固攝失司,“其氣化不能閉藏以收攝沖氣,則沖氣易于上干”[4]。所以兩者皆可致沖氣上逆,一則血隨氣升,則發為經行吐衄,二則沖氣不下行,血液運行失常,易生瘀滯,“下行之路有所壅塞”[4],最終形成虛實夾雜之象。
1.2.2 胸中大氣下陷,胃氣不攝沖氣 張錫純在原文按語部分補充醫案:“曾治一室女,倒經半年不愈,其脈象微弱。投以此湯,服藥后甚覺氣短。再診其脈,微弱益甚。自言素有短氣之病,今則益加重耳。”[4]他通過審脈察癥后推斷胸中的大氣下陷引起氣機逆亂亦可致倒經。“胸中大氣”的概念由張錫純首次提出,并明確解釋胸中大氣就是胸中宗氣[5]。胸中大氣司呼吸,為諸氣綱領,能通過氣化以主持全身之氣機,故當其下陷時,“綱領不振,諸氣之條貫多紊亂”[4]。其所致氣短表現為“呼吸之外氣與內氣不相接續者”[4],他還點明應與氣郁不舒,或氣逆而喘,或寒飲結胸等病因所致氣短相互鑒別。胸中大氣亦是“周身血脈之綱領”[4],當大氣下陷時,無力鼓動氣血運行,故可見脈象微弱。而對于本病張錫純將胃氣視為胸中大氣與沖脈聯系的重要環節。“大氣常充滿于胸中,自能運轉胃氣使之下陷,鎮攝沖氣使之不上沖”[4],胸中大氣可通過調達胃氣的運轉從而促使沖脈之氣運行有常。因此當大氣下陷時,胃氣不下行,沖氣不得鎮攝而上逆,則生倒經。
2 脈象詳略之異
在疾病診療過程中,傅青主從證略脈,而張錫純脈證兼具。因傅青主為明末清初醫家,西學剛傳入國內,尚未對中學造成明顯影響,《傅青主女科》中對倒經的論治多傳承于《內經》等中醫經典,且成書年代是中醫理論體系較為成熟時間,故傅青主略脈象重病證,行文簡潔易懂,追求實用性,不僅為其他醫家參閱,也可供百姓所用。而張錫純生活于清末民初時期,并受時代思潮影響形成了中西醫匯通的學術思想,他主張以中醫經典理論為主,再輔以西醫理論佐證中醫。張錫純闡述中醫理論多征引《內經》《傷寒雜病論》等典籍,受張仲景影響對脈象較為重視,且當時中醫受到西醫的沖擊和質疑,西醫高等教育事業首先發展,張錫純有意培養中醫人才,因此原文論述倒經診療部分不僅理法方藥兼具,且驗案豐富,脈證詳備,寫作具有教材風格,有利于初學者學習及討論。
3 治法方藥的不同
3.1傅青主重視肝腎脾,寓順于補
傅青主著眼于肝腎,兼顧脾胃,寓順于補,“必須于補腎之中,用順氣之法,方用順經湯”[3]。傅青主認為順氣之法內涵有二,一為補益肝腎以順氣,方中用熟地黃甘溫入腎經以補精養血,白芍酸寒入肝以柔肝補血,兩者合用,酸甘化陰,大補肝腎之血;再予當歸與白芍相配,養肝血而解肝郁,牡丹皮清肝瀉火以助降逆之功,以上諸藥合用可達“肝不逆而腎氣自順”[3]之效。二為和血以順氣,黑芥穗引血歸經,使離經之血重回脈中,血歸自氣順,故原文指出:“于補腎調經之中,而引用引血歸經之品,是和血之法,是寓順氣之法也。”[3]方中還加用茯苓、沙參補益脾氣,既可防肝木過度制約脾土,又能補后天之氣助先天之氣。全方用藥性平和,寓順于補,調和氣血,使經血下行為順而吐衄自除。傅青主雖未描述具體煎服法,卻略有提及用藥療程,“一劑而血止,二劑而經順,十劑不再發”[3]。由此可推出,順經湯藥簡力專,一到兩劑藥即可見效,但不應“血止”“經順”立即停藥,恐其有復發之勢,需用足十劑藥,也從側面佐證腎虛為本之病機,故用藥時間較長。
3.2張錫純主張調沖降氣,辨證用藥
張錫純主張調理沖脈來治療倒經,又指明應辨證用藥,“致病之因既不同,用藥者豈可膠柱鼓瑟哉”[4]。
對于胃腎兩虛所致沖氣上逆的倒經,張錫純受陳修園的經驗啟發,選用“麥門冬湯”化裁,該方為《金匱要略》中治療“火逆上氣,咽喉不利”之驗方,原方甘寒清潤,潤肺益胃,張超等[6]基于三陰三陽開闔樞理論分析麥門冬湯有“降陽明、開太陰”之效,故方中麥冬與半夏的用量比例為7∶1,重麥冬涼潤肺以開太陰且制半夏之燥,輕半夏降陽明胃氣逆以又可防滋膩之礙。張錫純經辨證論治后,擬方“加味麥門冬湯”,方中半夏“稟秋金收降之性,故力能下達,為降胃安沖之主藥”[4],因此半夏為君藥;干寸冬、野臺參、大棗大補中氣、生津益胃,通過補益陽明胃氣以攝沖,同時滋陰以防半夏燥性傷陰之弊;半夏與干寸冬改為比例為3∶5,亦是為了加強半夏降逆的功效;又添山藥補益腎氣以斂沖;更以芍藥、丹參、桃仁開其下行之路,使沖中之血能歸故道而吐衄自止。張錫純用藥,既重視降逆藥物的調沖作用, 同時也注重補益藥物恢復腎胃兩臟之職[7]。張錫純認為經方含義深遠,并非為一病一證而設,經辨證加減后,可達良效,可見他推崇經方又不拘泥經方。
倒經另一證為胸中大氣下陷,胃氣運轉失常,沖氣失攝而上逆。張錫純以補氣升陷為法,擬方升陷湯,方中以黃芪為君藥,《醫學衷中參西錄》寫道“其補氣之功最優,故推為補藥之長”[4]“又善升氣”[4]。他還運用西學之理闡明黃芪的藥性,“人之呼吸,亦須臾不能離氧氣”[4],而胸中大氣通過肺之呼吸與外界清氣相通,黃芪“其質輕松,中含氧氣,與胸中大氣有同氣相求之妙用”[4],故重用之。還需加用柴胡與升麻引經恢復大氣的升提,“柴胡為少陽之藥,能引大氣之陷者自左上升。升麻為陽明之藥,能引大氣之陷者自右上升”[4]。方中加用知母,看似與全方補氣升陷之意無關,實則目的為知母涼潤可制黃芪之燥,使全方藥性平和,得以久服無弊;桔梗為藥中之舟楫,能載諸藥之力上達胸中。
4 用藥原則之同
4.1調經為治本,止血為治標
兩位醫家治法雖然不同,但都認可調經為治本,止血為治標是倒經的治療原則。兩位醫家治療倒經的方劑皆選用藥性純和之品,多為補氣養血、活血調經之藥,無一味止血藥。《傅青主女科》原文曾指出服用順經湯一劑已是血止,但仍繼續服用至十劑,可見“血止”不是停藥指征,“經順”才是達到治療效果。張錫純選用《金匱》麥門冬湯化裁而治倒經,雖無明確道出治療原則,但從其組方用藥可看出調經才是治療目的。在升陷湯的醫案中只提及停藥的時機為“短氣愈”,并無涉及經前吐衄血止,由此看出張錫純亦覺止血為治標,短氣愈、經水按時而下才為治本。
4.2引血歸經,氣血調和
關于氣血關系的理論最早起源于《內經》。《靈樞·五音五味》載道:“今婦人之生,有余于氣,不足于血,以其數脫血也”[8],闡述女子以血為本的生理及氣有余血不足的病理特點。傅青主和張錫純都認為倒經病機以氣機上逆為主,但在治療中加用活血藥可達到引血歸經,調和氣血的奇效。
傅青主寓順氣于和血,《傅青主女科》言:“夫肝之性最急,宜順不宜逆。順則氣安,逆則氣動。血隨氣為行止,氣安則血安,氣動則血動。”[3]傅青主就氣血關系論治倒經病機,肝為剛臟,以血為體,以氣為用,肝血充而血不滯,則肝氣順血自和,月事按時滿溢。若肝氣上逆,血隨氣升,從口鼻而出,則為經行吐衄。對此傅青主不僅用白芍柔肝養血、丹皮清肝活血降逆而平肝順氣,還加入黑芥穗引血歸經。黑芥穗即荊芥穗炭,荊芥最早以“假蘇”出現在《神農本草經》,有“破結聚氣,下瘀血”之功效。而“荊芥”一名始載于《吳普本草》,此后被各朝代所沿用。北宋以前荊芥多以全草入藥,自《本草圖經》提出荊芥穗入藥效果好后,明清亦延續了以荊芥穗為入藥部位,荊芥穗是荊芥植株最頂端的部位,升發之性更強,故其取代全草成為主要的用藥部位。傅青主多將荊芥穗制成炭用,《本草備要》:“治血炒黑用,以黑勝紅也”,荊芥穗炮制成炭,可入血分,他認為:“荊芥穗炭能引血歸經”[3],“通經絡, 則血有歸還之樂。”[3]李姝池等[9]對引血歸經的含義解釋為既可使離經之血, 重回脈中,又能預防離經之血日久成瘀。順經湯中無使用疏肝理氣之藥,蓋疏散之藥偏燥,恐更傷肝陰血加重肝逆之癥,故選用白芍、丹皮養血活血及荊芥穗引血歸經達到氣血調和,經血來潮之效。
張錫純亦重視引血歸經、氣血并調,雖在原文中未明確指出,但在加味麥門冬湯中,張錫純在鎮逆安沖,補腎益胃的基礎上,又增加活血通經藥,此乃因“特是經脈所上行者,固多因沖氣之上干,實亦下行之路,有所壅塞。觀其每至下行之期,而后上行可知也。故又加芍藥、丹參、桃仁以開其下行之路,使至期下行,毫無滯礙”[4]。沖氣上逆可致血不循經,一則部分血液隨沖氣上逆發為吐衄,二則經血下行無力,易停滯成瘀,故有下行之道壅塞的趨勢,需加芍藥、丹參、桃仁活血調經,通暢脈道,令離經之血重回故道,亦有引血歸經之意。《神農本草經》記載芍藥具有“除血痹”“利小便”之效,故芍藥具有活血之功及通利下行之勢,原文中未說明選用白芍或是赤芍,但張錫純在藥物篇中曾言,“至于化瘀血,赤者較優”,故選用赤芍化瘀通經。又言赤芍“與桃仁、紅花同用,則消瘀血”,但此方選用丹參,是因其認為紅花乃“破血之要品”,為瘀血在臟腑者多用,而下行之道壅塞則為經絡之瘀,丹參可化“瘀在經絡者”及“化瘀血之渣滓”,故棄紅花用丹參。張錫純還在方中特地注明桃仁應帶皮尖搗碎,蓋“桃仁不去皮尖者,以其皮赤能入血分,尖乃生發之機,又善通氣分”[4],既活血又可通氣分,與丹參、赤芍合用,亦是引血歸經,氣血同調之意。
5 傅青主與張錫純從不同環節調經
傅青主診療倒經以調理肝腎脾臟腑為主,張錫純辨治倒經主要圍繞調理沖脈為法,兩大理論看似獨立,實則相互聯系。關于月經來潮生理現象的描述首次出現在《黃帝內經》:“二七而天癸至,任脈通,太沖脈盛,月事以時下,故有子。”[10]女子月事能按時而下,有賴于腎氣充盛,沖任奇經通調。《諸病源候論》將月經失調的病因病機歸責于邪氣“客于胞內,傷沖脈、任脈”,顯示出胞宮與沖任二脈在月經病機的重要性。劉完素首次提出婦人不同生理階段應分別從腎、肝、脾論治,為以后朝代醫家提供了理論依據,如李東垣側重脾胃調經,張景岳認為腎主生殖與月經密切相關,葉天士提出“女子以肝為先天”等著名學術觀點。傅青主多受張景岳影響,重視補益腎之精血,亦注重調理肝脾,創制了溫經攝血湯、安老湯、調肝湯等可肝脾腎同治的調經方劑。張錫純看重沖脈,將沖脈冠于奇經之首,他創制的婦科方劑有17首,其中有7首是調理沖脈,如理沖湯、安沖湯、固沖湯等。故可見兩位醫家均是繼承前人理論基礎上,以女子月經生理過程的不同環節作為出發點去論治倒經。傅青主著重于肝脾腎臟功能運轉有常,臟腑氣血調和,沖任方能通暢,月經方能按時來潮。張錫純倡導從沖脈論治倒經是通過調補腎胃兩臟以保沖氣無上逆之虞,既重視了臟腑功能的正常運行,又突出了沖脈奇經在調治月經病的重要性,因此可將張錫純奇經理論視為傅青主臟腑五行理論基礎上的繼承及發揚。
6 總結
傅青主對本病的辨治貫穿了臟腑五行生化的思想,而張錫純則圍繞奇經沖脈的生理病理為要點,指出胃虛不降、腎失固攝,及胸中大氣下陷均可致沖氣上逆。傅青主追求實用性,從證略脈,張錫純受《傷寒論》影響且有教學目的,脈證具備。對于病機及治法,兩位醫家觀點雖不同,但均以調經治本,止血治標為用藥原則,注重引血歸經,調和氣血。張錫純調理奇經需以恢復臟腑功能為前提,故其可視為傅青主臟腑五行理論基礎上的繼承及發揚。
兩位醫家對倒經的論治有所不同,但均能在臨床上取得良效,蓋為辨證施治之功。傅青主重視辨病,指出應與內科吐血鑒別,并根據病因用藥;張錫純則注重辨證,明辨病機再加以用藥。通過精讀兩位醫家的著作,可學習到不同診療思路及臨床經驗,同時也應病證同辨,完善并運用所學辨證體系,抓住本質,方可藥到病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