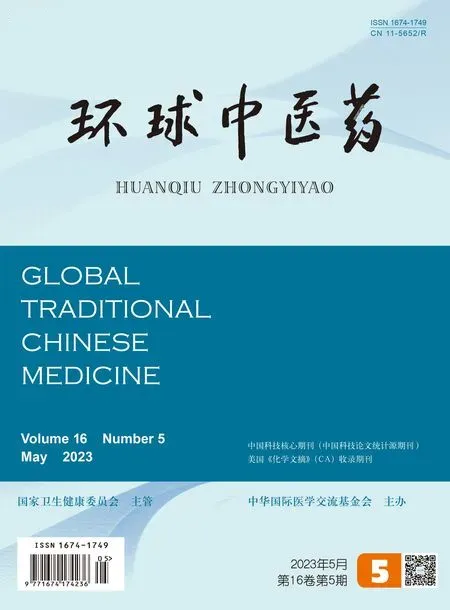范新發陽法復脈治療女性更年期心悸淺析
谷寧飛 徐亞嶺 王翠平 范凌云 蔡增博 張君實 路雯瀟
1 陽法復脈的學術源流
1.1復脈法及源流
“復脈法”之名出自復脈湯,首見于《千金翼方·五藏氣虛》:“主虛勞不足,汗出而悶,脈結心悸,行動如常,不出百日危急者,二十一日死方。”該法源于張仲景和營通脈之代表方——復脈湯即炙甘草湯,原文177條:“傷寒脈結代,心動悸,炙甘草湯主之”被譽為“通陽復脈第一方。”復脈法是以血脈論為基礎,參佐復脈湯及其類方組方用藥,和陰陽、調臟腑、通血脈,恢復機體血脈功能的一種中醫治法,適用于脈道失利(沉微結代),或肢體疼痛,或神志昏昧,甚則厥逆者,其含義深邃,馮慧等[1]臨證時首辨陰陽之不同,隨證加減,根據復脈湯中陰藥、陽藥之用量之多少分為復脈陰法、復脈陽法,還根據五臟陰陽各不同,提出了五臟皆可復脈,非獨心也復脈臟腑法的觀點,其核心在于補益脾胃,中焦旺則氣血盛,陰血足則血脈充,心陽復而血脈通。汪嶸等[2]則根據其病位衛陽、真陽層次不同分為桂枝復脈法、附子復脈法兩類,桂枝復脈法用于病位在上焦,病機為衛陽虧虛,表現為胸悶心悸、脈促等癥候者,以桂枝攻表扶衛陽;附子復脈法用于病位在下焦,病機為真陽不足,表現為腹滿下利、脈沉微等癥候者,以附子救里溫真陽。
1.2陽法復脈現代應用
陽法復脈是以甘溫益氣、辛溫發散而通陽,辛熱之品通血助陽以復脈救心,氣行則血行,陽旺則脈通,實為寒邪傷陽或體弱陽氣虧虛之人所設。后世醫家師仲景之法,辨病變臟腑之異,化裁應用復脈湯,創制多首復脈湯類方,如人參復脈湯、加減復脈湯、一、二、三甲復脈湯、大定風珠、龍牡復脈湯、清燥救肺湯等。一方面繼承了建中培本復脈的核心;另一方面基于臟腑生克制化與血脈的關系,或益胃生金、或滋水生金、或培土抑木、或滋水涵木、或扶正復脈等治法而發展了復脈法的變化與應用,現代廣泛應用于治療心血管疾病、呃逆、咳喘、肝風、眩暈、痙厥、脫證、外感溫病等一系列疾病。
范新發教授用陽法復脈治療更年期女性心悸獲良效,其中陽法不僅僅包括了偏于發越、溫煦、推動作用陽性藥物的使用,還有擇午時服藥助陽、補氣通陽、益氣溫陽、甘溫扶陽、陰中求陽等,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復脈法的臨證應用內涵。
2 范新發從陽虛為本論治女性更年期心悸
2.1陽虛為本為更年期心悸的核心病機
心悸最早由張仲景描述為疾病并提出診療方法,如“寸口脈動而弱……弱則為悸”。《瀕湖脈學》稱脈氣“始于腎,生于胃”,心脈的節律均勻、從容和緩,謂之有神,是由于脾胃之氣不衰和腎氣充沛保證的。西醫更年期綜合征是指婦女在絕經前后由于卵巢功能衰退引起的一系列以自主神經系統功能紊亂為主,伴有神經心理癥狀的一組癥候群[3],認為其發病基礎在于卵巢功能減退、雌激素分泌減少。祖國醫學認為女性更年期心悸是由于這一時期腎氣由盛漸衰,天癸得不到腎氣的滋養而由漸少至衰竭,精血日趨不足,陽氣日漸虛衰致陽常不足,陽氣虛弱,鼓動血脈無力,脈氣不相續接,對心臟失于溫煦而致心臟拘攣,則悸動不安,脈來或結或代,至數不齊[4]。國醫大師劉志明亦認為心腎陽氣的盛衰直接影響心率快慢和脈象虛實[5]。周平安教授認為更年期諸癥以腎精虧虛、陰陽失衡、五臟不安為發病病機,陰陽不平,氣血不和,病及周身,治療時選用二仙湯合四物湯為主方調整陰陽,以平為期為主要治法獲得良效[6]。陳士鐸[7]認為腎精腎氣虧虛基礎上的心腎不交,心陽虛性偏亢是更年期心悸的基本病機。唐麗穎等[8]調查研究發現更年期綜合征患者體質類型以陽虛質比例最高,且發病程度呈中、重度,與女性的生理特點和現代女性承受職場和家庭雙重壓力,熬夜,穿戴暴露過多,加之過多食用寒涼冰凍食物易形成畏寒怕冷、手足不溫等陽虛內寒體質。
范新發教授認為更年期女性心悸的發生根本在于體內臟腑陽氣不足,而在臟腑陽氣之中又格外注意顧護心之陽氣,心陽虧虛,血脈瘀滯,心神失養,則心臟搏動無力致心悸的發生。根據祖國醫學腎與生殖內分泌的內在聯系,腎陽為全身陽氣之根本,具有溫煦、溫通血脈的作用,脈生于營,營屬心,心體陰而用陽[9]。脈行氣血,陰陽相貫,如環無端,陽氣旺則血脈通,氣血充足,陰陽調和,則血脈通利。若腎陽虧虛,命門火衰,溫煦無力,則心陽不足;若心陽不足而累及腎,可見心腎之陽俱虛之證。腎陽虛則虛寒內生,氣血凝滯,沖任失調,影響胞宮的正常功能[10],如《傷寒明理論·悸》記載:“氣虛者,由陽氣內虛,心下空虛,正氣內動而悸也。”
2.2重視肝、脾二臟對心悸發生的影響
由于婦女以血為本,范新發教授臨證非常注重肝、脾二臟對心悸發生的影響。肝藏血而潤心,主疏泄,體陰而用陽,其性主升、主動,條達、升動是陽氣的特性。《四圣心源》曰“肝木即腎水之溫升者也,故肝血溫暖而性升”,肝臟陽氣充沛,能使人體氣機的條達升動之性發揮正常,如肝氣、肝陽不足,木郁不達,氣滯不通,就會氣機不暢則易郁而化火,郁火耗傷津,發為虛熱上擾心神,阻滯血行,氣血郁聚于胸中,使心脈閉阻;出現如憂郁、脅肋疼痛、膽怯、焦慮等陽虛類精神癥狀,與肝寒肝氣失于溫升條達有關。《明醫雜著·醫論》中有“凡心臟得病,必先調其肝腎二臟,腎者心之,肝氣通則心氣和,肝氣滯則心氣乏,此心病先求于肝,清其源也”。若該時期女性肝臟藏泄功能失常,則多出現焦慮抑郁、心煩不寐、心悸等情志不遂肝氣不舒證候,現代研究認為可能與影響下丘腦-垂體-卵巢軸功能而出現女性神經-內分泌的紊亂致圍絕經期的心臟神經官能征有關。
心主血、統血,脾生血,血濡心,心乃形之君,血充則心君自安。脾胃屬中焦,乃后天之本,氣血生化之源,故血充有賴于脾胃功能的正常。正常情況下,胃納脾運,心血充盈,若脾胃功能失職,化源不足,血不養心,必致心脈不利,從而出現驚悸、怔忡之癥,脾虛生化不足,則心失所養而致悸。且脾胃運化不及,水飲停于胃后患者亦有心慌的感覺。若脾胃損傷,脾陽不振,運化無權,水濕停聚,導致痰濕內生,阻滯氣機,阻遏陽氣,脈道不暢,故見心悸氣短,另一方面氣血津液生化乏源,中氣衰弱心氣亦因之不足,心氣不足則推動血運無力,致脈道運行不暢,氣虛不能自護則心悸動而不寧。正如李東垣在《脾胃論》中說:“治肝、心、肺、腎,有余不足,或補或瀉,惟益脾胃之藥為切。”這一觀點也符合婦科“青春期重在補腎,生育期重在調肝,絕經期重在健脾”的一般治療規律。
肝氣疏泄功能失調,肝氣犯脾致脾氣虛弱,運化失司,升降之樞紐,脾的運化有賴于肝的疏泄,肝氣疏泄亦有賴于脾胃之暢達。對臨床更好的理解和運用通陽復脈法,靶向治療不同臟腑、不同部位的陽虛證,做到精準辨治具有指導性意義。
3 范新發陽法復脈治法的臨證用藥特色
范教授在組方治療更年期女性心悸時,補氣通陽而不燥烈,滋陰養血而不柔膩,臨證靈活化裁,注重顧護人體之正氣,兼顧肝脾二臟,組方配伍和平精當,平和之中,又以陽法為主,充分體現了陽法復脈在本病中的運用。
3.1擇午時陽氣最盛時服藥,增強通陽療效
范教授臨證中根據祖國先賢基于“天人合一”思想的子午流注理論,“流者,往也。注者,住也”。在原方記載炙甘草湯日三服的用法基礎上,時辰與經脈相配屬,擇辰(9:00~11:00)、午(11:00~13:00)、酉(17:00~19:00)此三個時辰服藥,正值胃、心、腎經當令。在這三經所配所屬之時辰,該經氣血充盛,功能活動相對旺盛,自身敏感性增強,起增效作用。一日的24 小時從23:00開始,劃分為12個時辰,分別與十二條經脈相對應。人體的氣血按照這一規律在不同的時辰流注到臟腑經絡,循環有序,如環無端,依時灌注,周流不息,至時為盛,過時而衰,盛衰有時,具有節奏性、時相性,與《素問·生氣通天論篇》記載:“平旦人氣生,日中而陽氣隆,日西而陽氣已虛,氣門乃閉”的自然界周期循環的特點相應。根據上述氣血灌注臟腑時間學說,辰時經脈氣血灌注于胃,辰時當令,經行足陽明胃經,此乃多氣多血之經,易于升動,故胃氣旺于辰時,脾胃為后天之本,水谷之海,同時胃為腎之關,胃氣大開,方能起衰,入腎之藥,先入于胃,“欲補腎中之精,先求胃土之旺”,此時服藥正應“清陽乃升”之意。亦可以充分發揮胃土的榮養功能,達滋養腎水之效。午時對應心,一日之中光照度最高的時點[11],人體陽氣最為盛行的時辰,此時氣血旺行。更年期心悸之病位在心,位居上焦屬陽,在五行中屬火,“火曰炎上”,午時陽氣最盛氣血流注心經,迎時而至,心經氣血旺盛,因勢利導,順水推舟,此時服藥能更好的發揮其心陽的溫煦作用,正取復脈定悸,養心安神之意,臨床療效更佳。酉時對應腎,為腎氣所主,腎經當令,經行屬足少陰腎經,此時恰逢陰入陽,陽氣漸弱,陰始旺于陽,兩經交接,陰虛尤甚[12],氣血失和,陰陽失調,此時進藥可糾正陰陽氣血之偏頗。范教授巧妙運用時間學說,擇時服藥恢復臟腑之陰陽平衡,精準靈活,每有桴鼓之效。
3.2陽法復脈基礎方——炙甘草湯的具體組方及應用
范新發教授之“陽法復脈”以炙甘草湯通陽復脈,滋陰養血為基礎。臨證化裁組方炙草復脈湯:炙甘草15 g、桂枝15 g、生姜10 g、人參10 g、苦參10 g、甘松6 g、生地10 g、阿膠烊化8 g、麥冬15 g、火麻仁10 g、大棗25 g,煎藥時兌入黃酒200 mL,水煎服, 辰、午、酉時服藥,日三次。煎煮時用黃酒代替原方中的清酒,因原方中清酒是冬釀接夏而成者,用清酒恐病人依從性差。而黃酒取材方便價廉,其性溫,入肝經,溫服更有補益心氣之功,有助于養心通脈[13]。臨證時根據患者辯證分型特點調整藥物用量、藥味加減或者合用他方等靈活化裁,具有補氣通陽、益氣溫陽、甘溫扶陽、陰中求陽等功效,極大地豐富了陽法復脈的內涵。
3.2.1 補氣通陽固正氣 方中炙甘草、桂枝均15 g,用量最大為君,入心,補中氣以充化源,使后天之本生化有源,固護正氣,正氣存內,邪不可干。則全身氣血恢復,脈中的陽氣自然恢復。炙甘草、人參、甘松、大棗補氣,桂枝、生姜、黃酒在補氣的基礎上通陽,脈中陽氣得以恢復,血液得以溫化,血脈得以暢通,脈搏跳動恢復正常。
3.2.2 益氣溫陽活血通心氣 在炙甘草湯基礎上,若患者癥見:心悸、怕冷、肢涼、乏力、納差、氣短者,為心陽不足,脾氣虛弱者;易人參為黨參10 g,生姜為干姜10 g,與甘松、大棗、桂枝、黃酒等辛溫藥物同用,甘溫益氣,溫陽散寒,溫通血脈,促進血液運行。臨證酌加黃芪、淫羊藿黃芪入肺、脾兩經,既補肺益氣,又培土生金,淫羊藿入腎經,補腎助陽,二者益氣溫陽,金水相生共用;兼有血瘀者,合用丹參飲,丹參30 g、檀香8 g、砂仁6 g活血祛瘀,方中丹參色赤入心,用量最大,活血涼血化瘀而不傷氣血,兼有安神之效,檀香、砂仁溫中行氣,若兼有心神不寧、怔忡驚惕者,加當歸、酸棗仁、柏子仁、遠志、茯神寧心安神。
3.2.3 甘溫扶陽益脾氣 據“陽之動始于溫”“甘與辛合而生陽”的理論,以甘溫辛熱為主,如炙甘草湯用炙甘草、人參、桂枝、生姜、黃酒等辛溫扶陽強心藥,加甘潤滋陰養血之麥冬、生地黃、阿膠、大棗,以期陰陽雙補,心脈通利。方中的芳香之品甘松,味辛、甘、溫,歸脾、胃經,行氣開郁醒脾,《本草綱目》記載其“理元氣、去氣郁、開脾郁、醒脾氣”,有補、和、緩之功效,具有抗心律失常、保護心肌細胞的作用[14]。若患者癥見腹痛喜溫欲按,虛煩心悸不寧、面色無華、手足煩熱、咽干口燥等,病機屬中焦虛寒,肝脾失調者,范教授采用甘溫平和之小建中湯,用桂枝、甘草、生姜、大棗之品,辛甘化陽,酸甘化陰,兼加飴糖大棗甘溫之品補虛緩中,中氣健,化源足,陰陽和,則心悸虛煩自除,取其補其中而生其陽之意。
3.2.4 治其陽者,必調其陰 方中生地、苦參、麥冬、阿膠清熱滋陰養血,生地、麥冬甘養脾健胃,麻仁潤燥,意在通陽復脈同時滋陰養血,氣血雙補,滋陰養血而不凝滯,通陽行血而不傷陰,陰陽氣血復原,陽通脈復,于是脈結代、心動悸之證緩解。滋陰藥物可制約桂枝、生姜、黃酒的燥烈之弊,防止產生副作用。原方基礎上加用苦參,苦參其性苦、寒,合用增強清熱滋陰之效,減少原方中生地用量,現代藥理研究表明,主要活性成分氧化苦參堿具有較好的抗心肌缺血作用,對心臟有正性肌力、減慢心率、抗心律失常作用、保護心肌細胞的作用[15]。
4 病案舉隅
患者,女,49歲,主訴:心悸反復發作、胸悶、氣短2年余,2020年12月18日來診,刻診:心悸,手足不溫、乏力,性急易怒,情緒激動時明顯感脅肋、乳房脹痛,停經3年,納差食少,舌紅,苔薄白,脈結代。靜態心電圖:竇性心律 心率86次/分,室性早搏。根據主證中醫診斷:心悸(陽虛肝郁證),西醫診斷:室性早搏,治以溫補心陽、養心安神。方選炙甘草湯合逍遙散加減,治以益氣溫陽、疏肝理脾,具體處方如下:炙甘草20 g、火麻仁10 g、生地20 g、阿膠烊化10 g、甘松10 g苦參10 g、桂枝10 g、麥冬20 g、白芍10 g、赤芍10 g、柴胡10 g、枳實10 g、瓜蔞10 g、薤白10 g、丹參30 g、延胡索10 g、川楝子10 g、木香8 g、生姜3片、大棗5枚,7劑,日1劑,水煎服,日3服。
2020年12月29日二診:患者訴服藥后心悸發作次數明顯減少,胸悶氣短、脅肋脹痛癥狀緩解,進食量較前增多,手足轉溫,又出現早醒寐差,大便溏,是由于素體陽虛,寒邪內郁,不能外達,氣血運行不暢,血不歸心所致,去原方之瓜蔞、薤白、川楝子、延胡索、木香,加柏子仁10 g、當歸10 g、炒酸棗仁30 g、夜交藤10 g行氣養血安神。
2021年1月6日三診:患者心悸偶有發作,夜寐安,舌紅,苔薄,脈細滑。效不更方,繼以原方10劑服用調理,囑其慎起居,調情志,節飲食。2022年1月28日告知諸癥緩解,心悸未再發作。
按 患者心悸、胸悶、氣短,手足不溫,舌紅,苔薄白,脈結代由于自身氣血不足,陽虛血少,情志不暢所致,主要是陽虛致悸、氣滯不舒擾心造成胸悶、氣短、手足不溫。方中炙甘草、火麻仁、桂枝、阿膠、甘松益心氣,補脾氣; 生地、甘松、苦參清熱,延胡索、丹參、川楝子活血理氣止痛,瓜蔞、薤白通陽泄濁定悸,赤白芍同用疏肝,養血活血祛瘀止痛、枳實、柴胡、木香疏肝行氣解郁、健脾消食,生姜辛溫通陽、大棗甘溫補氣健脾,諸藥合用共奏益氣溫陽、復脈定悸、疏肝解郁止痛之功。服藥后二診又出現早醒寐差,大便溏,系因陽虛寒邪內郁,不能外達,氣血運行不暢,血不歸心所致,故加柏子仁、當歸、酸棗仁、夜交藤行氣養血安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