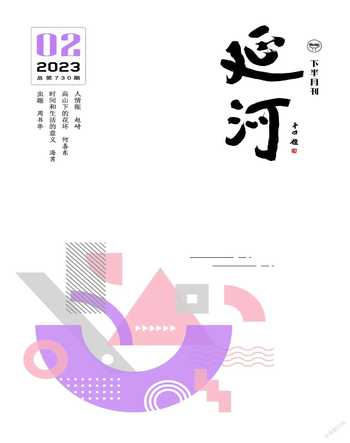落寞老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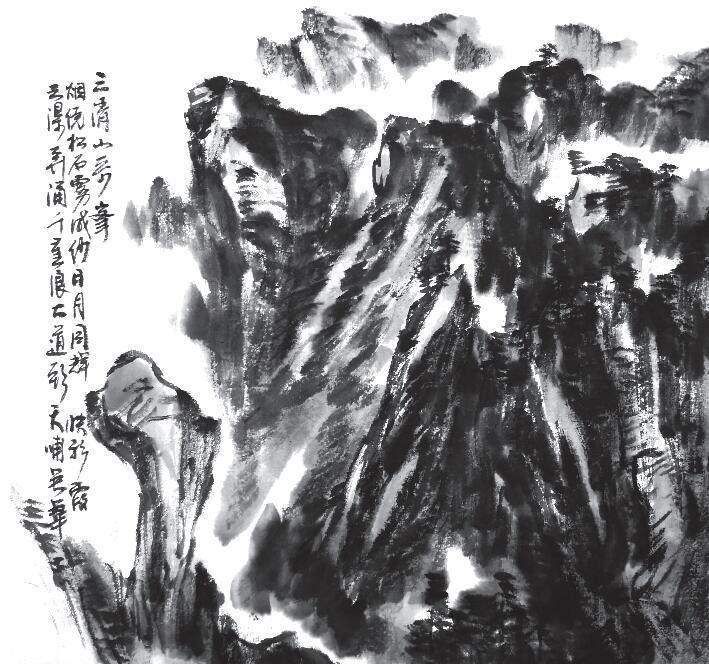
1
“老三,放月假回來呀,一路辛苦了哦。”
“二伯,不辛苦,您提水呢。我幫您提回家里吧。”
“哦,不用了,不用了,就在這里,很近,你趕緊上去回家吧。”
“那行,我馬上就上去,您慢點喲。”
今天是月末,我剛剛放月假從學校回到村里。這是我的村,我出生的村,我生活了十幾年的村。村的名字很古怪,叫作古石村。一看這個名字就知道跟石頭有關。的確,村里到處是大小不一、形狀各異的石頭。
曾經聽爺爺說起過,我們村之所以叫古石村,是因為在村的東北方向有一塊巨石。
我問爺爺:“為什么我們村叫作古石村?”
爺爺對我說:“在很久很久之前的一場暴雨之后,這塊巨石像是獲得神力,瞬間濃煙滾滾,“砰”的一聲,它就從地里面冒了出來。后來巨石的故事傳到了外面,那時候每天都有外地的人來到村里觀看這塊石頭,大家議論紛紛,有的說這是一塊古石,有的說這是一塊奇石,有的說這是一塊怪石……再后來傳著傳著,我們村就被叫成了古石村了。”
巨石是立著的,長約5米,寬約3米,高約10米,遠遠看去如同一幢高聳的大廈矗立在那。任憑日曬雨淋,風吹霜打,電閃雷擊。白晝交換,四季輪回,巨石始終絲毫不動,絲毫不損。
村子坐落在崇山峻嶺之間的大峽谷。村南村北以及村西,三面環山,村東與更高的連綿不斷的山遠遠相望,可謂四面環山。地勢西高東低,所以村里的房子大多坐西朝東,村民也就大多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村的東面有一條最初的,也是唯一的出入村子里的馬路,雖說是一條馬路,實際上是祖輩們用鋤頭挖出來的一條土坯路。馬路從省道接入,從接入口開始,這條馬路就很少有平坦的路段,大多沿著山體左轉右拐,盡量避免直上直下,大多是蜿蜒順勢而上,直到村口的停車場。每次走這條馬路,都會讓人產生不一樣的心情。在春天,尤其是陰雨連綿的時候,黃泥充斥著整個馬路,誰也不愿意這個時候從這里走一趟出遠門。在初夏,馬路已經長滿了青草,青草中也會夾雜開著一些不知名的野花,站在村口那幾塊大石頭上面望去,整條彎彎曲曲的馬路像一條迎風招展的彩帶,彩帶上經常有出門勞作的村民走動,從踩出來的痕跡便可知道,大家在這個時候是非常愿意來馬路上走走的。在深秋,特別是秋高氣爽之際,青草野花早已褪去,留下的只是蕭條的枯草和黃土,然而正是這一片片枯草和黃土卻構成了一條金燦燦的馬路。風嘯之時,漫天翻滾的不知是枯草還是黃土,或許更多的是塵煙滾滾,誰又會在這時候去湊這個熱鬧呢?在寒冬,馬路上一派蕭條,空空蕩蕩,不時傳來幾聲鳥的悲鳴,讓馬路顯得更加寂靜悲涼。
東面除了這條馬路之外,其余都是良田沃土。受地勢的影響,村里大多數的梯田都在村的東面,每到春耕之際,家家戶戶牽著牛扛著犁,對自家或者鄰里的水田進行翻耕。整個村東面的上空不時傳來“嘿”“吁”“嚯”“喲”之聲,那一片片梯田也布滿了忙碌的背影,整個東面熱鬧非凡,一年的希望之種也在這忙碌的時候精心種下。此時的情景在幾個月之后仍會再一次出現,只不過那時就是豐收的喜悅了。
村的西面,也是村的后面,是山。山的名字叫作白麓嶺,這座山是連綿群山的主峰,主峰之下就是我們的村子。我小的時候問過爺爺這座山有多高,爺爺沒有一絲猶豫就告訴了我這座山有三千米。那時候對于三千米的概念并不清晰,總以為高聳入云的這座山應該有三千米,畢竟爺爺不可能說假話騙我。直到我學習地理知識后,在地理教科書中發現,那些高達三千多米的山峰都是著名的山峰,哪怕它是二千多米也是可以查得到的,而我卻怎么也找不到自己村里的白麓嶺。于是從地理老師那里了解到,其實二千多米的山都是比較高的山了,更不用說三千米。雖然村后面的白麓嶺沒有三千米,也沒有二千米,但是幾百米總還是有的。
在山的兩側各有一條從村后延伸而上的山道,一條通往山頂,一條通往山后。通往山頂的這條路,途經村后的公家小山,小山在很久以前全是松樹,常年綠油油的一片,無論從哪一個方向望去都讓人有一種置身于綠色海洋中的感覺,風吹綠浪洶涌。后來不知道什么原因,松林燃起了大火,火海滔天,整個村子被灰蒙蒙的濃煙籠罩了三天三夜。大火之后的第二年,整個小山奇怪地長滿了映山紅,每到春暖花開之際,小山的映山紅也開始綻放。從那時起,每年春天,血紅的映山紅鋪滿整個小山,村子的上空也通通泛紅,如同映山紅開到天空,成了天空之花。順著這條路,也許會艱難地爬上一到兩個小時才會到達山頂,當到達山頂時,一陣陣心曠神怡的感覺便會油然而生。
山頂并非真正的山頂,而是令人意想不到卻能令人心胸開闊的草原。如果是在春夏之際,一定能看到成群結隊的牛羊和翩翩起舞的蝴蝶,更能將云海奇峰,、如畫之景盡收眼底,就像童話世界充滿奇幻卻又如此逼真。不過讓人意外的是在這個如草原般的山頂的中央立有一塊像一座小山的巨石,巨石正前隱約可見一個不大不小的坑。
村的南面和北面各有一條通往鄰村的山路。山路翻過山腰,穿過山谷,連通著南北鄰村。
這次放假回到村里的時間已經接近黃昏。村里已經沒有了落日,只有晚霞散發出的光紅彤彤映在天邊。我是在路過那條由一塊塊長方體石塊鋪成的村中主道時,正巧碰到了正在提水回家的二伯。二伯提的水,正是從村中央那口老井里打出來的。
村里還有四口老井,分別分布在村的東南西北四個方位。南北兩口井,具有季節性。每到秋冬之際,兩口井的井水缺少,稍有干旱之際,井水則會退去,井底也隨之裸露,不能為民所用。村東面的老井,雖常年流水不斷,但因為地勢低洼,其周邊大多是水田,所以其水質不佳,口味略顯苦澀。村西面的老井,地勢是最高的,水量也不是很大,除了臨近的幾戶人家時有打水之外,很少有人去取水。而村中央的老井,雖然和其他四口老井同處一片天,同在一片地,但是有著天壤之別。村中央的老井,井水冬暖夏涼,清甜可口,流水長年不斷,默默地滋養著整個村里的人。它就像是一位偉大無私的母親,用她源源不斷的奶水喂養著她的每一個嬰兒。爺爺曾經告訴我,因為村中央的這口井養育了整個村子,于是老井也就成了它的專用名字。
2
老井最初并不是冬暖夏涼,清甜可口,長流不息。它也渾濁過,苦澀過,斷流過。直到有一天,村里發生的那件事。事后,老井徹底改變,變成了如今的冬暖夏涼,清甜可口,長流不息。
這件事現在很少有人知道,而我也是從爺爺那里得知的。在很久很久以前,那時候村里只有幾戶人家,現在村里的另外四口井還沒有打造出來。那時候白麓嶺側后方也只有少許的幾戶人家。
有一天,村里一位李姓老人突然去世了。李家大兒子李福從外地請來了一位李先生,來給老人尋找墓地。
李福領先生在村里四處尋找上佳的寶地,卻始終沒能如意。先生看向了白麓嶺,對著李福說道:
“李先生,介不介意讓老人家葬在山頂上面。”
“會不會對村里造成不好的影響?”李福擔心地詢問起來。
“有一丁點小影響,但問題不大。”
“此話當真?沒任何影響?能確保沒任何影響嗎?”李福再一次問了起來。
“我以我名聲和性命擔保,絕對沒問題。”李先生斬釘截鐵地說。
李福將信將疑領著手拿著羅盤的李先生走向了白麓嶺山頂。在路過一片竹林時,先生隨手扯下了一根細長的枯死的竹子。時間已經來到傍晚,李福和先生也來到了山頂。先生拿著羅盤在山頂勘察了一番。指著一處說:
“這里正好,位置開闊,前有騰云駕霧,后有巨石如山,這塊巨石就是靠山,左邊長河如游龍,右邊山湖如浩海,這是一個上好的位置。老人家在此,必定造福后代,福延古石村。”
“如此甚好,如此甚好。”李福聽得兩眼發光,于是高興地說道。
此時,李先生半蹲在地,雙手用力,把隨手從路上扯來的細長的枯死的竹子插在了泥土里,并示意讓李福也蹲下來。
“明天早上趕在太陽出來之前,不能太晚了,你喊幾個信得過的人和你一起悄悄地來看看這根竹子有沒有發芽,如果發芽了,說明這塊地已經可以啟用了,你們就做好記號,”李先生輕聲地說。
“好的。”
“記住,一定要把其他人早點喊來,不能太晚。”李先生對李福再三叮囑,接著拿出了一把小鏟子,在這根枯死的竹子旁邊挖出一把泥土用布包好放進了口袋。
第二天早上,李福帶著幾個要好的兄弟來到了昨天插下竹子的地方。讓人奇怪的是竹子沒有發芽,但仔細一看又好像有發過芽的跡象。李福望向了遠方,太陽早已升起。
下了山,回到家。李福把看到的一切說給了李先生。先生很是驚訝:
“怪事,難到我看錯了?還是隔墻有耳,還是……”
“先生是遠近聞名的人,不會看錯吧?”李福問道。
“應該錯不了,走,我們再去后山頂看看。”李福和先生再次來到了山頂。
枯死的竹子依舊插在那里。先生拔出竹子,讓人驚訝的一幕發生了,這根枯死的竹子其地面以下的部位已經開始發芽長根。看到這一幕,李福和先生陷入了沉思。
“快,回家,地面上的芽一定被人動了手腳,趕緊回去。”先生稍作思考后,拉著李福邊走邊說。
回到家,李先生急忙拿出了昨天用布包好的泥土,慌張地問著李福:
“村里用的水哪來的?”
“離這不遠的地方,那有一口井,村里都在那打水。”李福回答道。
“行,快去井那里。”
李福帶著風水先生一路小跑來到井旁。李先生快速解開了包裹好的泥土,右手抓起一把泥土,嘴里念念有詞地把泥土撒到了井里。
“山頂的那塊地肯定是被人動了手腳,我們得趕在他們啟用之前先使用上,所以把泥土撒在井里,希望那塊寶地能在這口大家都在用的井里有所體現。”先生向李福說道。
七天后的晚上,白麓嶺山頂電閃雷鳴,村里人議論紛紛。第二天早上,為了一探究竟,李福帶著幾個年輕人上了山頂。李福幾人來到山頂時發現,昨天夜里電閃雷鳴的地方竟然是七天前他和李先生插那根枯死的竹子的地方。只不過現在這里已經成了一個不大不小的坑,坑的旁邊散落了幾塊奇怪的木板。此時,從白麓嶺另外一個方向也來了一伙匆匆忙忙的村民,他們是隔壁村的。走在最前面的那個臉色蒼白的男人,突然猛地一下跪到坑前,放聲痛哭著:
“爹爹,我對不起您啊,我不應該偷聽別人談論這塊地兒,我不應該偷偷地把那些竹芽拔掉,把您葬在這塊土地,啊……啊……啊……。”
這個時候李福才明白,為什么那根枯死的竹子地下那節發了芽,而地上的那節卻沒有。
在白麓嶺山頂電閃雷鳴那個晚上之后的第三天早上,李福提著桶到井里打了水,在井旁,他蹲下來,扶著桶,探著頭,喝了一口水。他驚訝地發現,井水不再是以前那樣澀,那樣苦。相反的,井水甘甜可口,好像放了糖一樣,井水也第一次從井口慢慢溢了出來。
也就是從那時起這口井變成了如今的冬暖夏涼,清甜可口,長流不息。也就是從那時起白麓嶺山頂上那個不大不小的坑一直到現在都在那里沒有變化,唯一變了的只是坑里長滿了綠油油的野草。
3
我的家離老井只有幾米之隔,家在高處,井在低處。從家向下走十來步石梯,然后再往左在用長長的石塊鋪成的巷道上走五米就來到了老井所在之處。坐在家里的大門檻上便能看到每天來來往往打水的情形。也因此,發生在老井的任何事情我家是最先知曉的。
隨著夏天的到來,老井成了村里最為熱鬧、最有故事的地方。一天當中,早晨和傍晚的老井是最熱鬧也是最繁忙的。每天早晨,太陽剛剛照進大門的時候,村里每家每戶都會有人挑著水桶到老井來打水。來到老井時,大家也習以為常地十分默契地相互打著招呼。
“來啦,來打水了。”
“哎,來了,你也來了啊。”
然后又各自謙讓著讓對方先打水。
“你先打,我不急。”
“不,還是你先打,我比你近。”
雖然來打水的人很多,但大家無須排隊,以村里先遠后近、先急后緩特有的秩序井然有序地打著水,挑著水。
早晨除了大家都在打水挑回家里之外,還有一些人也趕在早晨來洗菜,把一整天的菜都洗干凈。我曾經坐在家門口看到過母親和村里另外幾位大娘洗菜的奇怪一幕。后來我才明白,那可能是作為母親特有的智慧之處。
一天早晨,母親看到村里幾位大娘拿著菜到老井來洗,于是母親也手挎著菜籃,菜籃里放著十幾根紅蘿卜到老井去了。
“幾位大姐也來洗菜了呀。”母親說。
“是啊,妹子,你也來了。”一個大娘應聲答道。
“哎喲,大姐,你這個絲瓜好新鮮,好嫩哦。”母親笑著說。
“哈哈哈,剛剛從地里摘的,家里有沒有呢?沒有的話拿幾根去吃吃。”大娘也笑著說道。
“大姐客氣了,我這里有些紅蘿卜,你也拿些去嘗嘗。”母親接過絲瓜,順手拿了幾根紅蘿卜遞給了大娘。
另外幾位大娘也過來了,手里也拿著菜。
“哎喲,你們家的茄子真好啊。”
“喲,這個四季豆好好哦。”
“喜歡?拿點回去給小孩子嘗嘗。”
“你太客氣了,這怎么好意思呢,來,拿一點豇豆去。”
十幾分鐘后,母親挎著籃子回到了家里。那幾位大娘也笑著離開了老井。我看到了母親菜籃子里的紅蘿卜只剩下了三四根,卻多了一些絲瓜、茄子、四季豆、豇豆,還有一些其他的蔬菜。
夏天傍晚的老井是那些還沒長大的小男孩和他們父親的老井。這個時候,老井沒有了早晨那么多打水的人,也沒有了那么多洗菜的人。于是,忙碌勞累了一整天的男人帶著自家沒長大的小孩,拿著香皂,提著水桶,拿著水盆走向了老井。
有時候放學回到家我會看到這樣一幕,三五個男人領著七八個小男孩來到老井,一刻也不停歇便開始準備洗澡。大男人們說說笑笑地先把水提到老井旁邊那塊地,那塊早晨村里人洗衣服和洗菜的空地,然后把水倒在水盆里,脫去小孩子的衣服和褲子,讓小孩子光著屁股自顧自地玩著水。這個時候小孩子也就沒有了那么多顧忌,相互間耍水玩才是唯一的快樂。
小孩子開始玩耍,大男人們開始洗澡了。
大男人們從老井打起水,提到空地,又把水舉到頭頂,將水直接從頭頂沖下來,放下桶,涂抹香皂,讓泡沫從身上流走。一桶又一桶水從老井打來,一桶又一桶水從頭頂沖下,沖走一天的疲憊也沖走一天的愁緒。十幾分鐘后,大男人們收起水桶、香皂和水盆,領著自家的小孩,相互點起了一根煙,平靜地往家里走去。
4
炎熱夏天的中午,村里處處悶熱。樹上的知了沒有了“吱呀吱呀”的叫聲,房頂的瓦片上熱浪騰騰一片繚繞,分不清楚是瓦片太熱產生了熱浪,還是熱浪讓瓦片沸騰。此時,連圈養的畜生也張著嘴不停地喘息。
每到這個時候,家里圈養的豬也開始昏昏沉沉。父親總會從老井提來水沖在豬圈,讓豬圈的溫度降下來。一天中午,和往日的中午一樣,父親先走進豬圈觀察了家里養的四只雪白的母豬。四只母豬是從二姨家里領養的,領養的時候還是四只白白嫩嫩的小豬仔,在母親的心細照顧之下,如今它們已經長成了白白胖胖重達兩三百斤的母豬了。豬圈里悶熱難耐,父親進去不到一分鐘,衣服已經濕透。四只母豬張著嘴安靜地躺在豬圈里,其中兩只平穩緩慢地喘息著,耳朵有規律地拍打著。另外兩只呼吸急促,一動也不動,父親見狀連忙朝母親喊道:
“哎,你快些來,感覺兩只豬不對勁,快來看看。”
母親飛速跑到豬圈。父親指著呼吸急促一動也不動的兩只豬說:“就是這兩只。”
母親立馬蹲在了這兩只豬的旁邊,一邊雙手輕輕地撫摸著那兩只豬,一邊著急地喊著:“老三老四你們倆怎么了?快醒醒啊。”母親像是在跟人說話一樣。此時,另外兩只豬聽到了母親的聲音,便很快地站了起來走到了母親身邊嗅了嗅。母親又如同跟人交流一般,對這兩只豬說:“老大老二,你們倆看看老三老四是怎么了。”兩只豬好像聽懂了,點了點頭,發出了“哼哼”的聲音,并用豬嘴拱著躺在地上呼吸急促一動不動的那兩只豬。
母親看向了父親,對父親說:“你說這可咋辦啊?”
“應該是中暑了,我去喊人來,不要慌,你先等一下,再看看怎么辦。”
不一會兒,德祥二伯跟著父親來到了豬圈。二伯是村里讀書最多的人,村里很多事情都是他在幫忙處理。二伯走進豬圈,看著兩只躺在地上的豬,擦了擦汗,說道:
“不用擔心,沒事的,天氣太熱了而已,把溫度降下來就好了。先這樣子,你去找一個碗片來,給這兩只豬放放血。”二伯示意父親去找一個破碗來。
父親從家里拿了一個碗遞給了二伯。二伯把碗摔爛,拿起一片鋒利的碎片,走近了那兩只豬。他左手揪住豬的耳朵,右手用碎片輕輕地在豬的耳朵上劃了一個小口,用力擠壓了一下,血,暗紅色的血流了出來。接著和父親說道:
“血出來了,沒事了,行了。去提幾桶水來,把豬槽倒滿,太陽落山的時候把豬圈的屋頂全部淋濕。”
父親送走了二伯,母親從老井提來了水把豬槽加得滿滿的。幾分鐘之后,那兩只豬輕輕地晃了晃腦袋,醒來了。母親欣喜地拍了拍兩只豬的屁股,豬站了起來,緩慢地走到了豬槽邊上。母親臉上露出了歡喜的笑容。
就在我家的那兩只豬醒來后不久,隔壁孝仁叔叔家的豬實在是受不了豬圈里的悶熱,一躍而起,飛出了豬圈,慢悠慢悠地走向了老井。
我坐在大門檻上,看著那只側身零星幾處黑色斑點、屁股肥大的豬正在靠近老井。豬的尾巴左右擺動,屁股也跟著左右搖擺,它加速跑了起來,試圖跨越老井。
“媽,快看,那只豬要跨過老井。”我急忙把母親喊到了大門。
“哎呀,不得了,那只豬要搞壞事。”母親出了大門,想把豬引開。
“啰……啰……啰……”
雖然母親在極力引開那只側身有黑色斑點的自己偷偷飛躍豬圈門的豬,但是在隨著“撲通”一聲之后,豬沒能跨越老井,下半身卻掉進了井里。
“哦豁,豬掉進老井里去了。”我似乎有點高興又有點擔心。父親聽到了我的喊叫聲,也從家里出來,往老井跑去,我也跟著跑了過去。
“孝仁,你們家的豬掉老井了,快點出來啊。”父親邊跑邊喊著。
孝仁叔叔先是驚訝地“啊”了一聲,見父親跟我跑到了井邊,他也匆匆忙忙跑了過來,孝仁叔叔的老婆田妹也跟在后面小跑著。
豬的上半身還搭在井邊,嘴巴不停發出害怕的叫聲,兩前蹄還在慌亂地掙扎。由于兩后蹄已經落水,又是懸在水中沒著地,根本沒法使上勁,接著又是“撲通”一聲,豬翻倒到了水里。此時,這只豬已經在慌亂中完全掉進了水里。
豬在水里驚慌失措地尖叫,豬每尖叫一聲就嗆一口井水,每嗆一口井水就使勁掙扎,越掙扎豬越往下沉。看著豬不停地尖叫,不停地掙扎,孝仁叔叔在井邊不知所措。
人越來越多,已經把老井圍得水泄不通。大家七嘴八舌不停地說著各種方法想把豬撈出老井,可每一個方法都被否定被放棄,總之沒一個方法可行。豬在此時,在被黑壓壓的人群圍觀之下,已經沉到了水里,只露出了半個腦袋。這個時候,二伯也來到老井,他看了看吵鬧的人群,看了看沉在水里的豬,大聲說道:
“我說,大家不要吵了,再吵豬都要過去了。”
大家逐漸安靜了下來,二伯繼續說:
“孝仁,你去找個大網來,快點啊。”
大家竊竊私語,不知二伯用意。
“網來了,網來了。”孝仁叔叔氣喘吁吁抱著一張大網跑來。
“整理一下,把網丟到井里去。”二伯說。
“丟到井里去?”大家一臉疑惑。
“對,丟到井里,快。”
大家你看我我看你。
“哎呀,聽我的,不要裝糊涂。”二伯奪過網,扔到了井里,繼續說:
“把網丟到井里,我們在井邊假裝造勢去打撈這只豬,好讓它鉆進網里,困住它,然后我們把豬和網一起拖上來,再把它抬到豬圈里去。”
“哦哦,原來是這樣子哦,這個法子好,這個法子行得通,看來還得是您啊!”
果然在大家假裝打撈之下,豬很快鉆進了網里,然后四五個男人把豬從井里拖了出來,又抓豬耳朵的抓豬耳朵,拽尾巴的拽尾巴,提網子的提網子,一群人把豬抬進了豬圈。
豬已經出了水,可井里已經被豬屎彌漫,雜物漂浮,渾濁不堪,老井需要徹底的清洗。田妹阿姨回到家里取來了水桶,母親也從家里取來了水桶,并提了一大袋石灰粉。田妹阿姨用手把井里的樹葉、雜草全部清理了出來。母親則站在井邊開始用水桶一桶一桶往外倒水。這個時候,二娘穿著雨衣帶著雨冒拿著瓢盆也加入了清洗老井的隊伍。隨著水一桶一桶、一盆一盆地往外倒。大娘來了,孝仁叔叔來了,四叔來了,我也加入了清洗老井的隊伍。清洗老井隊伍的人數越來越多,多到后來井邊完全不夠站,大家也就只好輪流著打水倒水。大約半個小時后,老井的水已經被往外倒掉了大半。人站在井邊已經夠不著井水,為了盡快把井里的水打完,孝仁叔叔和四叔紛紛跳到井里,先用桶打好水,再把桶往上傳遞給井邊的人,井邊接到水的人再把水倒到外面。等到水慢慢減少時,又用盆舀水裝到桶里,然后再把桶傳給井邊的人倒掉。大約又過了半個小時,直到把瓢也用上時,井里的水已經沒有多少了。接著,孝仁叔叔和四叔從井里爬了上來,田妹阿姨則下到了井里。她用刷子把井刷了幾遍,又用水把井沖洗了幾遍。然后爬出來,換母親下去。母親把井里的污泥用瓢和盆舀出來,遞給了井邊的人。最后把石灰粉撒在了井里的墻壁和死角,終于在村里人的集體勞作下,老井被清洗得干干凈凈。
看著一個個滿身濕透、有氣無力的人兒,田妹阿姨滿是歉意地說:
“今天給大家添麻煩了,真是對不住,今天晚上大家就到我家吃飯吧。”
大娘說:“田妹,你這是說的什么話,老井是大家的老井,怎么能去你家吃飯呢?大伙說是吧?”
“對對對,就是,我們還是趕緊回家換衣服去吧。”
“真是不好意思,那就去我們家里喝茶吧。”田妹阿姨繼續說道。
“喝茶可以,我昨天還想去你家嘗嘗你們的新茶葉,哈哈哈。”二娘打趣道。
“那就這么決定了,大家換好了衣服就來吧。”
“行,就來。”
“要得,要得。”
太陽西落,又到了傍晚。經過幾個小時的蓄水,老井里的水已經恢復到了原來模樣,只不過水面漂浮了幾處石灰粉。
5
自從孝仁叔叔家里的豬掉進老井里之后,離老井近的幾戶人家都把豬圈的門閂高了。從此,再也沒有豬或者牛或者羊等掉進老井。第二年夏天,村里先是遭遇了干旱,之后又是暴雨連連,可以說,村里遭受了前所未有的災難。
那年夏天,我放假回到村里,離上次回村已經三個多月了。此時的父親和母親早在年前就去廣東打工了。我還是傍晚抵達村里,依舊路過老井,這個時候井里的井水已經只剩下不到一半。我把繩子系在水桶上,然后將系了繩子的水桶放到了井里,牽著繩子蕩了蕩水桶,水桶傾斜入水,我順勢把水桶提了上來,打了半桶水。接著,用瓢舀起痛快地喝了起來,水還是那么的清甜可口。
回到家我放下書包,連忙去了爺爺家,爺爺正在吃晚飯。晚飯后和爺爺聊起了今年夏天的天氣和老井。
“爺爺,老井怎么只有一半的水?”我疑惑地問起了爺爺。
“老井有一半的水,已經是我們村的福分了,至少還能勉強有口水喝,其他村連喝水都成問題。”
“為什么會這樣?”
“你可能不知道,今年天氣怪得很,前幾個月沒下半滴雨,天天太陽,村里的小河小溪斷流,連村里的池塘水庫都快要見底了。后來又天天暴雨,房屋都被沖垮好幾間。”
“那村里的莊稼呢?”
“還莊稼,早在干旱開始的時候,村里的年輕人都去廣東打工了,今年的莊稼沒法種,老井的水也沒有多余的流出來。”爺爺望向了村口的方向,長嘆了一口氣,繼續說,“哎,估計以后都很難再種了。”
我沒明白爺爺的意思。
“哦,對了,之前下暴雨的一天晚上,白麓嶺有一處山體滑坡,形成了泥石流,幸好老天保佑,泥石流從村旁邊沖走而沒直接從后山來,否則我們這個村就得被掩埋一半,后果不堪設想。泥石流雖然是從村旁邊過的,就是挨著你們那片李樹林那過的,但是那天晚上太可怕了,差點被嚇死,從來沒遇到過。整個村彌漫著轟隆隆、嘩啦啦、噼里啪啦的混亂的巨響,大家都覺得白麓嶺那里肯定是有妖怪在作怪,哭天喊地冒著暴雨全部摸黑往隔壁村跑,你三爺爺還摔斷了腿,現在還躺著呢,想起來就覺得可怕。第二天早上,我們從隔壁村趕來,在路上看到白麓嶺的半山腰處,崩裂了一個缺口,然后一路泄下來,沿著山溝,沿著那條河道直接沖到很遠。你可以去李樹林那看看,那些泥巴、石頭、樹杈之類的都還在。”
在爺爺的建議下,我打算去看看泥石流沖過的地方。我直接來到了李樹林,映入眼簾的一切讓我目瞪口呆。泥石流所到之處,寸草不生,不堪入目。從缺口處開始,整個山溝全部被泥石流沖過一遍,到村里時,已經有幾十米寬的沖撞痕跡了,我沿著這條幾十米寬的痕跡走去,似乎明白了爺爺那聲哀嘆。一路走去,泥石流沖沒了植被,沖爛了沃土,沖壞了良田,沖垮了水塘,沖毀了路基,也沖散了全村的希望。我來到了村口,泥石流像一把巨扇在此打開,原本此時村口是稻苗綠浪滔滔,一派生機。如今卻是污泥遍布,亂石穿空,雜木橫斜,滿是心酸。
第二年春,在縣政府的主導下,泥石流全部被清除。泥石流沖過的地方,如同一條深深的疤痕,永遠留在了村里。老井也是在第二年春天才開始水流增大,到初夏時才恢復了原來的模樣。
我原本以為隨著夏天的來臨,老井熱鬧的場景也會隨之而來,然而卻只有孤獨的老井在那里安靜地流淌,時有村里的老人來打水,老井,顯得更老更落寞。
或許,老井是在等待下一個春天的到來。
彭昭曙,筆名彭慕之,1993年出生于湖南桂陽。寫小說,現生活于四川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