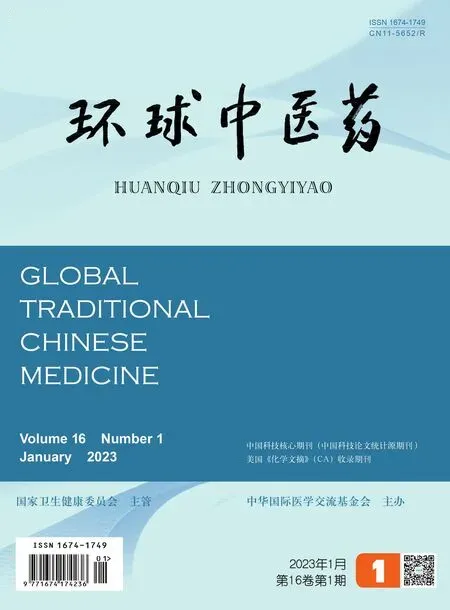“因勢利導”思想在疫病中的應用探討
盧軒禹 盧云
“因勢利導”是指順應事物發展的自然趨勢,向有利的方向引導。因勢利導最早見于《史記·孫子吳起列傳》之“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討論兵家的“道、天、地、將、法”。《黃帝內經》最早將因勢利導思想作為治療原則引入醫學,《靈樞·師傳》言“未有逆而能治之也,夫惟順而已矣”,指出治病應根據疾病之勢,基于正邪交爭的發展趨勢,用巧法以最大程度、最有利地扶正祛邪,達到疾病痊愈的目的[1]。
《素問·六元正紀大論篇》最早載“厲大至,民善暴死”;張仲景經歷“建安紀年以來,猶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傷寒十居其七”后著書《傷寒雜病論》;吳又可親歷崇禎辛巳大疫后撰書《瘟疫論》。有文獻記載從公元前770年至公元1911年間,中國平均四年就有一年發生過疫災,可以毫不夸張地說,疫病推動著中醫學的發展,中醫發展史是一部疫病斗爭史[2]。而“因勢利導”思想一直貫穿在中醫防治疫病的過程中,對于疫病來勢兇猛、傳變迅速、病機復雜的特點,根據邪氣之勢,結合機體的正邪傳變趨勢、因勢利導、扶正祛邪,往往能事半功倍。
1 因病邪性質、位置之勢而利導,巧逐疫邪
《素問·五常政大論篇》王冰注:“夫毒者,皆五行標盛暴烈之氣所為也。”清代何秀山亦云:“疫必有毒。”[3]毒乃邪氣蘊積不散而成,由于疫病邪毒亢盛,較于其他疾病,其病勢更兇猛,侵犯部位更廣泛。故疫病治療應以祛邪為要,以盡早、徹底為度。如吳又可在《溫疫論·注意逐邪勿拘結糞》言:“大凡客邪貴乎早治,乘人氣血未亂,肌肉未消,津液未耗,病人不至危殆,投劑不至掣肘,愈后亦易平復。”《醫宗金鑒·卷二十八》言:“急逐之法,非汗即下,是為病尋出路也。”但因勢利導、驅逐疫邪之法不僅有汗、下,更在“透”與“通”,重在給邪以出路。如中醫名家蒲輔周先生認為:“溫病最怕表氣郁閉,熱不得越;更怕里氣郁結,穢濁阻塞;猶怕熱閉小腸,水道不通,熱遏胸中,大氣不行,以致升降不靈,諸竅閉滯。”熟悉病邪性質,辨清病邪表里上下之勢,順勢“通”“透”,能更快更徹底地逐邪外出。
1.1 透邪外達,上以祛邪
“透”指透散,引邪外出之意,遵循《素問·陰陽應象大論篇》“其高者,因而越之”“其在皮者,汗而發之”的因勢利導治則。對于在表、在上之邪,“透”法能快速徹底地引邪上出。疫病初期,病邪在表,理當透邪出表。治療上依據疫邪寒熱之性,選擇辛溫發散或辛涼清解之法務求迅速透盡疫邪。如《傷寒論》針對寒疫襲表,用麻黃、桂枝、葛根等藥,辛溫開通玄府、透散寒邪。溫病學派用銀翹散、桑菊飲等輕以去實,透邪出表。現代臨床研究表明銀翹散合麻杏石甘湯能降低病毒的載量,明顯縮短H1N1流感病毒感染患者的發熱時間[4]。
同時在疾病過程中,病邪有外散之性,亦應順勢“透”邪外出,不似針對疫邪襲表,重在透邪,而是在清熱、涼血、溫陽等正治之法上稍加辛透之藥,宣開達表之路,由里向外,層層透散,防止閉門留邪。如《傷寒論》301條言“少陰病,始得之,反發熱,脈沉者,麻黃附子細辛湯主之”,寒毒疫邪直入少陰,尚屬表邪,仍有外散之意,但少陰羸弱,不能鼓邪外出,寒主收引,表竅、經脈閉塞,故用附子、細辛溫陽救逆、鼓動陰中之陽,溫通經脈,配伍麻黃辛溫發散,透邪達表而解以防寒疫毒邪繼續傷陽。而熱性疫邪,本有向上之勢,全程都可應用“透”法,祛邪外出,如《素問·六元正紀大論篇》言“火郁發之”,葉天士亦云“戰汗透邪”“入營尤可透熱轉氣”“急急透斑為要”,即言熱入營血都可配合“透”以解邪。張景岳《類經》言:“凡火所居,其有結聚斂伏者,不宜蔽遏,故當因勢而解之,散之,升之,揚之。”《溫病條辨》中清營湯以銀花、連翹透邪出營分,以微汗為度;青蒿鱉甲湯中青蒿引血分郁熱外出。所以,宣透之法可順勢給疫邪開通達表之路,防止邪郁傷正。對于寒疫可配伍麻黃、桂枝、荊芥等辛溫透散之藥,對于熱疫可配伍薄荷、銀花、升麻等辛涼清解之藥。
1.2 通至邪出,下以逐邪
“通”指通暢,有下導邪滯之意,遵循《素問·陰陽應象大論篇》“其下者,引而竭之”“中滿者,瀉之于內”的因勢利導治則。《素問·靈蘭秘典論篇》載“主不明則十二官危,使道閉塞而不通,形乃大傷”,《金匱要略·臟腑經絡先后病脈證》云“五臟元真通暢,人即安和”,所以五臟六腑都以道路及氣機通暢、相互協調為要,若閉塞不暢則功能失用,百病生成。北齊醫家徐之才首發“通可去滯”之言,張子和闡述為“所謂通劑者,流通之謂也。前后不得溲便,宜木通、海金沙、大黃、琥珀、八正散之屬。里急后重,數至圊而不便,宜通因通用”,所以通法中主要以下、利二法導邪下出。現代病理學研究表明傳染病病原體侵入人體后,會激發人體的急性炎癥反應,即以滲出、組織變性、膿性分泌物積聚為主要表現的機體保護措施[5-6]。如果在一定時間內無法抑制病情,滲出或組織被破壞所釋放的細胞因子會介導大量免疫細胞向患側聚集浸潤,并激活細胞內信號轉導途徑,再次激活大量細胞因子與炎性細胞聚集,構成惡性循環,最終形成細胞因子風暴,導致機體嚴重損傷。根據中醫取象比類的思維方式,西理中用,結合局部水腫、瘀血、出血等表現,細胞因子風暴的核心病機是疫病邪毒聚集于內,阻滯氣血,產生濕濁、氣滯、瘀血、痰飲等病理產物,使邪無外出之路,不通而病。故對于疫邪入里,應重視通暢人體氣血運行,用行氣、活血、化痰、消瘀、通絡等法疏通邪滯,再配合下、利等法順勢導下以祛邪。
通至邪出,其一是疏通氣機,防止疫邪聚集,用升降散、三仁湯、小柴胡湯等方疏通氣機,分散疫邪。如葉天士言“通陽不在溫,而在利小便”,利小便并非僅用淡滲利水之藥,而當以溫膽湯或杏、樸、苓等藥,以宣暢三焦氣機為主,使濕與熱之邪分消走散。氣機通暢則津血運行,痰濁、瘀血之邪無以生成。現代藥理研究表明升降散可以抑制細胞間黏附分子-1、核因子-κB p65的過度表達,抑制致炎因子白介素-1等,防止疫邪凝聚,再配伍大黃順勢祛邪下瀉,從而顯著降低流感病毒小鼠肺部炎癥范圍[7]。《宋會要輯稿·恤災》記載臨安疫,“初伏,差醫官給散夏藥。上宣諭曰:‘比聞民間春夏中多是熱疾,如服熱藥及消風散之類,往往害人,唯小柴胡湯為宜。’令醫官揭榜通衢,令人預知。頗聞服此得效,所活者甚眾”[8]。此即疏通人體氣機,以使疫邪有出路,若僅用逐邪之法,往往使邪氣內竄,導致內陷、走黃等。
其二是消除邪結,使邪氣有外散之勢。《瘟疫論》言疫邪侵犯膜原,即是戾氣郁滯三焦。邪氣痼結而無活動之勢,且邪結三焦,故汗、下之法無以祛邪,待疫邪聚集到一定程度便會出現壞證、逆證。故用檳榔、草果、知母等以消除邪結,使疫邪有外散之勢。《神農本草經》載檳榔、草果、知母等藥有“除邪氣”或“主結滯”的功效。現代臨床實踐發現瘀血、痰濁也為邪聚之病理產物,如在新型冠狀病毒肺炎(以下簡稱“新冠肺炎”)疾病過程中,急性炎癥期會有滲出液阻塞于小氣道中,黏稠難以咯出,形成痰結;在細胞因子風暴發生時,會出現彌散性血管內凝血,從而出現瘀血。所以,疫病治療中應辯證論治配伍化痰、消瘀、散結之法,使疫邪松動,可以外散[9]。
其三是利尿通便,順勢祛邪。在疏通氣機,邪結松動有外散之勢后,當順病邪在里之勢,用大黃、芒硝等通腑瀉濁,或以木通、茯苓、澤瀉等利水滲濕,達到快速祛邪下瀉的目的。現代臨床研究表明下法可以讓部分細菌與有害物質大量排出,從而改善腸道菌群,恢復腸黏膜屏障[10]。臨床實踐亦證明“下”“利”之法能提高患者的腸功能,有效改善重癥肺炎的通氣效率,并降低抗生素、激素等藥物的副作用[11-12]。國醫大師陳紹宏教授治療急性細菌性痢疾(疫毒痢)急性期時,用清瘟敗毒飲加大黃以疏通清解、瀉火解毒排邪,其中重用生石膏至180 g,取其辛消邪結,清十二經熱毒以梳理氣機之用,再配合大黃排除疫毒(內毒素和病原體),通至邪出,取得良好療效[13]。
2 因傳變之勢而利導,安正祛邪
疫病起病急驟,傳變迅速,葉天士言“熱病傳變最速”,《瘟疫論》載疫有九傳,所以疫病的辨證論治不僅在見癥辨證、有是證用是藥,還應根據疫病病邪的性質、規律與患者稟賦等多方面因素推測疾病的進展趨勢,用動態、辯證的思維順勢而治,基于疫病的整體趨勢,先安未受邪之地,此即《黃帝內經》“病必傳行”和“治于傳”的動態思想[14]。在疫病的臨床診治中,因戾氣兇猛、邪氣暴盛,大多未慮正氣的虛損,以祛邪為主,先證而治,防止病邪傳入未受邪之地,此即“截斷”之法。如滬上名醫姜春華提出在治療急性傳染病時,早用清氣、通腑、涼血之法,先證而治[15];葉天士言“若平素心虛有痰,外熱一閉,里絡就陷”,用郁金、丹參、菖蒲等藥化瘀消痰以防逆傳心包;國醫大師朱良春教授提出“通下豈止奪實,更重在存陰保津,既能泄無形之邪熱,又能除有形之穢滯,一舉數得,誠治本之道也”,在包括傳染病的急性熱病初期即用表里雙解法,破除溫病三禁,先發制病,發于機先[16]。而《金匱要略·臟腑經絡先后病脈證第一》中言“見肝之病,知肝傳脾,當先實脾”,先安未受邪之地,即指補充可能被傳變區域的正氣。若正氣充足,則病邪無法侵犯或損傷較小。《瘟疫論·傳變不常》強調“一隅之虧,邪乘宿昔所損而傳”,所以,及時順應人體之勢補充疫邪將傳變之地的虛損正氣,或峻補正氣,或補瀉兼施,有預見性地制約疫病,也可有效地截斷疫病的傳變,頓挫病邪,使之更易外出。
其一,激正固衛,防邪于外。疫病預防階段,疫病病邪從外侵表,可固護激發衛氣,用藿香、佩蘭、艾葉等芳香辟穢之藥以香囊、熏蒸之法防邪侵入。徐靈胎[17]言“香者氣之正,正氣盛則除邪辟穢”,現代藥理研究表明芳香藥物的揮發油進入人體循環,可以激發人體的免疫防御功能(衛氣),如刺激鼻黏膜產生分泌型免疫球蛋白A,從而御邪于外[18]。
其二,補氣安肺,降低邪損。疫病初期,中期,疫邪從口鼻而入,首先犯肺,可先安肺之宗氣,用人參、黃芪等藥補氣以益肺。劉良教授團隊在對新冠病毒肺炎死亡患者的解剖中發現新冠肺炎從損傷大氣管開始到引起深部氣道和肺泡損傷為主,且滲出非常明顯[19]。依據中醫肺主氣、氣可攝津的理論,宗氣不足則攝津無力,津液外流而滲出明顯。而且,病邪入肺到深入小支氣管和肺泡尚有一定時間,在祛邪為主的同時配伍人參、黃芪等藥補益肺之宗氣,氣行則血動不留瘀,氣行則津運不成痰,攝津抗邪可以有效地緩解疾病的損害和進展。
其三,健脾補腎,防邪深入。疫病危重癥多為老年或有基礎疾病的患者,此類病人或多或少都有脾腎虧虛之象,而疫病中后期多順傳脾胃,直入下焦肝腎,因此可以先健脾為防,若邪盛致脾胃陰津大耗,則應急補腎精以滋陰。如李東垣在《內外傷辨惑論·脾胃勝衰論》中言“脾氣一虛,肺氣先絕”,故元氣虛損之人,感疫后之熱象非邪盛之癥,乃“至虛有盛候”,用補中益氣湯以補中焦脾胃,培土生金。葉天士對于溫病疫邪在中焦,但斑出不解者,慮其胃津耗損,主以甘寒;若腎水素虧,則加入咸寒之藥兼補腎陰以防熱邪乘虛下入,劫爍真陰。臨床研究表明健脾之法可以調節細胞免疫功能,減輕應激狀態,祛除炎癥風暴的病理產物,促進炎癥的消散和吸收[20]。所以在體虛或疫病中后期患者中及時應用健脾補腎之法,能有效地防止疫氣深入。
《孫子兵法·勢》曰:“故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勢如彍弩,節如發機。故善戰者,求之于勢,不責于人,故能擇人而任勢。”在疫病的診治中,當“謹守病機,各司所屬”,以動態的辨證論治思維處理疾病,因病位表里上下及病性寒熱虛實之勢,以“通”“透”之法盡逐疫邪,同時注重順人體之勢扶正以先安未受邪之地,防邪深入,審機度勢,以祛邪為要,注重順勢安正,實現“邪去則正安”“正安則邪退”。
3 典型病例
患者,男,96歲,新冠肺炎確診病例。2020年3月4日自覺發熱,伴乏力氣短,就診查體溫38℃,白細胞:6.14×109/L,中性粒細胞:83.2%,C-反應蛋白:100 mg/L。胸CT提示左下肺磨玻璃影,查新冠核酸(+),遂轉入專科醫院。入院生命體征:體溫38.2℃,心率90次/分鐘,呼吸21次/分鐘,血壓120/84 mmHg,靜息未吸氧狀態血氧飽和度91%,診斷:新型冠狀病毒肺炎(重型)。
盧云教授3月24日一診:患者發熱,體溫最高達38.5℃,經常規治療20天后乏力明顯,氣短難續,頭暈,神疲,倦臥不語,胸悶,咳嗽、咯少量白色黏痰,不欲飲食、食入則吐,便溏、一天2~3行。形體消瘦,面色萎黃,舌淡苔少,脈弱稍沉。中醫診斷:肺疫,氣虛發熱證,治以升陽舉陷,健脾益氣兼以透邪,方予補中益氣湯:生黃芪60 g、炙黃芪40 g、紅參60 g、炒白術30 g、陳皮15 g、升麻6 g、柴胡6 g、當歸15 g、炙甘草6 g。2劑,水煎服,一日一劑,分3次服,每次150 mL左右。
3月26日二診:患者熱退,體溫正常,食欲好轉,可以起身坐位吃飯、說話,頭暈、氣短癥狀好轉,大便成形,仍覺乏力,咳嗽、咯少量白色黏痰,舌淡苔薄,脈弱。治從上法,從宣肺化痰透邪出入,予上方加杏仁15 g、紫蘇葉10 g。3月31日患者病情穩定,咳嗽、乏力等改善明顯,轉為普通型。
按 新冠肺炎是由感染新型冠狀病毒所致的呼吸道傳染病,患者多出現發熱、咳嗽、乏力等臨床癥狀,病情嚴重者可出現呼吸窘迫乃至多器官功能衰竭,屬中醫“疫病”范疇。本案患者高齡,形體消瘦,面色萎黃,素體脾胃虛弱,《靈樞·論痛》載“其瘦而薄胃者,皆不勝毒也”,當先安未受邪之地即補益脾胃。然患者感受疫毒20天,正邪交爭,肺氣大損,毒漸傳中焦。肺氣不足則神疲乏力,倦怠懶言;脾胃受損,運化失常,則不欲飲食、便溏;脾氣不足,清陽不升則頭暈;中氣不足,陰火與邪氣內郁化火,火性炎上,則發熱。結合舌淡苔少,脈弱稍沉,辨為氣虛發熱證。患者正虛邪不盛,當順脾胃之勢以補益為主。《素問·藏氣法時論篇》言“脾欲緩,甘補之”,《素問·至真要大論篇》言“勞者溫之”。《神農本草經》載“黃芪,甘,微溫,主大風癩疾、補虛”“人參主補五臟,除邪氣”,故重用炙黃芪、人參益氣以除邪。同時,重用生黃芪配伍升麻、柴胡以取托里透毒之效,使不盛之邪從漸入脾胃透轉至肌表以排除。《脾胃論·調中益氣湯》言“從下上者,引而去之;上氣不足,推而揚之”,脾胃主升清降濁,且陰火內郁,欲從下向上,故用小量升麻、柴胡因勢利導生發脾胃之清氣,除陰火之內郁,并配合陳皮梳理氣機。脾胃為后天之本,氣血生化之源,脾胃損則氣血不足,故稍加當歸以補血。諸藥合用,順脾胃之性,升清氣,降濁陰,散陰火;順邪氣之勢,透邪外出。脾氣一生則肺氣生化有源,故患者服藥兩劑后,發熱除,諸癥改善。二診針對咳嗽,咯少量白粘痰,稍加杏仁以順肺金肅降之氣,配合紫蘇葉共奏宣肺化痰之效,消散邪結,令余邪順勢透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