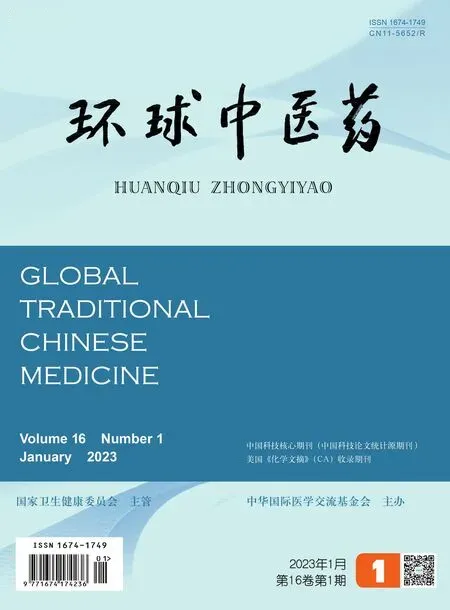楊文輝教授針藥結合分期論治血管性癡呆經驗擷要
莊澤欽 李明慧 曾文瑞 鄭諒
血管性癡呆(vascular dementia, VD),主要表現為認知、記憶缺損,或伴有言語等功能的失常[1],是癡呆的第二大常見原因[2],約占老年性癡呆16%[3]。我國VD的發病率約為3.0%[4],隨著人口老齡化,VD的發病數逐年升高,現狀不容樂觀[5-6]。預后研究表明患VD后,女性生存率約為6.7年,而男性約為5.1年[7]。現代醫學認為VD是由于腦血管性疾病導致腦神經元壞死,認知功能下降[8],治療為改善腦組織循環、控制血壓等[9]。VD屬于祖國醫學“癡呆”“呆病”“善忘”等范疇。關于VD病因病機,歷代醫家主要集中五臟虛損、痰、瘀方面[10]。如《靈樞》“血、脈、營、氣、精神,此五臟之所藏也。至其淫泆離臟則精失……智慮去身者”,《石室秘錄》“痰勢最盛,呆氣最深”,《血證論》“血在上,則濁蔽不明矣”。楊文輝教授為廣東省名中醫,曾任廣州中醫學院針灸系針灸治療學教研室主任。多年的臨床實踐,楊文輝總結出了“三才單式提插補瀉手法”[11-12]、“CT圍針”[13-15]、“八髎壓灸”[16]等寶貴經驗。在VD方面,結合早年研究[17-19],楊文輝提倡針藥結合,分期論治VD,形成一套獨特的診療思路,臨床療效顯著。
1 剖析本質,闡明病機
VD主要發生在年邁者,是嚴重危害中老年人生存質量的常見病[20],也是繼阿爾茨海默病后第二大常見的癡呆癥[21]。《靈樞·天年》中也提到:“五十歲,肝氣始衰……魄離,故言善誤……五臟皆虛,神皆去,形骸獨居而終矣。”楊文輝提出此病多發于中老年人,與脾腎衰敗、精虧髓少之本密切相關,而在臨床實際中,氣血逆亂、痰瘀內生之標亦不少見,認為本病屬本虛標實之證,脾腎衰敗、精虧髓少為本,氣血逆亂、痰瘀內生為標。
1.1 氣血逆亂、痰瘀內生為標
臨床中VD常在腦卒中之后發生,而急性腦卒中發生與氣、血、痰、瘀密切相關。楊文輝結合多年治療VD的經驗,指出氣血逆亂、痰瘀內生為VD發生之標。或情志所傷,思慮過度,氣機郁結,木郁土衰,而痰濁內生,蒙蔽清竅,發生癡呆;或因久郁化火,煉液成痰,迷蒙清竅;或因性情過激,肝火過亢,迫血妄行,亦或氣滯血瘀,以至瘀阻腦絡,腦氣不通,神明不清。《辨證錄》也提到:“肝郁則木克土,而痰基于胸中,盤踞于心外,使神志不清,而成呆病。”陳士鐸直接指出“痰勢最盛,呆氣最深”。清代醫家林珮琴也提到血瘀于內,而善忘如狂。而現代研究中,趙偉苗[22]通過研究發現血液中血漿黏度、血小板聚集率等在血管性癡呆疾病中有重要的臨床診斷價值。馬青等[23]也指出瘀血阻滯與VD的發生密切相關。
1.2 脾腎衰敗、精虧髓少為本
楊文輝在臨證中發現VD患者脾腎虧虛不在少數,腎精及水谷精微不上承腦髓,腦髓失養,則神機失用。人秉天地之氣而生,脾又為后天之本,氣血生化之源,因此,人的生存賴后天脾胃之補養。脾胃虧損,化生不足,氣血不足,無以補養神明,則使人意舍不清,誠如《三因極一病證方論》所言:“今脾受病,神明被阻,則意舍不清,心神不寧使人健忘。”《內經》的八正神明論篇同樣指出氣血對神明的重要性,即“血氣者, 人之神, 不可不謹養”。脾為土臟,灌慨四旁,因此五臟中皆有脾氣,其余臟腑皆賴脾的供養。脾臟受損,則一損俱損,易出現神機失用、健忘癡呆。閔冬雨等[24]基于“脾藏意”也提出了從脾論治VD,為中醫治療VD豐富了治療思路。腎藏精,主骨生髓,通于腦,腦又為元神之府。《醫學入門》中也提到:“腦者髓之海……髓則腎主之。”可見腎與腦髓的關系極為密切。人步入中老年時期,腎氣逐日衰退,精氣虧竭,元神失養,故而發生癡呆。《內經》也指出男不過八八,女不過七七,天地之氣皆竭。陳士鐸直接指出人老而健忘,猶若茫然,是腎水之竭。楊文輝指出人之所以保持記憶、認知等功能正常,是腎臟源源不斷地將腎精通過經絡絡屬上傳化為腦髓,保證元神正常工作的基本物質。孫理軍等[25]通過基礎研究也證實補腎類中藥有益于腎虛型VD鼠恢復記憶等功能。阮娟娟等[26]通過臨床研究發現補腎填精的治法能夠顯著改善VD患者臨床癥狀。楊文輝認為人始生,需先成精,精成后腦髓生,腦髓需要依賴腎精的充養,人之所以保持記憶、認知等功能正常,是腎臟源源不斷地將腎精通過經絡絡屬上傳化為腦髓,保證元神正常工作的基本物質,腎精不足,腦髓必然虧虛,則最終出現神明失養,發生癡呆,因此腎精虧損也是VD發生的根本原因之一。
2 緊扣病機,創新分期
楊文輝在臨床治療VD時非常注重首先對病機證候的判別,而后對VD患者進行分期,期定則法成,法成則方立。楊文輝對VD的分期不同于以往謝穎楨等[27]對VD的分期。后者將VD分為平臺期、波動期和下滑期三期,其分期主要依據患者的癥狀及病情平穩與否。楊文輝以為此分期方式未能直接反映病人的病機證候,對中醫辨證施治指導意義有所欠缺。經過多年臨床觀察及實踐,楊文輝發現在發病的前期,VD主要以痰瘀為主,后期以脾腎衰敗、精髓虧損為主。根據“急則治其標,緩則治其本”,楊文輝將VD分為兩大期,即氣血逆亂、痰瘀內生期(前期)和脾腎衰敗、精虧髓少期(后期)。楊文輝對VD的分期更加注重VD患者所處的病機證候,對指導臨床治療更有實際意義。
2.1 氣血逆亂、痰瘀內生期(前期)
楊文輝認為此期主要的病機為氣血逆亂,直沖犯腦,致氣血津液運行不暢、化生痰瘀。臨床多數VD患者發病多先經歷此期。此期為情志過極、肝陽暴張或痰熱內生等,引發體內氣血逆亂,橫竄經脈,直沖犯腦,血瘀腦絡,發為呆病。主要表現為急躁易怒,煩躁不安,頭暈目眩;表情呆滯,不言不語,忽歌忽笑;喜忘,反應遲鈍,動作笨拙;常伴口眼歪斜,偏身麻木,半身不遂等。
2.2 脾腎衰敗,精虧髓少期(后期)
楊文輝認為此期主要的病機為脾腎衰敗、精虧髓少。此期為久病不愈,致使腎精虧少,腦髓不足,元神失養,或后天失養,氣血生化不足,或先天不足,年邁體虛,神機失用。臨床主要表現為忘失前后,興趣缺失,行走緩慢,動作笨拙;反應遲鈍,易驚善恐,食少納呆;多夢易驚,少言寡語等。楊文輝強調此期病人不一定經過氣血逆亂期發展而來,可由于年老體衰或后天失養等,發病即為此期,斷不可以病程簡單判斷病人的病期,而應根據臨床實際鑒別病人所處病期。
3 期定而法成—楊文輝的特色療法及方案
對VD患者進行分期后,楊文輝便根據患者的具體情況給予相應的療法及方案。首先,楊文輝針對VD治療獨創頭顱CT定位圍針法,即根據患者病灶的位置、大小、形狀、數量具體運用,使治療方案更具針對性。同時,楊文輝提倡在臨床治療VD時,需充分利用針刺和中藥湯液各自的優勢,在VD不同分期中發揮各自獨特的作用。《內經·移精變氣論》中提到:“微針治其外,湯液治其內。”《異法方宜論》中也提出:“故圣人雜合以治,各得其所宜。”唐代著名醫家孫思邈認為:“針灸而不藥,藥而不針灸,尤非良醫也。”因此在臨證中,楊文輝非常注重針藥結合,認為針刺本質屬于外治法中一種,在臨床應用時善于調理氣血、疏通經絡;而中藥湯液屬于內治法,在臨床中善于調節臟腑、扶正祛邪。現將楊文輝治療VD的特色療法及針藥結合方案介紹如下。
3.1 獨創頭顱CT定位圍針,啟智開竅
頭顱CT定位圍針治療腦病是楊文輝自1998年首創的,現如今已為多家醫院針灸科應用[28]。“頭為諸陽之會”,人體手足三陽經皆上交會于頭部。楊文輝認為“經絡所過,主治所及”,頭顱CT定位圍針可以廣泛調節多條經絡。VD患者的病變在頭部,在頭部行CT定位圍針可以直接起到對局部氣血的調節。倫新等[29]實驗研究證明頭顱CT定位圍針治療癡呆患者,可以明顯改善患者的智能情況及血流流變指標。因此在臨證治療VD患者時,楊文輝提倡根據頭顱CT結果予CT定位圍針治療,以達疏通經絡、調節陰陽、啟智開竅之效。不過現在隨著顱腦MR檢查的普及,楊文輝提出亦可根據顱腦MR結果行定位圍針治療。頭顱CT定位圍針治療VD時,以CT所示病灶在同側頭皮的投射區周圍為毫針針刺的部位。一般根據病灶的大小在投射區周圍圍刺4~8針,針尖朝投射區中心,進針方式同常規頭皮針。得氣后行平補平瀉手法,以局部明顯酸脹為度,留針30分鐘,一般中間間斷行針2~3次,以保證持續的刺激,此外,楊文輝亦提倡有條件的可加電針儀,通以疏密波,如此刺激量更強,療效更好。
3.2 疾病前期,針貴在疏通,藥貴在化濁
疾病前期即氣血逆亂、痰瘀內生期,楊文輝提出此期治療重點在“疏通”與“化濁”。“疏通”即應用毫針針刺療法以疏肝經、調氣血,使逆亂上沖之氣血得以平降,一則有助VD患者恢復氣血調和狀態,二則預防逆亂之氣血進一步造成更危險的腦血管疾病。“化濁”即應用中藥方劑化痰祛瘀,楊文輝認為中藥湯液可深入臟腑,直達腦部,此期所形成的痰、瘀病理產物,借助中藥直達病所以化痰祛瘀,事半功倍。
除頭顱CT定位圍針,其余針刺選穴以足厥陰肝經、督脈為主要治療經脈。楊文輝在此期取穴主要為百會、膻中、期門、太沖、曲池、血海、膈俞、陰陵泉、豐隆。百會系督脈與手足三陽經之會穴,有開竅醒神,疏利神機的作用;膻中為八會穴之氣會,有理肺氣、通乳絡之功,在本病治療中可起到舒暢氣機的作用;期門與太沖為足厥陰肝經腧穴,期門系肝之募穴,太沖亦是厥陰肝經原穴,二者配合,可加強疏肝理氣、平肝熄風之效;曲池為手陽明大腸經之合穴,有行氣活血之功;血海與膈俞起到活血化瘀之功;陰陵泉與豐隆,一為足太陰脾經腧穴,一為足陽明胃經腧穴,兩經互為表里,可有祛痰降逆、疏經活絡之功。在操作手法上,楊文輝針對不同的穴位均有不同的操作思路。針刺百會時,向后沿皮斜刺,行平補平瀉手法,以局部明顯酸脹為度,留針20~25分鐘;膻中、期門、太沖用捻轉瀉法,使針感傳到腹部或下肢,留針20~25分鐘;曲池用提插平補平瀉法,以局部明顯酸脹為度,留針20~25分鐘;陰陵泉、豐隆、血海及膈俞進針后施以白虎搖頭法即瀉法,以使針下感覺放散為度,留針20~25分鐘。
中藥治療此期患者時,楊文輝以自擬通神湯加減治療。此方主要為桃仁、紅花、半夏、陳皮、郁金、遠志、石菖蒲、鉤藤、石決明、天麻、杜仲、桑寄生。楊文輝認為此期病人須當以化痰祛瘀為主,以桃仁、紅花化瘀行血,兼加石菖蒲以化瘀通竅醒神,直達腦絡解決血瘀之證,半夏與陳皮取二陳湯之意,以達燥濕化痰、理氣行滯之功,郁金與遠志以加強化痰益智之功,鉤藤、石決明和天麻以平肝熄風潛陽,杜仲和桑寄生補益肝腎以之本。楊文輝指出此方抓住此期病人“痰”“瘀”的主要病機,以化瘀祛痰、平肝潛陽為主,兼以益腎啟智,治標為主,兼以固本。此外楊文輝指出在臨床應用時需結合脈癥,細心辨別患者所屬證候,若是病人瘀象偏重,則需加強化瘀之力,諸如赤芍、田七之類,若是陽亢較甚,可加龍骨、牡蠣等重鎮降逆。如此針藥結合,此期VD患者氣血因針刺氣血得以調和,腦髓痰瘀因湯液得以化散,氣血經絡通暢,無痰瘀蒙蔽腦神,加以腦功能訓練,如計算、記憶等,則病必漸愈。
3.3 疾病后期,針貴在調神,藥貴在補虛
疾病后期,即脾腎衰敗,精虧髓少期。楊文輝提出此期多病情較重,病程較長,大部分為氣血逆亂、痰瘀內生期遷延不愈,內耗精氣,損傷脾腎而成,亦有少部分是由于先天不足、脾腎虛弱等,發病即為此期。故楊文輝提出此期治療重點在“調神”與“補虛”。“調神”即通調元神,利用針刺調經氣以通元神、疏利神機。“補虛”即利用湯藥以補益脾腎、填精益髓。
除頭顱CT定位圍針,其余針刺選穴以足太陽膀胱經、督脈為主要治療經脈。楊文輝此期主要取穴為百會、本神、四神聰、太溪、足三里、脾俞、腎俞。百會系督脈與手足三陽經之會穴,有開竅醒神、疏利神機的作用;本神內應腦髓,可起刺激腦髓之功;四神聰為經外奇穴,配合本神可起醒神益智之功;太溪、脾俞和腎俞三者配合,可起補益脾腎之功;足三里為胃經之合穴,保健之大穴,可起補養脾胃之功。針刺百會時,向后沿皮斜刺,行平補平瀉手法,以局部明顯酸脹為度,留針20~25分鐘;斜刺四神聰時,針尖朝向百會,行平補平瀉手法,以局部明顯酸脹為度,留針20~25分鐘;本神用捻轉補法,以局部明顯酸脹為度,留針20~25分鐘;太溪、足三里、脾俞和腎俞均采用青龍擺尾法即補法,以使針下感覺放散為度,留針20~25分鐘。
中藥治療時楊文輝以自擬復元湯為主。主要藥物有鹿茸、益智仁、枸杞、黃芪、杜仲、桑寄生、菟絲子、黃精。楊文輝認為此期患者急需湯液以填精益髓,上供腦部恢復元神,故重用鹿茸,鹿茸為補真元之專藥,能夠起壯腎陽、益精血之效,配合益智仁可加強補腎益智之效,枸杞和黃芪益氣補血,相得益彰,加強后天補養之力,菟絲子為腎虛平補良藥,助鹿茸補益腎精,杜仲和桑寄生補益肝腎,黃精專養脾胃,配合枸杞、黃芪固護后天。楊文輝指出此方為一派補益藥物組成,源于此期病人須補益脾腎、填精益髓為主,然病久必然并發一系列痰瘀病理產物,臨證之時須加以鑒別,按證給予化痰、祛瘀、理氣等藥物。此外,楊文輝提出此期病人由于病情較重,損傷精髓,預后較差。此期針藥結合治療方案可在一定程度上恢復損傷的元神,但要取得遠期較好療效需患者配合持久的補養。
4 小結
楊文輝結合多年臨床經驗,緊扣VD患者臨床病機,創新提出了將VD患者分為氣血逆亂、痰瘀內生期和脾腎衰敗、精虧髓少期兩期,不同于以往對VD的中醫分期,更加注重患者所處的實際證候,能夠更好地指導臨床。在治療方面,針藥結合,氣血逆亂、痰瘀內生期利用針刺以疏通氣血,應用湯液以化散痰瘀,脾腎衰敗、精虧髓少期利用針刺以調元神之逆亂,應用湯液以補脾腎之虧虛。此外,針灸獨創了頭顱CT定位圍針,中藥自擬了通神湯及復元湯等,在臨床中取得了顯著的療效。這套針藥結合、分期而治VD的診療思路,系統且獨具特色,療效顯著,值得臨床工作者借鑒推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