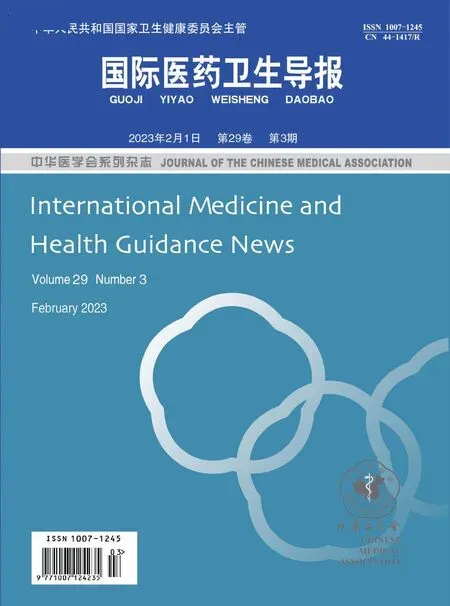超聲技術評估宮頸在預測早產中的新進展
隋禎慧 唐麗瑋 張明珠 董景云 高巖冰
濱州醫學院附屬醫院超聲醫學科,濱州 256600
全球早產發生率逐年提高,占5 歲以下兒童死亡總數的18%,占新生兒死亡總數的35%,目前早產已經成為我國新生兒死亡的首要因素[1]。臨床上主要是通過Bishop 評分、宮縮監測、胎兒纖維連接蛋白(fetal fibronectin,FFN)及超聲評估宮頸等手段預測早產。但是,Bishop 評分受主觀因素影響較大且易引發宮縮;而宮縮監測及FFN 易受其他因素影響,預測效能較低。超聲技術可實時觀察宮頸形態及長度變化,評估宮頸硬度值,具有簡單便捷、無輻射、重復性好的優勢。本文對超聲技術評估宮頸預測早產的研究現狀進行綜述,以期為臨床預測早產提供更有價值的信息。
早產的定義及危險因素
早產是指妊娠滿28 周不足37周,胎兒體質量≥1 000 g的分娩。目前臨床上將早產分為3 種類型:自發性早產、胎膜早破型早產及醫源性早產,其中以自發性早產較為常見,在整體早產中約占45%[2]。早產的高危因素包括:(1)早產史;(2)孕婦年齡過大(>35 歲);(3)孕婦體質量指數過大或過小;(4)妊娠間隔<6個月;(5)宮頸手術史;(6)孕婦子宮畸形;(7)胎兒畸形;(8)多胎妊娠;(9)孕婦存在全身性感染及生殖道感染;(10)吸煙史;(11)孕婦心理壓力等[3]。孕婦既往有早產史是早產最主要的危險因素,有早產史的女性在隨后妊娠中再次發生早產的風險將增加4~6 倍。所以,孕期加強產前檢查,盡早發現潛在高危因素,才能及時對早產進行干預,從而降低圍生兒不良結局。
妊娠期宮頸組織結構變化
妊娠期宮頸發生的一系列變化稱為“宮頸重塑”。“宮頸重塑”包括宮頸軟化、成熟、擴張、產后復舊4 個階段。宮頸是水合的膠原結構,其細胞含量極少,僅占10%~15%。妊娠期宮頸承受著由不斷增長的妊娠組織重量和子宮壁拉力所產生的一系列復雜的作用力。妊娠期宮頸組織的機械強度主要取決于膠原網絡的強度與組織的水合程度。隨著妊娠進展,膠原纖維之間的距離增加,膠原纖維的形狀和大小發生變化,膠原蛋白網絡的整體結構開始變得紊亂,宮頸的機械強度也隨之改變。除了膠原網絡的整體結構外,膠原網絡的強度還與膠原纖維排列以及膠原纖維之間存在的交聯程度和類型密切相關[4]。而組織的水合作用被認為是破壞膠原蛋白網絡的一種機制,它會使宮頸組織中的水分含量逐漸增加,從而導致宮頸軟化[5]。此外,宮頸并不是一個均質的結構,宮頸內口含有50%~60%的平滑肌,肌束圍繞宮頸管排列且沿宮頸外口方向含量逐漸減少,而宮頸外部主要以膠原結構為主,基質中僅含有少量的平滑肌細胞,所以妊娠時宮頸內部更具有收縮性,從而使胎兒順利娩出。
宮頸的超聲評估
1.宮頸長度(cervical length,CL)
現如今,臨床常用的CL 測量方法主要為經陰超聲和經腹超聲。與經腹法相比,經陰宮頸超聲檢查受母親肥胖、宮頸位置和胎兒出現部位陰影的影響較小,且其測量的CL 與早產預測相關性更強,因此,被認為是CL 測量的金標準[6]。2021 年美國婦產科醫師學會發布的《自發性早產的預測和預防指南》中對經腹超聲測量CL 的價值進行評估,其中指出若以經腹法測值35 mm為臨界值時,經陰超聲測得CL≤25 mm的靈敏度及特異度較高,從而使部分孕婦免于經陰道超聲檢查[7]。
妊娠期超聲測量CL 可以識別出有早產風險的女性。Guzman等[6]研究指出,CL<25 mm 預測早產的靈敏度在妊娠<28、30、32、34 周時分別為99%、99%、98%和96%;而在妊娠32 周以后,CL≤15 mm 在預測早產方面具有更高的準確度。由于研究人群及胎齡的差異,CL 預測早產的截斷值也有所不同,我國中華醫學會婦產科學分會在《早產臨產診斷與治療指南(2014)》將孕中期CL<25 mm作為早產的高風險因素。此外,CL 在預測雙胎及多胎妊娠的早產也具有重要意義。一項meta 分析表明,CL≤20 mm 與32 周及34 周前的早產具有相關性,其結果顯示妊娠20~24周時CL是無癥狀雙胎妊娠孕婦早產的良好預測指標[8]。而在多胎妊娠的前瞻性研究中發現,在妊娠15~24 周時,CL≤25 mm 預測3 胎妊娠早產的特異度和靈敏度較高;CL≤20 mm 是妊娠25~28 周預測3 胎早產的理想截斷值。但是,雙胎及多胎妊娠的孕婦宮頸縮短更快,僅通過單次測量CL 可能無法有效預測早產發生。Meller等[9]研究發現,妊娠中期CL 的連續測值較單次測值預測早產的靈敏度更高,通過妊娠中期宮頸縮短的程度,可以實現對早產的最佳預測。所以妊娠期CL 的連續測值有助于提升預測早產的準確度。目前,對于雙胎及多胎妊娠的研究多為回顧性分析且樣本量較少,CL 對多胎妊娠早產的預測效能尚不明確,其能否應用于臨床還需進一步研究。此外,有學者發現CL 聯合FFN 可能比單一指標更具價值。目前以CL、FFN 及早產危險因素構建的臨床輔助支持系統,可以相對準確計算有癥狀孕婦的早產風險,有望成為預測早產的新方式[10-11]。
2.宮頸漏斗
正常妊娠情況下,宮頸內口呈“T”型,而其異常擴張時,則會轉變為“Y”型、“V”型或“U”型。宮頸漏斗的形成代表著宮頸重塑進入擴張階段,所以在一定情況下,宮頸漏斗的形成預示著早產的發生。研究發現,在CL 為1~5 mm時,宮頸漏斗100%存在;CL 為6~10 mm 及11~15 mm時,宮頸漏斗的形成率均為98%;CL 為16~20 mm時,51.3%形成宮頸漏斗;CL 為21~25 mm 時其形成率約為12.3%;而CL為26~30 mm時,僅有2.5%會形成宮頸漏斗[12]。這表明隨著CL 的縮短,宮頸漏斗的形成率也逐漸增加。此外,Mancuso等[13]發現孕婦宮頸為“U”型漏斗比“V”型漏斗和無漏斗發生早產的時間更早,而宮頸為“V”型漏斗與無漏斗的孕婦發生早產的時間無明顯差異,說明“V”型漏斗可能只與宮頸縮短有關,沒有任何臨床意義。因此,宮頸漏斗的形成雖然是早產風險之一,但在預測早產方面并不能比CL 提供更多信息。
3.宮頸角
宮頸角是指宮頸內口與子宮前壁下段的連線與宮頸內外口連線之間的角度。妊娠期間子宮前壁下段具有向上“托起”的作用,減輕了胎兒及前羊膜囊對宮頸內口的壓力,避免宮頸內口擴張。當宮頸角變鈍時,子宮前壁下段的“托起”作用減小,壓力直接作用于宮頸內口,使宮頸被動擴張,從而發生早產[14]。Dziadosz等[15]研究發現,宮頸角與早產間具有顯著的相關性,宮頸角≥95°和宮頸角≥105°分別是妊娠<37 周與妊娠<34 周早產的最佳閾值,宮頸角預測早產的靈敏度比CL 高80%~81%。所以,在預測早產方面宮頸角可能比CL 更具有價值,妊娠中期宮頸角的測量可能有助于對單胎妊娠婦女早產風險的評估。然而,有部分學者認為先前研究可能高估了宮頸角的預測效能,對于早產高危患者及有早產癥狀的孕婦來說,宮頸角可能并不是最佳的早產預測工具[16-18]。目前國內外學者對于研究人群、宮頸角測量的合適孕周、宮頸角最佳檢測方式及宮頸角預測早產的最佳閾值尚未達成共識,宮頸角雖有希望成為早產預測的一種手段,但是并不足以引入臨床實踐中,后續仍需擴大樣本量進一步研究。
4.宮頸超聲彈性成像
近年來超聲彈性成像因其簡單、可操作性強、定性定量評估組織硬度等特點,目前已廣泛應用于肝臟、乳腺、淋巴結等疾病。國內外已有學者將其應用于宮頸并預測早產,其中以應變彈性成像及剪切波彈性成像應用較為廣泛。
4.1.應變彈性成像 應變彈性成像是利用探頭對組織施壓,通過檢測施壓后組織位移變化、評估組織應變能力來測量組織硬度的一種彈性成像技術,常應用應變值、應變率、彈性成像指數、彈性成像評分等來半定量評估組織硬度變化[19]。研究發現,正常妊娠期間宮頸不同部位的軟硬度差異顯著且與孕周相關[20]。而且隨著孕齡和Bishop評分的增加,宮頸前唇和宮頸管逐漸變軟;而隨著母親年齡、體質量和產次的增加,宮頸后唇明顯變硬。這表明妊娠宮頸的應變能力與Bishop 評分和其他母體因素(孕婦年齡、產次、體質量等)具有顯著相關性,這為宮頸彈性的變化評估提供額外的參考信息。Gesthuysen等[21]比較了應變率、彈性成像指數及彈性成像評分三者預測早產的效能發現,彈性成像指數與彈性成像評分具有更高的預測潛力,曲線下面積(AUC)分別為0.805 9 和0.771 6。但是,該技術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在手動加壓過程中,所選擇的感興趣區可能會脫離原始跟蹤位置,測得的宮頸彈性數值可能會受影響。為解決上述問題,基于應變彈性成像的E-cervix 技術,即通過人體生理運動觸發的宮頸組織彈性應變來半自動監測宮頸組織彈性相關指標變化的技術開始應用于早產研究。Patberg等[22]發現妊娠中期宮頸彈性對比指數與自發性早產具有顯著相關性,這表明妊娠中期,宮頸的異質性程度越高,發生自發性早產的風險越大。此外,妊娠期間初產婦與經產婦宮頸各部分軟化程度并不均一。隨著孕齡增加,經產婦是以除宮頸內外口之外的部分變化為主;而初產婦則是以宮頸內口軟化為主,且宮頸內外口硬度差逐漸縮小[23]。E-cervix技術不受患者呼吸及操作者壓力大小的影響,具有一定的客觀性與準確性,有望成為未來預測早產的可靠工具。
4.2.剪切波彈性成像 剪切波彈性成像是通過聲束產生的聲輻射力,在組織不同中發生Mach Cone 效應,使組織粒子高效震動引起位移變化產生剪切波,通過成像系統,得到實時的組織硬度分布圖[24-25]。我們用楊氏模量或者剪切波速度來定量描述組織硬度。部分學者研究發現,隨著孕周增大,正常妊娠孕婦的宮頸軟硬度逐漸減小,且宮頸硬度從內部到外部呈梯度下降,這為宮頸彈性的研究奠定了基礎[26-27]。隨著研究的不斷進展,李凌等[28]發現,在預測早產方面,宮頸內口的預測效能要優于宮頸外口,這可能是宮頸內口比外口膠原蛋白交聯程度更強、膠原蛋白縱向纖維密度更大,從而使宮頸內口的膠原蛋白網的高度非均質性所致。剪切波彈性成像有望成為預測早產的潛在新指標,但該技術受操作者的技術水平、呼吸運動和胎動影響,可能會影響測量的準確性,且宮頸彈性模量值的測量點選取的位置尚未統一,后續仍需擴大樣本量進行進一步研究。
5.宮頸定量紋理分析
定量紋理分析是從特定組織的圖像中提取紋理信息來評估分析組織中的細微結構改變的技術。它具有安全、無創、便捷、客觀的特點,現已在CT、MR 中被廣泛應用。Ba?os等[29]分析了妊娠20.0~41.6 周正常孕婦宮頸前唇中部的宮頸異質性,研究發現宮頸定量紋理分析可以從宮頸超聲圖像中提取與胎齡相關的特征,這為分析妊娠各時期宮頸結構的變化提供了新的方向。在此基礎上,部分學者研究發現,在妊娠中期,宮頸紋理評分與自發性早產保持著顯著相關性,且其預測自發性早產的效能明顯優于CL,靈敏度及特異度分別為70.4%和77.7%[30-31]。目前宮頸定量紋理分析技術雖然尚缺乏大數量的數據驗證,但其作為評價妊娠宮頸的一種方法仍然值得期待。
小結
綜上所述,早產已成為產科不可忽視的常見并發癥,了解妊娠期宮頸重塑機制對早產預測具有重要意義。隨著新技術如宮頸彈性成像、定量超聲紋理分析等技術的發展,彌補了常規超聲技術的不足,多種技術綜合分析將是未來預測及診斷早產的方向,為今后改善不良妊娠結局及早產兒的預后提供更有價值的幫助。
作者貢獻聲明隋禎慧:論文撰寫、修改;唐麗瑋、張明珠、董景云:論文指導;高巖冰:論文審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