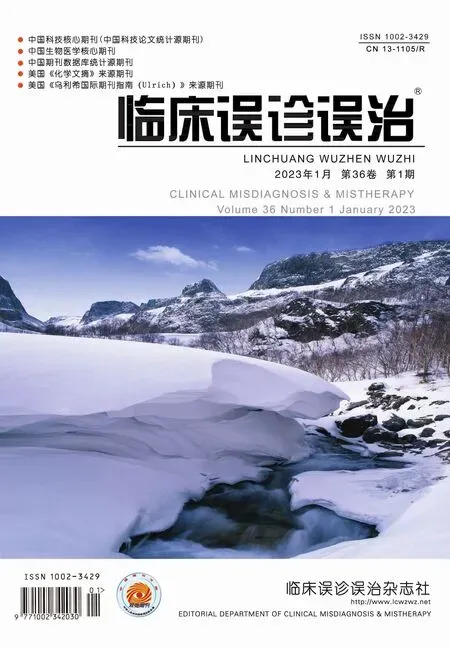高遷移率族蛋白B1在膿毒癥及其相關急性腎損傷中的研究進展
周 浩,常德輝,康印東
高遷移率族蛋白B1(HMGB1)屬于典型的損傷相關分子模式分子,參與許多疾病的發生和發展。越來越多的體內和體外研究表明,HMGB1在膿毒癥炎癥反應和免疫抑制過程中起著關鍵作用[1]。HMGB1可存在于所有細胞類型,是一種能在細胞內外發揮功能的蛋白質,細胞外HMGB1從細胞中主動釋放或細胞死亡時被動釋放后,作用于特定的細胞表面受體,并發揮促炎癥反應作用。HMGB1一旦進入循環會與晚期糖基化終產物受體(RAGE)和Toll樣受體(TLR)等多種靶細胞受體相互作用,刺激促炎細胞與趨化因子釋放,隨著膿毒癥病情惡化,HMGB1促損傷作用加劇,導致組織和器官進行性損傷。有研究表明,靶向給予HMGB1抗體可以減輕炎癥反應,從而降低膿毒癥等相關疾病損傷[2]。本文就HMGB1的結構、功能、受體及在相關疾病中的研究進展等進行綜述如下。
1 HMGB1概述
1.1HMGB1的結構 1973年,有學者首次在小牛胸腺中成功提取高遷移率族蛋白(HMG),該名稱基于其在聚丙烯酰胺凝膠電泳中的流動性。HMG包括A、B和N 3個家族,其中B1即HMGB1。1999年,WANG等[3]將小鼠在內毒素暴露8~32 h后發現血清HMGB1水平升高,延遲施用HMGB1抗體會減弱小鼠內毒素的致死性。HMGB1在人體中廣泛表達,所有的哺乳動物體中都含有豐富的HMGB1,在酵母、植物和細菌中,HMGB1存在于細胞質和細胞核內,以細胞核內聚集為主,并且在生物進化中高度保守,哺乳動物和人類具有99%的同一性。在人體中HMGB1表達 215個氨基酸,由2個同源DNA結合域(box-A和box-B)及一個帶負電荷的羧基端(C末端)組成, box-B能在細胞外刺激時誘導促炎癥信號,box-A可誘導拮抗作用,帶負電荷的羧基端是介導RAGE和TLR結合的區域。
1.2HMGB1的生物學性質 HMGB1的功能和分泌取決于其氧化還原狀態,該狀態由3種氧化還原敏感的半胱氨酸所決定(box-A中的C23、C45及box-B中的 C106)。其3種形式分別為烯丙基硫醇形式、二硫鍵形式和完全氧化形式。HMGB1表達3個半胱氨酸硫醇殘基,但在細胞核中主要依靠全巰基型HMGB1發揮作用,參與DNA復制、轉錄、翻譯和調節等,對動物生命活動不可或缺。在細胞核及細胞質之間HMGB1可通過核孔任意穿梭,HMGB1發生翻譯后修飾可使其從細胞核向細胞質聚集,參與機體的炎癥反應和程序性細胞死亡等。HMGB1受到各種翻譯后修飾的影響,包括乙酰化、N-糖基化、ADP-核糖基化、磷酸化和甲基化。HMGB1可在細胞外發揮作用,從細胞內到細胞外,主要有2種方式:其一是受損或壞死細胞被動釋放,通過促炎細胞因子如腫瘤壞死因子-α立即引發炎癥反應;其二是通過免疫細胞主動釋放,但分泌機制目前尚不完全清楚。細胞外,HMGB1可通過RAGE、TLR4及CXC基序趨化因子受體4(CXCR4)相互作用而發揮生物學效應。壞死及凋亡細胞釋放的HMGB1大多數處于全巰基形式。全巰基形式HMGB1與趨化因子配體12(CXCL12)形成雜合物,并與CXCR4結合,誘導細胞遷移產生化學吸引作用;二硫化HMGB1通過MD-2途徑刺激細胞因子的產生和影響自噬體的形成;氧化型HMGB1大多累積在細胞質中,HMGB1的氧化狀態和分泌動力學決定機體免疫功能,氧化型HMGB1可抑制其他HMGB1形式的細胞因子或趨化因子活性,最終誘導免疫耐受[4]。綜上,細胞外HMGB1能刺激及介導炎癥反應、參與凋亡和自噬等多種活動。
2 HMGB1受體及信號通路
2.1RAGE 細胞外HMGB1參與了多種不同的受體系統。現已報道的HMGB1受體列表相當廣泛, RAGE和TLR4在大量研究中被鑒定為HMGB1特異性受體。RAGE是細胞表面分子免疫球蛋白超家族的多配體成員,具有多種配體庫,這些配體包括非酶基糖基化的產物(晚期糖基化終產物、HMGB1、淀粉樣β肽和S100家族蛋白等)。RAGE是第1個與HMGB1結合的受體[5]。RAGE在正常生理條件下表達水平較低,但在慢性炎癥條件下由于RAGE與多個配體之間的相互作用形成正反饋環上調RAGE,最終導致病理學的改變。此外,有研究證實RAGE在先天性和適應性免疫過程中具有重要作用,包括HMGB1誘導的細胞自噬、免疫反應、黏附和遷移等,均是通過有絲分裂原活化蛋白激酶、核因子(NF)-κB信號通路進行的[6-8]。
2.2TLR TLR屬于Ⅰ型跨膜受體家族,信號傳導控制細胞增殖、存活、凋亡、血管生成、重塑和組織修復的過程。它是一種保護性受體,可感知損傷相關分子模式分子和病原體相關分子模式分子。HMGB1在配體識別后,可與TLR(TLR2、TLR4和TLR9)相互作用,通過初級反應基因88(MyD88)依賴的NF-κB通路,產生細胞因子和趨化因子,誘導機體發生顯著炎癥反應[9]。在FENG等[10]研究中,TLR2通過與HMGB1結合激活NF-κB信號通路調節狼瘡性腎炎中的腎小球系膜基質沉積。TLR2不僅可促進炎癥的發生,還可導致其他免疫疾病的發生。TLR4導致機體的各種炎癥,包括腸道炎癥、神經炎癥和腎損傷等,通過抑制TLR4引導的MyD88/NF-κB信號通路,對其治療有著不錯的效果[11-12]。以往針對TLR9的研究較少,TLR9與HMGB1相互作用并調節心肌損傷的機制尚不清楚。最新的研究發現,TLR9對于心肌梗死的修復至關重要,主要表現在TLR9缺乏不利于心肌梗死后的傷口愈合和瘢痕形成、加重心肌梗死后早期心肌細胞和成纖維細胞凋亡及導致心肌梗死后血管生成不足[13]。
2.3其他受體
2.3.1CXCR4:CXCR4屬于趨化因子蛋白家族成員之一,結合其配體時可以觸發多種信號通路,這些信號通路協調細胞遷移和造血等,還具有直接促進造血細胞增殖作用。CXCR4的典型配體是CXCL12。全巰基亞型HMGB1與CXCL12形成絡合物,隨后與CXCR4結合發揮趨化和遷移作用,其趨化性依賴β-arrestin1和β-arrestin2[14]。ZHAO等[15]在缺乏HMGB1的小鼠模型中發現小鼠表現出CXCL12/CXCR4的異常表達和RAGE的表達降低,間接證明了HMGB1與CXCR4之間的聯系。
2.3.2黏蛋白結構域(TIM)-3:TIM-3是TIM家族的一員,于2002年正式被發現,最初發現它在Th1表面表達,后來陸續發現在其他免疫細胞中也有表達。TIM-3作為負性調節因子,與配體半乳糖凝集素-9結合,可以介導Th1細胞凋亡[16]。TIM-3配體包括磷脂酰絲氨酸、HMGB1及最新的癌胚抗原相關細胞黏附分子。有研究表明,膿毒癥誘導的免疫抑制患者CD4+ T淋巴細胞上免疫球蛋白和TIM-3的表達顯著升高;此外,膿毒癥患者中TIM-3 CD4+T淋巴細胞的百分比與膿毒癥誘導的免疫抑制病死率相關,CD4+T淋巴細胞中TIM-3條件缺失和全身性TIM-3缺失都能降低小鼠膿毒癥的病死率[17]。因此,通過阻斷TIM-3可能會為自身免疫性疾病、慢性病毒感染和腫瘤治療提供一條新的思路[18]。
2.3.3熱穩定抗原24(CD24):CD24是一種糖基化的糖基磷脂酰肌醇錨定表面蛋白,于1978年首次被發現,其與多種損傷相關分子模式相關,如HMGB1和核仁蛋白等。現關于CD24的報道較少,在SONG等[19]的研究中,可溶性CD24可以通過與細胞外HMGB1和熱休克蛋白結合減輕損傷相關分子模式誘導的廣泛炎癥反應,并幫助其恢復免疫穩態,從而促進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征治療的進一步發展。
2.3.4結合珠蛋白(HP):HP是一種分子量為100 kDa的酸性糖蛋白,分子由2對肽鏈(α鏈與β鏈)共同形成α2β2的四聚體。HP首先在肝臟中產生,隨后作為急性期蛋白分泌到循環中,與HMGB1形成復合物刺激巨噬細胞血紅素氧合酶-1釋放,并以CD163依賴的方式誘導IL-10的產生,同時對HMGB1在膿毒癥中的致死性具有顯著保護作用[20]。此外,膿毒癥誘發的高血清 HMGB1 水平和低血清HP水平的患者可能具有較差的長期預后[21]。因此,抑制HP水平可能代表了一種新方法,用于治療由HMGB1過度釋放引發的各種炎癥性疾病。綜上,加深對參與HMGB1相關信號通路受體的理解,有助于進一步研究HMGB1在多種疾病中的作用,以便后期對疾病進行進一步研究及治療。
3 HMGB1與膿毒癥及其相關急性腎損傷
3.1膿毒癥 有研究發現,靶向給予HMGB1抗體的小鼠,內毒素血癥、盲管結扎和穿刺誘導膿毒癥模型生存率均明顯提升,其對二次感染也表現出一定的抵抗力,表現出先天免疫細胞表型和細胞因子反應,阻斷HMGB1可能有助于抑制膿毒癥中炎癥信號的強度,使患者對進一步的治療性免疫調節更敏感,同時靶向給予HMGB1抗體治療也對早期炎性因子有一定的影響[22]。HMGB1抗體治療膿毒癥可能通過控制疾病急性炎癥期及通過恢復免疫穩態和功能來進行,從而提高短期生存率。現階段靶向給予HMGB1抗體治療膿毒癥的策略主要用于革蘭陰性菌感染,在革蘭陽性菌膿毒癥的研究中,部分研究表明HMGB1抗體在革蘭陽性菌引起的膿毒癥條件下也能獲得成功[23-24]。靶向給予HMGB1抗體的方法已經證明在革蘭陰性菌引起的膿毒癥模型中降低了病死率,但HMGB1阻斷對復雜的膿毒癥和革蘭陽性菌引起的膿毒癥炎癥微環境影響仍然需進一步的研究。
3.2膿毒癥相關急性腎損傷
3.2.1炎癥風暴:腎臟為膿毒癥最常見的累及器官之一,膿毒癥相關急性腎損傷具有較高的致死率。膿毒癥引起急性腎損傷的主要機制是細菌內毒素釋放到循環中,激活腎臟中相關的炎癥級聯反應,最終導致腎損傷。NF-κB作為一種經典的炎癥信號傳導途徑,通過多種炎性因子和趨化因子產生和分泌,在炎癥和免疫的調節網絡中發揮關鍵作用。WEI等[25]研究表明,通過沉默信息調節因子1介導的HMGB1脫乙酰化可降低血清尿素和肌酐水平、減輕腎臟細胞凋亡等,隨后抑制下游炎癥信號傳導,增加膿毒癥模型小鼠的存活時間。一方面,通過HMGB1自身的拮抗可以改善其存活率;另一方面,通過抑制HMGB1相關炎癥通路(RAGE/TLR)也能改善其存活率。
3.2.2組織細胞凋亡及自噬:膿毒癥相關急性腎損傷是由免疫增強到免疫抑制的過程,往往伴隨著組織細胞凋亡和自噬。眾多藥物研究表明,托達洛內酯、烏利司他汀、血栓調節素等藥物能通過靶向抑制HMGB1/TLR/NF-κB通路緩解膿毒癥相關急性腎損傷中炎癥及凋亡指數,包括Bax/Bcl-2比值降低、Caspase3指標上調,明顯減輕膿毒癥引起的急性腎損傷[26-28]。此外,有文獻報道,重整注射液及其有效成分葉黃酮苷通過抑制HMGB1的分泌和易位,以及HMGB1介導的TLR4/NF-κB/MAPKs信號通路的激活來預防膿毒癥,并表現出顯著的保護作用[29]。自噬方面,丙酮酸乙酯在CaCl2條件下通過抑制HMGB1與Beclin-1的結合下調細胞自噬水平,從而減輕腎小管上皮細胞損傷[30]。綜上,HMGB1可通過調節細胞凋亡和自噬水平改善腎細胞損傷程度以及預防和延緩腎損傷。
3.2.3免疫調節:盡管引起膿毒癥的病因不盡相同,但重癥患者均表現為嚴重免疫抑制狀態,然而其誘導免疫抑制的機制現仍未闡明。起初CHEADLE等[31]研究報道,膿毒癥創傷患者出現了顯著淋巴細胞減少。后續膿毒癥患者淋巴細胞減少開始引起越來越多的關注[32-33]。有學者報道膿毒癥誘導凋亡導致B細胞和CD4+T淋巴細胞的耗竭[33]。而HMGB1可通過與免疫細胞表面受體結合影響其增殖、分化和成熟。有研究顯示,HMGB1刺激人外周血T淋巴細胞48 h后,能明顯抑制T淋巴細胞增殖,同時能誘導T淋巴細胞免疫功能出現Th1優勢向Tp優勢偏移[34]。此外,有研究發現膿毒癥患者中TIM-3 CD4+T淋巴細胞的百分比與膿毒癥誘導免疫抑制的病死率相關[19]。HMGB1作為其配體,可能參與其調控。有學者進一步研究RAGE在Treg上的表達,發現RAGE表達明顯高于常規T淋巴細胞,HMGB1和RAGE相互作用后Treg功能明顯增強,但HMGB1對不同T淋巴細胞亞群功能的影響仍不明確[35]。免疫細胞凋亡方面,有學者發現抑制HMGB1-PTEN信號傳導可有效降低T淋巴細胞凋亡率,增加T淋巴細胞增殖活性,增強膿毒癥患者單核細胞功能[36]。另有研究顯示,膿毒癥大鼠中血清HMGB1水平升高對細胞免疫功能障礙有顯著影響,其機制尚不明確[37]。綜上,膿毒癥患者體內存在長期的免疫功能紊亂,HMGB1及其受體能否有效調節免疫細胞功能和凋亡,通過檢測相關下游通路探索其調控機制將是現階段的研究熱點。
4 小結
HMGB1是一種豐富的結構染色體蛋白,具有多種生物學功能,在細胞核內參與DNA復制、轉錄和翻譯等,還參與維持核小體的完整性,對生命活動不可或缺[38-41]。膿毒癥是一種由感染引起的危及生命的免疫障礙和器官功能障礙[42-44],膿毒癥引起的急性腎損傷最為常見,膿毒癥患者體內長期持續的炎癥反應及免疫功能紊亂是其病死率較高的最主要因素。現大多數學者對其研究方向聚集于下調HMGB1水平或抑制其相關信號通路,減輕炎癥風暴、改善組織受損程度,但單一減輕膿毒癥患者炎癥反應,對其致死率影響相對較小,現有的研究雖表明HMGB1對免疫細胞具有調控作用,但機制卻不明確。因此,從免疫紊亂角度出發,探索HMGB1對膿毒癥患者免疫功能的調節機制可能會是將來的研究熱點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