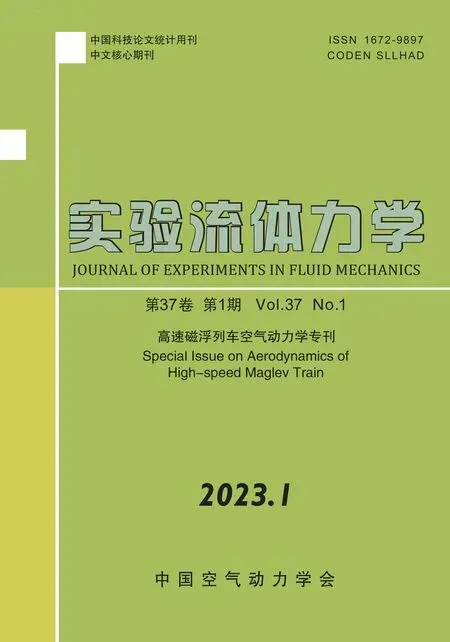真空管道磁浮交通車體熱壓載荷分布特征及其非定常特性
胡嘯,馬天昊,王瀟飛,鄧自剛,*,張繼旺,張衛華
1.西南交通大學 牽引動力國家重點實驗室,成都 610031
2.西南交通大學 超高速真空管道磁浮交通研究中心,成都 610031
3.西南交通大學 力學與航空航天學院,成都 610031
0 引言
超高速磁浮列車具有綠色、高速、輕量化等優點,是未來軌道交通的重要發展方向之一,相關技術研究也是當下熱議話題[1]。若將磁浮列車置于低真空管道內運行,將大幅度降低氣動阻力,減少氣動噪聲污染,使得磁浮列車速度有望達到跨聲速甚至超聲速[2-3]。從2019年開始,國家陸續出臺了《交通強國建設綱要》和《國家綜合立體交通網規劃綱要》等系列文件,支持超高速磁浮列車的發展。600 km/h常導磁浮交通系統以及高溫超導高速磁浮工程化樣車及試驗線的下線啟用,標志著我國高速磁浮領域取得了跨越式進展。為了開展高速試驗,2020年西南交通大學開始建設大科學裝置“多態耦合軌道交通動模型試驗平臺”(最高試驗速度1 500 km/h 的超高速真空管道磁浮交通試驗系統)。2021年,中北大學與中國航天科工集團第三研究院采用超導電動磁浮技術聯合建設高速飛車大同(陽高)試驗線,目標速度為1 000 km/h。
國內外學者對真空管道磁浮交通相關的基礎科學問題也開展了大量的研究。盡管磁浮列車在低真空管道內運行,減阻效果明顯,氣動阻力值與管內氣壓呈線性關系[4-7],但與空氣動力學相關的問題仍然存在。由于列車兩端為流線型頭型,運動的列車與管道系統構成動態的拉伐爾噴管[8-10](C–D 噴管)。根據等熵極限與Kantrowitz 極限,給定某個列車速度,存在著一個臨界車/管阻塞比,當實際阻塞比大于該值時,管內氣流將進入雍塞狀態,在尾流區產生激波,并在管道壁面反射傳播,惡化列車運行環境[7-8,11-12],這與進氣道中啟動/不啟動問題相似[13]。
Li 等[14]基于一維無黏等熵理論,推導了亞聲速管道列車在雍塞/非雍塞狀態下的氣流參數,與仿真結果吻合較好,同時Jang 等[15]對比了這兩種方法對氣動阻力的預測結果。侯自豪等[16-17]采用準一維數值模擬方法計算了3 種流動狀態(亞聲速通流、壅塞和超聲速通流)下特長管道內部流場特性,研究了管壁摩擦和列車加速對激波運動的影響。Yu 等[18]以質量流量為指標,理論分析了管道雍塞的相關規律和影響因素,同時基于二維軸對稱模型,利用CFD 仿真分析了管道列車在雍塞/非雍塞狀態下的氣動熱特性[19-20]。Zhong 等[21]考慮了車軌間隙,建立了三維車/管模型,重點比較了管道列車在雍塞/非雍塞狀態下的尾流演化,展示了尾渦結構和三維激波形態,與二維軸對稱模型的計算結果有著顯著差異,Hu 等[22]也得出類似結論。為了緩解雍塞效應,提高列車運行效率,國內外學者從列車外形[23-24]和管道結構[9,25]兩方面開展了優化設計研究。
綜上,管內雍塞狀態對列車運行環境帶來了嚴峻挑戰,目前的研究主要基于低維模型以及對稱模型對管內流場的預測,鮮有研究關注三維列車幾何表面熱壓載荷的分布特性[21,26]及其非定常特性,而車軌間隙流場[11]、尾渦脫落[22]和激波與邊界層干擾[27]均會造成車體載荷波動,帶來列車壁板氣動彈性問題[28]以及蒙皮材料的氣動疲勞損傷[29],從而威脅列車運行安全性、影響乘客舒適性。
鑒于此,本文建立高溫超導磁浮列車三維幾何模型,利用IDDES 模型求解管道列車周圍流場,探明雍塞/非雍塞狀態下列車表面熱壓載荷的分布特征;此外,由于通過傳統的CFD 結果難以厘清列車表面載荷的全局非定常特性[30],本文利用本征正交分解(Proper Orthogonal Decomposition,POD)提取流場重要相干結構,識別列車表面載荷非定常較強區域,揭示列車表面載荷時空演化規律。研究結果可為管道列車車體結構設計提供參考,助力真空管道交通模型試驗平臺的建設。
1 管內流動狀態判定
1.1 等熵極限與Kantrowitz 極限
車/管阻塞比和列車運行速度共同決定管內流動狀態(雍塞與非雍塞狀態),一般來說,給定某個列車速度,可通過等熵極限(式(1))與Kantrowitz 極限(式(2))求出臨界阻塞比[31-32]。
式中:β為車/管阻塞比,即列車車體橫截面積與管道凈空面積之比,下標IL 和KL 分別代表等熵極限和Kantrowitz 極限計算出的臨界值;vtr為列車運行速度;c 為聲速;γ為空氣比熱比,一般取1.4。
根據式(1)和(2)繪制了管內不同狀態下阻塞比與列車速度的對應關系圖(圖1)。可以看到,等熵極限與Kantrowitz 極限將管內流動狀態分成3 個區域,分別是非雍塞區域、雍塞區域和雙解區域[16-17]。雙解區域位于超聲速等熵極限和 Kantrowitz 極限之間,當列車運行條件位于此區域時,則管內流動存在兩種可能的解。
1.2 計算工況
目前真空管道磁浮交通的設計目標時速為高亞聲速和跨聲速,本文固定列車速度為800 km/h。為了比較管道雍塞和非雍塞狀態下車體熱壓載荷的非定常特性,這里根據圖1 設計了A、B 和C 這3 個計算工況,其中工況A 和B 屬于雍塞類型,而工況C 為非雍塞類型,具體參數如表1所示。

圖1 阻塞比與列車速度的臨界關系Fig.1 The cri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blockage ratio and train speed

表1 計算工況Table 1 Calculation case
2 數值模型
2.1 幾何模型
如圖2所示,本研究中使用的列車模型是基于高溫超導磁浮系統特點建立的全尺寸高速磁浮樣車。安裝在懸浮架上的低溫容器(也稱杜瓦),提供保溫隔熱作用。置于杜瓦底部的超導體在液氮的冷卻作用下進入超導狀態,并與永磁軌道提供的磁場環境相互作用,在宏觀上產生與磁浮列車本身重力平衡的懸浮力,并提供橫向穩定所需的導向力。高溫超導磁浮列車具有自懸浮、自導向、自穩定特性[1]。

圖2 真空管道磁浮交通系統幾何模型Fig.2 Geometric model of the evacuated tube maglev transportation system
列車編組方式為三車編組,包括頭車、中間車和尾車,各車廂之間采用風擋連接,每節車安裝兩個懸浮架,編號如圖2(a)所示,即頭車處為B1-1、B1-2,中間車處為B2-1、B2-2,尾車處為B3-2、B3-1。列車高度(Htr)為3.8 m,作為流場特征長度。列車流線型鼻長(Lsn)、車寬(Wtr)和列車總長(Ltr)分別為2.82Htr、0.89Htr和21.51Htr。此外,懸浮間隙(Hsg),即杜瓦底部和永磁軌道之間的垂向距離,為5.26×10?3Htr。低真空管道截面形狀參考高速鐵路的隧道斷面形狀,根據阻塞比大小確定工況A、B 和C 的管道凈空面積,其值分別為39.43、59.15 和118.29 m2。
2.2 計算區域與邊界條件
管道列車流動具有內外流場耦合特征,這與傳統高速列車的空氣動力學特性有較大區別[33-34]。具體來說,在流向方向上需要足夠長的計算域來應對由激波傳播引起的較大范圍干擾。根據初步的迭代計算結果,將列車放置在圖3所示的位置處(頭車距離入口130 Htr,尾車距離出口80 Htr),保證在采樣時間內激波不會從計算域的兩端溢出,從而避免邊界處能量損失。
模型中應用了三種邊界條件。綠色虛線表示自由流邊界,也被稱為壓力遠場,用于計算域的入口和出口,其中氣流的馬赫數、表壓和溫度分別設定為0.65、0 Pa 和288 K。為了模擬地面效應和管道效應,地面、軌道和管道使用移動壁面,即圖3 中的黑色實線,移動壁面的切向速度大小指定為來流馬赫數。紅色實線表示靜止壁面,應用于列車表面。

圖3 計算區域與邊界條件示意圖Fig.3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computational domain and boundary conditions
此外,管內的初始溫度(T0)和壓力(p0)分別為288 K、0.01 atm(1 013.25 Pa)。為了便于后續討論,坐標系的原點O 固定在尾車鼻尖下的地面上,坐標軸x、y、z 分別表示流向、展向和垂直方向。
2.3 計算設置
本文重點關注車體表面熱壓載荷的非定常特性,因此湍流的建模至關重要。本文采用IDDES 混合方法對湍流進行求解,指定SSTk ?ω模型對邊界層處進行建模,這種方法被廣泛應用于高速列車[35-36]和真空管道交通[21-22]的氣動特性研究中。
考慮管內氣流的強可壓縮性,采用STAR–CCM+軟件中的耦合隱式流體求解器。選擇AUSM+格式處理對流通量,可以準確捕捉激波的不連續性。對于對流項,選擇混合二階迎風/有界中心方案,混合系數為0.15。二階隱式時間步進格式用于離散時間項,時間步長為0.013 tref(tref= Htr/ vtr),保證大部分流場單元的庫朗數小于1。當計算時間到達46.78 tref后開始取樣計算平均量,此時流場的物理量沒有明顯的波動,除了由瞬態流場結構引起的非定常振蕩。整個采樣時間持續到112.58 tref。
2.4 網格劃分和獨立性驗證
利用STAR–CCM+軟件中Trimmer 網格和Prism layer 網格對計算區域進行空間離散。為了捕捉車體表面熱壓載荷波動,對車體表面和尾流區域進行多級網格加密,如圖4所示,列車表面最小網格尺寸為0.013 2Htr。為了求解列車壁面速度邊界層和熱邊界層,對列車表面劃分22 層棱柱層網格,拉伸比為1.2,第一層棱柱層網格厚度為5.26×10?5Htr。工況A、B 和C 的網格總數分別為2.44×107、2.62×107和2.91×107。

圖4 計算網格加密方案Fig.4 Refinement scheme of the calculation grid
雍塞狀態存在氣流阻塞以及尾部激波現象,流動較為復雜。這里挑選工況A(β=0.3,雍塞)來驗證網格獨立性,劃分3 套具有相同網格策略但密度不同的網格,詳細的網格參數如表2所示,其中y+為壁面第一層網格的無量綱高度。

表2 用于網格獨立性研究的3 套網格分辨率Table 2 Three sets of grid resolutions for grid independence studies
壓力系數Cp定義如下:
式中:p為靜壓,ρ為空氣密度。
圖5 比較了3 套網格下列車側表面平均熱壓載荷的計算結果。可以看到,3 套網格計算的熱壓載荷分布趨勢一致,主要差異在于局部流動分離區域(如風擋處、尾車流線型處),而這些局部流動分離區往往是非定常特性較強區域,此外中網格和細網格的結果差異比粗網格和細網格的結果差異小得多。對比圖5(a)和(b)可以發現,相較于壓力,溫度對網格尺寸更加敏感。

圖5 不同網格密度對列車側面(z=0.53Htr)平均熱壓載荷的影響Fig.5 Effect of different grid densities on the time-averaged temperature and pressure load on the side of the train(z=0.53Htr)
綜合考慮計算資源和計算準確性,本文使用中等網格密度來評估真空管道磁浮交通車體熱壓載荷分布及其非定常特性。
2.5 風洞驗證
截至目前,尚未有公開的真空管道交通系統氣動試驗數據,相關高速試驗平臺正在建設中。本節利用Inger 等[37]在克蘭菲爾德大學航空學院跨聲速風洞測試的試驗數據來驗證數值方法在模擬管內雍塞狀態氣動特性的可靠性。如圖6所示,風洞試驗底部平順,上表面安裝了半徑(R)0.58 m、高度0.02 m的圓弧凸塊,其截面變化構成了一個拉瓦爾噴管,與本研究中的列車截面積變化非常類似。為與風洞試驗進行對比,設置驗證工況參數與試驗一致(來流馬赫數0.73,初始溫度310 K),坐標系為x'O'y',其他參數可參見文獻[37]。

圖6 跨聲速風洞試驗段模型設置示意圖Fig.6 Schematic drawing of model setup in transonic wind tunnel test section
圖7 比較了模型上表面壓力系數(Cp)的試驗數據與數值仿真結果。從結果來看,兩者吻合良好,并且數值仿真對激波位置和強度的捕捉也較為準確。觀察壓力系數隨截面變化的趨勢可以發現:在收縮段(0 m 圖7 上表面壓力系數分布對比Fig.7 Comparison of upper surface pressure coefficient distribution 本征正交分解(POD)也被稱為主成分分析,是數據降維和模態分解中最普遍使用的方法之一,被廣泛用于識別列車尾流相干結構[30,38-39]。總的來說,POD 算法將流場矩陣分解為一系列相互正交的基函數和對應的時間系數,保證基函數在最小二乘意義上是最優的,以捕獲盡可能多的能量。基函數代表流場的空間模態,時間系數則表示時間模態,即POD 算法主要分析空間模態隨時間的演化過程,其具體分解過程如下: 1)對一段時間區間[t1,tn]的空間流場進行采樣,在ti(i=1,2,···,n)時刻,m 個空間網格點流場數據構成的向量u(ti)=[u(x1,ti),u(x2,ti),···,u(xm,ti)]稱為一個流場快照。空間網格點流場數據可以是瞬態數據,也可以是瞬態數據減去平均值后的脈動值,本文使用脈動值進行降階分析。 2)將n 個流場快照數據合并為矩陣U: m × n 維矩陣U集合了流場的時空信息。按照POD 定義,將矩陣U分解為如下形式: 式中:?j(x)為一個基函數(空間模態),aj(t)為對應的時間系數。 3)為保證基函數在最小二乘意義上是最優的,求解矩陣U的協方差矩陣R的特征向量和特征值。協方差矩陣R定義如下: 在工程應用中,通常降階區域的網格數量m 很大,矩陣R的維度(m × m)也會非常大,使得求解困難。本文采用Sirovich[40]提出的快照POD 算法,將R簡化如下: 求矩陣R的特征向量ψj和特征值λj的方法如下: 4)在確定了上述較小維度特征向量ψj后,通過以下方式擴展到原始 POD 模態: 時間系數aj(t)為空間向量u(t)在基上的投影: 當?j為單位化的基,上式可寫成: 本文對列車表面溫度和壓力標量進行采樣,采樣時間間隔為0.065tref,快照總數為1 000 個,對頭車、中間車以及尾車熱壓載荷分別做POD 降階分析。 圖8 比較了管內雍塞/非雍塞狀態下列車表面壓力與溫度分布。根據列車截面變化,將列車表面分成3 個區域:頭車流線型區域,即收縮段(?21.51 從圖8(a)和(b)可以看出,雍塞狀態(工況A 和B)和非雍塞狀態(工況C)下的列車上表面熱壓載荷分布特征對應著拉瓦爾噴管的兩種模式[41]。結合圖9(a)和(b)可以看到,對于工況A 和B,氣流在收縮段加速,車體上表面壓力和溫度快速下降;在平直車身區域,除了風擋截面變化引起的局部流動分離,車體上表面熱壓載荷繼續下降,但下降幅度小于收縮段,這是由于邊界層發展造成的氣流流動面積進一步減小,本質上頭車流線型區域和平直車身區域均屬于收縮段,前者是幾何截面變化,后者屬于物理流動面積變化;在擴張段,氣流繼續加速至超聲速,直到遇到激波,氣流減速,溫度和壓力上升。同時比較工況A 和B,除了激波產生位置和激波角度(圖9(d)和(e)),兩者分布規律基本相同。增大阻塞比,激波位置向車尾鼻尖移動,易發生激波脫離[26]。與雍塞狀態相比,非雍塞狀態(工況C)下車體上表面熱壓載荷分布最大差異體現在擴張段,由于喉部速度未加速到馬赫數Ma=1.0(圖9(c)),氣流在擴張段減速,壓力和溫度升高,車尾也無激波產生。其次在平直車身區域,非雍塞狀態氣流順利通過,車體上表面壓力和溫度下降速度遠小于雍塞狀態。 圖9 y=0 平面時均馬赫數分布Fig.9 Mean Mach number distribution projected on a plane at y=0 如圖8(c)所示,由于狹小的車軌間隙和懸浮架腔體的截面突變,列車下表面熱壓載荷分布較為復雜,使得列車核心部件—懸浮器處于惡劣的環境,非常值得關注,而這部分在已公開發表的文獻中鮮有涉及[22]。從壓力分布來看,沿流向(車頭→頭尾)總體呈下降趨勢,在懸浮架腔體處壓力出現大幅度波動,特別是頭車第一個B1-1 處,工況A 在此處的壓力系數波動幅值達到3.36,減小阻塞比能夠緩解波動強度。氣流從頭車鼻尖分流,一部分沿著頭車流線型向管道上方發展,另外一部分突入車軌間隙處,當遇到第一個懸浮架腔體,會形成局部滯止點,這也是壓力大幅度波動的原因。 圖8 不同流動狀態下列車表面熱壓載荷時均分布對比Fig.8 Comparison of the time-averaged distribution of train surface temperature and pressure load under different flow conditions 從溫度分布(圖8(d))來看,不論管內是雍塞還是非雍塞狀態,車底溫度都顯著高于車頂,這對車底蒙皮材料強度提出了挑戰。對于雍塞工況A 和B,由于氣流在平直車身區域阻塞,熱量無法及時耗散,在尾車第二個懸浮架B3-2 附近達到峰值,工況A 和B 的峰值分別為382 和375 K。在較小阻塞比(工況C)下,溫度峰值反而比雍塞工況大,高達420 K,位于尾車第一個懸浮架B3-1 腔內。 為探究其產生原因,繪制了尾車底部附近時均流線分布,如圖10所示。在工況A 中,激波使得尾車邊界層分離,隨后重新附著,在列車頂部和側墻下洗氣流與底部上洗氣流相互作用下再度分離,在尾車鼻尖附近形成了兩個連貫的分離泡V1 和V2,兩種氣流在鞍點S 處混合為一股氣流,向尾流后方發展。在工況B 中,列車頂部和側墻下洗氣流增強,形成回流突入尾車流線型底部,并與底部上洗氣流相互作用,形成一條分割線l。在工況C 中,頂部和側墻下洗氣流繼續增強,在尾流中占據主導地位,以回流方式進入尾車底部,將底部上洗氣流“堵”在尾車第一個懸浮架B3-1 腔內,造成局部阻塞,產生局部高溫。 圖10 y=0 平面時均流線與溫度分布Fig.10 Mean flow velocity streamlines projected on a plane at y=0 colored by temperature 為了研究車體表面壓力和溫度載荷隨時間的演變規律,在列車上下表面典型位置布置一系列氣動參數監控點,如圖11所示。其中序號P1-1和P3-1分別位于頭、尾車鼻尖,P1-2、P2-1和P3-2分別在頭、中、尾車平直車身頂部,P1-3、P1-4、P2-2、P2-3、P3-3和P3-4分別在懸浮架腔體內部中心處。 圖11 列車上下表面監控點分布Fig.11 Distribution of monitoring points on the top and bottom surfaces of the train 圖12 和13 分別給出了尾車鼻尖監控點P3-1、中間車懸浮架腔內監控點P2-3的熱壓載荷時間歷程曲線和頻域分布。限于篇幅,其余監控點的相關統計信息整理在表3 中,不再單獨贅述。圖中時間用無量綱時間t*表示: 如圖12所示,隨著阻塞比增大,尾車鼻尖流場波動加劇,特別是溫度載荷。工況A 的溫度波動最大幅值(最高溫度–最低溫度)達到75 K。流動分離和尾渦脫落是引起載荷波動的主要原因,結合圖10可以發現,工況A 尾車鼻尖附近存在兩個連貫的分離泡,工況B 僅有一個分離泡,而工況C 僅可觀察到一個較小的回流區,因此相較于工況A 和B,工況C 載荷波動較小。從頻域來看,對于阻塞比為0.3 的工況A,壓力和溫度載荷波動的主頻分別為0.89 和13.35 Hz,同時還存在多個峰值的次頻,說明存在著多尺度非定常流場結構。對于阻塞比分別為0.2 和0.1 的工況B 和C,壓力和溫度載荷波動的主頻均為小于5 Hz 的低頻。 如圖13所示,由于列車底部流動非常復雜,監控點熱壓載荷均值與阻塞比沒有對應關系,主要由底部流動狀態決定。3 個工況下壓力載荷均呈現準周期波動,波動頻率在15 Hz 附近。溫度載荷從總體看呈現上升趨勢,這是因為底部熱量因無法及時耗散而累積,使得溫度波動主頻為低頻(0.89 Hz),同時溫度載荷在上升過程中,由于底部流動分離和尾渦脫落也存在著小范圍的準周期波動。 圖13 中間車懸浮架腔內監控點P2-3 瞬時載荷波動和頻域分布Fig.13 Transient load fluctuations and frequency domain distribution of monitoring point P2-3 at the bogie cavity of the middle car 基于POD 降階方法,提取3 個工況頭車、中間車以及尾車的熱壓載荷主要振蕩模態和頻率,識別非定常強度較強區域。圖14 給出了尾車載荷前25 階模態能量占比。由圖可見,能量占比隨著模態階數增加衰減很快,前幾個高階模態對載荷非定常貢獻較大,捕獲了大部分振蕩特性,特別是溫度載荷,工況A、B 和C 的第一階模態能量占比分別為74%、68%和68%。因此本文重點分析前兩階模態模式與頻率特性。 圖14 尾車熱壓載荷各階模態能量占比對比Fig.14 Comparison of the energy contribution of each mode in the pressure and temperature loads of the tail car 圖15~17 分別給出了頭車、中間車和尾車的壓力載荷前兩階POD 模態,其中為降階之后的無量綱壓力系數。如圖15所示,對頭車壓力載荷波動貢獻較大的區域位于車底懸浮架腔內,從模態云圖來看,頭車懸浮架底部存在多種尺度的非定常流動結構。從時間系數的頻率分布亦可看出,除了主頻峰值外,還存在多個峰值的次頻。 圖15 頭車壓力載荷前兩階POD 模態Fig.15 The first two POD modes of head car pressure load 如圖16所示,與頭車壓力載荷波動相比,中間車波動較為規律。3 個工況下占主導地位的均是頻率在14 Hz 附近的單一流動結構,再結合表3 和圖13(c)可以發現,這與監控點P2-2和P2-3的壓力主頻或次頻較為一致。從云圖分布來看,除了相位差導致的正負差異,3 個工況的模態結構非常相似。 圖16 中間車壓力載荷前兩階POD 模態Fig.16 The first two POD modes of middle car pressure load 如圖17所示,尾車壓力波動模態主要位于兩個區域。其一是列車上表面和側面,只存在雍塞工況(工況A 和B)。對于雍塞工況,尾車表面產生斜激波面,激波與邊界層相互作用,造成流動分離,是一個非定常源。由于激波強度的差異,工況A 激波導致的非定常波動出現在一階模態,而工況B 則出現在二階模態。其二是列車底部懸浮架腔內,從模態云圖來看,波動較強區域主要位于尾車第二個懸浮架B3-2 處,并且流動結構與中間車底部較為類似,主頻也在14 Hz 附近,這說明14 Hz 為該懸浮架的一個特征頻率。同時對于工況C,二階模態的振動頻率除了主頻16.02 Hz 外,還存在29.37 Hz 次頻,該頻率下的流動結構可能與二階模態云圖中區域Ⅰ相關。這也與圖10 分析結果吻合,在工況C 下,頂部和側墻下洗氣流將底部上洗氣流“堵”在尾車第一個懸浮架B3-1 腔內,造成非定常脈動。 圖17 尾車壓力載荷前兩階POD 模態Fig.17 The first two POD modes of tail car pressure load 圖18~20 分別給出了頭車、中間車和尾車的溫度載荷前兩階POD 模態,其中T*為降階之后的無量綱溫度。如圖18所示,與壓力載荷類似,對頭車溫度載荷波動貢獻較大區域也位于車底懸浮架腔內,特別是兩個懸浮架后端杜瓦表面。一階模態和二階模態空間結構相似,且波動頻率相同,因此一、二階模態為一對模態,且存在相位差,這種關系對應于流動結構中的對流[30,38]。 圖18 頭車溫度載荷前兩階POD 模態Fig.18 The first two POD modes of head car temperature load 如圖19所示,中間車溫度載荷一階模態與壓力載荷截然不同,從時間系數來看,溫度載荷一階模態呈現增長趨勢,這是因為中間車底部熱量在密閉低氣壓環境下無法及時傳遞與耗散,隨著列車運行累積在底部,這也是表3 中監控點P2-2和P2-3溫度載荷波動主頻為0.89 Hz 的原因。本質上該現象不是非定常流動結構造成的,而是熱量累積導致的超低頻頻率。由于采樣時長等因素的影響,本文最低識別頻率為0.89 Hz。從模態云圖(圖19(a))看,熱量累積較強區域位于中間車第二個懸浮架B2-2前端區域Ⅱ,需要重點關注此處的溫度極限。溫度載荷二階模態則為非定常流動結構導致的周期波動,波動主頻在14 Hz 附近,與壓力載荷波動頻率一致。 圖19 中間車溫度載荷前兩階POD 模態Fig.19 The first two POD modes of middle car temperature load 如圖20所示,對于尾車溫度波動一階模態,工況A 與工況B、C 有較大差異,從時間系數來看,工況B、C 呈現上升趨勢,與中間車溫度載荷一階模態類似,而工況A 則無明顯增長趨勢。這主要是因為3 種工況中尾車底部也均存在著熱量累積,與中間車類似,熱量累積較強區域位于尾車懸浮架前端區域Ⅲ和Ⅳ處。但是工況A 尾車上表面還存在激波引發的局部非定常區域,與底部熱量累積效應“中和”,因此在時間系數上表現為無明顯增長趨勢。這點在尾車鼻尖監控點P3-1的瞬時溫度載荷波動(圖12(b))中也有所體現。尾溫度載荷二階模態為非定常流動結構導致的周期波動,3 個工況波動主頻均在14 Hz附近,與壓力載荷波動頻率一致。同時觀察到工況C 的波動幅值最大,這是由于下洗氣流回流導致的。 圖20 尾車溫度載荷前兩階POD 模態Fig.20 The first two POD modes of tail car temperature load 本文從時均分布、瞬時波動以及POD 降階3 方面研究了真空管道磁浮交通雍塞狀態(β=0.3,0.2)與非雍塞狀態(β=0.1)下車體熱壓載荷分布特征及其非定常特性,得到結論如下: 1)列車上表面載荷分布特征與拉瓦爾噴管相似。兩種狀態下載荷分布差異主要位于擴張段,雍塞狀態下氣流加速至超聲速,載荷降低,直至激波產生,氣流減速。非雍塞狀態則相反,且不會產生激波。 2)列車下表面熱壓載荷分布較為復雜。氣流在第一個懸浮架腔體形成局部滯止點,造成壓力大幅度振蕩。同時熱量在列車底部無法及時耗散,雍塞狀態下在尾車第二個懸浮架達到峰值,而非雍塞工況的峰值則在尾車第一個懸浮架腔內,且大于雍塞工況的峰值。 3)頭車壓力載荷脈動較強區域位于車底懸浮架腔內,存在多種尺度的非定常流動結構,造成中間車壓力波動為14 Hz 附近的單一流動結構。雍塞狀態下尾車壓力波動位于激波處和底部懸浮架腔內,非雍塞狀態則只位于懸浮架腔內。 4)頭車溫度載荷脈動較強區域位于懸浮架后端杜瓦表面。中間車溫度載荷一階模態體現為熱量累積過程,二階模態為非定常流動結構導致的周期脈動。不同阻塞比的尾車溫度載荷一階模態存在差異,工況B 和C 為熱量累積過程,而工況A 則是激波引發的局部非定常效應與熱量累積耦合作用。 在面向真空管道交通運行的車輛設計過程中,需特別關注列車底部熱量累積,避免蒙皮材料損傷,同時需進一步優化平順懸浮架結構,降低載荷波動。此外,雍塞狀態的尾車激波作用處也需特別關注。 致謝:感謝國家超級計算鄭州中心支持!
3 本征正交分解(POD)
4 結果與討論
4.1 車體熱壓載荷時均分布特征



4.2 車體熱壓載荷瞬態波動特征


4.3 POD 降階分析







5 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