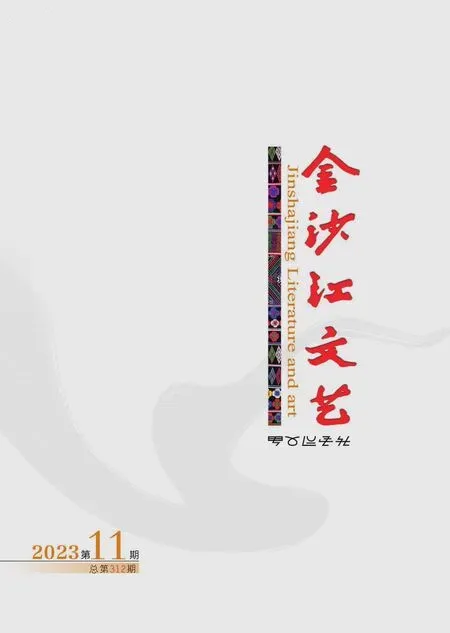桃花鉤月夜
◎李紹全(彝族)
1
不想不想又想著了,就像麥田里流淌的灌溉水,從高往低,嘩啦啦,灌滿一條地縫,又鉆入另一條地縫,漫無目的,哪兒低洼就往哪兒淌,把麥苗喊醒,把油菜喊醒,把小蟲兒嚇跑,把他攆到月光下,仿佛快要抓著他了。桃花越想越起勁,越想越溫暖,就像邁過了冬天,奔跑在春天里。
婆婆尖細的目光一下子就鉆到桃花的心里了,說,給他打個電話吧。
婆婆說的他,是桃花的男人鄭向乾。鄭向乾在正月二十的早晨,和村里的一群男女擠上一輛大班車,前往江蘇無錫打工去了,桃花不是不想鄭向乾,但這時她想的不是自己的男人,而是想著那個不知是誰的男人,叫項派。
桃花明明是看準了婆婆癡迷地看著電視的時候才開始想的,這樣,她的表情無論多么豐富,婆婆都不會看見自己的心事。但是,在她忍不住微笑一下的剎那,婆婆突然冒出那么一句話,就把她嚇了一跳,心頭好像被電觸了一下。莫非婆婆知道自己的心事了?桃花抬頭看一眼婆婆,婆婆的目光落在她手里的苞谷棒子上,苞谷籽在她熟練地搓剝中嚓嚓嚓地脫落下去,婆婆并沒有抬頭看她。桃花輕輕地吸了吸氣,把自己放松下來,說,不,不打了。
鄭向乾上個月打電話說準備在過年的時候回來。過幾天,又打回來說江蘇的疫情非常嚴重,一陣子封這個廠,一陣子又封那個小區,估計過年也回不來了。不回就不回,安心上班吧。桃花本來是希望自己的男人早點回來的,但話到嘴邊卻又變了,好像是被項派代替她說了似的。壞透了,壞透了,桃花覺得鄭向乾和項派壞透了,把她的心扯過來拽過去的。
打吧,婆婆又說。
不打,免得影響他們休息,桃花說。
桃花的心跳還沒有完全平靜下來,項派還在她的心上轉悠著,她不知道在電話里和鄭向乾說點什么,她和他一直不怎么說話,他們誰眨一下眼,對方就猜到了要說什么,這種感覺曾經讓她擔心在一夜之間失去說話的功能,此時,她覺得自己擔心的事情正在發生了。
你不打我打,婆婆說,把剝了一半的苞谷棒子丟在腳邊,順手抓過手機,急切地劃拉著屏幕。這時,夜有些冷,時間還不算晚,十點來鐘,村里卻靜了,靜得仿佛能聽到星星的吵架聲。
趁婆婆忙碌時,桃花暗暗趕著項派快點離開自己的心窩。她在心里念到,快點走,快點走,最好婆婆接通電話之前就走開。但是,她越是這么想,項派的影子就越清晰,離她就越近。桃花一點辦法都沒有,在婆婆撥打電話的間隙,又忍不住想了一會兒。這時,她感覺越來越迷亂了,亂得有些滋味,好像是甜的,又好像是苦的。桃花一邊使勁地看電視畫面,一邊狠狠地搓剝苞谷棒子上的籽兒。
婆婆用手示意她停手,她沒有看見,苞谷籽在她凌亂的雙手中嚓嚓嚓地脫落。婆婆就生氣了,用命令的口吻說,不要弄出聲音來。
桃花趕緊停下手中的活計,把電視機關在靜音上。剛安靜下來,婆婆的手機里就傳來了響亮的男高音:“有哪樣事?趕緊說。”
那是公公鄭梁柱的聲音。
婆婆本來想聽一聽男人雄厚的聲音,讓男人的聲音在心中立起一座大山,在男人的聲音里找一片春天的鮮花,給生活增添一份精彩的。但是,公公鄭梁柱的聲音非常生硬,像陽光炙烤的馬路牙子,用火柴輕輕一擦,就可能擦出火星子來。
“這頭老水牛,你哞哞什么,給是家里的婆娘都不會想了。” 婆婆的聲音比公公的聲音還剛硬,像彎彎的鐮刀碰撞水泥地板。
“沒事就掛了,影響大家休息。”電話里又傳來公公的聲音。顯然,公公他們住的是集體宿舍,一聲簡潔的道別,就什么聲音都沒有了。
婆婆怒氣沖沖,把手機遠遠地丟在滿是苞谷籽的沙發上,對桃花說,電話打通了也不知道好好說幾句,還說影響大家休息,難道這么早就睡了?難道真的變雞了?
桃花說話的功能突然強大了起來,說,媽,你一大把年紀了還天天想男人,那么想就不要讓他去打工呀,羞羞羞,一邊比畫著鬼臉,一邊向另一間屋子躲。婆婆好像想起了什么,說,明明是你在想,臉都想成紅桃了,還說我想,我才不想呢,老男人有什么想的呢。讓你打,你又不打,還害得我受那死老倌的氣。一邊拿玉米棒子砸向桃花,一邊又故意不砸著桃花,砸得苞谷籽滿地飛濺,像凌亂的子彈,打得婆媳倆心花綻放。桃花一邊開心地尖叫著,一邊抱頭沖進自己的臥室躲子彈去了,把無聲的電視畫面和靜寂的客廳留給了婆婆。
桃花一關上臥室的門,項派就闖進了她的心窩窩。
2
那是中秋前夕的傍晚,桃花買東西從縣城返回,租了一輛出租車,兩百元,有點貴,但沒有辦法,六七十公里路,還帶著過節的食品,司機又是女的,有安全感。桃花和司機有一句沒一句地聊,驅散一些陌生感,勾起許多美好的憧憬,要是自家也有一輛車,想慢就慢,想快就快,想去哪兒就去哪兒。桃花和丈夫鄭向乾曾經想過要買一輛車,但那是長遠的目標,他們剛建好房子,還欠了不少賬。桃花把遙遠的鄭向乾想到了身邊,幻想著司機是鄭向乾,車里是一群親人。但意外總是在不經意間在美好的心情下發生,影響著她愿意或不愿意的心情,只聽嘣一聲爛響,車蛇行了幾米遠就不動了。女司機說,完了完了,拉開車門,下車,說爆胎了,走不了啦。女司機打了一個電話,是免提,聽得出是向她丈夫求援。司機的丈夫好像很忙,說不上幾句話,她們就在電話里吵了起來,不說來,也不說不來。女司機把電話裝回包里,又繞車子走了一圈,爆胎的位置是左前輪,剛才爛響的那一聲是車在蛇行中碰撞到了路邊的護欄上了。
桃花又急又怕,說,大姐,要什么時候才能處理得好,還能不能走,能不能在天黑前把我送到家。女司機說,妹子,你別怕,再等下,我再問問,要是他不來,我就打電話給修理廠,要是一會兒弄不好,我就另外叫一輛車,把你安全送回家就是了。桃花說,好,好,那太謝謝你了,我家里的男人不在家,婆婆盯得緊,要是天黑了才回去,婆婆就會猜疑,就會和我鬧,弄不好還會向我男人瞎告狀,讓他瞎擔心。正說間,旁邊來了一輛黑色轎車,緩慢地駛過來,走了幾米遠,又把車停下來,伸出頭說,美女,需要幫忙嗎。男人是對著女司機說的,他好像看見她的車胎爆了,他好像知道有人同路。桃花不知道男人其實已經猜到她要回新村,至少是同方向,男人其實就是想幫助她的,但她不知道,她不敢出聲,她只是希望男人能夠幫助出租車司機。這時,出租車司機快步走過去,說,大哥,真的要麻煩你了,我的車爆胎了,前保險桿也撞了快掉下來了,我要報保險,一時半會處理不好。想請你把這位妹子帶到新村一下,路費我付給你。男人笑笑,說,上車吧。出租車司機慌忙幫桃花把東西拎到男人的車上,讓桃花從右后門上車。男人說,坐前面吧,給我指路呢。出租車司機就把副駕駛門打開,讓桃花坐上去。桃花本來是不坐男司機的車的,打出租時,就喊了第七輛車才攔到那個女司機的車,還被那些男司機罵她是神經病。但在半路出了意外,雖然也是一個男司機,但她沒有選擇了,半推半就,勉強坐上去了。出租司機說,小妹,對不起你了,就讓這位大哥拉你回去吧。然后又再三感謝男人。說,大哥,我把車費付給你,你手機給我掃一下碼,我沒帶現金。
男人不說要,也不說不要,啟動車子緩緩朝前。走了二十多米遠,男人說,小妹,請你把安全帶系上。桃花就去拉安全帶,但沒有拉動。男人說,輕輕拉,拉重了拉不出來、桃花輕拉重拉也沒有把安全帶拉出來,臉就紅了。男人就把車停在路邊,伸手去幫她拉安全帶。男人輕扯重扯也沒有扯出安全帶,異常了。
桃花對男人的排斥感就是在這個停車、系安全帶的環節上產生的。男人的手碰到了桃花的胸口,桃花的臉原本就紅了,此時仿佛點燃了,火焰燎滿了全身,魂都掉了。這個男人可能有壞心思,要提防呢,但她不知道怎么堤防,下車不坐了,顯然是不行的,新村沒有公交車,平時,過路車也很少,搭車十分困難。正在胡亂思想,男人下車了,從左邊繞到右邊,拉開車門檢查了一下,安全帶被座椅卡住了。男人想起來了,那是前天下午,他把座椅放平,在上面躺了一會,聽了一陣音樂,收座椅時沒有注意安全帶被卡住。他向桃花解釋說,安全帶卡住了,這兩天都沒有人和我坐車,也不注意卡住了。桃花沒有出聲,她還在胡亂地想著擔心著。男人把右后門打開,把安全帶從卡住的位置解開,輕輕拉長,遞給桃花。這時,他才發現桃花的臉紅得像春天的桃花,白里透紅,漂亮極了。新村留給他的破敗的景象因桃花的羞澀一掃而光。出于禮節,沒有多看,他把目光快速移開了。桃花的心都要跳出來了,婆婆交代過她,她男人不在家的時候,她不準與其他男人眉來眼去的,特別是陌生的男人和油腔滑調的男人。婆婆的話有些封建,還霸道,像一捆干刺,橫攔在面前。此時,桃花和男人挨得那么近,又塞在一輛車里,陌生的氣味彌漫開來,包圍著她,就那么一瞬間,她感覺婆婆的雙眼狠狠地瞪著她。同時,她懷疑男人會不會用藥水把她迷倒,用煙霧把她弄昏,然后……,這種想象仿佛是一個幽靈,住在冬天與春天的分水嶺上,往左是冰封大地,讓人迷茫而絕望,往右就是春暖花開,讓人充滿希望。桃花的想象走向了冬天,她暗自問,今天是怎么了,坐個出租車,車胎爆了,坐順路車,安全帶又卡住了。桃花越想越亂,竟然連男人遞到手里的安全帶都插不進去了。男人就把頭伸進副駕駛室,幫她系上安全帶。男人說,不系安全帶,遇上交警會罰款,主要是為了安全,安全帶也叫生命帶。桃花不好意思地應了一聲,覺得男人的解釋非常合理。但不知道為什么,發生在身上的異樣感覺讓她對男人越來越排斥,男人的手仿佛是一道電光,劃過胸口,猶如觸電。桃花的男人鄭向乾出去打工以后,桃花沒有和別的男人打過交道,更沒有像此時此刻,和陌生的男人挨得那么近。平時,她和姐妹們閑聊,有時會聊聊情感問題,三言兩語,總會激起她一種莫名的渴望。此時,那種渴望卻消失殆盡,取而代之的是強烈的排斥感,她得看住男人不準用噴霧劑之類的東西,也不準抽煙。車離家越近,排斥感越強烈。桃花甚至懷疑男人停車、幫她系安全帶這個環節是他故意設的圈套,是自己傻傻地鉆進了他的圈套。
男人名叫項派,是上面派來幫助新村鞏固脫貧攻堅成果和鄉村振興的。男人第一次來,桃花把他引到村委會。
3
桃花一有心事,就找事情做,最喜歡做的事情是剪紙,最好的手藝也是剪紙,《紅軍長征過我家》 那幅作品還獲得縣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展優秀獎,獎狀還在床頭柜里,壓在珍貴的項鏈、戒指和手鐲下面。有一次,桃花去縣文化館參觀民間文藝作品展,遇到一個穿著彝族服飾的大姐,那些構圖簡單、色彩鮮艷、對比強烈,彌漫著春天氣息的圖案,瞬間把她深深吸引了。桃花魂不附體地輕輕飄過去,仔細地欣賞,忍不住用手摸了摸那鮮活著一樣的茶花圖案,愛不釋手。大姐很客氣,對她微微一笑,親切地說,小妹,你也喜歡刺繡呀。桃花陶醉著點點頭,感覺靈魂被她帶著飄起來了,很輕很輕,在空中飄舞著。她們熱情高漲地談論起刺繡和剪紙,心靈一下子就近了,一下子就粘在一起了。桃花覺得那就是愛好相同,就是興趣吻合,就是志同道合。雖然她是剪紙的,大姐是刺繡的,但不知道為什么,桃花就是覺得有一個神秘的人物在她們中間,一手拉著她,一手拉著大姐,堅定地朝一個開滿鮮花的春天奔跑。大姐的名字叫羅潔。羅潔說,我只會剪一些傳統的老式圖案,都是年輕的時候母親手把手教我剪的,現在母親已經不在人世了。羅潔說,有一次,北京那邊過來一個老板,見我剪的圖案和一件衣服上繡的花很像,就問我剪紙與刺繡是什么關系,我告訴他衣服上的圖案是我剪的,是我的師姐刺繡上去的。那老板一聽,臉上樂開了花,說那才是真正的手工作品,是真正的藝術作品,就高價買走了那套衣服。老板還讓我在剪紙方面加入一些現代元素,多一點符合年輕人喜歡的元素,那樣銷路就會更廣,但我沒有多少文化,哪里知道什么現代元素。桃花不知道該怎么接上羅潔的話,她把羅潔拉到一幅 《春漫彝家》 的剪紙作品前,說,大姐,這是我剪的作品,我喜歡想象,像做夢一樣,你幫我提提意見吧,看我能不能再提高一些手藝。桃花的剪紙手藝引起了羅潔的強烈興趣,羅潔的刺繡也激發了桃花極大的興趣。桃花從羅潔那里拿了一份訂單,說休閑時試試,看能不能繡成功,如果繡不成功,她會負責所有費用。桃花天生手巧,第一件作品就讓羅潔吃驚了。羅潔分給了她一部分訂單,桃花坐在家里都能掙錢了。婆婆說,桃花真能干,坐在家里也能掙錢,要是兩個男人在家也能掙錢就好了,我們就不必守活寡了。桃花撲哧一聲笑了,說,媽,世上哪有那么好的事啊,我掙的只是零花錢,沒有辦法的辦法,要致富還得外出打工。
桃花剪紙時,總是天馬行空,蕩漾在春天的花海里,每剪完一幅作品,她都感覺如獲至寶。這一天,桃花正在醞釀一幅作品,是鄉婦聯的約稿,要參加縣上的展覽。桃花構思的內容是美麗村莊方面的,名字都取好了,叫 《春到新村》。有了內容,有了名字,一幅生動的作品就在心中展現出來。桃花很激動,只有用剪刀把心中的圖案表現在眼前,心里才會輕松,她看準了一個切入點,準確地剪了一刀,剪刀還沒有展開,外面傳來了一聲尖叫,仿佛是剪刀剪在了誰的胸口上。桃花停住了手,聽出那是婆婆的聲音,像雨點打在彩鋼瓦上,嘀嘀嗒嗒,凌亂而不可收拾。婆婆又和別人吵起來了,婆婆對自己好得像親閨女,但對外面的人卻不好,她反復說防賊防狗防蛇防干部,一樣都不能少。
桃花丟下剪刀和紙,風一樣跑出門。天吶,婆婆扯著男人的手袖,用尖厲的女高音命令男人拿錢,男人無助地任她擺布著。婆婆說,不給錢就別想走。婆婆果然又做出意想不到的舉動,連桃花都想不開了。桃花從她們旁邊的黑色轎車上準確地判斷出婆婆的心思了,她在訛詐項派。
“樹活一張皮,人活一張臉。” 桃花的腦海里突然閃過這句諺語。她沖到婆婆面前,扯一下婆婆的袖子,生氣地說,媽,你做什么嘛,快放開人家,人家是上面派來的干部。桃花差點把我還欠人家車費這句話說出來了,好在反應快,把話塞回肚子里了。婆婆說,管他是什么部,碾著我家地板就得賠錢。桃花欲言又止,忍了一會兒,終究沒有忍住,說,媽,你丟死人了! 婆婆哪能受得桃花生氣和指責,說,我丟人,我丟誰的人了,他又不是你的野男人,再說,野男人你就更不能在我面前護著他。桃花欠男人的車費,婆婆又向人家索要錢,場面戲劇般沖突起來。
婆婆向院子里掉頭的司機索要掉頭費,掉頭一次,索要十元錢,誰勸都不聽,說,哪個開車的會缺十塊錢。婆婆想出的這一招,誰都沒有想到,誰都勸不住他,那就讓他收吧,大家都這么說,慢慢地,附近有車的人就不再走這個死胡同了。桃花家在村尾,一條狹窄的村間道路直通村尾,司機一旦把車駛入,就只能前行,行駛到桃花家的院子就無法再前行。桃花家院子寬敞,倒是能輕松掉過頭來,駛出那個問號一樣的狹窄的村間道路。桃花的男人鄭向乾出去打工之前,曾經向村里提議,要把村間道路繼續往前修,繞兩個彎接上主路,這樣就四通八達了,但村小組長當時就答復他,說,哪來的錢修路,白日做夢。鄭向乾又把這個建議寫成書面材料,交給村里的人大代表,請他和村委會提議。后來,鄭向乾就出去打工去了,她家院子就成了掉頭場。桃花的婆婆看見車來車往,被人叫了個晦氣的名字,就使勁地想出了一個辦法,她讓桃花剪一幅 “歡迎調頭,每次十元” 的紅字,貼在顯眼的位置上。桃花勸過婆婆,說這樣做是違法的,不允許的,但犟不過婆婆的糾纏。
婆婆對項派出手太狠,看見黑轎車駛來,她先是笑逐顏開、畢恭畢敬地迎接,把車讓在院子里面掉頭,正掉好頭,她突然用掃豬糞的長掃把攔住了車頭,說,請交調頭費。項派突然懵了,問,交什么費?婆婆放聲說,同志,請你交調頭費。項派在城里經常交停車費,但沒有聽說過交掉頭費,覺得十分好奇,就再問,交多少錢。婆婆說,本來是交十塊錢,但你的車把我家的羊屎果碾爛了,還要賠我碾碎羊屎果的錢。項派一時沒有反應過來,覺得這事一時也說不清,就下了車。婆婆一把拉住他的袖子,說,一顆羊屎果賠一塊錢,另外再加十塊調頭費,你自己數數。項派被桃花的婆婆拉著來回數,總共148顆,項派明白被人訛了。婆婆無理得離譜,讓人哭笑不得。如果不滿足她的要求,項派恐怕走不了了。桃花想以后再找機會向他解釋和道歉。她狠狠心,說,“你把錢給她吧,要想走的話。”
“你家夠厲害的!” 項派起步的時候,撂了一句話。
桃花看著黑色的轎車緩緩駛在狹窄的村間道路上,心里突然空了,一縷冷風趁機吹進了心里。
4
桃花覺得男人的話像一把尖刀,刺進胸口,不深不淺,剛好疼痛,剛好滴血。“你家夠厲害的”,沒頭沒尾,但又有始有終,一棍子打死一家人,好賴不分。讓他拿錢給婆婆,分明是在幫他,給他出主意,給他一把樓梯下,他怎么就感覺不到別人的好呢。桃花心里迷亂,七上八下,不敢讓婆婆看出破綻,就早早地鉆進臥室,把門關嚴,睜大眼睛,開始釋放心中的恨意。要不是讓他拿錢走人,婆婆一定會做出更加過激的行為,說不定,她會把他拽進屋里,揪住衣領,鬼哭狼嚎,招引來不明真相的鄰居,然后說他非禮她,毀他的名聲,滅他的理。也許真的是為了訛點錢,也許還為了別的什么。破財免災這個簡單的道理,項派怎么就不明白呢,怎么就覺得我也在訛詐他呢?村里多半是留守婦女、孤寡老人、留守兒童,男女關系本來就敏感,一點小小的火星,弄不好就會燒起一大片。要是婆婆真的那么一鬧,恐怕毀掉好名聲的首先是她的寶貝兒媳桃花。但婆婆沒有拐過彎來,她鉆進了狹窄的無法轉身的陰暗的心靈胡同。你想啊,那么大的一個院子,就兩個女人,一老一少,要說非禮,婆婆那個年紀,那副兇模樣,誰信啊。但換另一個方向,另一個角度,另一個模樣,如狼似虎的年紀,如花似玉的樣貌,那就一定會有精彩的故事。桃花原本就防備項派,陰影一直跟隨著她,好了,感覺被驗證了,男人竟然追到了家門前,誰知道他在想什么呢,好在婆婆給她擋起了一堵安全的隔墻。
桃花的思緒不覺間又飛向了那輛倒霉的出租車,想起了男人給她系安全帶的情景。桃花不敢再想下去了,她覺得必須立馬把車費付給男人,必須立即斬斷一切與他聯系的方式。她立馬打開手機,翻開男人的微信,她轉的158元又自動退回來了,她后來又轉過兩次,都自動退回來了。她把車費連同婆婆訛的錢從微信上轉給男人,她希望他立馬收取,然后就徹底刪了他。她死死地盯著微信看,過了五分鐘,再過十分鐘,聊天窗口依然一片空白。時間在她面前變得越來越慢,仿佛不是向前走,而是跑進了她心里的港灣,把難堪的往事一件一件地翻出來,在寂靜的微風習習的夜晚數落她的過錯,讓她無地自容。等了將近一小時,桃花終于忍無可忍了,一股冰冷的柔軟的情緒,猶如黑夜里傾瀉而下的暴雨,瞬間把她淋濕了,她不禁微微顫抖了起來,抖出許多孤獨和寂寞來。她覺得十分無助,情不自禁地在心里呼喊起來。說,你這個無情無義的魔鬼,為什么緊緊纏著我,我再錯,我也是個女人,你難道就不能包容一下嗎?她很想打個電話跟他吵一架,但發現沒有他的電話。微信上倒是可以打,但她從不用微信打電話。電話號碼也可以查到,比如向杜曉娟要。但是,當她看見了通往男人的一道曙光時,她又突然轉身了,面對堅硬的沒有門和窗戶的墻壁,她想無聲無息地遇見男人,又無聲無息地離開男人,就像一陣風遇到了一棵樹,來也匆匆,去也匆匆,各自心安,各走一方。但狂躁的心還是穿過她精心設置的防線,促使她從微信上回了一句,她說,對不起,這是那天你拉我進來時應該付給你的車費,本來早就付給你的,但我們農村人心眼小,想得多,還誤會你,所以遲遲沒有給你,你別介意。桃花目不轉睛地盯著手機看,大約是半個小時,眼睛都盯疼了,男人也沒有回復。不知為什么,這一夜,她的眼睛一直在盯著孺子牛這個微信聊天窗口,思緒緊緊纏在孺子牛上。孺子牛就是項派,項派就是那個不知是誰的男人,她的情感和男人緊緊地糾纏上了。隨著夜的深入,她希望孺子牛立即收取她轉過去的錢,或者回她一句最最難聽的話,或者干脆臭罵她一頓,她都會舒服一些。但沒有,孺子牛很冷酷,像夜里的風,讓你感覺到清冷,但你趕不走他,也抓不住他。
桃花恨得累,退出微信,重新登錄,反反復復,時間在指尖上悄悄流過。直到涼風變冷,夜深十丈,她才把孺子牛的微信調成有聲提示,準備睡覺,不管睡得著還是睡不著,都要有模有樣地睡了。
桃花家的房子是東西向,后有靠山,前有悠長的河灣,河灣的上空有一輪彎彎的鉤月,行色匆匆,從一朵云里出來又鉆入一朵云。月亮也有心事,月亮用行走表達心事。桃花又增添了一束黑色的傷感,覺得很孤單。她把窗戶關上,把窗簾也關上,準備向著夢的方向睡去。但是,她發現門窗關不住心,心在四處游蕩,不知道在尋找著什么,漫無目的。此時,手機里傳來了一聲悅耳的鳥鳴,很輕,但有力量,直接鉆入心窩窩。她知道孺子牛回信了。她的微信過去不設有聲提示,全都關了,今晚是特意為孺子牛設置的。
桃花的心像一只受驚的小鳥,在胸口里撲通撲通地撞,她迫不及待地打開微信,看看孺子牛把錢收了沒有,收了,這一夜便能安然入夢。但是,微信錢包還在,孺子牛給她提了一個陌生的問題,他問,發生什么情況了?
桃花突然懵圈,以為自己發錯什么消息了,趕緊檢查聊天內容,但沒有差錯。她已說得很明白,是把車費和婆婆訛的錢通過微信轉賬付給他。他要么直接點收,要么客氣一番再收,要么不收,繼續折磨她歉疚的心。但項派沒有按照桃花的思路演繹下去,而是試探著敲了一下她的心門。這讓桃花左右為難,不回復吧,似乎這一夜等的就是她,心有不甘。回答呢,又三兩句話說不清。
桃花試探著問道,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項派說,那換一種說法吧,你為什么要轉錢給我。
桃花理直氣壯地回答說,很簡單,我喊了出租車,說好價錢,讓司機送我回家,但她沒送成,是你幫她送我家,所以我應當付你車費。
孺子牛說,我是幫助出租車司機順路拉你家,你要付就付給出租車司機。
我去哪里找她呀,我又不認識她,車牌號也記不得。
所以你不要付給我。
桃花覺得孺子牛真的很狡猾很聰明,幾句話就把她想得通徹的問題擋回去了。桃花有點失望,又不知道該怎么繼續聊下去,她把話題轉移到另一個問題上,說,那我問你,那件事你是不是特瞧不起我。
沒有,絕對沒有,孺子牛說。
桃花故意不說明是哪一件事,看他是不是放在心上,是不是和她想的一樣。他立馬做了回答,桃花就認為他肯定是放在心上了,要不然就是他們心有靈犀一點通了。
桃花心情愉悅,膽子膨脹,略施調皮地說,肯定有,你肯定有。
項派再次確定說,沒有,絕對沒有。
桃花看著的是孺子牛的微信聊天窗口,但見字如見面,宛如項派就站在面前,她說,你家挺厲害的,這句話還記得嗎
項派沒有傳送文字內容,只發個調皮的表情。但桃花領悟了他的意思,還調皮,真壞,女人最怕的就是男人的這點壞和調皮。她說,我一輩子都忘不了,就像被人狠狠地抽了一鞭子,傷已印在心上了。
項派當時沒來得及具體分析,沒有換位思考,此時沉默了。
有人傾聽,桃花覺得心情越來越舒暢。她是準備把憋在心里的不悅全部釋放出來的,但是,男人沉默了,一分,兩分,五分,時間飛速地流逝,男人始終沉默。桃花覺得有一個無形的人把她一步一步地推向夜的深處。桃花怕黑夜,黑夜里裝滿了孤獨、寂寞和欲望,突然一陣心酸,淚水奪眶而出。她關了微信,把自己重重地丟在床上,然后拉起被子,埋了頭,低低地哭出聲來。
5
桃花后來才知道項派被她冤枉了。
新村在縣城北邊的A鄉,80多公里盤山公路,屬山區,山多樹多。項派從縣城出發時,勾畫著新村的美景:山清水秀、干干凈凈,鳥語花香,民風淳樸,勤勞善良。但一路驅車,美好的想象漸漸淡去。到新村的時候,心中的美景被一路的風塵涂抹得不堪入目。目光所及之處,一片頹廢景象,凌亂的田地,彎曲的山路,污濁的河流,空氣中彌漫著濃烈的腐葉味。還好,村莊空曠,放眼望去,有山有樹,白云飄舞,鳥鳴聲聲。山如畫,樹入畫,水流畫中,這使他消沉的心情稍稍好轉。他想,只要帶著鄉親們苦干實干,一天干一點,新面貌一定會出現。他做了一套改變新村面貌的規劃書,想先和副主任杜曉娟交流,聽取她的意見,修改完善后再正式提交村兩委討論。他剛來新村,覺得杜曉娟活潑能干,還關心他,是個可以掏心掏肺作交流的人。
杜曉娟聽了他的設想,只是笑了笑,沒說好,也不說不好。項派急了,說:杜副,你說說可不可行。杜曉娟把身子俯在辦公桌上寫著什么,頭也不抬地說,作為一個夢想倒是挺好的。項派等了一會,沒等到杜曉娟的下句話,更急了,說,你具體點說說你的看法嘛。杜曉娟抬起了頭,又給他一個甜蜜的微笑,說,那我直說了,新村要人沒人,要錢沒錢,大片的土地今年荒一塊,明年荒一片,要是不照顧小孩和老人,一個勞動力也不會留下來。你的規劃,自己想想還可以,別當真,免得有挫敗感。
項派已經有失敗感了,熬過一夜,黎明剛出現,他就向新村最高的金牛山爬去。金色的太陽剛剛露出頭的時候,炊煙一縷接一縷地升起來,田野的露珠閃閃發光,這情景充滿了詩意,讓他突然對新村產生了強烈的期待,每一縷炊煙都維系著一個家庭,每一顆露珠都呼喚著一個有希望的孩子,怎么說沒有人呢。然而,當他走在村間道路上時,那些美好的景象又悄悄地躲藏起來了,田地里空無一人,路上只有爺爺奶奶外公外婆一輩的人。他們彎著腰,走路只看路面,不看遠方。還好,遠處正好有朗朗的讀書聲,一幀鮮艷的五星紅旗在村里最高最漂亮的那幢房頂上高高飄揚。直到有一天,當他在半路上遇到一輛同向行駛的出租車出了故障,遇到了桃花,才突然覺得鄉村其實是美麗的,充滿生機的,一定能夠孕育希望的。當他無意中聽到桃花會作剪紙作品時,心里一顫,驚喜無處躲藏。
桃花仿佛是一顆飛行的火星子,勾起了項派美好的欲望。他迫不及待地想和桃花探討剪紙,他姑姑就是一個剪紙迷,耳濡目染,他也喜歡剪紙。說實在的,來到新村,他找不到一個有共同心靈感受的人,找不到一個有共同語言的朋友,長久待在縣城里,每天長篇大論地拼材料堆成績留痕跡,應付了這頭,又應付那頭,靈魂離地面很高,風吹到哪里,他就飄到哪里,心里虛空,沒有方向。到新村,一切都是那么真實,可他還是像一只氣球,怎么也落不下來,粘不在新村的土地上,枯燥死了,憋悶得慌。剪紙這個名詞像一顆種子,有重量,在他心里落地,浸潤,膨脹,發芽,成長,開花。
在一個彌漫著松花粉的下午,鄉文旅中心主任打電話給杜曉娟,說縣上要舉辦鄉村振興美術作品展,要求新村提交一件佳作,這使項派突然想到了桃花的剪紙。然而,杜曉娟卻面有難色地說,李主任,這藝術的東西,你讓我們拿什么交啊,你也知道,新村要人沒人,要錢沒錢,哪有什么美術作品,我們新村交不出來。李主任說,我的意思就是讓你去通知桃花。杜曉娟喊了一聲李主任,想解釋一下,把這事推了。但李主任把電話掛了,不給杜曉娟解釋的機會。杜曉娟嗔怪地說,這個李主任,只會整天坐在辦公室里安排,一點也不求實際,不知道我們有多難做工作,這美術的東西又不是誰都會,還叫通知人家創作呢,他怎么不去通知。
項派把通話內容聽得清清楚楚,他和杜曉娟的看法恰恰相反,他正想通過這事,去見一面桃花。他和桃花心是近了,但見面后會是什么樣子,他猜不到,他還陷在桃花的婆婆給他挖好的坑里。他說,杜副,我倒是覺得這是好事,正好可以給桃花一個展示才華的機會。杜曉娟說,問題是太難了,桃花說話有時也不靠譜,有一次,她都答應我了,我也給李主任答應得好好的,但她把事情做黃了,李主任見我一次念叨一次,見我一次念叨一次,說我工作沒做好。最氣的是,年底考核中扣了重分,為這事,新村考核排末位。桃花也是,作不出來,當時就不要答應,事情就沒有那么復雜了。
項派也覺得杜曉娟肯定沒有把工作做細做深,讓桃花無從下手,導致好事辦黃。但他沒有直說,他說,杜副,你抽個空,我和你去桃花家請她,讓她一定要支持新村的文化建設,一個村,如果沒有文化,魂就不在了。就像一個人,魂丟了,連家門都找不到了。
杜曉娟冷笑了一聲,項派明顯地感覺到排斥感,但他沒有表態,冷靜一下也好。只聽杜曉娟嗬嗬笑起來,說:項派,你說得怎么那么好聽,我想一輩子都想不出那句話來,“魂丟了,連家門都找不到”,那好吧,我先打電話問問桃花,免得我們白跑一趟。
項派說,不要打電話,還是我們親自去她家請她,正好,我也該走訪走訪群眾了。
6
桃花的剪紙作品 《春到新村》 在一千多件美術作品中脫穎而出,進入州級展廳,這是項派期望的目標。項派想把桃花帶到州上參觀,讓她開闊視野。新村的文化旅游這塊由杜曉娟分管,項派就把想法和杜曉娟說了。杜曉娟說,桃花怎么可能去州上,你不知道,她的婆婆管得賊死,不會讓她去的。項派說,沒那么夸張吧,什么年代了,婆婆還管得了兒媳。杜曉娟說,桃花家的兩個男人都出去打工去了,本來桃花也想跟她男人一塊去的,她婆婆聽說年輕媳婦出去打工后,基本上都跟別人跑了,所以,她不讓桃花出去。在村里,也基本不讓桃花跟男人說話。項派知道這個情況,但他知道婆婆管不住桃花的心,就暗自笑了,說,那萬一管不住呢。杜曉娟說,管得一天算一天,管得一月是一月,管得一年是一年。
也是,項派想,正好可以逗她開心一下,就說,杜副,那你是由誰管,管得賊死嗎?杜曉娟沒有想到他會這么逗她,先是愣了一下,沉思了才說,我現在是自己管自己,管得也是賊死的。項派說,對呀,自己管自己才管得住嘛。
項派后來才知道,杜曉娟也曾經歷過感情的折磨,以為到村委會擔任副主任以后,事情會風平浪靜了,但她的男人不信任她,看見她坐男人的摩托,他就跟她賭氣兩三天,憋著憋著就開始鬧。有時,聽到一點小道消息,也跟著鬧,鬧著鬧著還出手打架,差點就分了手。不過,杜曉娟最后還是制服了丈夫的野脾氣,現在都乖乖地聽她的話了。遇到杜曉娟干不了的重活,他還主動來村委會幫她干。項派見過杜曉娟的男人,1.7米左右的個子,肩膀寬寬的,慈眉善目,一表人才,能說會道。
項派還是鼓足了勇氣,說,杜副主任,我想,桃花的作品能上州級,這是鄉上的榮耀,也是桃花的榮耀,更是新村的榮耀,是你分管的這口工作的最大成績。你想啊,桃花的作品再好,要是沒有經過你的推薦,也上不了那趟藝術的航母,你說是不是?杜曉娟笑了,笑得自信而有成就感,說,再悲觀的事情,經過你的藝術加工,就成美好的東西了。項派要的就是杜曉娟這個陽光的心態,見她露出笑容,料到事情有希望了,就說,這樣吧,由你出面協調,帶著桃花婆媳倆,由我開車,吃飯問題由我負責,一定要帶桃花去州上看看美術作品展,這對你負責文化旅游的領導來說,或者對桃花這樣愛好美術的來說,都是一個非常難得的提升機會。同時,我也想趁這個機會去提高一下自己的欣賞水平,一天時間就夠了,你看行不行。
杜曉娟知道項派骨子里有一股沖勁,認定的目標,不管采用什么方法,他都要堅定地向前。她手上雜事太多,還不如避繁就簡,依了他吧,就爽朗地說,我看行,就依你吧,只是隨時給你添麻煩,心里有些過意不去。
項派說,小事小事。
杜曉娟意識到這件事情確實很有意思,她沒有采取簡單的辦法,不管怎樣忙,都得抽時間去桃花家,把桃花的作品被遴選到州上參展的消息告訴桃花和婆婆,感謝桃花對她文旅工作的支持。這次,杜曉娟沒有帶項派去,她在晚飯后,搭了一輛過路的摩托車去到桃花家。和她想象的一樣,桃花和婆婆都在家,正擺好飯,還沒動筷。桃花的婆婆這次無比熱情,一定要讓她一起吃飯。杜曉娟本來吃過飯了,但她了解阿婆,都請你坐下來吃飯了,那就不是兩三句話說得清的,那就坐下來慢慢聊,一定要把項派安排的事情辦妥。
杜曉娟一邊吃飯一邊聊家常,故意把正事藏著掖著,等到三個女人把話說到熱乎處了,她才開始說正事,阿婆,我有個想法,桃花的作品上了州級展廳,這是桃花的光榮,是我們村的光榮,是我們鄉我們縣的光榮,但我們不知道桃花的作品和州上的相比,到底有沒有差距,差多少距離,有沒有再提高的可能性,俗話說藝無止境,所以,我想帶著你和桃花去州上看看,當天去當天就回來了,耽擱不了家里的活計,你看行不行。
杜曉娟估計桃花會同意的,就故意不問桃花,但桃花已經喜形于色。婆婆想了想,說,那要多少錢才夠花呀?杜曉娟說,阿婆,費用你就不用管了,這事算公家的事。我是這樣想的,上次來你家的那個人,他叫項派,有自己的車,我想讓他帶我們三個去,熟人熟路,直接去展室,看完就回來。要不然自己沒有車,到了州上,還得這兒打車,那兒打車的,不但不方便,還花冤枉錢。
婆婆說,天黑之前能回來嗎。杜曉娟說,正常情況下,應該沒有問題。
阿婆說,你帶著桃花去我放心,那你們去吧,出去開開眼界,真的很好,我怕暈車,我不去了,坐一趟車幾天都吃不了一口飯,難受。
杜曉娟再三勸說,婆婆堅持不去,這倒是出了杜曉娟的意料之外,事情竟然這么順利。
杜曉娟離開桃花家的時候,婆婆送到了門口,在朦朧中,婆婆塞了一團紙給杜曉娟,說,請你轉給他,告訴他永遠不要打桃花的主意。告訴他,我把桃花拴得緊呢。
杜曉娟本來想告訴婆婆,男人不會傷害桃花,再說,有她陪著呢,但她緊捏著紙幣冷靜了一下,又放棄了想好的話,說,好,婆婆放心,天黑前我一定把桃花送回來。
7
參展之行,在途中出了點意外,項派開車拉著桃花和杜曉娟,從新村出發,剛到城邊,即將走上高速公路的時候,杜曉娟接了個電話,說,停車,停車。項派把車緩緩停到路邊。杜曉娟說,我去不了了,我家男人在工地上受傷了,要來縣醫院治療。
突然改變了計劃,項派有些失落,計劃把杜曉娟送回城內,幫她把事情辦妥,看情況再打算。到了醫院,杜曉娟下車時,項派突然不知道該怎么幫杜曉娟,就問她,我們需要幫你什么忙。杜曉娟說,去,你們去吧,說好的事情就克服困難去辦,我這兒你們也幫不上忙,我男人的事工地上的人會處理的,估計我也只是陪陪他。項派發現他忽略了桃花,又不好解釋,就看看桃花,問她怎么辦?桃花說,如果曉娟姐不需要幫忙,那我們就去吧。
桃花從后排座位上下來,坐到副駕駛位上,心情突然復雜起來,思緒又飛到了那輛出租車上,邂逅項派的情景猛然闖入腦海,過去的漫長時光,朝朝暮暮,陰陰晴晴,如夢如幻。此時,正坐在項派的身邊,活生生的現實,心里卻沒有在夢里渴盼的樣子,那些珍貴的沒有名字的味道一點也沒有了。桃花側眼望了望項派,希望項派能說點什么,或者做點什么,但項派目不轉睛地一直向前看,緩緩起步。桃花故意不系安全帶,車叮叮叮報警了,項派說,請系上安全帶。桃花說,我不會系。那是逗他,但她真的不系。項派說,你輕輕拉過來,把卡頭插這里就行了。桃花調皮地笑,說,我真不會。項派知道桃花在逗他,突然有點慌了,在那些月光發白的夜晚,心曾經一次次飛翔,一次次渴望著跟一個懂藝術的女子在一起,但那是在月亮下,此時,陽光正好,風景很美。杜曉娟又在中途退場,圓滿完成這次任務,責任就落在了他一個人身上,他很清醒。
在經過紅綠燈時,項派說,桃花,請你把安全帶系上,不系會罰款的,還要扣駕駛證的分,不劃算。桃花就利索地系上,感覺美好的心情被一聲咔嚓卡扣聲槍斃了。
去往州府的路有兩條,一條是高速,100多公里,一條是老路,120多公里,原計劃要走高速的,但還沒有出城,項派發現桃花的心情變壞了,一點也不像在微信里聊天時那么開心。他有點憐香惜玉,該和她說點什么有趣的話才是,就往老路上走。
桃花還沉迷在項派給她系安全帶時羞澀、尷尬和害怕之中,沉迷在無數個月亮走云也走的夜里,當她想起項派給她講的一個夢境時,忍不住嗤一下笑起來了。項派心里一顫,緊繃的心突然放松下來了,加大車速往前開,經過兩個彎道,桃花說,請你開慢點,我頭暈,項派就把車速降下來了。到一個左右兩邊萬丈絕壁的峽谷地帶,路邊有十幾個停車位,還建了休息的小涼亭,項派就把車開到停車位上,說,桃花,你暈車就休息一會兒,時間夠用的。桃花說,聽你說,我今天……桃花本來是想說我今天就交給你了,但突然覺得不對。陽光下,還有三輛轎車,七八個人在那里聊天吃零食,險惡的地理環境被這些人過成了浪漫的仙境。項派提議繞小景點走一圈,桃花同意了,邊走邊驚嘆自然的神奇,因欣賞美景而走了神。桃花還絆了一跤,差點跌倒,但沒有倒,她尖叫了一聲。此時,她多么希望項派來拉她一下,但項派沒有,卻引來了好幾雙辣辣的目光。
桃花想,無數個夜晚,她都在想和他單獨在一會兒,哪怕一瞬間,把初次邂逅的感覺找回來。今天終于和他成雙成對,但仿佛又是陌路人,項派和她始終保持著那么一點距離。桃花無數次在想,可能是我錯了,項派心里根本就沒有別人,也好,就像這些遠行的人一樣,自自然然,把今天的事情做完。想到這里,她又一次感覺欠這個男人太多了,簡直都不好意思說出來。項派其實也猜不到桃花的心事,他腦子里畫著一個橢圓的路線,就是從新村起步回到新村,目前只走了近三分之一的路程。他有目標,并按著目標挺進,不到目標不罷休,他想盡快離開,但有一個故事必須講給桃花。他說,桃花,你看這景色美不美?桃花說,很奇特。他說,這里過去是南方絲綢之路,所有商品都靠人背馬馱,當馬幫走到這里時,土匪就會從兩邊的山上沖下來搶劫財物,搶不到就會把人殺了,所以這里死過好多人。桃花聽見死過好多人,嚇得一把拉住男人的手,說,我怕。這倒讓項派害怕了,他沒有想到桃花會拉他,他也不是故意要嚇他,他是想把歷史故事講給她聽,他覺得搞藝術的人應該知道很多歷史。他說,不怕,那是幾百年前的事了。后來,官府還在這兒修建關卡,據說就在腳下這個地方。桃花越來越害怕,仿佛踩到了死人一般,把他的手拉得越來越緊,說,快走,快走,不在這個鬼地方了。
返回的時候,項派選擇了高速路,五點過十分就進入縣城了。項派說,桃花,你在縣城里還有事情要辦嗎。桃花說,沒事了,要早點回去,婆婆在家等著呢。項派就給杜曉娟打了個電話,問她事情辦妥沒有,是否可以跟他們一起回去了。杜曉娟說她已經返回到家,讓他們慢慢回來。
項派的車到上次出租車輪胎爆裂的那個位置時,又看見兩個人,男的,走在路上,拎著大包小包的東西,像從遠方回來。項派想,一定是新村人,應該帶帶他們,人在路上,都不容易。他慢慢減速,車到面前,男人轉身讓路,桃花就叫了聲爸。項派把車停下,桃花又喊了聲向乾。項派知道他們是一家人,就打開后備廂,幫他們把行李放進去,請他們上車,把他們一家三口帶回到新村的家里,這一次桃花的婆婆沒有向他要調頭費。
望著項派遠去,桃花想,有些事是緣分決定的,想想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