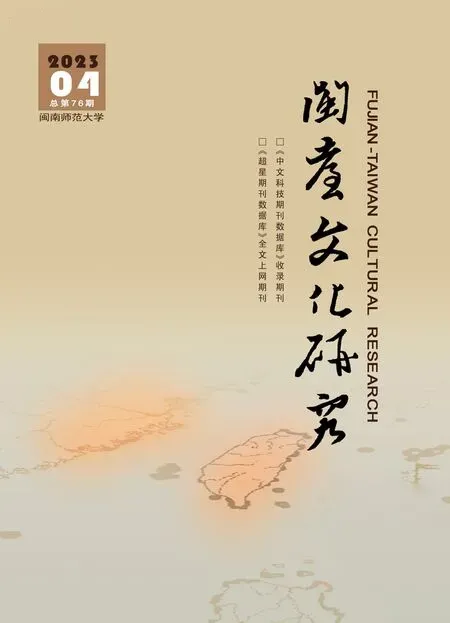“緝捕私鹽”與“唐鹽接濟”:閩臺關系視角下臺灣地區私鹽問題研究
李博強
(福建師范大學社會歷史學院,福建福州 350007)
康熙統一臺灣后,設立臺灣府,隸屬福建布政司,參照大陸的政治、經濟、社會架構,形成閩臺一體的發展模式。臺灣地區的鹽政在清代時期不斷發展,其中經歷興衰、變革,與福建地區的專賣體制緊密聯系在一起。并且,福建的鹽業生產技術傳入臺灣,臺灣鹽場得到不斷開辟,曬場規模擴大,鹽產數額提升,鹽專賣制日益完善,成為清政府開發臺灣、鞏固統一的重要舉措。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產銷分離及官辦鹽務的存在,臺灣的私鹽問題也較為突出,與其它行銷區域趨同,私鹽弊病伴隨政局的衰頹而日益深重。
在研究清代時期鹽專賣體制下的私鹽問題時,學界或較多的從宏觀層面進行闡述分析,或將焦點集中于兩淮、湖廣和四川地區,而以閩臺地區為中心進行研究的較少。[1]部分學者涉及臺灣地區私鹽問題的研究,研究視角大多集中在北臺灣新竹地區,注重分析私鹽問題的成因及其表現,挖掘私鹽現象屢禁不絕的現實中縣官與鹽官的行政博弈的問題。[2]現有研究總體上呈現了研究視角單一和解讀碎片化的問題,屬于典型的“就臺灣論臺灣”,一是未將清代時期臺灣地區的鹽政置于清政府統治下的鹽政體系進行總體討論;二是沒有深入探究閩臺關系視角下“唐鹽接濟”的問題。因此,本文以《臺灣文獻史料叢刊》和《淡新檔案》等資料作為基礎史料,重點探討臺灣地方政府如何在制度層面進行建構,實踐層面進行操作,力圖改革私鹽弊政。同時,為充分論述“唐鹽接濟”的問題,本文的研究時限也適當延伸至甲午戰后,即日本殖民統治臺灣的前十年。
一、改革私鹽弊病:制度層面的建構
臺灣鹽業生產起源較早,素被稱為“魚鹽滋生”之地。1683 年,清政府統一臺灣后,進行一系列政治、經濟制度構建。為羈縻人心,同時鑒于治理臺灣初期,臺灣鹽業受戰亂及課稅繁重等因素影響,造成鹽丁逃散、鹽場失修,鹽業蕭條的情形,于是一切內政多從臺灣舊制,并未實行內地所推行的鹽專賣制。[3]“鹽皆歸于民曬民賣。其鹽埕餉銀,由臺、鳳兩邑分征批解”[4]。然而,自由運銷在實行過程中,源于“民曬民賣,價每不平”[5],“時低時昂,分爭迭起,官府亦厭聽訟之煩”[6]。而且,內地私鹽的流入,也一定程度上影響到本島鹽業的銷售。臺灣縣知縣季麟光就指出:“官鹽之不行,實由私鹽之撓阻,臺灣環海,港澳甚多,泊舟之處即賣鹽之處,奸商之私鹽即不及問,悍卒之私鹽則不敢問。蓋奸商潛匿遠港,與漁人私相交賣,縣官無分身兼視之法也,悍卒之來多系營船,虎威狐假,不容盤驗,縣官有抗顏起釁之慮也。所以私鹽既多,官鹽難銷……而私鹽禁不嚴,仍聽其公然出入……將使在臺無食官鹽之民,其害寧可問乎”[7]。由此可見,官鹽難以與私鹽相抗衡,鹽政弊端層見疊出,政府不勝其擾。福建總督覺羅滿保在雍正三年(1725)指出臺灣雖“遠在海外,民番雜處,土俗民情與內地不同”,但應仿照內地的鹽專賣制,“官給價銀,盡數收買……府治則設館,聽民赴買……一出銀兩,除撥還鹽本及支給外,悉以歸公。”[8]從而保證“灶既樂得多價,民亦皆食賤鹽,兩皆稱便”的局面。在此建議下,雍正四年(1726)四月,清政府正式廢除自由運銷,實行鹽專賣制,希冀實現“既絕私煎、私販之弊,復無忽低、忽昂之患;裕課便民,誠胥善焉”[9]。
實行鹽專賣制的核心要旨在于仿照大陸鹽政體制實行產銷分離、行商銷售的模式。在管理方式上,規定全臺鹽政,由“臺灣府專管”[10]。臺灣知府在府治之內設立鹽館,為總匯全臺鹽課之地,又稱為“鹽課大館”。[11]臺灣府并未實行戶部頒發的引票,而是獨自印發支單、路引,既作為各館繳課后支鹽之依據,又作為領運后之運鹽憑證。[12]依據現有文獻資料,清代中前期臺灣的鹽專賣應是推行官收,即將各場曬丁之鹽,官給價銀,盡數收買,然后既有官運,又有商運的產銷體制,商運則體現在“鳳山、諸羅、彰化、澎湖等處路遠,難以官運,俱招殷實販戶買運行銷”[13]。實現“官收、官商運”,就可以在府治之內,設立鹽館,不準鹽民私自銷售,所產食鹽必須統歸鹽館收購,貯存在鹽館附設的官庫,稱為“官鹽”,如果產戶與民私相買賣,就是“私鹽”,訂有刑章,違者處罰。府治之下,各縣販賣“官鹽”的商戶,必須經有司核準,并頒領“鹽引”,再由府內鹽館依各縣人數,核發銷鹽數量,發給各縣鹽商,轉售給居民。
與其它鹽產區不同的是,在產銷體系上,臺灣食鹽運銷以自產自銷為主,產于本地銷于本地。相對來說,這種自給自足的產銷模式,能夠有利于保持食鹽生產的穩定性,便于商人運銷及政府收稅。當然,臺灣食鹽僅限銷售本地,銷售地域較為單一,產量較為恒定,容易導致生產食鹽的質量較差,價格較高,增加百姓生活負擔,而且給福建沿海私鹽的侵銷提供一定市場。到同治元年(1862),經戴春潮之亂,私風益熾,官鹽幾無銷路,販商多數歇業,曬丁無以為生,邊遠人民又有淡食之苦。[14]為進一步加強對臺灣的鹽政管理,改革私鹽積弊,同治六年(1867),清政府將全臺鹽務移交給臺灣兵備道管轄,以臺灣道兼任鹽務督辦,設立全臺鹽務總局,主持鹽政。[15]另外,在臺南設立臺南鹽務總局,主管產運銷業務,管理鹽產,俾利官收。在運鹽要道及沿海地區,密布員兵駐扎,嚴緝私賣私販,在銷岸要地,則劃分區域,各設總館。總館之下,視銷額之多寡,分設子館,辦理銷務。在邊遠銷少之地方,則有商人設立贌館,承辦零銷。[16]田秋野就針對臺灣府實行全面控制鹽業運銷的措施指出:“較諸就場販售,放任運銷之專賣,自勝一籌”,原因在于“總館按其轄銷境內需鹽數量,申請總局,領發館引,藉以稽核發賣及領運之數量”[17]。此行鹽方法確立了政府對鹽產運銷各個環節的控制,從制度上確保產、運、銷體系的連貫和統一,形成從上至下的監管體系,確保專賣制度的穩定,阻止私鹽的偷漏。
至光緒十四年(1888),其時臺灣已建立行省,巡撫劉銘傳采取多項舉措進一步加強對臺灣鹽政的管理。他以巡撫之職兼鹽務總理,主持全島鹽政,“于臺北設立全臺鹽務總局,于臺南府治置臺南鹽務總局,全臺之鹽務分南北二屬,北部由布政使掌之;南部由臺灣道掌之,并任(兼)鹽場與鹽館之督辦”。[18]為便于控制全臺鹽務,遏制私鹽侵銷,劉銘傳推動實施官收、官運、官銷的全部專賣制度,在全臺十地分設十個鹽務總館,總館之下又設立多處子館,掌管官鹽的運售批發,并招各地地方士紳擔任批售官鹽的業務,力圖通過官商一體、官督商銷控制官鹽的運銷,擠壓私鹽的生存空間。[19]然而即便如此,私鹽問題仍然難以真正解決,臺南鹽務總局委員胡傳就認為私鹽問題源自多端:“臺南沿海之地,處處可以曬鹵成鹽……奸民可自曬以售私;加以場員、場丁漏私,緝私弁勇包私”,此受病之源也,“即大改弦更張,亦恐難以起色”[20]。
二、緝捕私鹽:實踐層面的操作
“鹽政之壞,皆歸咎于官鹽之壅滯;官鹽之壅滯,皆歸咎于私鹽之盛行。故講求鹽政者,莫不以禁私為首務”[21]。由此可見,鹽法之弊莫甚于私販,鹽法之要莫急于緝私。[22]臺灣府在進行制度層面的建構過程中,也著力從鹽場制鹽到行銷運鹽的不同階段采取緝捕私鹽的措施以抑制私鹽泛濫的態勢。
在鹽場制鹽及收購的過程中,為防止“場私”的出現,南北地區鹽場設立總理、頭人、族長、戶首各名目,“管束曬丁,以杜走私”[23]。而且“每場設管事一人,派家丁一人,專司稽查,以防透漏。每埕所出之鹽,盡數用制斛盤量收倉。”[24]鹽場曬鹽過程中,均“派有緝私委員帶同巡勇,每日于傍晚時,會同場員隨帶哨勇,遍歷各鹽田,眼同曬丁,將曬成鹽粒掃刷凈盡,押令挑赴場內,先堆倉外,俟隔夜流鹵稍干,次早,場員眼同曬丁過秤,再入倉廒。鹽面,蓋用鹽印,不致暗被偷漏”。[25]而后,鹽場“募雇哨丁晝夜巡邏,不準私鬻并私添埕格”[26]。對于鹽場官吏利用職權謀私、販私者,給予嚴懲。光緒十一年(1885),劉銘傳“通飭各場暨各館委員如有透私舞弊,互許索賄情弊,一體革除,倘再有犯,定予嚴參外,理合具文詳請憲臺察核”[27]。同年七月,札飭新竹縣嚴查北場族長陳火珠“名為在海邊查看鹽埕,實則與曬丁舞弊走漏私鹽,一擔分得錢二、三百文不等”的案件,要求“先行開革,亟應重懲”[28]。對于鹽場哨勇賣放私鹽者,“誠于監守自盜無異,現值旺曬之際,亟宜整飭”,要求從嚴究辦,枷責示眾,以儆效尤。[29]鹽生產完成之后,由鹽館收購,進入官收環節,“各館持引來場運鹽……曬丁秤手,憑引發鹽”[30]。按照規定,每一引的重量為鹽五十石,但在實際稱量過程中,不時會出現鹽場委員不檢點,“每鹽一石,過秤稍高,即可溢鹽二、三觔不等”的情況[31]。為防止鹽場委員徇私偷漏場鹽,“與若輩聯同一氣”“串同甲首、曬丁、巡勇、左右鄰”等,臺灣府要求南北各鹽場嚴格用人,“慎擇委員”[32]。
在食鹽運銷的過程中,為防止“商私”的出現,臺灣府首先明確行銷規制,“府治設所名曰鹽館”,鹽商需要按照要求到鹽館領取鹽引并繳納鹽課,“每一石交番廣銀三錢,腳費三分,而執單取鹽于場。”[33]通過這一措施,嚴格管控鹽館售鹽和商人領鹽、運鹽、銷鹽的額度,固化從生產到銷售環節的流程,防止鹽商偷運私鹽。其次,臺灣府對私鹽運銷的緝捕一直保持高壓態勢,“凡買私賣私即肩挑背負者,一經拿獲,輕則枷責發落,重則加倍罰賠”[34]。乾隆時期,臺灣府就檄飭各縣查拿代買私鹽之犯,“于內地及外洋一帶,嚴飭所屬,上緊緝拿,勿任遠飏漏網”[35],“船只、私鹽分別入官充賞”,對“自臺灣私渡出入各口,并內地失察私船出口文武各職名”,也要“查明另參”[36]。而根據《道光朝軍機處檔》的記載,道光十四年(1834)七月,閩浙總督程祖洛奏報的9 名載運私鹽犯人清單中,均以犯無引私鹽受雇馱載的罪名,各杖八十,徒二年。[37]這與清《鹽法律條》中刑律條文“(受雇)挑擔馱載者,杖八十徒二年”的規定并無二至,說明至道光時期臺灣地區對私鹽的查禁、審理仍然依照法律嚴格執行。但依據于《淡新檔案》的記載,又可發現到光緒十七年(1891)八月新竹縣在抓獲販賣私鹽者時,“著笞責枷號三個月示眾,以昭炯戒而冀自新”[38],而在《鹽法律條》中則明文規定“凡犯(無引)私鹽者,杖一百,徒三年”[39]。以此觀察,隨著時代的變遷,政府對載運販賣私鹽的刑罰有著一定的減輕。不過,上述材料僅反映新竹縣一地的懲辦情況,是否其它地區也沿用同樣辦法尚需更多史料予以證明。
以上這9 人中,最年輕者21歲,最年長者50歲,皆受雇于人,載運私鹽,但雇傭他們的人卻是“逸犯”,仍逍遙法外。在查辦私鹽的過程中,為確保官鹽的銷路,政府便將鹽館銷鹽數額的任務著落于當地“頭人”身上,“或具結保銷,或立限認配”,希圖實現“官鹽不致短絀,私鹽從此禁絕,庶于鹽政有益,鄉民無擾”[40],但實際效果并不如預期,部分地方仍然出現莊民“恃眾抗拒”的情況[41]。
道光中后期,臺灣各屬實行“賣鹽收錢,易銀繳課”的政策,由于銀價日漸昂貴,導致鹽商、鹽販“成本虧折”,稅課負擔不斷加重,當時臺屬各販戶“核計成本,虧折甚巨”[42]。隨著制鹽、運鹽成本的日益增加,鹽商難以承擔經營損失與苛重的鹽課,疊求增加鹽價。至道光二十六年(1846),福建鹽法道同意“臺灣各屬鹽價,每斤準予酌增制錢三文,以示體卹”[43]。增加鹽價雖可解決鹽商運銷之困境,但是高昂的鹽價也使百姓不愿購買官鹽,為私鹽的侵銷提供了市場,“內地私鹽每斤二文,偷載至臺每斤賣四、五文;而官鹽每斤十二、三文,故民間趨之若鶩,內山生、熟番及粵莊人,皆食私鹽”[44]。道光末年,這一弊病更為凸顯,“私鹽之所以日多,則以谷價日賤,富民不能養貧民,貧民無可傭趁、無可挑負,而私販糊口也。禁之過嚴,緝之過猛,將驅而為盜矣”[45]。由此可見,運用增加鹽價的方法,不但未能解決鹽商疲敝的困境,反而導致私鹽猖獗的局面。
需要指出的是,緝捕私鹽的效果未能達到政府預期,不僅在于部分人貪圖私鹽價廉易得,“買食私鹽,在所不免,屢經各前府飭屬查拿,未見斂跡”,還在于政府官吏的放任怠政,貪墨腐敗,個別水師守備“海口時有私鹽往來,緝私不力,技藝亦屬庸劣”[46],甚至出現“官自為私,官蠹烹分,遂逋正賦”的情況[47],致使“地方煎販私鹽明目張膽,毫無忌憚”[48]。所以,像道光四年(1824)閩浙總督趙慎畛在復奏中指出的新任署府抵任后,“移行營縣廳員及守口文武員弁認真緝拿,鹽務漸有起色”的局面也只是短暫的一瞬,一段時間后,私鹽盛行的局面便死灰復燃。[49]
同時,為降低私鹽侵銷的規模,臺灣道吳大廷開創化私為官的形式,對私鹽采取“以征為禁”的措施,在港口數處設立局卡,抽收外省船只盤運閩鹽出口的私鹽厘金。[50]而掌管臺南鹽務總局的胡傳則對臺灣府以征稅形式默認福建沿海地區私鹽侵銷臺灣的情形并不認可,他更為強調臺灣本地產鹽本島銷售,以實現“如能杜絕內地之私,改銷本地所產之鹽,則沿海窮民歲可增五萬余金以資生計”的局面[51]。
三、唐鹽接濟:閩臺地區緊密關聯的典型表現
閩臺關系十分密切,其中食鹽產銷方面的典型表現就是“唐鹽接濟”。這源自于臺灣長期依賴于福建鹽的配銷來解決食鹽供給不足的問題。“臺灣鹽務場產不足,半由內地運售,名曰唐鹽”[52]。唐鹽的詞義來源于“臺人以內地為唐山,故名鹽曰唐在泉”[53]。
唐鹽能夠輸入臺灣,首先是為代銷內地食鹽,解決福建部分鹽場銷路不暢的問題。根據《漳州府志》記載,道光四年(1824),漳浦、詔安鹽場年產鹽九萬七千七百零一擔,府屬各縣行銷坐配,由于“閩省南靖、長泰兩縣鹽務系官運中最為疲敝之區”,因此“南靖、長泰二縣鹽引(出現)阻滯”[54],“內地各官商均已自顧不遑,勢難再為目[勻]代”[55],遂“以南靖、長泰二縣額引撥出一萬二千石歸入臺灣府勻銷”[56],并且規定“所征正、溢課厘,雖留臺撥充防費,尚有抵解內地鹽務雜支之款。每屆奏銷,由福建鹽法道匯核造報”[57]。光緒初年(1875),政府特許臺灣購買閩鹽配運各縣,以補不足部分,福建鹽商通過船政運輸以食鹽換取臺灣所產煤、谷及樟腦成為主導之勢[58]。光緒十四年(1888),劉銘傳在基隆、淡水、安平、高雄四港口各設一配運局,負責唐鹽的收購及調配轉運事務。其中,收買唐鹽“每擔約二三百文,至臺后由官給洋一元收鹽兩石,其稱名曰一三五,蓋以一百三十五斤為一石”[59]。福建鹽調入臺灣銷售,說明閩臺兩地在經濟上的互相依賴關系和行政管理方面的聯系是十分密切的。[60]
其次是為解決臺灣北部地區食鹽不足的問題。根據《憶臺雜記》記載:“臺北所收之鹽,多系春夏間海舟由泉州載來者”,這里指出了北臺灣地區的食鹽主要來自于泉州的輸入。[61]光緒二十一年(1895)前后,臺南有瀨南、瀨北、瀨東、笨北、洲南、洲北各鹽場,足資民食,而臺北無之,轉運于臺南,時或脫節[62],因此“特收買福建鹽,配運各鹽館,以補充缺額”[63]。臺灣北部地區缺鹽的原因主要基于兩點:一是臺灣鹽因管理混亂、生產無序,加之運輸等原因,所以乾嘉之后島內鹽價居高不下,百姓叫苦不迭。特別是宜蘭民眾只好食用福建惠安、興化所產鹽斤,每斤售價僅7~8 文,此乃私鹽。臺灣鹽商甚至囤積居奇,至秋冬二季福建漁船鮮有入境時,再以20~30 文高價牟利。[64]二是臺灣地理位置較為特殊,西部海岸鹽田地帶容易遭遇風雨災害的襲擊,“本島鹽田,構造極劣,不獨暴風雨時,被害頗巨,且鹽埕之崩壞,年甚一年”[65]。尤其是北門嶼產鹽地區“客夏以風雨災祲,鹽田堤決,制鹽異常損失,平局室如懸磬,一陷窮境,則救死不瞻,無暇旁及修理”[66]。由此,“惟南、北各鹽場所產之鹽,尚不敷本省人民之需求,尤其北部產鹽較少,時常發生鹽荒,政府雖在北部滬尾、基隆及南部安平設立配運局,專司轉運南鹽以濟北部食需,仍感不足,故每年夏秋兩季,西南順風,廣東蔗林、汕頭,福建惠安、頭北、金門、獺窟、祥芝、秀塗等地,來臺載米之商船,多自粵、閩兩省附帶鹽斤,停泊安平、基隆、滬尾,請求配運局收購”[67]。
唐鹽的售運不是隨意的,而是必須運載到臺灣府指定的港口販賣才可以,否則就會轉化為私鹽。光緒八年(1882)四月,全臺鹽務司規定:“內地唐鹽不準來竹(新竹),統歸基隆配運局收買”“倘有借名遭風進口,概作私販例論”[68]。新竹縣“迅速出示嚴禁中港口等處船只,不準勾通奸民,私相販售……務即查拿詳辦,勿得徇延”[69]。雖有時會因“體恤民艱”而有所變通,“內地船只每有以鹽壓載因遭風到竹者,案奉憲行準其量收給價”,但是并未采取縱容放任的態度,“至內地唐船,嗣后遇有借鹽壓載遭風到竹者,均作私論”[70]。不過,隨著唐鹽輸入臺灣地區的規模越來越大,且私人夾帶福建等地食鹽運至臺灣,唐鹽原本是政策允許且應發揮接濟補充作用的官鹽轉而成為侵犯臺灣鹽銷路的特殊私鹽,出現了“沿海一帶,叉港分歧,每有奸梢載運內地私鹽,停泊各口,暗勾奸民,私相販售”的局面[71],甚至“居民僻處遐陬,不知販買私鹽實干法紀,故家家戶戶相采買”[72]。這不僅與政府的要求相背離,更與販賣官鹽的贌商利益相沖突。贌商為維護自身承贌利益,以“情殷報效,認真經理,公平售價,以期商民相安”為理由,要求地方政府出示曉諭以重鹺務,“務請嚴行究治”,禁止“內地船載私鹽駛至海口,勾串本地奸民起駁售賣”,以免“銷路大有妨礙”[73]。
1895 年7 月,為強化日本在臺灣的殖民統治基礎,臺灣“總督府”頒布“官鹽廢止”告示,實現食鹽的自由買賣。[74]這導致內地食鹽大量涌入臺灣島內,“臺北鹽政當清國官辦時,每元可購八九十斤,至我國(日本)則一改而為民辦,由是泉興各船咸得自行配運,無緝拿私鹽之禁而鹽價遂大廉,每元或一二百斤或二百余斤不等”,可見此項措施為販賣私鹽提供了便利和獲得豐厚利益的空間。[75]然而即使有私鹽的涌入也難以解決臺灣北部地區食鹽短缺的問題。《臺灣新報》在1897年12月對此有所記載:“官不抽厘,民間仍吃貴鹽……其價不但有增無減,誠恐無船接濟,不敷食用也。”[76]
隨后,臺灣“總督府”不得不重新實施鹽專賣制,實際上是對清政府所施行的鹽專賣制進行重構,并試圖以提供的補助金的形式修復舊有鹽田,開設新鹽田,增加產鹽量,緩解臺灣的食鹽缺口。需要指出的是,“總督府”的補助金雖能夠解決鹽田開發中所遇到的資金短缺及災害問題,卻難以解決臺灣南北鹽場生產不均衡的結構性難題,導致唐鹽不斷增加,呈現私鹽買賣盛行的局面。當然這只是其中一個原因,更為重要的原因在于甲午戰后,臺灣鹽業仍處于恢復階段,人口卻已達267 萬之多,人均食鹽量預定為15 斤,隨著移入人口的不斷增加,又時常因“旱魃為虐,農產歉收”,分配到百姓手中的鹽,“人不過十三斤五分七厘余”,布袋嘴以南,人均更只有“九斤六分九厘余”,難以滿足食用需求。[77]
顏義芳在《日據時期賣捌人史料選編》中認為“至明治29 年度以前年年皆需由對岸輸入來補其不足”,而在“明治33 年(1900)便能充分供應島內需求,且尚有能力輸出”。[78]這一論斷應該是指臺灣中南部地區實現自產自銷,能夠自給自足并可以供應其他地方,實際上從表1中可以看出,鹽專賣制施行后,大陸輸入臺灣食鹽在此時期雖時增時減,但總體仍保持著十分龐大的進口量。1906 年6 月的《臺灣日日新報》中,就記載了臺灣北部缺鹽從福建進口唐鹽的史實,當時,“(臺灣)北部需鹽……向清國泉州府之惠安縣各港灣采買唐鹽,配到淡水港基隆港及新苗各港灣,以供民食……因之臺北食鹽,有時告匱,即如去年冬間起,臺北官鹽總館議采唐鹽若干萬”。[79]毫無疑問,即使施行專賣制度,臺灣在日據初期仍然需要依賴福建地區進口大量食鹽。
1899 年5 月2 日,臺灣總督府發布第52 號告示,依據《臺灣鹽務章程》確定“應給外國載來進口食鹽價值,茲特酌定每一百斤四十錢”。[80]此章程中,所提“外國”即指代大陸地區。同年7月2 日,“臺灣總督”兒玉源太郎公布訓令第199 號,在此要求“進口食鹽以其入庫稱量數,交付抵償金額”。[81]實際承認了唐鹽輸入的合法性,并確定了唐鹽的收購辦法。唐鹽此刻已在政策上默許為受控制的“官鹽”。其后,專賣局按以上章程,要求“外來鹽船自必遵照定例,報明鹽務局或稅關,水上警察照價收買,斷不得仍前自向民間私相買賣,業經定期買收,從此載鹽之船務須悉數繳官,給予官價,毋得偷漏”[82]。事實上,上述嚴格的規章制度并不能真正阻止唐鹽的涌入,“淡水口入港之清國帆船聯[連]續共有十八只,各船皆有私鹽入港”[83]。而且,無論是合法進入臺灣的唐鹽,還是私鹽,對島內所產食鹽都形成較為明顯的擠壓態勢,因此“督府近為經營利益起見”,自1901 年起,“所有外國鹽均禁絕進口”。[84]這一政策實則未考慮到“海上常險惡,南部鹽不能輸送北部”導致北部人口密集地區缺鹽的現狀,所以不過多久便改易規則“限其斤量許可輸入外國鹽”[85],并要求“由支配人配員在泉州府惠安縣、南安縣兩處配運,唐鹽先后報到臺北、臺中各港”[86]。
綜上所述,清代臺灣地區的私鹽問題較為突出,也比較復雜,既有島內場私、商私的存在,同時又因于臺灣偏于東南一隅,鹽產有限,福建地區的食鹽不斷涌入臺灣,形成“唐鹽接濟”的局面。“唐鹽接濟”的問題是值得我們深入研究的課題,體現了閩臺地區在經濟上和管理上密不可分的依賴關系,特別是甲午戰爭前后,唐鹽在政策上形成了有“官”有“私”到化“官”為“私”,再到默許運銷的過程。面對私鹽日漸盛行的形勢,清政府在臺灣仿照大陸鹽政體制建立鹽專賣制,不斷在制度層面完善產銷體系,重視緝捕私鹽。這些舉措與兩淮、湖廣和四川等地查禁私鹽的方法既有相似性,又有一定的區別,根源在于臺灣鹽政是以自產自銷,自給自足為中心的產銷模式,政府強化控制產銷體系,緝捕私鹽的重點是以防止島內和大陸地區的私鹽為核心,而兩淮、湖廣等地區則以查禁場私、官私、鄰私為主旨。在實際執行過程中,無論是清政府還是臺灣總督府,雖處處設置障礙防止作為私鹽的出現,但是面對龐大的食鹽缺口,私鹽問題未能得到真正遏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