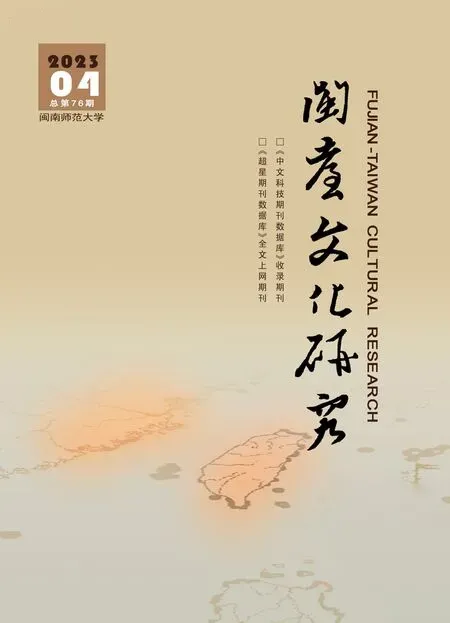弘一大師著述中的華嚴學意蘊
韓煥忠
(蘇州大學宗教研究所,江蘇蘇州 215123)
弘一大師雖然以研究和弘揚南山律宗為畢生志業,以往生極樂世界為終極歸宿,但是他對《華嚴經》及賢首義理亦極為傾心。我們閱讀其存世的著述,可以體會到其中所蘊含的豐富的華嚴學意蘊。
弘一大師,俗名李叔同,祖籍浙江平湖,于清光緒六年庚辰九月二十日(1880年10月23日)出生于天津。五歲喪父,七歲啟蒙于仲兄,除學習儒家經典外,還曾肆力于篆隸刻石。受風氣感染,主張維新,以康有為門下自居,戊戌變法失敗后,攜眷奉母避居上海。光緒三十一年乙巳(1905)母亡后東渡日本,入東京美術學校(戰后改名為東京藝術大學)學繪畫、音樂,與學友創春柳社。曾參加徐淮賑災義演,飾茶花女。宣統三年辛亥(1911)畢業歸國,任直隸模范工業學堂圖畫教員。民國元年(1912)春至滬,初任教城東女學,未幾主編《太平洋報畫報》主編,為曼殊編輯發表《斷鴻零雁記》,秋間赴杭州任浙江兩級師范學校(次年改稱浙江省立第一師范學校,簡稱浙江一師)圖畫音樂教員。民國五年丙辰(1916)秋,曾在杭州大慈山定慧寺實行斷食發二十余日,自此購閱佛書,出入佛寺,有離俗之意。民國七年戊午(1918)七月十三日依杭州虎跑寺了悟上人披剃,法名演音,法號弘一,九月至靈隱寺受具足戒,馬一浮貽以《靈峰毗尼事義要集》及《寶華傳戒正凡》,披覽后遂發心學戒。居止多在浙、閩二省,弘律亦曾至于上海、江蘇、山東等地。衣單儉樸,持戒精嚴,法緣廣被,道望隆盛。民國三十一年壬午(1942)九月初四日午后八時安詳示寂于泉州不二祠溫陵養老院晚晴室,世壽六十三歲,僧臘二十五年。[1]
弘一大師沒有專門的華嚴著述,因此他的華嚴思想也就沒有集中體現的形式,而是散見在他撰寫的序、跋和題記之中。我們對相關資料進行總結和概括,可以發現弘一大師的華嚴思想包括課誦研讀華嚴、悉心體會華嚴、隨緣弘揚華嚴等幾個方面,下面分而述之,以就正方家。
一、課誦研讀華嚴
《華嚴經》是中國佛教界普遍尊奉的經典,華嚴宗著述被認為是對《華嚴經》最好的注疏和詮釋。弘一大師披剃不久,即與《華嚴經》和華嚴宗著述結下深厚的因緣,遂將讀誦《華嚴經》奉為日課,由此開啟了他對《華嚴經》和華嚴宗著述的終生研讀。
日常修持,弘一大師將《華嚴經》奉為課誦的基本內容。1926年十二月十一日,弘一大師在杭州致蔡丐因居士信中說:“朽人讀《華嚴》日課一卷以外,又奉《行愿品》別行一卷為日課,依此發愿。又別寫《凈行品》《十行品》《十回向品》(初回向及第十回向章)作為常課。每三四日或四五日輪誦一遍。附記其法,以備參考。”[2]就是說,對于唐譯八十卷《華嚴經》七處九會三十九品,弘一大師對于《行愿品》《凈行品》《十行品》《十回向品》(初回向及第十回向章)極為重視,他將這幾品單獨寫出,每天讀誦一卷《華嚴經》之外,再加誦這幾品中的一品。后來他發現徐蔚如讀誦《華嚴經》方法不錯,于是就借鑒過來,并推薦給弟子。1931 年四月廿八日,他在上虞法界寺致弘傘法師信中說:“徐居士說讀《華嚴經》法,讀唐譯至五十九卷《離世間品》畢,應接讀貞元譯《行愿品》四十卷,共九十九卷。應日誦者為《凈行品》《問明品》《賢首品》《初發心功德品》《如來出現品》,及《行愿品》末卷,又《十行品》《十回向品》初、十二章。”[3]我們據此可知,弘一大師日常讀誦的《華嚴經》是將八十卷本和四十卷本整合為一的本子。直到現在,他這一做法還被不少修學《華嚴經》的信眾奉為圭臬。通過十幾年的每日都不間斷的課誦修學,弘一大師對《華嚴經》的文句稔熟于心,乃至形諸夢寐。癸酉(1933)正月八日年,他移居廈門中山公園妙釋寺,夜間夢見自己變身為一少年,正與一位儒師同行,聽到身后有人在唱誦《華嚴經·賢首品》偈頌,非常動聽,于是就與那位儒師返回,看到十幾人席地聚坐,其中一人彈琴,一老者唱偈,“余乃知彼以歌說法者,深敬仰之;遂欲入坐,因問聽眾,可有隙地容余等否?彼謂兩端悉是虛席。余即脫履,方欲參座,而夢醒矣。”[4]他連忙挑燈將夢中老者所唱偈頌書寫下來,并發愿今后永遠讀誦受持和如說修行。俗話說,日有所思,夜有所夢,弘一大師夢為少年得與華嚴法席,正是現實中他希望自己能像善財童子那樣廣參善知識、廣學諸法門的心理折射。而按照佛教傳統的說法,此夢也是弘一大師修學《華嚴經》有所成就的體現。
課誦之余,弘一大師依據華嚴宗諸祖的章疏建立起對《華嚴經》的理解。他對中國華嚴宗的實際創始人、三祖賢首法藏非常欽佩,故而他致信丁福保:“竊謂欲重見正法住世,當自專崇佛說始,賢首以經釋經,不為無見,佩甚佩甚。”[5]在他看來,賢首法藏的《華嚴經探玄記》就是“專崇佛說”“以經釋經”的典范,因此他認定“此書極精要。”[6]華嚴宗四祖清涼澄觀依唐譯八十卷《華嚴經》撰造疏鈔,為歷代疏釋《華嚴經》的集大成之作,因此深得弘一大師的重視。1921年十一月初六他從溫州致信真如居士:“朽人于華嚴,唯略習《清涼疏鈔》,未嘗卒業。”[7]此處所謂“略習”“未嘗卒業”云者,雖為弘一大師以謙遜自處,但已可充分顯示他對《華嚴經大疏鈔》的用力。1931年四月廿八日,弘一大師在上虞法界寺致信弘傘法師:“音近數年來頗致力于《華嚴疏鈔》,此書法法具足,如一部佛學大辭典。若能精研此書,于各宗奧義皆能通達(凡小乘論、律,三論、法相、天臺、禪、凈土等,無不具足)。仁者暇時,幸悉心而玩索焉。”[8]多年的研讀,使他體會到,劃分經疏段落,佛教稱為“科判”,由此形成的“科文”,非常有利于修學者對經疏的理解和掌握,因此他于1924年十二月初三日在溫州致信丐因居士:“《華嚴經疏科文》十卷,未有刻本。日本《續藏經》第八套第一冊、二冊,有此科文。他日希仁者至戒珠寺檢閱。疏、鈔、科三者如鼎足,不可闕一。楊居士刻經疏,每不刻科文,厭其繁瑣,蓋未嘗詳細研審也。……今屏去科文而讀疏鈔,必致茫無頭緒。北京徐居士刻經,悉依楊居士成規,亦不刻科。……朽人嘗致書苦勸,彼竟固執舊見未肯變易,可痛慨也。”[9]希望他能改變刻經的這一做法做些努力。1941 年十一月十八日,他在泉州致信無我、圓凈兩位居士:“《華嚴經疏科文表解》出版時,乞寄二部,致泉州承天寺交弘一收,致感!”[10]此時的弘一大師已是年老體弱,但仍想著繼續深入研讀《華嚴經大疏鈔》,對于深入研讀《華嚴經》宗旨和義理表現出一種至老彌篤的堅韌和勇毅。
弘一法師還曾親近當時華嚴大德的講經法筵。1928 年11 月,弘一大師為了編輯出版《護生畫集》的事情,特地趕到上海,他聽說當時以華嚴著稱于世的大德高僧應慈老法師正在清涼寺講《華嚴經》,于是特地抽空去聽。著名佛教史家蔣維喬先生(號竹莊)《晚晴老人遺牘集序》中對此有所述及:“回憶戊辰乙巳間,上海清涼寺請應慈老法師宣講《華嚴經》,余恒往列席。某日有一山僧翩然戾止,體貌清癯,風神朗逸,余心異之;但在法筵,未便通話。歸而默念,莫非弘一法師乎?既而會中有認識法師者,告我曰是也。余擬于散會時邀之談話,而法師已飄然長往矣。”[11]應慈老法師是華嚴大學創辦者月霞大師的師弟,也是華嚴大學最主要的教師,在月霞大師圓寂后一力承擔起主辦法界學院、弘揚華嚴經教的重任,培育了持松、常惺、慈舟、南亭等一大批華嚴宗高僧,其法譽道望深受當時佛教界的尊崇。弘一大師慕名列席應慈老法師的法筵,并且表現如此低調,絲毫沒有擺什么名僧高人的架子,正是他極為尊崇華嚴高僧、虔修華嚴經教的集中體現。
從當時中國佛教界的實際情況來看,將《華嚴經》奉為日課的僧人與居士大有人在,但他們極少會去研讀華嚴宗著述,因而很難形成對《華嚴經》的正確理解,從而實現改造和提升自己思想境界的修行目標。學界雖然有人研讀華嚴宗祖師著述,但其主旨卻在于勾勒華嚴宗的思想體系,而非當做修行的途徑。弘一大師將這兩者有機結合起來,大有恢復中國佛教興盛時期解行并進優良傳統的意味。
二、悉心體會華嚴
弘一大師在俗時,于繪畫、京劇、話劇、篆刻諸技藝無不通達,且皆能臻其玄妙,其出家后則一切摒棄,唯保留書法一藝,因為中國人比較重視書法,世人得到他所書寫的諸佛菩薩名號、經典及佛語,無不視為珍寶,張掛懸耀之際,正可引人企向佛教。他運用自己的書法藝術,手書《華嚴集聯三百》并抄寫《凈行品》《賢首品》《十回向品》初章及十章以及《普賢行愿品》等經文,為中國佛教文化的豐富和發展留下了非常寶貴的藝術珍品。而從弘一大師為這些書法作品所做的序言或跋語中,我們還可以看出他對《華嚴經》思想義理的深刻理解和悉心體會。
最能體現弘一大師對《華嚴經》的悉心體會的,當為他1931 年手書并在上海付印的《華嚴集聯三百》。對聯作為建筑裝飾的基本方式,是我國傳統文化的重要形態之一,要求內容關聯,語言警拔,對仗工整,平仄和諧,并以適當的書法藝術呈現出來。弘一大師將《華嚴經》中偈誦文句集為對聯,看似簡單,實則包含著他對《華嚴經》偈頌文意的深刻理解和悉心體會,包含著他在書法藝術上的匠心獨運。筆者不懂書法,于此略置不論,且從其著作中抄錄相關文獻二則于此。其一為《贈萬均法師華嚴集聯跋》:“去歲萬均法師著《先自度論》,友人堅執謂是余撰,余心異之,而未見見其文也。今歲法師復著《為僧教育進一言》,乃獲披見,嘆為稀有,不勝忭躍。求諸當代,罕有匹者,豈余暗識,所可及也。因呈拙書,以志敬仰。丁丑三月,集華嚴偈句,一音。聯曰:‘開示眾生見正道,猶如凈眼觀明珠。’”[12]一音為弘一大師書法作品常用署名之一。弘一大師認為萬均法師發表的有關僧教育的論文具有為眾生開示正道的作用,而眾生認真學習閱讀萬均法師的論文,必定會有非常大的收獲,就像以清凈之眼觀看寶貴的明珠一樣真切可貴。弘一大師運用引用《華嚴經》偈頌文句,以贈送書法對聯的形式,向關注僧教育并有真知灼見的高僧萬均法師表達了自己誠摯的敬意。其二為《贈僧懺上人華嚴集聯并跋》:“當度眾生界,當凈國土界;普入三昧門,普游解脫門。唐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入法界品彌勒菩薩說頌集句。僧懺上人供養,歲次甲戌五月尊勝院沙門髻目敬書。”[13]髻目也是弘一大師書法作品所用署名之一,不過不如一音、演音等常用。弘一大師向僧懺法師贈送這幅對聯,意在鼓勵僧懺法師荷擔如來家業,實踐大乘佛法,下化眾生,上求菩提,為中國佛教做出自己應有的貢獻。毋庸置疑,弘一大這些墨寶的精神鼓勵作用是巨大的,其中運用之妙自然也是他悉心體會《華嚴經》的藝術成就。
弘一大師的《華嚴集聯三百》在朋友和弟子間頗得好評。他的音樂學生、《華嚴集聯三百》印行事務經理人劉質平在所撰《華嚴集聯三百跋》中說:“為太師母七十冥辰,我師緬懷罔極,追念所生,發宏誓愿,從事律學撰述,并以余力集華嚴偈為聯語,手錄成冊,冀以善巧方便,導俗利生。質平偶因請業,獲睹宏裁,鴻朗莊嚴,嘆為稀有。亟請于師付諸影印,庶幾廣般若之宣流,永孝思之不匱。世界有情,共頂禮之。”[14]由此可知,弘一大師印行《華嚴集聯三百》還具有為其母追念冥壽的意義。1937年,國學大師馬一浮先生避寇桐廬北郊,遇劉質平,獲睹《華嚴集聯三百》,遂撰跋語,中云:“質平得大師片紙只字,皆珍若拱璧。積冊至多,裝褙精絕。余為題曰:‘音公雜寶。’此《華嚴集聯》,亦大師欲以文字因緣方便說法之一。非質平善根深厚,何以獨見付囑鄭重如是耶?大師書法得力于張猛龍碑,晚歲離塵,刊落鋒穎,乃一味恬靜,在書家當為逸品。嘗謂華亭于書頗得禪悟,如讀王右丞詩。今觀大師書,精嚴凈妙,乃似宣律師文字。蓋大師深究律學,于南山、靈芝撰述,皆有闡明。內熏之力自然流露,非具眼者,未足以知之也。”[15]馬一浮先生也是民國時期最為著名的書法家之一,而且其儒學與佛學造詣當世皆罕有其匹,所以他對弘一大師《華嚴集聯三百》在佛教上獨特意義以及其在書法藝術上的獨特造詣都能夠做出極為恰當、公允的評價。劉質平及馬一浮先生之評價,也可以說是因弘一大師對《華嚴經》的悉心體會而深心有得者。
弘一大師深知其中的艱難,他極為擔心有人也來效仿自己,因此在《華嚴集聯三百序》中特別闡明:“割裂經文,集為聯句,本非所宜。今循道侶之請,勉以綴輯。其中不失經文原意者雖亦有之,而因二句集合,遂致變易經意者頗復不鮮。戰兢悚惕,一言三復,竭其努力,冀以無大過耳。茲事險難,害多利少,寄語后賢,毋再賡續。偶一不慎,便成謗法之重咎矣。”[16]也許弘一大師有見于深入經藏、游心華嚴者世罕其人,如果率爾操觚,必致人法兩損,又慈悲心重,故而如此垂誡后世。在筆者看來,弘一大師如果不是深心有會于《華嚴經》的話,何能作如此痛切之語!
三、隨緣弘揚華嚴
除了讀誦、研究、書寫華嚴,弘一大師還非常注意運用做演講、撰寫題記、回復信函的時機,隨緣弘揚華嚴。
弘一法師高尚的道德品格得到了社會各界的廣泛尊重,因此很多地方都非常喜歡邀請弘一大師前去演講。如壬申(1932 年)十月,他在廈門妙釋寺為大眾演講凈土法門時說:“至于讀誦大乘,亦是觀經所說。修凈土法門者,固應誦《阿彌陀經》,常念佛名。然亦可以讀誦《普賢行愿品》,回向往生。因經中最勝者——《華嚴經》。《華嚴經》之大旨,不出《普賢行愿品》第四十卷之外。此經中說,誦此普賢愿王者,能獲種種利益,臨命終時,此愿不離,引導往生極樂世界,乃至成佛。故修凈土法門者,常讀誦此《普賢行愿品》,最為適宜也。”[17]在這里他將讀誦《華嚴經》,尤其是讀誦《普賢行愿品》的重要性給予了特別的強調。癸酉(1933 年)七月十一日,他在泉州開元寺為幼年諸學僧講:“《華嚴經行愿品》末卷所列十種廣大行愿中,第八曰常隨佛學。若依華嚴經文所載種種神通妙用,決非凡夫所能隨學。但其他經律等,載佛所行事,有為我等凡夫作模范,無論何人皆可隨學者,亦屢見之,今且舉七事。”[18]如佛自掃地、佛自舁弟子及自汲水、佛自修房、佛自洗病比丘及自看病、佛為弟子裁衣、佛自為老比丘穿針、佛自乞僧舉過,“如是七事,冀諸仁者勉力隨學。遠離驕慢,增長悲心,廣植褔業,速證菩提。是為余所希愿者耳!”[19]《普賢行愿品》重視發心實踐,但如何實踐呢?弘一此處以佛為例,生動展現了樸實和平凡的生活就是實踐普賢行愿的最好的道場。戊寅(1934 年)十月七日,他在安海金墩宗祠為大眾演講佛法各種宗派,其中說到華嚴宗:“華嚴宗,又名賢首宗。唐初此土所立,以《華嚴經》為依。至唐賢首國師時而盛,至清涼國師時而大備。此宗最為廣博,在一切經法中稱為教海。宋以后衰,今殆罕有學者,至可惜也。”[20]弘一大師對華嚴宗的衰落充滿了惋惜之情,也透露出他對大眾深入華嚴教海的殷切期望。戊寅(1934年)十月八日,他在安海金墩宗祠人天教門,就運用華嚴宗的判教思想,認定人天教是當下最為適宜的佛法。他說:“佛法寬廣,有淺有深。故古代諸師,皆判‘教相’以區別之。依唐圭峰禪師所撰《華嚴原人論》中,判立五教:一、人天教,二、小乘教,三、大乘法相教,四、大乘破相教,五、一乘顯性教。以此五教,分別淺深。若我輩常人易解易行者,惟有‘人天教’也。其他四教,義理高深,甚難了解,亦難實行。意欲普及社會,又可補助世法,以挽救世道人心,應以‘人天教’最為合宜也。”[21]弘一大師這些對華嚴的隨緣弘揚,自然會引起聽眾的企向之心,有利于華嚴思想的普及和深入人心。
弘一大師還很喜歡印施《華嚴經》并為其撰寫題記,以利于流通和學習。如,很多知識分子喜歡他的《華嚴集聯三百》,他希望大家能夠由此發心深入學習和研究《華嚴經》,遂于卷末別述《華嚴經讀誦研習入門次第》一卷,實際上是將自己讀誦和研習《華嚴經》及華嚴宗祖師著述的心得體會和盤托出。在《圓覺經如來本起清凈因地法行題記》中,他說:“圭峰宗密禪師《行愿品鈔》云:‘發菩提心者,謂菩提是求果德,即無上菩提。’心是現前能求之心。以發是求菩提之心,故名發菩提心也。或曰菩提名覺,即覺察覺悟也。謂了諸煩惱過患,不起放逸,達本心源,慧光內燭也。以起是心,故名發菩提心。”[22]引用華嚴宗五祖圭峰宗密的論著,告訴大家什么是發菩提心,如何發菩提心。中國人普遍信仰觀世音菩薩,他就將貞元譯四十卷《華嚴經》中善財童子參訪觀世音菩薩一章單獨析出,別為一卷,并撰寫《觀自在菩薩章序》[23],顯然具有借助觀世音菩薩的風行而為《華嚴經》開道的意味。其《溫陵刻普賢行愿品跋》云:“戊寅正月元旦始,講《普賢行愿品》于草庵。二月一日始,復講此品于承天寺。三月一日始,講華嚴大意于清塵堂,并勸諸善友集合讀誦《普賢行愿品》十萬部,可謂殊勝之因緣矣,于泉州先后印行《普賢行愿品》共千數百冊,普施大眾隨喜誦讀。以上所有功德,悉皆回向法界有情,惟愿災難消除,身心安豫,同生極樂世界,速成無上菩提。慧水大華嚴寺沙門一音并記。”[24]其《福州鼓山庋藏經版目錄序》謂鼓山所藏清初刊刻《華嚴疏論纂要》“為近代所稀見者。余因倡緣印布,并以十數部贈予扶桑諸寺,乃彼邦人士獲斯校寶,歡喜忭躍,遂為攝影鏤版,載諸報章,布播遐邇。因是彼邦僉知震旦鼓山為庋藏佛典古版之寶窟。”[25]弘一大師自奉非常儉樸,但在印行《華嚴經》方面卻不吝金錢,布施法寶時也不論什么此土彼邦,正是高僧具足無緣大慈、同體大悲的體現。
至于在回復門人弟子的書信中弘揚華嚴的例子就更多了。如1929 年八月十四日,弘一大師在溫州致豐子愷信中說:“‘不請友’三字之意,即是如《華嚴經》云:‘非是眾生請我發心,我自為眾生作不請之友’之意。因尋常為他人幫忙者,應待他人請求,乃可為之。今發菩提心者則不然,不待他人請求,自己發心,情愿為眾生幫忙,代眾生受苦等。友者,友人也。指自己愿為眾生之友人。”[26]他希望他的得意弟子能夠成為《華嚴經》所說的眾生的不請之友。特別是給蔡冠洛(丐因居士)的心中,幾乎每一封都有暢談如何讀誦修學《華嚴經》、如何研讀《華嚴經大疏鈔》的內容,此處不再一一例舉。
弘一大師著作中的華嚴學意蘊雖然是點滴的、散見的呈現,但由于他個人具有廣泛而持久的影響力,自然會給近代華嚴學的復興帶來極大的助力。在他圓寂五十多年之后,時任中國佛教協會會長的趙樸初居士在給弘一大師所寫的贊詩中還不忘肯定他的華嚴學造詣。1994年6月,樸老寫《華夏出版社重印弘一法師寫經,觀后敬題,次韻吳昌碩先生題弘師手書<梵網經>絕句二首》:“端嚴恍見頭陀像,亂世淄門第一人。春滿花枝非忘世,悲心淚濕大千塵。華嚴梵網悉心參,賢首南山共一龕。喜見化身千百億,遍虛空界雨優曇。”[27]第一首表彰了弘一大師的人格和僧格,第二首表彰了他在華嚴學和南山律方面的深厚造詣。1995 年8 月,樸老還撰寫《弘一大師誕生一百五十周年書法真跡文物展覽贊辭》:“猗歟大師,國族之光。丁年游學,播譽扶桑。文藝維新,絳帳初張。教育英才,德學兼長。博聞窮理,傾心圣諦。力決世網,出家入釋。普賢行愿,南山戒律。心持躬踐,畢生無斁。書道猶龍,行空御風。以順眾生,以啟盲聾。南天展示,妙跡遺蹤。甘露普施,贊嘆無窮。”[28]這首贊辭不但縷敘了弘一大師的生平經歷,還特意強調了他對普賢行愿的努力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