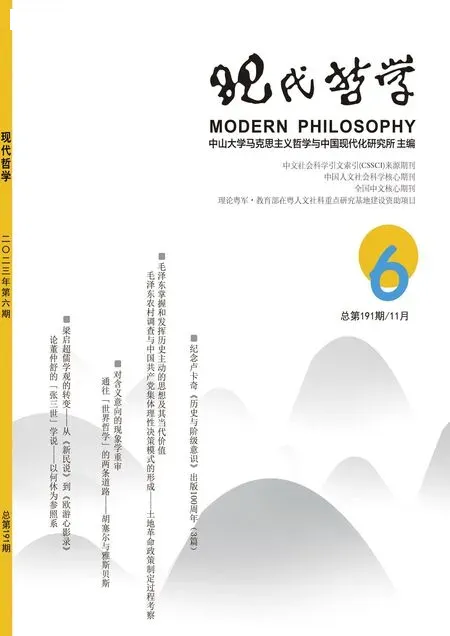論康德道德哲學(xué)中的責(zé)任倫理思想
——基于對至善思想的考察
羅亞玲
自馬克斯·韋伯(Max Weber)提出責(zé)任倫理(Verantwortungsethik)的概念以來,尤其是漢斯·約納斯(Hans Jonas)的責(zé)任倫理思想得到廣泛傳播以來,康德的倫理學(xué)獲得一個(gè)富有特色的標(biāo)簽——意念倫理(Gesinnungsethik)。這是一個(gè)帶有貶義色彩的標(biāo)簽,它表示這種倫理學(xué)只強(qiáng)調(diào)遵循道德原則、不考慮行動(dòng)后果,因此是對康德道德哲學(xué)的一種批評。這種批評其實(shí)并不新鮮,一直以來對康德道德哲學(xué)的所謂原則倫理、嚴(yán)格主義以及圣人倫理之類的批評表達(dá)的也是同樣的意思。但在康德研究領(lǐng)域,意念倫理之說的提出還是在德國學(xué)界引發(fā)了一小波相關(guān)討論熱潮,馬提亞斯·凱特納(Matthias Kettner)和哈拉爾德-克爾(Harald K?hl)等學(xué)者都直接針對康德道德哲學(xué)是否為意念倫理的問題發(fā)表過著述,并對此給出了肯定的答案。(1)See Matthias Kettner,“Kant als Gesinnungsethiker?”,Deutsche 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e 40 (5),1992,S. 525-541;Harald K?hl,Kants Gesinnungsethik (Quellen und Studien zur Philosophie Bd. 25),Berlin/New York:Walter de Gruyter,1990.此外,阿佩爾派的對話倫理學(xué)家,包括阿佩爾(Karl-Otto Apel)本人及其弟子迪特里希·伯勒爾(Dieterich B?hler)及再傳弟子米夏·H·維爾納(Micha H.Werner)等人,在闡發(fā)對話倫理學(xué)思想時(shí)都指出對話倫理學(xué)的貢獻(xiàn)在于通過引入一個(gè)責(zé)任倫理的維度來補(bǔ)充康德道德哲學(xué)的不足,這表明他們都預(yù)設(shè)了康德的思想本身是缺乏責(zé)任倫理之維的意念倫理。據(jù)此,康德倫理學(xué)之為意念倫理似乎是毋庸置疑的事實(shí)。
但康德倫理學(xué)究竟是否為缺少責(zé)任倫理之維的意念倫理,始終是一個(gè)可以繼續(xù)追究的問題。在德國學(xué)界,奧特弗里德·赫費(fèi)(Otfried H?ffe)自1970年代以來一直嘗試以亞里士多德主義的視角來理解康德的普遍主義倫理思想,強(qiáng)調(diào)判斷力在其中的地位和意義;克里斯托弗·胡比希(Christoph Hubig)等則試圖從康德和亞里士多德那里獲取思想資源建構(gòu)其責(zé)任倫理思想;萊納·維默爾(Reiner Wimmer)指出康德的定言命令式具有雙重功能,即一方面作為基本的道德原則,另一方面作為道德判斷的程序性原則(2)Reiner Wimmer,“Die Doppelfunktion des Kategorischen Imperativs in Kants Ethik”, Kant-Studien 73(3),1982,S. 291-320.,表明定言命令式與阿佩爾的對話原則的相似性,直接提示了康德道德哲學(xué)中可能生發(fā)責(zé)任倫理的空間。他們的工作無疑為回答我們的問題提供了新思路。
本文隸屬于一個(gè)系統(tǒng)性的研究項(xiàng)目,該項(xiàng)目旨在通過深入康德道德哲學(xué)的諸多環(huán)節(jié),展現(xiàn)其義務(wù)論倫理學(xué)的責(zé)任倫理之維。基于對責(zé)任倫理之要旨和可能性的基本把握,本文聚焦于康德的至善思想,通過對至善思想之內(nèi)涵和論證思路的系統(tǒng)梳理,表明其所包含的責(zé)任倫理思想。
一、責(zé)任倫理的要旨和可能性
責(zé)任倫理概念最早由馬克斯·韋伯在其1919年題為《以政治為業(yè)》的著名演講中提出。在當(dāng)時(shí)剛剛經(jīng)歷戰(zhàn)爭創(chuàng)傷、處于混亂之中的德國,韋伯深刻地意識(shí)到,“人們身上普遍和存在的缺陷”使得我們“根本沒有權(quán)力假定人的善良和完美”,不完美的人和不完美的世界使得世上的事從來都是善因未必結(jié)出善果,他因此反對用目的把手段神圣化,反對簡單地把“出于純潔意念的行動(dòng)最終造成的惡果”歸諸“這個(gè)世界”,歸諸“世人的愚蠢”或“創(chuàng)造這些愚人的上帝的意志”。(3)[德]馬克斯·韋伯:《以政治為業(yè)》,《馬克斯·韋伯全集》第17卷,呂叔君譯,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223頁。他提出意念倫理和責(zé)任倫理的區(qū)分,前者指那種只考慮遵循道德原則不顧行動(dòng)之可能結(jié)果的倫理學(xué),后者主張同時(shí)納入對行動(dòng)后果的考慮。他批評意念倫理沒有充分考慮現(xiàn)實(shí)世界的缺陷,不足以指導(dǎo)真實(shí)世界中人們的行動(dòng)。他提倡的責(zé)任倫理盡管因主張對行動(dòng)的可能后果負(fù)責(zé)而區(qū)別于意念倫理,但作為對意念倫理的補(bǔ)充(4)同上,第234頁。,又區(qū)別于后果論的倫理學(xué),它預(yù)設(shè)了所謂意念倫理的基本義務(wù)或原則。
責(zé)任倫理在當(dāng)代的發(fā)展與漢斯·約納斯《責(zé)任原則——建構(gòu)一種適合科技文明的倫理學(xué)的嘗試》一書的出版有著重要關(guān)系。約納斯認(rèn)為,在科技文明條件下,人類行為發(fā)生的本質(zhì)性變化使其面臨新的倫理挑戰(zhàn)。這種本質(zhì)性變化在于:一方面,人類行動(dòng)后果可能產(chǎn)生重大和深遠(yuǎn)影響,重大到可能毀滅人類,深遠(yuǎn)到可能涉及遙遠(yuǎn)的子孫后代;另一方面,由于人類行動(dòng)的集體性和累積效應(yīng),其后果變得越來越難以預(yù)知,人類逐漸失去對其行動(dòng)后果的掌控能力。(5)Hans Jonas,Das Prinzip Verantwortung,F(xiàn)rankfurt a.M.:Suhrkamp,1984,S. 27ff,31.之所以說這種情況使得人類面臨新的倫理挑戰(zhàn),是因?yàn)樗袀鹘y(tǒng)倫理學(xué)都是“當(dāng)前倫理”(Ethik der Gegenwart),都直接預(yù)設(shè)了人類的存在和人類本質(zhì)的恒定不變,沒有一種傳統(tǒng)倫理學(xué)考慮人類可能毀滅或人的本質(zhì)可能發(fā)生變化的問題。(6)Ibid.,S. 22ff.約納斯主張?jiān)诳萍紩r(shí)代,人類應(yīng)當(dāng)承擔(dān)起對其行動(dòng)之長遠(yuǎn)后果的責(zé)任,這是其責(zé)任倫理的主題。阿佩爾稱約納斯主張的這種責(zé)任為未來責(zé)任,以區(qū)別于韋伯的后果責(zé)任。但約納斯和韋伯一樣,把自己的責(zé)任倫理與康德的意念倫理相區(qū)別,并且把責(zé)任倫理視為對意念倫理的補(bǔ)充。
在約納斯出版其《責(zé)任原則》一書之前,阿佩爾的對話倫理學(xué)就已經(jīng)表達(dá)了與未來責(zé)任原則相一致的主張。其先驗(yàn)語用學(xué)路向的對話倫理學(xué)通過兩個(gè)步驟完成基本道德原則的倫理:首先通過對理想交往共同體之可能性條件的先驗(yàn)反思,確立了平等權(quán)利和參與對話的義務(wù)等基本原則(這被稱為其對話倫理學(xué)的A部分),然后基于對現(xiàn)實(shí)交往共同體的局限性以及理想和現(xiàn)實(shí)的辯證關(guān)系的考慮,證成了兩條基本的策略性道德原則作為補(bǔ)充原則,為道德原則在具體情境下的靈活應(yīng)用提供合理性辯護(hù)和指引性原則(這被稱為B部分)。B部分證成的兩條原則是以保護(hù)人類的持續(xù)存在為要旨的生存原則,和謀求社會(huì)進(jìn)步的解放原則。(7)[德]卡爾-奧托·阿佩爾:《哲學(xué)的改造》,孫周興、陸興華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7年,第337頁。盡管阿佩爾當(dāng)時(shí)尚未使用責(zé)任倫理的概念,但其生存原則和解放原則可以說既包含了韋伯對現(xiàn)實(shí)世界之缺陷的考慮,也包含了約納斯對科技時(shí)代人類行動(dòng)可能的毀滅性后果的考慮。這使得阿佩爾在約納斯《責(zé)任原則》出版之后,一方面看到約納斯未來責(zé)任原則的深刻洞見,另一方面也敏銳發(fā)現(xiàn)其未來責(zé)任思想在論證和應(yīng)用上的困難。出于對未來責(zé)任問題的關(guān)注,阿佩爾后期在其對話倫理學(xué)中強(qiáng)化責(zé)任概念,并提出對話-責(zé)任倫理學(xué)(Diskurs-Verantvortungsethik)之說。其中,阿佩爾進(jìn)一步明確其對話倫理學(xué)的A、B兩個(gè)部分的論證思路,并將其兩部分確立的道德原則闡發(fā)為平等權(quán)利和共同責(zé)任兩大原則,以此為未來責(zé)任原則提供合理的哲學(xué)論證,同時(shí)闡明其應(yīng)用之可能性。這些工作既是對韋伯和約納斯的責(zé)任倫理思想的整合,也體現(xiàn)了一個(gè)明確的意圖,即讓責(zé)任倫理成為一種獨(dú)立的倫理學(xué)思想,而不僅僅是作為對意念倫理的補(bǔ)充。
結(jié)合上述責(zé)任倫理從韋伯到阿佩爾的發(fā)展歷程,可以做兩點(diǎn)總結(jié),為下文考察康德的思想提供參照。第一點(diǎn)涉及責(zé)任倫理的基本主張。不難發(fā)現(xiàn),責(zé)任倫理既不同于原則倫理意義上的義務(wù)論倫理學(xué),又區(qū)別于后果論倫理學(xué)。責(zé)任倫理的要旨在于,在承認(rèn)普遍有效之道德原則的基礎(chǔ)上,在原則應(yīng)用的環(huán)節(jié)中納入對行動(dòng)后果的考量,并通過這種方式進(jìn)一步建構(gòu)基本的道德原則。因此,一種獨(dú)立的責(zé)任倫理就是要整合義務(wù)論和后果論,或者說要建構(gòu)一種義務(wù)論倫理學(xué),這種義務(wù)論倫理學(xué)既承認(rèn)道德原則的普遍有效性,又能為道德原則在具體情境下的靈活應(yīng)用留下空間和進(jìn)一步的原則指導(dǎo)。第二點(diǎn)涉及責(zé)任倫理的可能建構(gòu)思路。雖然韋伯和約納斯并沒有完成建構(gòu)一門獨(dú)立的責(zé)任倫理的任務(wù),但阿佩爾的工作給出了較為充分的提示。阿佩爾的A、B兩部分論證策略從根本上說就是:首先從一個(gè)抽象的理性的視角出發(fā),即通過對理想交往共同體或理想對話之可能行條件的先驗(yàn)反思,確立一些基本的道德原則;然后結(jié)合對現(xiàn)實(shí)世界之局限性的認(rèn)識(shí),將之前確立的基本道德原則視為指導(dǎo)性理念,進(jìn)一步確立具有責(zé)任倫理意涵的策略性道德原則。第二步的論證是對第一步的擴(kuò)展,為第一步確立的原則在現(xiàn)實(shí)世界中的靈活應(yīng)用提供進(jìn)一步的指導(dǎo)原則,其總體思路完全符合責(zé)任倫理整合義務(wù)論和后果論的基本宗旨。
二、至善理念的基本主張
至善這一概念在康德的三大批判、《純?nèi)焕硇越缦迌?nèi)的宗教》以及《道德形而上學(xué)》(8)《純?nèi)焕硇越缦迌?nèi)的宗教》(Die Religion innerhalb der bloβen Vernunft)是康德有關(guān)宗教思想的系列論文集編,以下簡稱《宗教論文集》,標(biāo)注縮略為Religion。《道德形而上學(xué)》(Die Metaphysik der Sitten),以下縮略為MS。《實(shí)踐理性批判》(Kritik der praktischen Vernunft),以下縮略為KpV。本文引用康德文獻(xiàn)均在正文中標(biāo)注著作名稱的德文簡寫及科學(xué)院版卷次和頁碼。等重要著作中均有出現(xiàn),可謂康德思想中最重要的概念之一。一直以來,盡管圍繞與其相關(guān)的德福一致問題以及靈魂不滅和上帝存在兩大預(yù)設(shè)有較多討論,該概念在康德思想中的地位和重要性仍未得到足夠重視,以致至善與其道德哲學(xué)的相關(guān)性甚至被當(dāng)成一個(gè)值得懷疑的問題。本文無意在整個(gè)康德哲學(xué)的框架內(nèi)對至善思想展開全面考察,而是試圖在其道德哲學(xué)中對至善的內(nèi)涵和論證思路進(jìn)行系統(tǒng)梳理,表明其所包含的責(zé)任倫理思想及其對理解康德倫理學(xué)基本主張的重要意義。
(一)至善即德福一致
康德至善概念對應(yīng)的德文詞是das h?chste Gut,可直譯為“最高的善”,但康德用此概念并非意指德性的最完善狀態(tài),而是指“有理性能力的有限者”的“完整和圓滿的善”(KpV 5:110)。盡管“有理性能力的有限者”和“完整和圓滿的善”等表述的特殊含義有待進(jìn)一步明確,但康德在提出至善概念時(shí)即明確指出,至善即在于“德福一致”,它包含“德”和“福”兩個(gè)要素,是對德福相匹配的要求。
弗洛里安·馬韋德(Florian Marwede)指出,康德的至善概念包含的“德”的要素,在不同語境下可分別理解為“美德”(Tugend)或“道德”(Sittlichkeit)(9)Florian Marwede,Das h?chste Gut in Kants deontologischer Ethik,Berlin/Boston:de Gruyter,2018,S. 115.,這在《實(shí)踐理性批判》有關(guān)至善的部分不難找到印證,也沒有太多理解上的困難,在此不多討論。相反,至善概念中“福”的要素有較多的敏感性和爭議,盡管康德其實(shí)明確表明這個(gè)“福”無非就是作為人之感性欲求對象的幸福,即人的塵世生活的滿足。康德強(qiáng)調(diào),至善所包含的“德”和“福”是“兩個(gè)在種類上完全不同的要素”(KpV 5:112)。他因此批評伊比鳩魯派和斯多亞派的思想,認(rèn)為前者把德視為實(shí)現(xiàn)福的手段,后者主張德即是福,兩者其實(shí)都否定了德和福是兩種不同的要素(KpV 5:111-112)。康德尤其對斯多亞學(xué)派的主張做了嚴(yán)厲批評,認(rèn)為他們“根本不想讓至善的第二個(gè)成分,亦即幸福,被視為人的欲求能力的一個(gè)特殊對象”。
他們的智者(指斯多亞派的智者,筆者注)宛如一個(gè)意識(shí)到自己人格的卓越性的神祗一般獨(dú)立于自然(在他的滿意方面),因?yàn)樗麄冸m然使這位智者遭受不幸,但卻使他不屈從于這些不幸(同時(shí)也把他表現(xiàn)為脫離了惡的),這樣就實(shí)際上刪除了至善的第二個(gè)要素,亦即自身的幸福,因?yàn)樗麄儼堰@一要素僅僅設(shè)定在行動(dòng)和對自己人格價(jià)值的滿足中,從而將它包括在道德思維方式的意識(shí)中,但在這里,他們通過自己的本性的聲音就已經(jīng)能夠充分地被駁倒了。(KpV 5:127)
這個(gè)“福”之所以帶有敏感性,是因?yàn)樵诳档碌赖抡軐W(xué)的語境中,引入“幸福”作為至善的不可刪除的組成要素,這很容易遭致各種批評。康德在其道德哲學(xué)的不同著作中反復(fù)強(qiáng)調(diào)道德形而上學(xué)的必要性,排除作為經(jīng)驗(yàn)性概念的幸福在道德奠基中的地位。在他看來,幸福是理性存在者現(xiàn)實(shí)的目的,“作為促進(jìn)幸福的手段”的行動(dòng)要求只是“機(jī)智的建議”,是實(shí)然的假言命令式,而非道德的定言命令式。為此,叔本華和黑格爾曾批評康德在引入至善的理念時(shí)顯得自相矛盾或不純粹,因?yàn)檫@雖然可以調(diào)和其形式主義倫理學(xué)和幸福論倫理學(xué)的緊張關(guān)系,但也會(huì)威脅其倫理學(xué)的自律道德基礎(chǔ),使其陷入他律道德。當(dāng)代的艾倫·伍德(Allen W. Wood)認(rèn)為康德的至善的思想包含了目的論的考慮(10)Allen W. Wood,Kant’s Moral Religion,Ithaca and 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0,pp. 69-99;Kant’s Ethical Thought,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國內(nèi)學(xué)者如孫小玲和張會(huì)永也在相關(guān)文章中指出其中有后果論的思想(11)參見孫小玲:《康德倫理學(xué)中義務(wù)與目的之貫通》,《哲學(xué)研究》2021年第9期;張會(huì)永:《論一種康德式的至善后果主義》,《哲學(xué)研究》2018年第6期。,雖然他們對此的評論有所不同,但在對把至善理解為一種目的這一點(diǎn)上基本一致。
但康德對道德形而上學(xué)的堅(jiān)持使他根本無意與幸福論扯上任何曖昧關(guān)系,他也一直對此保持足夠的警惕。即便是在其晚年的《道德形而上學(xué)》中,我們還能看到這樣鮮明的表態(tài):“如果幸福(幸福原則)取代自由(內(nèi)在立法的自由原則)被確立為原則,其后果便是一切道德的安樂死。”(MS 6:378)因此,我們對德福一致的理念不能作這樣的理解,好像幸福被作為道德的規(guī)定根據(jù)而被納入到康德的思想中。米歇爾·阿爾布雷希特(Michael Albrecht)和蘇珊娜·韋佩爾(Susanne Weiper)等德國學(xué)者在駁斥上述他律嫌疑時(shí),都強(qiáng)調(diào)康德在《實(shí)踐理性批判》中把至善視為純粹實(shí)踐理性或純粹意志的完備對象而非規(guī)定根據(jù)。他們指出,康德在“純粹實(shí)踐理性的辯證論”中提出至善理念,是作為對純粹實(shí)踐理性的對象問題的回答,這不同于其在“純粹實(shí)踐理性的分析論”對純粹意志的規(guī)定根據(jù)問題的回答。(12)Michael Albrecht,Kants Antinomie der praktischen Vernunft,Hildesheim u.a.:Georg Olms,1978,S.58ff;Susanne Weiper,Triebfeder und h?chstes Gut:Untersuchung zum Problem der sittlichen Motivation bei Kant,Schopenhauer und Scheler (Epistemata,Würzburger wissenschaftliche Schriften,Reihe Philosophie,Bd. 275),Würzburg:K?nigshausen &Neumann,2000,S. 57.盡管至善何以成為純粹意志的完備對象還需要進(jìn)一步的說明,但可以明確的是,純粹意志之規(guī)定根據(jù)問題和純粹意志的對象問題是兩個(gè)不同的問題,對它們的處理在康德這里是兩個(gè)步驟的工作,后者在前者的基礎(chǔ)上展開,前者確立了道德法則(這是“德福一致”之“德”的依據(jù)),后者得出至善的理念(德福一致)。這意味著,道德法則是“使至善和至善的造就或者促成成為自己的客體的根據(jù)”(KpV 5:109)。這一點(diǎn)非常重要,康德說“在此即使最小的誤解都會(huì)歪曲意向”,并特地提醒我們至善作為純粹意志的完備對象的提出,并非“在道德法則之前把某個(gè)客體以一種善的名義假定為意志的規(guī)定根據(jù),然后從它派生出至上的實(shí)踐原則,在這種情況下,這種道德原則任何時(shí)候都會(huì)帶來他律,并排斥道德原則”(KpV 5:109)。
因此,在至善的理念中,“德”和“福”不是作為兩個(gè)并列的要素被納入其中,“德”是“第一個(gè)條件”,“福”是“第二個(gè)要素”,兩者之間是一種“隸屬關(guān)系”。(KpV 5:119)“德”是“配享幸福的條件”,“福”以“德”為前提,是“與對義務(wù)的那種遵循相適應(yīng)的幸福”(Religion6:5)。在德福一致的主張中,“福”“并非獨(dú)自就絕對善并在一切考慮中都是善的東西,而是在任何時(shí)候都以道德上的合乎法則的行為為前提條件” (KpV 5:111)。幸福在此完全不是幸福論或目的論倫理學(xué)中確立起來的那種應(yīng)然的目的,這種目的是道德的直接根據(jù);幸福或?qū)π腋5淖非笤诖宋銓幷f是作為一種實(shí)然的要素出現(xiàn),這種事實(shí)要素構(gòu)成道德行動(dòng)的限制要素。德福一致表達(dá)的是合乎道德地追求幸福的要求,以及把幸福分配給有德之人的要求,如果說前者主要是對個(gè)人德性的要求,那么后者則包括對社會(huì)公正的要求,但這都意味著至善不是作為一個(gè)目的被引入康德的道德哲學(xué)之中,它表達(dá)的還是規(guī)范性的要求。如此解讀在康德有關(guān)至善與上帝理念的論述中,以及在其至善的論證思路中,都能得到進(jìn)一步的印證。
(二)至善與上帝的理念
康德在提出德福一致的理念之后,顯然需要進(jìn)一步探討如何實(shí)現(xiàn)至善。不可否認(rèn),在此問題上,康德的思想在不同著作中有一些矛盾和搖擺。在《純粹理性批判》和《實(shí)踐理性批判》等著作中,康德指出至善的理念需要預(yù)設(shè)靈魂不滅和上帝存在:前者是實(shí)現(xiàn)德之完善的條件,因?yàn)榈轮晟埔粋€(gè)是無止境的進(jìn)步過程,這“惟有預(yù)設(shè)同一個(gè)理性存在者的一種無限綿延的實(shí)存和人格性(人們把這稱為靈魂的不死)才是可能的”(KpV 5:122);后者是實(shí)現(xiàn)德福匹配的條件,“惟有假定自然的一個(gè)擁有與道德意向相符合的因果性的至上原因,塵世中的至善才是可能的”(KpV 5:125)。這有濃厚的宗教和神學(xué)的色彩,容易給人一種印象,好像康德雖然在至善思想中務(wù)實(shí)地納入了對道德行動(dòng)之后果的思考,但最終又將之交給來生和仁慈的上帝。這似乎是一種與其啟蒙思想和理性精神相悖的消極做法。(13)Susanne Weiper,Triebfeder und h?chstes Gut:Untersuchung zum Problem der sittlichen Motivation bei Kant,Schopenhauer und Scheler,S. 96ff.此外,如佐布李斯特(Marc Zobrist)所指出的,康德對德作為至善的“至上條件”的強(qiáng)調(diào),以及對具有神圣意味的永福(Seligkeit)概念的闡發(fā),也容易擠壓至善理念中福的維度,最終使得至善的思想局限于如何修德以配享幸福的問題,從而退回到其所批評的斯多亞主義的立場。(14)See Marc Zobrist,Kants Lehre vom h?chsten Gut und die Frage moralischer Motivation,Kant-Studien 99(3),2008,S. 305ff.但如果回到《宗教論文集》和《道德形而上學(xué)》等論著,我們還是可以獲得一個(gè)在其自律道德思想中較為自洽的理解。
在《宗教論文集》的第一版導(dǎo)言中,在引出那個(gè)把我們的“義務(wù)”以及“與對義務(wù)的那種遵循相適應(yīng)的幸福”“結(jié)合在一起并包含在自身之中”的“塵世上的至善理念”之后,康德馬上指出,“為使這種至善可能,我們必須假定一個(gè)更高的、道德的、最圣潔的和全能的存在者,惟有這個(gè)存在者才能把至善的兩種要素結(jié)合起來”。(Religion6:5)不難發(fā)現(xiàn),與之前的著作相比,這里只提到“一個(gè)更高的、道德的、最圣潔的和全能的存在者”(即上帝),而沒有提靈魂不滅這一前提。此外,在《宗教論文集》中,康德在處理道德完善性問題時(shí)不再執(zhí)著于道德完善的最終實(shí)現(xiàn),而是更關(guān)注在難以達(dá)到真正完善的有限生命中,如何通過不斷向善的努力得以配享幸福。針對這一問題關(guān)切,上帝作為“知人心的審判者”出場:“一個(gè)知人心的審判必須被設(shè)想為這樣的審判,它是從被告的普遍意念,而不是從這意念的顯象、從與法則相背離或者相一致的行動(dòng)作出的。”(Religion6:73)康德以此提示,即便達(dá)不到真正的道德完善,改惡向善的努力也足以表明善的意念,從而能夠合理地希望得到相應(yīng)的幸福。而到更晚出版的《道德形而上學(xué)》之《德性論的形而上學(xué)初始根據(jù)》(簡稱《德性論》)中,康德已經(jīng)不再提靈魂不滅的前提,他探討的是在完善性理念指引下的實(shí)踐要求,即促進(jìn)自己的完善和他人的幸福的德性義務(wù)。
康德之所以說上帝是一位知人心者,是因?yàn)樯系凼亲鳛槭怪辽频靡钥赡艿臈l件被設(shè)想和引入其思想之中的。因此,這個(gè)上帝是人的一個(gè)理念,而非外在的權(quán)威,上帝“(創(chuàng)世的)終極目的也就是那種同時(shí)能夠并且應(yīng)該是人的終極目的的東西”(Religion6:6)。這個(gè)上帝之所以是“更高的、道德的、最圣潔的和全能的”,顯然是基于對現(xiàn)實(shí)中造成德福不一的各種原因的考慮,比如缺乏公正的環(huán)境(好人得不到好報(bào))、缺乏對行動(dòng)后果的認(rèn)知(好心辦壞事)或純粹的壞運(yùn)氣。對上帝的描畫就是對德福一致之前提條件的構(gòu)想。如果說“更高的、道德的、最圣潔的”是針對人的德性和制度公正的要求,那么“全能的”就進(jìn)一步涉及對行為之可能后果的認(rèn)知等方面的要求,這與后來韋伯和阿佩爾對于現(xiàn)實(shí)世界之缺陷的考慮完全一致,甚至約納斯責(zé)任倫理所主張的獲取知識(shí)的義務(wù)(15)Hans Jonas,Das Prinzip Verantwortung,S. 28.也已經(jīng)包含于其中。康德因此指出,“上帝存在”這個(gè)命題是從道德中產(chǎn)生的,是在實(shí)踐關(guān)系中被假定的,它不是一個(gè)理論命題,而是一個(gè)實(shí)踐命題。可見,“上帝存在”這一命題的提出,其意圖不在于在理論上要求承認(rèn)有一個(gè)超越的存在者,而是表達(dá)實(shí)踐上的希望和要求,希望至善實(shí)現(xiàn)并要求努力促使其實(shí)現(xiàn),即“每個(gè)人都應(yīng)該使塵世上的至善成為自己的終極目的”(Religion6:6)。
需要注意的是,這一表述雖然出現(xiàn)了“目的”概念,但這個(gè)“終極目的”并非古希臘哲學(xué)中那種處于目的金字塔頂尖的最高目的(人們是為了欲求這個(gè)最高目的而欲求別的目的),而是 “包含著其他所有目的的不可避免的、同時(shí)又是充足的條件的目的”(Religion6:6)。也就是說,至善之所以應(yīng)當(dāng)成為每個(gè)人的“終極目的”,是因?yàn)樗鳛楸WC人們所有其他目的得以實(shí)現(xiàn)的“不可避免的、同時(shí)又是充足的條件”而被純?nèi)坏睦硇运M蛞蟆K磉_(dá)的依然是規(guī)范性的要求,它之所以可被稱為目的,是因?yàn)檫@種規(guī)范性要求不只是消極的、限制性的要求,而是有著積極的內(nèi)容。這啟發(fā)我們回過來理解前面提到的至善作為有理性能力的有限者的“完整和圓滿的善”,康德在其他語境下還有“純粹實(shí)踐理性對象之無條件總體”或“純粹意志的全部客體”之說(KpV 5:108,109),他的意思顯然不是說至善囊括了純粹理性所有的對象,而是說至善是使所有其他的對象得以可能的條件。
至此,至善的內(nèi)涵及其所包含的道德要求就更加清楚了。需要指出的是,康德以至善理念作為道德向宗教過渡的思想環(huán)節(jié),這充分表明其宗教思想的理性特質(zhì):它無關(guān)乎傳統(tǒng)意義上的信仰,而關(guān)乎希望,是對康德的“我能夠希望什么的問題”的回答。在此意義上,《宗教論文集》的文章可以被理解為借助傳統(tǒng)宗教的概念和故事闡發(fā)其理性宗教思想的嘗試:善的原則與惡的原則的斗爭涉及個(gè)體道德完善的問題,倫理共同體的思想則包含了對制度的思考,這些都是作為使德福一致能為可能的條件來討論的。如此則康德的宗教思想完全符合啟蒙和理性主義精神,他并未將至善的實(shí)現(xiàn)寄托于來世,寄托于那個(gè)作為信仰對象的上帝,而是以至善為指導(dǎo)性理念提出諸如個(gè)體完善和制度建設(shè)等積極的和理性的道德要求。
三、至善理念的論證
結(jié)合至善的內(nèi)涵及其所包含的道德要求,其實(shí)已經(jīng)能夠初步體會(huì)其責(zé)任倫理的意味,但為了更清晰地呈現(xiàn)其責(zé)任倫理的思想,有必要進(jìn)一步考察康德如何在其思想中引入至善的理念。這涉及至善的論證問題:至善何以成為純粹意志的完備對象?或者說,為何每個(gè)人都應(yīng)當(dāng)使塵世上的至善成為自己的終極目的?康德回答這些問題的思路對于把握至善的思想顯然有重要意義。盡管這正是至善思想之所以困難和充滿爭議的原因所在,康德似乎并未專門對此進(jìn)行系統(tǒng)的論證,甚至說這些結(jié)論的得出只是基于一種“洞察”(Religion6:6)。但基于康德在《實(shí)踐理性批判》和《宗教論文集》等文獻(xiàn)的相關(guān)論述,我們還是可以試著重構(gòu)其基本論證思路。
(一)兩步論證法
在《實(shí)踐理性批判》中,德福一致的理念出現(xiàn)于“純粹實(shí)踐理性的辯證論”部分,康德強(qiáng)調(diào)這部分是在“純粹實(shí)踐理性的分析論”的基礎(chǔ)上展開的,這表明康德對至善的論證是通過兩個(gè)步驟才最終完成。按照康德的說法,“分析論”包括純粹實(shí)踐理性的邏輯論和感性論(KpV 5:90),旨在分析闡明純粹實(shí)踐理性的原則、概念以及敬重作為道德情感的先天可能性,最終確立了道德法則作為純粹意志的規(guī)定根據(jù)所具有的純粹性和約束力。“辯證論”則轉(zhuǎn)向純粹理性在實(shí)踐中的應(yīng)用,追問純粹實(shí)踐理性的對象,并確立至善作為“純粹實(shí)踐理性對象的無條件總體”或“純粹意志的全部客體”(KpV 5:108,109)。不難發(fā)現(xiàn),從“分析論”到“辯證論”的推進(jìn),有一個(gè)視角或立足點(diǎn)的變化或擴(kuò)展:前者基于一個(gè)抽象的、理性的視角,它雖然預(yù)設(shè)了作為道德行動(dòng)者的人的感性方面(否則就談不上道德),但懸置了人的感性有限性問題,重在表明道德的純粹性和約束力;后者轉(zhuǎn)向理性在實(shí)踐中的應(yīng)用,立足于作為有限的理性存在者的人,需要一種理性思考兼顧感性需求的雙重視角。
之所以在純粹實(shí)踐理性的應(yīng)用中需要進(jìn)一步追問純粹理性的對象,從行動(dòng)理論的角度看,在于意志僅有形式的規(guī)定尚不能形成行動(dòng)。康德曾指出:“倘若不與目的發(fā)生任何關(guān)系,人就根本不能做出任何意志規(guī)定。”(Religion6:4)而道德的行動(dòng)沒有先行的目的,只能通過設(shè)想可能的結(jié)果確定其目的。這在純粹實(shí)踐理性的應(yīng)用中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因?yàn)樽鳛榈赖滦袆?dòng)者的人是有限的理性存在者,人的自然屬性決定了他總是以追求某種幸福為目的,也決定了他需要在意道德行動(dòng)的后果。
雖然就道德來說,為了正當(dāng)?shù)匦袆?dòng)并不需要一個(gè)目的,相反,從根本上來說,包含著運(yùn)用自由的形式條件的法則對它來說就足夠了。但是,從道德中畢竟產(chǎn)生出一種目的,因?yàn)閷τ诶硇远裕卮稹皬奈覀兊倪@種正當(dāng)行為中究竟產(chǎn)生出什么”這個(gè)問題,以及即使正當(dāng)行為會(huì)產(chǎn)生什么結(jié)果并不完全由我們掌握,但我們能夠以什么作為一個(gè)目的來調(diào)整自己的所作所為,以便至少與它協(xié)調(diào)一致,這些都不可能是無關(guān)要緊的。(Religion6:5)
這里說的“協(xié)調(diào)一致”也就是人的自然本性與道德本性的協(xié)調(diào)一致。結(jié)合上文對德福一致之可能性的分析可以得出,追求兩者協(xié)調(diào)一致的重點(diǎn)在于克服德福不一可能帶來的兩者之間的沖突,或者更確切地說,在于克服人的自然有限性方面的限制對道德行動(dòng)的阻礙。按照康德的理解,盡管法則具有絕對的必要性,并且對法則的敬重本身就是一種強(qiáng)有力的道德情感(MS 6:408),但對于有限理性存在者而言,德福不一無疑會(huì)對敬重情感的自然生發(fā)構(gòu)成障礙。正是基于這樣的考慮,理性必須把德福一致規(guī)定為“終極目的”。這也是佐布李斯特和韋佩爾等當(dāng)代學(xué)者把康德的至善思想與動(dòng)機(jī)問題聯(lián)系起來的原因,盡管他們對至善思想的具體理解和評價(jià)有所不同,但都看到至善的理念是為克服道德動(dòng)機(jī)的可能障礙而提出的。(16)Marc Zobrist,Kants Lehre vom h?chsten Gut und die Frage moralischer Motivation,S. 285-286;Susanne Weiper,Triebfeder und h?chstes Gut:Untersuchung zum Problem der sittlichen Motivation bei Kant,Schopenhauer und Scheler,S. 56ff.
至此,至善的思想經(jīng)由分析論到辯證論兩個(gè)步驟的論證思路就很清楚了。需要強(qiáng)調(diào)的是,辯證論將人的自然本性納入考慮,并不意味著轉(zhuǎn)而直接出于偏好而行動(dòng),而是據(jù)此提示:純?nèi)坏睦硇员囟ㄐ枰罢疹櫋钡饺说男枨螅瓜鄳?yīng)行動(dòng)的結(jié)果成為人所“喜愛的東西”(Religion6:6)。這也是辯證論基于分析論之說所意謂的。因此,盡管我們出于修辭的考慮稱“辯證論”的視角為“雙重視角”,但這種雙重視角并非理想視角和現(xiàn)實(shí)視角或理性與感性的相互摻合或妥協(xié),而是在理性基礎(chǔ)上對感性的接納和規(guī)范。并且其中對人的感性方面的考慮只是形式性的,尚未涉及人的具體感性規(guī)定性,并非經(jīng)驗(yàn)意義上對感性的把握,而只是對人的自然屬性的確認(rèn),或者說對人的感性先天性的確認(rèn)。
對照阿佩爾在其對話倫理學(xué)的B部分論證中提出的理想交往共同體和現(xiàn)實(shí)交往共同體之雙重先天性之說(17)[德]卡爾·奧托·阿佩爾:《哲學(xué)的改造》,第335-336頁。,康德這里可以說包含了“理性感性雙重先天性”的思想。如此,康德才有理由說至善是純粹實(shí)踐理性的完備對象,也才有理由說“‘要使塵世上的至善成為你的終極目的’這一命題,是一個(gè)先天綜合命題”。(Religion6:6)據(jù)此,我們就能斷言,康德論證至善思想的思路與阿佩爾對話-責(zé)任倫理學(xué)B部分論證思路基本上是一致的。“分析論”和“辯證論”就是康德道德哲學(xué)的A、B兩部分,前者基于“理性先天性”闡明了純粹實(shí)踐理性的形式規(guī)定根據(jù),得出相互平等和尊重的基本道德規(guī)范,后者基于“理性和感性雙重先天性”闡明了作為純粹實(shí)踐理性之完備對象的至善理念,并由此得出“要使塵世上的至善成為你的終極目的”的道德要求。
康德在《實(shí)踐理性批判》中將至善視為“理性的興趣”或“純粹理性的實(shí)踐興趣”,并稱這是“理性的應(yīng)用在某個(gè)別的、亦即實(shí)踐的意圖中的擴(kuò)展,這與理性那本身在于限制思辨的違禁的興趣是根本不相悖的”(KpV 5:121)。有評論者以康德也將至善視為純粹意志的規(guī)定根據(jù)(KpV 5:109-110)為由,指責(zé)康德之混亂或自相矛盾(18)Marc Zobrist,Kants Lehre vom h?chsten Gut und die Frage moralischer Motivation,Kant-Studien,S. 291ff.,因?yàn)樗罢f過法則是純粹意志的規(guī)定根據(jù),而至善是其完備對象。但基于上文分析過的至善理念中“德”和“福”兩要素的隸屬關(guān)系,以及這里所說的“擴(kuò)展”,這個(gè)所謂的混亂或矛盾并非不可消解。至善的理念是在分析論中建構(gòu)的道德法則的基礎(chǔ)上確立起來,其確立擴(kuò)展了道德法則的內(nèi)涵,就此而言可以說是純粹意志的規(guī)定根據(jù)。
這一“擴(kuò)展”是康德道德哲學(xué)中的一個(gè)重要環(huán)節(jié),康德倫理學(xué)之所以被簡單認(rèn)定為意念倫理或原則倫理,與這一環(huán)節(jié)沒有得到充分重視不無關(guān)系。這一擴(kuò)展涉及對人的感性有限性的考慮,旨在協(xié)調(diào)理性和感性的關(guān)系。這充分表明康德思想的落腳點(diǎn)不是任何抽象的理性存在者,而是“有理性能力的有限者”或“有限的理性存在者”,其倫理學(xué)決不是韋伯所批評的“圣人的倫理”,而是如艾塞爾(Andrea Marlen Esser)所說的“有限者的倫理”(19)Andrea Marlen Esser,Eine Ethik für die Endliche. Kants Tugendlehre in der Gegenwart,Stuttgart:frommann-holzboog,2004,S. 17.。從“分析論”到“感性論”兩個(gè)步驟的論證,不僅彰顯了理性的權(quán)威,而且顧及感性的障礙和限制。由此擴(kuò)展出來的至善理念,甚至就其具體主張而言,若不考慮一些具體的細(xì)節(jié)和側(cè)重,與阿佩爾的責(zé)任倫理有很多一致之處:相互平等和尊重的要求與阿佩爾的平等權(quán)利原則基本一致,而至善理念所包含的德性完善和制度完善的要求也與阿佩爾B部分的進(jìn)步原則有重合之處。康德的倫理學(xué),無論在問題意識(shí)、解決思路甚至在觀點(diǎn)上,都與阿佩爾的責(zé)任倫理有著驚人的一致。(20)當(dāng)然這不是說他們的觀點(diǎn)完全一致,兩者之間還存在一些不同,比如阿佩爾更側(cè)重于制度建設(shè),而康德則發(fā)展出較為體系化的德性論思想,毋寧說,這是不同時(shí)代中哲學(xué)家的不同側(cè)重。康德的法權(quán)論對應(yīng)于阿佩爾的制度建設(shè)主張,而阿佩爾雖然沒有強(qiáng)調(diào)美德培養(yǎng),但這不意味著其倫理中不能生發(fā)出德性論的維度。(參見羅亞玲:《平等權(quán)利和共同責(zé)任——阿佩爾對話倫理學(xué)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77頁。)
(二)對一個(gè)可能的質(zhì)疑的回應(yīng)
以上重構(gòu)的兩步論證法使得我們較為便利地把康德的思路與阿佩爾關(guān)聯(lián)起來,從而發(fā)現(xiàn)他們思路和觀點(diǎn)的相似性。但佐布李斯特和馬韋德等學(xué)者在重構(gòu)至善思想的論證思路時(shí),都不曾特別強(qiáng)調(diào)這種兩步論證法:佐布李斯特認(rèn)為康德在論證中預(yù)設(shè)了一個(gè)理性的視角,而馬韋德則指出康德是通過一個(gè)思想實(shí)驗(yàn)完成至善理念的建構(gòu)。這是否會(huì)成為對本文的一個(gè)質(zhì)疑?
佐布李斯特和馬韋德的判斷都基于康德宗教論文集中的這段文字:
假定有一個(gè)人,他尊重道德法則并且思考這樣的問題(這是他很難避免的),即如果他能夠的話,他會(huì)在實(shí)踐理性的指導(dǎo)下為自己創(chuàng)造一個(gè)什么樣的世界,而且他還要把自己作為一個(gè)成員置入這個(gè)世界,那么,他就會(huì)不僅恰好像至善的道德理念在選擇純?nèi)宦爲(wèi){至善時(shí)所造成的那樣來選擇世界,而且還會(huì)要求確實(shí)存在一個(gè)世界,因?yàn)榈赖路▌t要求實(shí)現(xiàn)通過我們而可能的至善,即使他按照這一個(gè)理念發(fā)現(xiàn)自己有為了自己的人格而喪失幸福的危險(xiǎn),因?yàn)樗赡軙?huì)不能符合以理性為條件的幸福。因此,他會(huì)感到這一判斷是完全公允的,如同由一位局外人作出的,但同時(shí)又會(huì)感到理性強(qiáng)迫他承認(rèn)這一判斷是他自己的判斷。(Religion6:5-6)
康德在此假定了一個(gè)人,這個(gè)人顯然是一個(gè)真實(shí)的、可能偏私的有限理性存在者,他在思考他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應(yīng)當(dāng)是怎樣的世界。這就是馬韋德說的思想實(shí)驗(yàn)。按照康德的分析,這個(gè)人必定會(huì)設(shè)想一個(gè)能夠?qū)崿F(xiàn)至善的世界并且希望這樣的世界能夠存在,這不是因?yàn)樗ㄟ^計(jì)算發(fā)現(xiàn)這樣的世界有利于他本人的生存(考慮其現(xiàn)實(shí)情況,結(jié)論未必如此),而是“理性強(qiáng)迫他”做出這樣的判斷。也就是說,理性強(qiáng)迫他懸置他本人的德性和幸福的可能狀態(tài),“像一個(gè)公允的局外人一樣做出判斷”。這也就是佐布李斯特所說的理性的視角。
但這一思想實(shí)驗(yàn)何以適合用作對至善思想的論證?康德如何能夠合理地預(yù)設(shè)一個(gè)理性的視角?康德在此必定考慮到人的感性和理性雙重屬性,并預(yù)設(shè)了理性的權(quán)威和約束力,這主要對應(yīng)于兩步論證法中的第二步工作。正如佐布李斯特批評康德沒有充分論證其理性的視角,這一工作孤立地看是有問題的,只有將之置于兩步論證的架構(gòu)中,其中有關(guān)理性權(quán)威和約束力的約束才不至于顯得突兀。
有意思的是,阿佩爾也有類似的淡化兩個(gè)步驟的論證策略。在駁斥哈貝馬斯將交往行動(dòng)和策略性行動(dòng)作為兩種不同的行動(dòng)類型相提并論的做法時(shí),阿佩爾強(qiáng)調(diào),一個(gè)現(xiàn)實(shí)的行動(dòng)者雖然事實(shí)上可能采取策略性行動(dòng),但當(dāng)其需要針對其他相關(guān)者為自己的訴求辯護(hù)時(shí),即當(dāng)他在面臨合理性檢驗(yàn)的時(shí)候,他必須——用康德的話就是“理性強(qiáng)迫他”——作為一個(gè)對話者進(jìn)行自我辯護(hù),必須超越自我中心的立場考慮所有相關(guān)者的利益。(21)Karl-Otto Apel,Auseinandersetzungen in Erprobung des transzendentalpragmatischen Ansatzes,F(xiàn)rankfurt a. M.:Suhrkamp,1998,S. 712ff.這里同樣包含一個(gè)預(yù)設(shè),即對交往行動(dòng)之基礎(chǔ)性地位或交往理性的預(yù)設(shè),而這一預(yù)設(shè)同樣需要置于阿佩爾對話-責(zé)任倫理學(xué)的兩步論證之中才能得到充分的解釋。
因此,佐布李斯特和馬韋德重構(gòu)出來的至善思想論證方式,不足以作為對兩步論證法的反駁,相反,只有置于兩步重構(gòu)法的大框架之中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釋。當(dāng)然可以進(jìn)一步質(zhì)疑兩步論證法,這將是一個(gè)更大的課題。但無論是在康德這里還是在阿佩爾那里,兩步論證的策略都充分表明了其義務(wù)論倫理學(xué)的責(zé)任倫理意識(shí)。
四、小 結(jié)
以上我們首先結(jié)合責(zé)任倫理的發(fā)展脈絡(luò)分析得出:責(zé)任倫理作為一種整合義務(wù)論倫理學(xué)和后果論倫理學(xué)的嘗試,其要旨在于既承認(rèn)道德原則之普遍有效性,又主張?jiān)谠瓌t應(yīng)用中納入對行動(dòng)后果的考慮。建構(gòu)一門獨(dú)立的責(zé)任倫理需要通過兩個(gè)步驟,首先從一個(gè)抽象的理性的視角出發(fā)確立義務(wù)論倫理學(xué)的一些基本道德原則,然后結(jié)合原則應(yīng)用的現(xiàn)實(shí)處境,將之前確立的基本道德原則視為指導(dǎo)性理念以證成策略性的道德原則作為補(bǔ)充。而通過對至善所包含的德福一致理念和上帝理念的分析,以及對至善思想的論證思路的梳理,尤其是通過將康德的論證思路與阿佩爾對話責(zé)任倫理的論證思路進(jìn)行對照,我們發(fā)現(xiàn):康德的至善思想,無論就其基本主張還是就其論證思路而言,都與阿佩爾對話倫理學(xué)B部分闡發(fā)的責(zé)任思想有很多一致之處。這些一致體現(xiàn)了康德道德哲學(xué)中的責(zé)任倫理思想,盡管他當(dāng)時(shí)尚未使用責(zé)任倫理的概念。
其實(shí),如果把康德的道德哲學(xué)體系與阿佩爾的對話責(zé)任倫理學(xué)體系做進(jìn)一步的對照,甚至還能進(jìn)一步得出,至善思想可以說就是康德道德哲學(xué)中的B部分。如此,我們還能更為鮮明地呈現(xiàn)康德道德哲學(xué)的責(zé)任倫理之維以及至善思想在其中的關(guān)鍵地位。當(dāng)然,這需要基于對至善在康德道德哲學(xué)中的地位的考察,本文限于篇幅暫且打住。無論如何,通過發(fā)掘康德道德哲學(xué)中的責(zé)任倫理思想,我們希望能夠回應(yīng)針對康德的所謂信念倫理或嚴(yán)格主義的批評,為重新理解康德道德哲學(xué)以及其當(dāng)代意義提供新的視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