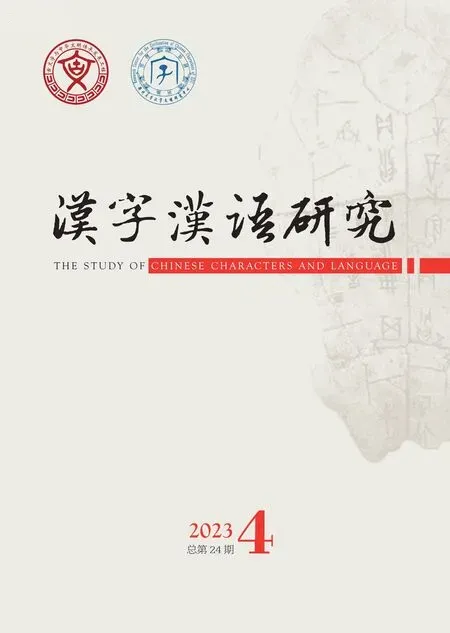域外漢字異體字發展的趨勢與特征*
——以日本漢文古辭書《倭名類聚抄》為例
劉 寒 青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中國語言文學學院)
提 要 本文站在漢字發展史的視角下,將域外漢字異體字的發展情況納入整個漢字系統的研究當中。以日本漢文古辭書《倭名類聚抄》為例,窮盡性整理《倭名類聚抄》不同時代抄本中異體字的情況,并且參照同時期其他日本漢文古辭書。在此基礎上,本文提出了“日存變體”這一概念,并總結出域外漢字異體字在發展中呈現出的幾種趨勢與特征:1.繼承性和保守性;2.字形變異程度加劇;3.類化原則影響加深;4.增補漢字異體字發展材料。
域外漢字所呈現的漢字使用與發展情況,是漢字系統龐大根系伸向域外的一根枝條,它根植于中國本土的漢字發展情況,又產生新的變化,具備新的特征。日本漢字是域外漢字中重要的一脈分支,從傳入日本開始,漢字便在日本生根發芽,漢字作為外來文化進入日本,經歷了“接受—使用—改造—融合”這樣逐漸深化的過程。本文站在漢字發展史的視角,將漢字的域外發展情況納入整個漢字系統的研究當中,分析漢字在域外漢文典籍中表現出的發展趨勢和特征。而研究日藏漢文典籍中域外漢字異體字的使用和發展情況,是了解域外漢字發展的必經之路。
《倭名類聚抄》是日本漢學家源順于日本平安時代承平初年編纂的百科全書式漢和辭書,通篇以漢語寫成,是日本現存最古老的意義分類辭書。流傳至今的《倭名類聚抄》抄本種類豐富,從平安時代到明治時代都有抄本傳世。《倭名類聚抄》版本系統中最古的兩個抄本是高山寺本①高山寺本是二十卷本系統中最古老的抄本,藏于日本天立圖書館。該本為殘本,現存五卷,即卷六至卷十。和真福寺本②真福寺本是十卷本系統中抄寫年代最早的本子,藏于日本名古屋市大須寶生院。真福寺本殘損非常嚴重,只剩余卷一和卷二的部分內容,卷一為完整的一卷,卷二為殘卷。,高山寺本為平安時代抄本,大致相當于我國晚唐五代時期;真福寺本為鐮倉時代抄本,大致相當于我國的南宋時期。伊勢十卷本、二十卷本《倭名類聚抄》的抄寫年代均為室町初期,相當于我國的元朝初年,是除了高山寺本和真福寺本之外,年代較早的抄本,天正本則為室町中期的抄本。
雖然《倭名類聚抄》的不同抄本之間存在著一定的時間跨度,但其中所體現出的文字問題卻是相互關聯的。遠離了漢字使用的本土環境,域外漢字的發展狀況并不與中國本土的漢字發展同步,其存在著四種鮮明的發展趨勢和特征。
1.繼承性和保守性
1.1 繼承性
《倭名類聚抄》各個抄本中使用的異體字,見于中國字書、韻書,或其他文字材料中的占了絕大部分。經過系統對比,《倭名類聚抄》抄本中的異體字與漢魏碑刻及敦煌寫卷中的字形有著極高的吻合率,尤其是敦煌寫卷。《倭名類聚抄》抄本中那些不常見于傳世字書、韻書中的異體字字形往往能在敦煌寫卷中找到對應關系。
《倭名類聚抄》抄本中異體字與漢魏碑刻及敦煌寫卷的字形吻合,不僅是一字一形的,更是在變異方式和變異類型上存在一致性。《倭名類聚抄》抄本中異構字義符和聲符的替換、增刪等都與敦煌寫卷中的異構字特征一致。例如,《倭名類聚抄》中異構字的聲符換用體現出西北方音的特點。如《倭名類聚抄》中的“院”常寫作“ ”,這種情況在敦煌寫卷中也較為常見。“ ”是“院”改換聲符的異構字,“院”字為云母,“宛”為影母,影母歸入喻母,與云母相諧,是唐五代西北方音中存在的現象。
相比異構字,異寫字的隨意性更強,因時代、書手的不同而形態各異,但在《倭名類聚抄》和敦煌寫卷中,不僅異構字有著相似的變形規律,異寫字的變異也呈現出較為一致的走向。
1.2 保守性
《倭名類聚抄》成書于日本平安時代承平初年,相當于中國的晚唐五代時期,這個階段《倭名類聚抄》中使用異體字的情況自然受到中國本土通行的異體字的影響,與敦煌寫卷和更早期的漢魏碑刻呈現出一致性。但就如同離開軀干的枝條無法繼續生長,隨著日本逐漸停止遣唐使的派遣,兩國之間交流逐漸滯緩,平安時期之后日本漢字的使用與發展情況逐漸顯現出保守性與滯后性。《倭名類聚抄》不同時代抄本中使用異體字的情況并不與同時期的中國本土的漢字發展情況直接相關。
因避諱而產生的異體字時代特征最為明顯。《倭名類聚抄》抄本中因遵循唐代避諱規則而導致的異體字十分常見。敦煌寫卷的唐代文獻中“世”字和一系列以“世”為構件的字如“牒”“葉”“棄”②“棄”字中的構件并非“世”字,但因中間的部分與“世”字相近,也常因避諱而改寫。等,常因唐太宗李世民而避諱改寫,宋張世南《游宦紀聞》卷九:“‘世’字因唐太宗諱世民,故今‘牒’‘葉’‘棄’皆去‘世’而從‘云’。”這樣的避諱規則同樣在《倭名類聚抄》抄本中發揮著作用,并且這種避諱字的書寫習慣并沒有隨著時代的前進而消失,室町早、中期(相當于我國的元朝早、中期)《倭名類聚抄》抄本中的“世”字,包括以“世”為構件的字依舊因循著和唐代一樣的避諱寫法。如“世”字的缺筆,《倭》卷八“久世”③久世,地名。地處美作鄉大庭郡。,其中“世”字天正本作“”。《倭》卷十三“葉椀”,其中“葉”字伊勢二十卷本作“”,天正本作“”。《倭》卷十三“牒”,伊勢二十卷本作“”,天正本作“”。除了避諱字之外,《倭名類聚抄》抄本中還有一些時代性非常鮮明的異體字。如鐮倉時代和室町時代初期的《倭名類聚抄》抄本中,武周新字依舊偶有使用,如“國”寫作“圀”等。
《倭名類聚抄》不同時代抄本中使用的異體字,見于中國字書、韻書,或漢魏碑刻及敦煌寫卷等文字材料中的占了絕大部分,這是受到日本平安時期漢字具有較高的社會地位和日本較為保守的文化傳統的影響,日本的漢字學習者和使用者會盡量維持漢字字形的原貌。所以《倭名類聚抄》在編纂和抄寫的過程中較為忠實地記錄和摹寫了中國文字材料中的異體字字形。然而包括日本漢字在內的域外漢字,因遠離漢字使用的本土環境,容易形成“孤島型”的封閉使用環境,從而使域外漢字的異體字發展具有保守性和滯后性。
2.字形變異程度加劇
除了繼承自中國文字材料中的異體字,《倭名類聚抄》抄本中還存在部分并不常見于中國的字書、韻書,或其他文字材料中的異體字。然而中國不僅傳世文字材料卷帙浩繁,出土文字材料的數量也在逐年增加,在實際考察中很難做到對自古至今所有的文字材料進行窮盡性、徹底的排查。所能依靠的是對各類文字編、異體字字典和數據庫進行檢索,對在上述范圍內依舊未檢索到的異體字,本文提出了“日存變體”這一概念。“日存變體”這一概念的提出,并非執著于討論這部分異體字是否產生于日本,而是突出這些異體字在中國本土異體字發展序列中的非典型性。
雖然稱之為“日存變體”,但它們依舊與中國文字材料中的異體字有著密切的聯系,可以說是一脈相承。很多“日存變體”類異體字是在中國文字材料中常見異體字的基礎上加深了變異的程度。“日存變體”中異寫字占絕大多數,這種現象說明在印刷時代之前,漢字規范的關注焦點更多地集中于構件層面,對于非漢語母語的學習者來說,他們在使用漢字時主要容易在筆畫層面發生書寫變異。例如:
《倭》卷六“綴喜”①綴喜,地名。地處山城鄉綴喜郡。兩見,其中“喜”字高山寺本皆作“”。《倭》卷八“久喜”②久喜,地名。地處長門鄉厚狹郡。,其中“喜”字高山寺本作“”。《說文·喜部》:“喜,樂也。從壴從口。”“”字為構件“壴”發生了筆畫上的變異。從《倭名類聚抄》中保留的“喜”字的其他異寫形體,我們能夠看到從“喜”到“”的筆畫變異過程,《倭名類聚抄》中“喜”亦常寫作“”,這個字形在漢魏碑刻和敦煌寫卷中也十分常見,如北魏《司馬王亮等造像記》“喜”作“”,北齊《居士諱道明墓志》“喜”作“”,甘博003 號《佛說觀佛三昧海經》中“喜”作“”,敦研016 號《自在王菩薩經》中“喜”作“”。在此基礎上,“”字中與“口”相接的短豎進一步拉長歪斜之后,變為一撇,導致整體字形的變異進一步加深,則有“”形。
《倭》卷十二“幗,婦人喪冠也”,其中“喪”字伊勢二十卷本作“”,天正本作“”。“”是“喪”字構件簡省和筆形變化形成的異體字,其字形的由來并非無跡可尋,《倭名類聚抄》中“喪”的形近字的異體變化形式為追溯“喪”字的異體字變化軌跡提供了充足的材料。如《倭名類聚抄》中“囊”多寫作“”,《倭》卷十二“袋,囊名”,其中“囊”字伊勢二十卷本作“”。“囊”字又寫作“”,《倭》卷十三“漉水囊”,其中“囊”字伊勢二十卷本作“”;《倭》卷八“美囊郡”,其中“囊”字高山寺本作“”。《說文·?部》:“囊,橐也。從?省,襄省聲。”《干祿字書·平聲》:“囊”,“上俗下正”。“囊”字上部構件本是“?”字之省,因書寫變異而成為“”,《倭名類聚抄》抄本中“”的短豎變為一撇,并發生相對位置變化,則成為“”,“”進一步減省構件“口”,則有“右”“古”等構件。“”與“喪”字上部構件同形,兩個同形構件一定程度上可以共享同樣的變異軌跡,受到類化原則的影響,《倭名類聚抄》中“喪”字亦常寫作“”。
【刄】
《倭》卷十三“叉,兩歧鐵[叉]②[ ]內文字為《倭名類聚抄》底本中有脫文,根據他本或上下文義補足,下同。,柄長六尺”,其中“叉”字伊勢二十卷本及天正本作“刄”。中國字書、韻書中未見載有“刄”“叉”二字之間的異體關系,《宋元以來俗字譜》收錄“刄”為“刃”之異體,與“叉”字無涉。漢魏碑刻及敦煌寫卷中也少見“叉”字寫作“刄”的實例。“叉”寫為“刄”是筆畫類型發生了變化,點畫變為一撇,《倭名類聚抄》抄本中“叉”寫作“刄”并非孤例,且抄本中其他以“叉”為構件的字也發生了同樣的變異,如靱(靫),(刈)等。《倭名類聚抄》抄本中“靱”為“靫”之異體,表示“箭袋”之義,與“韌”之異體“靱”為同形異字,音義無涉。《倭名類聚抄》中“”為“刈”之異體,《倭》卷十七“穧,刈[禾]把數”,其中“刈”字伊勢二十卷本作“”,天正本作“”;《倭》卷十五“刈”,其中“刈”字伊勢二十卷本、天正本皆作“”。通過上文例字,可以看出從“刈”到“”的演變過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以“”為中間過渡形體,“”字中的構件“刄”仍是從“叉”變異而來,刈——形成了“刈”完整的異體字發展軌跡。
《倭》卷十五“轆轤,圓轉木機也”,其中“圓”字伊勢二十卷本作“”,天正本作“”。“”字是構件記號化形成的異體字,中間一筆為“純符形體”,起到減省筆畫的作用,“純符形體是隸書之后漢字中出現的新的形體現象,是漢字不完全追求構形意圖及形義統一的情況下產生的。這種情況一直傳到了楷書中”(王貴元,2016:158)。“”字進一步發生變異,則成為日本常用的和制漢字“円”。造成純符形體出現的原因有兩個:一是字體之間的轉寫,包括篆隸轉寫和草楷轉寫兩種。篆隸轉寫發生在漢字發展的早期階段,草楷轉寫主要發生在楷書的定型期。二是趨于簡化的漢字字形發展趨勢,“書寫便捷”是貫穿整個漢字發展史的內在驅動因素,脫離象形階段之后,漢字發展中一直存在用筆畫簡單的記號構件替代原有字形中的聲符、義符的現象。使用記號構件來實現筆畫減省的情況,在域外漢字的發展過程中更是屢見不鮮。如,《倭名類聚抄》抄本中,除“圓”字外,仍在其他字形中有不同的構件被省寫為一撇或短豎,如(風)(面)、(同)等。
《倭》卷六“尾張鄉”,卷七“真張”①真張,地名,地處下野鄉山田郡。,卷十二“開張以臂屈伸”,卷十三“張華《博物志》”,其中“張”字高山寺本、伊勢二十卷本、天正本皆作“”。日本同時代較早期的漢文字書《新撰字鏡》中“張”字亦寫作“”。構件“”并非源自構件替換,而是“弓”的異寫形體。敦煌寫卷中作為構件的“弓”常寫作“”“”等形,在此基礎上進一步發生形變,變連筆為斷筆,即“”形。我們從《倭名類聚抄》抄本中“張”字其他的異體字書寫時留存的筆道也可以看出從“弓”到“”的發展軌跡,如(張)。除了“張”字外,《倭名類聚抄》抄本中其他從“弓”的字,也發生了一致的變異,如(引)、(弘)等字。變異后的“弓”與“方”形似,這就導致了在《倭名類聚抄》抄本中“方”和“弓”兩個構件的替換是雙向的,《倭名類聚抄》抄本中“方”在作構件時也常被寫作“弓”形,如《倭》卷二“《九族圖》”,其中“族”字伊勢二十卷本作“”,天正本作“”,中國文字材料中少見“族”字的此種寫法。
《倭》卷十五“以食誘魚鳥也”,其中“食”字伊勢二十卷本、天正本皆作“”。《倭》卷十六“宜食白飲”,其中“食”字伊勢二十卷本、天正本皆作“”。《說文·食部》:“食(),一米也。從皀亼聲。或說亼皀也。”《字匯·食部》:“,食本字從?,古香字,米之氣味也”。“”“”在漢魏碑刻和敦煌寫卷中均是較為常見的字形,如北魏《元懌墓志》“食”作“”;敦研032 號《四分律》“食”作“”。構件“厶”“匕”進一步發生書寫變異成為“八”,則形成了《倭名類聚抄》抄本中常見的“”字。
《倭名類聚抄》中很多從“埶”的字其中的“坴”都寫作“生”。《倭》卷八“安藝郡”,其中“藝”字高山寺本、天正本皆作“”。《倭》卷十三“勢似飛來”,其中“”字伊勢二十卷本、天正本皆作“”。《倭》卷十六“食熱膩物”,其中“熱”字伊勢二十卷本、天正本皆作“”。《倭》卷十四“褻器”,其中“褻”字伊勢二十卷本、天正本皆作“”。從“坴”到“生”并非構件的改換,而是受到類化原則的影響而導致的構件趨同。敦煌寫卷中“勢”字常寫作“”或“”,構件“坴”因筆畫減省變為“圭”,繼而因形近與“主”發生混同,“主”又因與“生”形近而發生形混,遂有《倭名類聚抄》中常見的“”形。
從上述字例可以看出,很多“日存變體”類異體字是在中國文字材料中常見的異體字的基礎上加深了異化的程度,如食——,囊——等。在漢字的原生使用環境中,很多字形如果過度變形,容易與其他漢字的異體字發生混淆,例如“”字很容易與“貪”的異寫字“”①字形見于《漢隸字源·平聲·覃韻·貪字》引《巴郡太守張納功德敘》,電子科技大學出版社,2017 年。相混淆。在漢字發展過程中,漢字構形系統的別異性原則會制約著漢字形體的過度異化,而當漢字作為外來文字進入其他國家的語言環境中時,這種制約性相對地被削弱了,導致部分異體字的變異程度進一步加劇,形成了本文所說的“日存變體”。
3.類化原則影響加深
類化原則是漢字發展過程中一直存在的,影響異體字的產生與發展的幾個原則之一。因類化原則而形成的異體字,通常都是受到形近字、前后字的影響,或者是受到使用語境的影響,增減或改換構件,與其他漢字字形趨于一致。部分類化字是不符合漢字構形規律的,是無理據的形體,所以這部分類化字具有臨時性和條件限定性,而受到漢字構形系統性和表意性的制約,漢字系統本身不容許存在大量的不符合其構形理據的類化字。
《倭名類聚抄》抄本中,類化原則同樣發揮著作用,且因為脫離了漢字的原生環境,漢字構形系統性和表意性的制約力減弱,類化原則在域外漢字異體字中的影響進一步擴大和加深。例如:
《倭名類聚抄》抄本中類化原則影響的往往不僅是某一個單獨的漢字字形,而是一系列字。如敦煌寫卷中從“卯”的字,常見的變異方式是變“卯”為“夘”,如“柳”字的異體作“栁”,“卿”字的異體作“”。而《倭名類聚抄》抄本中很多與“卯”無涉的字,受到類化原則的影響,其中的部分構件也都趨向于寫作“夘”或“夕(歹)”形。如,《倭》卷六至卷九“鄉里部”地名中涉及的“鄉”字,高山寺本多作“”,天正本多作“”。《倭》卷十“弘徽殿”,其中“徽”字高山寺本作“”,天正本作“”。《倭》卷十“孫炎”,其中“孫”字高山寺本作“”,除此之外還有(辨)、(斑)等字。這些漢字中不同的構件如“鄉”“系”“文”“子”等,本與“卯”字無涉,但因構件間的趨同效應,均變異為“夘”或“夕(歹)”,這是類化原則加深造成的趨同。
《倭名類聚抄》抄本中類化原則的加深,不僅體現在其帶來的更大范圍的不同構件之間的趨同,也體現在趨同后的獨體字在參加構形時所產生的影響。《倭名類聚抄》抄本中“土”字存在“土—圡—”這樣的變異路徑,中國文字材料中雖然存在少量“土”寫作“”的例子,如唐《開業寺碑》中的“土”字作“”,但以“土”為構件的合體字則少見以“”構形的,大多是以“土”“圡”作為構件。而《倭名類聚抄》抄本中,從“土”的字以“”構形和以“土”“圡”構形的頻率幾乎是一樣的,如(壁),(堂),(塞),(塾)等。究其原因,除了字形變異程度的加劇,也是受類化原則的影響,受到“云”“嘗”“去”“丟”等字中形近成分的影響。相較于“圡”字,“”變形過度,容易與其他字形混淆,如“去”,“立”的異寫形體“”等,所以在中國文字材料中“土”作為構件最多變異至“圡”的程度,這是漢字構形系統自身所具有的別異性對于字形變異程度的約束。但在《倭名類聚抄》中,因為離開了漢字本身的原生環境,這種約束性遭到了破壞。
與“異化加劇”主要針對同一漢字縱深發展不同的是,“類化加深”是發生在一系列具有相同或相似構件的漢字中間的。歸并形近構件,用形體相對簡單的構件同化復雜構件,減少記憶與書寫的負擔,是域外漢字異體字發展中類化原則影響加深的一個重要原因。
4.增補異體字發展材料
《倭名類聚抄》中留存的字形,可以為漢字異體字發展提供補充材料。漢字字形的發展往往具有延續性和繼承性,斷裂式的發展是比較少見的,一些看似無理或無法厘清變異脈絡的異體字形,大部分是因為缺少了中間一環的字形,《倭名類聚抄》中留存下來的一些異體字形恰好能夠彌補部分缺失。如《龍龕手鏡》卷四“,古文,音峻”,“”字于中國字書、韻書中少見,《漢語大字典》未收,《中華字海》僅收錄字形、字音,而字義未詳。結合《倭名類聚抄》抄本中留存的相關字形及其他文字材料,可知“”當為“囟”字之異體。《說文解字·囟部》:“,頭會,匘蓋也。象形。”裴務齊正字本《刊謬補缺切韻》:“,腦會。亦。”《倭》卷三“會”條目下,收錄了“囟”的不同寫法,真福寺本“會”,“字亦作”;天正本“會”,“字亦作”。其中“”“”皆為“囟”的異寫字,結合裴務齊正字本《刊謬補缺切韻》中的字形“”,可知“”為“囟”的異寫字無疑。《倭名類聚抄》抄本中留存的字形“”“”與“”“”一起,構成了“囟”的異寫字發展序列。
5.結語
《倭名類聚抄》抄本中異體字所呈現出的特點,與中國文字材料中的異體字一脈相承,又具有其自身的特性。當漢字進入域外其他國家或地區的語言環境時,漢字系統所具有的表意性、別異性等原則的制約能力會有所減弱,以致域外漢字在發展中常見字形變異加劇、類化原則影響加深等現象。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倭名類聚抄》等域外文獻作為遠離漢字原生土壤的域外漢字材料,不僅有助于研究漢字域外傳播的各類現象,也可以通過對比研究來反觀漢字自身,那些原本僅從漢字原生材料視角難以發現的現象,在域外漢字材料的對比之下得以呈現。利用域外漢字材料進行異體字字形、字用方面的研究已經越來越受到學界的關注,但在漢字構形理論和漢字發展史理論觀照下的域外漢字研究仍是目前有待進一步研究的學術領域,也是有待形成系統性理論的領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