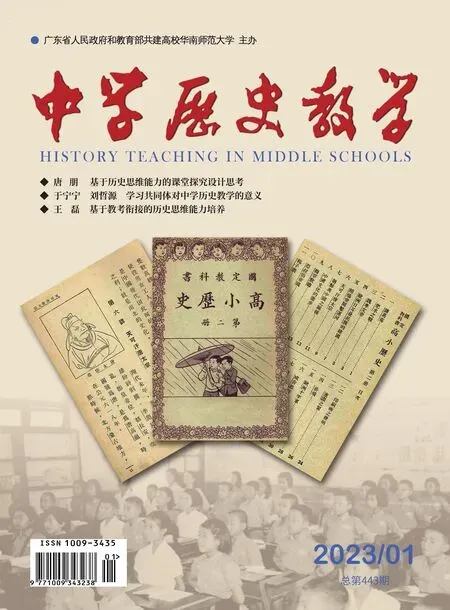指向深度學習的歷史課堂教學策略改進*
李應平 蕪湖市繁昌區教師發展中心
深度學習是一種基于理解的學習,是以發展高階思維和解決實際問題為目標,指向立德樹人,指向發展核心素養,指向培養全面發展的人。[1]隨著課改的不斷深化,指向深度學習的歷史課堂教學策略須加以改進。
一、回歸生活的情境,歷史信息深加工,遇見有意義的歷史
深度學習,“深”在對知識和信息的深度加工與意義生成,回歸生活情境,讓學生親近歷史課是深度教學的一種策略。“情境可使靜態的歷史知識得以敞開,它既可彌補歷史知識形成的過程及其運用的方法,更能進一步彰顯歷史知識發現者的直覺洞見、求知熱情及其精神追求,有助于實現多維度知識、能力、方法與情感的有機統一。”[2]
歷史事件大多離學生生活有一定距離,如果不能回歸生活,學生頭腦中缺乏相應的物象,則很難激起學生同情同理心,對歷史的理解也會管窺蠡測。第一次世界大戰死傷人數眾多,但龐大而冰冷的數字學生無法直接感知。某老師在談論此次大戰死傷人數時,讓學生先在紙上寫出5 位最親近的人,然后讓學生一一撕去,告訴他們這些人將在戰場上離自己而去。回歸學生生活情境,學生對戰爭的創傷感觸會更深刻。回歸生活的情境,觸發學生的“體驗”,歷史教學才會實現知、情、意的統一。
歷史是一門講究邏輯的學科。“邏輯推演是基于史料到結論的必然性,而合理想象則提供了史料到結論的可能行”。[3]再豐富的歷史都存在“空白”和“裂隙”,它需要歷史研究者和學習者“穿針引線”“女媧補天”。安徽師范大學附屬外國語學校張楓老師在執教《青銅器與甲骨文》一課時,先展示甲骨文“人”“森”“鹿”“宮”“日”“牧”“斗”“月”“夢”,讓學生依據所學猜測以上對應的是今天的哪些漢字。在學生辨識出這些甲骨文后,教師告知學生以上文字均出自同一片甲骨,引導學生展開歷史想象,講述可能發生的故事。
學生甲:有一個人,清晨出門,路過一片森林,看到一只活蹦亂跳的梅花鹿,向遠處看,有方正的宮殿,抬頭看看太陽。此時他的身邊走過一位趕著牛的牧人,因為不小心碰了一下,兩人發生了一場斗毆。夜晚,彎彎的月亮掛在空中,人們躺在床上,漸漸進入夢鄉。
學生乙:從前有一個獵人,在森林里打獵,看到了一頭鹿。他望向遠處的宮殿,心想若能給大王送貢品,便能得到一筆賞金。于是他拉弓,準備……還沒等他放箭,一只牧羊犬咬住了他,牧羊犬的主人走過來呵斥道:“你這樣肆意傷害動物,你的良心呢,為了得到一筆錢就這樣肆意妄為?”于是獵人和牧羊人打了起來(斗),烈日如同審判者映照著獵人的雙眼,又像神靈一樣照耀著牧羊人的身軀……夜色降臨,獵人拖著遍體鱗傷的身體,眼睜睜看著其他人進入夢鄉,自己卻只能自我反省,陷入深深自責。
為何同樣的素材,在不同學生腦中顯現出不同畫面?讓學生通過課堂學習的親身體驗使其明白,歷史認識亦是如此。面對殘缺不全、支離破碎的歷史遺存,學生“基于歷史知識和歷史證據生成歷史想象,對歷史進行合理的設想和理解,構想歷史的真實圖景,形成和表達自我的歷史理解,從中獲取能夠指導人生實踐的價值觀念”[4]。“森”“牧”“鹿”反映了當時生產狀況(原始農牧業);“宮”“斗”反映了當時生活狀況(階級狀況)。歷史學習的價值不僅在于對史料的理解,更在于通過我們的梳理、選擇,建立起有意義的歷史敘事,探究歷史背后的真諦。正如王爾敏所言:“凡史料以至史實,不經史家之解釋,即無史學之意義。”[5]史料是“死的”,史識是“活的”,對信息進行深加工,在有限史料與客觀歷史之間架起橋梁,最大限度地“還原”歷史從而獲得較強的歷史現場感。因此,歷史教學的價值在于揭示史料背后所蘊涵的歷史寓意,進而獲得深度認知。
二、回歸認知的邏輯,教學思路深理解,遇見有智慧的歷史
深度學習是一種運用高階思維對歷史現象、復雜概念進行認知與理解的學習,“深刻”是其重要特征。我們認識歷史的一般邏輯是,先看到歷史現象,然后探究其發生的原因,從中汲取歷史的智慧。但在課堂教學中,一些教師囿于教材編寫體例的限制,不敢越雷池半步,以致教學缺乏智慧的火花。
七年級上冊第6 課《動蕩的春秋時期》包括的三目依次是“春秋時期的經濟發展”“王室衰微”“諸侯爭霸”,很多教師習慣按照教材順序,由原因到現象,致使探究性大打折扣。某教師在執教本課時,對教材內容進行整合,依次為“因·動蕩之因——王室衰微”“象·動蕩之象——諸侯爭霸”“源·動蕩之源——經濟發展”。筆者在觀課后建議其調整為:“象·動蕩之象——諸侯爭霸”→“因·動蕩之因——王室衰微”→“源·動蕩之源——經濟發展”。調整緣由在于回望歷史,我們首先看到是諸侯爭霸的歷史現象,探究直接原因,不難發現是王室衰微,失去對諸侯的控制,進而繼續探究,就會發現其發生的根本原因是經濟發展推動上層建筑變革。基于邏輯次序的調整,歷史學科的思辨性、探究性的魅力得以體現。唯有深究才能引發思維碰撞,思維發展才能彰顯歷史學的智慧之用。
讀史明智,這里的“智”不僅是知識,更是一種對現象背后原因的洞察。歷史認識建立在一定的邏輯基礎之上,邏輯的錯位或者缺乏,都會有損歷史學科“讀史明智”的宗旨。
三、回歸時空的場閾,歷史情感深滲透,遇見有溫情的歷史
深度學習不僅在于認識的深刻,還在于情感的深度滲透,回歸時空的場閾,移情換位不失是一種良好的方法。歷史學習的內容大多離學生生活較遠,由于時空的阻隔,很難激起學生對歷史人物、歷史場景感同身受的同情與理解。
某教師在執教《辛亥革命》時,引用了一段秋瑾赴刑場的道白:“我此番赴死,是為革命,中國婦女還沒有為革命流過血,當從我秋瑾始。縱使世人并不盡知革命為何,竟讓我狠心拋家棄子。我此番赴死,正為回答革命所謂何事,革命是為給天下人造一個風雨不侵的家,給孩子一個溫和寧靜的世界,縱使這些被奴役久了的人們早已麻木,不知寧靜溫和為何物。我此番赴死,是為革命,死并非不足懼,亦并非不足惜,但犧牲之快、之烈,犧牲之價值,竟讓我在這一刻自心底喜極而泣。”第一個“我此番赴死”表現了秋瑾為革命敢于赴死,第二個“我此番赴死”展現了秋瑾為革命愿意赴死,第三個“我此番赴死”體現了秋瑾為革命樂于赴死。遺憾的是,教師在這段道白完成后,沒有后續,“歷史”依舊冷冷的聳立在遙遠的時空中。觀課后,筆者建議教師能否采用“時空對話”的方式,讓學生和秋瑾來一段“時空對話”。無獨有偶,不久聽一位教師執教《從九一八事變到西安事變》,教師引用了趙一曼烈士寫給兒子的遺書,教師沒有聲淚俱下的朗讀,而是讓學生作為革命的后來人給“趙媽媽”寫一封信,告訴“趙媽媽”我們今天的生活和自己的努力。在這里,我們感受到了歷史的溫度,那些遠去的歷史、逝去的英雄并不孤單,我們今天正以各種方式紀念著他們、告慰著他們。歷史教學不是觀望歷史,而是和歷史的對話,是對往事的理解與揚棄,是深刻的反思與決然的前行。
歷史課堂是有生命的,歷史學人也應是有溫情的,對歷史最好的紀念就是繼承與批判、革故與創新。歷史教學需要理性,但理性不是冷冰冰的看待,是基于了解的同情,是換位思考,是積極走進歷史的場閾。唯有對歷史的溫情與敬意,才有對當下生活的珍惜。
四、回歸真實的對話,教學活動深開展,遇見有生機的歷史
深度學習需要由表及里,把握歷史事件的本質。唯有活動深開展,課堂才會成為“奇妙的旅程”。教學中,我們已經習慣于教師提問,學生回答,習慣于學生無問題,習慣于代替學生提問題。我們以為學生回答了問題,學生就在思考。至于哪些是學生想問的問題、學生的思考在哪,我們茫然無知。
如執教《從九一八事變到西安事變》,通常教師都會出示史料,引導學生思考“日本為什么要發動九一八事變”,筆者在執教這節課時,讓學生當“老師”進行提問:“如果你是老師,你會問學生什么問題”,結果學生問的是“日本為什么能發動九一八事變”。“為什么要”是老師想探究的問題,“為什么能”是學生想探究的問題。從“為什么要”到“為什么能”說明學生想探究的不僅有“為什么”問題,還有“怎么應對”的問題。在學習西安事變時,教師一般都會引導學生探討“釋蔣還是放蔣”問題,而學生更關心的是“張學良為何要護送蔣介石去南京,他是否擔心蔣介石變卦”。因為學生覺得教材中已有結果即“釋蔣”,討論意義不大,而探究張學良當時的心路歷程更有價值。沒有真實的對話,何來課堂之生成?
真實的對話一定是基于真問題、真疑惑。只有給學生提問的機會,活動深開展,才能暴露學生的真困惑。有了對真困惑的探究,教學才有發展的空間,才有師生的共生共長。
五、回歸史家的視野,歷史解釋深挖掘,遇見有新意的歷史
深度學習的效果旨在使學生能夠舉一反三,能運用所學解決復雜問題。在實際課堂教學中,很多教師習慣于用現成的歷史結論教育學生,搞得歷史結論似乎“一成不變”,教學的淺層化,也消減了學生學習的興趣。
筆者在執教“偉大的抗日戰爭”一課時,基于“十四年抗戰”的教學要求,進行了如下設計:首先請學生制作“抗日戰爭”大事年表。然后引導學生思考:如果要對抗日戰爭進行階段劃分,你會如何劃分?比較學生不同劃分后進行討論:影響抗日戰爭起點、階段劃分的因素有哪些?讓學生回到史學家分析問題的“原點”,嘗試史學家分析問題的路徑與方法,分享自己開放性、獨見性成果,這比教師直接灌輸“十四年抗戰”效果要好。在探究過程中,學生感受到“史家的視野”不僅受“史料實證”影響,也受史家自身立場、觀念、利益等影響,歷史階段的劃分因史家個人因素的不同而不同,也隨著人們認識的發展而不斷變化。以親歷的場景,讓學生看見歷史的豐富多樣性。感受歷史的多元,更容易加深學生對歷史復雜性的理解。歷史解釋深挖掘,學生看到的不僅是有新意的歷史,更提升了解決復雜問題的能力。
課堂教學引導學生回歸“史家的視野”進行探究,不僅有助于彰顯歷史學科研究的方法和魅力,也有助于學生核心素養的達成。
【注釋】
[1]郭華:《深度學習與課堂教學改進》,《基礎教育課程》2019 年第2 期,第10 頁。
[2]王德民、李應平:《指向歷史核心素養的教學目標設計》,《歷史教學問題》2019 年第2 期,第109 頁。
[3]苗穎:《“史料實證”素養的教學分解初探——基于對2000 年以來相關高考試題的分析》,《歷史教學》(上半月刊)2017 年第2 期,第52 頁。
[4]郭元祥、王秋妮:《參與歷史:歷史想象及其能力培養》,《課程·教材·教法》2021 年第11 期,第109 頁。
[5]王爾敏:《史學方法》,北京:中華書局,2018 年,第158 頁。
[6]吳曉波:《激蕩三十年》(上),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年,第68 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