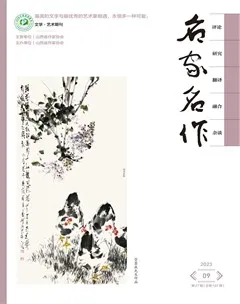從《樂(lè)記》看藝術(shù)的功能與當(dāng)代藝術(shù)接受
劉 苑
《樂(lè)記》是中國(guó)古代美學(xué)思想史上第一部自成體系的音樂(lè)理論專著,堪稱中國(guó)古典美學(xué)的奠基石。《律呂正義》 評(píng) 《樂(lè)記》為:“囊括古今言樂(lè)之道, 精粗本末,縷無(wú)遺。”宗白華先生在《美學(xué)散步》一書中也肯定了《樂(lè)記》的價(jià)值,他指出:“中國(guó)古代思想對(duì)于音樂(lè),特別對(duì)于音樂(lè)的社會(huì)作用、政治作用,向來(lái)是十分重視的。早在先秦時(shí)期,就產(chǎn)生了一部在音樂(lè)美學(xué)方面帶來(lái)總結(jié)性的著作,就是有名的《樂(lè)記》。《樂(lè)記》提供了一個(gè)相當(dāng)完整的體系,對(duì)后世影響極大。”現(xiàn)在所見到的十一篇就分析了樂(lè)的產(chǎn)生、禮樂(lè)關(guān)系、樂(lè)的功能等音樂(lè)美學(xué)方面的問(wèn)題。雖不是鴻篇巨制,卻很精微,其中大部分篇幅是對(duì)禮樂(lè)功能的論述,因此當(dāng)代藝術(shù)教育可以從中汲取精華,打造藝術(shù)教育的新范式。
一、《樂(lè)記》對(duì)藝術(shù)功能的論述
(一)樂(lè)由心生,隨心而動(dòng)
《樂(lè)記》是儒家禮樂(lè)思想的代表性文獻(xiàn),以“中和之美”為主旨,闡明了藝術(shù)的審美認(rèn)識(shí)與審美教育功能。
藝術(shù)史上關(guān)于藝術(shù)起源的解釋主要有模仿說(shuō)、游戲說(shuō)、表現(xiàn)說(shuō)、巫術(shù)說(shuō)、勞動(dòng)說(shuō)等,由于藝術(shù)的起源比較復(fù)雜,很難用一種學(xué)說(shuō)來(lái)闡釋,于是就出現(xiàn)了一種新的解釋——多元學(xué)說(shuō),即運(yùn)用多種學(xué)說(shuō)來(lái)解釋藝術(shù)的起源,那么音樂(lè)的起源也可以運(yùn)用多元學(xué)說(shuō)來(lái)解釋。《樂(lè)記》認(rèn)為“聲”“音”“樂(lè)”三者不同。在《樂(lè)記·魏文侯篇》就提出了:“今君之所問(wèn)者樂(lè)也,所好者音也。夫樂(lè)者與音,相近而不同。”這與現(xiàn)代人對(duì)音樂(lè)的解釋不同,是思考問(wèn)題的起點(diǎn)。而《樂(lè)記·樂(lè)本篇》進(jìn)行了具體的闡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dòng),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動(dòng),故形于聲。聲相應(yīng),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lè)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lè)。”這里明確指出了“聲”“音”“樂(lè)”三者的區(qū)別,“聲”是自然存在的,天地之間有三籟:天籟、地籟、人籟,聲音是復(fù)雜多變的;“音”是藝術(shù)創(chuàng)作主體內(nèi)外交互作用之下,有節(jié)奏的音符;而“樂(lè)”是內(nèi)容和形式的結(jié)合,《樂(lè)記·樂(lè)象篇》更突出了“樂(lè)”之核心在“德”,“德者,性之端也;樂(lè)者,德之華也。金石絲竹,樂(lè)之器也。詩(shī),言其志也;歌,詠其聲也;舞,動(dòng)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樂(lè)氣從之。”這段文字道出了“樂(lè)”源于心的本質(zhì),既是對(duì)原始藝術(shù)形式的概括,也是對(duì)其內(nèi)容的申述。“德”是內(nèi)容,“樂(lè)”是形式,可見這是一個(gè)逐漸發(fā)展的過(guò)程,是從自然審美到藝術(shù)審美的過(guò)渡。
這又引申出另一組有區(qū)別的概念:性與情、欲,性是靜止的,而情、欲是由外物感發(fā)所以變動(dòng)不居的,“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動(dòng),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后好惡形焉。好惡無(wú)節(jié)于內(nèi),知誘于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音樂(lè)是表現(xiàn)人的性、情、欲的,應(yīng)有一定的法度,因?yàn)樘斓刂g是有一種秩序、節(jié)奏存在的,如果沒(méi)有很好地得到平衡,而是執(zhí)著于紛繁的外部世界,就破壞了天地之美。當(dāng)代藝術(shù)教育既要從情感出發(fā),以情動(dòng)人,又要從自然之美出發(fā),體味山水之趣與天地之美。
(二)樂(lè)以治心,移風(fēng)易俗
藝術(shù)的功能,小到個(gè)人修養(yǎng),大到國(guó)家政教。從治心到治國(guó),藝術(shù)與生命、家國(guó)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凡音者,生于人心者也。樂(lè)者,通倫理者也。是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lè)者,眾庶是也。惟君子為能知樂(lè)。”人之所以為人的體現(xiàn)之一則是知禮樂(lè),通過(guò)藝術(shù)教育來(lái)啟蒙開智。由此看來(lái),藝術(shù)教育一方面要承擔(dān)審美認(rèn)識(shí)的功能,另一方面要承擔(dān)審美教育的功能,甚至在《樂(lè)記·師乙篇》還可以看到藝術(shù)的審美體驗(yàn)與審美娛樂(lè)功能:“故歌之為言也,長(zhǎng)言之也。說(shuō)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zhǎng)言之,長(zhǎng)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通過(guò)詩(shī)歌樂(lè)舞的表達(dá),藝術(shù)與個(gè)人、社會(huì)生活交織在一起,塑造著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jià)值觀。
“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dòng)于中,故形于聲;聲成文,謂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lè)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guó)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如此,則國(guó)之滅亡無(wú)日矣。”音樂(lè)折射出社會(huì)的政治狀況,通過(guò)它可以觀社會(huì)風(fēng)俗,引導(dǎo)社會(huì)良性發(fā)展。“鄭衛(wèi)之音,亂世之音也,比于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guó)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鄭衛(wèi)之音自古是惡劣的政治環(huán)境的寫照。因此在某種程度上,對(duì)音樂(lè)的關(guān)注有著極強(qiáng)的政治色彩,《樂(lè)記·樂(lè)施篇》:“樂(lè)也者,圣人之所樂(lè)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fēng)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這段話強(qiáng)調(diào)了音樂(lè)可以移風(fēng)易俗,成為社會(huì)教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樂(lè)記·樂(lè)言篇》中載:“律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以象事行。使親疏貴賤長(zhǎng)幼男女之理,皆形見于樂(lè)。故曰:‘樂(lè)觀其深矣’。”這樣才算是能深刻觀察人類社會(huì)。“禮節(jié)民心,樂(lè)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lè)刑政,四達(dá)而不悖,則王道備矣。”又:“故禮以導(dǎo)其志,樂(lè)以和其聲,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禮樂(lè)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禮樂(lè)刑政四者中,足以見藝術(shù)對(duì)于社會(huì)治理的重要性。
(三)禮樂(lè)合一,天下皆寧
禮和樂(lè)是互相顯發(fā)的,不管是作為人倫制度的禮,還是作為陶冶性情的樂(lè),都是從內(nèi)在和外在來(lái)規(guī)范人生的,是一種生命秩序的體現(xiàn)。“樂(lè)由中出,禮自外作。樂(lè)由中出故靜,禮自外作故文。大樂(lè)必易,大禮必簡(jiǎn)。樂(lè)至則無(wú)怨,禮至則不爭(zhēng)。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lè)之謂也。”這就是儒家所倡導(dǎo)的禮樂(lè)文化的精髓所在,禮樂(lè)的制定要既簡(jiǎn)單又平易,才有可行性。藝術(shù)的最高境界是讓人的心靈歸于平和、寧?kù)o。這樣才能無(wú)為而無(wú)所不為,宇宙自然、人文社會(huì)才有良好的秩序。
《樂(lè)記·樂(lè)論篇》中提道:“樂(lè)者為同,禮者為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樂(lè)勝則流,禮勝則離。合情飾貌者,禮樂(lè)之事也。”音樂(lè)是從內(nèi)統(tǒng)一人的,因?yàn)橥獠渴澜缡秦S富多彩的,而人的內(nèi)心世界是千姿百態(tài)的,音樂(lè)作為一種精神宣泄和引導(dǎo)是對(duì)于社會(huì)秩序的正向建構(gòu),也許這就是音樂(lè)存在的真正社會(huì)意義。禮則是從外統(tǒng)一人的,雖說(shuō)禮體現(xiàn)的是尊卑、長(zhǎng)幼等倫理秩序,但禮在深層次上也指向了良好社會(huì)秩序的正向建構(gòu),因而禮樂(lè)是相輔相成的,都是人類社會(huì)正常秩序的建設(shè)者。“樂(lè)由天作,禮以地制。過(guò)制則亂,過(guò)作則暴;明于天地,然后能興禮樂(lè)也。”禮樂(lè)如果沒(méi)有統(tǒng)一于天地之和,就違背了宇宙生命的法則。“大樂(lè)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jié)。和,故百物不失節(jié),故祀天祭地。明則有禮樂(lè),幽則有鬼神,如此,則四海之內(nèi),合敬同愛(ài)矣。”又有:“樂(lè)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別。”這才是天人合一的大化生命之美。“禮樂(lè)皆得,謂之有德,德者得也。”德是最終收獲,是生命的光輝。“春作夏長(zhǎng),仁也;秋斂冬藏,義也。仁近于樂(lè),義近于禮。”這是自然的恩澤與人世的禮樂(lè)相得益彰的結(jié)果。
然而禮樂(lè)皆是人情的表現(xiàn),《樂(lè)化篇》中講道:“故樂(lè)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紀(jì),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樂(lè)情篇》中講道:“樂(lè)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樂(lè)統(tǒng)同,禮辨異,禮樂(lè)之說(shuō),管乎人情矣!”這種秩序的背后是一種深厚的審美生命意識(shí)。通過(guò)審美愉悅,實(shí)現(xiàn)個(gè)體生命的充盈與社會(huì)的和諧安寧,由此可見,藝術(shù)對(duì)于促進(jìn)社會(huì)和諧發(fā)展有非常重要且積極的作用。
二、《樂(lè)記》與當(dāng)代藝術(shù)接受
《樂(lè)記》闡明了藝術(shù)的功能,是對(duì)孔子、荀子藝術(shù)功能觀的繼承,在中國(guó)藝術(shù)理論史上產(chǎn)生了深遠(yuǎn)的影響,至今仍為當(dāng)代的藝術(shù)接受帶來(lái)新的啟示。尤其是藝術(shù)教育轉(zhuǎn)型一直是一個(gè)有探討意義的話題,藝術(shù)教育面臨多重選擇與轉(zhuǎn)型發(fā)展的新時(shí)代課題,既要從傳統(tǒng)文化中汲取優(yōu)秀的藝術(shù)成果,又要面對(duì)多元的接受群體創(chuàng)新藝術(shù)發(fā)展的新方法,因此,結(jié)合藝術(shù)接受現(xiàn)狀,對(duì)當(dāng)代藝術(shù)接受有以下幾點(diǎn)思考。
(一)遺音遺味,直面生活
隨著時(shí)代的發(fā)展,藝術(shù)也呈現(xiàn)出新的風(fēng)貌,大量藝術(shù)家、藝術(shù)作品、藝術(shù)思潮不斷涌現(xiàn),讓人應(yīng)接不暇。高新技術(shù)一方面加快了藝術(shù)發(fā)展的速度,我們可以足不出戶欣賞各類藝術(shù)作品,另一方面技術(shù)也改變了我們的審美體驗(yàn)方式,除了體驗(yàn)真實(shí)的世界,也可以暢游虛擬世界,這恰恰提出了新的問(wèn)題。面對(duì)多元的文化藝術(shù)選擇,我們的審美感受力反而在下降,人們?cè)缫蚜?xí)慣了技術(shù)和經(jīng)驗(yàn)式的表達(dá),缺乏直面生活的審美體驗(yàn)。《樂(lè)記·樂(lè)本篇》中提出了“遺音遺味”的概念:“樂(lè)之隆,非極音也;食饗之禮,非致味也。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倡而三嘆,有遺音者矣。大饗之禮,尚玄酒而俎腥魚,大羹不和,有遺味者矣。”在大饗之禮上,魚肉以原本的樣態(tài)呈現(xiàn),并不加以烹飪,肉湯也不加入佐料,而是盡可能以本然的樣態(tài)來(lái)呈現(xiàn)。在重要的禮儀場(chǎng)合之所以這樣選擇,并不是因?yàn)楫?dāng)時(shí)的人不善于烹飪,不知道什么樣的味道更能滿足味蕾,而是要以此來(lái)表達(dá)禮樂(lè)合一的藝術(shù)觀念。
這里的“遺音遺味”目前有三種解釋,一種是余音余味,一種是無(wú)音無(wú)味,還有一種是忘音忘味,這三種解釋,無(wú)論哪一種,都對(duì)藝術(shù)接受極具啟示意義。如果說(shuō)莊子“心齋坐忘”是對(duì)藝術(shù)接受方法的啟示,那么“遺音遺味”就是對(duì)接受效果的描述,是對(duì)藝術(shù)接受的進(jìn)一步表達(dá),也是進(jìn)入藝術(shù)批評(píng)的必經(jīng)之路。這與西方文藝?yán)碚撝械摹拔炊c(diǎn)”概念相呼應(yīng),而這一概念又是在現(xiàn)象學(xué)美學(xué)和解釋學(xué)美學(xué)的基礎(chǔ)上,從海德格爾的“先在結(jié)構(gòu)”、伽達(dá)默爾的“前見”和英伽登的“具體化”概念衍化而來(lái)的。由此可見,中西方藝術(shù)盡管在具體形態(tài)上、藝術(shù)精神上表現(xiàn)出明顯的不同,但是在接受層面卻有著相近的藝術(shù)規(guī)律。
藝術(shù)接受要從審美體驗(yàn)出發(fā),直面生活,尋找“空白”,一方面是重新審視生活,另一方面是尋找藝術(shù)的“言外之意”“象外之象”“味外之旨”,在直面生活的基礎(chǔ)上,回歸藝術(shù)本身,又超乎藝術(shù)之外。藝術(shù)的核心功能是審美體驗(yàn),情感又是審美的根本,所以直面生活不僅是一種直觀的勇氣,更是一種自由的熱愛(ài)。對(duì)于藝術(shù)創(chuàng)作和接受都是如此,要從自然、社會(huì)、歷史、人生出發(fā),感受四季的變化,善于發(fā)現(xiàn)時(shí)代和社會(huì)的發(fā)展。具有敏銳的生命意識(shí)與廣博的藝術(shù)眼界,不僅應(yīng)具有扎實(shí)的專業(yè)知識(shí)儲(chǔ)備,還應(yīng)具備豐富的人文素養(yǎng)。由此可見,面對(duì)經(jīng)典的藝術(shù)作品,以“陌生化”的手法,回歸生活本身,喚醒接受者的審美體驗(yàn)意識(shí),才是藝術(shù)接受的有效途徑。
(二)禮樂(lè)合一 ,傳承發(fā)展
藝術(shù)除了具有審美體驗(yàn)功能,還有一個(gè)重要的功能就是審美教育。“夫物之感人無(wú)窮,而人之好惡無(wú)節(jié),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于是有悖逆詐偽之心,有淫泆作亂之事。……是故先王之制禮樂(lè),人為之節(jié)。”藝術(shù)的產(chǎn)生是對(duì)人的行為的一種平衡和調(diào)節(jié),天地有大美而不言,正是一種秩序的體現(xiàn),因而合和則是藝術(shù)精神的可貴之處,讓大千世界和而不同,有自己的“道”。“地氣上隮,天氣下降,陰陽(yáng)相摩,天地相蕩,鼓之以雷霆,奮之以風(fēng)雨,動(dòng)之以四時(shí),暖之以日月,而百化興焉,如此,則樂(lè)者,天地之和也。”由此可見,藝術(shù)教育從個(gè)體而言,可以表達(dá)內(nèi)心的感受;從社會(huì)而言,可以增強(qiáng)社會(huì)凝聚力,弘揚(yáng)正確的價(jià)值理念。當(dāng)代藝術(shù)教育一方面要繼續(xù)傳統(tǒng)的藝術(shù)精神,另一方面要打造傳統(tǒng)藝術(shù)的新范式,弘揚(yáng)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藝術(shù)成果,促進(jìn)當(dāng)代藝術(shù)教育的發(fā)展。
在接受過(guò)程中,將現(xiàn)代化技術(shù)與藝術(shù)相結(jié)合,通過(guò)多種形式的互動(dòng)體驗(yàn),形成審美感知與藝術(shù)直覺(jué),有助于藝術(shù)接受的正向體驗(yàn)。可以通過(guò)數(shù)字化資源整合、沉浸式藝術(shù)體驗(yàn)館、文創(chuàng)產(chǎn)品開發(fā)、城市文化空間構(gòu)建等方式,引導(dǎo)接受者理解直面生活的意義,增強(qiáng)審美的體驗(yàn)。比如講讀博物館、敦煌莫高窟數(shù)字展示中心、“馬王堆漢代文化沉浸式多媒體大展”全球IP 招標(biāo)、故宮文創(chuàng)產(chǎn)品設(shè)計(jì)開發(fā)、地鐵數(shù)字藝術(shù)館等方式,達(dá)到“是故先王之制禮樂(lè)也,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這是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中禮樂(lè)精神在當(dāng)代的傳承與發(fā)展,通過(guò)展示優(yōu)秀的傳統(tǒng)文化藝術(shù)成果,既能推動(dòng)社會(huì)文化的繁榮,構(gòu)建良好的社會(huì)秩序,又能增強(qiáng)中國(guó)文化的影響力,堅(jiān)定文化自信,從而激發(fā)文化創(chuàng)新的活力。
三、結(jié)語(yǔ)
《樂(lè)記》是中國(guó)古代重要的藝術(shù)理論典籍,不僅闡述了音樂(lè)的產(chǎn)生、功能以及它與社會(huì)發(fā)展之間的關(guān)系,更是對(duì)禮樂(lè)精神的總結(jié)與思考。音樂(lè)作為表情藝術(shù),也是大眾最熟悉的一種藝術(shù)類型,可以實(shí)現(xiàn)和心、和天地、和民的藝術(shù)功能。通過(guò)對(duì)《樂(lè)記》藝術(shù)功能的探究,給予當(dāng)代藝術(shù)接受新的啟示,思考中國(guó)優(yōu)秀的傳統(tǒng)藝術(shù)新的接受路徑與發(fā)展形態(tài),更加堅(jiān)定文化自信,激發(fā)文化創(chuàng)新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