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新發現史料看中央特科的活動情況
■楊 田
1934年9月26日,中央特科紅隊在上海公共租界槍殺叛變的特科原成員熊國華。此后,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巡捕房聯合上海市公安局對中央特科紅隊成員進行大搜捕,抓獲紅隊成員多名并查獲多份資料。根據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察情報處外事科科長丘比羅斯的建議,工部局警察情報處副總監命令情報處勤務警部助理伊姆·高爾德,根據被捕人員的供述、查獲資料及多年來偵破的涉中央特科的案件,撰寫中央特科的活動情況報告。12月6日,高爾德完成報告——《中國共產黨特務隊的活動情況》。1935年7月,日本內務省警保局將該份報告從英文譯成日文,并刊登于《外事警察報》 (第156期),標注密級為“特密”。
因工作性質特殊,中央特科沒有留存檔案,這為后來的黨史研究留下一大難題。近年來,關于中央特科的研究成果不斷出現。2021年,中共中央特科機關舊址紀念館也于上海建成。但是,關于中央特科的研究,更多的是依據一些老同志的回憶和當年租界巡捕房及國民黨有關機構保存的口供。日本《外事警察報》中刊載的此份報告,雖然是翻譯資料,但應該是目前已知的早期比較系統地介紹特科的資料之一,而且是出自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之手,其內容可信度較高。現將有關內容簡要介紹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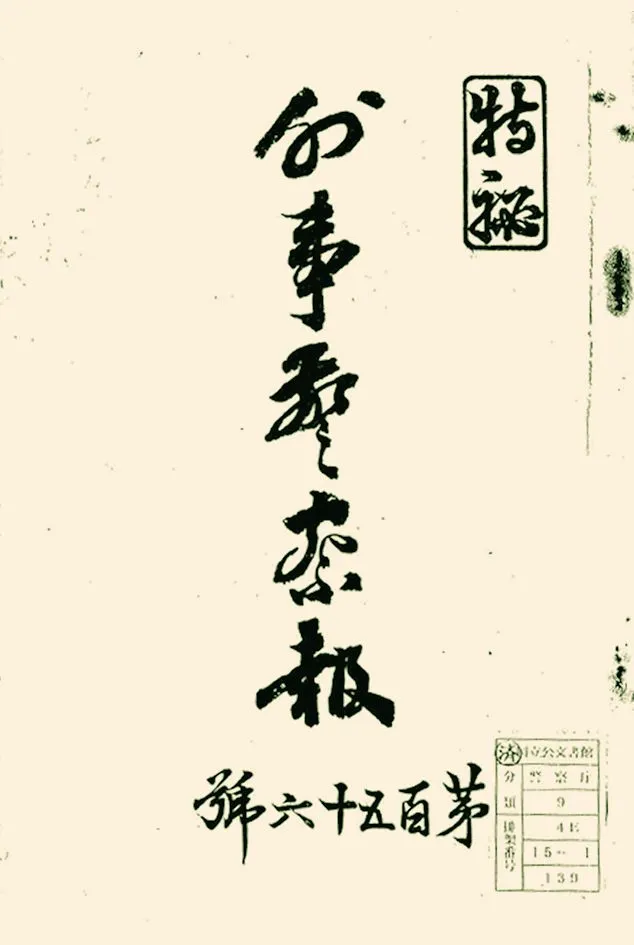
日本《外事警察報》 (第156期)封面
關于中央特科的名稱及中央特科紅隊開始活動的時間
該份報告通篇沒有出現“中央特科”或“特科”的稱謂,而是使用“中共特務隊”。原因可能有二:一是公共租界巡捕房不知道中央特科的名稱,故用自創的“中共特務隊”來代指“中央特科”;二是公共租界巡捕房知道“中央特科”的名稱,但由于是中譯英翻譯問題,使用了某一特定英語詞匯,后來日本譯者從英文翻譯為日文時,譯成了“中共特務隊”。
從中日語言翻譯的慣例來看,“中央組織局特務科”這八個漢字在日語中都存在,如當時日本譯者知道“中央特科”這一組織,肯定會直譯為“中央特科”,而不會另譯為“中共特務隊”。基本可以判明,至少在1935年之前,日本內務省警保局尚不知道中央特科的具體名稱。
從報告內容來看,公共租界巡捕房關注的更多是特科的行動,對特科的總務、情報和無線電通信并不關注,所以該份報告中的“中共特務隊”指的主要是特科的紅隊。報告中專門提到了中央特科紅隊開始活動的時間,是這樣表述的:
“關于中國共產黨的格別烏,即中共特務隊的成立時間,目前有用的信息不多。不過據中共特務隊的前領導人顧順章介紹,大約在1928年秋天,中共特務隊開始在上海活動。自1925年至1927年間,中共也組織過一些懲處活動,但那都不是中共特務隊所為。中共特務隊是中共在原有保衛力量的基礎上,補充精干力量并進行更為專業的訓練后形成的一個專門的行動機構。”
報告中還列出了兩個表格,表一為1925年至1934年中共在公共租界內開展懲處行動的日期、死亡人數、受傷人數及被逮捕人數的數據統計。表二為中共組織的懲處行動的日期、死亡者姓名、行動地點,以及被逮捕人數的數據統計。
從表一中可以看出,1929年后,除1931年受“愛棠村事件”影響外,每年“死亡人數”較1927年、1928年明顯下降。在表二中,1927年的懲處行動達到頂峰,共計28起。這應該與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前后殘酷的斗爭形勢有關。但特科在1927年11月14日才成立,所以此年度的絕大多數懲處行動應與中央特科無關。1928年懲叛鋤奸行動10起。進入1929年后,每年的懲叛鋤奸行動直線下降至兩三起。
根據已知史料,紅隊自特科成立伊始就已組建,從未被授予過任意行動、濫殺的特權,每次采取制裁行動,都要經過嚴密偵察,掌握確鑿證據,并且須報經黨中央、中央特委批準,執行嚴格的審批制度。綜合報告中提及的顧順章關于紅隊開始活動的有關表述,以及表一和表二中紅隊1929年前后懲處行動在數量上的急劇變化,紅隊自1928年秋季開始在上海開展懲處行動的可信度還是非常高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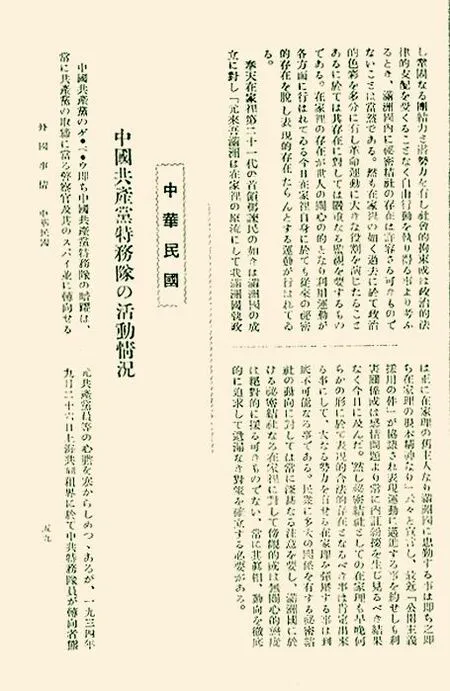
《外事警察報》 第156期刊載的《中國共產黨特務隊的活動情況》 報告
特科紅隊開展懲處行動的細節
根據報告所述,紅隊開展懲處行動大致分為前期準備、具體實施和后期收尾三個階段。
一、前期準備階段。“死刑執行部部長向暗殺組下達懲處指令,附帶行動目標的照片或者畫像等。執行部部長從成員中挑選出一到兩位經驗豐富的人員擔任此次懲處行動的組長,負責組織實施整個行動。”“組長到懲處目標的住處進行踩點,確定便于懲處且容易撤退的地點,并做好準備工作。待一切準備工作就緒后,組長向執行部部長匯報行動方案。執行部部長審核行動方案,確定具體實施時間。”
報告中的“死刑執行部部長”應為中央特科紅隊的主要負責同志。制裁行動由黨中央、中央特委批準后,紅隊主要負責同志才會挑選具體人員參與懲處行動。根據報告所述,紅隊成員人數應較為可觀,每次可根據不同的懲處任務確定不同的人員構成。而且確定好人員后,紅隊主要負責同志還會確定一名或者兩名成員擔任組長,由其負責整個懲處行動。在所有準備工作完成后,具體行動方案還要履行審批手續,由紅隊主要負責同志審定后才能具體實施。可以看出,懲處行動在具體實施前都要充分做好前期準備工作,并履行嚴格的審批手續,相應地就需要一個較長的時間周期,因此在報告中公共租界巡捕房評價紅隊的懲處行動:“懲處行動比較緩慢,但是組織良好,而且成員大多為忠誠的中共黨員,所以行動成功率非常高。”
二、具體實施階段。“在行動的前一天,暗殺組組長或者受其指派的成員會提前到行動地點附近,以假身份在兩個不同的旅館內各開一個房間,或者租借兩處房屋,一處用于行動前集合,一處用于行動后會合。在行動前一個小時(有時也為兩個小時),所有參與懲處行動的成員會到其中一處房間或房屋內集合,做行動前的準備工作。所有人不攜帶武器。最后由死刑執行部部長或者部長的代理人將武器送到集合點。武器平時藏在部長的家中,運輸時采用兩人前后掩護的方式。探路人在前,運送人緊隨其后二三十米。如果突遇警察盤查,探路人會第一時間發出預警,運送人立即掉頭逃走。到達集合點后,運送人將武器分發給每名成員,然后大家散去各就各位,按照預定方案執行懲處任務。兩名成員不參與懲處行動,騎著自行車在行動地點附近往返騎行,如果發現成員被捕,這兩人會立馬逃走,告知執行部部長人員被捕情況,同時告知其他未參與行動的成員迅速變換住所。”
報告較為詳盡地介紹了紅隊開展懲處行動的細節。一是執行制裁任務時,會提前在行動地點附近物色兩處臨時住所。二是紅隊隊員平時不帶武器。武器由紅隊隊長保管,只有在執行懲處任務時,紅隊隊員才能拿到武器。此外,報告中還提及“基層成員最近(1934年9月熊國華被懲處之后至該報告撰寫期間)每人還配備了一把錘子,主要用于自衛”,也從側面證明紅隊隊員平時不攜帶武器。三是武器雙人運輸。前面的人負責預警,后面的人負責運輸。四是在行動現場,除參與執行懲處任務的成員外,還會安排兩名成員全程觀察,如任務失敗,可第一時間預警。
三、后期收尾階段。“當行動順利完成時,所有參與人員會到租下的另一處房屋或者另一家旅館的房間會合,將武器交出后立馬各自離去。”
中央特科的保密手段
報告中提及:“中共慣用的保守秘密方式,不適用于特務隊。特務隊的保密要求更高。”這與黨的隱蔽戰線比黨的其他機構保密要求更高的史實相符。報告列舉了中央特科的部分保密要求:
(一)禁止前往茶館等復雜場所。
(二)禁止與非成員交友。
(三) 非成員,如無特殊理由,不得進入特務隊成員的房間。
(四)進門后,房門必須反鎖。
(五) 會面時,要使用約定暗號聯系,如吹低音笛子或者往窗戶上扔硬幣等。
(六) 郵寄物品必須使用假名,嚴禁郵寄涉密文件資料。
報告還提及了中央特科的部分保密手段。如,使用不同顏色的信封代表不同含義。公共租界巡捕房在工作中發現,“中共特務隊的很多信封內部并沒有任何東西,僅靠收件人的寫法和信封的顏色就可以傳遞信息”。又如,使用特殊的暗號傳遞信息。報告中提及:“中共特務隊成員在住處被外方巡捕逮捕后,普遍會請求巡捕打開窗戶透透氣。歐洲人不喜歡長時間待在不通風的房間內,如果被捕人員提出類似要求,外方巡捕一般都會答應。后來巡捕房逐漸認識到,打開窗戶就是特務隊成員約定的一種暗號。一旦看到某位成員的窗戶開著,就意味著該成員出事了。其他同伙自然不會再靠近。”“從窗戶邊伸出一根小竹竿意味著平安無事,如果沒有則是指出事了。”“在窗戶上貼一張小的正方形的紙片,意味著自己在房間里。”
在大街上碰面時的暗號也是多種多樣:摘下帽子,用手絹擦額頭上的汗;用左臂或者右臂夾著包;摘下帽子,擦帽子內檐的汗;手里拿個手絹或者用手絹包著手;假裝牙痛,用手捂著臉;等等,不同的動作代表不同的含義。
中央特科紅隊的經費來源和武器來源
根據報告中“中共特務隊的經費來源至今不明”這一表述,基本可斷定公共租界巡捕房當時并不掌握中央特科的經費來源情況。不過報告中提到了1934年10月4日法租界法方巡捕在麥琪路麥琪公寓34號查獲的《1934年4月中共特務隊支出情況》。公共租界巡捕房根據這份文件,同時結合被捕人員的口供,判定中央特科日常運行僅使用現金,不會開立賬戶或者使用支票等。
此外,報告中還提到一個細節,“中共特務隊有一個姓葉的副隊長。1934年9月27日在成都路被逮捕的鄺惠安曾用鄺奇的化名從這名姓葉的副隊長手中領取了自己及下屬隊員的現金津貼”。此位姓葉的同志具體是誰,根據現有史料還無法確定。當時很多特科的同志都用化名,至于是否真的姓葉也很難確定。不過,鄺惠安是特科后期紅隊的主要負責人,從他領取現金津貼的細節來看,基本可以斷定這位姓葉的同志應為特科內較重要的一位領導或者負責財務的同志。
公共租界巡捕房對中央特科的武器來源有一個認知轉變的過程。在前期,公共租界巡捕房認為中央特科的武器都是從蘇區通過秘密渠道運到上海來的。但是,后來隨著偵破案件的增多,以及被捕人員的口供,公共租界巡捕房逐漸查明,中央特科使用的武器基本是從上海等地購買的。其中有部分武器甚至是國民黨軍隊看管軍火庫的士兵從軍火庫中偷出來,然后賣給中央特科的。
中央特科紅隊的培訓
報告中提及了“中共特務隊”的培訓情況,但從培訓內容來看,主要指的是紅隊的培訓。培訓內容包括:
一是上海城市概況。讓隊員熟悉公安局、政府部門、主要道路和車站位置等。
二是跟蹤訓練。主要練習跟蹤和識別目標人物。
三是熟悉旅館及出租房等的內部結構。
四是模擬演習。分成兩組,一組為觀摩組,另一組為行動組。演習前,觀摩組到預定行動地點就位,觀摩整個演習過程,積累經驗,查找不足。行動組完全模擬實戰,在規定時間規定地點實施行動。行動完成后迅速撤回之前預定地點。在整個演習期間,安排專人騎著自行車在行動地點附近來回騎行,對行動進行監視。
五是尋找指定地點。教官要求培訓人員去尋找某一旅館或某一出租屋等。培訓人員自行前去尋找,找到指定房屋后,要將周邊情況及居住人員的情況調查清楚,然后回來報告。尋找練習有時間限制,而且還會受到教官的監視。
六是“弄內斗爭”培訓。公共租界巡捕房在撰寫報告時對“弄內斗爭”培訓的具體情況還不掌握,僅是在1934年9月27日搜查到的一份文件中發現了“弄內斗爭”的有關文字,猜測可能它與利用上海狹小的弄堂開展懲處行動有關。

中央特科機關舊址
對特科成員的評價
報告中對特科成員的評價較高。“現在中共特務隊的成員大多是從紅軍中精心挑選的。他們是忠誠的共產主義信徒,堅信共產主義可以救中國,可以幫助自己實現政治和經濟上的自由,并且愿意為了實現共產主義去冒任何生命危險。中共特務隊成員清楚地知道自己早晚會被逮捕,但依然毫不畏懼地繼續冒險犯難。在對特務隊成員進行審訊時,他們的供述也充分體現出上述特點。如,當被問到某某是不是你殺的,他們會很痛快地回答,是就是,不是就是不是,但如果被問到你們的領導是誰,他們肯定不會透露任何姓名或住址,甚至會胡亂編個荒唐無稽的人物來糊弄你。1934年9月27日,我們逮捕了一批特務隊成員,相信他們與未歸案的特務隊成員肯定有聯系,但他們卻沒有招出任何一人,導致我們到今天也沒能抓到其他人。”
報告中提到的1934年9月27日逮捕的特務隊成員,其實就是鄺惠安、孟華庭、趙軒和祝金山等特科紅隊領導和成員。根據報告內容,可斷定上述人員在獄中是堅貞不屈的,沒有泄露任何秘密。
此外,報告中還提到,“中共特務隊中黨員數量很多,他們沒有私心,信仰堅定,能力突出”,“中共特務隊成員并不是從上海黨組織中補充的,而是來自紅軍,所以即便冒再大的危險,他們也會嚴格執行命令。與在滬共產黨員相比,除了建立蘇維埃政權這一中共黨員共同的目標外,紅隊成員與他們沒有任何相同點”。
報告有貶低上海黨組織的中共黨員之嫌。由于報告是站在公共租界巡捕房的立場,這種認知自然不具有客觀性。不過這也從側面證明,中央特科,特別是紅隊的成員并不是從上海黨組織中補充的,而是從各根據地的紅軍中補充的,他們都是信仰堅定、能力突出的紅軍戰士。
該篇報告的最初版本是英國人用英語撰寫的,后來由日本人從英語譯成日語。筆者在寫作此文時又將日語翻譯成中文。通常來說,一篇文章,每被翻譯一次,內部的細節就會丟失一部分。到目前為止,英文版報告還尚未發現。相信英文版報告會還原更多中央特科的細節,對我們研究中央特科的歷史將大有裨益。期待這一報告的英文版能夠早日重見天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