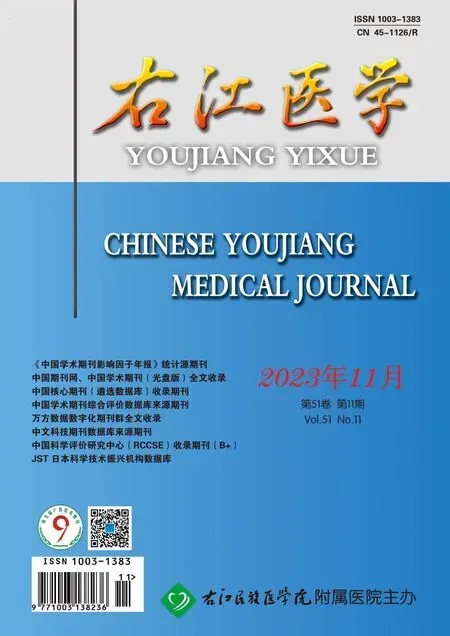RIPK1和RIPK3介導的壞死性凋亡在腦梗死中的研究進展
方子文,陳玉珍,蒙蘭青
(1.右江民族醫學院附屬醫院神經內科,廣西百色 533000;2.右江民族醫學院研究生學院,廣西百色 533000)
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人們發現了壞死性凋亡這種特殊的細胞死亡方式,受體相互作用蛋白激酶1(receptor interacting protein kinase 1,RIPK1)和RIPK3是介導壞死性凋亡最為關鍵的細胞內信號因子,當死亡受體與配體結合時,形成RIPK1/RIPK3/混合譜系激酶域樣蛋白(mixedlineage kinase domain-like protein,MLKL)復合物介導細胞發生壞死性凋亡,導致炎癥反應的產生。多項研究表明壞死性凋亡參與腦卒中、心肌再灌注損傷、腫瘤、免疫炎癥等病理機制的發生發展,近年來備受關注。本文就RIPK1和RIPK3介導壞死性凋亡在腦梗死中的研究進展進行闡述,分析RIPK1和RIPK3介導壞死性凋亡的分子通路機制是否有可能為腦缺血損傷提供可靠的治療靶點。
腦梗死是導致死亡和殘疾的主要原因,是嚴重威脅我國居民健康的重大公共衛生問題。腦供血中斷后發生的細胞死亡主要分為兩類:壞死和凋亡[1]。壞死被定義為一種細胞溶解形式的死亡,其特征是質膜完整性的快速喪失和促炎細胞內容物的釋放,是一種被動且不可調控的細胞死亡。與細胞壞死相反,細胞凋亡是一種caspase介導的細胞死亡形式,表現為細胞縮小、核固縮、碎裂,避免了質膜破裂免疫炎癥的產生,是受基因自主調控的細胞死亡。與細胞壞死不同,RIPK1和RIPK3介導的壞死性凋亡是一種由眾多細胞因子參與且受到高度調控的細胞死亡方式,其主要核心機制為:當caspase被抑制時,RIPK1和RIPK3磷酸化激活下游的MLKL,最終形成壞死小體引發細胞死亡[2]。這需要在特定的條件下刺激產生,如炎癥介質TNFα、IFNγ、內毒素和FasL等,通過TNFR1、TNFR2、IFNR、TLR3/4和Fas/TRAILR等信號通路均可啟動導致壞死性凋亡的信號級聯反應[3],其中TNF的促炎作用最強,且TNF是神經系統疾病中研究最廣的神經炎癥因子之一,因此將以TNF/TNFR1為例來闡明壞死性凋亡信號通路。
1 TNF/TNFR1啟動的壞死性凋亡
TNF與TNFR1細胞外部分的預配體組裝域相互作用,誘導TNFR1三聚體形成,與TNFR1相關死亡結構域蛋白(TRADD)、RIPK1、適配蛋白2和5(TRAF2、TRAF5)、泛素連接酶1和2(cIAP1、cIAP2)、LUBAC(由Sharpin、HOIL-1和HOIP組成的線性泛素鏈組裝復合體)結合組裝成復合體Ⅰ[4]。在復合體Ⅰ中,RIPK1受多種泛素化修飾,在調節RIPK1的活化中起著關鍵作用[5]。當TRAF2/5和cIAP1/2催化RIPK1的K63泛素化時,生長因子-β-活化激酶1(TAK1)被募集和激活,介導下游IκB激酶(IKKs)的活化,促進核因子-κB(NF-κB)通路的激活,細胞存活[6]。研究發現cIAP1和cIAP2缺乏會導致小鼠體重快速下降和炎癥發生,并伴有異常的細胞死亡[7]。因此cIAP1和cIAP2的缺乏使得RIPK1的泛素化受到抑制,加速了細胞凋亡和壞死的發生。
RIPK1的泛素化、去泛素化和磷酸化是三種不同的反應機制,其導致的結局也不同。CYLD是一種特異性去泛素化酶,可介導RIPK1的K63去泛素化,加快復合體Ⅱa形成過程。復合體Ⅱa主要包括pro-caspase-8、RIPK1、FADD和TRADD,當caspase-8未被抑制時,激活細胞發生凋亡[8]。cIAP、TAK1或NEMO表達被抑制時,復合體Ⅰ轉化為一個死亡觸發復合體Ⅱb,該復合體由FADD、pro-caspase-8、RIPK3和RIPK1組成。caspase-8活性不足或被抑制時,RIPK1通過RIPK同型相互作用基序(RHIM)與RIPK3相互作用使RIPK3磷酸化[9],激活下游MLKL、PGAM5和CaMKⅡ。大量研究表明MLKL的磷酸化是由RIPK3介導完成的,MLKL可在多個位點被RIPK3快速磷酸化,磷酸化的MLKL從胞質轉移至細胞膜上與磷脂酰肌醇磷酸(PIP)結合,MLKL寡聚形成通透性孔道[10-11],導致質膜破裂,最終發生壞死性凋亡。同時,磷酸化的MLKL也可使線粒體上形成一個復合物,該復合物由PGAM5l連接RIPK1-RIPK3-MLKL及PGAM5s,激活動力相關蛋白1(dynamin-related protein 1,DRP1),最終導致線粒體裂解,引發鈣超載、大量活性氧(ROS)簇生成。磷酸化的MLKL也可介導CaMKⅡ參與神經細胞ROS的過度生長以及線粒體通透性過渡孔(MPTP)的開放,細胞最終壞死引發炎癥。
2 RIPK1、RIPK3通過介導壞死性凋亡參與腦缺血損傷
RIPK1和RIPK3是絲氨酸/蘇氨酸蛋白激酶家族的成員,該家族成員的N端因其具有同源的激酶結構域而表現出類似的生物學功能[12],但因C端結構各有差異而表現出功能上的多樣性,其中以RIPK1和RIPK3的研究最為廣泛。腦卒中是腦血管疾病中最常見的一類疾病,分為缺血性腦卒中和出血性腦卒中,其中以缺血性腦卒中更為常見。研究如何通過干預神經元細胞的壞死和凋亡過程來提高患者預后、減少致殘率一直是研究者們努力的方向。
YANG等[13]采用光血栓形成模型誘導C57小鼠大腦皮層局灶性缺血,發現敲除RIPK3和MLKL可使缺血皮質中小膠質細胞/巨噬細胞的激活從M1型轉變為M2型,而M2型為缺血腦組織中的抗炎表型,此后也有研究證明了M1型巨噬細胞更容易以RIPK3激酶活性依賴的方式發生炎癥相關的細胞死亡,M1型巨噬細胞則正好相反[14]。該研究發現RIPK3和MLKL缺失對病變大小和運動功能恢復也有影響,皮層局灶性缺血后,野生型動物(WT)、RIPK3-/-和MLKL-/-小鼠的前肢活動立即減少到大約40%的基線水平,從第7天開始,與WT對照組相比,RIPK3-/-和MLKL-/-小鼠的前肢運動顯著恢復。足部故障試驗表明,缺血很快導致所有小鼠出現明顯的步態故障,在RIPK3-/-和MLKL-/-小鼠中,從第7天開始,足斷層步數顯著減少,不對稱指數顯著降低。以上實驗結果均表明阻斷RIPK3、MLKL可以減少腦缺血后神經元的損傷,并有助于功能恢復。
ZHANG等[15]建立大腦中動脈缺血再灌注(MCAO/R)模型模擬腦缺血再灌注損傷,在MCAO/R后24 h,小鼠梗死區域內檢測出不可溶性RIPK1、RIPK3和MLKL的水平升高。在MCAO/R模型的基礎上分別設計出兩種RIP1激酶死亡小鼠(Rip1K45A/K45A和Rip1Δ/Δ mice32)、RIP3缺乏小鼠(Rip3-/-小鼠)、MLKL缺陷小鼠(Mlkl-/-小鼠)進行研究,與WT小鼠相比,Rip1K45A/K45A小鼠和Rip1Δ/Δ mice 32小鼠、Rip3-/-小鼠、Mlkl-/-小鼠均可減輕細胞壞死和神經炎癥來保護MCAO/R后的腦損傷,這與壞死性凋亡通路是高度一致的,說明由RIPK1、RIPK3介導的壞死性凋亡參與了腦缺血再灌注后的腦損傷。在NAITO等[16]的一項研究中,僅靠局部腦缺血不足以上調小鼠MCAO模型中磷酸化的MLKL,上調P-MLKL需要腦缺血再灌注這一條件。因此MLKL磷酸化有可能參與介導腦缺血再灌注損傷后的細胞損傷,臨床上發現有一部分急性腦梗死患者腦血管再通后出現不同程度的腦損傷,但腦缺血再灌注損傷目前機制尚未完全明確,因此這一發現是有重大意義的。
3 RIPK1在腦梗死中的研究及其干預藥物
RIPK1是在細胞凋亡、壞死或存活中均起到調控作用的一個蛋白,已經成為治療腦卒中、神經退行性疾病、自身免疫疾病和炎癥疾病的治療靶點[16-18],且這一觀點得到了廣泛研究的支持。在腦血管疾病的研究中,Necrostatin-1(Nec-1)是應用最多、最廣的RIPK1抑制劑,Nec-1可阻斷RIPK1磷酸化的發生。在MCAO大鼠模型和OGD誘導的星形膠質細胞損傷模型中,ZHU等[19]發現反應性星形膠質細胞中RIPK1顯著升高,延遲給予RIPK1抑制劑Nec-1可下調膠質疤痕標志物,改善缺血性卒中誘導的壞死形態和神經功能缺損,并減少腦萎縮體積。此外,他們還發現敲低RIPK1可以減少星形膠質細胞的死亡和增殖,促進神經元軸突的生成。同時,活性星形膠質細胞中血管內皮生長因子D(VEGF-D)及其受體VEGFR-3均升高,這些結果表明RIPK1通過損害正常星形膠質細胞反應和增強星形膠質細胞VEGF-D/VEGFR-3信號通路參與星形膠質細胞病和膠質瘢痕的形成,因此,抑制RIPK1可減少星形膠質細胞增生和膠質疤痕的形成,促進腦功能恢復。
Nec-1是一種組蛋白甲基轉移酶(Dot1L)抑制劑,研究發現Dot1L被敲低或抑制的卒中模型小鼠中可逆轉缺血誘導的神經元凋亡,RIPK1 K63泛素化的增加和RIPK1/caspase 8復合物生成的減少可下調RIPK1依賴性的細胞凋亡,從而降低腦損傷的程度[20]。但Nec-1因其代謝穩定性差等缺點,未能獲得臨床應用,也已被證明不適合用于人類[21]。此外,有研究表明鋅指蛋白91(zinc finger protein 91,ZFP91)可以通過誘導RIPK1去泛素化、增加線粒體ROS的產生,從而促進細胞死亡[22]。卡泊芬凈是臨床上常用的一種抗真菌藥物,有研究發現卡泊芬凈可以通過上調Pellino3(一種泛素E3連接酶)使得RIPK1泛素化增加和壞死性凋亡相關蛋白下降,改善腦梗死后的神經功能損害。研究還發現其他藥物如川芎素、氯丙嗪和異丙嗪均可通過抑制RIPK1/RIPK3/MLKL通路改善梗死后的腦損傷[23-24]。
4 RIPK3在腦梗死中的研究及其干預藥物
RIPK3是一種可通過caspase-8進行調控的蛋白因子,當caspase-8活性不足或被抑制時,RIPK3被磷酸化激活下游效應蛋白MLKL引發壞死性凋亡。而當RIPK3被敲除時,只能由RIPK1介導引起細胞凋亡。因此,在腦缺血后發生的壞死性凋亡中,RIPK3作為介導腦缺血后炎癥反應中最具特異性的信號分子是極為關鍵的。研究發現當RIPK3表達下降時可通過抑制程序性細胞死亡來減少腦缺血性卒中小鼠模型中的腦梗死體積、神經功能缺損和神經元超微結構損傷,同時也進一步證實了RIPK3表達下調后穩定了線粒體膜電位,抑制了鈣內流的增加和ROS的產生,從而減少了炎癥的發生[25]。
通過找出RIPK3的特異性抑制劑有可能改善腦缺血后神經元的損傷和減少卒中后炎癥反應的發生,但RIPK3抑制劑的臨床應用一直滯后。最早一批抑制劑如GSK'840、GSK'843和GSK'872這些化合物可以高效結合并抑制RIPK3,但是當單獨使用時以濃度依賴性的方式誘導細胞凋亡[3]。此前達拉非尼(Dabrafenib)被證實是有效的高親和力RIPK3抑制劑[26],是通過競爭ATP結合位點抑制RIPK3的激酶活性,阻斷TNF誘導壞死性凋亡的發生,并且在人血管內皮細胞中得到驗證[27]。研究發現在栓塞誘導缺血性腦損傷1小時后的小鼠腹膜內給予Dabrafenib 10 mg/kg,第二天C57BL6小鼠的梗死灶面積明顯減小,同時TNF-α的上調明顯減弱,這表明Dabrafenib可能會減輕缺血性腦損傷后TNF-α誘導的壞死性途徑[28],但該藥物在腦卒中疾病中的臨床研究鮮有相關報道。研究者采用氧糖剝奪(OGD)和MCAO模型模擬缺血性腦卒中條件,發現zad-fmk(一種凋亡抑制劑)、GSK'872(RIPK3抑制劑)聯合治療可減輕腦細胞死亡和缺血性腦損傷[29]。
5 小結
在腦梗死中壞死性凋亡介導的腦損傷機制復雜且受到多方面的嚴密調控,其中以RIPK1/RIPK3/MLKL通路為代表介導的細胞壞死被視為核心部分,在該通路上的任何一個蛋白信號分子以及結合位點的不同程度改變都可引起不同的結局。在此基礎上發掘的一系列RIPK1、RIPK3等信號通路分子抑制劑可以在腦血管病中起到很好的神經保護作用,但在該通路中對治療腦梗死相關臨床實驗以及抑制劑的藥物毒性研究仍較少,未來仍需不斷深入挖掘相關分子作用機制及與其他壞死通路的關系網,以期研發能用于臨床上抑制壞死性凋亡的藥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