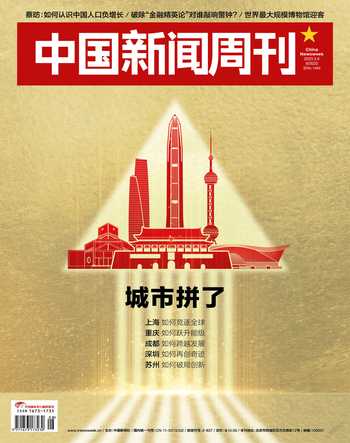“穩(wěn)經(jīng)濟”謀一年與謀五年應銜接
張文魁

圖/視覺中國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1月份顯著上調(diào)對2023年中國經(jīng)濟增速的預測,從去年秋天的4.4%調(diào)高到5.2%,反映了對中國優(yōu)化疫情管控政策之后的樂觀態(tài)度。但奇怪的是,在2月份發(fā)表的研究報告中,IMF下調(diào)了對中國未來五年經(jīng)濟增速的預測,不但把2024年的預測值下調(diào)到4.5%,而且把2025年和2026年預測值大幅下調(diào)了0.9個百分點,預計2026年中國經(jīng)濟增速首次降到4%以下,2027年則只有3.8%。
其理由是,中國經(jīng)濟增長將遭遇一些中長期逆風(headwinds),會導致生產(chǎn)率提升的放緩。IMF認為,未來中國經(jīng)濟增速在較大程度上依賴于如何提振較為疲弱的生產(chǎn)率,而一些重大的結(jié)構(gòu)性改革,譬如提高增長的普惠性,強化社保從而促進居民消費,延長退休年齡從而增加勞動力供給,推進國企改革從而縮小國有和民營部門的生產(chǎn)率差距,都非常有用。其測算表明,這些改革可以使中國未來五年的收入水平提高大約2.5個百分點。
IMF突然大幅下調(diào)對中國未來幾年經(jīng)濟增長的預期,與中國經(jīng)濟學界的預測存在較大差異。在中國經(jīng)濟學界中,很少有人預測2026年中國經(jīng)濟增速會降到4%以下。
很難說IMF的分析預測是否更加周密和準確,但顯然,其對中國經(jīng)濟增速預測值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中國結(jié)構(gòu)性改革推進的快慢。而這一點,卻與國內(nèi)許多專家的研究結(jié)果比較吻合。我曾就中國國企改革與經(jīng)濟增長之間的關(guān)系進行了量化分析,模擬結(jié)果顯示,即使實施比較溫和的國企改革,每年也可提高零點幾個百分點的經(jīng)濟增速,這比出臺刺激性的財政和貨幣政策、放任債務擴張和杠桿率上升,副作用和后遺癥要小得多。
如果僅僅盯著今年,IMF似乎比國內(nèi)許多專家對中國經(jīng)濟更樂觀。IMF很可能是對的,因為疫情管控措施實質(zhì)性解除之后,中國內(nèi)需支出的擴張,包括住戶部門在商品和服務消費方面的支出擴張,比許多專家預想的要更加有力。在生產(chǎn)端,恢復的情況截至目前也不錯。因此,即使從較有把握的態(tài)度出發(fā),中國今年經(jīng)濟增速應該定為5%。
去年底的中央經(jīng)濟工作會議提出,要突出做好“穩(wěn)增長、穩(wěn)就業(yè)、穩(wěn)物價”工作。中央把“穩(wěn)增長”擺在“三穩(wěn)”首位,很可能并不只是著眼今年這一年,而是著眼更長遠。二十大就提出,要推動經(jīng)濟實現(xiàn)質(zhì)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把“穩(wěn)增長”擺在首位,應該就體現(xiàn)了二十大提出的質(zhì)與量互促的戰(zhàn)略思維。因此,我們需要從戰(zhàn)略視野、中長期視角,來認識、來落實“穩(wěn)增長”要求,也就是說,“穩(wěn)增長”不僅僅是對今年經(jīng)濟工作的要求,更是對未來五年甚至十幾年經(jīng)濟工作的要求。
為什么需要這樣認識和理解“穩(wěn)增長”?二十大深入闡釋了中國式現(xiàn)代化的基本概念和推進方略,以及各階段的重要目標。到2035年的目標是,中國將基本實現(xiàn)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經(jīng)濟實力、科技實力、綜合國力大幅躍升,人均國內(nèi)生產(chǎn)總值達到中等發(fā)達國家水平。中等發(fā)達國家盡管不是一個嚴格的學術(shù)概念,IMF等國際組織也沒有相關(guān)衡量標準,而且國內(nèi)學者對此也有不一致的認識,但仍然可以認為,中國人均國內(nèi)生產(chǎn)總值(人均GDP)于2035年達到中等發(fā)達國家水平,是一個比較明確的指標。我做的一些研究顯示:如果按新冠疫情前的2019年的情形來看,將當年人均GDP為2萬美元左右的國家視為中等發(fā)達國家,是比較合適的;而如果將世界上一些主要經(jīng)濟體未來十余年的通脹率和匯率變化的情景考慮進來,到2035年,中等發(fā)達國家的人均GDP基準線,將達3萬美元左右甚至更高。
人均3萬美元左右,并不只是一個紙上的數(shù)字,它實際上是人民生活水平和國家綜合實力的核算匯總,也是社會生產(chǎn)力的真實體現(xiàn),并反映了高質(zhì)量發(fā)展的自然結(jié)果。中國2022年人均GDP約為1.27萬美元,與2035年的3萬美元左右還有很大距離,這非常直觀地解釋了中央為何把“穩(wěn)增長”擺在如此重要的位置。
從2023年到2035年有13年時間,但未來五年將決定著實現(xiàn)2035年現(xiàn)代化目標的基本盤。如果在這五年里,中國經(jīng)濟增速如IMF預測的那樣滑落到4%以下,那么五年后人均GDP可能只有1.7萬美元左右;而且,由于存在趨勢性因素,一旦“下掉”,便難“上翹”,此后經(jīng)濟增速便很難回到4%以上,并有可能繼續(xù)滑落到2030年之后的3%左右或更低,那么到2035年,人均GDP就難以達到中等發(fā)達國家水平。
只有在這五年里,把中國經(jīng)濟增速穩(wěn)在明顯高于4%、力爭保持在5%以上的水平,才可能使人均GDP在這五年內(nèi)超過1.8萬美元或更高,才可能使五年后以及2030年后的經(jīng)濟增長,建立在較高速度的基礎(chǔ)之上,那時即便出現(xiàn)規(guī)律性的自然下滑,也可以保持在4%左右或略低一些的水平,從而能夠如期實現(xiàn)2035年基本實現(xiàn)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的目標。
如果這五年的基本盤比較牢固,那么第一步,中國將邁入世界銀行所劃定的高收入經(jīng)濟體行列。世界銀行2022年公布的高收入經(jīng)濟體門檻線為13205美元,預計2023年還將因全球通脹率高企而顯著上調(diào),如果中國近幾年的經(jīng)濟增速能夠穩(wěn)定在5%以上或左右,大約兩三年內(nèi)即可邁入高收入行列。而第二步,就是要往人均GDP 2萬美元水平靠近,要進入高收入安全區(qū)。國際經(jīng)驗教訓方面的研究顯示,即使一些國家邁入或觸碰高收入經(jīng)濟體門檻,也有可能再掉下來,譬如俄羅斯和土耳其,都曾在2012年前后邁入或觸碰高收入門檻,但后來卻“降級”為中等收入國家。我個人將高于高收入門檻線1/3以上的區(qū)域,設定為高收入安全區(qū)。中國經(jīng)濟只要基本盤穩(wěn)固,就可以在兩三年之后仍然保持一定的增長動能,力爭在2030年前后進入高收入安全區(qū)。
只要這兩步走得穩(wěn),中國實現(xiàn)2035年現(xiàn)代化目標就大有希望,到本世紀中葉就一定能夠建成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強國。
中國需要將5%以上的經(jīng)濟增速維持得盡量長一些,最好能從今年開始連續(xù)保持五年,即實現(xiàn)“雙5”增長。那么,中國有可能實現(xiàn)“雙5”增長嗎?從已經(jīng)發(fā)布的許多機構(gòu)的預測分析報告來看,似乎不太可能。
但是,進行經(jīng)濟增速的分析預測,決不能忽視重大政策對經(jīng)濟增速的抑制或提振作用;在中國,尤其要考慮重大改革對經(jīng)濟增速的影響。我們不能靜態(tài)地、機械地分析潛在增速。如果看不到中國民間蘊藏的巨大增長潛力,就不能正確地認識中國的發(fā)展前景。
過去幾十年的發(fā)展歷程證明,只要大力推進市場化改革、制度型開放,只要充分釋放企業(yè)家精神和民間活力,經(jīng)濟增長就會比較有力。事實上,過去幾十年的歷史中,一些研究機構(gòu),包括非常著名的研究機構(gòu),對中國經(jīng)濟增速的預測,就曾被改革開放所釋放的巨大增長動能“打臉”。
譬如,在上世紀末,許多國內(nèi)和國際機構(gòu)對中國“十五”時期經(jīng)濟增速的預測值大都在6%~7%,而實際上,由于在本世紀初中國加入WTO釋放出巨大的開放紅利,加之上世紀末國企改革釋放了巨大的改革紅利,“十五”期間平均增速達到了9.5%,“十一五”前兩年均超過了10%。所以十六大的時候,中央作出了一個戰(zhàn)略判斷:綜管全局,21世紀頭二十年,對中國來說是一個必須緊緊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zhàn)略機遇期。現(xiàn)在回頭再看,中央的判斷以及相應的發(fā)展部署,是何等正確。
因此,只要我們下決心深化改革、擴大開放,中國不但可以把今年經(jīng)濟增速保持在5%以上,而且確有可能把這個增速維持5年。“雙5”增長不但有必要,而且有可能。現(xiàn)在的關(guān)鍵,是要把謀劃一年經(jīng)濟增長與謀劃五年經(jīng)濟增長結(jié)合起來,并扎實地實施下去。
實際上,去年底的中央經(jīng)濟工作會議就提出,要更好統(tǒng)籌當前和長遠,既要做好當前工作,又要為今后發(fā)展做好銜接。中央明確提出這個“銜接”,就屬于戰(zhàn)略性、前瞻性思維。在實際工作中,應該從戰(zhàn)略高度看待“穩(wěn)增長”,應該把謀一年與謀五年相銜接,才能把政策資源在一年和五年之間進行合理分配,才能避免過于重視如何把今年的經(jīng)濟增速搞上去,而忽視如何把五年的增長動能放出來。
如果確立了“銜接”的戰(zhàn)略部署,似乎不應該把過多的精力、過多的資源、過多的政策放在今年,因為根據(jù)目前的形勢和趨勢來看,不需要過多的精力、資源、政策投入,譬如并不需要顯著增加各類債券發(fā)行和貨幣投放規(guī)模,更不需要為了快上重大項目而放松環(huán)評程序和標準,即可以實現(xiàn)5%以上的經(jīng)濟增速。IMF把今年中國經(jīng)濟增速上調(diào)0.8個百分點,很可能是因為看到了這一點。
如果我們把注意力過度集中于不太需要發(fā)力的今年,而不去籌劃和實施一兩年甚至兩三年之后才能見效的重大改革與開放政策,那么“雙5”增長就難以實現(xiàn)。只有從今年就著手謀劃“雙5”增長,才能避免中國經(jīng)濟增速在五年內(nèi)滑到4%以下,才能筑牢中國經(jīng)濟基本盤。
謀一年與謀五年相銜接,實現(xiàn)“雙5”增長,比把今年增速搞到5%以上,要難得多。“雙5”增長部署,在很大程度上是市場化改革、制度型開放部署。
中央對市場化改革、制度型開放非常重視,二十大報告有很多相關(guān)論述。二十大報告以及去年底的中央經(jīng)濟工作會議,都強調(diào)要把實施擴大內(nèi)需戰(zhàn)略同深化供給側(cè)改革有機結(jié)合起來,就應該成為“雙5”增長的重要抓手。
推進一些重要的結(jié)構(gòu)性改革,不但可以理順諸多重大關(guān)系,還可以直接為需求擴張?zhí)峁┯辛χ巍6翢o疑問,內(nèi)需擴張,特別是住戶部門消費需求的擴張,是“雙5”增長的重要基礎(chǔ)。要擴大居民消費,雖然實施稅費減免、發(fā)放消費券、創(chuàng)造新消費場景等舉措可以起到短期刺激作用,但從中長期來看,根本還是在于提高居民可預期的可支配收入。如果只為了今年保增長,政策上似乎應該繼續(xù)采取上述短期舉措以刺激消費,但為著謀一年與謀五年相銜接,由于去年消費基數(shù)低,今年反彈動能較強,當下這一年的消費增長并沒多大問題,此后幾年的消費增長才是大問題。
因此,應著眼于中長期如何提高居民可預期的可支配收入。這就需要大力推進結(jié)構(gòu)性改革。構(gòu)建更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的營商環(huán)境,特別是營造一個讓廣大中小微企業(yè)有穩(wěn)定感、有安全感、有自主感的營商環(huán)境,從而有效地增加居民就業(yè)和收入,有效地提振有支付能力的需求。
當然,就擴大內(nèi)需而言,還需要進一步調(diào)整和強化社會保障,并探索形成居民可支配收入持續(xù)增長、勞動者報酬持續(xù)提高的良性機制,而這些良性機制的形成,也涉及到企業(yè)部門的生產(chǎn)率能否得到持續(xù)提升、企業(yè)部門投資與債務的螺旋式上升能否受到節(jié)制、政府部門與企業(yè)部門之間的關(guān)系能否得到改進,等等。

2月25日,廣西欽州港自動化集裝箱碼頭,塔吊在運送集裝箱。圖/新華
總之,整個企業(yè)部門的改革,以及企業(yè)部門與政府部門之間關(guān)系的改革,至關(guān)重要。這無疑需要進一步推進國企的市場化改革。國企市場化改革的深化,很可能是開啟許多重大改革的樞紐。國企市場化改革所能帶來的正面效果,并不完全限于IMF在前述研究報告中所指出的縮小生產(chǎn)率差距(close the productivity gap)。盡管國企產(chǎn)出占中國GDP的比重并不太高(約為30%左右),但在許多重要產(chǎn)業(yè)中占有主導地位,對市場的開放性、競爭的公平性、企業(yè)進入和退出的順暢性,都有非常重大的影響。
深化國企市場化改革,有助于糾正資源錯配和市場扭曲,有助于非國有企業(yè)在大致公平競爭的環(huán)境中發(fā)展壯大,有助于企業(yè)家精神的發(fā)揚光大。中央早已指出,國家要保證各種所有制經(jīng)濟平等使用資源要素、公開公平公正參與市場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去年底的中央經(jīng)濟工作會議提出,要從制度和法律上把對國企民企平等對待的要求落下來。
國企改革,不僅僅是國有部門自己的事,也是關(guān)乎整個市場化改革和公平競爭環(huán)境的事。
更進一步,國企市場化改革能否繼續(xù)推進,也涉及到中國既有經(jīng)濟增長模式能否順利轉(zhuǎn)換。在過去若干年里,中國國企債務有了比較明顯的新擴張,特別是一些地方的國企工具化、國資擔保化的傾向較為嚴重,使得政府與企業(yè)之間的財務邊界更加缺乏清晰性和透明度,蘊藏了較大的宏觀風險。
中國經(jīng)濟增長模式為什么難以擺脫債務推動?中國不同企業(yè)為什么有著不同的流動性策略和態(tài)度?企業(yè)部門的流動性策略和態(tài)度所導致的宏觀結(jié)果是什么?也許宏觀經(jīng)濟學家只關(guān)心宏觀指標,而并不在乎和關(guān)注這些問題,但一些經(jīng)濟學家,譬如諾貝爾經(jīng)濟學獎得主本特·霍姆斯特朗和讓·梯若爾等人從微觀經(jīng)濟學視角得到的研究結(jié)論,足以讓我們更加認識到微觀部門改革對于宏觀經(jīng)濟的意義。如果忽視企業(yè)部門改革,僅從宏觀經(jīng)濟角度來尋求增長模式轉(zhuǎn)換的方案,是難以如愿以償?shù)摹?/p>
實現(xiàn)“雙5”增長,還需要我們堅持走開放的道路,特別是要貫徹落實中央提出的制度型開放。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經(jīng)濟增長奇跡,與對外開放、融入全球化密切相關(guān)。而且,開放已經(jīng)成為一種生活方式。如果中國與外部世界走向“隱形脫鉤”。那就不僅僅會影響到中國的產(chǎn)業(yè)鏈、供應鏈、創(chuàng)新鏈的開放性和全球化,不僅僅會影響到中國未來的經(jīng)濟增速,而且也會影響到其他許多方面。
中央指出,要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要積極推動加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伙伴關(guān)系協(xié)定(CPTPP)和數(shù)字經(jīng)濟伙伴關(guān)系協(xié)定(DEPA)等高標準經(jīng)貿(mào)協(xié)定,并要主動對照相關(guān)規(guī)則、規(guī)制、管理、標準來深化國內(nèi)相關(guān)領(lǐng)域改革。只要我們更加有力地推進這些工作,相信中國的制度型開放會取得新進展,而“雙5”增長也會有更好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