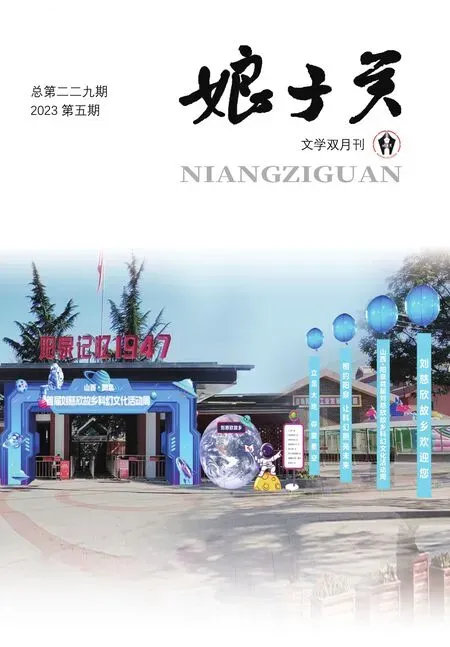創(chuàng)作談
◇推石
余華曾說(shuō):“寫(xiě)作使我擁有了兩個(gè)人生,現(xiàn)實(shí)的和虛構(gòu)的,它們的關(guān)系就像是健康和疾病,當(dāng)一個(gè)強(qiáng)大起來(lái)時(shí),另一個(gè)必然會(huì)衰落下去。于是,當(dāng)我現(xiàn)實(shí)的人生越來(lái)越貧乏之時(shí),我虛構(gòu)的人生已經(jīng)異常豐富了。”
于我而言,貧乏與豐富如立在海平面上的天平兩端,當(dāng)偶爾飛過(guò)的海鷗在其中一端駐足時(shí),另一端便會(huì)沉入海水中,浸泡在陽(yáng)光逐漸褪去溫度的場(chǎng)域內(nèi)。而情緒則毫無(wú)限制地游離在汪洋之中,檢索著記憶的每一個(gè)角落。記憶是一種有分量的幻象,只有通過(guò)表達(dá)才能將這種虛幻的分量帶入現(xiàn)實(shí),將私人的情緒轉(zhuǎn)化為可以被分享與閱讀的實(shí)體,而我則選擇用文字來(lái)承載它。我不知道文字究竟要如何引領(lǐng)人生,也不知道最終走向何方。二十多歲的時(shí)光與閱歷或許太過(guò)單薄,即便張愛(ài)玲在與我同樣的年齡便發(fā)表了代表她創(chuàng)作最高成就的系列作品,余華也在不到三十歲時(shí)便躋身先鋒作家之列。天賦是生來(lái)的賜物,自己沒(méi)有倒也不必過(guò)分艷羨他人,特別是與站在人類(lèi)巔峰的那些明珠相較。我拿著自己人生的劇本手足無(wú)措的同時(shí)也在思考著,忽然覺(jué)得此刻的迷茫也不過(guò)是刻在時(shí)間長(zhǎng)廊里的一段痕跡而已。
當(dāng)我懷著強(qiáng)烈的意愿想要將心中壓抑著的情緒抒發(fā)出來(lái)時(shí),卻發(fā)現(xiàn)情緒的黏稠阻塞了自己闡述的道路。也難怪魯迅先生說(shuō)“感情正烈的時(shí)候,不宜作詩(shī),否則鋒芒太露,能把‘詩(shī)美’殺掉”。唯有等候情緒褪去,冷冽的筆鋒才能敏銳地篆刻出回憶里的些許模樣。其實(shí)回憶也與情緒一般,是一種幻象,同樣會(huì)隨著時(shí)間流逝變換著顏色和質(zhì)感。那么,究竟什么才是永恒呢?我給出的答案是文字,起碼在有限的人生里,曾經(jīng)留下的文字算得上是一種長(zhǎng)存了。哪怕作品經(jīng)過(guò)刪改,那也不過(guò)是在已有的痕跡之上再添一道罷了。
閱讀使人經(jīng)歷別樣的人生與情感,寫(xiě)作則是將那些或?qū)儆谧约夯驅(qū)儆谒说慕?jīng)歷與情緒,通過(guò)一種宛如錯(cuò)覺(jué)的描述轉(zhuǎn)達(dá)給更多的人。如果說(shuō)寫(xiě)作是一種不準(zhǔn)確的表達(dá),那么閱讀就更是一種誤讀了。正如偶然能給人帶來(lái)意外的驚喜與驚嚇,那么橫在作者與讀者之間的這種偏差,或許就是屬于文學(xué)的某種獨(dú)特性質(zhì)與魅力吧。
最后引用史鐵生在為曾文寂作序時(shí)轉(zhuǎn)述的友人所說(shuō):“人生一世,最后會(huì)發(fā)現(xiàn)名利財(cái)富都是空,人能夠擁有的只有生命本身。但生命的流逝使得它難以實(shí)現(xiàn)超越時(shí)段的自我確認(rèn),唯有文字能夠擔(dān)當(dāng)此任,宣告生命曾經(jīng)在場(chǎ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