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白期”刑法司法解釋的適用
文/洪凌嘯 葉惟烽
刑法修正案對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的罪狀修正,將法定刑升格,雖然不會影響刑法條文的整體適用,但導致“空白期”的出現,新舊司法解釋適用的問題存在爭論。基于此,本文重點探討了刑法司法解釋填補刑法修正案條文空白的溯及力。
刑法修正案(十一)于2021年3月1日起正式施行。刑法修正案(十一)將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條修改為:“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或者變相吸收公眾存款,擾亂金融秩序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或者單處罰金;數額巨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數額特別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處罰金。”自此,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增設了“數額特別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處罰金”的法定刑。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非法集資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的決定》于2022年3月1日起正式施行,增加“非法吸收或者變相吸收公眾存款,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條規定的‘數額特別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一)非法吸收或者變相吸收公眾存款數額在5000萬元以上的;(二)非法吸收或者變相吸收公眾存款對象5000人以上的;(三)非法吸收或者變相吸收公眾存款,給存款人造成直接經濟損失數額在2500萬元以上的。非法吸收或者變相吸收公眾存款數額在2500萬元以上或者給存款人造成直接經濟損失數額在1500萬元以上,同時具有本解釋第三條第二款第三項情節的,應當認定為‘其他特別嚴重情節’”。自此,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的“數額特別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有了具體規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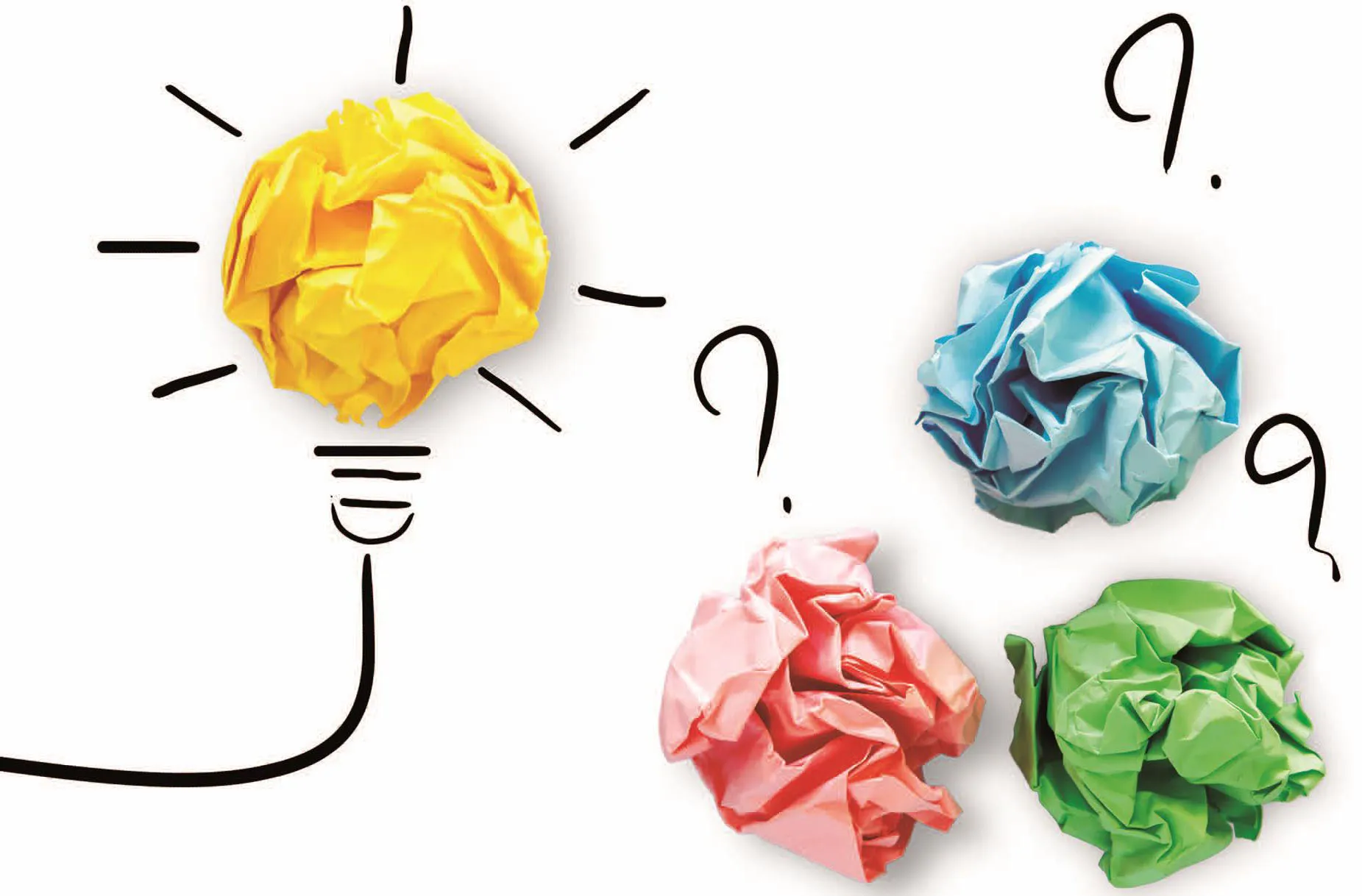
新舊司法解釋適用問題思考
如何適用量刑區間
以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數額在5000萬元以上的為例,若行為時間在2021年3月1日之前,則適用舊刑法,量刑區間為3—10年;若行為時間在2022年3月1日之后的,則適用新刑法,量刑區間為10—15年。那么,若行為時間發生在2021年3月1日之后,2022年3月1日前完畢的,其量刑區間為3—10年還是10—15年?這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
值得注意的是,2010年制定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非法集資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針對的是刑法修正案(十一)之前的非法集資類案件。當時因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沒有10年以上的法定刑,所以舊司法解釋沒有“數額特別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的具體規定。
關于適用量刑區間的爭論,主要存在兩種觀點:
一種觀點認為,應當適用10—15年的量刑區間。根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適用刑事司法解釋時間效力問題的規定》(以下簡稱《關于適用刑事司法解釋時間效力問題的規定》)第二條“對于司法解釋實施前發生的行為,行為時沒有相關司法解釋,司法解釋施行后尚未處理或者正在處理的案件,依照司法解釋的規定辦理”的規定,對于新的司法解釋施行后尚未處理或者正在處理的案件可以直接適用。
另一種觀點認為,應當適用3—10年的量刑區間。根據《關于適用刑事司法解釋時間效力問題的規定》第三條規定:“對于新的司法解釋實施前發生的行為,行為時已有相關司法解釋,依照行為時的司法解釋辦理,但適用新的司法解釋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利的,適用新的司法解釋”,新的司法解釋只是對舊的司法解釋的修改,并不表示行為時沒有相關司法解釋,因此應當適用舊的司法解釋。
關于溯及力的討論
討論溯及力,實際上解決的是選擇適用司法解釋的問題,而選擇時的判斷標準應當是遵循“從舊兼從輕”的原則。在此原則下,對于條文內容的理解、解讀要從有利于被告人的角度出發,在量刑時考慮到量刑平衡等實踐問題,最大可能地“有利”“從輕”。本文同意前述的第二種觀點,具體理由如下:
從規定上看,《關于適用刑事司法解釋時間效力問題的規定》第二條規定在該問題中沒有適用的空間。
《關于適用刑事司法解釋時間效力問題的規定》第二條規定依照新的司法解釋的規定辦理案件,前提條件是行為時尚無相關司法解釋對其進行規定。而第三條則明確,如果行為發生在新的司法解釋施行之前的,則應當適用舊的司法解釋,除非適用新的司法解釋會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更有利的情況。《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非法集資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的決定》,是對原有司法解釋的進一步修改和完善,從其名稱中判斷亦可得知,行為在此前已有司法解釋,故而第二條在所討論的問題中,并沒有適用的空間。
產生爭議的主要原因在于,“行為時有無相關司法解釋”中對“行為時”的“行為”的理解有出入。持第一種觀點的人認為,非法集資時,“數額特別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的行為沒有相關的司法解釋,因此應當適用第二條。行為,指受思想支配而表現出來的外表活動。討論的問題中,行為指的是非法集資的行為,而非法集資數額達到5000萬元是此行為帶來的結果。將數額的多少理解為行為,顯然偏離了人們的常識,屬于違背罪行法定原則的限制解釋。
從法理上看,基于“從舊兼從輕”的原則也不應當適用《關于適用刑事司法解釋時間效力問題的規定》的第二條規定。
從《關于適用刑事司法解釋時間效力問題的規定》第三條內容中“適用新的司法解釋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利的,適用新的司法解釋”可知,《關于適用刑事司法解釋時間效力問題的規定》始終遵循一個原則,即司法解釋的新舊適用問題,不能突破刑法所確認的“從舊兼從輕”的量刑基本原則,應考慮對當事人是否有利的情況進行適用。基于刑法司法解釋所存在的擴張性與滯后性特征,刑法司法解釋對其生效之前發生的、未經處理或者處于處理中的行為同樣應遵循“從舊兼從輕”的溯及力原則。對于行為時沒有相關刑法司法解釋的情形,法官在裁判時,應與行為時適用司法解釋及法律的一般做法進行“是否有利”的比較,對行為人作出有利的選擇。當出現新舊刑法及新舊司法解釋交叉并行的情形時,應以“分層式”的判斷規則,在刑法規范條文與刑法司法解釋兩個層面上分別適用“從舊兼從輕”原則。“從舊兼從輕”是罪刑法定原則的基本內容與根本精神的高度統一,根據該原則,適用舊司法解釋,對所討論問題中的涉案人員及單位有利,因此不應當適用修改后的司法解釋。
從實踐上看,不適用《關于適用刑事司法解釋時間效力問題的規定》的第二條規定才能做到量刑均衡。
對于發生在2021年3月1日與2022年3月1日期間,同時又是在此期間被處理完畢的行為,因修改后的司法解釋未出臺,對其量刑只能按照3—10年的區間來進行。相較于行為發生在同時間段,但是在司法解釋出臺后被處理的,對其量刑適用10—15年的區間,顯然使在同一刑法規范下的同一行為得到輕重不一的量刑結果,量刑不平衡。量刑,是人民法院依據刑法確定對被告人是否判處刑罰、判處何種刑罰以及判處多重刑罰的司法活動。對共同犯罪中被告人,對同類行為的被告人量刑時,從橫向比較、從縱向比較都應做到量刑的均衡。量刑不均衡,將破壞法制的統一,喪失法律的公正性。因此,不適用《關于適用刑事司法解釋時間效力問題的規定》的第二條規定才能做到量刑的均衡,做到罪責刑相適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