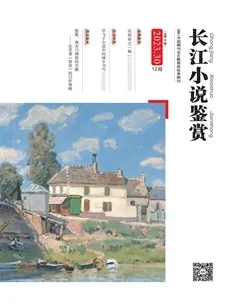有島武郎《親子》中的父子關系深剖
[摘? 要] 有島武郎(1878-1923年) 是日本明治、大正時期的小說家,白樺派的代表作家之一。有島清楚地認識到小說創作與自身的關系,他致力于以自己的思想和感情為基礎創作小說,執拗地追求藝術理想。在自己與他人、他人與社會的關系中,有島最關心的是人本身,尊重人的個性與自由。無論是《一個女人》的主人公葉子,還是《該隱的后裔》的主人公廣岡,抑或是《親子》的主人公“他”,他們苦苦追求、堅守的都是獨特的自我。在這篇具有自傳性質的短篇小說《親子》中,陷入倫理困境的“他”,在與父親的交流過程中,經歷了從反抗到理解的過程,在理性意志下做出了倫理選擇,重新找回了內心的自我。作者本人也通過《親子》解決了與父親之間的糾葛。
[關鍵詞] 有島武郎? 《親子》? 父子關系? 倫理
[中圖分類號] I106.4? ? ? [文獻標識碼] A? ? ? ?[文章編號] 2097-2881(2023)30-0044-04
《親子》是有島武郎自殺前兩個月創作的小說,與志賀直哉的《和解》一樣,《親子》也是一部帶有自傳性質的作品。有島從創作之初就關注倫理問題,以家庭這個最小的倫理組織為窗口,通過家族內部的矛盾討論日本社會整體的倫理問題。而對于一切倫理關系中的父子關系的關注,貫穿了有島的創作始終。兒子們雖以各種的方式逃離了父親,但這種逃避始終是一種自我欺騙。因為兒子對父親的感情深度早就超出了自己能控制的范圍。
《親子》主要講兒子陪父親去農場辦事時發生的事。人物、故事都很簡單,但有島真正著重描寫的是兒子的心理活動。通過兒子或“他”到達農場后的一系列心理活動,讀者可以捕捉到兒子對父親看法的改變,也可以捕捉到兒子從服從轉向反抗,然后與父親達成某種程度的和解的心理軌跡。小說中的這位父親與有島武郎的父親、兒子與有島武郎之間在性格上有重合之處,有島武郎通過《親子》解決了與父親的父子問題,繼而探索獨立的自我。
一、父子沖突與倫理關系
倫理環境也稱為倫理語言環境,是指文學作品所處的歷史空間[1]。文學倫理學批評強調回到歷史的倫理現場,站在當時的倫理立場來解釋文學作品,找出文學產生的客觀倫理原因,解釋它是如何成立的,分析作品中影響社會事件和人物命運的倫理因素,從倫理角度解釋事件、人物等問題,從歷史的角度進行道德評價。因此,文學倫理學批評具有歷史相對主義的特征。回到有島武郎生活的時代,理解《親子》中描寫的父子沖突將變得不那么困難。
小說中“他”自出生以來,就經常目睹父親在生意場上討價還價的場面。父親曾長期當官,后踏入實業界,主要擔任銀行和公司的審計員,工作能力被眾人稱贊。“他”對這位工作能力很強的父親既害怕又尊敬。在經歷了這種混雜著敬畏和尊敬的復雜沖擊很久之后,兒子所有的心理活動,歸結成了一句“不知怎么的,對父親的反抗情緒一下子涌上心頭”。然而,與其說兒子想要反抗父親這個人,不如說“他”想要反抗父親所象征的社會秩序。站在兒子的立場上,父親因為生下了“他”,所以對“他”有養育之恩和管控權。兒子對父親要報恩,要言聽計從。父親將兒子置于一種無法反抗的禁錮之中。結果,兒子失去了自主選擇權,只能一步步變得無能。“但是,兒子的無能也存在于父親身上。”父親的能干突出了兒子的無能,但如果兒子仍舊一味服從父親,兒子就會變得更加無能[2]。
小說中的“他”想要反抗的是父親代表的資產階級。在看到即使辛苦勞作卻依然一貧如洗的農民時,作為農場主的父親認為:“如果他們變成有錢人的話,那么就不會再有人頂著烈日繼續在地里干活吧。”在有島看來,資本主義壟斷了衣食住行等一切資源,留給無產階級的只有勞動自由權,同樣的,小說中的父親也壟斷了農場的一切資源,只留給農民勞動自由權。
“他”雖出生在資產階級家庭中,卻對父親這種言論深惡痛絕,作為本該繼承家中產業的長子,“他”選擇以“五年都不與家里親近”來反抗父親。“他”不希望被資本主義思想浸染,對資產階級壓迫農民這件事更感憤怒,“他”渴望沒有謊言、沒有壓迫、充滿人性主義光輝的社會。然而在陪同父親處理農場事務期間,時隔五年,“他”再一次切身體會到了農民對于資產階級壓迫的無奈。在面對父親的強勢詢問時,誠實正直的農場管理人早田一五一十地將農場情況上報,但父親卻始終以一種“防備的、攻擊的”姿態來審問他;對畢恭畢敬,甚至要下跪的早田母親,父親既冷淡又嚴格。父親似乎沒有憐憫之心。在這樣的場景下,與父親同行的“他”感到自己像是“占領了敵地,并且以勝利者的姿態來巡視這塊土地的敵軍將士”,而農民也在“他”面前有意無意地說些在父親面前不敢說的話,如“連年歉收,真是沒辦法啊”“是啊,夏收不好就算了,秋收也是這副模樣”等,這使“他”對父親的厭惡感進一步增加。最終,父子二人所代表的兩種思想發生了激烈碰撞。
在現實生活中,有島武郎的父親不僅是銀行董事,還兼任日本郵船、日本鐵路的董事。身為長子的有島自幼接受劍法、騎馬、弓箭等最為嚴格的教育[3],除此之外,父親還讓他學習歐美文化和儒家思想。長大后,有島也不能決定自己的學業、婚姻和工作。在父親面前,有島沒有發言權,沒有自己的想法,他是個對父親充滿敬畏的兒子。另一方面,有了父親的經濟支持,有島才能接受良好的教育,所以有島不得不感激父親。
二、兒子面臨的道德困境
日本歷史上,以天皇世襲制、將軍世襲制沒有改變,世襲制在統治權力、財產等方面長期存在,因此這種階層成為貫穿社會各個領域的重要倫理規范[2]。此外,血親之間也有尊卑關系。受儒家思想的影響,父子關系類似君主與臣下的關系;另一方面,君臣一般的父子關系中也有溫情的存在,家族內部的尊卑關系因此更為穩固。這樣一來,父親自然會左右兒子的言行,主宰兒子的生活。也就是說,兒子的一舉一動都離不開父親的指揮。因此,《親子》的主人公“他”作為父親的繼承人被動地和父親來到農場,在父親處理農場事務時只能袖手旁觀。“他”的袖手旁觀說明了“他”服從于父親。因為“他”既沒有權力干預父親的工作,也沒有權力左右父親的決定。也就是說,“他”陷入了道德困境。
根據文學倫理學批評,倫理困境是文學作品中倫理混亂所帶來的無法解決的矛盾和沖突[1]。“他”面對的是自古以來在日本就確定了的尊卑有別的父子關系,即使在快速的近代化進程中,這種關系也沒有本質上的改變。《親子》中,小說真正的主人公是一位曾經身處官場,現在需要管理好農場的農場主父親,兒子作為敘述者,起到推動情節、控制故事節奏的作用,整部小說從兒子的視角展開故事,以兒子的心理活動為主要內容。但是,“他”所看到的、所想到的、所害怕的、所擔心的都是父親,兒子的身體和心理、情緒的起伏、憤怒、無能、膽怯、孤獨等都與父親相關。在與農場承包者矢部進行最后談判的時候,“他”為了緩和一下一觸即發的緊張氣氛,提出“早已經過了晚飯時間了,要不晚飯后再商議吧”,卻遭到了父親嚴厲批評。父親認為“他”的無能給農場工作的勝利交接產生了不好的影響,對“他”的人格進行了“極度侮辱”[4]。在談判勝利后,矢部不甘地離開,此時農場里只剩下父子二人,而父親似乎忘了在矢部面前“好像在批評十一二歲的小孩”一樣將“他”狠狠數落的事,于是在一陣不愉快的沉默后,“他”感到“心里好像被什么堵著一般,今天要是不痛痛快快地說出來,肯定是睡不著的”。“用農民的貧瘠生活換來的農場富饒,這樣的農場經營哪里算得上成功?這樣對農民太過分了!不這樣農場就沒有利益可圖的話,那農場經營這份工作本來就是資本主義給農民撒的一個謊!”“他”一股腦兒地把一直以來積壓的不滿和憤怒都發泄了出來:
“你對這樣的情況看不慣嗎?”
“看不慣!”“我看得慣。”
“他”憤怒到了極點。“我可看不出來。”
父親此時也暴怒:“你就是這么跟父親說話的嗎?……你也是五十步笑百步,你自己生活過嗎?知道這世上的規則嗎?你有能拿得出手的成績嗎?”
“他”被噎得說不出話。一直以來強調要反抗資本主義的“他”,卻是在父親的支持下,才能一直不用考慮生計問題。
“你想要考慮農民的感受吧。其實,我小時候也是生活在貧苦農民家中,跟母親兩個人相依為命,農民生活是什么樣我最是清楚的。我付出了比別人多一倍的努力,才有了今天。至于為什么讓你繼承農場,是因為有了農場至少你和弟弟妹妹們不用挨餓。”父親的語氣變得柔和:“我這個年紀再處理這些事,別人半天就夠了,可我得一整天。”
“他”不知道說什么,想著今晚就要跟父親分個黑白的那股子勁兒也被深深壓了下去。
父母必須為了孩子盡心工作,才能給孩子提供好的生活環境。如果父母將孩子的養育工作交給社會,那么父母對孩子的愛會更為單純。小說中的“他”面臨的也正是這種困境。“他”想要反抗父親,反抗父親身后的資本主義,自己卻已身處其中,因為父親一直以來的資金支持,自己才有精力關心農民的生活,而父親也是這制度下的受害者。
三、從倫理選擇中尋求自我
陷入倫理困境的兒子為了追求自我,不得不做出倫理選擇。倫理選擇是文學倫理學批評的核心概念,面對兩個或兩個以上的道德選擇,選擇不同,結果也就不同,每個選項都具有倫理價值[1]。在父親與監工談判成功后,他完成了在農場的工作,又恢復了從東京來后就未曾展露過的笑臉,并喝起酒來。然而,“他”對父親滿腹的反感使“他”不愿意看父親一眼,因為父親在剝削佃農們。
那天晚上,在自由意志的支配下,“他”像一個完全不同的人似的,大膽吐露對父親的不滿。在文學倫理學批評中,“斯芬克斯因子”由“獸性因子”和“人性因子”構成,這兩種因子有機地結合在一起,前者受后者控制,于是人就有了倫理意識。“斯芬克斯因子”是理解文學作品中的人物形象的重要概念,其中,“自由意志”和“理性意志”分別是獸性因子和人性因子的意志體現。自由意志主要來源于人類的動物本能,主要表現形式是人類的不同的欲望,如性欲、食欲等人類基本的生理需求和心理動態。在與父親的互動中,兒子不是唯一一個在與父親的矛盾中受到傷害的人,父親也同樣受到了傷害,“他”看到了父親的憤怒、辛勞和疲憊,“他”理解了父親的孤獨,自己也陷入了更深的孤獨之中。理性意志控制了自由意志,兒子做出了倫理選擇:站在父親的立場上,改變自己的看法。在父親管理農場的過程中,兒子反復證明了自己的無能,同時“他”最初的憤怒和沮喪也消失了,意識到了父親也是同樣的受害者。就像兒子一樣,拋開父尊子卑的等級觀念,父親也不知道應該如何與兒子相處,更不知道如何表達對兒子的關心和愛護,實際上父親得不到兒子的支持。兒子逐漸明白了這一點,在敬畏父親的同時,也對父親產生了憐憫和同情。“他”第一次感受到了父親身處此制度下的無奈與悲哀,與父親產生了共鳴。看到父親的背影,“他”突然感到一陣深深的寂寞。在小說的結尾,作者寫道,“不可思議的感激——那似乎只有血緣關系才會產生的濃烈的、寂寞的感激卻使他的眼淚奪眶而出”。“他”渴望回到單純血緣意義上的親子關系。
日本文學評論家本多秋五在解讀《親子》中父子關系時說道:“明治以來描寫父子關系的文章中,《親子》是絕對不可忽視的存在。”[5]在有島武郎為數不多的私小說中,《親子》可以說是代表性的作品[3],與同為以父子關系為主線的志賀直哉的中篇小說《大津順吉》及《一個男人和她姐姐的死》相比,《親子》中站父親的立場進行的一系列心理活動描寫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而這也是有著小說之神之稱的志賀直哉在他的小說中有所忽視的部分。
再從他本人的作品來看,雖說從寫給失去母親的三個孩子的書信《給幼小者》中已經展現出他內心的矛盾,但作為絕筆的《親子》卻更能反映出他自身核心的矛盾所在。他以往的作品中,主人公真誠、熱情,敢于大膽追求想要的東西[6],可以說是徹頭徹尾的現實主義者。而他本人卻是一位理想主義者,他在這樣矛盾的思想中度過了短暫一生。《親子》是他在選擇結束生命之前,最真切地直面這種矛盾心理的一部作品。
四、結語
《親子》是有島武郎以農場經營為題所作的唯一一部作品,也是他自殺之前的最后一部作品,包含了作者最深刻的思想矛盾。小說中,“他”在意識到血緣的尊卑秩序后,從反抗父親到理解父親,這說明無論“他”對自由的理解有多少偏見和誤解,也依然無法擺脫對自由的尊敬和向往,“他”便把被放逐的自由放回心中,但也只找回基本的自我[7]。
參考文獻
[1] 聶珍釗.文學倫理學批評導論[M].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
[2] 李俄憲.日本文學的倫理學批評[M].北京大學出版社,2020.
[3] 譚杉杉.親子觀視域中的有島武郎小說研究[D].武漢:華中師范大學,2010.
[4] 外尾登志美.『親子』- 有島武郎の挽歌[J].日本近代文學,1980(27).
[5] 有島武郎.有島武郎集[M].東京:新潮社,1962.
[6] 姚繼中,林茜茜.日本文學理念(17)新理想主義文學——「白樺派」[J].日語知識,2011(5).
[7] 劉立善.有島武郎文藝思想中的自我[J].日語學習與研究,1997(1).
(責任編輯? 陸曉璇)
作者簡介:魏文敏,遼寧大學外國語學院,研究方向為日語語言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