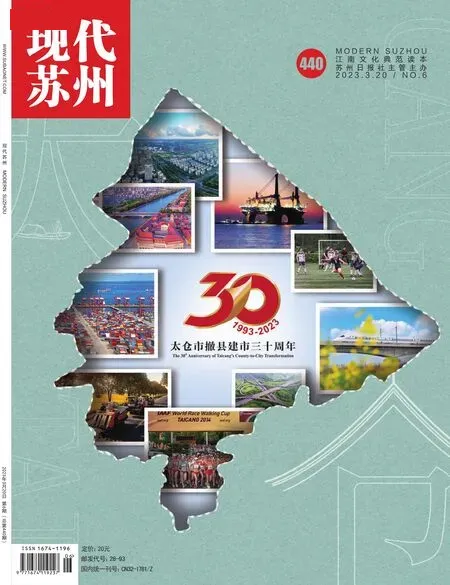顧艷龍:一路伴書香,一書一心境
記者 王嬌蓉
“泡書房是慰勞自己的一種形式。”江蘇省作家協會會員、蘇州創元集團職工筆會會長顧艷龍說。現代社會競爭激烈,因此人們頗喜休閑,休憩的方式可能會因知識結構、年齡、個人偏好等因素影響而差異頗大,這些慰勞方式只要適合自己就好,而他基本上以泡書房為主。對他而言,書房不僅是休憩的空間,還是與無數靈魂對話的空間。
與書為伴,走過流金歲月
人生在不同階段,大都會以不同的身份示人,其中較多的身份標簽是社會的、外在的,而顧艷龍對自己認可的“身份”則更為私人。在一篇文章中,他曾自稱為“讀書愛好者”,然而改稿時對這個詞又產生了懷疑:“一直以來,我感到喜歡讀書是一種自然而然的行為,自稱為‘愛好’似乎有些做作的成分了。此外,本人還有點文字緣,庶幾也可稱為‘寫作愛好者’吧。”
這位“讀書愛好者”的成長經歷,可以說是一路與書為伴的。在他看來,書房代表了一種生存方式、一種生活態度。
20世紀60年代中葉,顧艷龍出生在蘇北沿海的某個小鎮,初中畢業后即參加工作,建立家庭前,他一直住單位的單身宿舍,那時他所住的宿舍一般由值班室、倉庫之類改造而成,基本都很局促。因為不斷增加的圖書,顧艷龍從家里搬來一個木箱,后來又購置了一個書柜,這才為自己心愛的各類書籍找到了棲身之所。

書房不僅是休憩的空間,還是與無數靈魂對話的空間
當時,他基本上將自己晚上以及節假日的業余時間都泡在了書里,同時也在業余寫一些新詩,他回憶說:“似乎大多寫作者年輕時都這樣。”那個時期,宿舍就是顧艷龍的書房,除了上班,他這樣靠讀書生存著,也在書籍和寫作中獲得了無限的快樂。
談及自己的生活態度,顧艷龍認為,每個人在一生中的不同重要階段,都會對生活有不同看法,“參差乃生命之美”,對他這樣性格比較內向的人來說,無論何時,即使書房十分簡陋,只要保持心境的自在、泰然,有一冊書在手,似乎就可以忘掉一切煩惱。
筆耕不輟,記錄歲月如歌
在書房,顧艷龍做的最多的事情就是看書、寫作以及收拾、整理書籍。
作為一名新詩作者,他最喜歡的書籍有泰戈爾的《新月集》、惠特曼的《草葉集》、顧城的詩集等。從事文學創作以來,他曾出版詩集《風景線》,報告文學集《黃海兒女》,在全國各類報刊發表幾百首新詩。年輕時,顧艷龍的寫作主要定位于新詩,隨著年齡增長,他的創作愛好也有所轉移。
“年輕時寫作詩歌,可能主要還是靠荷爾蒙和激情吧。中年以后,再寫作新詩時就覺得自身突破比較難,當然,我也不是全部放棄詩歌,持續創作的同時,我將創作重心逐漸轉換到了文史寫作上。”
2006年,顧艷龍來到蘇州工作,這也促成了他創作重心轉移的一大因素。顧艷龍說,蘇州的文史底蘊豐厚,一些外地來蘇工作的朋友也在進行這些方面寫作,加上自己向來對此也是感興趣的,幾方面因素交織作用之下,讓他對文史寫作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來蘇州后,顧艷龍購買了王稼句的各種文史散文集,并到舊書市場淘到了《蘇州史志》等文史資料,以及各類與蘇州或吳地相關的書。蘇大李峰教授的《蘇州歷代人物大辭典》,黃惲介紹民國時期蘇州人物的書都包含在內。
通過書籍,顧艷龍了解到了范煙橋在吳江創辦同南社時的社友印水心,這位民國學者、鹽城老鄉,曾編輯《吳江鄉土志》,晚年又寓居蘇州直到逝世,與蘇州有千絲萬縷的關系。同在異鄉為異客,寫作和閱讀讓他在書房里完成了與前輩的對談。
為了通過文史寫作,挖掘并致敬這位鄉賢,顧艷龍曾寫過兩篇關于印水心的文章并在《姑蘇晚報》發表,目前,他正在編寫《印水心文鈔》,同時也做一些與蘇州及家鄉鹽城兩地有關的文化人物的研究、采訪與寫作。
理想書房,營造精神居所
顧艷龍的書房實際上是個十幾平米的客臥,擺放了一張床、一個書架、一張電腦桌,用他的話說“十分寒磣”。這小小的客臥里擺放了大約幾千本書,其中有一大半不得不打包藏在床下,也可稱得上汗牛充棟了。不過作為愛書之人,顧艷龍常常覺得讓愛書不見天日,十分對不住它們。
因此在他理想的書房中,首先就要盡可能收集全自己喜愛的類型圖書,電子書也不妨同時使用,閱讀或寫作參考兩不誤。
其次,他希望能為自己營造一個舒適的讀書及寫作空間。上海巴金故居的常務副館長周立民有本書名叫《躺著讀書》,引起了不少書友的共鳴。想來自在讀書之樂大概就是隨意讀書吧。將喜愛的讀書全部上架,且觸手可及;一張漂亮的書桌、幾株綠植必不可少;朋友送的字畫也可裝裱上墻,還可以給書房起個名字……因為住在唯亭,顧艷龍曾經想將自己的書房起名為“草鞋山南居”。
“我無大志向,達到這個標準也就夠了。”他說。
可能是怕自己的底牌被人識破,過去有種說法是“書房不可示人”,但顧艷龍覺得書房恰恰是適合朋友間進行清談的場所,與志同道合的朋友在書房里,聽聽電腦里播放的古琴之音,品茗交流讀書之樂、寫作之樂,“聽君一席話,也會勝讀半年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