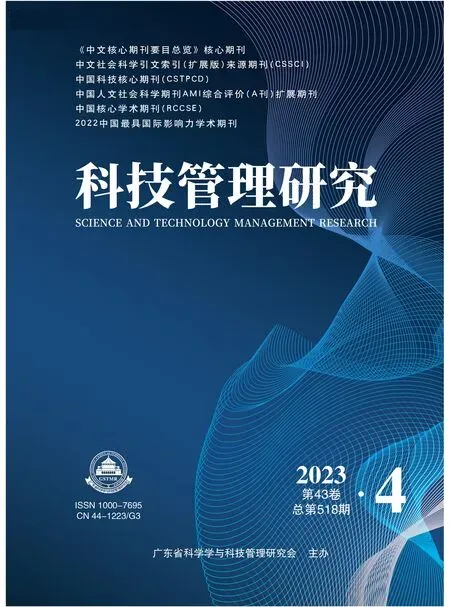制造商與供應商合作時機對創新績效的影響
祝明偉,李隨成
(1.西安理工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陜西西安 710054;2.西安交通大學經濟與金融學院,陜西西安 710065)
1 問題的提出
面對科技創新困境,尤其是“卡脖子”技術難題,提高突破關鍵核心技術能力是企業必經之路。構建創新生態、協同創新發展是當前企業技術創新的新范式[1]。制造業是擔負科技創新的主體,而制造業越來越倚重供應商提升技術創新能力[2],如Sabahi等[3]、Pulles 等[4]的研究均表明,供應商擁有企業所需的獨特創新價值資源,有效發掘與利用供應商資源為企業創新提供動力,另一方面供應商利用專長探明用戶需求,為制造業企業提供更加符合市場動態需求的創造性方案,進而提升創新績效。因此,有效地構建與管理供應商合作關系成為制造業企業成功的關鍵[5]。
現有關于制造商與供應商的研究,總體上可概括為“尋找關系—鞏固關系—共創價值”的研究框架。其中,尋找關系方面主要研究如何搜尋更為合適的供應商,如Li 等[6]、李隨成等[7]研究指出建立洞察能力是尋找供應商的關鍵;鞏固關系是研究供應商的主流話題,包括信任機制建立、利益分配準則、平衡三元(多元)關系、加深合作程度等,如李勃等[8]、楊偉等[9]、武夢超等[10]、李隨成等[11]、李娜等[12]的研究;共創價值主要探討在平等互利的前提下如何最大程度利用供應商價值,如Siaw 等[13]的研究。盡管上述研究框架不斷得到豐富與完善,但存在如下不足:首先,多為關注供應商的合作關系、合作績效、合作能力,忽視了合作時機這一重要因素。事實上,何時選擇正確的供應商以確保創新活動延續,從時間維度破解制造業創新難題是提升企業創新能力亟須解決的問題。其次,雖然部分研究強調了合作時機的重要性,但多數采用二分法將合作時機割裂分為早期與晚期,如Smirnova 等[14]的研究,但創新是一項持續的過程性活動,傳統的二分法難以厘清何時與供應商合作才能產生最大價值。最后,合作時機對創新績效的影響受情境因素限制,依據知識基礎觀,必要的知識是降低風險、提升創新能力重要因素,面對復雜變動的環境,及時獲取、掌握新穎性知識是企業持續獲取創新能力的重要源泉,如Grant[15]、榮雪云等[16]的研究,因此新穎性知識的整合與應用是影響合作時機與創新績效的情境因素;此外,Scandura[17]建議從技術與市場兩個維度分類研究知識新穎性,因此有必要探明技術與市場知識新穎性作用下合作時機對創新績效的影響關系會發生怎樣的變化。
綜上分析,本研究從制造商視角出發,以制造商與供應商合作時機何時影響創新績效為研究內容,同時依據知識基礎觀探明技術知識新穎性與市場知識新穎性在合作時機對創新績效中發揮的情境作用,為制造商選取供應商合作伙伴提供時間維度的理論支持與實踐指導。
2 理論回顧與研究假設
2.1 制造商與供應商合作時機
創新競爭的日益激烈和外部環境的不斷變化迫使企業擴大對外部資源和合作伙伴關系的使用[2],而如Sabahi 等[3]、Pulles 等[4]研究表明,與供應商建立長期、穩固、信任的關系是制造業企業獲取創新資源、緩解競爭壓力的關鍵要素。Smirnova等[14]、Walsh 等[18]的研究指出,為搜尋關鍵供應商,進一步激發供應商創新潛能,制造商不僅應關注加強與供應商建立合作關系、增進信任水平,更需要關注何時引入供應商,即重視與供應商的合作時機。依據資源基礎觀,企業若想在長期競爭中保持優勢,難以復制替代的獨特性資源是必須的[19]。而“時機”作為一種稀有的、寶貴的時間維度資源,亦是企業搶占競爭高地的關鍵資源[20],即使兩家企業擁有完全相同的資源,選擇最佳時機引入和調度供應商等外部資源會區分領先者和跟隨者。
制造商與供應商的合作時機指,制造商在創新過程的某一階段或某一時間段激活與供應商的合作關系。Hempelmann 等[21]將合作時機按照創新過程分為早期(包括創意階段、初步創造階段等)和晚期(包括市場化、商業化等)兩類。鑒于現有研究多數側重于創新的具體階段,基于創新全過程的合作時機研究仍較缺乏,且僅將合作時機分為早期和晚期割裂了創新周期的全過程,難以準確反映合作的具體時間,因此,借鑒霍國慶等[22]、Cooper[23]的研究,采用創新生命周期的階段劃分,將合作時機分為創意想法產生、技術孵化、產品開發、產品推廣、商業化等階段,以此探索制造商與供應商在何時合作會產生更高的創新效益。
2.2 制造商與供應商合作時機和創新績效
與供應商建立穩定關系是制造商提升創新績效的重要因素,現有研究認為合作時機(早期和晚期)的選擇是發揮網絡效應的前提。具體而言,制造商在新產品啟動階段,由于對新技術的高需求以及需建立容忍試錯的環境,因此,獲取關鍵資源、引入外部知識成為提升新產品績效的重要因素[24]。早期激活供應商參與,為創新提供關鍵性知識、新市場動態以及直接資源支持,塑造新產品開發方向,因此早期階段引入供應商參與創新是必要的。另一方面,將創新成果推向市場階段,制造商難以精準把控市場需求、細分市場差異性以及競爭對手結構,而下游供應商更為熟知市場動向,為新產品順利推向市場出謀劃策有助于刺激創新銷售增長、創造客戶價值[18],因此在晚期階段供應商的參與亦是關鍵的。
雖然現有研究證實了制造商與供應商早期和晚期兩類合作時機對創新績效的重要作用,但早期或晚期與供應商合作亦存在負面效應。研發項目早期的知識隱性度和復雜性高[25],因此合作變得困難。一方面,知識隱性度限制了企業清晰表達或傳播知識的能力,從而使得供應商誤解或部分理解制造商意圖,增加交易成本[26];另一方面,從機會主義入手,前期新想法或技術雛形尚未及時受到保護,隱性與復雜性會使知識容易被他人盜用[27]。關于晚期合作,此階段新技術較為成熟、且多輪市場測試也部分證明了新技術的市場可行性[28]。雖然與供應商的合作可以繼續提升新產品的技術性能與市場屬性,但提升的程度較低,相對于合作交易成本,未能給制造商帶來顯著的創新價值[29]。
因此,本研究認為,制造商與供應商合作時機定在中期(如技術孵化、產品開發、產品推廣等)更能推動創新績效的提升。一方面,新產品的技術原理性知識已在早期階段攻克,逐步轉向技術放大與大規模產品開發階段,此時制造商更多需要大型設備、工藝流程、程序性知識等支持[25],在該階段與供應商建立關系,借助供應商對專業零件建構的流程知識與技術能力破解新產品批量開發的難題[30];另一方面,此階段新產品初步過渡至市場,檢測新產品的市場接受度,而下游供應商所提供的市場新需求、競爭對手產品動態等市場信息為制造商改進新產品方向、賦能市場屬性提供了方向[31]。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如下假設:
H1:制造商與供應商合作時機與創新績效呈現倒“U”型關系,即相對于創新的早期與晚期階段,中期階段與供應商的合作更能促進制造商創新績效的提升。
2.3 知識新穎性的調節作用
雖然制造商與供應商合作時機對創新績效具有影響,但合作時機并非一成不變的,受相應情境因素的影響,企業會放寬或緊縮與供應商合作的時機,因此,探究合作時機對創新績效的邊界條件尤為重要。依據知識基礎觀,通常創新是一項風險性高、過程復雜且模糊的活動,對企業的技術創新能力和知識應用能力是極大挑戰[4]。Grant[15]、榮雪云等[16]、Wagner 等[32]認為,獲取充足、必要或特定領域獨有的知識是企業提升創新能力、降低創新風險的重要軟因素,尤其在企業面臨全新或顛覆式創新過程時,新穎性知識的識別、攝入與消化是加快創新步伐的關鍵。隨著產品創新所涉及的技術和市場復雜性日益增加,企業可能無法利用自己的內部知識開發新產品,需要加強與外部供應商的合作,進而有效破解技術開發與市場引入相關難題,因此,知識新穎性是影響合作時機與創新績效的關鍵情境因素[33]。依據Scandura[17]的建議,從技術與市場兩個方向探究知識新穎性在制造商與供應商合作時機與創新績效的調節作用,這是因為:首先,技術知識與市場知識出現于創新不同階段,技術知識通常應用于研發或干中學階段,而市場知識通常側重于新產品市場測試或分銷渠道建設等方面,表明創建技術知識和市場知識的項目完成標準可能不同[34];其次,在實踐中,兩種類型的知識存在于企業不同部門,有必要從技術與市場兩個方向研究知識新穎性所發揮的作用[35]。
(1)技術知識新穎性的調節作用。由于核心技術、關鍵制造工藝等技術知識的快速變化,企業需要將最新的技術知識融入到新產品中,以確保新產品獲取絕對競爭優勢[34]。若企業忽視新知識的攝取,僅僅利用現有的技術知識設計、開發和制造新產品,則會陷入與其現有技術知識相關的熟悉度陷阱,但企業難以在短期內獲取、吸收與消化新穎的技術知識以及對高端技術新穎性知識的潛在缺乏都可能阻礙企業成功應對新技術的高度復雜性、風險和不確定性[36]。為獲取外部新技術知識,制造商會加快與供應商合作步伐,通過與供應商建立合作關系,快速熟悉技術發展趨勢、技術熟化因素等關鍵性知識,為新產品開發解決技術障礙[14]。反之,若制造商沒有提前或延長與供應商的合作,則在短時期內難以消化關鍵性技術知識,新舊技術在新產品開發項目中的碰撞增加了創新失敗的可能性[26]。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如下假設:
H2:技術知識新穎性對制造商與供應商的合作時機和創新績效之間的關系存在正向調節效應,即技術知識新穎性會使制造商與供應商的合作時機和創新績效之間的倒“U”型關系變得更為平坦。
(2)市場知識新穎性的調節作用。隨著市場需求快速更新,企業需要熟悉客戶需求以及潛在競爭對手的市場信息才能保證其擁有的市場知識和新產品所需市場知識保持一致性[33]。同樣,企業僅僅將成熟產品的客戶性質與細分市場目標復制于新產品推廣,則會鎖定其使用現有的市場知識推銷新產品[25],不利于新產品市場化。因此,提前與供應商建立聯系、延長合作時間,通過合作獲取下游用戶的新市場知識,包括創建或獲得新的市場推廣部門、職責和例行程序系統[36],熟悉新產品推廣時所需的溝通策略、分銷渠道和營銷技巧,有助于加速新產品商業化進程。反之,若制造商未能提前或延長與供應商的合作關系,限制了制造商成功識別、吸收和利用他們可能在新市場中接觸到的任何新興的和潛在有用的市場知識的能力,難以準確把控市場知識的變動程度[37];即使意識到市場變動的趨勢和方向,也難以在短期改進新產品市場屬性,進而阻礙新產品性能提升。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如下假設:
H3:市場知識新穎性對于制造商與供應商的合作時機和創新績效之間的關系存在正向調節效應,即市場知識新穎性會使制造商與供應商的合作時機與創新績效之間的倒“U”型關系變得更為平坦。
綜上,提出本研究的理論框架如圖1 所示。

圖1 理論框架
3 研究設計
3.1 量表設計
首先,初步編制量表。對于創新績效、技術知識新穎性、市場知識新穎性均采用國內外成熟量表,而對制造商與供應商合作時機則參考國外量表進行編制,由此形成初始量表。其次,邀請新產品開發、供應商創新等相關領域的7名教授和博士進行訪談,深化對上述概念的認知,同時邀請其填寫量表,對量表的語境、斷句與關鍵詞進行修訂。隨后,與浙江吉利控股集團有限公司、陜西國德電氣制造有限公司、西京電氣總公司進行初步訪談,邀請有關中層管理者填寫問卷,獲取一手直觀數據,依據其所提的建議改進問卷題項。最后,通過問卷星發放78份問卷,對問卷結果進行預試分析并形成正式量表。除控制變量外,所有變量均采用五點量表進行測量。具體測量如下:
(1)解釋變量。依據創新生命周期,將制造商與供應商合作時機改編為一個題項,即“我們主要在下列階段與供應商合作:1=想法產生,2=技術孵化,3=產品開發,4=產品推廣,5=商業化”。
(2)被解釋變量。創新績效的題項借鑒Bell[38]的量表,包括新產品推廣的時間、新產品質量與收益成本等因素;同時,結合李隨成等[11]的量表以貼切制造業企業情境,形成包括“與同行業相比,我們常在行業內率先推出新產品或服務”等6 個題項。
(3)調節變量。技術知識與市場知識新穎性方面,借鑒Mahr 等[39]和Ozer 等[36]的相關量表,結合國內情境修訂更改。其中,技術知識新穎性包括“我們在開發新產品時很大程度上應用到與以往不同的技術知識”等3 個題項;市場知識新穎性包括“我們在開發新產品時搜尋了新用戶可能存在的需求”等3 個題項。
(4)控制變量。考慮企業性質、地域與企業規模等因素對創新績效產生影響,結合Ozer 等[36]與李娜等[12]的建議,選取企業性質、企業地域、企業規模、關系長度與行業性質作為控制變量。其中,企業性質設置為“1=國有企業,2=民營企業,3=三資企業”;地域1)設置為“1=東部企業,2=中部企業,3=西部企業”;企業規模設置為“1=<100 人,2=100~<300 人,3=300~<500 人,4=≥500 人”;關系長度設置為“1=<3 年,2=3 年~<5 年,3=5年~<10 年,4=≥10 年”;行業類型設置為“1=汽車制造,2=電子制造,3=儀表設備,4=交通運輸,5=食品飲料,6=機械設備,7=金屬制造”。
3.2 樣本選擇和數據收集
大樣本調查時間集中于2022 年1 月12 日至2022 年3 月15 日,選取較為成熟的制造行業,包括浙江吉利控股集團有限公司、多弗國際控股集團有限公司、杭州海康威視數字技術股份有限公司、陜西國德電氣制造有限公司等制造業企業,在浙江、陜西、北京、上海、湖北、四川等13 個省份的代表性制造業企業發放問卷。由于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疫情原因,采用線上問卷方式進行發放,共發放896份問卷,收回832 份問卷,回收率為92.86%。為確保回收的問卷質量,加強對問卷的篩選,邀請2 名碩士研究生共同參與問卷的篩選,剔除填寫時間少于60 s、不屬于制造業、填寫數字過于集中或存在“Z”型分布、統一類型題項前后矛盾明顯的問卷,并采用SPSS21.0 軟件查找問卷極端值。最終得到有效問卷472 份,有效率為56.73%。
4 實證分析
4.1 描述性統計
相關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見表1。可以看出,制造商主要在技術孵化、產品開發與產品推廣階段選擇與供應商合作,按照創新生命周期理論,初步印證制造商主要集中在創新中期和供應商合作。

表1 變量描述性統計結果
4.2 信效度分析
由于解釋變量制造商與供應商合作時機為單維度題項,因此僅對創新績效、技術知識新穎性與市場知識新穎性進行信效度分析。如表2 所示,所有變量的克隆巴赫系數(Cronbach's Alpha)與組合信度(CR)值均大于0.7,因此量表具有較好的信度。效度方面,所有變量的KMO 值均大于0.50,標準化載荷量均大于0.60,SMC 值均大于0.36,AVE 值均大于0.50,均符合效度標準,因此變量具有較好的信效度。

表2 變量信效度檢驗結果
4.3 相關分析
如表3 所示,所有變量的相關系數低于0.8,說明變量間不存在顯著的共線性問題。此外,創新績效、技術知識新穎性、市場知識新穎性開根的AVE 值大于其對應的其余行列的相關系數,表明變量的選取具有良好的區分效度。

表3 變量相關分析結果
4.4 同源偏差檢驗
為避免樣本出現同源偏差,采用以下3 種方法進行檢驗。首先,問卷設置與發放方面,打散原有題目編號重新排序,以防止受訪者猜測題意;同時對創新績效和技術知識新穎性設置共2道反向題目,以檢測問卷質量。其次,采用Harman 單因素檢驗法進行檢驗,將制造商與供應商合作時機、創新績效、技術知識新穎性與市場知識新穎性的所有題項同時放入主成分分析中,得出第一個旋轉因子的變異量為22.39%,小于30%的臨界值。最后,采用Amos 21.0 軟件進行潛在誤差變量控制法檢驗,對比將所有題項放置在一個維度前后的變化,結果顯示模型適配指標變化輕微,GFI、NFI、IFI、RMSEA 等指標變化量均小于0.03,表明問卷數據不存在同源偏差問題。
4.5 假設檢驗
采用多元回歸分析進行假設驗證。在進行回歸分析前,對所有控制變量、解釋變量、被解釋變量以及調節變量進行中心化處理,以避免驗證倒“U”型和調節關系時共線性問題,結果顯示所有方程的VIF 值均小于5,即不存在多重共線性問題。表4 中,模型1 僅包括控制變量;模型2 加入了制造商與供應商合作時機進行回歸分析;模型3 加入了制造商與供應商合作時機平方項;在主效應模型的基礎上分別加入調節變量知識新穎性和市場知識新穎性,及其和制造商與供應商合作時機的交互項,得到模型4 和模型5。結果顯示制造商與供應商合作時機的平方項對創新績效存在顯著的負向關系,即制造商與供應商合作時 機和創新績效呈倒“U”型關系(β=-0.238,P<0.05),H1得到證實;制造商與供應商合作時機的平方和技術知識新穎性的交互項對創新績效存在顯著的正向關系(β=0.105,P<0.05),證明了技術知識新穎性的調節效應,H2得到證實;制造商與供應商合作時機的平方和市場知識新穎性的交互項對創新績效有顯著的正向關系(β=0.120,P<0.05),證明了市場知識新穎性的調節效應,H3得到證實。

表4 制造商與供應商合作時機對創新績效的多元回歸分析結果
技術知識新穎性與市場知識新穎性對制造商與供應商合作時機和創新績效倒“U”型關系間的調節效應如圖2 所示。

圖2 技術知識新穎性與市場知識新穎性對制造商與供應商合作時機和創新績效的調節效應
5 結論與啟示
5.1 研究結論
(1)依據創新生命周期,制造商更多選擇在技術孵化、產品開發與產品推廣階段激活與供應商合作關系。由此可以看出,相對于創新的早期和晚期階段,企業通常選擇在中期與供應商建立聯系。鑒于早期技術項目知識的獨占性以及晚期市場化大范圍推廣,在創新中期與供應商建立合作是實踐中企業的首選方式。
(2)制造商與供應商合作時機和創新績效之間存在倒“U”型關系,證實了相對于創新的早期與晚期階段,中期階段與供應商的合作更能促進制造商創新績效提升的觀點。這表明,中期階段選擇與供應商合作,避免早期知識泄露或晚期合作成本較高的風險,利用供應商在工藝開發、零件選型、市場需求等資源加速提升新產品大規模開發,最有助于企業創新績效的提升。
(3)技術知識新穎性與市場知識新穎性在制造商與供應商合作時機和創新績效之間存在正向調節效應,即技術知識新穎性與市場知識新穎性會使制造商與供應商合作時機和創新績效之間的倒“U”型關系變得更為平坦。這表明,為降低失敗風險、精準掌握核心技術,制造商需擴大知識基,提前或延長與供應商合作,強化知識獲取與整合,以滿足新產品技術特征與市場需求。
5.2 相關啟示
以上結論對制造業企業有以下實踐啟示:
(1)注重尋求與鞏固外部合作的同時也要關注合作時機。企業不僅僅要注重搜尋供應商、強化與供應商的信任機制建設,同時也要強調合作時機的重要性,根據具體產品的生命周期做好提前布局,規劃新產品各階段的資源需求、技術障礙與失敗風險,在不同時間點選取破解當前問題、提供穩定資源的供應商作為戰略聯盟伙伴。因此,時間是企業創新的重要維度,應與結構維度、關系維度等同等重視,并納入相關機制建設。
(2)針對不同創新階段,企業應制定差異化的供應商激活與引入策略,尤其注重在新產品技術孵化、產品開發與產品推廣階段的合作關系建立。在新產品開發中期,企業往往在技術開發與市場導入方面均出現難題,及時引入供應商破解技術與市場難題成為關鍵。因此,企業仍需厘清創新項目的時間階段,動態觀測創新項目的管理、資源、技術與市場因素,同時加入一些非正式、更加彈性的合作方式與互動方式;此外,不斷總結先前合作經驗,細化發掘與供應商的最佳合作時機,為提升潛在創新能力提供經驗支持。
(3)動態掃描外部環境,相機引入適宜供應商。尤其針對快速變革的行業而言,及時關注技術前沿動態以及市場精細化需求以獲取技術新穎性知識與市場新穎性知識是必要的,這就要求企業必須不斷正視創新項目與外部環境的匹配度,不斷掃描外部技術與市場訊息,根據實際重整戰略需求,必要時提前建立與供應商合作關系或延長與供應商合作時間,確保創新項目及時獲取關鍵資源與知識;同時有針對性地與供應商協同培養知識整合能力和資源協奏能力,為提升新產品價值屬性提供必要舉措。
5.3 研究不足與未來展望
本研究主要探討制造業企業與供應商的合作時機對創新績效的影響,未來可進一步研究包括服務業等其他產業與高校、供應商、分銷商等合作時機,豐富研究情境;同時,可從更多相關理論視角入手,進一步厘清創新時機對創新績效的影響條件。此外,未來可進一步采用案例研究或面板數據驗證本研究結論的同時,拓展研究的縱向視角。
注釋:
1)根據國家統計局2003 年發布的我國31 個省份的經濟區域劃分規定,東部包括北京、天津、河北、遼寧、上海、江蘇、浙江、福建、山東、廣東、廣西、海南12 個省、自治區、直轄市;中部包括山西、內蒙古、吉林、黑龍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9 個省、自治區;西部包括重慶、四川、貴州、云南、西藏、陜西、甘肅、寧夏、青海、新疆10 個省、自治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