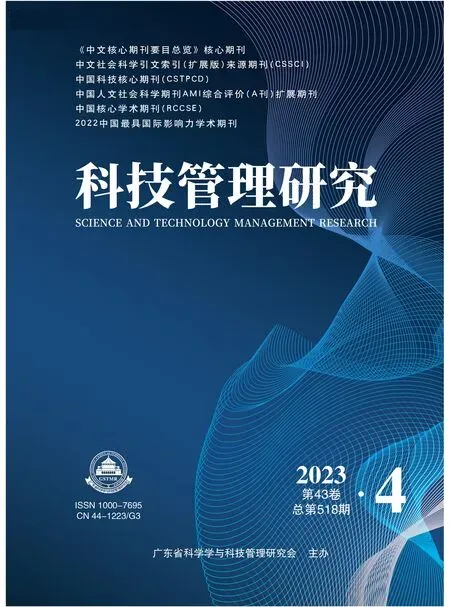碳排放權交易試點政策的碳減排效應
——基于綠色技術創新和能源結構轉型的中介效應
成瓊文,楊玉婷
(中南大學商學院,湖南長沙 410083)
1 問題的提出
近年來,全球氣候變暖這一問題對地球的生態環境造成了嚴重的破壞,這主要歸因于CO2的排放。作為全球的能耗大國,中國主動承擔環境保護的國際責任,通過出臺一系列的環境保護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改善環境的作用。《2020 年中國生態環境狀況公報》顯示,相比2019 年,2020 年中國空氣質量達標城市占比提高13.3%,CO2排放強度下降1.0%[1],可見環境質量在這個階段得到了較為明顯的改善。2020 年9 月22 日,習近平總書記作出了中國力爭2030 年前實現碳達峰,2060 年前實現碳中和的“雙碳”國際承諾。這既是中國作出的國際承諾,也是中國對走低碳、綠色、環保、高質量、可持續道路的一種堅持和自我施壓。2011 年印發的《關于開展碳排放權交易試點工作的通知》也是中國為了推進碳減排進程而實行的市場型環境規制政策之一,將北京、上海、天津、重慶、湖北、廣東和深圳作為第一批試點地區,批準其開展碳排放權交易。碳排放權交易試點省市于2013 年陸續開始啟動碳市場。
作為市場激勵性環境規制工具,試點地區將碳排放權交易試點政策視作一種以低成本實現環境規制效果的政策工具,重點在于規制高碳排放企業降低其碳排放,理論上不僅能通過交易機制和配額分配機制刺激區域綠色技術創新,也能夠利用成本-效益原則推動區域能源結構朝著清潔能源的方向轉變。那么,作為低碳綠色發展和實現“雙碳”目標道路上的重要決策,碳排放權交易試點政策是否顯著促進了試點地區的碳減排?碳減排效應是否以犧牲地區經濟發展為代價?各試點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產業結構、控排主體等多方面存在異質性,其碳減排效應是否也存在差異性?碳排放權交易試點政策的減排機制又是如何?隨著全國碳排放權交易市場在發電行業開啟交易,圍繞上述問題,如何基于試點地區的現實情況及其實踐經驗對現行的政策規定進行改進是當前學術界和政府相關部門的重點關注。為此,本研究利用2005—2019 年中國30 個省區市面板數據,通過多期雙重差分模型檢驗碳排放權交易試點政策的實施是否對試點地區存在碳減排效應,并進一步分析其碳減排路徑和減排效應的地區異質性。
2 理論基礎與研究假說
2.1 碳排放權交易試點政策的減排效應
碳排放權交易市場作為一種市場化的交易減排機制,目前已經是全球范圍內能源和氣候經濟學等相關學科的關注熱點。從本質上來說,碳排放權交易市場從科斯的產權理論中演化而來,20 世紀60 年代末,Dales[2]則在這一基礎上進一步地提出了“排污權交易”概念,指出地球地總體環境資源有限,可以通過商品化排污權并為其建立相應的交易市場,從而實現排污權交易規范化和合理化,通過市場機制和非市場機制來達到更低成本的環境治理目的。Zhang 等[3]和Liu 等[4]站在市場理論的視角,構建理論模型對碳排放權交易市場進行運作前的情景模擬分析,結果表明中國碳市場在將來能夠以較為客觀的低成本實現環境治理并達到碳減排的目的。自2013 年開始,隨著中國碳排放權交易試點政策的推進,北京、上海等碳排放交易權試點地區的交易市場陸續上市,國內外學者更多地將其視作一個準自然實驗,并通過對其進行理論層面以及實證層面的分析來檢驗這一政策的碳減排效應。
Zhang 等[5]從碳排放、Zhou 等[6]從碳強度以及Chen 等[7]從技術進步方面分別檢驗并證實了碳排放權交易市場的政策效果。其中,Zhang 等[5]對深圳的工業企業碳排放權交易試點政策實施前后的碳排放量進行實證研究,指出以2010 年作為比較基期,2015 工業企業的總碳排放量下降了11%,碳排放權交易市場機制推動試點地區減排的初步成效已經顯現;Hu 等[8]通過對中國碳市場2005—2015年的相關數據進行比較分析發現,試點地區主要控排行業的能源消費量下降了22.8%,碳排放總量下降了15.5%。但是,有關試點地區的碳減排效應是通過降低單位生產總值的碳排放量還是抑制地區經濟發展來實現的爭論尚未得到解決。例如,Zhou 等經過實證分析發現,在碳排放權交易政策實施后,試點地區的碳排放量和碳排放強度都顯著降低;但Zhang 等經過研究發現,試點地區碳排放量下降主要是通過抑制地區經濟發展而非降低碳排放強度來實現的。鑒于此,提出以下研究假設:
假設1:碳排放權交易試點政策的實施能夠推動試點地區的碳減排進程。
假設2a:試點地區碳排放權交易市場通過降低碳強度來降低碳排放量;
假設2b:試點地區碳排放權交易市場通過降低經濟產出來降低碳排放量。
2.2 綠色技術創新與碳排放權交易試點政策減排效應
綠色技術創新是指在節能環保、清潔生產、低碳循環等領域能夠提高效率、改善環境質量,從而達到促進經濟綠色低碳可持續發展目的的技術創新[9]。由于綠色技術創新具有雙重外部性,一種是因為技術外溢導致無法獨享創新收益的正向外部性,另一種是進行綠色技術創新的社會效益大于個人效益的污染治理本身存在的負外部性,因此企業在涉及綠色技術創新的產品或者技術開發時意愿較低,缺乏有效激勵導致企業研發動力不足[10]。而碳排放權交易試點政策通過限制企業的碳排放額提升企業進行碳排放方面的研發意愿,從而提升碳市場試點地區的綠色技術創新水平[11]。作為一種市場型環境規制政策工具,碳排放權交易試點政策能夠有效激勵地方企業進行綠色技術創新活動,不僅能夠在企業層面促進實現減排成本的降低,也能在地區層面促進經濟綠色發展,加強增大區域減排效應。基于宏觀層面的視角,碳排放交易權試點政策主要是通過宏觀政策“信號-預期”機制來發揮減排作用,如王為東等[12]通過運用合成控制法進行反事實實證分析發現,碳排放權交易政策的實施能夠提升試點地區的綠色低碳技術創新水平,這也驗證了“信號-預期”機制在碳排放權交易試點政策促進地區碳減排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基于微觀層面的視角,如宋德勇等[13]、黎文靖等[14]、李廣明等[15]研究指出,存在碳市場本身的配額分配以及價格信號兩種機制,可以通過刺激企業綠色技術創新來進一步達到地區碳減排目的。因此,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3:碳排放權交易試點政策通過推動試點地區的綠色技術創新實現碳減排。
2.3 能源結構轉型與碳排放權交易試點政策減排效應
在碳達峰碳中和的愿景下,我國以煤炭消費主導的能源結構轉型任重道遠。碳排放權交易試點政策的實施,將企業對環境的污染成本化,從而提高了企業碳排放成本。碳排放配額和定價機制不僅激勵企業進行綠色技術創新減排,也能引導企業提高相應的能源技術和配置的運行效率,進而達到節約能源和調整能源結構的目的[15]。此外,碳排放權交易制度能夠促使各消費主體逐漸轉換其能源消費結構,從而實現地區碳減排。但另一方面,能源結構轉型的同時也可能會以犧牲部分的經濟增長為代價[16],如清潔能源的使用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減少地區CO2的排放和SO2的排放,但煤炭消費的減少也會對地區生產總值產生影響。因此,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4a:碳排放權交易試點政策借助推動能源結構轉型實現降低碳強度的碳減排;
假設4b:碳排放權交易試點政策借助推動能源結構轉型實現降低經濟產出路徑的碳減排。
3 研究設計
3.1 模型構建
選取2005—2019 年的相關面板數據,以2013年開始正式實行的碳排放權交易試點政策作為一項準自然實驗,研究其減排效應。由于我國試點地區碳市場上市時間并不統一,因此選擇運用多期雙重差分模型來實證分析政策實施前后實驗組與對照組的碳排放總量和碳排放強度差異,將北京、廣東、湖北、天津、上海和重慶這6 個碳排放權交易試點省市作為處理組1),國內其余省區市則作為控制組納入模型進行分析。構造多期雙重差分模型(亦為基準模型)如下:
式(1)中:下標i表示地區;下標t表示年份;Yit代表地區碳排放量或碳排放強度;DIDit是核心解釋變量多期雙重差分變量,DIDit=treati×postit,其中treati表示是否是處理組,postit表示試點地區碳排放權交易試點政策的正式實施時間;controlit代表會隨地區和時間變動并且會影響碳排放量或碳排放強度的控制變量;ui表示地區固定效應;γt表示時間固定效應;ηrt代表年份與區域2)的交乘項,控制了隨區域或時間變化的因素;εit則表示誤差項。
此外,是否處理組的取值規則為:當i表示6個試點省市時,treati=1;當i代表其他非試點地區時,treati=0。6 個試點地區碳市場開始啟動交易的時間分別為北京、上海、廣東和天津2013 年,湖北和重慶2014 年,所以試點政策正式實施時間的取值規則為:當i表示北京、天津、上海、廣東這4 個省市且或者i表示湖北或重慶且時,postit=1;除此之外,postit=0。如果碳試點政策的實行顯著地降低了試點地區的碳排放總量或者碳排放強度,則多期雙重差分模型中β1顯著為負。
參考黎文靖等[14]、王桂軍等[17]的研究,將中介變量綠色技術創新和能源結構嵌入基準模型中進行實證檢驗,構建如下中介效應檢驗模型:
式(2)同基準模型。式(3)式中,被解釋變量MVit分別代表中介變量綠色發明專利申請量(EnvInvPat)、綠色實用新型專利申請量(EnvUtyPat)和能源結構(ES)。
根據逐步回歸原理,如果式(2)的回歸系數β1顯著,則開始中介變量的回歸檢驗;其次檢驗式(3)的回歸系數φ1和式(4)的回歸系數ρ,如果兩者均顯著,則存在中介效應;最后,若式(4)中的回歸系數δ1也顯著,則稱其為部分中介效應,否則稱為完全中介效應。
3.2 特征事實
通過對比發現,處理組相比控制組具有低碳排放量和低碳排放強度的特點,且通過共同趨勢圖1可以看出,兩者在2011 年前存在平行趨勢。

圖1 處理組和控制組地區碳排放量和碳排放強度的年度均值趨勢對比
3.3 變量選取和數據說明
(1)被解釋變量和核心解釋變量。被解釋變量為地區碳排放量(ce)和碳排放強度(cegdp),模型中對其取對數形式(即ln ce 和ln cegdp)。核心解釋變量為多期雙重差分變量(DID),表示該地區是否已經實行碳排放權交易試點政策。
(2)控制變量。由于地區碳排放量和碳排放強度與地區經濟發展密切相關,所以為了使得試點地區與非試點地區的碳排放量和碳排放強度不受其他因素干擾、具有可比性,需要在模型中加入涉及到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的相關指標。選取的控制變量為:1)人均地區生產總值(ln pcgdp),用地區的人均實際生產總值并取對數表示,具體數值按照2005 年的不變價進行換算獲得;2)產業結構,借鑒Shao等[18]的做法,用地區第二產業占比(stind)和第三產業占比(stser)兩個指標來表示;3)外商投資占比(stwz),借鑒張宇等[19]的做法,用地區的當年外商投資金額和當年生產總值的比值表示;4)財政依賴度(stpub),用地區的當年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和地區生產總值的比重表示;5)環境規制(ster),處理組和控制組本身存在的環境規制的地區差異也會給地區的減排效應造成影響,用地區的工業廢水、廢氣污染治理費用與工業總產值的比重表示。
(3)中介變量。
1)綠色技術創新。專利產出是衡量技術創新最直觀的數據體現,參考齊紹洲等[10]的研究,通過匹配中國國家知識產權專利數據庫和WIPO 的國際專利分類綠色清單,識別出地區綠色發明專利申請量(envinv)和綠色實用新型專利申請量(envuty),以此度量處理組和控制組的綠色技術創新水平,并對其進行對數處理。
2)能源結構(ES)。參考馬麗梅等人[20]的做法,運用高一次性能源消耗的8 個工業行業的生產總值之和與地區當年生產總值的比值衡量,指標值越低則表示地區的能源結構清潔化程度越高。計算公式如下:
式(5)中:j表示高煤炭消耗行業;m表示行業個數;GDPit表示第i個地區t年份的生產總值;HCI 表示行業產值,依據現有數據和《中國統計年鑒2020》,選取了8 個主要的高煤炭消耗的工業行業作為樣本代表(見表1)。煤炭的消耗是CO2排放的重要源頭,因此通過測度高煤炭消耗工業行業的產出占地區生產總值的比重來衡量能源結構,并以此來反映地區經濟發展的產業能耗結構。

表1 2019 年中國8 個高煤炭消耗工業行業
(4)數據說明。選取中國30 個省區市(未含西藏和港澳臺地區)2005—2019 年的面板數據作為研究樣本來檢驗相關假設。碳排放量數據來自中國碳排放核算數據庫;碳排放強度通過碳排放量數據的進一步計算獲得;專利數據來源于中國國家知識產權局;其他數據來源于歷年的《中國工業經濟統計年鑒》《中國統計年鑒》《中國能源統計年鑒》和各省區市統計年鑒。利用STATA 作為研究分析工具。
4 實證結果及穩健性分析
4.1 變量描述性統計
本研究模型和相關檢驗中運用到的變量含義及其描述性統計結果如表2 所示。

表2 變量含義及描述性統計結果
4.2 基準回歸結果
如表3 所示,未加入控制變量前,30 個省份碳排放總量和碳排放強度的DID 系數均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為負,加入控制變量后,結果基本上不變,表明研究的回歸結果具有一定的穩健性,即碳排放權交易試點政策的實施同時降低了試點地區的碳排放量和碳排放強度,假設1 和假設2a成立。

表3 基準回歸結果
4.3 平行趨勢檢驗及政策動態效應分析
參考張國建等[21]的研究思路來進行多期雙重差分模型的平行趨勢假設以及政策動態效應分析。為了展示碳排放權交易試點政策實施前后試點地區的碳排放量和碳排放強度的變化情況,將碳排放權交易試點政策正式實施前8 年這一時間節點定為比較基期,引入碳排放權交易試點政策啟動前7 年、政策當期和政策啟動后6 年的時間趨勢變量,構建對應模型如下:
同時可以看出,處理組中的試點地區正式啟動其碳市場的時間集中在2013 年和2014 年,所以政策施行當期的前一兩年就是2011—2012 年。出現預期政策效應可能是由于國家發改委早在2011 年10月已經批準了7 個省市的碳排放權交易市場試點工作,試點地區從那時就開始加快其經濟朝低碳方向轉型以應對不遠將來更強的碳排放約束和更高的碳排放成本問題。Liu 等[22]通過研究中國碳排放交易權試點市場的企業動態指出,試點地區的高排放企業在2011 年碳市場試點政策剛宣布時就感知到未來市場變化方向,并相應地改變或升級其生產技術和生產方式,以更好地適應未來的碳排放約束并提前實現企業碳減排。
通過平行趨勢檢驗和政策動態效應圖,可以更加直觀地觀察試點地區的碳市場政策動態效果。從圖2 中可以直觀地看出,碳排放量和碳排放強度的系數估計結果和變化趨勢基本一致。在碳排放權交易試點政策實施前7 年至前2 年,二者相關系數都不顯著,滿足平行趨勢假設;碳市場正式啟動前1年二者對應系數顯著,出現預期政策效應;政策實施當期和實施之后,二者對應系數絕對值都在逐年增加。這與表4 的估計結果一致,進一步驗證了假設1 和假說2a。

表4 平行趨勢檢驗及動態效應檢驗結果

表4 (續)

圖2 平行趨勢檢驗和政策動態效應
4.4 穩健性檢驗
4.4.1 安慰劑檢驗
為了確保本研究關于碳減排效應與碳排放權交易試點政策的因果關系存在,排除變量的選擇性偏差,從而得到可信度更高的因果效應分析,運用反事實邏輯隨機生成處理組(試點地區)來進行安慰劑檢驗。對于安慰劑檢驗的具體運用方法,學者Bertrand 等[23]提出,在運用時間跨度較大的面板數據進行雙重差分檢驗時,可能會存在因為變量間存在序列相關問題而導致標準誤差出現偏差的問題,從而進一步導致在檢驗回歸時發生檢驗過度、拒絕原假設的現象。針對這個問題,吳茵茵等[24]、陸菁等[25]選擇運用非參置換檢驗法來對其基準回歸結果進行安慰劑檢驗,借鑒其做法,具體采用的非參置換檢驗操作方法如下:對樣本數據中的30 個省區市和時間點進行不重復的實驗省市和政策時點的隨機抽樣,每次抽樣選取6 個省份作為虛擬試點地區,因為在多期雙重模型中要求在政策實施前后都至少有1 年時間,所以在安慰劑檢驗階段數據處理中,僅針對2006—2018 年中的時間段選取隨機的模擬政策時間點;剩余的24 個省份則作為虛擬非試點地區。重復500 次上述隨機抽樣過程并進行回歸,進而獲得500 個虛擬實驗組、其對應的虛擬政策實施時點及兩者交互項虛擬DID 的回歸系數。如果在隨機抽樣進行回歸的過程中,虛擬DID 的估計系數并不顯著,則說明碳排放權交易試點政策和碳減排效應的因果關系存在,本研究的基準回歸結果具有穩健性。
如圖3 所示,實線表示DID 回歸系數的概率密度累計分布,虛線表示正態分布。從圖3 可以看出,真實回歸系數都位于安慰劑檢驗置換參數曲線的低尾處,屬于虛擬實驗組回歸的異常值,表明本研究的基準回歸結果通過了安慰劑檢驗。

圖3 安慰劑檢驗系數累計分布
如圖4 所示,橫軸除0 值外的虛線表示本研究基準回歸結果的對應系數(ln ce 的對應系數為-0.163,ln cegdp 的對應系數為-0.366)。可以發現,不管是碳排放量還是碳排放強度,估計系數對應的P值都在0.1 以上,隨機抽樣的回歸系數均值非常接近零,本研究基準回歸結果處于低尾處,且P值小于0.1,說明隨機抽樣的結果并不顯著,碳排放權交易試點工作在虛擬實驗組中不具有減排效應。這進一步表明 本研究的基準回歸結果具有穩健性,排除了未知因素的干擾,通過了安慰劑檢驗。

圖4 安慰劑檢驗估計系數P 值分布
4.4.2 PSM-DID 檢驗
基于樣本中處理組和控制組可能在碳排放權交易試點政策實施前就具有較大的個體差異的考量,為了避免在多期雙重差分模型的樣本選擇中出現選擇性偏差的問題,運用傾向得分匹配雙重差分法(即PSM-DID)進行進一步的穩健性檢驗。鑒于平行趨勢檢驗和政策動態效應分析的結果表明,早在2011年試點地區就已經因為“信號-預期”機制顯現出碳減排效應,且2011 年試點地區名單就已公布,所以在進行傾向得分匹配檢驗時只選取2011 年之前的樣本,以保證所選樣本并未受到政策影響。具體檢驗方法為:以基準模型中的控制變量作為PSM-DID中的匹配變量進行逐年匹配,匹配方法分別運用到半徑匹配、近鄰匹配和核匹配,并且在進行逐年匹配后只保留在每個匹配年份都處在共同取值范圍內的控制組樣本點,具體回歸中運用Logit 方法,最后針對匹配后的保留樣本,根據基準模型進行多期雙重差分模型回歸。如表5 所示,不管具體采用的是哪種匹配方法,多期DID 變量的回歸系數均顯著為負。因此,本研究關于碳排放權交易試點政策的碳減排效應的基準回歸結果具有穩健性。

表5 PSM-DID 檢驗回歸結果
5 進一步討論
5.1 碳排放權交易試點政策的減排路徑檢驗
5.1.1 綠色技術創新的中介效應檢驗
表6 和表7 展示了根據式(3)(4)模型進行的,分別以綠色發明專利申請量、綠色實用新型專利申請量來衡量地區綠色技術創新水平的中介效應檢驗結果。從表6 可見,僅以綠色發明專利申請量來度量地區綠色技術創新水平時,碳排放權交易試點政策的實施并沒有對試點地區的綠色技術創新產生顯著的影響,也即表明未產生中介效應;當以綠色實用新型專利申請量來衡量地區的綠色技術創新水平時,碳排放權交易試點政策的實施顯著地提升了試點地區的綠色技術創新水平。從表(7)可見,綠色實用新型專利申請量的回歸系數均通過了顯著性檢驗,且DID 的回歸系數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為負,結合中介效應檢驗模型式(3)(4)可知,碳排放權交易試點政策可以通過提升試點地區的綠色技術創新水平來降低其碳排放量和碳排放強度,且綠色技術創新在其中發揮部分中介效應,則假設3 成立。至于表6 與表7 的差別,本研究認為可能是綠色發明專利相比綠色實用新型專利的實驗期限更長、申請程序更復雜,所以相比碳排放權交易試點政策的施行會存在時間滯后性的特點。

表6 基于綠色發明專利申請量的中介效應檢驗結果

表7 基于綠色實用新型專利申請量的中介效應檢驗結果
為了解綠色技術創新在碳排放權交易試點政策的減排效應中發揮了多大作用,利用回歸結果進一步計算綠色技術創新在中介效應模型中的效應量,結果表明綠色技術創新在碳排放權交易試點政策降低碳排放和降低碳排放強度的效應中分別發揮了12.38%和5.51%的中介效應作用。
這一中介效應檢驗結果也符合碳排放權交易試點政策設計的初衷。從生產角度,當碳排放存在排放配額并在市場上作為商品進行交易時,高碳排放企業由于碳排放成本較高會選擇進行生產技術的創新或生產方式的改變來減少其碳排放量;此外,企業積極進行綠色技術創新使得企業碳排放指標存在富余時,可以將碳排放指標作為商品在市場上進行交易,從而獲得降低成本外的創新收益,這也將進一步激勵企業進行技術創新,從而達到了以經濟手段的政策實現低成本的環境規制目的。
5.1.2 能源結構轉型的中介效應檢驗
同理,根據式(3)(4)模型對能源結構的中介效應檢驗。如表8 所示,DID 的回歸系數均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為負,說明碳試點政策的實施有效地促進了試點地區的能源結構轉型;能源結構的回歸系數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下為正,且DID 系數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為負,根據逐步回歸法判斷存在部分中介效應,表明碳排放權交易試點政策可以通過推動試點地區的能源結構轉型來降低當地的碳排放量和碳排放強度。綜上,表明假設4a 成立。

表8 基于能源結構的中介效應檢驗結果
為了解能源結構轉型在碳排放權交易試點政策的減排效應中發揮了多大作用,利用回歸結果進一步計算能源結構在中介效應模型中的效應量。結果表明,能源結構在碳排放權交易試點政策降低碳排放量和碳排放強度的效應中分別發揮了3.74%和0.47%的中介效應作用。
進一步通過比較綠色技術創新和能源結構轉型在碳排放權交易試點政策的碳減排效應中發揮的作用可以發現,綠色技術創新發揮的作用更大。
5.2 地區異質性分析
在基準模型中加入各試點地區與DID 變量的交乘項來檢驗碳排放權交易試點政策的減排效應是否在試點地區存在區域異質性。表9 為北京(bj)、天津(tj)、上海(sh)、湖北(hb)、重慶(cq)這5 個碳排放權交易試點地區相較于廣東(gd)的回歸結果,可得出以下結論:(1)北京的碳減排效應最顯著,其次是上海和天津,筆者推測因為這3個試點地區的政策落實到位以及市場發育程度較高;(2)雖然天津的碳排放量的對應系數不顯著,但碳排放強度的系數較為顯著且系數值較大,表明相較于廣東,天津的碳排放強度減排效應明顯;(3)相比較其他試點地區,湖北和重慶在政策實施后碳減排效應較弱,筆者推測是由于湖北和重慶的碳排放權交易市場主體占地區碳排放主體的比重較低導致。

表9 地區異質性分析回歸結果
6 結論與政策建議
本研究基于2005—2019 年中國30 個省區市的面板數據,運用多期雙重差分模型來實證檢驗碳排放權交易試點政策對試點地區是否存在碳減排效應,并采用平行趨勢檢驗、安慰劑、PSM-DID 等方法檢驗碳減排效應的穩健性,通過中介效應分析檢驗綠色技術創新和能源結構轉型的傳導路徑,最后分析試點政策的地區異質性。研究結論如下:
(1)整體而言,碳排放權交易試點政策的實施顯著地推動了試點地區的碳減排進程,這種減排效應是通過同時降低試點地區的碳排放量和碳排放強度實現的,并未影響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這一結果通過了一系列的穩健性檢驗。
(2)中介效應方面,綠色技術創新和能源結構轉型都是碳排放權交易試點政策發揮碳減排效應的路徑,且都能夠同時促進試點地區碳排放量和碳排放強度的降低。相比綠色發明專利申請量,以綠色實用新型專利申請量作為衡量指標時,試點地區的綠色技術創新水平才受到碳排放權交易試點政策的顯著影響。綠色技術創新在降低試點地區的碳排放量和碳排放強度過程中分別發揮了12.38%和5.51%的中介效應作用;能源結構轉型在降低試點地區的碳排放量和碳排放強度過程中分別發揮了3.74%和0.47%的中介效應作用。
(3)地區異質性方面,北京的碳減排效應在6個試點地區中最強,其次是上海和天津,湖北和重慶的整體碳減排效應較弱。
以上研究結論對中國加快碳減排進程,從而早日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目標的策略制定和政策實施具有如下政策啟示:
第一,加強全國碳市場建設。碳排放權交易試點政策的實施能夠在試點地區存在顯著的碳減排效應,為實現“雙碳”目標,需要進一步加快全國碳市場相關體系建設并加大減排主體范圍,并從試點地區的配額分配方法、交易機制、約束機制、市場調控機制等多方面吸收、借鑒其實踐經驗,以發揮試點地區的先行示范和持續激勵作用。
第二,積極推進綠色技術創新和能源結構轉型(及相關的產業結構轉型)。綠色技術創新不僅能夠提升相關能源的利用效率,還能推進能源結構轉型,從而弱化一些重工業企業對煤炭等化石能源的依賴,不以犧牲地區經濟發展為代價地降低地區碳排放量。所以,政府需要出臺相應的財政補貼和稅收優惠政策來促進企業開展綠色技術創新研發及其成果轉化;加大對低碳技術研發人才的引進獎補力度;持續推進高碳排放企業與所在地區的高校及科學研究院進行產學研深度合作,搭建以綠色技術創新、能源結構轉型和碳減排為導向的產業結構體系和經濟體系,加快推進低碳綠色環保的高質量現代經濟。
第三,各省區市要因地施策,制定差異化的減碳政策。各地區根據自身的經濟發展階段和經濟發展水平制定差異化的綠色技術創新、能源結構轉型和碳減排政策,并適當地將資源向減排潛力大的省份傾斜,從而實現低成本高減排。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地區可以加大對清潔能源和綠色技術創新的投資;經濟發展中等水平的地區以制造業發展為主,這一行業的生產流程中需要消耗大量的化石能源,從而會排放大量的CO2,所以需要根據地區的資源稟賦結構來發展其優勢資源,加快經濟發展步伐。與此同時,加快綠色技術創新,從而提升能源利用效率以降低碳排放。
注釋:
1)鑒于深圳市歸屬于同樣作為碳排放權交易試點的廣東省,因此在處理組中不再單獨納入深圳市。
2)根據《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促進中部地區崛起的若干意見》《國務院發布關于西部大開發若干政策措施的實施意見》等經濟政策文件,將我國31 個省份劃分為東、中、西、東北四大區域。東部包括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上海市、江蘇省、浙江省、福建省、山東省、廣東省、海南省;中部包括山西省、安徽省、江西省、河南省、湖北省、湖南省;西部包括內蒙古自治區、廣西壯族自治區、重慶市、四川省、貴州省、云南省、西藏自治區、陜西省、甘肅省、青海省、寧夏回族自治區、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東北地區包括遼寧省、吉林省、黑龍江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