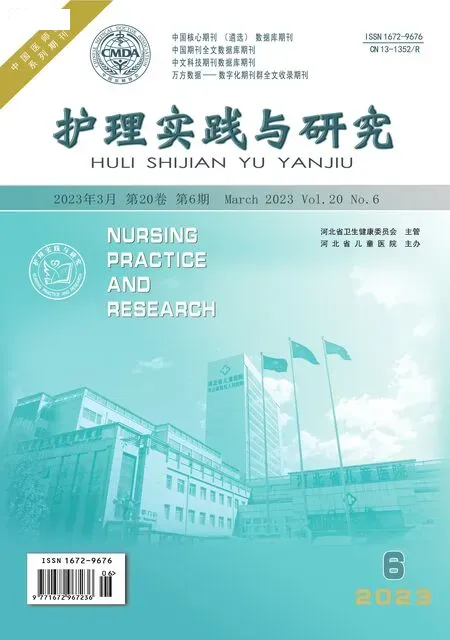微視頻教育模式對產婦母乳喂養自我效能與極低體重兒體質量水平的影響
馮劍美 高麗娟 張琳
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等多部門于2021年聯合印發的《母乳喂養促進行動計劃(2021—2025年)》[1]中明確要求,到2025年,我國母嬰家庭成員母乳喂養支持率達到80%以上,但有關數據顯示[2],當前我國母乳喂養率僅為30%,而非純母乳喂養不僅會限制新生兒的早期智力發育和免疫力水平的提高,還有可能加大新生兒喂養不耐受的發生風險,尤其是營養狀況相對較差的早產極低體重兒,因此,采取何種方式才能有效提高母乳喂養率逐漸成為醫學領域的重點關注內容。有研究指出[3],母乳喂養相關知識的掌握程度與早產極低體重兒產婦產褥期喂養方式的選擇有較大聯系,及早開展健康教育,提高產婦母乳喂養認知,對促進母乳喂養率的提高有積極作用。近年來,隨著各類社交媒體平臺的快速崛起,集互動性、娛樂性、短快精等特征于一體的微視頻日益流行起來,且得益于能夠更加直觀地為觀看者提供相關信息,微視頻先后在各類疾病的健康教育中得到應用[4-5],相比口頭宣教、分發健康圖冊等傳統教育手段,更易被患者所接受,但有關微視頻在早產極低體重兒產婦中應用的報道卻較為少見。為尋求一種能有效提高早產極低體重兒母乳喂養率的健康教育模式,本研究為其實施微視頻教育模式,并對其臨床價值進行研究分析,現報道如下。
1 對象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選擇2020年1月—2021年12月在常州婦幼保健院早產分娩的產婦120例作為研究對象。納入條件:初產婦,單胎分娩;新生兒為早產極低體重兒,出生時體質量<1500 g,孕周28~<37周;感官功能正常,能獨立使用手機或其他移動終端設備;具備小學及以上文化水平;家屬知情,自愿參與,簽訂知情同意書。排除條件:妊娠期和產褥期精神狀態不佳,愛丁堡產后抑郁量表評分≥12分;產后因各種原因回奶;妊娠期或產褥期經歷嚴重家庭或護患糾紛;新生兒伴先天性器質性疾病;新生兒伴胃腸功能障礙,或伴心、肝、腎等器官嚴重功能障礙;新生兒住院時間≥6周。剔除條件:中途退出研究,或新生兒出現突發性疾病;填寫問卷時遭受外界人為因素干擾。倫理審核:根據《世界醫學大會赫爾辛基宣言》[6]中制定涉及人體對象醫學研究的道德原則,本研究獲得本院醫學倫理委員會的批準。按照組間基本特征均衡可比的原則,將產婦分為對照組和觀察組,各60例。對照組:產婦年齡20~37歲,平均28.63±4.61歲;孕周28~36周,平均31.92±2.04周;分娩方式:自然分娩41例,剖宮產19例;文化水平:初中及以下19例,高中20例,專科及以上21例;極低體重兒出生時體質量 1123.34~1393.49 g,平均 1257.03±54.52 g。觀察組:產婦年齡20~40歲,平均28.70±4.91歲;孕周29~36周,平均32.50±1.88周;分娩方式:自然分娩40例,剖宮產20例;文化水平:初中及以下19例,高中23例,專科及以上18例;極低體重兒出生時體質量1108.21~1400.40 g,平均1243.00±56.83 g。兩組產婦年齡、孕周、分娩方式、文化水平及新生兒出生時體質量等基線資料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
1.2 干預方法
1.2.1 常規護理 兩組產婦入組后,均予以常規護理,內容包括:①創造良好的休息環境,保證室內溫濕度適宜,避免受涼,定時通風,盡量保持安靜,確保產婦產褥期休息充足;②注意調整飲食,盡量以高蛋白、高熱量、易消化的食物為主;③根據身體恢復情況適當參加體育運動,避免長時間臥床;④定時使用碘伏或高錳酸鉀清洗外陰及周圍皮膚,保證外陰清潔。
1.2.2 健康教育 在常規護理基礎上,組建健康教育研究小組,包括1名護士長、2名主管護師及4名護士,小組成立后由護士長組織小組全員進行業務知識培訓,培訓內容包括早產婦女產褥期護理措施、早產極低體重兒護理措施及母乳喂養相關知識,培訓后進行考核,要求小組成員熟悉掌握以上內容,全員通過后分別為兩組產婦實施健康教育,包括產后注意事項(產后不適癥狀的預防與應對策略)、母乳喂養知識(母乳喂養的優點、重要性及母乳喂養的操作流程和技巧)、產后自護知識(產后飲食、用藥、運動等居家自我護理的操作流程和技巧)3部分內容。兩組產婦干預期間享有完全相同的醫療資源,僅在健康教育模式上存在差異,其中對照組采取常規手段進行健康教育,觀察組采取微視頻教育模式。
(1)對照組:常規健康教育以口頭宣教、健康講座、宣傳圖冊等為主要手段,對于母乳喂養技巧等操作性較強的內容,由護士手把手演示教學,并發放圖解教程,供產婦隨時查看學習,產婦出院前,對其進行產后居家自護知識教育,并指導其添加“產后常規教育”微信群,叮囑產婦居家期間可隨時通過微信群向醫護人員尋求幫助。
(2)觀察組:微視頻交由專人制作,包括視頻內容設計和語音錄制,專業知識則由護士長提供,微視頻制作完成后,由小組全員對微視頻內容進行審核,確保內容無誤、畫面語音清晰。待產婦產后體征和情緒穩定后,指導其添加“產后微視頻教育”微信群,并將按照健康教育流程,在群中分享微視頻,首次觀看由護士全程講解。出院后,采取微信對兩組產婦進行定期隨訪,1次/周,連續隨訪4周。
1.2.3 質量控制 ①入院后,將兩組產婦分別安排于不同病房,以避免造成組間沾染;②叮囑兩組產婦及家屬禁止談論有關研究的事宜;③護士長全程監督護士工作情況,對于擅離職守、態度消極、故意與產婦或其家屬發生沖突者,予以嚴肅批評。
1.3 觀察指標
(1)健康知識掌握度:采用本院自行設計“健康知識掌握度評分表”評價產婦健康知識掌握度,該評分表涉及產后并發癥預防、母乳喂養、產后康復等內容,共10道判斷題,每題1分,評分越高健康知識掌握越好。該評分表經2輪專家函詢,Kendall W=0.145~0.155,通過信效度檢驗測得該評分表信效度良好,Cronbach’sα=0.793~0.921。
(2)母乳喂養自我效能:采用Dennis等[7]于1999年編制母乳喂養自我效能量表(Breastfeeding Self-Efficacy Scale,BSES)評價產婦母乳喂養自我效能,該量表涉及技能(20個條目)和內心活動(13個條目)2個領域,每個條目設置5個選項(1=完全沒有信心,2=略有信心,3=有信心,4=較有信心,5=總是很有信心),總分33~165分,評分越高,代表產婦母乳喂養自我效能越高,該量表信效度良好,Cronbach’sα=0.884~0.925。
(3)極低體重兒母乳喂養率:觀察極低體重兒喂養方式,包括母乳喂養、人工喂養及混合喂養,比較兩組母乳喂養率。
(4)極低體重兒體質量:調查并記錄兩組極低體重兒體質量。
1.4 資料收集方法
分別于入組時和干預4周時,指導產婦在獨立房間內填寫問卷(包括健康知識掌握度評分表和BSES),填寫時要求產婦家屬回避,護士不得給予產婦影響研究結果的建議。于干預4周時調查并記錄產婦的新生兒喂養方式。另分別于入組、干預1周、干預2周、干預3周、干預4周時用嬰兒磅秤測量并記錄極低體重兒體質量水平。本研究共為120例產婦發放問卷和指標檢測,回收有效資料116份,資料有效回收率96.67%。
1.5 數據分析方法
采用SPSS 26.0統計學軟件進行數據分析,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表示,組間均數比較進行獨立t檢驗或雙因素重復測量方差分析;方差不齊時采用t’檢驗。計數資料計算百分率,組間率的比較采用χ2檢驗。以P<0.05為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兩組產婦健康知識掌握度評分比較
入組時,兩組產婦健康知識掌握度評分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干預4周時,兩組產婦健康知識掌握度評分均較入組時提高,且觀察組產婦健康知識掌握度評分高于對照組(P<0.05),組間比較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見表1。

表1 兩組產婦健康知識掌握度評分比較(分)
2.2 兩組產婦母乳喂養自我效能評分比較
入組時,兩組產婦BSES技能領域評分、心理活動領域評分及量表總分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干預4周時,兩組產婦BSES技能領域評分、心理活動領域評分及量表總分均較入組時提高,且觀察組產婦BSES技能領域評分、心理活動領域評分及量表總分均高于對照組(P<0.05),見表2。

表2 兩組產婦自我效能評分比較(分)
2.3 兩組極低體重兒母乳喂養率與體質量比較
喂養方式方面,對照組產婦選擇母乳喂養的占比為34.48%,觀察組產婦選擇母乳喂養的占比為53.45%,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3。極低體重兒體質量方面,整體分析發現,兩組極低體重兒組間效應、時間效應、交互效應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進一步兩兩比較,組內比較兩組極低體重兒干預1周、2周、3周及4周時體質量均較入組時提高,組間比較兩組極低體重兒入組時、干預1周、干預2周時體質量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觀察組極低體重兒干預3周、干預4周時體質量均高于對照組(P<0.05),見表4。

表3 兩組產婦母乳喂養率比較

表4 兩組極低體重兒入組時至干預4周時體質量比較(g)
3 討論
本研究結果顯示,若以6分為健康知識掌握標準,入組時本研究所有產婦中僅36例健康知識掌握度達到標準,約占總體的31.03%,表明本研究產婦健康知識水平普遍較低,低于馬琛琛等[8]研究中產婦健康知識掌握水平,通過進一步分析發現,馬琛琛等研究中產婦學歷在專科及以上的占比為77.00%,高于本研究的32.76%,因此本研究認為,文化水平是影響產婦健康知識掌握度的主要因素,且馬琛琛的研究結果也證實了這一觀點。另有研究指出[9],高學歷產婦更積極主動了解母乳喂養相關知識,出院后更愿意繼續選擇母乳喂養。孫銘第等[10]就影響早產兒產婦母乳喂養決策的因素研究指出,早產兒產婦喂養知識掌握程度與喂養選擇聯系緊密,醫護人員需要重點關注早產婦的母乳喂養知識掌握程度及意愿,了解其是否存在知識缺乏及誤區,母乳喂養方法是否正確,必須在出院前做好充分的指導與健康宣教。Balogun等[11]研究指出,針對產婦開展有關母乳喂養的健康教育,對產后3個月的純母乳喂養率有著明顯的促進作用。以上研究充分證明,針對早產兒產婦積極開展健康教育對提高其產褥期母乳喂養率有著積極作用。
傳統健康教育以口頭宣教、健康講座、宣傳圖冊等為主要手段,但由于圖片和文字的信息表達形式相對抽象,不夠具體,且缺乏連貫性,導致采取以上途徑向產婦傳遞信息時具有較大的局限性,從而使得產婦無法真正掌握相關知識。微視頻教育模式集文字、圖片、語音、視頻于一體,相比單純的圖文介紹,利用視頻向產婦展示相關健康知識更能給產婦沖擊力,直觀的內容呈現,更便于產婦深入理解相關內容,加之清晰的背景語音介紹,既能輔助介紹視頻內容,又可避免長時間觀看文字使產婦出現焦躁情緒,因而可進一步提高健康教育的效率與質量。本研究結果顯示,干預4周時兩組產婦健康知識掌握度評分雖較入組時均有提高,但觀察組評分提高幅度更大,且干預4周時觀察組產婦健康知識掌握度評分高于對照組,提示微視頻教育模式在提高產婦健康知識掌握度方面作用突出,與顧爭妍等[12]研究結果一致。分析其原因,微視頻內健康知識顯示連貫,易被各文化層次的產婦所接受,此外,借助微信平臺向產婦發送微視頻,不僅打破了地域限制,便于產婦隨時隨地學習,同時也解決了居家期間無法隨時讓醫護人員為其進行實時講解的問題,產婦僅在家中即可通過微視頻反復收聽有關母乳喂養的語音視頻講解,進而加深產婦對相關知識的印象。張萍等[13]研究發現,產婦母乳喂養方面的知識增加,能幫助其提高自我效能,加之微信群中產婦相互交流,相互分享母乳喂養經驗,同樣有益于產婦母乳喂養自我效能的提高。本研究結果顯示,干預4周時兩組產婦BSES技能領域評分、心理活動領域評分及量表總分均較入組時提高,且觀察組產婦BSES技能領域評分、心理活動領域評分及量表總分均高于對照組,與張貴清等[14]研究結果一致。隨產婦對母乳喂養的了解不斷加深,可使其不斷明確母乳喂養對新生兒所產生的積極影響,加上產婦母乳喂養效能不斷提高,促使產婦更傾向于選擇母乳喂養,本研究結果顯示,觀察組產婦母乳喂養率高于對照組。另有研究指出[15],相比人工喂養和混合喂養,純母乳喂養新生兒的胃排空更快,且母乳內所含的膽汁可刺激脂肪酶在新生兒十二指腸內被膽鹽激活,促進母乳中脂肪的乳化成為小微粒,更有助于被新生兒消化吸收,進而加快新生兒體質量增加,本研究結果顯示,入組時至干預4周時期間,觀察組極低體重兒的體質量提高幅度更大,尤其在干預3周和干預4周時,觀察組極低體重兒體質量水平高于對照組。
綜上所述,針對早產極低體重兒產婦開展微視頻教育模式,有助于提高其健康知識掌握度和母乳喂養自我效能,促使產婦提高母乳喂養傾向,加快極低體重兒體重水平提升。但由于移動設備和互聯網的不斷普及,大多數產婦都可以通過網絡搜索等方式自主獲取相關知識,可能會對研究結果造成一定影響,因此今后還需采取一定手段對這一問題進行控制,以進一步提高研究結果的準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