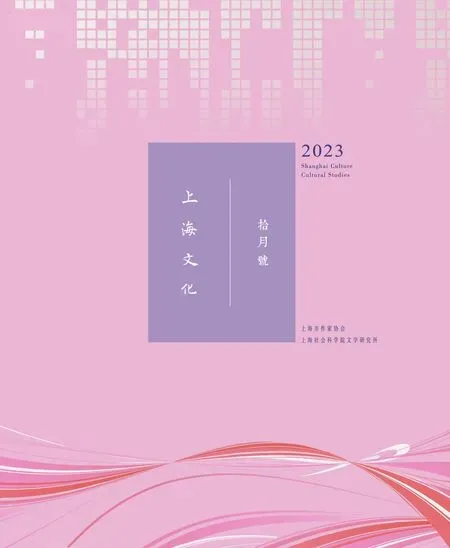地理與空間批評:近年歐美城市文學與文化研究新動向二題
陳昉昊
歐美城市文學研究①本文所涉及的諸多城市文學研究并不僅限于大型城市聚落、超大型城市、大都會城市等所謂“都市研究”,而常常涉及次級城市、二三線城市、衛星城、邊緣城市等研究。盡管英文術語urban studies常常譯為“都市研究”,然而本文在涉及此英文術語時,依然以“城市研究”指代,因“城市研究”的范疇在學科意義上比“都市研究”的范圍更大。以下同。作為獨立學科興起至今已有幾十年,近來歐美學界出版了大量城市文學與文化研究專著。而歐美文學城市學(literary urban studies)研究也日趨完善,涌現了許多優秀的學術成果。歐美文學城市學研究以文學研究為基礎,結合地理學、心理學、社會學、藝術學、歷史學等理論資源,采用跨學科的研究方法,不斷擴大城市研究的邊際,出現將社會情境學理化、抽象概念具體化、城市理論體系化等趨勢。本文旨在通過總結與評析近5年來在英語學界出版的、以地理與空間批評為框架的4本專著,分析這兩大理論框架對于我們理解城市空間的發展變遷、城市與市民雙向構建的互動關系、城市品格與特質的確立、城市文藝與景觀的關系等具有的重要意義。
一、地理批評:文學制圖學與心理地理學
西方地理批評學者往往強調地理與文學的相互影響。城市空間理論研究學者將使城市各區塊連為一體的街道作為“城市血管”,充當重要的聯通與交互的職能。地理批評學的理論同樣可以引入文學研究之中。以下兩位學者基于對兩大世界城市(紐約與倫敦)的文學與藝術研究,做了一些在文化研究領域內的新的嘗試,提供了諸多富有前瞻性的洞見。其中一本關于20世紀60至70年代紐約制圖學的研究專著,旨在從不同藝術家的文學創作和藝術品創作出發,展現戰后美國藝術家如何有意識地進行親身實踐、概念批判甚至政策干預,充分表現了知識分子的擔當與情懷;而另一本探討倫敦文學的專著,勾勒了所謂的“倫敦性”(Londonness)——與所謂的資本主義擴張時代帶有“帝國榮光”的“倫敦性”不同,作者探討了關于倫敦的英國文學如何從心理地理學角度勾勒出倫敦的迥異于非現實性的特點。對于作者來說,“倫敦性”或者“英國性”(Englishness)并不是只有一個固定版本,而是具有開放性與多樣性的。
文學制圖學脫胎于美國文學批評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遜(Fredric Jameson)的認知繪圖(cognitive mapping)理論,指的是作者在建構文學空間的時候已經規劃了一個地圖空間體系,如設置情節、安置人物、規劃動線等。美國城市文化研究學者莫妮卡·馬諾列斯庫(Monica Manolescu)新近出版的《紐約與其他戰后美國城市的制圖學:藝術、文學與城市空間》①Monica Manolescu,Cartographies of New York and Other Postwar American Cities: Art,Literature and Urban Spaces,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2018.文中所提及的英文學術著作書名與原文引文,如無專門注明,均系本人根據原文所譯,以下不予贅言。基于文學制圖學理論,探討文本與基于場所的實踐(site-oriented practices)之間的相互作用。②關于文學制圖學理論的研究,詳見Robert,Tally,Literary Cartographies: Spatiality,Representation,and Narrative,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2018。所謂場所實踐,指的是在步行與丈量中,城市圖景的空間構型通過位移的方式逐漸生成。換句話說,空間感并不只是基于靜態的視覺觀察,而是基于動態移動中的視覺捕捉而生成的。作者關注“城市繪圖是如何將文本與視覺再現納入認知、經歷與想象城市的龐大的體系之中的”。③Monica Manolescu,Cartographies of New York and Other Postwar American Cities: Art,Literature and Urban Spaces,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2018,p.1,239.在馬諾列斯庫看來,城市成為“難以辨認的書本”“互動戲劇的劇場”“卑鄙與貧窮的處所”“文學與建筑的肌理”“地圖與敘事的無限來源”。④Monica Manolescu,Cartographies of New York and Other Postwar American Cities: Art,Literature and Urban Spaces,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2018,p.1,239.該書探討了美國戰后藝術如何對城市進行空間構型,并擴大藝術創作的疆域。與此前學者批評戰后美國知識分子缺乏對城市建設、治理與管理的智性參與、理性批判的觀點不同,作者提出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盡管美國城市呈現日漸衰落的狀態,美國知識分子仍然在身體力行地參與城市的建設、再現與表述。正是這些文藝知識分子的不懈努力,使得紐約逐漸成為一個多樣的藝術表現場所。與罪惡化、田園化美國城市的兩極觀點不同,馬諾列斯庫從一個文學研究者的角度來理解藝術史與制圖學,探討20世紀60年代至70年代紐約的美學潛能(aesthetic potential)。在藝術家尋求突破的進程中,他們不斷地考慮自我與他者的關系,也不斷地考慮藝術能夠介入生活、介入政治的更具有具身性的參與方式。
正如該書作者所強調的,標題中的“文學”一詞不僅包括傳統意義上的文學范疇,同時也嘗試將藝術案例納入文學研究領域,討論文學文本如何與其他文本甚至藝術作品產生互文性的效果,以及在藝術與建筑領域的許多“修辭技巧”。許多藝術家同樣也進行詩歌與散文等創作實踐,彰顯藝術理念。該書的主要目的在于分析文學以及其他制圖技巧如何致力于將紐約、紐約郊區以及其他美國城市作為物質環境,作為文化和歷史建構,以及作為社會交往的空間來探討。①Monica Manolescu,Cartographies of New York and Other Postwar American Cities: Art,Literature and Urban Spaces,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2018,p.4.制圖學研究有其豐富的理論根基,近年來發展迅速。制圖者、藝術家以及作家都在建構制圖式想象的過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們往往通過想象圖譜來再現、建構城市。該書主要關注20世紀60至70年代的紐約藝術家的實踐——紐約的空間與都市身份被不同藝術家一再表述、修改甚至變異。通過關注在行走與測繪過程中的路徑、軌跡以及繪圖策略,該書呈現了步行藝術家在紐約與帕塞伊克的實驗性藝術方式。該書第2章從愛倫·坡的小說《人群中的人》(The Man of the Crowd)出發,探討都市現代性的核心問題:如何在人群中定位個人主體性?愛倫·坡的都市現代性體驗對于當代美國藝術家的創作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第3章主要關注在20世紀60年代的美國曼哈頓,各類藝術家在雕塑、裝置、表演等藝術形式上的實驗性嘗試。小眾畫廊的藝術家們通過藝術語言不斷定義對城市生活的理解,甚至有時候表達對政府規訓的反叛與不滿,體現鮮明的藝術風格與態度。第4章通過關注維托·阿肯錫(Vito Acconci)的詩歌、都市行為藝術、城市相關項目與建筑裝置這3個職業階段,追溯了阿肯錫從單純現代主義目的論的創作手法向文化話語與指涉(reference)方式的轉變,特別是將美國神話引入其創作之中,強調傳統小說遺產的重要性。第5章聚焦美國著名的大地藝術家羅伯特·史密森(Robert Simithson),作者認為史密森關于新澤西小城帕塞伊克的描寫并不只是旨在構建一個與紐約曼哈頓相對立的城市,而是將這座城市納入了美國與歐洲之間的文化交流之中。第6章關注的是戈登·馬塔-克拉克(Gordon Matta-Clark)最具概念化的創作項目“現實產權:虛假房產”(Reality Properties:Fake Estates),馬諾列斯庫指出,既往對于馬塔-克拉克的研究往往關注他在建筑學概念層面上對建筑物的破壞與分解的先鋒實驗性操作,而他真正關注的是財產、家園、土地測量、所有權等城市居住議題,這些議題暗含在他的藝術實踐與操演之中。最后一章從美國東海岸移至西海岸,關注舊金山文學家麗貝卡·索爾尼(Rebecca Solnit)的《無限之城:一部舊金山地圖集》(Infinite City:A San Francisco Atlas)。《無限之城》作為一部培育地方身份與歸屬感的制圖再現性質的散文作品,通過將故事與地圖疊加于地方之上,提供多版本的文本與地圖的契合模式,創造一種關于身份認同的全新觀念,同時也通過鮮活的故事描繪舊金山這座城市的別樣圖景。
該書為讀者打開了認識城市、了解國家、識別地圖的全新維度。當我們在談制圖學的時候,我們談的是關于永恒性、地產價值、社會規范等的各類概念,而不僅限于測量與制圖本身。文學制圖學歸根到底是研究文學地方性的問題,研究地方性元素以何種方式被呈現在作品之中。文學制圖學不是單純尋找文學作品中的地理界標與實際世界的一一對應,而是通過文學虛構地理坐標為我們重新定位,錨定個體的、具體的人在世界中的位置。馬諾列斯庫的研究為我們提供了通過文學制圖理論來認識文學地方性的全新角度,通過步行與測量的方式,呈現紐約是如何被定義、發現與再發現的。作者強調自己的研究不是鄉愁式的,也無關乎個體階級差異。我們在尋求文藝表達的多義性的時候也不要忘記,在所有的與地方相關的藝術創作和參與之中,蘊含其中的話語,值得我們一再推敲。從文學與藝術等虛構再現方式,到親身的實踐參與(步行、游蕩、穿越城市等),這些制圖或“反制圖”(counter-mapping,與現實相悖的空間想象模式),形成一種虛構/建構城市的全新模式。
而作為一部以心理地理學①近來中國學界關于西方文學心理地理學理論的引介與研究綜述,詳見孫銘:《文學心理地理學理論研究》,碩士學位論文,山東師范大學中文系,2019年。為理論基礎的文學評論著作,曹安(Ann Tso)的《倫敦文學心理地理學:艾倫·摩爾、彼得·阿克羅伊德、伊恩·辛克萊的不同世界》②Ann Tso,The Literary Psychogeogrpahy of London: Otherworlds of Alan Moore,Peter Ackroyd,and Iain Sinclair,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2020.將心理學、地理學與文學研究納入同一體系,這種跨學科研究在近年來并不多見,而該研究為我們提供了從心理學角度來解讀文本中的時空關系的角度。英國作家艾倫·摩爾是引領20世紀80年代美國漫畫變革的圖像小說家,他的許多作品深受大眾喜愛;而彼得·阿克羅伊德作為英國著名的傳記作家、歷史學者、小說家,其描寫城市的作品同樣值得大眾關注。該書第1章分析心理地理學家如何闡釋所謂的“倫敦性”。以往當我們探討“倫敦性”的時候,我們常常探討的是倫敦作為可復制的金融與交易中心的特性,而倫敦的奇思妙想性、不穩定性甚至矛盾性,構成了作家對于所謂“倫敦性”的全方位定義。對于倫敦這座城市,不同的人擁有不同的情景體驗。在第2章中,通過分析艾倫·摩爾的一本關于“開膛手”杰克的圖畫小說《來自地獄》(From Hell),作者指出杰克如何以超然的視角從倫敦歷史碎片中找到作為文化商品的英國遺產。艾倫·摩爾的這種將英國城市空間理想化的方式與其后來的作品《耶路撒冷》(Jerusalem)截然相反。在《耶路撒冷》中,城市變成混亂與不安的源頭。在小說家制造一系列空間概念的時候,往往也在挑戰想象與思考的極限。在第3章中,作者討論了彼得·阿克羅伊德的偵探小說《霍克斯默》(Hawksmoor),通過17世紀流浪者在倫敦這座迷宮般的城市的經歷,展示了心理地理學意義上的倫敦是如何以幽暗邊緣特質替代所謂的“帝國英國性”的。阿克羅伊德提供了貧窮、流浪以及發展停滯之類的讓“倫敦性”“貶值”的感官元素。在第4章關于伊恩·辛克萊的小說《白色的查普爾,猩紅色的蹤跡》(White Chappell,Scarlet Tracings)的討論之中,作者指出了理性規訓的不可能性。在最后一章中,作者提出了總結性的觀點:“倫敦性”是文學與心理地理學有機結合的產物,“倫敦性”或倫敦的城市性在文學作品中,往往存在于對城市隱秘性的解構與建構之中,在偶然的發現與挖掘之中,在切身感官體驗之中。文學心理地理學作為文學形式主義與革命政治結合的產物,其意義并不在于構建一個具有整體性意義的城市景觀,而在于不斷拆解與質詢,尋找不和諧的、多樣的城市身份政治。
二、空間理論:后現代時空與次級城市
城市空間不僅是人類生存的場所或背景,在城市研究學界漸漸達成共識,居民與空間互相形塑和影響。居民對于私人空間與公共空間的改造不斷更新城市的面貌,而城市本身也對居民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從時空維度來看待城市的發展與變遷,我們可以將城市與居民納入一個動態的、歷時性的、比較性的系統之中。邁克爾·凱恩(Michael Kane)的《小說與理論中的后現代時間和空間》①Michael Kane,Postmodern Time and Space in Fiction and Theory,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2019.探討了小說中的后現代時間與空間構型。空間并不只是小說故事情節的發生場所。空間是不穩定的、易變的,同時也是開放與包容的。當我們在討論空間問題的時候,從本質上我們是在討論現代性的遺產,討論城市居住的空間構型,討論時間與空間的關系等。該書主要討論的是在現代性意義上的時間與空間定義的變異(mutations)。作者借用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關于殘余(the residual)的定義,分析過去的因素是如何成為現在的有效的一部分的,不應完全拋棄過去而只關注現在。第1章《自然的空間》從討論浪漫派詩歌開始,作者認為“自然”并不是一種空洞的存在,而是往往被寫作者用來達到某些目的。也就是說,不同的作者在處理自然與風景等問題上,表現出極大的目的性。對于18世紀浪漫派詩人來說,自然被挪用為他們的自我想象,作為建構身份與組織記憶的材料。由人“制造”的崇高的(sublime)自然滿足了大眾的全部需求與想象,而這種所謂的后人類(posthuman)世界或后自然(postnatural)世界完全是基于由人改造的自然而形成的。在第2章中,作者從人類與自然空間關系的討論過渡到人類與城市空間關系的討論。這類時空關系往往鐫刻在城市的歷史脈絡之中,城市空間的歷時性與歷史性需要我們不斷加以推敲。第3章討論的是技術革新如何改變了大眾的時空觀念和感知。諸如電話、電影、自行車、汽車等科技工具的出現,不僅改變了人們的生活,也改變了人們的思考方式。然而作者對于技術改造的思考并沒有止步于追溯“改變”這一過程。在作者看來,通過對“時間”態度的考量,現代性與后現代性可以進行更明確的區分。第4章關注藝術的定義與藝術文化問題,論證本雅明、阿多諾與霍克海默之間關于文化工業之爭的問題。在最后一章,作者討論了后現代性甚至是超現代性的重要標志——旅行。旅行與旅游業對當地產生了什么影響?地方感以及關于自我的認知是如何通過旅行形塑的?作者的發問引人深思。當旅行成為一種個人甚至社會實踐的時候,旅行的意義就越來越豐富了。
這里主要詳談邁克爾·凱恩關于“城市空間”的研究。正如作者所說,近150年間,隨著人類活動空間范圍逐漸擴大、全球程式化進程加快,自然空間漸漸被城市空間所蠶食。從諸多文學作品以及理論研究出發,作者探討了大都會如何改變了個人精神生活。城市與現代性的辯證關系自19世紀以來不斷變革,通過討論本雅明、愛倫·坡、波德萊爾、恩格斯、狄更斯、福柯、陀思妥耶夫斯基對于19世紀城市的討論,邁克爾·凱恩展示了不同學者分析都市生活的方式。本雅明在《拱廊街計劃》中追溯了19世紀早期巴黎百貨公司的起源;鮑曼(Zygmunt Bauman)將在購物中心的購物者(stroller)定義為后現代的典型角色;齊美爾(George Simmel)在他1903年發表的著名文章《大都市與精神生活》中闡明都市生活對人的壓力:大眾建立了一種自我保護機制來避免受到外界的傷害,感官剝奪與方向感缺失成為城市居民在21世紀所面臨的最大問題。①關于保羅·維里亞奧的速度理論,詳見保羅·維里亞奧:《解放的速度》,陸元昶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4年。而該書所指出的便是城市人群如何定位自身的問題。根據作者的歸納和分析,現代城市生活經驗與現代資本主義的發展密不可分。資本主義發展史與城市日常生活經驗的關系是一個值得廣大研究者關注的問題。
目前眾多關于地理批評與空間批評的學者、地理學家、城市規劃學家等常常以城市的大小與功能、城市的位置、城市與周邊地區的空間結構關系等對不同城市進行分類;或使用經濟容量、人力資本、信息流通、政治參與、生活質量、文化底蘊等不同量化指標來劃定不同等級的城市。另外,許多后現代工業城市也無法納入這種等級體系之中。在《文學次級城市》(Literary Second Cities)②Jason Finch,Lieven Ameel,Markku Salmela,Literary Second Cities,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2017.中,眾多文學地理學研究者試圖挑戰這種分類機制。《文學次級城市》是一本集結2015年在芬蘭埃博學術大學(Abo Akademi University)召開的同名學術會議成果的論文集,該書引導大眾去關注那些被廣大研究者忽視的非一線的、具有標簽性和特色的城市——次級城市。③目前尚未有對second city統一與規范的翻譯。為避免與二類城市(second-tier city)概念相混淆,本文將second city譯為次級城市,用來指代被著名或重點城市名聲所遮蔽,但仍然在周邊區域甚至整個國家內占有重要的政治、經濟、文化或社會地位的那些次級城市。根據巴特·庫寧(Bart Keunen)的定義,次級城市指的是“只在世界部分地區具有有限可見度并且影響力有限”的城市,參見Jason Finch,Lieven Ameel,Markku Salmela,Literary Second Cities,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2017,p.22。諸如紐約、巴黎、東京、倫敦等特大綜合型城市常常被納入廣泛的考量與研究,而學界對于那些具有特色功能的城市往往投入的關注不多,比如拉斯維加斯、迪拜、威尼斯等。這些具有特色功能的城市同樣可以作為案例樣本來研究。在龐大的城市網絡中,我們往往會忽視中小型城市在全球城市資源流轉、功能分配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文學次級城市》為我們提供了理解那些不被我們關注的次級城市的文學再現。我們不再以面積、人口來衡量城市,而是從功能、作用等來定義城市。文學中的次級城市研究為我們理解城市發展路徑提供了全新的角度。
《文學次級城市》一書分為4個部分。第1部分不僅提出了文學城市研究的方法、路徑與核心議題,同時也對世界城市與次級城市的關系進行梳理。第2部分關注4個籠罩在一線城市陰影下的城市,包括18世紀的布里斯托、20世紀的伯明翰、愛沙尼亞第二大城市塔爾圖以及美國拉斯維加斯。在該書的第3部分中,“互為爭議的記憶”(contested memories)成為核心理論來源,許多“邊境城市”充當了重要的文化角色,這些城市提供的記憶資源與主流城市的記憶資源呈現相互對抗的局面。土耳其的迪亞巴克爾與愛沙尼亞的納爾瓦這兩個并不出名的城市均在國家歷史進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該書的第4部分探討了由互相關聯的小城市組成的次級城市。蘇菲·溫納斯基德(Sophie Wennerschied)從現象學角度研究當代瑞典小說,關注由青年占據的包括地窖、空置校園建筑以及荒原等特殊的城市“亞空間”,這些“亞空間”成為繁衍青年亞文化的重要場域。從小說的結構中我們可以發現,后工業城市的碎片化都市經驗與社會關系重新定義了城市生活。在該部分最后一篇關于移動文學景觀的研究中,杰德·彼得爾(Giada Peterle)提出在旅游城市威尼斯周圍,灰暗、樸素、平常的城市景觀與威尼斯的旅游美景完全不同,這就為我們打開了城市美學研究的全新維度。
作為文學城市學的代表之作,該論文集探討了如何通過文學再現來研究現實城市的問題。作為研究文學中的空間再現的學科,文學城市學涵蓋了文學地理學、空間人文以及地理批評學等學科資源。正如在該書結論部分所指出的,作者探討的所有文學城市(literary city)在某種意義上均屬于次級城市的范疇。對這些次級城市進行文學再現,不僅可以認識到這些城市的重要性,同時也揭示了如何認識城市的多樣性與多元性。我們不再以邊緣與中心的二分法來定義城市,而從更為實際的切面去認識那些被知名城市的光芒所遮蔽的城市。許多城市雖然沒有很高的聲譽,但卻依然在城市發展史中,特別是在城市更新與社會變革中擔任重要的角色。與此同時,這些城市也在不斷經歷著發展與演變。
《文學次級城市》的結語部分指出,目前研究城市文學有以下路徑:第一,文學地理學研究者運用城市文學材料,關注次級城市的生活經驗(次級城市形象與次級城市的地方感);關注次級城市淪為工業發展犧牲品的過程;關注城市空間身份政治(特別是移民);關注文學作品作為一種地理認識的來源——“一種對學術話語的補充與對立”。①Jason Finch,Lieven Ameel,Markku Salmela,Literary Second Cities,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2017,p.247.第二,關于城市的文學再現問題漸漸淡出研究視野,而基于文學創造、傳播、消費機制而確立的不同城市的等級標簽逐漸引起研究者的關注。換句話說,作者、作品、讀者與文學代理、出版機構在城市等級劃分中扮演了怎樣的角色?不同文學地圖的繪制是否暗含了復雜的權力關系?
三、結語
本文從空間和地理批評出發,總結了近來歐美城市文學研究的兩大新動向。歐美城市文學不斷更新、變換理論研究范式與框架,西方文學與文化研究領域中的地理與空間批評研究已逐漸開辟了新的道路與方向,為中國城市研究提供了諸多新思路。從理論貢獻來說,文學城市學研究為我們提供了諸多富有意義的觀點:第一,我們需要找到被宏大敘事所覆蓋的、歷史褶皺中的某些地方性與個體性元素,挑戰固化的城市建構觀,避免對城市采用單一化的量度與標準去評判。第二,我們也需要認識到不同的文藝形式參與了城市的建構,不可以忽視文藝形式所具有的巨大的功能性作用。對于城市的再現與批判,成為當代眾多知識分子的責任。第三,后現代城市的時間與空間的關系在當今社會具有鮮明的特色。城市空間的異質性以及空間與時間的互動性對于城市研究者而言是一大挑戰。第四,對于文學城市的書寫并不僅限于全球城市、特大城市或其他著名城市,我們也需要關注那些被忽視的邊緣性城市的歷史角色、發展脈絡以及城市架構。
文學城市學以文學地理學、空間人文、地理批評等理論為基礎,兼具跨學科的研究方法,為分析中國現當代城市文學與文化提供了借鑒,這些借鑒可以成為我們理解中國城市以及城市與人的關系的重要理論來源。中國現代文學城市學同樣是一個亟待研究者探索的領域。從文本再現的城市文學地理到城市文學心理學研究,中國現代城市文學需要借鑒更多其他學科的城市研究理論資源,豐富我們對中國現當代文學如何再現城市的理解與認知,并提供城市研究的“中國版本”。
不過,我們也要對國外城市研究方法的普適性與范式意義具有清醒的態度和認知。廣大研究者需要對國外研究理論框架是否能應用到中國情境之中加以甄別。
在對眾多不同類型文本的分析中,怎樣劃清學科邊界(或者,我們無需劃清學科邊界?),也需要有明確而深刻的認識。從文學研究的學科角度來說,文學與文化研究者往往基于文學文本研究文學對于城市的再現問題。從地理到空間,歐美城市文學研究者為我們提供了理解城市與文學關系的途徑。城市文學研究需要從文本出發,更好地厘清文學生產機制、文本構建形態以及文本歷史情境。在城市化進程急速推進的過程中,文學文本如何再現城市,城市如何影響文本,成為大家需要不斷思考的重要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