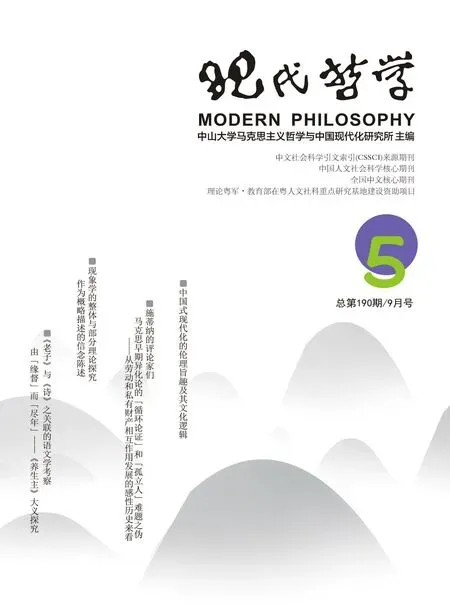先秦“樂”之五種審美形態的嬗變
王順然
一、緒論:作為背景的文化多元性
在近30多年的研究中,先秦時期“樂”常被劃分到“雅樂”與“新聲”(或“俗樂”“淫樂”)兩種類型中(1)簡摘數例,作為參考。比如,李方元在1991年和2018年的《音樂研究》中以“雅鄭”二元區分到:“在周代,宮廷雅樂是當時重要的音樂現象之一,與雅樂密切相關的另一重要音樂現象,是春秋初逐漸活躍起來的鄭聲……由此開始,歷史上雅、鄭觀念就形成了長期的對立。”“‘雅鄭’一語,初出春秋末孔子之口,‘雅鄭’對立之學術范疇亦由此而生。”又如,錢志熙以“雅俗”二元說,“所謂侈樂、鄭聲、淫聲,都是與雅樂相對的俗樂的代名詞,是春秋戰國音樂變革中的現象。”再如,有學者直說:“作為一種音樂學的術語,雅樂與俗樂相對……濮上之音與宋音、鄭音一樣都是俗樂。”(參見李方元:《周代宮廷雅樂與鄭聲》,《音樂研究》1991年第1期,第15頁;李方元:《“樂”“音”二分觀念與周代“雅鄭”問題》,《音樂研究》2018年第1期,第43頁;錢志熙:《音樂史上的雅俗之變與漢代的樂府藝術》,《浙江社會科學》2000年第4期,第124頁;鄒京航、曹建國:《試論周代雅樂制度》,《渤海大學學報》哲學與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1期,第115頁。),導致學界常以“雅”“淫”對立來解釋先秦乃至整個傳統文化中的“樂”審美(2)將多種審美追求統歸在“雅樂”一類之中,一方面使“雅樂”概念泛化,另一方面容易造成一種“雅”“淫”對立的印象。例如,修海林講:“從歷史文化的延承講,周代的禮樂活動只是原始祭典活動的延續、總結以及制度化。”“對立”的印象不斷固化,容易形成刻板印象,如“先秦俗樂,其主要目的是為了滿足感觀審美欲望的需要,因而其音聲中便包含‘淫’‘過’‘兇’‘慢’四種特征;先秦雅樂,主要適用于宗廟、朝堂等儀式需要,因而表現為緩慢、平穩,肅穆、莊嚴,廣大且曲直得當等音聲特征”。(參見修海林:《周代雅樂審美觀》,《音樂研究》1991年第1期,第74頁;何濤:《論先秦俗樂、雅樂的音聲特征》,《江海學刊》2007年第2期,第185頁。)。然而作為一種文化形式,“樂”審美形態的發展是在多元文化相融互攝的大背景下展開的:一方面新的形態往往根據舊有的文化元素發展而來,另一方面新的形態需要參與到多元文化的激蕩與選擇中,并在這一過程中不斷調整。(3)孔子對“三代損益”的討論就體現出這種文化、制度的動態發展。(參見陳來:《三代禮制之損益》,《古代宗教與倫理--儒家思想的根源》,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7年,第216-219頁。)這樣,“樂”之審美形態應呈現出多樣性與過渡性,以《禮記·明堂位》的記錄為例:
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于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昧,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納夷蠻之樂于大廟,言廣魯于天下也……土鼓、蕢桴、葦籥,伊耆氏之樂也。拊搏、玉磬、揩擊,大琴大瑟,中琴小瑟,四代之樂器也……夏后氏之鼓足,殷楹鼓,周縣鼓。垂之和鐘,叔之離磬,女媧之笙簧……
面對殊異的文化傳統,周公以“兼容并蓄”之策,在“制禮作樂”的過程中使虞、夏、商、周四代,華夏、夷蠻的不同文化有機共存。(4)“兼容并蓄”是小邦周的傳統,“周人在滅殷之后,最傷腦筋的問題,就是如何以自己微弱的主觀力量來有效地統治廣大的異族。當其封諸侯、建同姓的時候,其主要的目的,就是要這些有血緣關系的諸侯來‘藩屏’周室”。(參見李亞農:《殷代社會生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21頁。)這開啟了中華文明從“祭祀時代”走向“禮樂時代”的進程,也塑造了周初文化的多元性。(5)“夏以前的巫覡文化發展為祭祀文化,又由祭祀文化的殷商高峰而發展為周代的禮樂文化……夏以前是巫覡時代,商殷已是典型的祭祀時代,周代是禮樂時代。”(陳來:《古代宗教與倫理--儒家思想的根源》,第10-11頁。)同樣是對這一理念的貫徹,周公“作樂”,既有對不同制式樂器、樂律的融合,又有對不同風格樂曲、樂舞的兼采。由此,文化的多元性投射為審美形態的多元性。我們探討先秦時期“樂”之審美形態發展與變革,也要在這種文化多元性的大背景下展開。(6)文化的漸變體現在社會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對顏色的偏好與崇拜,也是其中的一個小中見大的角度。(參見郭靜云:《從上下到五方:禮儀的色譜與“無色”概念之形成》,《天神與天地之道--巫覡信仰與傳統思想淵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699-773頁。)
二、欲:從“靡靡之樂”到“亡國之音”
可以說,商紂王帝辛對傳統的叛離,拉開了“樂”之審美形態變革的序幕,我們也就不妨先從帝辛的“新聲”改革談起。帝辛對傳統的叛離,從《尚書·泰誓》記錄周武王姬發對他的批評中就可以看出,其言:“今殷王紂乃用其婦人之言,自絕于天,毀壞其三正,離逷其王父母弟,乃斷棄其先祖之樂,乃為淫聲,用變亂正聲,怡說婦人。”考慮到后世對商紂王罪狀的累加(7)顧頡剛曾綜合考證,發現紂的70多條罪狀都是周朝以后逐漸增加,劇情也逐漸強烈,戰國時期增加20項、西漢增加21項、東晉增加13項,對“德行”的崇尚,尤其是以“德行”衡量商紂王的行為,帶有明顯的周文化傾向。又以“酒”為例,《酒誥》借對“酒德”的確立展開對紂王的批判,但對“飲酒”本身而言,“酒德”是一種限制。(參見余治平:《周公酒誥訓--酒與周初政法德教祭祀的經學詮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158、171、236頁。),《史記·殷本紀》評價帝辛時說:“帝紂資辨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手格猛獸;知足以距諫,言足以飾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聲,以為皆出己之下。”這里,帝辛對傳統的反叛主要是以高揚個性、突出個人價值,來對抗祭祀傳統中對神祇的歌頌和對祖宗的宣揚。
“新聲”的創制也體現這一點,《殷本紀》說:“(帝辛)好酒淫樂,嬖于婦人……于是使師涓作新淫聲,北里之舞,靡靡之樂……益收狗馬奇物,充仞宮室……慢于鬼神。”帝辛以“新聲”廢棄“(殷)先祖之樂”,形成以“欲”為中心、“高揚個性、輕慢鬼神”之新審美形態。新的審美形態既表現為順從欲望的獵奇心理,如對“狗馬奇物”的追求,也表現在對新奇樂器、樂舞的創制。比如《釋名·釋樂器》說:“箜篌,師延所作靡靡之樂也,后出于桑間濮上之地,蓋空國之侯所存也。”(8)[漢]劉熙撰、[清]畢沅疏證、[清]王先謙補:《釋名疏證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第331頁。按照劉熙的講法,“箜篌”是紂王樂師師延專門為配合“靡靡之樂”而創造的、復雜的絲線類樂器。絲線類樂器多是小型樂器,本來有“更為靈活輕便,聲音也更為婉轉清脆、細膩柔美,表現力更強”的特點(9)楊華:《先秦禮樂文化》,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73頁。,而“箜篌”作為一種大型的絲線類樂器有著更廣的音域和更豐富的表現力,足見帝辛之“新聲”對“婉轉清脆、細膩柔美”的追求。
同樣出于“桑間濮上”的“亡國之音”,代表了帝辛以“欲”為綱的審美在后世的傳承與發展。《禮記正義》記鄭玄注說:“昔殷紂使師延作靡靡之樂,巳而自沈于濮水,后師涓過焉,夜聞而寫之,為晉平公鼓之。”(10)[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禮記正義》,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第14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1258頁。按照鄭玄的說法,“桑間濮上”的“亡國之音”與帝辛“新聲”有著明確的傳承關系。《韓非子·十過》對此記載較為詳細:
昔者衛靈公將之晉,至濮水之上,聞鼓新聲者而說之,乃召師涓而告之,曰:“有鼓新聲者,子為我聽而寫之。”師涓曰:“諾。”靈公遂去之晉。晉平公觴之于施夷之臺,酒酣,靈公起,公曰:“有新聲,愿請以示。”平公曰:“善。”乃召師涓,令坐師曠之旁,援琴鼓之。未終,師曠撫止之,曰:“此亡國之聲,不可遂也。”平公曰:“寡人所好者音也,子其使遂之。”師涓鼓究之……晉國大旱,赤地三年。平公之身遂癃病。(11)[清]王先慎:《韓非子集解》,《新編諸子集成》(全60冊),北京:中華書局,2018年,第67-70頁。
據文所見,衛國舊地“桑間濮上”保留了帝辛遺留的“新聲”。至春秋中期,衛靈公偶然得之,可知此“新聲”并不在常規演奏的周樂中。其中,師曠的表現也值得注意,他是在“(樂)未終”時制止了演奏,并非“樂”一開始便制止演奏。可見他雖未曾聽聞,卻應在樂師的傳承學習中了解“亡國之音”的特征。同時,重出江湖的“新聲”表現出強大的感染力,就通過衛靈公這次采風的契機很快在中原諸侯國流行起來。(12)照季札對《衛》的評價看,“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可以說,作為周姬姓子孫,早期衛國很好地傳承了周公禮樂的審美傳統,以“周德”所謂審美追求,所以季札在魯觀之《衛》并非“新聲”“淫聲”。衛靈公之于南子與帝辛之于妲己成呼應之勢,衛靈公“聞鼓新聲者而說之”可以算作帝辛審美的“知音”。在一定程度上,這種“淫聲”的迅速“崛起”擾亂了“正樂”的合理秩序,成為春秋禮樂崩壞的一個重要因素。按照《左傳》的編年,衛靈公見晉平公約在公元前533年左右,而子夏為魏文侯師約在公元前424年左右。
“新聲”的“復興”影響巨大,加速了先秦時期“樂”之審美形態的變革。《禮記·樂記》記子夏與魏文侯論樂一段,就講到“新聲”的審美發展出“鄭”“宋”“衛”“齊”四種風格:“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若以《左傳·襄公二十九年》記“季札論樂”為參照,我們能看到百年間“鄭”“宋”“衛”“齊”四地之樂的變化趨勢:其一,季札評“鄭”是“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而子夏說鄭音“好濫”,以“濫”取“濫竊”“過度”之意,顯然鄭音“細”而繁瑣的特點在“新聲”審美的刺激下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13)鄭玄依照《詩經·鄭風》中男女寄情的篇目較多而注“濫”為“濫竊”,可備一說。([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禮記正義》,第1311頁。);其二,季札的品評雖不包含“宋”,但子夏口中宋音之“燕女”是講樂舞中女子妖嬈的表現,體現了以“欲”為綱的審美特點;其三,季札評“衛”是“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這里的“衛”是周天子樂,是正面地表彰“衛康叔、武公之德”,而子夏評衛音是“趨數”,鄭玄注“促速”有追求表演技藝之意(14)表演技巧分很多類,其中就包括對樂器、樂律的追求,《漢書》記“泰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為二十五弦”。類似“箜篌”一樣,絲弦樂器如果弦音過密,旋律的情緒表現力就會加強。“破其瑟”的說法,即將相鄰弦音變大。,或可說衛靈公以降,衛國受“新聲”的影響而改弦易轍;其四,季札說“齊”是“泱泱乎,大風也哉”,這種“昂揚”的風格經“新聲”宣揚個性的鼓動,轉為“敖辟”之音。
總之,帝辛創“新聲”在叛離傳統的同時,拉開了“樂”審美形態嬗變的序幕。在“高揚個性、順從欲望、輕慢鬼神”的審美追求指引下,“新聲”至戰國初期已經發展出“鄭”“宋”“衛”“齊”等多種風格。風格的多樣性出于“欲”的追求,如《韓非子·十過》中平公所講:“寡人所好者音也,子其使遂之。”(15)“在一片批評聲中,戰國俗樂仍不可阻擋地發展,不僅吸引了一般的人,就連魏文侯這樣的好古者,也不得不承認新樂對于他的吸引力遠遠勝于古樂。”(錢志熙:《音樂史上的雅俗之變與漢代的樂府藝術》,《浙江社會科學》,2000年第4期,第125頁。)為順遂各國國君不同的“所好”,以“欲”為中心的“新聲”得到從樂器到樂曲、再到樂舞等層面的多重發展。值得補充的是,除了器物、樂理的層面外,到漢武帝時期,樂師李延年追求以天性之欲直擊人心,是以“每為新聲變曲,聞者莫不感動”(《漢書·外戚傳》),由“欲”進“道”,代表著形上層面對“新聲”的辯護。
三、語:從“接引神祗”到“圣王德行”
帝辛創“新聲”背棄“先祖之樂”,這里的“先祖之樂”指的是殷商祭祀傳統的“古樂”。周公“制禮作樂”效法“四代樂”“六代樂”,這里的“四代樂”“六代樂”指上古傳承的“古樂”。總體上,無論是“先祖之樂”,還是“四代樂”“六代樂”,基于其形式的一致性和傳承(說)的連貫性,可以統稱為“古樂”。這里“形式的一致性”是指,這類“古樂”通過“在舞臺上構建起一個脫胎于歷史情景的意義世界”來“展現圣王德性生命的歷程”。(16)王順然:《從“曲”到“戲”--先秦“樂教”考察路徑的轉換》,《哲學動態》2017年第5期,第47頁。而“傳承(說)的連貫性”是指,傳世或傳說的“古樂”比較固定(17)從指稱內容上看,對帝辛而言的“先祖之樂”相對確定,是指以湯樂《大濩》為代表的殷商祭祀之“樂”,而周公假托的“四代樂”或“六代樂”卻存在爭議。但無論是數目問題差異還是篇目差異,基本不影響本文的討論,故不贅述。。質言之,“古樂”審美的核心是“語”,是帶有政治功能的言說。我們可以借用以下文段來簡要概括:
(上)古者祀天地皆有樂,而神祗可得而禮。(《史記·孝武本紀》)
(中)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夔始制樂以賞諸侯。(《禮記·樂記》)
(下)夔!命汝典樂,教冑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尚書·舜典》)
由引文(上)可以看出,“古樂”在祭祀中發揮重要作用,用以接引神靈、祖先。《尚書·益稷》記錄帝舜時期創制《韶》的過程也有類似描述:“夔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群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閑。鳥獸蹌蹌;《簫韶》九成,鳳皇來儀。夔曰:‘于!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這里的“夔”是帝堯、舜時期的樂官,他是以“詠”的形式讓樂來“語說”祖宗的光輝事跡,而特定樂器、樂曲的運用是為了讓這些贊揚傳遞給祖宗神靈。“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閑”,就是以特定的聲音、節奏來引導神靈的降臨。可見,整個樂舞的文辭、配樂、配舞都是為了方便接引祖宗神靈。反之,只有祖宗神靈降臨的樂舞具有了“神跡”,才能保證神圣意志、保證祭祀傳統中樂舞的正統性。
這種對“古樂”神秘性與神圣性的強調,似乎更符合殷商以前的祭祀傳統,從文獻看也是這樣。李方元就認為,“西周后的雅樂作為直接體現宗教精神的意義開始有所減弱,而作為社會政治工具以維護等級制的功能在加強”(18)李方元:《周代宮廷雅樂與鄭聲》,《音樂研究》1991年第1期,第21頁。。而周以降,“古樂”的祭祀價值發生兩大變化。
其一,強調祭祀用樂的規范化。如《周禮·大司樂》講:“舞《云門》,以祀天神……舞《咸池》,以祭地示……舞《大韶》,以祀四望……舞《大夏》,以祭山川……舞《大濩》,以享先妣……舞《大武》,以享先祖。”祭祀的神圣性顯然受“神跡”的影響:既然只有“夔”能夠以樂引“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群后德讓”,那么“夔”就有擔當“大司樂”的神圣身份;既然“《簫韶》九成”能使“鳥獸蹌蹌、鳳皇來儀”,那“樂”就有與天地、鬼神、鳥獸的神秘關系。《周禮·大司樂》對“六代樂”演奏的規范,削弱了其中的神秘性:一方面,“六代樂”的演奏分別對應著“天神”“地示”“四望”“山川”“先妣”“先祖”,這種關系清晰明確;另一方面,對演奏的次數及效果,從“一變(遍)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示”到“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講明了準確的對應關系。
其二,對“古樂”解釋的德行化。《白虎通·禮樂》就講:
黃帝曰《咸池》者,言大施天下之道而行之,天之所生,地之所載,咸蒙德施也;顓頊曰《六莖》者,言和律歷以調陰陽,莖者著萬物也;帝嚳曰《五英》者,言能調和五聲以養萬物,調其英華也;堯曰《大章》,大明天地人之道也;舜曰《簫韶》者,舜能繼堯之道也;禹曰《大夏》者,言禹能順二圣之道而行之,故曰《大夏》也;湯曰《大護》者,言湯承衰,能護民之急也;周公曰《酌》者,言周公輔成王,能斟酌文武之道而成之也;武王曰《象》者,像太平而作樂,示已太平也;合曰《大武》者,天下始樂周之征伐行武,故詩人歌之:“王赫斯怒,爰整其旅。”當此之時,天下樂文王之怒,以定天下,故樂其武也。
引文的這種解釋顯然是在《大武》定型之后才得以系統建立,它將“古樂”在祭祀中的神秘作用,轉化為人人可理解的德行表現。以《韶》樂為例,前引《尚書·益稷》文本重點講《韶》的演奏如何產生神秘現象,卻并沒有說以《韶》是“舜繼堯道”;到《春秋繁露》,是說“舜時,民樂其昭堯之業也,故《韶》。‘韶’者,昭也”,這種講法依然保留了一些神秘的意味;到了《白虎通·禮樂》,就只剩下“舜繼堯道”的說法。
綜上,“古樂”在祭祀中的神秘作用,逐步轉化為對祖先、神靈之德行的宣揚,“語(說)”的對象也從“祖先、神靈”轉向“人”。可以說,以“語”為核心的“古樂”審美形態發生了從崇拜“神秘”向效法“德行”的轉化。《周禮·春官宗伯》對“大司樂”職責的解釋證明了這一轉折:“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于瞽宗。以樂德教國子……以樂語教國子……以樂舞教國子……”這里體現了周代學校對“樂”的使用,主要是以其中德行的體現來教化學子。
除在祭祀的作用外,(中)(下)兩條引文則體現著古樂“封賞諸侯”和“教化冑子”兩種作用。這兩種作用也是相輔相成,代表著古樂以“語”為核心的審美宗旨。
從封邦建國的角度看,以“樂”封賞諸侯表達了天子對諸侯政治身份的認同,也代表著文化共同體的建立。孔穎達在《禮記正義》對“制樂以賞諸侯”有這樣的疏解:“禮樂既備,后乃施布天下也……明圣人制樂以賞諸侯,其功大者其樂備。舜有孝行,故以此五弦之琴歌《南風》之詩,而教天下之孝也。‘夔始制樂以賞諸侯’者……欲天下同行舜道,故歌此《南風》以賞諸侯,使海內同孝也。”宣揚《南風》之教化,是諸侯對其政治身份的認同。這里的“孝”重在德行與政治規范,是“欲天下同行舜道”的一環,與后來儒家所重之“德性”有所不同。當孝行成為自上而下的風尚,也代表著天下對帝舜的擁戴。
王道施之于諸侯與王道傳承于“冑子”是同樣的道理:前者是將“孝”等德行與政治規范,依靠樂之“語(說)”封賞諸侯、宣告天下;后者則如《舜典》所說,是將“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等為政者的政治德行通過樂之“語(說)”教化“冑子”。隨著“古樂”宣揚之德行價值不斷凸顯,它們便化身為“語說”圣王“德行”的載體,“古樂”的神秘性弱化的同時,其用以“封賞諸侯”和“教冑子”的兩種作用也變得更為重要。
可見,以“語”為審美宗旨的“古樂”和以“欲”為審美宗旨的“新聲”有很大不同,前者注重效法前賢的政治德行,后者追求個性的極致表現。這種差異經商周兩代的文化互動而愈發顯明,催動著“樂”審美的發展與變化。
四、美:多元價值的混合
“古樂”“新聲”之爭為先秦時期“樂”審美形態的發展提供了內在動力,而周公的“制禮作樂”則將多族群不同審美傳統融合到周樂的體系中。如前引《禮記·明堂位》所見,周公制作之“樂”是融不同樂器、樂律于一體,在同一場景中按照特定次序進行演奏,如文見:“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昧,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納夷蠻之樂于大廟,言廣魯于天下也。”按《禮記正義》孔穎達疏曰,“升樂工于廟堂而歌《清廟》詩”,“堂下吹管,以播《象武》之詩”(19)[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禮記正義》,第1094頁。,這是講堂上、堂下進行著不同形式的表演。又曰“非唯用四代之樂,亦為蠻夷所歸,故賜奏蠻夷之樂于庭”,這是講“樂”之制作既容許《大夏》《清廟》等六代樂共存,又容許“奏蠻夷之樂于庭”,根據《白虎通》的解釋,庭中所奏的蠻夷之樂“《朝離》《南》《昧》《禁》”分別表達“生、養、殺、藏”四種不同價值。綜合來看,周公的“兼容并蓄”稍顯雜亂,這種復雜的、排列式的融合降低了“樂”審美形態的內在一致性。
上述《明堂位》的引文代表了相當一段時間內周樂的演奏形態,使得這一時期的審美不可避免地具有“多元性”。換言之,在整個“樂”在演奏過程中,每一部分的“美”都可以進行獨立的判定。《左傳·襄公二十九年》記“吳公子季札觀周樂”一段對此有充分的展示,文見:
吳公子札來聘……請觀于周樂。
(一)
使工為之歌《周南》《召南》,曰:“(a)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
為之歌《邶》《墉》《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
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
為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
為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
為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
為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b)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也。”
為之歌《魏》,曰:“美哉,沨楓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
為之歌《唐》,曰:“(c)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
為之歌《陳》,曰:“(d)國無主,其能久乎?”
自《鄶》以下無譏焉。
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
為之歌《大雅》,曰:“(e)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
為之歌《頌》,曰:“(f)至矣哉……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
(二)
見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
見舞《大(20)“大”字的出現代表著季札所欣賞的“周樂”已經是幾經更迭的周樂,較之周公制作之樂已經有所豐富。(參見王順然:《從〈大武〉“樂”看戲劇教化人心之能效》,《戲曲研究》第104輯,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17年,第147頁。)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
見舞《韶濩》者,曰:“(g)圣人之弘也,而猶有慚德,圣人之難也。”
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修之。”
見舞《韶箾》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
季札繼承周樂傳統(21)吳公子對周公傳統的繼承,代表著周天子文化的熏陶。(參見陳來:《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年,第224頁。):其一,“吳公子請觀周樂”與《明堂位》所說“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契合,魯用周公之禮樂、傳承有序,季札來魯國賞樂、評樂是再現周公審美之意趣;其二,季札所賞之周樂確有“兼容并蓄”之氣象,八方諸侯之歌誦、“濩”“夏”“韶”“武”四代圣王之樂舞盡在其中。同時,季札賞評“周樂”是對樂曲所反應之諸國風俗、政治進行判定與預言,這一方式也是以樂封賞諸侯的傳統。
季札對周樂的點評確是對每一部分的“美”進行相對獨立的判定:其一,將堂上之歌誦(一)與堂下之樂舞(二)分而論述;其二,諸侯之“風”與周之“雅”“頌”各按標準;其三,“自《鄶》以下無譏”一句表現出除風俗政治的審美旨趣外還有其他的審美判斷。根據季札的評價可知,這一時期周樂的審美形態以“美”這一概念為核心,將多重含義、多重標準收攝其中:“美”既可以從政治規范的角度來講,是表現于《周南》《召南》的“勤而不怨”,表現于圣王之樂的“周之盛”“圣人之難”“勤而不德”“天之無不幬、地之無不載”,等等;又可以從感官感受的角度來講,是表現于《鄭》的“其細也甚”;同時,季札評價時使用的“(a)美哉”“(b)大之至也”“(c)思深哉”“(d)國無主”“(e)廣哉”“(f)至矣哉”“(g)圣人之弘也”等概念,都統攝在“美”的范疇之中。(22)為了表明《韶》樂“美”到極致,季札將“德至矣哉”“大矣”“觀止矣”等說法連起來,強調《韶》各方面的“美”。
當然,“各美其美”的審美形態也與政治、文化政策的“兼容并蓄”相互參照。周樂對不同傳統的容納,是在尊重不同傳統中“美”之多元性的同時,將多元文化傳統中的“樂”向著“四代樂”引導,突出對圣王德行的歌頌,這一點也印證了前文對“古樂”的討論。從政治、文化層面講,“兼容并蓄”有著實踐中的過渡性和局限性。同樣,“各美其美”作為一種多元文化互動的審美形態,創造了一個審美形態相互借鑒的氛圍。但這種審美形態并不穩定,不同傳統間的張力需要在變革與發展中獲得釋放。
五、人/仁:從“習樂見人”到“依仁游藝”
根據《左傳》《國語》等文獻的記錄,至春秋中晚期,多元文化傳統進一步碰撞,“樂”不僅在祭祀中的神秘作用不斷弱化,其政治功能和現實價值也逐漸消解。在此背景下,孔子提出“人而不仁如樂何”(《論語·八佾》)的說法,以“仁”之超拔,為“樂”開出“見其人”的審美形態。“見其人”一詞出于“孔子學鼓琴師襄子”,在《史記》《孔子家語》《韓詩外傳》等均有記錄。《史記·孔子世家》曰:
孔子學鼓琴師襄子,十日不進。師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習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間,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為人也。”有間,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焉。曰:“丘得其為人,黯然而黑,幾然而長,眼如望羊,如王四國,非文王其誰能為此也!”師襄子辟席再拜,曰:“師蓋云《文王操》也。”
引文將孔子學琴分為“曲”“數”“志”“人”等四個階段:一者,每一個階段都對應一種獨立的審美標準;再者,不同審美標準依次排列、不斷超拔,形成一統攝的審美形態。
將四個層次分而論之,依次來看:
“習其曲”,代表孔子從“欣賞者”轉以“演奏者”的身份來面對《文王操》,這種轉變能使孔子對樂曲的領會更為細致。一段時間后,師襄子第一次對孔子說“可以益”,鼓勵孔子增加一些新的內容(旋律)來學習。不斷尋求新的內容,對應著“好新聲”的審美追求。
孔子并未采納師襄子勸其求“新”的建議,而是進一步在“曲”中見“數”。前文見季札說《鄭》是“其細(數)已甚”、子夏評《衛》是“趨數煩志”,“數”“細”都是對應樂律來說的。“習其數”,一方面代表著孔子能夠像樂工一樣從樂律層面來處理樂曲,另一方面代表在跟隨感官感受而“求新”之外,知覺理性也可以介入對樂曲的理解。因此,“數”本身成為一個有別于“曲”的獨立審美標準。
順著“數”向前,“志”“意”就在理解中逼顯出來。“志”“意”與“古樂”的審美形態相關,重在樂的“語(說)”教化能力。師襄子傳承樂教,對“志”“意”之境很熟悉,也就能看出孔子“得(曲之)志”的不凡之處。真正令師襄子“辟席再拜”的,是孔子達致“見其人”之境界。
這里需要對照《韓詩外傳》的相關引文來看。(23)《史記·孔子世家》引文與《韓詩外傳》相關文本的差異需要注意。前者將孔子學琴分為“曲”“數”“志”“人”等四個階段,《韓詩外傳》則增至“曲”“數”“意”“人”“類”等五個階段。對照《論語》的語詞習慣來看,《韓詩外傳》所用的“偉”“粉”“彈”“麗”等不符合孔子的言說習慣,而且“類”更接近一種對“見人”的補充性解釋,由此推知《韓詩外傳》“孔子學琴”之成文當在《史記》之后。按照《韓詩外傳》的說法,孔子是以“偉”“粉”“彈”“麗”等樂曲表達的“志”“意”,歸納出作曲者有“仁”“和”“智”“殷懃”的德行,再根據這種德行之“類”倒推出作曲者是周文王。這一說法將“見其人”“得其類”“習其志”等都落在外在德行來講,反而丟失了“見其人”的境界意義。只有將“見其人”和“人而不仁如樂何”連看,才能在“人/仁”的這個最終境界中看到從外在“德行”向內在“德性”的審美轉向。
“德行”向“德性”的轉變有著重要意義。《五行篇》記曰:“仁形于內,謂之德之行;不形于內,謂之行。”仁德根植于內心的行為叫“德之行”,可以是尚未表現出來的“品性”,這和表現為事功之“(德)行”有差別。孔子透過樂曲看到的是文王的“仁”,這是“品性”而不僅僅是“德行”。所以說,《韓詩外傳》在文本上的補充雖然讓孔子之“見人”更符合邏輯,但在境界上反而落了下乘。當孔子起身“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焉”(《史記》)時,是樂曲演奏過程中,心靈產生的共振與感通。《禮記·樂記》說“(樂)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文王操》作為共振的中介,讓孔子對文王產生一種“同聲相應”的感通。
將四個層次統合來看:孔子所言之“見其人”是發前人之未發,在境界上是對“語”之審美形態的超越。這種審美標準的建立有兩層意義:一是將多種獨立的審美形態融合成系統,二是為“樂”建立起內在德性的價值。正面講,確立內在德性的審美價值,是將圣王之“圣”落在德性上講,不同的審美標準在這一體系中得以融攝;反面講,要提升審美境界,首先要確立對內在德性的追求。
與此相應,《樂記》記子夏論樂充分反應出子夏對孔子“見其人”之審美形態的繼承。對于文侯“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的“病癥”,子夏開出的對治之方是“君子之聽音,非聽其鏗鎗而已也,彼亦有所合之也”,這也是對“見其人”三字的解釋。以“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為例,君子借樂器(如“絲”)所發聲音對情感(如“哀”)的引動,喚起與情感對應的德性心理(如“廉”),再將此內在德性投射為外在德行(如“志義之臣”)。(24)《禮記正義》記孔穎達疏曰:“哀,謂哀怨也,謂聲音之體婉妙,故哀怨矣。廉,謂廉隅。以哀怨之,故能立廉隅,不越其分也。既不越分,故能自立其志。”([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禮記正義》,第1314頁。)由此,“琴瑟之聲”與“志義之臣”的共振,便是君子辨識“古樂”的進路,也是“見其人”的進路。
總之,孔子提出“見其人”,恰將“樂”看作體貼圣人內在德性的依憑。其云“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論語·陽貨》),就是強調在“見其人”境界中,“樂”成為啟發內在德性的鑰匙。
六、和:先秦“樂”審美的定型
“見其人”的審美形態已將傳統中多元的審美形態加以融攝,形成一個“曲”“數”“志”“人”層層遞進的體系。針對這一審美形態,先秦諸子還有進一步的爭論。
墨子的“非樂”雖然聞名,但其言“非以大鐘、鳴鼓、琴瑟,竽笙之聲,以為不樂也”,這對“樂”之審美形態而言并無損益。然墨子倡導以“利”為標準,判定當時之樂是“上考之,不中圣王之事;下度之,不中萬民之利”,可以看做是注重“樂”的現實功能性、政治性,也是對“語”之審美形態的復興。事實上,真正對以“仁/人”為核心的審美形態產生重要影響的,一是老莊對“自然”的高揚,二是孔門后學對先秦人性論討論的深入。
具體而言,于前者,不同于孔子以“樂”啟發人內在德性,老莊將“自然”作為“樂”審美的終極追求。無論是“大音希聲”(《道德經》41章),還是“女聞人籟而未聞地籟,女聞地籟而未聞天籟”(《莊子·齊物論》),老莊欲在逐步消解有聲之樂的過程中,進入無聲之“自然”。這就在“仁/人”之外又增加了“自然”的最高價值。于后者,人情、人欲是否應該放在審美形態的最底層,得到重新審視。《荀子·榮辱》說:“人之情,食欲有芻豢,衣欲有文繡……然而窮年累世不知不足。”在對“樂”之美感的探求中,人情、人欲本來就是樂官從事專業工作的重要基礎。當瞽叟成為上古樂官的代表時,感官欲求也已成為神秘且私密的認知方式。可見,人情人欲在“樂”的審美追求中有特殊價值,不能簡單地放在最低一層看。
同時,基于感官欲求而進行的樂器翻新、樂律更制與樂舞設計等,要分情況看待。拿樂器創制來說,有被稱為圣王德行的,如“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有被看作放縱欲望的,如“(周景)王將鑄無射,而為之大林”。既然帝舜造五弦琴、周景王造無射大鐘都離不開感官的指引,那么人情、人欲的“節制”與“放縱”就需要尋求新的標準來判定,“和”概念的價值也被重視起來。
按照《國語·周語下》的說法,“和”本來就是“樂”之審美形態的重要標準:“王不聽,卒鑄大鐘。二十四年,鐘成,伶人告和。二十五年,王崩,鐘不和。”然而,這里“和”的意義是不確定的,伶人口中制成“大鐘”的“和”,與“王崩,鐘不和”形成了判斷的對立結果。依賴于外在后果或者事后反思,都代表著此時“和”的審美理論還有模糊性。到《莊子·天地》說“無聲之中,獨聞和焉”時,“和”才被看作是一種獨立的審美形態。“聞和”代表著“和”成為一種追求、一種從“有聲”到“無聲”最終指向的境界。這種境界不同于“見其人”之處,就在于它不再以向內之“仁”為追求,而走向與天地自然為一體的新路向。“和”的上升并未就此止步,“仁”與“自然”也有相通之處。到《禮記·樂記》,“和”有了系統性的解釋,以“和”為核心的審美形態才得以完型。《樂記》論“和”有兩段重要的文字是:
(一)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和故百物不失,節故祀天祭地……地氣上齊,天氣下降,陰陽相摩,天地相蕩,鼓之以雷霆,奮之以風雨,動之以四時,暖之以日月,而百化興焉。如此則樂者天地之和也。
(二)《詩》云:“肅雍和鳴,先祖是聽。”夫肅肅,敬也;雍雍,和也。夫敬以和,何事不行?……是故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族長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親萬民也,是先王立樂之方也。
引文一是從宇宙氣化的角度講“和”,“樂”的審美要符合自然的規律,樂律的意義和感官欲求的價值由此建立。在這一點,“和”的理論具備了客觀性與普遍性。引文二則是從人倫道德的角度講“和”,這里包括君臣之敬、長幼之順、父子之親,還包括祖宗神靈的神秘關照(25)所謂“肅雍和鳴,先祖是聽”,肅肅敬也、雍雍和也。《禮記·少儀》也說“鸞和之美,肅肅雍雍”。可見,“和”在祖宗神靈的層面接續了“樂”在祭祀傳統中的審美旨趣。,安頓人情的尺度由此證成。“和”在宇宙氣化和人倫道德兩方面的意義是并行的:一部分感官之“欲”歸攝在對自然的認知和對自然美的追求之中,一部分性情之“欲”歸攝在對人倫的直觀和對倫常和諧的維護中。
以此再看“舜作五弦琴”和“景王作大鐘”兩例,不難發現:從自然的角度比較,帝舜之“五弦琴”和于音律、《南風》悅耳動聽,景王大鐘的巨大聲響反而直接傷害了景王的生命;從倫常的角度比較,《南風》宣揚孝悌、注重人倫,景王為造大鐘以君壓臣、耗費民財,違背君臣之敬、父子之親。這種審美標準不再向外尋求神秘后果,而是將判斷內化于“樂”本身之中。
可以說,《樂記》用“和”融攝了多元的審美形態,成為先秦時期“樂”之審美形態的一個綜合。“和”的審美,擺脫了“古樂”審美的外在性與神秘性,修正了“曲”“數”“志”“人”層層遞進的線性結構,吸收“欲”作為審美形態的一個支點,并開出通向“自然”“人倫”的兩層價值。
綜上,站在多元文化融合的立場上看,先秦時期“樂”之審美形態是在相互批判與吸納之中逐次展開的。在經歷“對立”“兼容”“歸攝”等階段后,“樂”之審美先后表現出以“語”“欲”“美”“人(仁)”“和”等觀念為核心的五種形態。加之每一種審美形態又發生著內在的轉化與革新,這使先秦時期“樂”的審美形態更加豐富,補充了以往學界“雅”“淫”二分的“樂”審美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