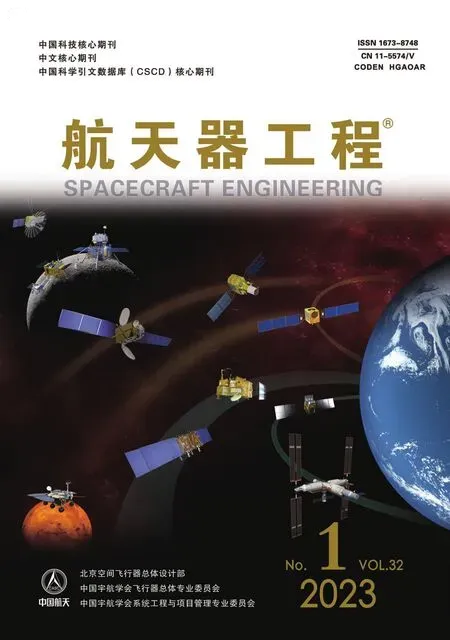國外衛星搭載有效載荷發展綜述
王久龍 徐晨陽 曾文彬 蔡盛
(中國科學院長春光學精密機械與物理研究所,長春 130033)
近幾年來,隨著航天技術的不斷發展和航天產業的日益擴大,以低軌巨型星座[1]為代表的商業航天得到迅速推進,航天產業呈現新的發展態勢,大規模低成本進入太空的時代已經來臨。同時,為保持太空優勢和太空行動自由,美國等發達國家全面調整了太空發展策略[2],提出以下一代太空體系架構、“黑杰克”項目等為典型代表的計劃,改變了以往以大型復雜單星為主的模式,將建設重點轉向由多顆小衛星組成的靈活、彈性、敏捷的低軌星座。
搭載有效載荷已經成為太空體系彈性發展的重要方式之一,為推動相關技術發展,美國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舉措。2010年,美國《國家太空政策》強調要聯合采辦可靠、進度符合政府要求,且費效比高的航天發射服務和搭載有效載荷,明確提出鼓勵政府發展搭載有效載荷,提高空間態勢感知和軌道碎片的監測能力。2011年,美國波音、洛馬、勞拉、軌道科學、歐洲衛星協會、國際通信衛星、銥星等7家公司發起成立搭載有效載荷聯盟,旨在架起政府和私營企業的溝通橋梁,促進搭載有效載荷的實施。2013年,美國海軍研究生院開展了搭載有效載荷的應用研究,建立了基于搭載有效載荷的天基局部空間態勢感知架構,將搭載有效載荷放置在宿主衛星平臺前后方,以對局部空間區域進行長期觀測,實現威脅自感知、目標檢測和碰撞預警,為實現天基態勢感知提供了新的解決思路[3]。2015年,美國空軍發布《在商業衛星上搭載軍用載荷指南》[4],分析了在商業衛星上搭載有效載荷面臨的挑戰,成立搭載有效載荷管理辦公室,簡化相關項目的授予流程,促進商業衛星搭載空軍有效載荷的實施。2018年,基于通用儀器接口項目,NASA聯合空軍空間和導彈中心的搭載有效載荷辦公室以及航天公司發布《搭載有效載荷接口指南提案》[5],描述了搭載有效載荷與宿主平臺之間的接口協議,包括尺寸、質量、功率和傳輸速率,旨在為相關組織開發基于低軌或高軌衛星有效載荷提供標準。為了研究搭載有效載荷的發展現狀和軍事應用價值,本文系統性的梳理了搭載有效載荷的概念和發展歷程,總結了典型項目的系統概況、指標參數,并提出相關建議。
1 搭載有效載荷概念
搭載有效載荷[6]是指除主要載荷外搭載在衛星平臺上的、為滿足特殊需求而設計的額外載荷(如轉發器、傳感器或者其他星載設備)。搭載有效載荷與主要有效載荷共用一個衛星平臺,使用戶能夠快速高效且低成本的將有效載荷送入太空。在某些情況下,搭載有效載荷也被稱為二級有效載荷或寄宿有效載荷。宿主衛星平臺為搭載有效載荷提供結構、能源和通信等資源,二者物理連接和傳輸接口關系如圖1所示。

圖1 搭載有效載荷接口Fig.1 Hosted payload interfaces
搭載有效載荷的費用僅是研制、發射與運行整顆衛星費用的一小部分,可以有效降低衛星建設和部署成本,因此,逐漸受到業界的廣泛關注,尤其是面臨預算壓力的機構。當然,在衛星平臺上搭載有效載荷也面臨一些挑戰,比如怎樣實現宿主衛星平臺與搭載有效載荷的接口標準化、如何確保搭載有效載荷與宿主衛星的研制周期相一致、怎么改變用戶對傳統衛星項目的管理方法、如何確定搭載有效載荷的價格等。
2 國外發展現狀
搭載有效載荷在國外已經初步得到廣泛的應用,任務領域包括空間態勢感知[7]、碎片監測[8]、激光通信[9]、定位導航[10]以及氣象監測[11]等領域;按照載荷的任務類型,本文從環境監測類載荷、技術試驗類載荷以及專用轉發器類載荷角度出發,介紹近年來國外搭載有效載荷的發展動態。
2.1 環境監測類載荷
為了研究空間天氣對氣候、全球定位系統、電力傳輸、高頻無線通信以及衛星通信的影響,NASA牽頭研制了太陽X射線成像儀(SXI Solar X-ray)[12],工作波段為0.6~6.0 nm,可每分鐘成像一次,每周7×24 h運行,2001年搭載環境觀測衛星-12(GEOS-12)發射。2005年,由美國勞拉空間系統公司建造、日本國土交通省和日本氣象廳運營的地球靜止衛星多用途運輸衛星-IR(MTSAT-IR)發射升空,搭載了航空類和氣象類2種有效載荷,航空類載荷分為通信載荷和導航載荷,為飛機提供通信和導航服務;氣象類載荷由1個可見光(分辨率1 km)成像載荷、4個紅外(分辨率2~4 km)成像載荷以及1個氣象通信載荷(S頻段、UHF頻段)組成。2008年,為執行對地觀測任務,美國軍方將可見光CCD相機作為有效載荷搭載在美國回聲星-XI(EchoStar-XI)和中圓軌道-G1(ICO-G1)衛星發射升空。2011年,為降低下一代天基紅外預警系統的研制風險,美國空軍啟動了商業搭載紅外有效載荷(CHIRP)項目[13],即用于導彈預警的寬視場紅外傳感器,搭載平臺為歐洲衛星公司2號衛星(SES-2)。2018年,美國導彈防御局啟動天基殺傷評估(SKA)項目[14],利用天基傳感器獲取導彈攔截狀態,并對攔截效果進行評估,為后續攔截提供支持。2017年,為解決航天器異常、識別潛在敵對行為提供詳細的空間輻射數據,美國空軍啟動商業搭載的響應式環境評估(REACH)[15]項目,在銥星(Iridium)星座上搭載32個有效輻射載荷。
2.2 技術試驗類載荷
搭載有效載荷為新技術的正式太空部署提供了一種測試、演示與驗證的新方式,美國軍方、NASA等部門都紛紛利用這種方式進行新技術的試驗。2009年,為在軌驗證思科公司的空間路由能力,美國國防部將空間因特網路由(IRIS)[16]有效載荷搭載在國際通信衛星-14上發射升空,該載荷質量90 kg,功率450 W,體積0.127 m3,用戶數據率60 Mbit/s。2011年,為驗證地球同步軌道與地球之間雙向激光中繼通信的效果,美NASA啟動了激光通信中繼演示(LCRD)項目[17],載荷由2個單獨的收發光通信終端和1個高速電子單元組成,地面系統由1個任務運營中心和2個地面站組成,2021年12月搭載空間測試計劃衛星-6(STPSat-6)上發射,初步研究結果表明:激光通信傳輸速率比射頻高10~100倍,可滿足空間科學和爆炸領域對更高數據速率的日益增長的需求。2018年,為將可釋放的有效載荷運送到地球同步軌道,降低天基系統研制成本,作為“鳳凰”計劃[18]的一部分,美國國防部先進研究計劃局啟動了有效載荷在軌交付系統(POD)[19]項目,將由4顆小衛星構成的POD發射成功,順利進入地球同步轉移軌道。
2.3 專用轉發器類載荷
專用轉發器作為搭載有效載荷,不僅可提供可靠的通信能力,還能夠根據用戶需求選擇特定通信頻段,已逐漸成為各國快速構建天基通信能力的主要手段。2003年,澳大利亞國防部在民用澳普圖斯-C1(Optus-C1)衛星平臺上搭載了軍用UHF/X/Ka頻段的通信載荷[20],UHF頻段有5個5 kHz和1個25 kHz的轉發器,用于低數據速率雙向語音和數據通信;X頻段有4個60 MHz的轉發器,用于中高數據速率單向、雙向視頻以及語音、數據通信;Ka頻段有4個33 MHz有源轉發器和1個備用轉發器,用于中高數據速率覆蓋和雙工視頻、語音和數據通信。2012年,由國際通信衛星公司為主承包商,攜帶澳大利亞國防部隊專用超高頻有效通信載荷(ADF UHF)的國際通信衛星-22(IntelSat-22)發射升空,載荷由波音公司研制,具有18個UHF轉發器,頻率為25 kHz,此外該星還搭載48個C頻段轉發器、24個Ku頻段轉發器。2005年,由美國勞拉航天公司和西班牙共同研制的“X星-歐洲”(XTAR-EUR)通信衛星發射升空,搭載了北約可配置X頻段載荷,具有12個72 MHz的轉發器,總功率100 W,用于加強西班牙與北約軍事、外交和保密通信業務。2006年,由美國勞拉公司研制的西班牙軍用電信衛星(Spansat)發射升空,搭載有效載荷為在軌可重構多波束天線(IRMA)[21],該天線的4個波束可以從地面單獨重新定向,無需移動天線本身,主要服務于西班牙國防部,與XTAR-EUR衛星一起使用,為軍事行動、圖像傳輸、大使館服務和政府通信提供支撐。2008年,美國海岸警衛隊將國家自動識別系統(NAIS)的甚高頻通信載荷搭載在軌道通信衛星(Orbcomm)上發射升空,該載荷質量3 kg,功率8 W,體積0.003 m3,數據率10 kbit/s,用于增強現有的自動識別系統,實現海域態勢感知。2005年,美國聯邦航空管理局將廣域增強系統[22]的L頻段轉發器作為有效載荷搭載在銀河-15(Galaxy-15)衛星以及加拿大阿尼克-F1R通信(Telesat Anik-F1R)衛星上發射升空,此后又分別于2008年、2016年、2017年、2022年搭載國際海事衛星-4F3(Inmarsat-4F3)、墨西哥-9通信衛星(Satmex-9)、歐洲衛星公司15號衛星(SES-15)以及銀河-30(Galaxy-30)衛星進行補充發射。2011年,搭載Ka頻段通信載荷[23]的高吞吐量衛訊衛星-1(ViaSat-1)發射升空,該載荷發射頻率為28.1~30.0 GHz,接收頻率為18.3~20.2 GHz,質量34 kg,功率185 W,用戶速率可達10 Mbit/s,設計壽命15年,主要為加拿大農村地區提供高質量寬帶服務。2012年,歐洲衛星公司5號衛星(SES-5)成功發射,主載荷為24個C頻段和36個Ku頻段轉發器,搭載有效載荷為L1和L5頻段的轉發器,作為歐洲地球靜止導航重疊服務(EGNOS)[24]一部分。2022年,美國空軍通過其增強型極地系統資本重組(EPS-R)計劃完成2顆超高頻通信有效載荷研制,旨在為北極地區的美軍提供安全、抗干擾的衛星通信能力,計劃2023年搭載在挪威太空公司的北極衛星寬帶任務上發射。
3 典型實例
近年來,國外成功開展了多項搭載有效載荷應用案例,領域覆蓋導彈預警、定位導航、衛星通信、殺傷評估等方面,本文選取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項目進行介紹,如商業搭載紅外有效載荷、廣域增強系統、澳大利亞國防部超高頻通信有效載荷、天基殺傷評估,分析搭載有效載荷的應用現狀。
3.1 商業搭載紅外有效載荷
商業搭載紅外有效載荷(CHIRP)由美國空軍于2010年提出,在一顆商業地球靜止軌道衛星上搭載一個軍用紅外載荷,通過在軌收集紅外數據,以研究用于導彈預警和防御的寬視場相機、紅外凝視型傳感器的性能。歷經39個月的研發,于2011年9月搭載SES-2衛星發射升空,在軌運行27個月后于2013年12月正式停止使用,運行期間共采集超過300T紅外數據,為美國空軍分析70多次導彈/火箭發射事件以及150次其他紅外事件提供幫助。CHIRP上的寬視場紅外望遠鏡由科學應用國際公司開發,長、寬、高尺寸為75 cm×54 cm×75 cm,質量為75 kg,探測波段包括短波紅外、中波紅外以及直視地表波段(See-to-Ground),像素規模2000×2000,可實現對1/4地球圓盤凝視觀測,外觀結構如圖2所示。

圖2 CHIRP紅外載荷Fig.2 CHIRP infrared payload
CHIRP載荷的宿主平臺為地球同步軌道通信衛星SES-2,衛星平臺為軌道科學公司開發的STAR 2.4,包含一個標準化的次級載荷接口、專用的有效載荷熱輻射器以及由宿主轉發器提供的任務數據通信模塊,CHIRP載荷在宿主平臺上的布局如圖3所示。

圖3 安裝在宿主機上的CHIRP載荷Fig.3 CHIRP payload mounted on host
CHIRP的任務目標包括:
(1)提供實戰環境數據,開發和評估寬視場(WFOV)地球圓盤凝視算法;
(2)驗證凝視算法的性能;
(3)使用大規模焦平面陣列(FPA)評估WFOV性能;
(4)評估衛星平臺對WFOV傳感器約束邊界,包括視軸穩定性、熱穩定性指標和性能。
3.2 廣域增強系統
廣域增強系統(WAAS)是美國專為民航開發的基于衛星的導航增強系統,該計劃始于1992年,由美國聯邦航空局負責實施,2003年7月10日開始運行。WAAS由38個廣域監測站、3個廣域主控站、7顆地球靜止軌道衛星、6個地面上行注入站、2個操作控制中心以及陸地通信網絡組成(見圖4),可覆蓋美國本土、阿拉斯加、加拿大和墨西哥等大部分北美地區[25]。

圖4 WAAS系統體系架構Fig.4 WAAS architecture
第11屆中國衛星導航年會上,美國國務院空間事務辦公室指出WAAS為北美4700多個民航機場提供帶垂直引導的航向道進近程序(LPV)服務,其中1000多個民航機場具備決斷高度為60.96 m的帶垂直引導的航向道進近程序(LPV-200)能力,達到I類精密進近操作(CAT-I)服務水平[26]。近年來,美國政府積極采用搭載有效載荷的方式開展WAAS系統的研究工作。2005—2008年,美國聯邦航空管理局采用在商用通信衛星上搭載有效載荷的方式,將L頻段轉發器托管在Galaxy-15、Telesat Anik-F1R、Inmarsat-4F3衛星上,有效載荷質量為60 kg,功率達到300 W,體積為1 m3,用戶數據率為10 Mbit/s。2016年6月,WAAS系統有效載荷搭載Satmex-9衛星發射升空,并于2018年3月投入使用,以取代Inmarsat-4F3衛星上的舊載荷;2017年5月,WAAS系統有效載荷搭載SES-15衛星發射升空,并于2019年7月投入使用,以取代Galaxy-15衛星上的舊載荷;2018年,美國萊多斯公司擊敗雷神公司獲得聯邦航空管理局1.17億美元訂單,用于開發第7代靜止軌道通信載荷,2020年8月搭載Galaxy-30衛星發射升空,2022年4月投入使用。圖5展示了WAAS系統歷史上所使用的商業衛星平臺。

圖5 WAAS的衛星Fig.5 WAAS satellites
3.3 澳大利亞國防部UHF有效載荷
超高頻(UHF)是指工作波長范圍為1 m~1 dm、頻率為300~3000 MHz的無線電波,廣泛用于軍事衛星通信領域,特別適合陸地、海上、空中部隊使用的移動手持終端[27]。為了給部署在中東和阿富汗地區的澳大利亞軍隊提供超高頻通信能力,2009年4月,澳大利亞國防部與國際通信衛星(Intelsat)公司簽訂1.67億美元合同,購買國際通信衛星-22(Intelsat-22)衛星上的超高頻段載荷的全部容量,即18個25kHz信道;根據合同要求,Intelsat公司負責ADF UHF有效載荷的研制、集成和運管,并且在衛星發射后的15年間為澳大利亞提供相關的載荷管理服務,包括超高頻通信系統監控和在軌測試等[28]。2012年3月,Intelsat-22衛星發射成功,運行在星下點72°E的地球同步軌道上,ADF UHF有效載荷擁有18個25 kHz的大功率轉發器,總體積為8 m3,約占Intelsat-22衛星總有效空間容量的20%,質量為450 kg,功率為2 kW。據澳大利亞政府估計,在ADF UHF載荷的15年壽命中,與單獨發射衛星相比,采用搭載有效載荷的方式可以節省1.5億美元。
3.4 天基殺傷評估系統
美國2014財年《國防授權法案》要求美國導彈防御局應為地基中段防御系統提供改進的殺傷評估系統,并最晚在2019年12月31日前具備初始作戰能力[29]。于是,2014年4月,導彈防御局啟動天基殺傷評估項目,截止到2019財年,總研發經費1.2億美元,實現了在軌初步運行。單個SKA傳感器質量約10 kg,由1個高速光譜傳感器、1個高速偏振成像傳感器和1個高速偏振非成像傳感器組成[30],從圖6可以看出,3個傳感器共用一套處理器、控制器和基座。高速光譜傳感器用于對攔截中產生的輻射、熱和光譜等信息進行成像,高速偏振傳感器主要用于確定攔截時產生物質(碎片、顆粒、等離子體、氣體等)的粒度分布,以確定彈頭的類型。

圖6 天基殺傷評估傳感器Fig.6 Space-based kill assessment sensor
迄今為止,美國國防部和導彈防御局未公布SKA載荷具體搭載在何種衛星上,結合美國2017財年導彈防御局預算申請文件[31]以及第二代銥星系統(Iridium NEXT)發射計劃,推測SKA載荷部署在Iridium NEXT通信衛星星座中的22顆衛星上。Iridium NEXT衛星可以搭載多個有效載荷,每個載荷的質量約為50 kg,體積30 cm×40 cm×70 cm,平均功率50 W(峰值200 W),載荷的安裝方向可以選擇向下或向衛星運行速度矢量方向。SKA對美國彈道導彈防御系統至關重要,可與彈道導彈防御系統的指揮控制元件連接,具備實時任務處理和報告能力,可與雷達數據融合用于綜合的、多現象學評估,主要用確定目標是否被攔截、確定目標的類型、確定是否是正面撞擊、確定目標是否被摧毀等問題。SKA工作過程包括3個步驟:第一步是通過高速光譜和偏振傳感器獲取攔截狀態信息,如攔截產生的熱輻射、高速碎片、等離子體;第二步是進行攔截時間評估,通過與毀傷數據庫、攔截彈數據庫、目標數據庫對比,建立基于時間序列的攔截時間評估模型,判斷攔截目標類型以及是否正面攔截;第三步是殺傷效果評估,利用耦合熱力學和流體力學激波物理代碼和材料碎裂特征,建立基于物理的目標攔截特征模型,以評估目標是否被摧毀,并給出是否需要二次攔截建議[32]。
4 展望與思考
在未來空間安全的形勢下,太空已成為與陸、海、空、電、網并列的作戰域,各國圍繞太空的軍事競爭與較量不斷升級。通過對國外搭載有效載荷的發展分析,可以看出:美國等國積極開展與其他國家、商業機構和國際組織的合作,尋求采用搭載有效載荷的方式提升太空裝備的彈性,確保在對抗環境下依然具備強大的用天能力。經過長期的發展,搭載有效載荷已經廣泛應用導彈預警、定位導航、衛星通信、殺傷評估等方面,正在逐步形成在軌應用能力。結合國外搭載有效載荷的主要用途,以及針對當前搭載有效載荷面臨的主要問題,本文給出以下思考與建議。
4.1 搭載低軌商業衛星,構建天基偵察探測預警體系
高超聲速飛行器、超音速隱身戰機等空天目標具有速度快、機動能力強、目標特性不明顯等特性,僅依靠單一的天基探測平臺很難實現快速捕獲與穩定跟蹤。為了探測、預警、跟蹤和識別高超聲速飛行器在內的先進空天目標威脅,美國正大力發展新一代天基低軌預警系統,包括太空發展局的國防太空七層體系架構和導彈防御局的超聲速與彈道跟蹤天基探測器。未來,加快推動研制更具彈性和生存能力的天基低軌星座的同時,應積極推動低軌小衛星搭載光學、紅外有效載荷的方案論證和系統研制,構建功能完備的全天時、全天候天基偵察探測預警體系,逐步實現對重點區域乃至全球范圍內高超聲速飛行器、F22隱身飛機等空天目標全生命周期的探測-識別-預警-對抗。
4.2 依托低軌衛星星座,提升軍用衛星通信系統彈性
在未來戰爭中,太空是最先介入的作戰領域,專用的軍事通信衛星首當其沖遭受攻擊。近年來,低軌通信衛星星座依靠其傳輸時延低、覆蓋范圍廣、數據帶寬高等特點,已掀起各國的研究熱潮,國外代表性系統有二代銥星、一網(OneWeb)、星鏈(Starlink)等,我國也提出“鴻雁”、“中國星網”等計劃。在低軌星座上搭載定制的通信有效載荷具有廣泛的應用前景,不僅可構建全球無死角高速衛星軍事通信網,使天基信息傳輸能力得到空前提升;還可以建立大容量、低延遲、高速率的天基信息指揮平臺,實現對無人系統的遠程控制、信息共享、目標分配和智能決策,提升聯合作戰指揮效能。
4.3 彌補現有系統不足,增強高軌空間態勢感知能力
地球同步軌道上運行著通信、氣象、數據中繼、電子偵察、導彈預警等高價值大型衛星,對這類衛星的監視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傳統的空間態勢感知主要依靠地基雷達和大型天基系統,地基監視系統存在盲區,而且容易受到天氣和大氣環境的影響,可能發生觀測誤差;天基監視系統雖然能夠全天時、全天候的工作,但是系統建設成本昂貴、建設周期長。隨著空間碎片急劇增加、空間目標機動性提升,傳統的空間態勢感知手段面臨極大挑戰。通過在高軌衛星上搭載有效載荷的模式,同時發展近場威脅感知技術、主被動防護技術,快速形成周邊全空域、大范圍、高時效性的長期持續監視、碰撞預警能力,從而提高天基高價值資產在強對抗環境下的態勢感知能力。
4.4 升級系統設計理念,制定平臺與載荷標準化接口
為宿主衛星平臺、載荷制定統一的接口與參數標準,對于加快搭載有效載荷的建設和應用具有重要意義。統一的接口標準有助于打破平臺與載荷無法互聯、各自為戰的局面,促進搭載有效載荷與宿主衛星平臺在尺寸、質量、功率方面的兼容。未來,衛星平臺廠商與有效載荷研制單位應積極參與標準接口制定工作,對不同功能和類型的衛星平臺、有效載荷、相關器件進行廣泛的標準化討論,加快通用化的接口規范制定,并建立高效合理的設計、制造、發射和使用流程,逐步完善搭載有效載荷的全鏈條應用。
4.5 統籌考慮各方因素,建立合理有效載荷價格模型
搭載有效載荷是降低航天任務成本、分散任務風險及實現快速發射的有效手段,受到業界的重視并得到廣泛應用。目前關于搭載有效載荷價格的相關研究較少,以往的案例中也沒有固定的價格標準,所以確定搭載有效載荷的價格仍是一項重大的挑戰。搭載有效載荷的相關方包括衛星運營商、搭載客戶以及制造商,在制定搭載有效載荷的價格時,應充分考慮相關方的需求、動機、期望等因素。常見的價格模型有收入損失價格模型、資源成本價格模型、衛星平臺或火箭升級價格模型,每種模型都有不同的優點和缺點,各自適用于不同的任務場景。為了降低搭載有效載荷的成本風險,建議搭載有效載荷相關方盡早參與制定合理有效的價格模型,以減少非技術因素導致的研制進度的不可控。
5 結束語
本文分析了搭載有效載荷的概念、優點以及面臨的挑戰,詳細闡述了國外主要國家搭載有效載荷的發展現狀,重點梳理了商業搭載紅外有效載荷、廣域增強系統、專用超高頻通信有效載荷、天基殺傷評估系統等典型項目的發展背景、系統概況及能力指標,研判了搭載有效載荷在預警探測、衛星通信、空間態勢感知等軍事領域的應用前景。研究結果表明:在衛星平臺上搭載有效載荷是將政府、部隊需求融合到宿主衛星任務中的創新方法,也是降低航天任務成本、分散任務風險及實現快速發射的有效手段,已經受到業界的重視并得到廣泛應用。未來,隨著航天科技的飛速發展,搭載有效載荷將成為極具吸引力的選擇,具有重大的應用前景,需要加強相關領域的工程應用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