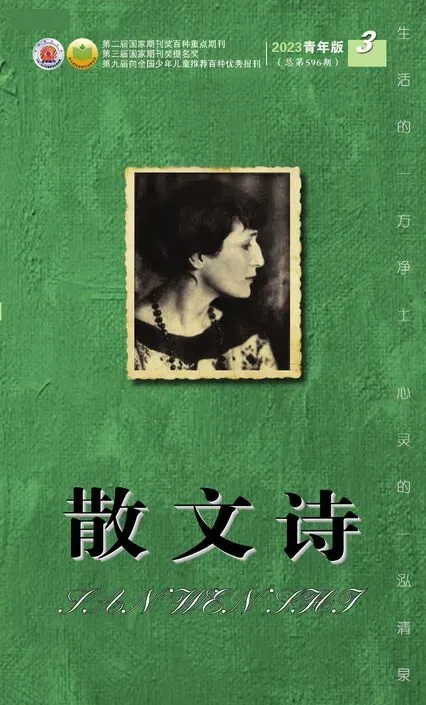第四維度
◎圖、文/黃 佳

等待發型 180cm×160cm 布面油畫 1992 年
第一空間
在生活和工作中, 我一直在恪盡職守, 像鐘擺一樣梭巡于工作和家庭之間。
隨著時間的推移, 我在創作中不斷往前推進, 開始有意地將心理意識的問題屏蔽掉, 從繁瑣的生活抽離出來, 在同一塊色域上重復涂抹不同的色彩, 最后隱入同一色彩之中, 讓所有最豐富的色彩, 都隱藏在最“虛無” 的同一色彩之中。
我試圖將造型語言精練化、 純粹化, 減少到最小的基本的線和面, 運用筆觸的韻律, 不斷重復在觸摸畫布的細枝末節中, 在不知不覺中, 隱現出的細微之間的色潤變化, 將作品本身的形式注入了富有特色的暗示性意義, 也是對人們在情感狀態之下感受到時間痕跡中, 色彩與空間層次的體驗。
不論真實還是虛無, 色塊之間被剝離、 突出、 演繹, 這些細節被賦予神秘性, 想象延續創造, 成為作品的一部分。 觀者在看的過程中, 分不清繪畫與現實的瞬間感覺, 從而動搖觀者的內心, 對正處于時間和空間中的觀者的身體, 產生更強的感知意識。
老 屋
小時候, 媽媽把我放在鄉下外婆家。 回城讀書以后, 每到假期, 我都祈盼著回到鄉下那棟開啟我幻想之門的老屋, 去擁抱曾經給了我溫暖和摯愛的外婆。
老屋是一座舊時的拜祭堂, 它的門前有一個大的草坪, 是曬谷場和放草垛的地方。 推開兩扇臨街的大木門, 進入一個天井, 天井就像一扇窗口, 春天, 我們常站在堂屋, 窺看天井外碧藍的天空, 看小鳥從天井飛過, 看天井瓦片間隙中長出嫩綠的小草, 看下雨天大人拿來木桶接屋檐滴水, 一滴急似一滴地化成水波紋, 像在笑, 在唱。
繞過天井, 是一間一百多平方米的大堂屋, 屋頂呈三角形, 足有兩層樓高, 整個建筑近乎刻板的外表下, 里面住著兩戶充滿了生氣的人家(足有二十多口人)。 站在堂屋, 房子分成左右兩邊, 結構對稱, 外婆一家住在右邊,從堂屋第一間房進入, 穿過兩間房, 然后從第四間房走出來, 居中的屋, 是沒有窗的, 很高的屋頂上, 亮著幾片明瓦。
整棟房子, 除堂屋和天井外, 沒有一點陽光的氣息。 只有當陽光從天井照到堂屋時, 整棟黑灰色的建筑物里面, 才有了一點紅色的光芒。
每到星期六的黃昏,我們小孩子就跑到屋后菜園里, 看那水塘披上薄霧。夜幕自遠而近, 看遠山漸入朦朧, 我們望著遠山,陰森森的, 依稀可見的那條小路延伸到山里, 仿佛又藏著無邊的希望。 我們只盼著一個人影的出現,就齊聲高喊:
外——公!
我們等待著外公回來。

日常·窺視 115cm×108cm布面油畫 2004 年

日常·合影 115cm×108cm 布面油畫 2004 年
當外公走進堂屋, 無數雙小眼睛已經睜得溜圓,紛紛盯著外公的布袋, 希望他能帶給我們一些小花片之類的零食吃。 有時,看到遠山移動的人影, 就像霧里看花, 朦朦朧朧的, 也常常喊錯了人。 這樣的好時光總是很短暫的。 不久, 外公就去世了。 那時, 我六歲。 所有的親人都回到了老屋, 大人們哭成了一團。 在送殯的路上, 披麻戴孝, 走了一圈又一圈, 直到我們這些小孩走不動了, 被鄰居送回來, 這時, 我才對死亡有了初步的認識。
透過蚊帳, 我望著頭頂上朦朧月光投射在明瓦上, 就像一雙明亮的眼睛穿透靈魂, 一瞬間, 靈魂的束縛被解除, 我的心里有一種莫名的恐懼。 明瓦, 就像漆黑的云海中飄蕩著的幾片白帆, 仿佛要載著我飄向天邊, 我開始在腦子里狂想各種夢境。 此時, 生命已經融化在漆黑的寂靜與寂靜的漆黑里。 我忘記了時間, 忘記了一切, 世界沒有別的, 就只有這幾片白帆。 我想飛翔, 卻又害怕飛離, 我使勁地拽著被子, 真希望身邊有一堵人墻將我深深地埋入。 埋入, 不愿出來。 忽然, 聽得蚊帳頂上嗖嗖聲響起, 白帆慢慢地消失了, 一束亮光照到了蚊帳的頂上。
外婆躡腳、 噤聲地坐在我的身邊。 大舅站在床邊, 一手拿手電筒, 一手拿棍子, 正在蚊帳頂上飛舞著, 一會兒, 只見一條一米多長的菜花蛇被大舅捉了出去。
學 畫
父親常常感嘆自己生不逢時, 因此, 他的遺憾須由我這個長女來填補。從小學到高中, 為了學畫這件事, 我不知挨過父親多少次的罵, 因此, 看到畫筆就生厭, 我常站在家中墻上的一面小鏡子前, 望著鏡子里可憐巴巴的自己, 想著鄉下的外婆和老屋里的趣事, 不知不覺地掉下傷心的眼淚。
在單位, 父母是很讓人羨慕的一對, 我媽還是單位的文藝骨干分子。 我和大妹是在鄉下外婆家長大的, 由于個子矮小, 皮膚黝黑, 沒進過幼兒園,不會唱歌跳舞, 回到城里, 我變得更拘謹, 不愛講話, 與城市同齡孩子相比, 顯得有點呆如木偶, 而內心卻很反叛。 記得剛從鄉下回到城里的時候,見到父母、 鄰居, 我從來不喊, 大家都說: “這孩子, 怎么像個啞巴?”

女人與皮鞋·之一 73cm×60cm 布面油畫 1989-1990

站立的女人 180cm×160cm 布面油畫 1996 年
一日, 全家在吃晚飯的時候, 我看到父親嚴肅的表情, 心里上下打著鼓, 飯也吃不下去。 這 時, 父 親 開 腔了:“你為什么不喜歡畫畫? 我小時候想學畫都沒有條件, 現在我給你創造了條件, 你卻不學, 你想氣死我嗎?”我輕輕地回答:“我不喜歡畫畫!” 父親睜大雙眼望著我, 問到:“那你喜歡什么?” 半天過去,我才從牙縫里擠出一句話: “我喜歡體操!” 父親無可奈何地望著我, 然后, 用手指著窗臺對我說:“你把一只腳放到窗臺上站直, 如果能堅持半小時, 我可以不要你學畫。” 我走到窗前, 奮力抬起右腳, 搭在齊胸高的窗臺上, 心想, 這下, 我一定要好好給自己爭口氣。
秒針在嘀嘀嗒嗒地走著……
我抬頭望著桌子上的小鬧鐘, 時間才過去十分鐘, 我的腿已經開始哆嗦起來, 我咬著牙, 扭頭看看兩個妹妹正津津有味地吃著飯, 還不時朝我做鬼臉。 爸媽一邊爭論我的前途, 一邊注視著我站立的腿。 又過了十分鐘, 左腳實在支持不住了, 急得我歪著倒向墻壁。 媽媽心痛地走到我面前, 穩穩扶住我。 這時候, 我的左腳像有成千上萬只螞蟻鉆入腳心。 我用雙手使勁揉搓腿腳, 好不容易, 腳才好受些了, 而我的心卻更加麻木了。
原本以為學習體操比學習繪畫好玩一些, 誰知才站一會兒, 腿就受不了, 我在內心感嘆: 要學好一樣東西, 都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 我看著父親那黑白分明的雙眸正望著我, 他溫和地走到我面前, 摸著我的頭, 語重心長地對我說: “你要好好地學繪畫, 做一個藝術家, 要知道前面的烏龜在跑,后面的烏龜才跟著爬, 要做好妹妹的榜樣。”
含著淚, 我方點頭默認。
春去秋來, 難得一個假日, 我們全家踏著秋日金色的陽光來到岳麓公園, 在綠色的樹葉和紅色的楓葉樹下漫步。 我望著陽光透過楓樹灑滿大地,心中一片歡喜。 我和妹妹俯身, 在地上挑撿各種顏色的楓樹葉, 只聽到父親的聲音從后背傳了過來:“佳佳你看, 那邊有一對白鶴雕塑, 你去把它寫生出來。” 我朝著父親指給我的方向望過去, 那是白鶴泉, 岳麓山的一個景點,此時的白鶴泉邊, 欣賞的游客絡繹不絕, 這個時候, 這種環境, 父親叫我去寫生, 這不是要我的命嗎?
我既擔心畫得不好丟了父母的面子, 又懼怕父親的威嚴, 只好拿著速寫本, 慢慢地移動腳步。 走過去, 看那白鶴、 水池、 天頂上倒映的白鶴畫面,和漫天的暮色, 我執筆凝思, 卻緊張得腦海里一片空白, 再好的景色此時也不能在腦子里沉淀, 只有心在加速跳動。 就這樣, 我像一個木偶般立在人堆中, 茫茫然不知如何下筆。 這時, 父親走了過來, 我匆匆地在畫紙上涂抹了幾筆, 算是完成任務, 結果, 遭到父親嚴厲地批評。 在那么多人面前被罵,我真恨不得有一個地洞讓我鉆進去。
對于學習繪畫, 有段時間我曾經感到極度痛苦, 每當全家出去游玩的時候, 我總是找出各種理由, 讓自己留在家中, 以免出去丟丑。 而父親為了鍛煉我的膽量, 培養我的自信心, 常叫我拿著速寫本去街道和菜市場寫生。 父之令, 大如天,沒辦法, 我只好硬著頭皮去寫生。

臺球桌(局部) 60cm×85cm 布面油畫 1985 年
有時, 我也不免自我安慰:不就是畫畫嗎!又不是上戰場。這樣一想, 心就平靜了許多。 接著, 我開始搜集各種圖片, 學著畫漫畫, 畫一些中國仕女圖, 久而久之, 居然在學校小有名氣,許多同學開始索要我的作品, 拿回家中, 掛在墻上欣賞。 此時, 我的自信心也增強了不少, 對待畫畫這件事, 也不那么生厭了。
進入高中, 父親花了幾毛錢, 買了個巴掌大的維吾爾族女青年石膏頭像, 他認真地示范、 講解素描的基本技法。 我的素描學習, 就是從這里開始的。 后來, 父親找熟人幫忙, 讓我加入青少年宮學習班學習繪畫。
高中畢業后, 父親讓我在家補習繪畫, 準備參加來年的美術高考。 我一個人呆在家中, 倍感無聊, 又要受到父親的監視, 就一心想擺脫他對我的管教。 于是, 我鼓動父親帶我到湖南師大找老師學習, 經老師介紹, 我進入長沙人民藝術專科學校學習。 當時, 藝校的地址在漁灣市農民房, 離我們家有二十多里地, 父親花了二十元錢買了一輛二八式的舊單車, 自己動手給我做了一個畫夾, 然后, 用三夾板鋸了一個長方形木盒子釘上, 再用鋸子從橫切面鋸開, 裝上搭扣, 切出一小段皮帶做把手, 這樣, 我就有了一個畫箱。
第二天, 我剪了個男式發型, 穿上夾克衫, 背著畫夾, 騎上二八單車,威風凜凜地開始了我新的學畫歷程。
半年后, 我考入湖南師范大學油畫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