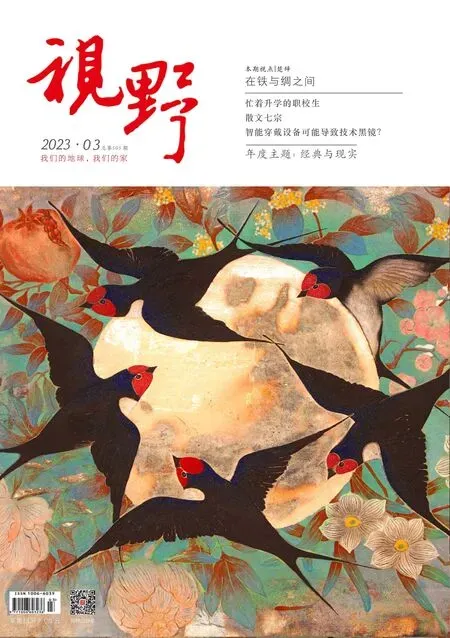散文七宗
/王鼎鈞
楊牧教授把中國近代散文歸為七類,每一類都有一個創始立型的人,這七位前賢是:周作人(小品),夏丏尊(記述),許地山(寓言),徐志摩(抒情),林語堂(議論),胡適(說理),魯迅(雜文)。他為此編了一部《中國近代散文選》。
夏丏尊
對夏丏尊先生我印象深刻,看到他的名字,想到《文心》和《愛的教育》對我的影響。他家境清寒,三次輟學,終身沒有一張文憑,二十一歲就就業賺錢,我青少年時期的坎坷和他近似。楊牧教授說,中國近代散文中的“記述”一脈由夏氏承先啟后,各種選集都收了他的《白馬湖之冬》。
說到記述,夏先生記述他同時代的幾個人物,寫豐子愷,寫弘一大師,那才是文以人傳、人以文傳。且看他寫的《魯迅翁雜憶》,他曾和迅翁在一所學校里同事,那時迅翁還沒有用“魯迅”做筆名,他說他倆服務的那所學校聘請了一些日本人做教員,需要有人把日文的教材譯成中文。他寫迅翁翻譯教材的時候,用“也”代表女陰,用“了”代表男陽,用“系”代表精子。他寫迅翁對他說過,當年學醫,曾經解剖年輕女子和兒童的尸體,心中不忍。這時的周樹人先生還沒有“橫眉冷對千夫指”,令人樂于親近,不失為一條珍貴的史料。夏先生又寫迅翁只有一件廉價的長衫,由端午穿到重陽,又寫睡前必定吸煙吃糕,意到筆隨,顯出散文之所以為“散”。
周作人
夏丏尊先生的名氣并不是很大,沒想到把他列為中國近代散文的七位宗師之一,說到周作人先生,那就是眾望所歸了。周先生的學問了不起,不知為什么,未曾以皇皇巨著像馮友蘭先生那樣以哲學名家,或是像顧頡剛先生以史學名家,留在散文這一行,以“小品”受我輩膜拜。學問大的人下筆總是旁征博引,周先生常常引用我們沒見過的書,從中找出我們需要的趣味。
周先生對散文提出兩大主張,一、美文,二、人的文學。他似乎不喜歡雄辯淵博的論著,所以始終沒說清楚,好在有人響應補充,有人以不同的術語引進相似的說法,今天我們可以印證,“美文”指形式,“人的文學”指內容。美文之美不是美麗,是美學,人的文學不是人欲,是人性。古人說,讀了《出師表》不流淚的,不是忠臣;讀了《陳情表》不流淚的,不是孝子。為什么會流淚呢?因為它發自人性,觸動人性。天下教忠教孝的文章多矣,為什么要拿這兩表說事兒呢?因為兩表達到美學上的要求,是藝術品。長話短說,可供欣賞的散文,內容見性情,形式有美感。
放下理論讀作品,周先生寫《水里的東西》,有一篇談溺死鬼,淹死的人的鬼魂一直留在他淹死的地方,不能離開,要想轉世投胎,得先“討替代”,拉一個人下水淹死,讓那個人的鬼魂代替他。溺死鬼常用的辦法是幻化為一種物件浮在水面,引誘人彎下腰撈取,他在水中趁勢一拉。他常常變成一種兒童玩具,讓小孩子上當短命,所以水鄉傳說中的溺死鬼往往是一群兒童,三五成群,一被驚動就跳下水去,猶如一群青蛙。
博學的周作人先生除了寫鄉野傳說,還寫到日本的河童,文字干凈明亮,行文舒展自如,風格莊重閑適,這些都屬于“形式美”。至于內容,孟子說“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周先生對河邊同一地點不斷有人淹死,筆端沒有溫度,為什么也大受歡迎呢?我有一個解釋:溺死鬼找替身云云根本是無稽之談,難怪他寫得既不恐怖,也不悲慘,“本來無一物”嘛!周先生談溺死鬼,有破除迷信的作用,應該高舉為無神論的上乘文學。無神論者不要禁止談鬼神,要任憑周作人這樣的作家去談鬼神,使人感覺并沒有鬼神。
林語堂
都說周作人先生喜歡在小品文中引用許多名著名言名人軼事,其實林語堂先生也是,兩位前賢讀書多,記憶力又強,一旦提筆為文,天上地下冒出來一群靈魂自動幫忙,“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或許可以如此解釋。王勃作《滕王閣序》,句句是典,當眾一揮而就。讀者覺得不是進了滕王閣,好像進了圖書館,這也是一道風景。
談散文欣賞,我們不用強調林氏的淵博,應該推薦他的幽默。眾所周知,他是中國幽默的發起人。論幽默,他有理論:“幽默家沉浸于突然觸發的常識或智機,它們以閃電般的速度顯示我們的觀念與現實的矛盾。這樣使許多問題變得簡單。”
他是怎樣“沉浸于突然觸發的常識或智機”的呢?他說:“世界大同的理想生活,就是住在英國的鄉村,屋子安裝有美國的水電煤氣等管子,有個中國廚子,有個日本太太,再有個法國的情婦。”他說:“派遣五六個世界上最優秀的幽默家,去參加國際會議,給予他們全權代表的權力”,世界上就不會有戰爭。他為這個幽默代表團擬了一個很長的名單,太長了,有些讀者覺得并不幽默。多數人認為幽默要有警句。林先生晚年住在臺北,有一所學校請他在畢業典禮中演講,那天有多位政界學界商界的名人出席,個個發表長篇大論,林先生上臺說:“演講要像女人的裙子,越短越好。”這是警句,全場大樂。報紙報道典禮經過,用這句話做標題。曾幾何時,那天達官貴人經世濟民的高論一概不傳,林先生的“越短越好”獨存。
林先生說莊子也幽默,孔子也幽默。莊子夢見化蝶,不知道是莊周化蝶,還是蝶化莊周。馬克·吐溫說,他的母親懷的是雙胞胎,臨盆生產的時候,其中一個胎兒淹死了,他不知道淹死的是他,還是他哥哥。這在馬克·吐溫是幽默,莊子因此也幽默嗎?孔子說,“無可無不可”。大廟里兩個和尚起了爭執,甲僧向方丈告狀,方丈說你說的對。乙僧也到方丈座前訴苦,方丈也說你說的對。丙僧得知情由,向方丈質疑,甲僧乙僧各執一詞,師父應該明辨是非曲直,怎可認為他們都是對的?方丈說,你說的也對。世人都說方丈幽默,孔子也因此幽默嗎?林先生這種廣泛的幽默論,很多人跟不上。
讀者大眾希望幽默大師開口閉口都是警句,別忘了林氏幽默是從英國文學的熏陶中提煉出來,幽默是一種修養,在平淡中形成,這種幽默往往是一種獨嘗的異味,未必哄堂大樂。我們現在常說幽默感,這個“感”字有講究,你我要有能力發現幽默,享用幽默,“感”是“我”銳敏的回應。“兩山排闥送青來”,我怎么看不到?“于無聲處聽驚雷”,我怎么聽不見?答案是主觀的條件不足,幽默也是如此。林先生認為莊子幽默,孔子幽默,連韓非都幽默。這么說,老子也幽默,他騎青牛,出函谷關,守關的官吏一定要他留下著述再走,他用一大堆含義模糊的句子隨手組合,讓你進入迷宮,讓后人視同秘典。林先生認為陶淵明也幽默,陶公作詩數落他的五個孩子,長子懶惰,次子不肯讀書,老三老四是雙胞胎,到了十三歲還不識字,最后這個小兒子九歲了,整天只知道找梨子找栗子吃。于是陶公說,既然老天爺這樣安排了,我還是喝酒吧!這么說,迅翁也幽默,他有一首詩寫失戀,“我”在女朋友那里接二連三碰釘子,百思不解,最后,“不知何故兮,由她去吧!”
徐志摩
接著讀下去,見到徐志摩先生。徐氏的才氣,跟周氏林氏的學識形成對比,他不管古人看見什么,重要的是自己看見什么,不論古人有什么感受,重要的是自己有什么感受。他寫翡冷翠,翡冷翠是什么地方?Florence,也譯成佛羅倫薩,歐洲文藝復興的發源地,在藝術、建筑、繪畫、音樂、宗教,各方面產生許多大師,留下許多古跡,后世更有源源不絕的論述,徐氏的《翡冷翠山居閑話》,1600 字,竟只引用了前人一句話。他寫康橋,康橋是什么地方?Cambridge,也譯為劍橋,英國最古老的大學城,多少世界名人跟這里有淵源,牛頓、達爾文、拜倫、羅素,徐志摩自己也曾在這里留學。他寫康橋,5800 字,幾乎沒有使用引號!他強調的是,啊,我那甜蜜的孤獨!他游天目山,看和尚,游契訶夫的墓園,想生死,所謂墓園只剩一塊石碑,他也寫了2800字,不抄書,完全自出胸臆。
徐氏散文的光彩奪目在描寫風景。這樣的風景描寫,在周作人、夏丏尊、林語堂諸位大師的文集中是找不到的,許地山先生也沒有這樣的文筆。到了現代,文評家一再指出,散文和小說中的風景描寫越來越少了!
許地山
許地山先生是臺灣人,對日抗戰發生以前就名滿全國,我十歲,他大概四十歲,語文教科書里選了他的文章。那時,臺灣和東北都被日軍占領,內地各省若有祖居臺灣的和祖居東北的作家,都受到文壇特別的重視,我們小讀者也對他們特別景仰。許先生常用“落華生”做筆名,“華”是古寫的“花”,落花生是小孩子愛吃的東西,“落華生”的意義就豐富了,除了是植物,還是在我們大中華落地生根的一個人,許先生如此命名,可見他對中國語文的敏感,欣賞文學作品的人也該有這種敏感。
散文多半“意念單調,語言直接”,許先生不同,他常常在散文里說故事,有時候甚至就用散文寫故事。這樣的作品你拿它當小說,略嫌不足,說它是散文,又覺得有余。當年并沒有人特別稱贊這種寫法,后來,我是說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七十年代,我和一些散文作家吸收了小說的技巧,給作品一個新的面貌,修改了散文的定義。這是散文的發展,文評家照例要給新生事物尋找源頭,找來找去找到了許地山,于是許先生的排名在朱自清、郁達夫之前,位列七宗之一。
請看許氏的《讀〈芝蘭與茉莉〉因而想及我的祖母》。
文章開端“我”正研究唐代佛教在西域衰滅的原因,對瑣碎的考證覺得厭倦。接著是從郵箱中發現《芝蘭與茉莉》,開宗第一句便是“祖母真愛我”!“我”因此想起祖母。先發一段議論:他說西洋文學取材多以“我”和“我的女人或男子”為主,屬于橫的,夫婦的;中華文學取材多以“我”和“我的父母或子女”為主,屬于縱的、親子的。中國作家敘事直貫,有始有終,原原本本、自自然然地說下來。這“說來話長”的特性——和拔絲山藥一樣地甜熱而黏——可以在一切作品里找出來。
議論之后,接著寫起“我的祖母”來。那是一個很長的故事,舊日大家庭憑著“七出”的條文,拆散年輕人的婚姻,那個受害的女子回到娘家沒有再嫁,戒了煙,吃長齋,原來的丈夫也沒有再娶,兩人有時還可以秘密見面,由陪嫁的丫頭在中間傳遞消息。后來女子生了重病,死前叮囑原來的丈夫和陪房的丫頭結婚,這個陪房的丫頭就是“我的祖母”。全文約八千字,祖母的故事占了六千,許老前輩能知能行,果然原原本本、自自然然地說下來,和拔絲山藥一樣地甜熱而黏。他這個寫法可以說是用散文拖著一個故事,當年是散文的別裁。
魯迅與胡適
現在應該談到魯迅和胡適了,這兩位大師名氣太大,幾乎用不著介紹。讀者的程度不同,背景不同,性情不同,各人心里有自己的胡適,自己的魯迅,“千江有水千江月”,每個月亮不一樣,也教人不知道怎樣介紹。
提起迅翁,不免首先想到雜文。雜文本是散文的一支,繁殖膨脹,獨立門戶。散文也是“大圈圈里頭一個小圈圈,小圈圈里頭一個黃圈圈”。迅翁那些擺滿了書架的雜文,是大圈圈里的散文,夾在雜文文集里的薄薄一冊《野草》,是黃圈圈里的散文。欣賞迅翁的散文,首先要高舉《野草》,討論《野草》。
以《野草》中最短的一篇《墓碣文》為例,迅翁把他內心深處的郁結,幻化成一個夢境,把讀者的心神拽入他的夢中。夢是陰暗的,猶不足,出現了墳墓,暗夜,荒野,孤墳凄涼,猶不足,墳墓裂開,出現尸體。尸體可怕,猶不足,尸體裂開,出現心臟,猶不足,尸體居然自己吃自己的心臟。迅翁使用短句,句與句之間跳躍銜接,搖蕩讀者的靈魂。迅翁使用文言,用他們所謂的“死語言”散布腐敗絕望的氣氛。這種“幻化”就是藝術化,散文七宗之中,唯有迅翁做得到,也只是《野草》薄薄一本中寥寥幾篇,它的欣賞價值超出雜文多多。但丁《神曲》寫地獄,《地藏王菩薩本愿經》也寫地獄,也許是因為經過翻譯的緣故,藝術性有遜迅翁一籌。迅翁何以有此稟賦,可幸,既有此稟賦又何以不能盡其用,可惜。
至于雜文,那是另一回事。雜文是匕首,是騎兵,寫雜文是為了戰斗,而勝利是戰爭的唯一目的,當年信誓旦旦,今日言猶在耳。迅翁被人稱為“雜文專家”,運筆如用兵,忽奇忽正,奇多于正,果然百戰百勝。戰爭是有后遺癥的,反戰人士曾一一列舉,我不抄引比附。此事別有天地,一言難盡,萬言難盡,有人主張談散文欣賞與雜文分割,我也贊成。
胡適先生的風格,可以用他的《讀經平議》來顯示。讀經,主張中小學的學生讀四書五經,政界領袖求治心切,認為漢唐盛世的孩子們都讀經,因此,教孩子們讀經可以出現盛世,似乎言之成理。胡先生寫《讀經平議》告訴他們并不是這個樣子。第一,看標題,他不用駁斥,不用糾謬,不說自己是正論,他用平議,心平氣和,就事論事。第二,他先引用傅斯年先生反對讀經的意見,不貪人之功,不掠人之美,別人說過了,而且說得很好,他讓那人先說。第三,他提出自己的反對意見,別人還沒有想到,可能只有他想到,他說得更好。第四,文章結尾,他用溫和的口吻勸那些“主張讓孩子們讀經”的人自己先讀幾處經文,不是回馬一槍,而是在起身離座時拍拍肩膀,然后各自回家,互不相顧。他行文大開大合,汪洋澎湃,欣賞此一風格可參閱他其他的文章,如《不朽,我的宗教觀》。
這兩位老先生都有信念,有主張,有恒心,有文采,兩老沒說過閑話,人家是三句話不離本行,這兩位前賢是句句念茲在茲。人家寫小說,編劇本,他倆寫散文,直截了當,暮鼓晨鐘,甚至沒有抒情,沒有風景描寫,可以算是近代文壇之奇觀。兩人作品內容風格大異,魯迅如鑿井,胡適如開河,胡適如講學,魯迅如用兵。讀魯迅如臨火山口,讀胡適如出三峽。那年代中國讀書人的思想不歸于胡,即歸于魯,及其末也,雙方行動對立對決。“既生瑜,何生亮!”論文學欣賞,既要生魯迅,也要生胡適,如天氣有晴有雨,四季有夏有冬,行路有舟有車,雙手有左有右。
每一本文學史都說,中國近代散文受晚明小品的影響很大,晚明小品“獨抒性靈,不拘格套”,使當時的文學革命家如歸故鄉。乘興為文,興盡即止,作品趨向小巧,張潮一語道破:“文章乃案頭之山水,山水乃大地之文章。”固然盆景也是藝術,然而參天大木呢?宣德香爐也是藝術,然而毛公鼎呢?印章也是藝術,然而泰山石刻呢?流觴曲水也是藝術,然而大江東去呢?晚明小品解放了中國近代散文,也局限了中國近代散文。
散文七宗之中,迅翁和胡博士是超出晚明小品局限的兩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