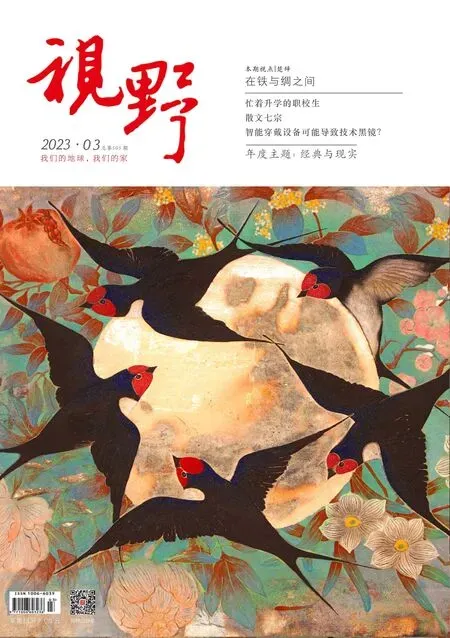楊主任
一
“您所撥打的電話暫時無法接通……”又沒打通。這是我第五次撥打楊主任的電話。楊主任是南湖中學的德育主任,管理一切學生事務。雖然我知道他很忙,但是沒有想到他連接電話的時間都沒有。我心里不禁犯起了嘀咕:這個項目還能成嗎?
第六遍撥打他的電話,終于通了。我說明來意,楊主任很高興:“好啊,那你下午到南湖中學來跟我當面聊一聊吧,我下午四點鐘有空。”還沒等我回復,楊主任又掛斷了電話,留下一個錯愕的我。
我是一名公益人,金麗是我在村中遇到的一個女孩,總是帶著內斂的笑容。九月,我發現她時常缺席社區活動;找到她時,在她的手腕上發現了許多深淺不一的割痕。金麗不是孤例,一些小朋友說,他們的哥哥姐姐都有過類似的行為。于是,我立馬聯系了金麗所在的南湖中學,想要和學校取得聯系,共同對這些學生進行干預。
然而,這談何容易呢?我們所在的地區本就是全省經濟最落后的地區,專業的心理資源少之又少。加之,南湖中學的老師大部分是四十歲以上的老教師,他們會如何理解心理健康?會同意我們的工作開展嗎?
二
帶著顧慮,我來到了南湖中學,找到了楊主任。出乎我的意料,楊主任并不是人們刻板印象中的那種教導主任,相反,他非常溫和。談話的時候,會很認真地注視你的眼睛并不會打斷。我們交談過程中,不斷有學生敲門來找他問各種事情:學生手冊在哪里領取,提交藝術節活動報名表,班主任帶著學生過來希望楊主任能給學生做思想教育……他一項一項處理,有些手忙腳亂,卻不急躁。一直到上課鈴聲響,楊主任才重新坐在了我們面前。“不好意思啊,事情太多了。”他帶著歉意的微笑,并急忙給我重新添滿了茶。
出乎我意料的是,楊主任早就注意到了學生的心理健康問題。“這在我們的學生中太普遍了。他們有70%來自附近的鄉鎮,有50% 是留守兒童,家庭關系非常復雜。大部分同學在學校寄宿,我們聯系他們的家長非常困難,許多家長也并不理解孩子的心理問題。很多時候,老師們更像他們的爹媽。”
“光是金麗所在的班級,就有七八個同學有過割腕的行為。有一些同學是單純的模仿,我們教育了之后就沒有再犯;然而還有一些真的存在心理健康方面的問題。現在僅僅是初二年級,確診抑郁癥的孩子就有12 個。”
我十分吃驚,一方面驚訝于心理健康問題在鄉鎮中學的普遍性,另一方面,也驚訝于楊主任對于學生的了解程度。楊主任苦笑一下:“在我們鄉鎮中學,老師們幾乎是24 小時待在學校看著學生,只有這樣才能出成績。但是上課、批改作業、行政任務,已經非常忙了,能留給老師做學生思想工作的時間太少了。”楊主任喝了口茶,停頓了一下,看茶葉在杯中起起伏伏,“況且,我們也沒有專業的心理背景。全縣只有兩名專職心理教師,都在縣高中,我們學校是請不起專職心理老師的。有的時候你知道這個孩子很痛苦,但是你無論怎么跟他談心,都沒有辦法進入孩子的內心世界。”
他好像想起了什么,抬頭望著窗外,嘆了口氣:“唉,力不從心啊。”
之后的日子中,我又走訪了許多其他的中學,老師們紛紛表示非常需要心理咨詢資源。談起曾經發生過的學生自殺事件,無不表示痛心疾首。“現在的小孩子太脆弱了,哪像我們小時候…”我不作聲,內心嘆了口氣。
三
在當地教育局的支持下,我們請到了專業的心理咨詢師為有需要的同學們做長期的心理咨詢。項目能夠落地,楊主任功不可沒:一面要聯系家長,取得他們的認可和支持;另一面,也要積極做通各個班主任的思想工作。趙老師就是一位需要做工作的班主任。
“天翼還是不肯上學?”掛掉楊主任的電話,我趕緊和咨詢師一起趕往南湖中學,與楊主任匯合后一起趕往天翼家中。趙老師,天翼的班主任也與我們一同前往。
“這個小孩,就是太驕傲了,所有人都太慣著他了。”趙老師憤憤不平。午后的陽光格外燥熱,人也不由得煩躁起來。楊主任仍嘗試耐心地為我們介紹情況:“天翼成績特別優異。但是,他覺得我們學校的教學水平沒有辦法滿足他的學習了,想要轉到另外一所學校。另一方面,因為他爸爸常年在外面打工,對他缺乏關心,他希望通過這個行為引起爸爸的關注。”
天翼的父母都在家。天翼過來坐下后,趙老師就開始了苦口婆心卻頗為刺耳的勸告:“天翼,你現在已經初三了,現在轉學有哪個學校肯接收你啊?你真的出色到那個地步了嗎?就算是科學家也要踏踏實實學習,你算什么?”隨后,他對著天翼父母開始了數落:“天翼在學校,雖然知識都會,但就是不做功課不聽講。咱們南湖中學,每年只有前10%的學生能進入重點高中;只有35%的同學能考進普通高中。再不努力,天翼就完了呀!”天翼全程一言不發。天翼的爸媽說,天翼已經幾天沒有說話了。心理咨詢師看不下去了,卻又不好打斷,于是把天翼單獨帶出去做咨詢。
出乎我意料的是,楊主任打斷了趙老師,對天翼的父母說:“趙老師是天翼的班主任,自然最了解天翼的情況。我作為德育主任,也跟天翼聊過很多次。天翼是很好的孩子,現在我們只看到他不上學,但是孩子一定有其他的苦衷。也許有些話我們應該等咨詢師跟孩子聊完了,聽一聽孩子的想法是什么……”
趙老師非常不滿:“楊主任,我是二十多年的老教師了,天翼這個年齡該做什么事情我不知道嗎?學生最重要的任務是學習,如果學生連學習都不管了,那還有什么未來?我這是在對學生負責!”楊主任把趙老師拉出房間:“趙老師,現在的孩子跟以前不一樣了。現在天翼已經幾天沒說話了,咱們最重要的是保證孩子不會做出極端行為,上學不是最重要的。”
院子的另一角,天翼抱著咨詢師,無聲地哭了。
四
項目進行到第三個月,合作的咨詢師突然對我說,南湖中學的老師非常不配合咨詢工作的開展。我很意外,那可是楊主任親自負責的項目,怎么會有問題呢?再次前往南湖中學,我沒有見到楊主任。原來,楊主任不再擔任德育主任,而調動成為了總務處主任。
我不能理解,其他老師也對此諱莫如深。后來,本地的司機師傅對我講,南湖鎮原先有兩所國營工廠子弟初中,楊主任就來自其中一所。十幾年前,產業升級改革,工廠撤出南湖鎮,兩所初中隨之合并。新當選的校長來自原有的另一所初中,那么一切都解釋得通了。我再次撥打楊主任的電話,但他依然沒有接。
一個月之后,我陪同愛心企業家到南湖中學走訪,南湖中學師生熱情地接待了我們。人群之中,我看到了久未見面的楊主任。他還是帶著如我們第一次見面時的微笑,遠遠地對我打了個招呼。隨即,繼續舉起相機,為我們拍照。
企業家走后,我問楊主任。楊主任只是笑笑:“做了十多年的德育工作,我也累了,也想休息一下了。”我不知道說些什么來安慰他。只是想到金麗,想到天翼,想到楊主任跟趙老師的爭吵,突然覺得,理解和尊重是太稀缺的東西。“哦對了,天翼還是轉學走了。我為他感到開心。”楊主任又接了個電話,帶著歉意對我笑了笑,擺擺手,又回到學生中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