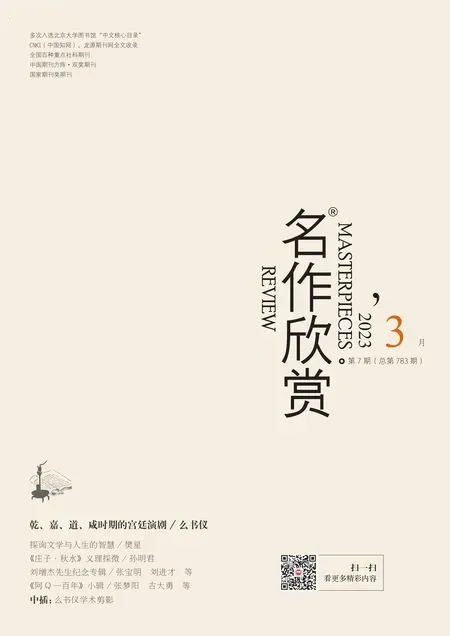《阿Q 一百年》寫作過程的回顧與反思
北京 張夢陽
我對阿Q 研究的思考,最早起始于1972 年7 月向何其芳先生求教時期。
我1964 夏從北京二中畢業,在韓少華老師那里得到了難得一遇的文學教育,考進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但沒上什么課,就到了1966 年。1968 年堅決閉門讀書,拒絕參與一切活動。然而當時圖書館都關了門,幸好父親是位明智的高級知識分子,1964 年入大學時給我買了一套1958 年版的《魯迅全集》。這套全集就成為我的“救命書”,整天捧著細讀。和很多人只讀表面、寫心得不同,我一開始就研究問題,出于對哲學的偏好,確定的題目是“魯迅后期雜文的辯證法問題”。1972 年寫出一篇一萬六千字的論文《〈“題未定”草(六至九)〉的哲學分析》,想向懂行的老一輩學者請教。后來成為電影導演的北京二中老同學徐慶東跟我關系很好,他跟何其芳先生的小兒子何辛卯說了此事,把論文交給他,請他問問父親愿不愿意指教。很快傳來消息,何其芳先生對論文很感興趣,愿意見見這位年輕人,談一談。于是約定一天晚上,我到西裱褙胡同何其芳先生家去,拜會這位學識淵博、才華橫溢的老人。他熱情地跟我談了論文的得失,我們結成了“忘年交”。后來我寫了文章就跑到他家里請求指點,他總是不厭其煩地教誨。空下來,也說些閑話,發些牢騷。他對自己的《論阿Q》被說成“跌入人性論的泥坑”不服氣,表示以后還要寫文章重論這個魯迅研究中的難題。這就激起了我對阿Q 典型問題的興趣,也有心探討一下。正好我在往《人民日報》送稿時,結識了李希凡、姜德明同志,后來找機會也聽取了李希凡對阿Q 典型問題的意見。
1977 年何其芳先生去世,他的夫人牟決鳴先生繼續關心著我,1978 年底介紹我結識了到北京參編1981 年版《魯迅全集》的陳涌(何其芳的學生)。熟悉后,陳涌講得最多的還是阿Q。1979 年10 月,我在林非先生的不懈努力、陳荒煤同志的堅決支持下,調入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魯迅研究室工作,編輯《魯迅研究》。正好陳涌調進中央政策研究室任文化組組長,住在平安里中組部招待所。我成為那里的常客。陳涌重新出山后,正式致力寫作的第一篇論文就是《阿Q 與文學的典型問題》。他因歷史原因,不愿交給當時所謂的“東魯”發表。我就憑著與他的私人關系,軟磨硬泡,終于把論文稿拿到手,經林非先生終審刊登在《魯迅研究》第三輯。以后又細讀了他關于阿Q 的其他文章,認真思考起這個被稱為魯迅研究中“哥德巴赫猜想”的核心難題,簡直成了“阿Q 迷”。1982 年至1991 編纂《1913—1983魯迅研究學術論著資料匯編》期間,我著力收集阿Q 研究的資料,只言片語也不放過。收集齊全后,按時間順序排列起來,不斷精讀、思考,并充分利用20世紀80 年代以來思想解放的條件,廣泛閱讀了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等有關書籍,涉獵了弗洛伊德、榮格、弗洛姆等人的心理學新論。1991 年用《1913—1983 魯迅研究學術論著資料匯編》完成后的半年時間,寫成了二萬五千字的長篇論文《阿Q 與世界文學中的精神典型問題》,1991 年10 月紀念魯迅誕生一百一十周年時,提交給國際學術研討會,受到廣泛好評。當時王信先生覺得很好,有意在《文學評論》發表,后因篇幅太長,又不好壓縮,舍棄了。最后收入彭小苓、韓藹麗編的《阿Q——七十年》(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3 年版)一書中。在此論文基礎上,我又在袁良駿先生的大力贊助下擴充成二十七萬字的《阿Q 新論》,編入《魯迅研究書系》,由陜西人民教育出版社于1996 年9 月出版。聊以慰藉的是父親彌留之刻見到了雪白的精裝書,含笑而去。
《阿Q 新論》出版后,受到學界好評。臺灣出版人士到西安從《魯迅研究書系》十六部書中僅挑選了這一部擬在臺灣出繁體字版。特別使我激動的是,2019 年8 月我應臨清縣邀請到臨清參加季羨林先生逝世十周年紀念會時,縣宣傳部副部長井揚同志陪我到聊城大學文學院參觀王富仁藏書紀念室,富仁先生在書系中僅存《阿Q 新論》一本,可見他的重視。錢理群先生在《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初版中談魯迅作品時,著重談了《阿Q 新論》。再版時,雖然加了新出版的其他書,但對精神現象一說,仍很注意。這都是對我的鼓勵!
此后,魯迅先生和他的代表作《阿Q 正傳》一直陪伴著我,從來沒有離開。
2018 年4 月,重建在“周氏兄弟舊居”的北京三十五中學,請我為師生開講座,我講的仍然是阿Q。講演提煉為《在阿Q 誕生地講阿Q》一文,在5月9 日《中華讀書報》家園頭條發表。
2021 年,是魯迅誕生一百四十周年和阿Q 發表一百周年。頭一年我就下決心重論阿Q 與世界文學中的精神典型問題。經五十年之積累、提煉,掌握了能夠找到的全部資料,又得天獨厚地親密接觸了所有重要的阿Q 研究專家,在他們的啟發下進行了深入的思考,應該說是有信心談出些新見的。
積五十年的積累、提煉,逐漸形成這樣的觀點:《阿Q 正傳》實質是思想家型的文學家魯迅創作的哲學小說。阿Q 是一位與世界文學中堂·吉訶德、哈姆雷特、奧勃洛摩夫等典型形象相通的著重表現人類精神弱點的特異型的藝術典型,可以簡稱為“精神典型”。以這種典型人物為鏡像,人們可以看到自身的精神弱點,“由此開出反省的道路”。阿Q 是中國現代文學貢獻給世界文學典型畫廊的唯一一個出色的典型形象。《阿Q 正傳》是中國現代文學的最高成就,也是第一部傳播到世界,受到羅曼·羅蘭等大作家稱贊的現代文學作品。
如陳涌所說:“魯迅即使沒有其他著作,只要有一部《阿Q 正傳》,就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最偉大的作家。”至今,《阿Q 正傳》仍然具有強烈的現實意義,因為阿Q 和他的精神勝利法在中國以至世界各地還很普遍!確實是“不存在而又到處存在的”,令國人驚醒!
在水利工程安全監測技術方面,引進了高精度GPS監測、雙星衛星定位監測、實時三維變形監測、機器人自動監測、無人機探測等高精尖技術和設備,開發了監測數據分析等軟件,改進了安全監測儀器設備,并在三峽大壩船閘高邊坡、清江水布埡臺子上滑坡級金沙江溪洛渡水電站等典型工程中成功運用;促進了我國邊坡安全監測、大壩安全監測、堤防安全監測、滑坡安全監測、水庫庫岸崩塌安全監測、水下工程安全探測等技術水平的提高,為保證我國水利工程的正常運行提供了支撐。
應當肯定,自己五十年來的跋涉是有成效的,僅從《阿Q 新論》和《阿Q 一百年》兩書來看,研究工作具有以下特點:
(1)資料比較扎實。我從不相信在學術研究中會有什么不從資料工作入手,僅憑一時靈感就能獲得成功的所謂“才氣”,只認定我所由衷敬佩的師長和同事樊駿先生的一段名言:“學術研究的每一個開拓、突破,都是從已有的成果、結論起步的,有所超越,也有所承襲,由此匯成學術發展的長河。”
所以我在決心研究阿Q 典型問題之始,就從收集、梳理前人的研究成果入手,連只言片語都不放過。然后將論著資料按照時間順序排列起來,反復閱讀,反復回味,反復把玩,反復思考,終于歸理耙梳出了阿Q 典型研究的學術發展鏈條,并提取出了其中的關鍵環節——馮雪峰的“思想性典型說”“精神寄植說”與何其芳的“共名說”。從這一關鍵環節出發,沿著“學術鏈”進行調整、梳理、闡釋和發展,在扎扎實實、繼承前人學術成果的基礎上提出自己的獨立見解。別人就算可以不同意我的觀點,但也不能否認我從事研究工作的每一步都是腳踏實地的,從來沒有懸空過。2021 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評我為“老有所為”先進個人,評語用三個詞概括我四十年來的研究工作——“務實、穩健、固本”。我感到非常準確。
(2)視野比較寬廣。致力于阿Q 典型研究,卻并沒有僅限于阿Q 的評騭,而是將眼光擴大到世界文學的廣闊視域中去,對阿Q 與堂·吉訶德、哈姆雷特、奧勃洛莫夫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人物進行了縱橫交錯的比較研究,發現了這一類世界級藝術典型之間所存在的深層共性與不同個性。并從此出發,考察了阿Q 的文學后裔,對中國當代文學的典型塑造問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以致聯想到某種帶有“星球意識”的宇宙智慧生物精神發展的深層共性,想到在那個遙遠時代和神秘空間里阿Q、堂·吉訶德、哈姆雷特的底蘊無窮的哲學啟悟意義。在古今中外、上下左右的縱橫馳騁中,展現了研究視野的廣闊。
(3)思考比較深入。以扎實謹嚴的資料為根基,卻沒有局限于史料的復述與連綴,也沒有因循守舊、沿襲陳說,而是堅實地進行了深入的開掘。在掌握和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前提下,汲取黑格爾、弗洛伊德、榮格和弗洛姆的有益見解,提出建立馬克思主義精神現象學的主張,并嘗試以精神現象學為視角,從更深層次聚焦透視阿Q,得出了阿Q 屬于側重反映人類精神現象的變異性藝術典型(亦可簡稱“精神典型”)這一前人未曾言說的觀點。并由此說明魯迅對阿Q 這一精神勝利典型的創造,同塞萬提斯創造堂·吉訶德、莎士比亞創造哈姆雷特一樣,是對“人類心靈方面的新發現”。這正是他們“擁有全世界意義的原因”。在“抽象與變形”一章中,又對《阿Q 正傳》的藝術特色,尤其是與印度《百喻經》的藝術淵源關系做了獨到的分析。對于這些觀點和分析,盡可各持所見,但是不能不承認是在前人基礎上進行了更為深入的開掘與思考,起碼是為后人的進一步研究提供了參照。
因此,《阿Q 新論》一書出版以后,雖然也有異議,然而從主導方面看還是得到了好評。在諸種評論當中,我最為看重的是未曾發表的當代著名作家馮驥才先生于1997 年4 月1 日給我的親筆來信。他在信中認為《阿Q 新論》中“精神典型的探討,乃是文學研究重大命題,亦是對魯迅研究高層次之深入”。
也可能是由于我曾經有過數量很大的創作,雖然因為各方面的原因未能發表,始終沒有實現少年時代就已做起的“作家夢”,但是這讓我的學術理論研究總是自覺地從創作實踐出發,想到作家藝術創作中的種種甘苦和需要,所以研究結果常常得到作家們的理解。對于這一點,我感到慶幸,并對作家們充滿了感激和欽佩之情。
但《阿Q 新論》問世后,學界幾無反響,只見到葛中義的一篇書評。二十年后,直到2011 年北京大學中文系的王麗麗教授才在《重評魯迅闡釋史上的一件往事——耿庸的〈《阿Q 正傳》研究〉對馮雪峰〈論《阿Q 正傳》〉的批評》(《魯迅研究月刊》2011 年第8 期)中指出:“對《論〈阿Q 正傳〉》的理論潛力認識得最充分的可能要數張夢陽。通過學術史的考察,張夢陽斷言:馮雪峰的‘思想性典型說’與‘精神寄植說’實質上是70 年阿Q 典型研究史上最值得珍惜、最接近阿Q 典型意義與魯迅創作本意的理論成果。”
看到這段話后,我確實有一種知音之感。而這位知音竟然是二十年之后才遇到的。
《阿Q 新論》出版以后,我沒有就此停止自己的研究,而是繼續鉆研下去。1998 年發表的論文《〈阿Q 正傳〉·“魯迅人學”·階級論》又有新的思考:
(1)從哲學人類學,亦即人學的高度,在人類的整個歷史發展范疇內,從人類的根本性的生存境遇和精神狀況出發,對阿Q 進行了更深層次的學術觀照和哲理反思,從而更為自覺地沖出了過去長期禁錮人們思想的階級論的牢籠。
(2)由《阿Q 正傳》透視了“魯迅人學”的主要方面:人的個體精神自由是群體覺悟的前提;阿Q 是“末人”的形象,從反面給人們提供了一面明鏡;深入人的精神機制中去,概括出精神勝利法這一人類的普通弱點,為人類認識自己做出獨特的貢獻。最后指出:從人類黑暗和苦難面切入的特殊思維方式和對被壓迫者悲慘命運的深切同情,使魯迅的《阿Q 正傳》等作品具有宗教式的哲學深度和為受難者而犧牲的高尚的人格魅力,從而顯示出永遠不會消失的“魯迅人學”特有的現代意義。
2000 年《文學評論》第3 期上發表的《阿Q 與中國當代文學的典型問題》是近一年心血的結晶,花費的精力簡直比寫一本書的功夫還大。該文實質上是長期致力的阿Q 典型研究的延伸與深化。延伸意味著由魯迅的阿Q 典型創造經驗延伸到中國當代文學中去,由此覓出了一條深層的貫通的線索——從魯迅的阿Q 到余華的許三觀,代表了20 世紀中國文學中一種全新的寫作態度和思維方式。這就是反常規地“接近真實”,不再去從事精細地描述人物的外貌和周圍環境這種無效勞動,而是去抓住最主要的事物,也就是人的內心和意識;不再竭力塑造人物性格,而是更關心人物的欲望,也就是精神,因為精神高于性格,欲望和精神比性格更能代表一個人的存在價值;也就是脫離常識,背棄現狀世界提供的秩序和邏輯,從而自由地“接近真實”。這種全新的文學流向,在中國,正是由魯迅作品,特別是《阿Q 正傳》所開創的。魯迅從本質上啟悟了余華,余華又從新的視角道出了阿Q 典型創造的奧秘。許三觀的內涵意義是形象地反映了中國人“求諸內”的傳統心理定式與精神機制。創造典型須把握“度”,注意人物性格的多極性與人物之間的對比,從哲學高度全面、深刻地反映社會歷史的真實。“人物第一”,“敘述革命”、文體創新須“貼”著人物進行。小說的突破主要在于哲學的突破,哲學又須通過個性化的人物形象體現,創造典型的難處在“形而上與形而下的結合部”。總之,是以阿Q 典型研究的成果為現實的文學創作提供理論借鑒;反過來又以中國當代文學的創作經驗和余華等優秀作家的超俗悟性,深化了阿Q 典型的理論研究。
我是這樣把余華的寫作方式與魯迅聯系在一起的。那是1999 年3 月14 日的下午,我正在為《文學評論》撰寫阿Q 與中國當代文學典型塑造的論文,余華是其中重要一節,所以幾乎讀遍了他的作品。寫作間隙外出散步,偶然從路邊報欄上看到北京《晨報》刊載的關于余華的訪談:《我相信自己的實力》,第一次讀到“20 世紀一種新的寫作方式”的提法,不禁眼前一亮,立即與魯迅創造阿Q 典型的歷史經驗聯系起來。馬上四處求購當天的北京《晨報》,然而訪遍了周圍報攤都沒找到,只得又回到報欄前重讀。當時真閃現過砸破玻璃把報紙“竊”走之念,當然,理智不會容許自己這樣做。情急之中想到了那時在《北京日報》工作的至交孫郁,趕緊給他寫信索要,他很快就把《晨報》寄來了,令我至今感激不已。我這個人很笨,但是終歸做了一些事,就在于做事情有股子全神投入的韌勁兒和不達目的誓不罷休的鉆研精神。這篇論文發表以后,好幾家媒體做了摘介。我曾經的同事、當代著名學者汪暉轉告我說:“余華講,在眾多關于他的評論中,你的這篇是最好的。”又有一位同行告訴我:余華在一次研討會上,拎著刊登該文的《文學評論》,稱我為“中國最大的阿Q 研究專家”。這使我既不敢當,又分外高興,更加對作家們充滿了感激和欽佩。正是余華使我對多年探討的阿Q 典型問題忽有所悟,而且找到了“精神高于性格”的理論支持。
一個阿Q 讓我思考、研究了五十多年,用力不可謂不勤,成果不可謂不多。然而,不能不感到遺憾的是,始終沒有能夠完全破解阿Q 典型性問題這個魯迅研究界乃至文學理論領域中的“哥德巴赫猜想”,未能摘取到這枚學術王冠上的明珠,與破解阿Q 典型性難題的距離尚十分遙遠。
需要進行自我反思的地方是——
首先,我們這一代學者的知識結構和思維模式是20 世紀五六十年代形成的,受到蘇聯文藝理論構架的嚴重束縛。這種文藝觀幾乎成了一種潛意識的不自覺的本能,雖然80 年代思想解放運動中從字面和形式上一而再再而三地對它進行著批判和抵制,但是一到分析文藝理論的具體問題尤其是阿Q 這種艱深難題時就不由自己意志為轉移地冒了出來,使你總想創新,卻總也跳不出舊有的窠臼,始終在典型、非典型中繞圈子,不能沖出思想的牢籠,另辟蹊徑。這種時代所造成的理論“怪圈”恐怕是非個人的才能和學識所能掙脫的,例如何其芳先生的才能和學識肯定是出類拔萃的,然而他在以空前的理論勇氣提出“共名說”的同時,卻把阿Q 典型研究的主要困難和矛盾歸結為:“阿Q 是一個農民,但阿Q精神卻是一種消極的可恥的現象。”以現在的眼光來看,這種歸結實在有點兒可笑了:難道農民就不能有消極的可恥的現象?為什么要把本來不矛盾的事情硬當成是矛盾的呢?然而,如果做一下換位思考,回到五六十年代的環境中去,就會對何其芳先生表示理解了。阿Q 典型研究的主要困難和矛盾,是到了80 年代中期才由葛中義做出正確歸結的:“阿Q 典型研究中的真正困難和矛盾在于阿Q 這個具體人物自身的性格復雜性,這種復雜性表現為阿Q 的思想意識和言行舉止上有明顯的反常性。阿Q 性格的反常性來自客觀社會生活的復雜性以及作家對阿Q 的性格與命運的評價與感情態度。解決阿Q 典型研究之困難的道路在于要給阿Q 的反常性以合乎社會生活邏輯的解釋,從社會整體現實的角度來認識阿Q性格的合乎社會生活邏輯的本質意義。”(葛中義:《〈阿Q 正傳〉研究史稿》,青海人民出版社1986 年版)
葛中義的這一見解極有理論價值,為以后的阿Q 典型研究指出了一條正確思路,然而也由于時代環境和知識結構的限制,他未及做出進一步的闡發和探討。時代環境和知識結構對學者的制約實在是太大了!我們試回頭看看20 世紀的學術發展史,后五十年不僅沒有出現魯迅、胡適、蔡元培等那樣的大家,就連陳寅恪、湯用彤等那樣的通才也沒有面世,多的是教科書的編寫人和時事的詮釋者。
其次,感到了自己知識結構的陳舊,想竭力汲取新的理論和新的方法,于是像牛進了菜園一樣拼命讀弗洛伊德、榮格和弗洛姆的書,下死力啃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這部“天書”。應該說這對研究視角的拓新、理論思維的深化還是起到了相當大的作用,但是由于時間的倉促和這些理論典籍本身的晦澀難懂,也出現了某種食洋不化、疏通不透的現象,未能進一步消化、融通、提煉,使得有些提法和論述顯得生硬。例如“精神典型”這一概括的確有些過于寬泛,在《阿Q 新論》一書中又做了更細的界定,說明是屬于一種側重反映人類精神現象的變異性藝術典型,文學典型中的一個分支,亦可簡稱為“精神典型”。比以前明晰了一些,但是仍然缺乏鮮明的個性色彩,究竟應該怎樣概括為好?看來已非我的才力所能想到,只能留待后來人去另辟新說了。
再次,雖然下了些功夫,但是遠遠不夠深廣、細透。何其芳先生在《關于〈論阿Q〉——〈文學藝術的春天〉序》中提出了典型問題的研究途徑:“研究各種各樣的典型人物,明了了不同類型的典型人物的差異和特點,并從他們概括出一些共同的規律。”我雖然盡力去研究了一些典型人物,例如堂·吉訶德、哈姆雷特、奧勃洛莫夫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人物等,但是與何其芳先生的要求相比,卻是遠遠不夠的,而且就研究過的典型人物來說,也進行得不夠深細、透徹,因而不可能達到更高的學術境界。
最后,書的一些章節文筆不夠通暢圓潤,顯得有些生澀、煩瑣、臃腫,不夠明快、爽朗,繞了不少圈子卻說不到點子上。當然,出現這種現象的根源還是許多問題連自己也沒有想透。倘若真正想透了,自然就不會這樣了。
值得反思的地方還有很多,主要談以上四點。
進行這種反思,一方面是為了提高自己,促使自己以后的書和文章寫得更好一些。但更為重要的另一方面是為了讓后來人汲取自己的教訓,少走彎路,盡早破解阿Q 典型性問題這個魯迅研究界乃至文學理論領域中的“哥德巴赫猜想”,摘取到這枚學術王冠上的明珠。人生是有限的,我們這一代學者明白自己的不足,卻已經無法彌補,只能期待后來人去超越了。因此,當我看到張全之教授的書評《魯迅研究的“清道夫”與“炭礦夫”》時,感到由衷的欣慰,特別是他對《阿Q 一百年》的批評:“歷史論”部分稍顯薄弱,“馬克思主義精神現象學”這一方法沒有貫徹得很徹底,帶有明顯的嘗試性和探索性等,切中肯綮!我不但衷心接受,還要做更尖銳的自我批評:“歷史論”不是稍顯薄弱,而是太薄弱了。這是在出版社進入最后編校時突然想起的,應該說是一個進展。自己雖然在大學畢業待分配、慈母溘然長逝的人生最艱難時刻,下狠心讀了《國語》《國策》《史記》《資治通鑒》等史書,寫了近一千張讀史卡片,但與專業歷史學者的研究無法比擬。這時再去重讀是根本不可能的,只好從我所信任的歷史學家,譬如雷賾那里,汲取一些研究成果,借以表述自己的觀點。這種二手的研究怎么會不淺薄呢?建立“馬克思主義精神現象學”是1992 年寫作《阿Q 新論》時的雄心,還企圖完成“精神現象史”“20 世紀精神現象史”等巨著。但真一著手,就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只好縮小到《中國魯迅學通史》,副題標了“20 世紀中國精神現象史的一個側影”。人生短促,精力有限,今生是不可能把計劃貫徹徹底了。
當然,我們也自有別人無法替代的地方。這就是我們這一代學者從思想牢籠中沖出的艱苦的精神歷程,《阿Q 新論》一書真正值得一讀的地方正在這里。倘若不愿意讀文藝理論部分的話,不妨讀一讀《悟性論》中的“哲學啟悟”一章“認識自己與認識世界”和《阿Q 新論》的后記“魯迅研究歷程上的三次‘煉獄’”。這里面飽含著我們這一代學者痛苦而深沉的生命體驗和人生感悟,從中也可以感受到阿Q 的真諦,通過阿Q 這面“鏡子”,我們不僅可以悟出自己的“病根”,而且能逐步理解真實魯迅的真實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