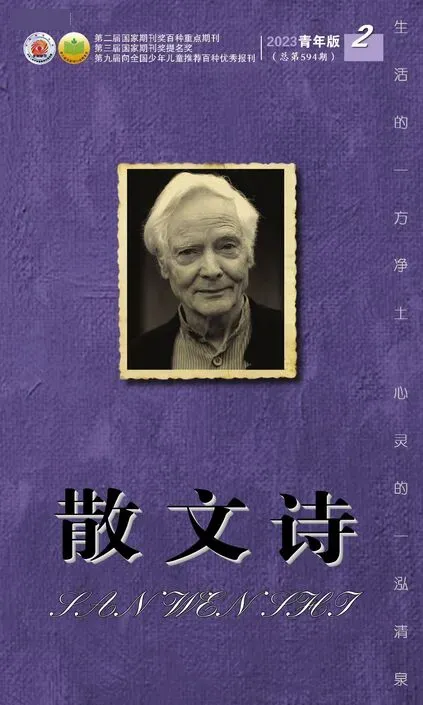創作手記:為了講述某種狀態而塑景
2023-04-05 04:14:32楊清敬
散文詩 2023年4期
關鍵詞:想象
我習慣把自己的寫作當成對某種狀態的塑建。一首詩的完成,就是一次布景的完成,也是這個狀態中自我心性的安置。當我寫作《想象樹葉的內心住著可愛的獸》 這組詩歌的時候,每一首詩的完成都存在一個或是多個場景,它借助我對時間之中觀物觀景時的自我反觀的一個結果,而在結果產生的過程中,我懷揣著自然環境中那些具象表現里言說著的抽象精神部分。
許多時候,我特別感懷于生活中的細小之物,它們易逝如陽臺青菜葉上的蟲子,風吹幾日就是蟲的一生;它們孱弱如田間地頭的蒲公英,受不住一點點風的力;它們光潔的內心如缸里的米粒,喂飽月光的同時也養活人們口中的詞語……在這些細小之物的隱喻里,它們其實都是時間之書的精神暗指,我更相信“消逝的不是盡頭/而是抒情里開始的呼吸”。
為了講述某種狀態而塑景,每天,我睜開眼睛,視野里那些鮮活的景狀,緩慢地走進自己的眼里、筆里、思考里……在我看來,用文字來講述的表達是一種充滿力量的方式,我選擇把一個字、一個詞語或是一句話當作自己講述的釘子、木板、立柱,像握著手錘,用不同的力道把一枚枚長短不一的釘子牢固在自己的城堡里,每使勁一次,面部的情緒就變換一些。
這個時候,我們該想象樹葉的內心為何住著可愛的獸?
猜你喜歡
兒童時代·幸福寶寶(2022年7期)2022-07-11 09:11:00
科普童話·學霸日記(2021年4期)2021-09-05 04:28:51
幼兒100(2021年15期)2021-05-26 06:21:56
小學生作文(低年級適用)(2019年12期)2020-01-18 07:50:36
少兒美術(2019年9期)2019-12-14 08:07:44
時代郵刊(2019年20期)2019-07-30 08:05:40
學與玩(2018年5期)2019-01-21 02:13:06
商周刊(2018年22期)2018-11-02 06:05:28
中國化妝品(2018年6期)2018-07-09 03:12:42
小學生優秀作文(低年級)(2018年5期)2018-04-24 02:05: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