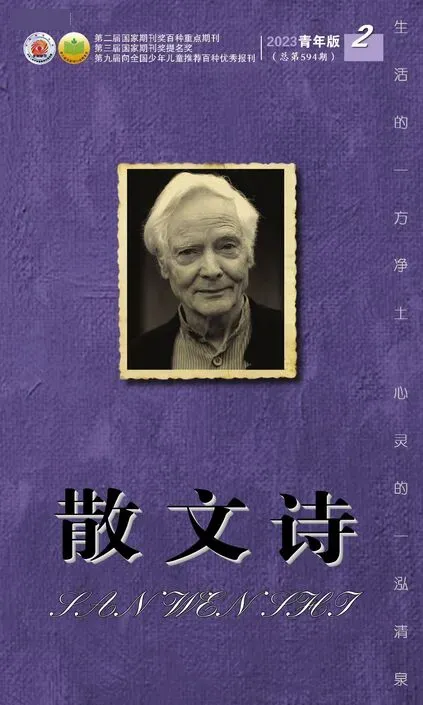行吟南北
雨 歌
水從天上來
滿地的瓷:瓷瓶,瓷碗,瓷罐,瓷娃娃。冒火的天,每粒泥土都站起來重新連接。一包又一包的土,被安放在時間的祭壇上。
鐵器與石頭在山麓中看不到叩擊,鋒利的鉆頭鈍下去。鐵器敲醒了大山。火車的長嘯,叫醒了大山亙古的沉睡,呼嘯聲填補了空洞,關山深處微微動蕩,大地連綿無際。還有什么比時間更有耐心,石頭的心也隨之軟下來,讓長嘯穿過洞穴,回旋。
想了很多年的佛,今日終得一見。老了,真的老了。我擔心她站在崖邊,一不小心就會掉下來。想著想著,禁不住淚水潸然:斑斑駁駁的皮膚,一片連著一片起皺、脫落,眼窩深陷,眼瞼下垂,眼圈烏黑,像我漸漸老去的母親,可依然慈眉善目,保持微笑。
一千多年了,還有什么能讓容顏永駐?只有一顆善心護佑蒼生,使我們站在任何一個角落,都能看見紅石崖上佛的尊容。像母親一樣時常剝一塊金身補貼東家,賜一顆寶珠貼補西家,把自己掏空,把大愛和慈悲播灑人間。
一條河水,穿過麥積山底。水從天上來,一路行吟,一路歌。
漫步大理
在洱海邊上,水,一直在盤子里晃蕩著。那個手端玉盤在江湖上行走的人,叫段譽。江湖如海,時而平靜,時而大浪,像一個人起伏不定的情緒。
也曾懷疑這里的天,傷心的時候不止是下雨,還留下豐碩的紅土地,長滿綠色的莊稼。
在南詔風情島走一走,時而有水,時而有石頭,不確定是沿著水邊走,還是沿著石頭走。長這么大,身上的黃土,覆蓋了一層,又抖落了一層。我還在繼續走,隔海看遠處,太陽島上升起優美的舞姿,聽說海平面一直在漲,等她老了,不知海水能淹到哪里?我的擔心都是多余的,我會一直抖落身上的黃土。
和紅嘴鷗一樣,這一次,我也飛到南方來過冬天。和它們一樣,在洱海邊迎風而立,讓輕盈的頭發隨風隨水起舞;在南國的水里徜徉,忘記南北東西,甚至今夕何夕。也想和它們一樣,歡快地鳴叫,忽高忽低,時而飛翔,時而靜臥水面,如一片片浮萍,在風里蕩漾,輕盈地漂浮,讓洱海的水在我們周圍,泛起陣陣漣漪。
長沙吟詩
葉子將落未落,扛起行囊前往南方。備一方信箋,寫水墨的南方,行詩意的南方,長江以南的南方,有雨巷的南方,姑蘇城外的晚鐘,愛晚亭的讀書聲。
才飲長江水,就喜歡上你。認識你,從一方院落,一池清水,一腔熱血流成的湘江水開始;從清水塘里,一方青石板,一棵盤曲的老樹,中山公園的一段廊橋,一池亭亭玉立的荷花出發。
橘子洲桔子正紅,秋色滿瀟湘。千萬米的距離,九千多天的日夜輪回,翻山越嶺來看你,只為在離心最近的地方觸摸到你。仰望注視,這是夢最敬仰的禮拜。
岳麓書院枯榮的矮草與我對視,塵埃之上的書香洇染了我身,還有什么沒有被我看到,瓦楞上一片經年的枯葉,一株深埋地下的竹筍,破土的聲音驚動衣袂間的風塵。我尾隨朱熹而來,庭院里,這里聚集了師長,他們在辯論,在沉思。
惟楚有材,于斯為盛。咦,于斯為盛——飽讀詩書,飲一滴晨露為詞,一彎明月為逗點,出口的,都是最厚重的詩句。
桂林行吟
從西安到桂林,坐在時間的軌道上,醒來又睡著。山連著山,洞連著洞,腳下的土地被一條繩索串聯,忽明忽暗之間,像手指在黑白鍵上反復地跳躍。單曲循環,曲終,便有一座水城在自己眼前,墨色未干,水洇染開,畫一座樓宇,給你做宮殿。
去桂林的七星公園做一塊石頭,當然是一個創世之舉。要學會忍耐,讓鋒利的尖刃,一刀一刀地刻出景仰、希冀。歷代書法名家在此留下翰墨,張壯飛寫下矢志不渝的決心,組合成蔚為大觀的碑林。還有那么多的石頭,都有自己的故事,它要替時間說話——慷慨激昂地說。八百壯士留下一塊石碑,除了說英雄的壯舉,還說著城市磐石一般的精氣神。秋天開始的時候,整篇文章又一次爬上石頭,把思念種在桂林的石頭上。
金銀塔在“兩江四湖” 的水里淘洗,白天的熱浪和腳下的水滴,只有在夜里才分外清醒。流水的快樂就在于,走走停停,最好不要因忙于趕路而忘記初衷。時不時彎腰,用大大小小的石頭打磨自己,有時停下來,決定再縱身跳入下一塊巖石,育苗,插秧,讓魚米共生。在漓江水上泛舟,讓受傷的身體和心靈,安放在母親搖籃般的溫柔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