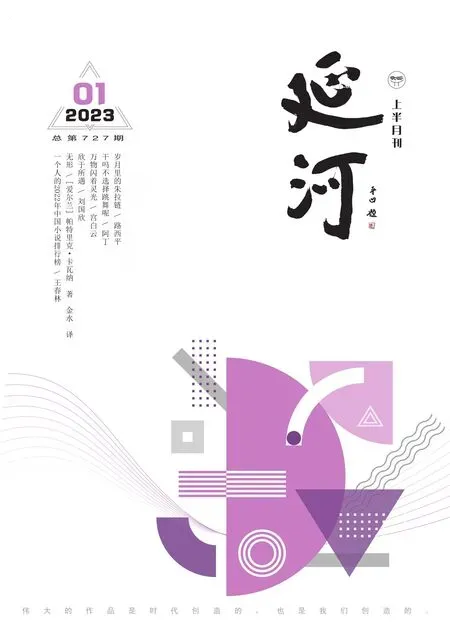2022年中國小說排行榜制榜札記
王春林
在2022年很快就要終結的時刻,返身回望這個新冠疫情依然肆虐的自然年度內我的長篇小說創作,的確感慨良多。無論如何都必須肯定的一點是,盡管新冠疫情的存在給作家們的日常生活帶來了極大的困擾,但神經格外堅韌的作家們,仍然沒有輕易停下手中的筆,仍然在揮毫潑墨,在想方設法以文學創作的方式來回應并對抗殘酷的新冠疫情。其他那些字數篇幅相對短小的文體且不必說,單只是在體量一向龐大的長篇小說領域,依然能夠一如既往地生產一些值得注意的優秀作品,不管怎么說都應該贏得我們的敬意。就我個人的有限觀察,2022 這一年度內,諸如王朔的《起初·紀年》、葛亮的《燕食記》、賈平凹的《秦嶺記》、孫甘露的《千里江山圖》、路內的《關于告別的一切》、付秀瑩的《野望》、喬葉的《寶水》、李鳳群的《月下》、李浩的《灶王傳奇》、艾偉的《鏡中》、王躍文的《家山》、馬伯庸的《大醫·破曉篇》《大醫·日出篇》、葉兆言的《儀鳳之門》、水運憲的《戴花》、須一瓜的《宣木瓜別墅》、石一楓的《入魂槍》、楊爭光的《我的歲月靜好》、霍香結的《日冕》、笛安的《親愛的蜂蜜》、龐貝的《烏江引》、房偉的《石頭城》、郭平的《廣陵散》、葉彌的《不老》、羅日新《鋼的城》、李明春的《川鄉傳》、陳繼明的《0.25 秒的靜止》、唐穎的《通往魔法之地》、吳君的《同樂街》、邵麗的《當歸》、老藤的《北障》、林筱聆的《故香》等,都產生了一定程度的影響,引起了我們的關注。細細地打量這些作品,從題材的角度來說,很多作家都在鄉村和城市兩大領域用力。
篇幅有限,且讓我在鄉村題材和城市題材中各取一部,略加評述。賈平凹《秦嶺記》所集中表達的,其實是一種建立在萬物有靈觀念基礎上的人與大自然之間生命的相互感應。比如第二章中的一個片段,寫藍老板明明看見三四只無名小獸跑進了屋,但等到他進到屋里的時候,卻只是看到地上有小板凳。吊詭之處在于,只有等到他坐在板凳上的時候,才突然發現這個板凳就是一只跑進來的小獸。小獸怎么可能變成板凳?二者之間到底是怎樣的一種關系?難道說是藍老板眼花了嗎?因為無法給出更合理的解釋,我們只能提出這樣的一些疑問。比如第四十七章,寫的是在2000年的那個夏末,月河東岸的草花溝一帶,曾經出現過一個戴竹帽的陌生人,“說是乞丐,卻穿著干凈的白衣白褲”。雖然他并不主動討要,但是在山民們施舍食物的時候,他還是樂于接受。沒想到,十天后,這個戴竹帽的陌生人走出草花溝,在月河上過橋去西岸的時候,竟然落水身亡:“河面很寬,橋是十幾根獨木接連起來的,又窄又長,他用竹竿敲打著,走到橋中間了低頭看,水往下流,橋往上走,叫了聲哎呀,人就跌下去。人在河里很快就被剝去了衣服,而且不再讓看到天,他漂浮了十五里,赤裸裸的,身子一直趴伏在水皮上。”這個人到底是干什么的?他到底為什么不僅會突然現身在草花溝,而且到最后居然還溺水而死?此后很長一段時間里,這個陌生人的落水身亡,還以各種疑問的方式留存在草花溝山民們的記憶中:“他肯定是在尋找,可尋找什么呢:前世和來生?婚姻和愛情?青春和希望?還是丟了魂,要尋找魂的。”“或許他受到了什么委屈和傷害,郁郁寡歡,在過橋時眩暈而失了足落水。或許河水如鏡,他在河水里猛地看見了自己,才哎呀一聲,故意跌下去自殺。”總而言之,由于人已經亡故而不能起死回生,所以,正所謂“一切皆有可能”,山民們(其實更是讀者們)的所有猜測,到頭來也終歸只能是猜測而已。真正令人感到神秘的一點,其實是草花溝一帶自然界發生的感應性變化:“第二年春上,草花溝里開始生長竹子,草花溝從來都沒有長過竹子呀,這竹子越長越多,形成了一片一片竹林。半夜風過,竹林里有一種聲響,混沌低沉,像是在訴說什么,又聽不清訴說了什么,老往睡夢里人的骨頭里鉆。”之所以說是自然界的感應性變化,主要因為從來都沒有長過竹子的草花溝里,自打那個陌生人落水身亡后,便開始發瘋一般地生長出了一片又一片的竹林。二者之間唯一的連接點,就是陌生人的頭上戴著竹帽,手里提著一根竹竿。僅僅因為竹帽和竹竿的緣故,草花溝便會破天荒地瘋長竹子嗎?這樣的一種情節處理所體現出的,毫無疑問是人與大自然之間某種難以用理性的話語加以解釋的因果關系。很大程度上,唯其因為無法做出理性的解釋,所以整部《秦嶺記》才會散發出某種詭異的神秘文化氣息來。而神秘文化氣息本身,也正是中國傳統筆記小說的一個側面。除此之外,第十七章中段凱的頭“就是一個大土豆”,第二十二章中一村人因“走山”(地震)而死亡后湖里突然生出的黑魚,第三十章中圓寂后的老和尚居然成了一截木頭,等等,也都可以從這個方面來加以理解。
閱讀《入魂槍》,令筆者感觸最深的一點,是石一楓對處于急劇變化過程中的社會現實的分外敏感。當然,這里的敏感主要是針對小說所表現的題材而言。盡管在很多時候,當下時代的文學批評領域相較于“寫什么”的問題恐怕更注重于“怎么寫”的層面,但在我的理解中,“寫什么”也即作品的取材問題同樣有著不容忽視的重要價值。讀到石一楓的《入魂槍》之前,在我有限的閱讀視野里,從來都沒有接觸過這一類以游戲或者說電競人群為主要表現對象的小說作品。當下時代或許早已有了類似的作品,但由于我的孤陋寡聞,毫不知情。與那些僅僅滿足于浮光掠影的關注表現類似題材的小說作品相比較,我更看重的,還是作品本身的思想藝術水準。從根本上說,只有那些真正抵達了相當思想藝術高度的作品,方才能夠進入我們的關注與批評視野。正是從這一點出發,我才特別看重《入魂槍》題材上的突破意義。一個相對陌生或者說全新的題材領域,能夠借助于石一楓的生花妙筆得以鮮活生動地呈現在讀者面前,乃是《入魂槍》思想藝術價值一個不容忽視的層面。早在閱讀《入魂槍》之前,我就對年輕人足不出戶、晨昏顛倒的“無論有漢,不知魏晉”的網游生活有所耳聞,但因為自己與這種生活的距離甚是遙遠,對于其具體的樣態,只有在先后兩次認真讀過《入魂槍》后方才有所了解。具體到小說,“我”和“湖里的魚”(魚哥)可以說是極好的例證。首先是“我”,“我”好不容易才考上了北京的名校,沒想到卻染上了難以戒斷的網癮(這網癮,很大程度上也可以被看作是一種時代病,或者說時代的標志)。為了打游戲,不僅足不出戶,晨昏顛倒,甚至還干脆犧牲了正常的大學生活:“說到底不就是打游戲嘛,反正我也沒閑著,自從上大學以來大部分時間都在打游戲。如果說新的世紀和新的城市向我展開了新的生活,那么這種生活就是由一臺破電腦、一根舊網線和一摞從中關村街口那些抱著孩子的婦女手里買來的盜版光盤組成的。為了打游戲,我已經犧牲掉了本該回家和我媽一起度過的寒暑假……我還有什么不能犧牲的呢?”如果說“我”如此這般的生活狀態的敘述還稍嫌籠統的話,那么,“湖里的魚”也即魚哥的撒尿事件就是一個很好的細節。誠所謂不打不相識,“我”和魚哥的結識,就源于他的尿液。那一次,正在專心致志投入游戲或者說電競狀態中的“我”,突然感覺到天上下雨了。沒想到,這雨到頭來卻是魚哥那憋不住的尿液:“說到這兒,也要解釋一下那泡從天而降的尿了,只不過從一個游戲玩家的角度來看,這一切都是那么合情合理——試想他打游戲打的廢寢忘食,就算廁所只在一墻之隔,又哪兒來得及臨陣脫逃去處理自己的生理需求?因此索性拎起可樂瓶子就地解決。而當幾個瓶子都尿滿了,很不幸尿又來了,他也只好把其中一個瓶子里的液體潑出窗外,才能迅速再把自己清空,以保證繼續投入戰斗。”打游戲竟然打到了連撒尿都顧不上的程度,那種“歇機不歇人”的極端投入狀態自然可想而知。與這些年輕人的極度入迷狀態相匹配的,是他們在參與諸如《反恐精英》這樣的網絡電競虛擬比賽時的那種積極與主動。比如,“我”和魚哥以及小熊(“湖里的熊”),不僅化敵為友的由原本的對手而組成臨時戰隊,而且還強拉上能夠“一發入魂”的“瓦西里”一起來與“康德姆”他們那個工科大學的戰隊在電競賽場上展開了高強度的激烈對抗。這種網絡上虛擬的激烈對抗場景,竟然被石一楓的那一支生花妙筆渲染得如同武俠小說一般因其緊張而極富吸引力。
準乎此,斷言長篇小說創作在2022年所取得的思想藝術成就不俗,就應該是一個相對靠譜的可信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