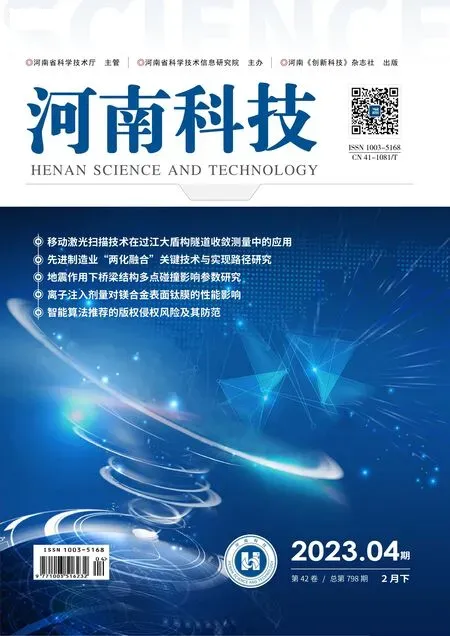“新污染物”的危機干預對策
彭梓洋
(西北工業大學航天學院,陜西 西安 710129)
0 引言
生態環境顯性多維(行業來源、損壞途徑、環節疊加)、隱性多元(化合形式、混合形態、病原構效)的污染治理,已突顯在新污染物的危機防控和補償修復方面,到了持續攻堅克難的關鍵期。實際上,污染與減碳高度相關,這是省級政府生態環境治理的抓手,是“無廢城市”建設和碳中和碳達峰治理的重要工作,也是生態環境保護與修復的具體行動。
1 “新污染物”的內涵及危害特性
隨著人們對化學物質環境和健康危害認識的不斷深入,以及環境監測技術的不斷發展,被新識別出的“新污染物”相對于大家熟悉的二氧化硫、氮氧化物、PM2.5等常規污染物而言,從感觀指標到微觀質性的構效關系上講,還只能以不斷貼合的方式去描述。
1.1“新污染物”的內涵
作為一種新型“改變常規方法和路徑”的污染方式,從外部環境轉向生物和人類生命體的健康質量層面是人們對新污染物的認知路徑。“新污染物”是一個不同于往常的新發現,它推進了人們對非常規污染的認識,在嚴謹的科學意義上,也是對非常規污染賦以最新詮釋。可以說,“新污染物”是一個相對的概念,它使往常的非常規污染具備了新污染形態。不管是惰性物質、活性物質,還是放射性物質,這些物質(污染物),可以造成水、空氣、土壤和生物(人體的器官和細胞)污染[1],給人體舒適、健康和福利造成潛在的危害(患病甚至死亡)。新污染突發事件對社會生活造成物質、身體破壞的同時,也會嚴重影響公眾的心理恐慌[2]。
1.2 新污染物的危害特性
新污染物具有危害嚴重、風險隱蔽、影響持久、來源廣泛和治理復雜等特征,在環境中難以降解,在生態系統中可長期蓄積在環境中和生物體內。新污染物治理的很多措施要通過在水、氣、土壤污染的治理中落實,體現出生態環境保護對環境污染防治修復的“牽引驅動”特點和規律。綜合分析,新污染物具有如下基本特性。
1.2.1 潛隱性。潛隱性是指人們在沒有覺察或不易發覺的時候,新污染物已經開始集聚入侵物料、人體、場所、環境。早期集聚危害的表征不明顯,人們對污染物質沒有發現或認識不足。以微粒污染為例,有1955年特曼等人報告輸液中的微粒和異物,有人們常規使用的材料(塑料、玻璃、橡膠等)和衍生物,有反復加工利用分裂的有機微粒,有在礦業生產中產生的固體粉塵,等等,這些都屬于潛隱介質。
1.2.2 嵌入性。新污染物是一些化學物質,會對人體產生長期的危害。所謂嵌入性,是指新污染物進入受體層間距(二維化合物之間的距離),并經集聚后使層間距增加,人們感官沒有覺察或不易發覺,疏忽或無暇顧及,感染的量級標志不明顯還無治理介入。集聚到一定程度污染物基團刺激器官、降低器官功能,當量和時間足夠的時候,逐漸產生破壞作用,它能傷害甚至殺死細胞,細胞可能會被替代,蛋白質及DNA都可能受到傷害,人們無法利用衍生物或支撐物抑制危害反應。
對人體的損害而言,潛隱性和嵌入性說明了新污染物的各種化學性混合污染物疊加帶來病理的頑固性、不可逆性。
2 新污染物治理存在的問題
“綠色產業”力求節約資源減少污染,《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的意見》也明確提出,到2025年,新污染物治理能力明顯增強[3]。由于全國產業資源稟賦的區域差異,各省份在“綠色產業鏈”方面尚受制于經濟社會的政策、技術與財政投入的總量與質量上的差異。總的來說,各省份要按規劃目標開展新污染物治理,就迫切需要前置性的技術進步與市場化治理機制的高質量運轉,以及后置性追責機制對資源的修復與補償。從全生命周期角度出發,由于績效評價不同,加之污染、排碳產品特性的差異、技術積累不對等、資源優勢的差異等,導致目前按年度劃定對比基準線情景,市政污泥、農業固廢填埋和無能源化焚燒的規范執行與督查,部門責任分擔還無法精準量化分配。另外,源頭減量、材料化利用、能源化利用、肥料化利用等環節存在違約違規行為,生態環境管理者面對類型復雜的污染物問責追責有一定的技術難度。當前主要存在如下幾個方面的問題。
2.1 固廢資源化利用水平偏低
固廢減量化、資源化、無害化,不同部門、不同領域、不同行業的融合不足[4]。固廢處理不好,新污染物就會更加泛濫,固廢末端治理是“無廢城市”建設與碳減排工作。高價值綜合利用工業固廢(包括一般工業固廢和危險廢物)、建筑垃圾、市政污泥、農業固廢,在回收資源化利用上還不能以成本分擔提高經濟效益。尤其重要的是生活垃圾、市政污泥填埋,建筑垃圾、工業固廢循環利用。
2.2 綠色技術創新與推廣存在短板
科學技術支撐需要人才和資金的投入,投入不足科技難以攻關,綠色技術難以引進[5]。盡管政府搭臺給予一定的支持,但是企業能力不足(尤其中小型企業),無法大力推廣節能新技術、新裝備、新工藝。治理常規污染和新污染物成本過高[6],難以在碳達峰碳中和中做好節能減排。
2.3 企業和個人參與的市場機制不完善
面對類型復雜的新污染物,從全生命周期角度出發,企業和個人對相關指標對待程度差異很大,既有主動參與的許昌樣板,也有無法跟進的地市,城市垃圾分類做得好的少之又少。難度最大的還是工業固廢、生活垃圾、再生資源、農業固廢和建筑垃圾等典型固廢源頭減量、循環利用和最終處置[7]。
以上問題需要多領域間的部門合作,從尾礦庫、赤泥庫、廢渣庫的嚴格監管做起,逐步探索碳排放核算體系的市場激勵機制,不斷完善減排市場機制,逐步把碳減排貢獻納入碳交易市場,不斷提高相關固廢行業企業市場競爭力。
3 “新污染物”危機干預的動力機制
新污染物,是一個技術和政策、生產與消費的綜合治理問題。科學與社會、政治與技術的博弈是“新污染物”治理中的行動主體。環境保護和修復一直是國際組織和國家政府的政治目標,當然,預防和抑制新污染物也同樣成為省級政府的一大使命。
3.1“新污染物”的危機干預
新污染物危機干預就是以危機機制消除所有新污染的理念、行為和技術。危機干預的本質包含著行將惡化的生態“危險”和可能出現管控(預防、保護、修復)拐點的“機會”。危機管控是一個應急行動,它要求干預者對正在實際發生的污染事件作出迅捷而準確的判斷,并立即對之采取行政的、法律的、技術的某種行動,然后又要迅捷地采取其他行動。危機干預要用到諸多保護和修復技術,往往是在多部門、多行業的綜合管控下,決斷諸多不確定的行動分解、技術應用。總之,在污染事件發生之前、之中和之后,都要有相應的政策法規、物質技術、人力財力投入[8],也要有教育培訓、問責追責、司法懲戒、法律救濟。從組織架構上,要有來自政府、非政府組織和個人等多方的公力、私力和社會干預。
3.2 新污染物的結構性危機與積累性危機
新污染物治理被動適應政治周期、技術壽命、財政配套等,這是制約修復的關鍵要素。從社會治理角度,新污染物的結構性危機說明了橫向的、上下游間的原料鏈、行政級差、技術鏈斷裂、資金局限等引發的危機。比如省級政府不能用連續的貨幣和財政政策來保證污染預防與修復補償。積累性危機,指諸多因素引發和制約行政協調、資金短缺、行動匹配、經濟衰退、排污技術、財政政策等,形成治而不力、治而無效的困窘狀態,繼續利用現有的技術資源也難以抵充修復成本。這種結構性危機一旦出現,事后修復沒有技術保障,便需要有大的應急行動,破解僵局。
3.3 新污染物危機干預的動力機制
契約讓渡理論決定政府是新污染物危機干預主體。從責任倫理角度,污染修復和補償的利益相關者都是責任主體。從行政建制角度,有政府、企業、社區、村鎮等。所謂新污染物危機干預的動力機制,也是一個有責任和義務的賦能行為主體——借助政治的、文化的、經濟的力量,在技術、道德、倫理、法律等層面出手制止、預防、修復和補償污染。具體而言,最初始于預防性危機管控,就是在人類某種不當活動產生前,有目的、有計劃地采取專業的技術附加、替代和修復措施及其他社會治理措施。行動前的精準研判,需要提前介入“原發過程”,有計劃地改變發展方向、有步驟地改變發展速度、有方法有路徑地改變發展結構和形態。執行中,可采取單一性模式,也可以采取綜合性干預模式,如采取技術干預、行政干預或社會干預(社會救濟)。通常,單一部門干預簡單易行,但效果相對較差,這是因為部門壟斷有一定的不透明性,或滋生腐敗,或低效。最后往往采取“院外技術、民間組織、第三方(媒體)”綜合性模式加以制約,盡管實際操作難度較大(存在偶發性、不確定性),但對這種干預模式往往產生更好的效果。
從目標靶向角度,管控的對象既可以為不當生態活動主體(群體或個體),又可以是生態活動的受體(資源)——各種自然(包括人工干預下形成的第二自然)力量(物質和能量)或作用。就修復而言,可直接針對干預對象,為危機宿主提供修復技術、補償資金或開設產業轉移培訓,也可通過對危機載體進行補救性回填還原、技術脫毒減害。可以直接,也可以間接進行,主要是利用開發新技術、產業培訓、教育疏導,這種干預著眼于改變人類的生產方式,早診斷、早控制。
4 新污染物危機管控的基本方法
對新污染物危害防范,企業往往是高成本、高代價和回報低微的[9]。比如對塑料制品(塑料袋)的管控,許多省份已經無法徹底實現治理預期。這多少給治理決策者、生態受眾帶來治理理念、生活災變、心理壓力等方面的憂慮。針對這種現狀,還需要引入激勵機制強化獎懲管控,具體方法如下。
首先,以企業信息化賦能逐漸提高綠色化改造水平。通過技術創新實現生產消費集約化、產業生態化,扭轉落后的生產生活方式,加大數字化綠色化的技術開發,尤其對普遍的或一般性的生產生活必需品進行綠色化生產。從材料檢測整治到生產消費方式,建立生產性點面-中轉站-垃圾場(無害化處理)全系統、全流程、全周期綠色管控機制,實現經濟產業、生態環境、社會高質量發展。
其次,強化固體廢物法律治理實踐。遵循《中華人民共和國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法》,借助政治系統推進經濟系統,進而推進到社會文化系統中。實際上,最終將污染管控、碳中和碳達峰綜合納入企業經營的成本要素,實現“環境保護與經濟并不抵觸”,使環境保護日益成為企業經濟生存的關鍵要素。
其三,強化污染評價評估制度。認知新污染物對社會的危害性,需要一場深入、全面的經濟績效反思,構建水域治理、空氣與土地污染管控平臺。不把經濟價值等同于健康福利,以污染評估指標調整生產、技術政策。組建一套精細的評估機構,把問題放在引發生態污染的質量層面,探究政府、企業、鄉鎮和社區的能力分擔。
其四,重視第三方生態環保組織。在省級人大環境資源委員會、環保局、主管部門等單位的大力支持下,政府可以采取政府購買服務,支持社會組織研究、教育和游說。依托法人主體的技術轉化、學術科研背景,本著社團宗旨,鼓勵第三方生態環保組織進行各種形式的環保調研、考察及宣傳活動,在知識普及、監督評價和問責追責方面做出行動。
5 新污染物危機干預的對策
新污染物治理是全社會的共同責任,不能簡單劃分為城鄉治理。面對不可逆轉的新污染源,我國法律對造成生態環境損害的處罰額度偏低,還難以彌補生態環境損害和治理成本,迫切需要政府通過人民代表大會改變現有法律條文,調動企業、社會組織、社區、家庭等全民監督、綜合治理。為此,需要注意如下幾個方面。
第一,各級政府應將新污染物管控納入政府治理范圍。加快構建廢棄物循環利用體系,協同推進減污、降碳治理現代化水平。作為區域治理,省級政府要不斷將生態優先、節約集約、綠色低碳理念推進到社會文化系統中,不斷提高公眾認知,達到產業結構調整、污染治理、環境保護協同發展。當然,作為誠信政府,必須要保持政府財政投入,以污染治理績效為增長目標,創建有助于提高新污染物修復能力的治理框架。尤其在涉及生產和消費領域之際,面對利益訴求最大化的不平等競爭模式,杜絕“排污罰款替代達標排放”,逐漸緩解“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的抵觸”。
第二,政府高度重視社會(公眾)救濟與私人救濟。對掣肘生態治理的習俗、技術,決策者不能放任自流,要充分認識社會組織與公眾的互補作用。在私人利益最大化的治理博弈方面,政府要在局部利益與整體權力邊際、技術與公共領域的利益邊界,利用社會力量改變賦能局限性。為此,要加大社會(公眾)救濟與私人救濟,激勵政府公允處罰,優化社會組織舉報投入和獎懲制度。
第三,政府引導高端化、智能化、綠色化的產業新業態,嚴格法律與市場秩序,既要淘汰落后產能,又要兼顧社會接受度,這就需要整合不同階層、群體的利益共同體——企業、社區、村鎮、非政府組織、宗教組織和政治組織等有效、及時、平穩地處理污染事件。逐漸使隱形的看不見的“虧本”的污染管控變成“贏利”的環境保護。先讓富裕地區“虧本”的環境保護變成“贏利”的環境保護,逐漸將治理費用的負擔從勞動和資本這些生產要素上轉移到無害化的能源、原料等這些使用要素上,將污染治理或保護和修復納入企業經營的成本要素,實現由市場決定要素成本與價格這一常態管控狀態。
6 結語
新污染物的危機干預是一個大系統治理體系,不能單一局限在一個環節、一個部門、一個地區的保護和修復技術,在資源和人才投入、行動分解、技術應用上,需要多部門、多行業的綜合管控。另外,在教育培訓、問責追責、司法懲戒、法律救濟方面,要充分利用來自政府、非政府組織和個人等多方的公力、私力和社會干預。最終,綜合利用制度、技術、市場和監管體系,實現多點面、多環節的污染防控,達到管控有力度、補償有成效,實現經濟社會的綠色化高質量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