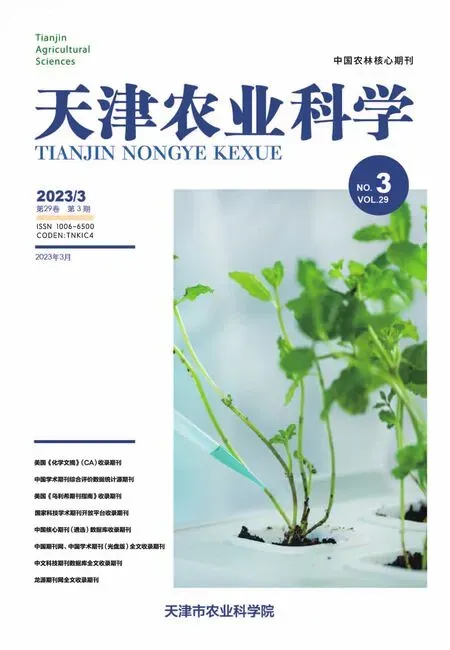大都市區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多維結構特征分析
——以天津市為例
李寧
(天津市自然資源調查與登記中心,天津 300201)
農村集體建設用地是我國城鄉建設用地的主要組成部分,是農村人地關系互動的核心和最強烈的表征形態,反映了農村生產生活的基本空間特征[1]。作為全球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我國農村人口眾多,農村集體建設用地量多面廣,第三次全國國土調查數據顯示,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占全部建設用地的比例高達53.67%。即使到2030 年中國城鎮化率達到70%,農村地區生活的人口仍將超過4 億。農村集體建設用地作為鄉村居民生活居住和產業活動的載體,是一個產住用地共同體[2],尤其是在都市郊區及東部經濟發達地區,城鄉功能交融互促、城鄉界限趨于模糊,農村集體建設用地類型由單一到多樣,由多樣到復合,兼有居住、工業、商服及旅游接待等多功能[3],具有顯著的多樣性特征[4]。
目前,政府和學界對農村集體建設用地研究較為關注,主要可分為兩大領域:從理論探討視角研究農村集體建設用地演變與利用規律,從國土資源管理實務角度研究農村集體建設用地整治[5-9]。在很長時期的土地利用現狀分類和調查框架下,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和城市、城鎮用地等是并列的土地利用類型,僅僅作為一個整體存在,而對其內部結構數據大多無從統計,相關研究多是將農村集體建設用地作為一個圖斑和整體進行研究[10]。隨著認識的不斷深入,農村集體建設用地研究也呈現出微觀化趨勢,部分學者將研究細化到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內部[11]。張佰林等[4]將農村居民點用地的微觀尺度界定為地塊尺度,即單個農村居民點內部的土地利用類型;朱曉華等[12]在評價空心村整治潛力時進行了村莊建設用地的分類;姜廣輝等[5]、曹子劍等[13]對農村居民點用地內部結構變化的區位特點進行了分析;李燦等[14]對農村居民點內部地類進行了統計。但總體來說,目前的研究大多是對農村集體建設內部土地類別進行簡單的定量計算,缺少對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內部結構組合類型的刻畫與提煉[15]。
為促進鄉村振興,國家鼓勵發展農村新產業、新業態,提出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戰略,試點宅基地制度改革和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旨在農村集體建設用地中布局產業用地助力農村產業振興。例如,自然資源部發布《關于加強村莊規劃促進鄉村振興的通知》《關于保障和規范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用地的通知》,要求通過村莊規劃等途徑安排一定比例的建設用地保障農村產業融合發展。對于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三條規定: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城鄉規劃確定為工業、商業等經營性用途,并經依法登記的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土地所有權人可以通過出讓、出租等方式交由單位或者個人使用。針對宅基地制度改革,《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意見》明確提出:“完善農民閑置宅基地和閑置農房政策,探索宅基地所有權、資格權、使用權三權分置,落實宅基地集體所有權,保障宅基地農戶資格權和農民房屋財產權,適度放活宅基地和農民房屋使用權”。上述政策均強調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多樣性和產住功能復合,留足產業發展空間,為鄉村產業振興提供用地保障。因此,探究農村集體建設用地結構及組合類型,深入剖析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多維結構特征,是實現村民生產又生活雙贏目標,創新宅基地制度改革和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改革思路,落實農村產業發展用地保障及服務鄉村振興戰略的客觀需求[16]。
天津市地處華北平原東北部,東鄰渤海,西靠北京,北依燕山,橫跨海河兩岸,位于海河下游,東西寬約117 km,南北長約189 km,陸域邊界1 137 km,土地總面積11 917 km2[17],是國家中心城市、超大城市。天津市對外面向東北亞,對內輻射周邊東北、西北、華北區域內省市自治區。同時,天津被國務院批準為中國北方對外開放的門戶,中國北方的航運中心、物流中心和現代制造業基地,截至2021 年末常住人口1 373 萬人[18]。《全國城鎮體系規劃綱要(2005—2020 年)》賦予了天津建設國際大都市的重任,具有典型的都市農業特征,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呈現多樣化和功能復合演化趨勢。在農村產業融合發展需求及農村土地制度改革雙輪驅動下,要實現鄉村振興,協調推進鄉村居民生活居住與農村產業發展,迫切需要對農村集體建設用地類型及結果特征的研究。基于此,本文以天津市為例,根據國土三調變更數據,運用GIS 空間分析、景觀格局分析、核密度分析方法,在整體深入分析大都市區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多維結構特征的基礎上,細化到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內部,以期在理論上深化認識農村集體建設用地轉型研究內容,在實踐中為指導宅基地制度改革和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助推鄉村振興提供科學支撐。
1 材料與方法
1.1 數據收集與處理
本研究的矢量數據來源于第三次天津市國土調查變更數據,遙感影像來源于自然資源部GlolbeLand30 產品,地區生產總值、常住人口、農村人口等社會經濟數據來源于《天津市統計年鑒》(2020 年)[19]。
矢量數據為編碼為203 的村莊用地,根據(TD/T1014—2007),包含農村居民點以及區內的商服、住宅、工業等企事業單位用地。根據地類含義,本研究將村莊用地界定為農村集體建設用地。據此,參考《全國土地利用現狀分類》(GB/T 21010—2017)中一級分類標準對天津市203 個村莊用地進行歸并,形成天津市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分類(表1)。然后,借助Arcgis10.2、Frag4.2 等軟件,將上述數據進行匯總、歸納,形成各區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內部結構數據(天津市中心城區的和平區、南開區、河西區、河東區、河北區、紅橋區沒有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因此本研究不包括天津中心城區)。

表1 天津市農村集體建設用地結構表
1.2 研究方法
1.2.1 GIS 空間分析法 以2020 年天津市第三次國土變更調查數據為基礎,結合天津市2020 年統計年鑒,對天津市集體建設用地內部各地類數量、類型情況等進行分區,運用Arcgis 生成不同條件下分區圖,為研究天津市集體建設用地多用途潛力及功能轉換的布局和優化奠定基礎。
1.2.2 景觀格局指數法 景觀格局一般指景觀在空間上的形態組織,具有一定的結構特征并能反映其背后的各類過程,目前常用的景觀指數包含三個層級四個類別。運用景觀生態學理論,選取景觀密度、多樣性指數、區位熵指數等景觀格局指數[5],對天津市農村集體建設用地進行景觀格局指數分析,認識天津市農村集體建設用地結構特征及其空間差異(表2)。

表2 天津市農村集體建設用地景觀格局指數選取表
1.2.3 核密度分析法 核密度分析方法廣泛應用于聚集類的實證分析研究[20],可用于分析實體空間密度聚集特征,能直觀表現研究對象的分布概率,其值的高低代表研究對象在空間分布上的集聚程度[6]。本研究利用核密度方法描述天津市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分布的集聚程度。核密度分析法是一種非參數估計方法。設(x1,x2,……,xn)是獨立同分布的n 個樣本點,于是有概率密度如式所示:
式中x-xi在[1,1]之間;h 為帶寬。帶寬越大曲線越平滑,距離遠近通過x-xi的大小來衡量。
2 結果與分析
2.1 天津市農村集體建設用地空間分布特征
2.1.1 整體概述 隨著工業化、城鎮化的推進,天津市農村產業結構發生了巨大變化,促進了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內部結構的多樣性、混合性,以及功能復合。天津市農村集體建設用地總量達到886.43 km2。從空間分布來看,集中在天津北部山區與南部區域。其中,薊州區、寶坻區、武清區、靜海區、濱海新區面積較大,分別為176.17、171.11、144.63、112.95、89.93 km2,分別占天津市農村集體建設用地總量的19.87%、19.30%、16.32%、12.74%、10.14%(圖1)。

圖1 2020 年天津市各區農村集體建設用地面積及占比
2.1.2 核密度分析 從核密度分布圖可知(圖2),天津市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分布呈現較為明顯的空間集聚特征,核密度熱點地區包括天津市北部山區及主城區周邊區域,呈現出“一環一帶”的特點,即環天津市中心城區帶及其連接的自北向南的集聚熱點延伸帶,濱海新區呈現較為明顯的核密度冷點,說明濱海新區農村集體建設用地集聚特征不明顯。

圖2 天津市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分布核密度結果
2.1.3 形狀指數 天津市農村集體建設用地景觀形狀指數整體數值較大,說明集體建設用地斑塊形狀不規則(圖3)。景觀形狀指數最大的是薊州區,其次是濱海新區,分別為73.01、55.69;其余各區由大到小依次為武清區、寶坻區、靜海區、津南區、寧河區、西青區、北辰區、東麗區,分別為53.89、53.14、49.91、43.66、40.80、34.84、32.24、28.54。薊州景觀區形狀指數最大,說明其農村集體建設用地斑塊復雜程度最高、形狀最不規則,這與其多山地的地形條件有關;東麗區、北辰區、西青區景觀形狀指數較低,說明該區域農村集體建設用地斑塊形狀較為規則,其復雜程度相較于其他區域也比較低。總體來說,天津市北部地區農村集體建設用地斑塊形狀相較于其他更加不規則,復雜程度更高。

圖3 天津市農村集體建設用地景觀形狀指數結果
2.1.4 斑塊密度 本研究選取斑塊密度用以描述天津市農村集體建設用地斑塊分布情況。根據斑塊密度分析結果(圖4),天津市農村集體建設用地斑塊密度最大的是東麗區,其次是西青區,分別為44.19、43.09 個·km-2;其余各區由大到小依次為津南區、北辰區、濱海新區、薊州區、寧河區、靜海區、武清區、寶坻區,其密度值分別為、34.92、34.92、30.18、28.94、22.35、19.94、18.99、14.09 個·km-2。總體上,天津市環城四區的集體建設用地斑塊密度高于濱海新區和遠郊五區。

圖4 天津市農村集體建設用地斑塊密度結果
2.1.5 空間分布特征形成原因 從農村集體建設用地整體分布特征和分布密度來看,東麗區、西青區、北辰區等近郊面積明顯較少,這主要是受天津市主城輻射作用較強,大量農村集體建設用地轉化為城市建設用地;同時,農村建設用地改革政策推行導致主城區周邊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分布較為集中,密度明顯高于濱海新區和遠郊五區。區位條件較差的邊遠地區農村非農產業發展緩慢,農村景觀十分典型,宅基地用地占據優勢,而企業用地較少。同時,諸如薊州區、寶坻區、武清區等區域受主城區輻射作用相對較小且受地形影響,非農化程度較低,農村集體建設用地面積較大且斑塊形狀不規則,復雜程度高。
2.2 天津市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內部結構特征
2.2.1 整體概述 農村集體建設用地的形成和發展往往受到經濟、社會、文化因素的影響,從而形成一定的利用形態和空間分布格局。長期以來,隨著天津市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功能趨向多樣性,其內部用地結構也出現了空間分異(圖5)。

圖5 天津市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內部結構
從天津市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內部各地類占比來看,占較大的地類依次為住宅用地、工礦倉儲用地、交通運輸用地、林地、商業服務業用地、水域及水利設施用地,比例分別為52.49%、13.02%、5.74%、5.17%、4.97%、4.64%(表3)。建設用地是村莊用地的主要構成,占比為80.01%;非建設用地(濕地、耕地、園地、林地、草地、其他土地等)占比為19.99%,是村莊用地的重要組成部分,尤其是林地、草地和耕地,三者之和占比達13.49%,這部分是建設用地整治潛力釋放的重要來源。需要指出的是,基于對203 村莊內涵的理解,傳統認知村莊大部分應該是建設用地。但是,通過分析可知,天津市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內部有大約20%的非建設用地;在剩余的80%建設用地內部,傳統認知上大部分應該是農村住宅用地,但實際分析結果顯示,農村住宅用地只占農村集體建設用地的50%,還有30%的其他建設用地,如工礦倉儲用地、商業服務業用地等。

表3 天津市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內部結構表
2.2.2 各區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內部結構特征 天津市各區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內部結構差異較大(表4、表5)。環城四區及濱海新區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內部結構較均衡。其中,西青區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占比最高類型為工礦倉儲用地,占比25.05%,住宅用地占比23.39%,商業服務業用地占比7.39%,此外,耕地、林地、草地等非建設用地占比也較高,分別達到10%、11.35%、、7.29%。東麗區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內部住宅用地占比明顯較小,占比8.84%,占比較高的分別為草地、水域及水利設施用地、林地,分別占26.7%、25.14%、20.35%。津南區農村集體建設用地中,住宅用地占比25.4%,工礦倉儲用地占比23.55%,非建設用地比例較高,林地、耕地、水域及水利設施用地及草地分別占比12.3%、9.3%、9.81%和8.31%。北辰區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內部住宅用地占比35.79%,工礦倉儲用地29.74%,商業服務用地9.47%,耕地、林地、草地、水域及水利設施用地分別占比3.85%、5.55%、5.08%、2.47%。濱海新區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內部結構趨向多元,其中,住宅用地占比21.8%,工礦倉儲用地占比17.36%,草地占比14.05%,水域及水利設施用地占比14.01%,交通運輸用地9.91%。由此可見,天津市環城四區及濱海新區,由于城鎮化水平較高,農村非農經濟發達,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內部結構較為均衡,住宅用地不再是唯一主導的用地類型,工礦倉儲用地、商業服務業用地等也占有較高的比重。

表4 天津市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土地利用類型面積 km2

表5 天津市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土地利用類型占比 %
相比之下,薊州區、武清區、寶坻區、寧河區、靜海區的農村集體建設用地相對單一。薊州區內部農村集體建設用地中住宅用地占67.81%,林地、交通運輸用地、工礦倉儲用地占比17.38%。武清區住宅用地占比64.39%,工礦倉儲用地及交通運輸用地占比17.09%。寶坻區住宅用地占64%,交通運輸用地、耕地、公共管理與公共服務用地占比15.65%。寧河區住宅用地占比57.18%,此外,工礦倉儲用地、耕地及交通運輸用地三類用地占比25.8%。靜海區住宅用地占比47.47%,工礦倉儲用地、商業服務用地占比31.19%。分析得知,天津市遠郊五區,受城鎮化發展輻射較小,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內部結構不均衡,仍以住宅用地占主導,其他土地利用類型占比相對較小。
2.2.3 多樣性指數 根據圖6 可知,天津市各區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多樣性指數從大到小依次為濱海新區>西青區>津南區>北辰區>東麗區>靜海區>寧河區>寶坻區>武清區>薊州區,其數值分別為2.13、2.07、2.00、1.87、1.85、1.61、1.54、1.42、1.37、1.30。這呈現出環城四區和濱海新區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多樣性指數高,遠郊五區多樣性指數低的分布特征。

圖6 天津市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多樣性分析
2.2.4 區位指數 如表6 所示,在寶坻區的農村集體建設用地中,耕地、住宅用地等5 類具有區位意義;北辰區林地、草地等5 類具有區位意義;濱海新區濕地、林地等8 類具有區位意義;東麗區耕地、林地等5 類具有區位意義;薊州區園地、林地等6 類具有區位意義;津南區耕地、林地等6 類具有區位意義;靜海區商業服務業用地、工礦倉儲用地、特殊用地具有區位意義;寧河區耕地、住宅用地等6 類具有區位意義;武清區濕地和住宅用地具有區位意義;西青區耕地、園地等8 類具有區位意義。

表6 天津市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區位指數
進一步分析可知,天津市各區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內部具有區位意義的地類存在一定差異,其中,西青區有8 個,為天津市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內部具有區位意義地類最多的區,武清區具有區位意義的地類最少,僅有2 個,其次是靜海區,僅有3 個;從地類的角度看,林地作為具有區位意義地類的數量最多,園地最少(表7)。

表7 天津市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內部具有區位意義地類數量
2.2.5 內部結構特征形成原因 近郊農村建設用地內部多樣性呈現出圈層化特征,即內部結構多樣性由環城四區向周邊遞減。主要原因是區位條件越好受到城區輻射越強,產業活動強度越大,農村居民點承擔的多功能性越強。環城四區緊鄰主城區,濱海新區是國家級新區,農村非農經濟發達,因此,農村集體建設用地類型齊全、結構均衡,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呈現出明顯的多功能特征;遠郊五區農村非農經濟相對欠發達,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內部結構不均衡,建設用地多功能不足。
3 討論與結論
(1)天津市農村集體建設用地空間分布特征。一是天津市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分布呈現出由中心市區向環城四區、遠郊五區及濱海新區階梯狀遞增的特征,其中,農村集體建設用地總量較多的區集中在天津北部與南部,靠近天津市中心的環城四區農村集體建設用地面積占比小。二是天津市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分布呈現較為明顯的空間集聚特征,其核密度熱點地區包括天津市北部山區及主城區周邊區域,呈現出“一環一帶”的特點。三是形狀指數顯示天津市北部山區和濱海新區的集體建設用地斑塊形狀相較于其他區域更加不規則,復雜程度更高。斑塊密度結果顯示,天津市環四區的斑塊密度高于其他區域,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密度相對較高。
(2)天津市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內部結構特征。一是天津市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內部以建設用地為主,占比為80.01%,其中,住宅用地占比為52.49%,工礦倉儲用地、商業服務用地等其他建設用地占比27.52%;非建設用地(濕地、耕地、園地、林地、草地、其他土地等)占比為19.99%,而這部分也是天津市農村集體建設用地的重要組成部分,非建設用地目前占比較大,表明當前天津市農村集體建設用地整治潛力較大。二是天津市各區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內部結構差異較大,城市經濟發達的環城四區和濱海新區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內部結構較為均衡,除了住宅用地外,工礦倉儲用地、商業服務業用地等也占有較高的比重,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多樣化程度高;相比而言,遠郊五區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內部結構較為單一,以住宅用地為主,多樣性指數較低,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功能多樣性不足。
(3)目前學界對農村居民點的研究,多基于單一尺度,從宏觀尺度研究農村居民點布局[21]、演變及驅動力[22]、重構與整治[8-10],從微觀尺度研究農村居民點用地內部結構[15]、功能[16]、混合利用[23],很少有研究將兩者結合起來,全面認識農村居民點用地結構多維度特征。本文通過對國土三調變更調查數據及社會經濟數據,運用核密度分析、景觀格局分析以及GIS 空間分析的方法對具有典型都市農業特征的天津市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多維結構進行分析,是從研究視角上對前人研究的補充和豐富;同時,在鄉村振興戰略和農村土地制度改革背景下,本文通過對天津市農村居民點用地結構的系統分析,研究結果可為天津市農村宅基地制度改革、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提供決策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