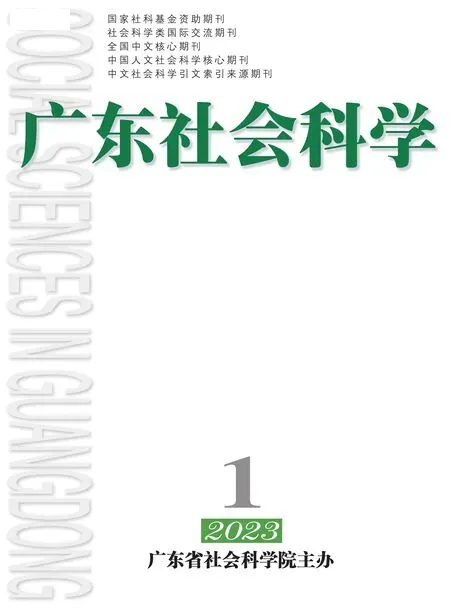理性與信仰的對立與融合:克爾凱郭爾的信仰觀及其啟示*
王仕民 金嬌
理性與信仰的關系處理是理解克爾凱郭爾信仰觀的重要線索,也是其批判現(xiàn)代性的核心部分。克爾凱郭爾主要圍繞理性與信仰的關系主題來建立信仰觀,因而其信仰思想相應地分為理性與信仰的對立與融合兩個部分。它們的問題意識如下:一是理性與信仰的對立關系如何影響到其真理觀的確立?二是理性與信仰的融合關系如何促成真理的實現(xiàn)?對第一個問題的回答,使克爾凱郭爾構建起基于信仰的主觀真理學說,從而對理性主義的偏狹和異化進行了批判。對第二個問題的回答則促使他認為理性的激情是個體進行信仰跳躍進而實現(xiàn)主觀真理的重要契機。盡管學界關于克爾凱郭爾的研究已有較多成果,但在從理性與信仰關系對立與融合來正面研究其信仰觀及其啟示性意義的成果則為數(shù)不多。首先,學界較多認為他所提出的“真理是主體性”“信仰是荒謬”等命題反映了他對理性的否定,具體表現(xiàn)為對工具理性、抽象思辨的反思和批判。學界盡管也看到克爾凱郭爾對理性有限的肯定態(tài)度,如利文斯頓①[美]詹姆斯·C.利文斯頓:《現(xiàn)代基督教思想(下)》,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640頁。,但對于理性與信仰的融合的論證卻不夠深入。其次,隨著國內(nèi)外對克爾凱郭爾研究的深入以及著作的翻譯,學界一方面逐漸開始認識到克爾凱郭爾思想彌合信仰與理性裂痕的努力,如劉阿斯②劉阿斯:《信仰與理性的沖突與諧和——對克爾凱郭爾信仰觀之合理性的一種辯護》,《宗教學研究》2010年第3期。、溫權③溫權:《信仰的悖論與理性的限度——克爾凱郭爾人神辯證法芻議》,《浙江工商大學學報》2016年第1期。等。另一方面也推進了學界對克爾凱郭爾信仰觀的時代意義的研究,有不少文獻也開始注意到克爾凱郭爾信仰觀對于培育真誠信仰的啟發(fā)性意義,如國外的休伯特·德雷福斯和簡·魯賓借助克爾凱郭爾的信仰觀批判現(xiàn)時代的虛無主義④Hubert L.Dreyfus,Jane Rubin,“Kierkegaard on the nihilism of the present age:the case of commitment as addiction”,Synthese,1994,98(1).pp.3-19.,而國內(nèi)學者劉森林也通過比較闡述了克爾凱郭爾思想對于培育真誠信仰方面的啟示⑤劉森林、馮爭:《從上帝之死到真誠信仰:恩格斯與克爾凱郭爾》,《馬克思主義與現(xiàn)實》2021年第2期。。針對本文所限定的理性與信仰的關系視角來闡述克爾凱郭爾的信仰觀及其啟示較少,本文試圖進一步闡明克爾凱郭爾關于信仰與理性融合的論證邏輯,推進兩方面的進一步合流。
一、理性與信仰對立:克爾凱郭爾信仰觀構建的基本框架
理性與信仰的功能差異和對象差異是克爾凱郭爾構建其信仰觀的基本視角,而理性與信仰的關系如何處理則直接決定了克爾凱郭爾宗教信仰觀提出的主觀真理思想。下面我們圍繞理性與信仰的關系分別探討克爾凱郭爾信仰觀提出的緣由、基本視角和主要內(nèi)容。
(一)理性主義的侵蝕:克爾凱郭爾信仰觀構建的思想史緣由
信仰本是中世紀毋庸置疑的時代基石,理性充其量只是其論證上帝的工具或附庸,從而臣服于信仰的權威。然而,隨著宗教改革和啟蒙運動的興起,理性主義突破宗教信仰的重圍逐漸興起,并在笛卡爾“我思故我在”的普遍懷疑中獲得其作為時代精神的地位。自此,理性昂首闊步,取代信仰成為時代的精神,理性鍛造和鑄就了現(xiàn)代性的精神內(nèi)核。康德試圖限制理性來為信仰開辟地盤,但黑格爾認為康德只是實現(xiàn)了理性與信仰之間外在的綜合。然而黑格爾對信仰的理性化處理,看似實現(xiàn)了一種基于理性的內(nèi)在化統(tǒng)一,卻在某種程度上遺忘了現(xiàn)實的個體生存。黑格爾哲學作為理性主義的一座高峰,是現(xiàn)代性在思想層面的自我確證,因而也是現(xiàn)代性思想的典型代表。黑格爾在“現(xiàn)實性”的討論中,將理性與現(xiàn)實進行了辯證法的關聯(lián)。“凡是合乎理性的東西都是現(xiàn)實的;凡是現(xiàn)實的東西都是合乎理性的。”⑥[德]黑格爾:《法哲學原理》,范揚、張企泰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1年,第12頁。黑格爾的這個格言并不能簡單地理解為對現(xiàn)存普魯士政府辯護。現(xiàn)實并非現(xiàn)存,黑格爾說“當我提到‘現(xiàn)實’時,我希望讀者能夠注意我用這個名詞的意義,因為我曾經(jīng)在一部系統(tǒng)的《邏輯學》里,詳細討論過現(xiàn)實的性質(zhì),我不僅把現(xiàn)實與偶然的事物加以區(qū)別,而且進而對于‘現(xiàn)實’與‘定在’,‘實存’以及其他范疇,也加以準確地區(qū)分。”①[德]黑格爾:《小邏輯》,賀麟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年,第43頁。恩格斯曾在《路德維希·費爾巴哈與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一文準確地指出:“在黑格爾看來,決不是一切現(xiàn)存的都無條件地也是現(xiàn)實的。在他看來,現(xiàn)實性這種屬性僅僅屬于那同時是必然的東西。”②《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21頁。恩格斯所說的這種具有“必然的東西”其實就是理性,所有現(xiàn)存的東西都是理性的外部表現(xiàn)。黑格爾哲學在精神辯證法的體系中調(diào)和理性與信仰的關系。他認為宗教信仰奠基于情感之上,而情感是主觀的偶然的,因此宗教信仰不具有客觀性和確定性。因此,黑格爾試圖用絕對精神的自我揭示的辯證過程來定位宗教信仰的位置。他認為宗教信仰的偶然性必然在絕對精神的發(fā)展中被揚棄,宗教必然在理性辯證法中轉(zhuǎn)化為哲學,才能達到理性普遍性的高度,才能以概念的形式把握宗教的本質(zhì)。“惟有通過思維對于事物和在事物身上所知道的東西,才是事物中真正真的東西。”③[德]黑格爾:《邏輯學》,楊一之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6年,第26頁。可見,在黑格爾的調(diào)和中,信仰成為絕對精神的一個必然被揚棄的環(huán)節(jié),信仰被黑格爾的理性主義納入到精神辯證法的體系之中,成為“精神自我認識的一種樣式。”④[加]查爾斯·泰勒:《黑格爾》,張國清、朱進東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2年,第739頁。黑格爾認為耶穌基督道成肉身的故事反映的是精神的理性活動,基督受難死亡象征有限性的毀滅,而耶穌死而復活則表征精神在揚棄有限性之后獲得自我的充實和完善。
克爾凱郭爾不認同黑格爾將宗教納入理性哲學中的做法,他堅決維護上帝的超驗性和理性的有限性之間的差異,理性的能力并非無限的,而信仰則在理性認識能力范圍之外。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洛維特認為克爾凱郭爾和馬克思都對黑格爾哲學進行了激烈的批判,“馬克思的經(jīng)濟學分析和基爾克果的試驗心理學無論在概念上還是在歷史上都是休戚與共的,都是黑格爾的一個反題。”⑤[德]卡爾·洛維特:《從黑格爾到尼采》,李秋零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14年,第217頁。克爾凱郭爾認為黑格爾對耶穌基督的概念化解釋表現(xiàn)了理性的無知和狂妄。“黑格爾最危險之處在于他篡改基督教——以使它和他的哲學相一致。”⑥[丹]索倫·克爾凱戈爾:《克爾凱郭爾日記選》,姚蓓琴、晏可佳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年,第130頁。道成肉身與其說是對理性精神的模仿,不如反過來說是思辨理性在低級層面上模仿信仰。黑格爾哲學的整個體系都在將基督教哲學化,從而使基督教遺忘了個體生存的激情,宗教日益成為世俗國家的附庸,基督徒與國家公民日益趨同,基督信仰已然名存實亡。為了深入批判信仰的理性化傾向,克爾凱郭爾圍繞理性與信仰的功能差異和真理觀差異對信仰觀進行了重新構建。
(二)功能差異:理性與信仰的對立關系
理性與信仰的功能差異是克爾凱郭爾信仰觀構建的基本視角,是其主觀真理得以建立的基本支撐。對克爾凱郭爾而言,人與上帝存在絕對的差異。作為信仰對象的上帝是一個無限者,它與人有著絕對的差異,上帝與時間中生存的人不同,上帝在時間之外,神是創(chuàng)造者,而人和時間都是被創(chuàng)造物。人的本質(zhì)由神來規(guī)定。因此神是超出理性能力理解范圍的“未知者”。與人絕對不同的永恒的神竟然通過道成肉身在時間中顯現(xiàn)。理性主義顯然無法認可神的這種奇跡性的顯靈。理性主義僅多承認歷史中存在著某個叫耶穌的宗教改革家,他開創(chuàng)了一個從猶太教分離出來的世界性宗教,但他絕不是真的神。理性無法理解這個悖論,因而無法接受歷史中的人如何能夠成為神,更無法理解神對人的愛。克爾凱郭爾認為只有在信仰跳躍的瞬間,人才能擺脫理性的限制從而擁抱神的恩典,否則理性的眼睛再雪亮都無法認識神真實存在。只有基于信仰的愛,并在神的恩典之下,人才能真正理解神,否則,理性眼中看到的只是絕對的悖謬。克爾凱郭爾認為,理性的最大悖論就在于想要“揭示思想本身不可能想到的東西”①[丹]索倫·克爾凱郭爾:《哲學片段》,翁紹軍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年,第50頁。。理性既不能也沒必要去證明上帝的存在。理性對上帝的認識其實是一種僭越,表明理性在認識未知者時的無能和不自知。未知者“是絕對的差異,才沒有任何識別的標記,規(guī)定絕對差異,看來像是接近對存在的揭示,但實際上并非如此,因為認識甚至不可能去思考絕對的差異。”②[丹]索倫·克爾凱郭爾:《哲學片段》,翁紹軍譯,第60—61頁。
假如理性不顧一切地取代信仰,強行對上帝進行解讀和把握,那么這種僭越就是對信仰的“冒犯”。冒犯不但表現(xiàn)了理性無知而盲目的自信,也屏蔽了作為悖論的信仰真理。克爾凱郭爾對理性能力的反思和限制,其實是對康德批判哲學的繼承。康德在純粹理性批判中將理論理性的能力限制在現(xiàn)象界,認為這樣就可以為道德和信仰留出地盤。康德認為上帝并不是有限的理論理性所能認識到的。理論理性一旦僭越就會造成二律背反。克爾凱郭爾對信仰的重視一定程度上受到康德“終止認識便為信仰留出空間”這一觀點的影響。康德限制理論理性的能力目的是為實踐理性敞開可能,如果說“康德走出了邁向主觀性的第一步,克爾凱郭爾則做出了最后的飛躍”③[美]蘇珊·李·安德森:《克爾凱郭爾》,瞿旭彤譯,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第48頁。。正是因為理性能力的有限性,基督的永恒神性根本上不能在具體的歷史事件中獲得證明。基督教不是現(xiàn)代理性思維方式奠基的歷史性宗教。“圣史”是一個“永恒的事實”,而不是普通的歷史事件,前者不具有直接性,因此我們不能用考古學的方式證明死而復生的耶穌基督的真實性。上帝的神跡純粹是一個悖論,信仰的真理與歷史真理截然不同,它不是數(shù)學公式,也不是待證實的歷史事實,因此,“對于基督教真理的一切世俗-歷史的爭吵、辯論和證明必須統(tǒng)統(tǒng)拋棄;唯一的證明只是一個‘信’字”④[丹]索倫·克爾凱戈爾:《克爾凱郭爾日記選》,姚蓓琴、晏可佳譯,第230頁。,亦即“內(nèi)在的證明”“靈魂的證明”是對基督教真理的唯一的證明。
對克爾凱郭爾而言,理性僭越產(chǎn)生的悖論恰恰意味著信仰的真理。他從詞源學的角度進一步闡述了悖論隱含的真理維度。“悖論”作為哲學的概念,在傳統(tǒng)思想史中主要是從認識論的角度進行界定的,如芝諾悖論和康德的二律背反,都認為悖論是指與理性的能力和規(guī)律相矛盾的現(xiàn)象或觀點。從詞源上來看,悖論源于希臘語Paradoxos的中性單數(shù),其基本意思是與主觀意愿相違背。由于該詞的前綴“Para-”具有“超過”“超越”的意思,使該詞具有兩個基本的內(nèi)涵:一是觀點理論的自相矛盾,二是在這個自相矛盾中暗含一個與常識相悖反的更具超越性智慧的論點。在理性看來是悖論的信仰之所以成為真理,就是因為克爾凱郭爾在上述第二層的意義上使用悖論概念,據(jù)此他將悖論的意義從認識論提升到了生存論的層面。因此,對克爾凱郭爾而言,上帝這類存在既然無法在理性之中得到理解,就必須在理性之外的人的生存意義中去闡發(fā)悖論所具有的真理內(nèi)涵。克爾凱郭爾認為,這種生存性的真理內(nèi)涵只有在個體與上帝的信仰關系中才能得到闡明。因此我們必須進一步來闡述克爾凱郭爾信仰觀所建立的主觀真理。
(三)主觀真理:克爾凱郭爾信仰觀的核心內(nèi)容
真理是什么以及以何種形態(tài)出現(xiàn)是以如何處理理性與信仰關系來決定的。克爾凱郭爾通過對比理性與信仰對真理的不同界定,進一步對真理的形態(tài)和內(nèi)涵進行了界定,從而確立了以主觀真理為核心的宗教信仰觀。信仰既然對于理性而言是一種悖論,那么作為悖論的信仰如何能夠成為一種真理呢?這是克爾凱郭爾進一步思考的問題。
克爾凱郭爾在《結論性的非科學的附言》中區(qū)分了主體與真理的關系,對思想史上存在的主觀真理和客觀真理進行批判性揚棄。主體對待真理有主觀反思和客觀反思兩種方式。兩種反思分別對應主觀真理和客觀真理。主觀真理以蘇格拉底為代表的,客觀真理則以黑格爾為代表的。客觀真理認為真理是客觀的、普遍的、確定的,為了避免主觀性所帶來的偏見和偶然,主體必須在反思對象時保持客觀中立的態(tài)度。克爾凱郭爾認為,這種客觀性意味著主體與真理處于一種冷冰冰的距離中,這種真理是遠離主體生存的。而且由于主體擯棄了自己的一切情感特征,這種主體也是客觀冰冷的“純抽象形式”。客觀真理“把主體變成了偶然隨機的東西,因而把主體的生存改造成了某種非人格的東西,而這種非人格的特征,恰恰既是其客觀有效性之所在。”①S.Kierkegaard,The Concluding Unscientific Postscript,Translated by David F.Swenson and Walter Lowrie,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41,p.173.與此不同,主觀反思則是一種具體性、內(nèi)在性的反思,它不像客觀反思那樣強調(diào)冷靜中立從而遠離生存,而是聚焦于主體自身,并在生存者領會自身。主觀反思的目的并不是為了在思想上把握真理,而是試圖要在生存中讓個體與真理形成密切的關聯(lián)。如果說客觀真理思考的問題是上帝是否存在,那么主觀真理思考的則是個體與上帝處于“怎樣”的關系。在克爾凱郭爾看來,蘇格拉底在審判中堅持自己的信念,對死亡毫不畏懼,足以成為主觀反思的典型代表。“他甘冒失去生命的風險,他擁有直面死亡的勇氣,憑著無限的激情,他如此決定了自己的生活的樣式……”②S.Kierkegaard,The Concluding Unscientific Postscript,p.79.
克爾凱郭爾對蘇格拉底堅守真理的信念大加贊賞,認為在世俗化、大眾化的時代,基督徒需要的不是對客觀真理的信仰,而恰恰是蘇格拉底淋漓盡致表現(xiàn)出來的對信仰的激情。否則,即使客觀真理的內(nèi)容是正確無誤的,但主體卻從未與之有任何的關聯(lián),從未在心底為之作出內(nèi)心的抉擇,那么客觀正確的真理也于主體無任何益處。“抉擇的因素是對無限者的激情,而不是無限者的內(nèi)容,因為其內(nèi)容正是其自身。主體性和主觀的‘怎樣’就以這種方式構成了真理。”③S.Kierkegaard,The Concluding Unscientific Postscript,p.76.有兩個案例很好地展現(xiàn)了主觀真理的確立需要主體內(nèi)心的抉擇。“上帝考驗亞伯拉罕”一例凸顯了信仰與倫理的對立。上帝愛人卻讓亞伯拉罕以子獻祭,在理性主導的倫理世界中顯然是一個無法調(diào)和的悖論。克爾凱郭爾認為古希臘神話中的悲劇英雄德行崇高,代表的是理性普遍性和可理解性,而作為宗教英雄的亞伯拉罕則抵制住世俗倫理的誘惑,在個體內(nèi)在的抉擇中選擇對上帝的絕對信任,其中彰顯的是個體與上帝關系的絕對性和隱秘性。決定亞伯拉罕抉擇的不是外在倫理的普遍規(guī)律,而是個體內(nèi)在的信仰,它需要在恐懼與戰(zhàn)栗中經(jīng)受悖論的考驗。而在寡婦與小偷的寓言中,寡婦在毫不知情的狀態(tài)下虔敬地把已被小偷掉包的錢包投入捐助箱,盡管錢已被偷去,卻絲毫不影響寡婦虔誠而喜悅的心情。可見為了信仰而全身心的投入使得信仰的悖論成為值得信任的真理。上述案例都印證了克爾凱郭爾將一種個體內(nèi)在信仰的抉擇作為確立真理的關鍵性意義。“人只有拋棄旁觀者的客觀角度,以內(nèi)里的熱情親身參與神人關系,才能認識神。……沒有信心的縱躍,人可以擁有倫理性的宗教,但絕不是正宗的基督教。”①[美]奧爾森:《基督教神學思想史》,吳瑞誠、徐成德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619頁。
二、理性與信仰的融合:克爾凱郭爾信仰觀的實現(xiàn)邏輯
通過對理性與信仰的對立的分析,克爾凱郭爾建構起一種基于信仰的主觀真理,但這種真理在個體的生存中如何具體實現(xiàn),在這個實現(xiàn)中理性對于實現(xiàn)主觀真理有何作用等問題卻依然未得到很好的闡明。下面我們將對這些問題做進一步的闡述。
第一,理性的激情是個體生存通往信仰真理的路徑。黑格爾想要通過精神的辯證法不斷揚棄概念的矛盾最終實現(xiàn)絕對精神自我認識自身的和諧,但克爾凱郭爾認為黑格爾的哲學體系過于強調(diào)矛盾的調(diào)和而缺乏激情,導致個體成了一個被敉平了任何沖突和悖論的平庸之輩。盡管克爾凱郭爾認為理性是對信仰的冒犯,從而會產(chǎn)生絕對悖論,但是克爾凱郭爾并不是絕對的否定理性的作用。為了闡明從理性的絕對悖論通向真誠信仰的路徑,克爾凱郭爾區(qū)分了兩種激情,即理性的激情和信仰的激情。前者是理性試圖認識未知者的沖動,后者則是對永恒福祉的愛。他認為蘇格拉底的哲學激情便是一個值得肯定的理性的激情。盡管蘇格拉底也是理性主義的代表,但蘇格拉底的哲學激情在本質(zhì)上是一種對智慧的“愛欲”,這種愛欲知道自己的無知,并沉醉于對真理的追求,即使不斷地面對挫折和失落。
如果說理性對上帝的思辨式把握是對神的冒犯,那么我們必須放棄工具理性的精明算計,冒險進行一場意志的抉擇。這種意志的冒險抉擇一方面表明其信仰與情感和意志息息相關。在丹麥語中,內(nèi)在性“Inderlighed”既可以是形容詞,指的是“內(nèi)部的”和“情感的”,也可以是副詞,指的是“真誠地”或“真摯地”②王齊:《生命與信仰——克爾凱郭爾假名寫作時期基督教哲學思想研究》,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54頁。。對克爾凱郭爾而言,主體生存的本質(zhì)就是作為內(nèi)在性的激情,沒有激情,人也就淪為一個理性機器。信仰一旦喪失激情,個體與上帝的關系就如同冷卻了的熱戀,變得沒有活力和溫度。“激情既是悖論的來源,也是對悖論的回答。”③S.Kierkegaard,The Concluding Unscientific Postscript,p.205.另一方面,由于克爾凱郭爾對理想激情的贊賞,這種冒險也與不斷攀登的激情有關。因此,當理性與悖謬遭遇的瞬間,必然產(chǎn)生兩種結果,要么彼此不融,要么相互理解。第一種結果是理性想要一勞永逸地消除看似悖論的東西,理性想要將其納入到自己的概念體系之中。當理性無法將基督道成肉身的荒謬合理化時,理性感到前所未有的“冒犯”,為此理性將“未知者”判斷為非真理的謬誤。這既是理性的狂妄,也是理性的不幸。現(xiàn)代性的種種困境也因此產(chǎn)生。第二種結果則是在信仰的跳躍中使理性與信仰獲得和解。和解的前提是理性具有不斷沖破自身邊界的沖動,克爾凱郭爾認為這種沖動其實就是哲學追求智慧的“愛”。
克爾凱郭爾提出了自愛與愛人的辯證關系,從而描述了理性從狂妄自戀到舍己成仁的轉(zhuǎn)變契機。“自愛是愛的基礎,但當它出于頂點時,它那悖論的激情就決意要它自己降下來。情欲之愛也決意要這樣做,所以,這兩種力量都在激情的瞬間出于共同的了解之中,而這種激情恰正就是情欲之愛。”①[丹]索倫·克爾凱郭爾:《哲學片段》,翁紹軍譯,第64頁。在克爾凱郭爾看來,自愛反映的是思辨理性自私傲慢、冷漠無情的面貌,其典型代表便是黑格爾。在《精神現(xiàn)象學》中,包含正-反-合三個步驟的精神辯證法亦步亦趨地將矛盾合理化,理性也就在不斷的揚棄中最終把握“絕對理念”。但克爾凱郭爾認為,黑格爾對理性和信仰的調(diào)和顯然是讓信仰理性化,使信仰不再有悖論,而悖論恰恰是激情產(chǎn)生的關鍵。一個缺乏激情的戀人,不過是一個平庸之輩而已。而愛情則發(fā)生在理性尋求通達悖論時迸發(fā)的激情的極致時刻,此時,激情的極致與尋求自身的毀滅合二為一,理性放棄自身的本性,向無法理解的悖論敞開胸懷,理性的自愛轉(zhuǎn)化為對上帝之愛。在這個轉(zhuǎn)化中,理性并未完全走向毀滅,而是揚棄在愛情之中。
愛情的典型代表是蘇格拉底。蘇格拉底所展現(xiàn)出來的哲學激情,是克爾凱郭爾提出信仰激情的原型。當然這兩者也有差別。蘇格拉底之所以被克爾凱郭爾看重,主要是因為蘇格拉底的哲學強調(diào)要認識人自身,要知道自己的無知。理性在他的哲學中具有一種謙虛的品格,理性面對悖論的冒犯,他不是退縮,而是沉醉其中,永不停歇地追求智慧。盡管蘇格拉底的哲學激情所追求的智慧并非上帝,但這種激情四射的品格卻是黑格爾為代表的啟蒙理性和世俗化的基督教所不具備的。
面對悖論的冒犯,人的處境趨于絕望。此時,理性的證明就像笛卡爾的玩偶,受制于各種邏輯規(guī)則。對于悖論理性已然束手無策。克爾凱郭爾認為,悖論并非毫無意義,在理性絕望之時,只有絕對的悖論在前方引路。悖論是個體在絕望中的救命繩。克爾凱郭爾把人與上帝的關系比作愛情,愛情需要情感和意志,一旦純粹靠理性的證明和計算,愛情就會降溫。既然上帝本身是不確定的,而且信仰的結果也是不確定的,那么從理性到信仰的跳躍將是一次意志冒險的抉擇。信仰并不是可以通過確定的事功行為就可以獲得的事件。救贖純粹是上帝的恩典,馬丁·路德宗教改革之所以反對贖罪券,就是因為贖罪券把信仰得救變成了一場交易。在信仰中,我們要做的是承認自己的罪責,然后做出自我棄絕的賭注和冒險。
第二,理性激情對于信仰跳躍的推動作用表明,克爾凱郭爾的主觀真理并不意味著信仰是一種任意的主觀性。信仰并不否定理性,只是限制理性的作用范圍。克爾凱郭爾認為極端隨意的主觀性同樣帶來壞的影響。克爾凱郭爾限制理性的同時也規(guī)定了信仰適用的范圍。信仰的真理只是針對宗教領域,他并沒有直接否定世界的實在性和理性在自身限度內(nèi)所獲得的客觀有效性。克爾凱郭爾反對和批判的是理性的僭越,而不是全盤否定理性的作用。正如利文斯頓所言,“克爾凱郭爾的神學不是一種極端的非理性主義。正相反,它的基礎,在于對人類理性的限度,對那些采取一種‘接近永恒狀態(tài)’立場的理性主義者的可笑自負,具有一種成熟的認識。”②[美]詹姆斯·C.利文斯頓:《現(xiàn)代基督教思想(下)》,第640頁。只要聯(lián)想到克爾凱郭爾所處的時代,他的宗教哲學其實是對現(xiàn)代性的一種清醒的反思。
理性與信仰之間的關系,要么是相互冒犯,要么是相互了解。主體居于何種狀態(tài),關鍵是對理性與信仰之間的差異是否了解。“如果差異得到確認,理性與信仰就完全可以在各自的地盤,獲得自身的合法性,反之,則產(chǎn)生所謂的冒犯。”③溫權:《信仰的悖論與理性的限度——克爾凱郭爾人神辯證法芻議》,《浙江工商大學學報》2016年第1期。按前文所說,冒犯的本質(zhì)是有限的理性無法理解無限者的悖論,但冒犯之所以產(chǎn)生并非受到悖論或者無限者的直接啟發(fā),而是需要主體主動的運用理性,去限制具有可能性的真理,并阻止由悖論所展示的超越理性的界限的真理,這就意味著,冒犯并不是理性所感受的無法突破邊界的消極恥辱,它是一種經(jīng)由主體理性的不斷攀登——就如蘇格拉底哲學激情所展示的那樣,才能出現(xiàn)的“瞬間”,正是這個瞬間的出現(xiàn),個體才能超越理性的有限,才能擁抱“永恒”。因此,冒犯不是被動的接受啟示,而是具有一種能動性,它以否定性的形式既表現(xiàn)出對理性自身的限制,又表現(xiàn)為對無限者的體驗。可見,個體要獲得對無限者的真誠的信仰,必須經(jīng)由冒犯的考驗。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克爾凱郭爾說:“所有冒犯在其最深層次上都是一種受難。”①[丹]索倫·克爾凱郭爾:《論懷疑者》,陸興華、翁紹軍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16頁。這就意味著,如果沒有理性突破邊界的思考和努力,信仰就將降格為一種愚信,這顯然也是克爾凱郭爾所反對的。對他而言,信仰是一件嚴肅的事情,這個過程絕非平坦舒適,而是飽經(jīng)磨難。當然,對克爾凱郭爾而言,信仰的跳躍還只是從信仰主體一方所做出的意志的選擇,信仰關系的形成還需要上帝的恩典,這是信仰關系達成的最基本的前提和條件。以蘇格拉底為代表的宗教A同樣具有激情,但宗教A沒有神的恩典的參與。因此每一個個體在面對絕對悖論的時候都處于被動的狀態(tài),從而凸顯了上帝作為絕對悖論在其中的重要地位,而理性激情在把握主觀真理上也就具有其局限性。
三、批判性啟示:克爾凱郭爾信仰觀的時代價值
克爾凱郭爾一方面通過對比理性與信仰的差異,揭示了理性主義至上的權威是對個體生存意義實現(xiàn)的傷害,因此他所確立的主觀真理在本質(zhì)上是對理性主義至上和忽視個體生存的抽象思辨的反思。另一方面,為了實現(xiàn)自己所提出的主觀真理,克爾凱郭爾又從理性與信仰的融合角度闡述了主觀真理實現(xiàn)的邏輯機制。綜上兩個部分都對新時代克服虛無主義,關注現(xiàn)實個體的生存境遇,進而實現(xiàn)理性與信仰的辯證的歷史的統(tǒng)一提供了重要的批判性啟示。所謂批判性的啟示是指從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出發(fā)汲取克爾凱郭爾信仰觀的積極因素來為新時代馬克思主義理想信念的培育路徑提供借鑒。
(一)培育真誠信仰:批判虛無主義的侵蝕
克爾凱郭爾認為自己所處的時代理性極度膨脹,無論是理性主義內(nèi)部的黑格爾將信仰理性化,還是基督教內(nèi)部把信仰世俗化,都面臨著相同的傾向,那就是按照理性的普遍性、世俗性、政治性、一致性來塑造自己,信仰于是淪為一種附庸,或者成為獲取功利目的之手段。但信仰所指向的主體內(nèi)在的激情卻并非一無是處,信仰的缺失恰恰讓時代的價值以及人的本質(zhì)發(fā)生異化。對克爾凱郭爾而言,信仰指向的是代表無限可能性的上帝,它是個體生存趨向自由和價值的唯一路徑。但是啟蒙理性的偏狹,讓主體崇尚功利的計算而摒棄內(nèi)在的激情,讓這個時代日益陷入金錢至上卻價值凋零的虛無主義的陷阱之中。隨著信仰最為內(nèi)在的激情被客觀理性所冷卻,人與他者的關系也日益變得空洞和單調(diào),甚至連宗教領域的虔誠也變得像是工廠流水線生產(chǎn)的商品。理性的功利化計算讓人與人的關系耗盡了原有的韻味和內(nèi)涵,變成一種沒有激情、責任與熱忱的純粹外在的抽象的關系。
克爾凱郭爾把其所處的時代與法國大革命時代進行對比,后者激情四射,而前者則單調(diào)貧乏。人們對金錢競相追逐,資本主義激發(fā)起全民利己主義的發(fā)財致富的社會風氣。人們拋棄了“統(tǒng)一和諧與有充分理由的倫理觀點”,整個社會陷入一種紙醉金迷的自私利己的惡性循環(huán)之中。克爾凱郭爾關于信仰的論述,蘊含著對大眾傳媒的社會、金錢至上、消費主義盛行的資本主義社會的批判。克爾凱郭爾基于信仰的主體性對啟蒙理性的反思在一定程度上和馬克思有相似之處。正如馬克思所言,“我們的一切發(fā)明和進步,似乎結果是使物質(zhì)力量成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則化為愚鈍的物質(zhì)力量。”①《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76頁。啟蒙理性自宗教改革伊始,確實為主體性的凸顯提供了理性支持,但也逐漸消解甚至坍塌了人的神圣、崇高的價值,導致虛無主義的泛濫。為此,克爾凱郭爾特別強調(diào)激情、內(nèi)在的真誠是主體通達真善美的必要環(huán)節(jié),僅有理性的計算和功利的衡量,一切高尚的行為都將變成有名無實的“電鍍?nèi)恕薄?/p>
盡管馬克思主義認為共產(chǎn)主義理想的實現(xiàn)需要一定的物質(zhì)奠基,而馬克思主義信仰也奠基于對社會歷史的科學認知和對客觀規(guī)律的科學把握,但共產(chǎn)主義運動作為一項締造理想社會的革命運動,在其實現(xiàn)過程中必然也會面臨種種困難和考驗,革命者必將歷經(jīng)思想上的彷徨甚至絕望。馬克思便曾明確指出,共產(chǎn)主義社會的實現(xiàn)作為社會歷史發(fā)展的一般規(guī)律,是一種占統(tǒng)治地位的趨勢,但這個作為平均數(shù)的趨勢“必然有某些起反作用的影響在發(fā)生作用,來阻撓和抵消這個一般規(guī)律的作用,使它只有趨勢的性質(zhì)。”②《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上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58頁。因此,克爾凱郭所談的信仰和激情自然在革命運動中變得非常之必要。這正是克爾凱郭爾的信仰觀給予我們的重要啟示。
(二)關注現(xiàn)實生存:反抗抽象思辨的空洞
克爾凱郭爾強調(diào)人的本質(zhì)并非外在于人的抽象思辨的概念實存,而是活生生的個體生存。對他而言,生存也不是像馬克思所說的現(xiàn)實的社會生存,而是個體內(nèi)在的精神信仰,具有內(nèi)在性、主體性的特征。他主要是在個體內(nèi)在的主觀情感體驗中把握人的現(xiàn)實生存,主觀自我與社會生存狀況之間的矛盾必然展現(xiàn)為憂慮、失望、懷疑、恐懼等主體的情緒。這些情緒也有其現(xiàn)實的根源,因而也是現(xiàn)實地影響人的個體發(fā)展的因素。他之所以批判資本主義社會矛盾和危機,根本原因是這些矛盾和危機加劇了人的異化和個體自由的喪失等現(xiàn)象。克爾凱郭爾的信仰觀的思想內(nèi)核其實是關注時代危機下的個體生存,他的思想在本質(zhì)上反映的是主體對自身生存境遇的不滿,并試圖從內(nèi)在真誠信仰來應對這些異化。克爾凱郭爾對基督教進行了內(nèi)部的批判,但他對基督教的理解主要是存在主義式的理解,他的宗教思想的關鍵詞主要是反映人的真誠的內(nèi)在精神和狀態(tài)的“激情”“熱忱”和“決斷”,這些情感性的價值依托在個體而不是社會之上,所以他說:基督教的真正精神在于個體內(nèi)在的激情或者反過來說,只有至上的激情才能使信仰展現(xiàn)為對個體永恒福祉的真實關切,脫離這一點都將淪為空洞的思辨。與克爾凱郭爾一樣,馬克思也批判黑格爾哲學對人的本質(zhì)規(guī)定的抽象性,但他認為人的本質(zhì)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因此一切異化都應在現(xiàn)實的社會關系的改變基礎上來加以克服。盡管克爾凱郭爾也批判資本主義對人的本質(zhì)的侵害,但他主要是從基于人的內(nèi)在性,即真誠信仰的達成和回歸來克服消費主義社會、大眾傳媒社會對人的內(nèi)在性的侵蝕,他忽略社會現(xiàn)實對人的本質(zhì)的根本性影響,因此他的措施其實是軟弱無力的虛幻的主觀想象。雖然馬克思強調(diào)要用社會性的革命實踐去克服這種異化,但他并不否定人具有內(nèi)在的精神世界,只不過他是在實踐基礎上認為人的本質(zhì)具有社會性和內(nèi)在性兩個辯證統(tǒng)一的向度。然而,以往學者在闡釋馬克思人的本質(zhì)學說的時候過于強調(diào)社會性和歷史性,一定程度上造成對人的內(nèi)在性的忽略。
克爾凱郭爾在個體內(nèi)在性方面的強調(diào),告訴我們必須重新關注馬克思對人的內(nèi)在性維度的規(guī)定。我們必須認識到,在實踐基礎上,人的內(nèi)在性是在社會性基礎上形成的,但人的社會性的發(fā)展亦需要內(nèi)在性維度的精神、道德和信仰的支撐,內(nèi)在性和社會性是辯證統(tǒng)一的關系。如果過于強調(diào)人的本質(zhì)的社會性和歷史性,那么個體在理想社會建設中的責任和價值就容易被忽略。從而導致如克爾凱郭爾所批評的大眾社會時代人的平均化現(xiàn)象,這種平均化現(xiàn)象最大的危害在于主體喪失自身的個體性,一味從眾而無革命的自覺。
在過去一段時間里,我們?yōu)榱嗣褡宓恼衽d而強調(diào)社會性的統(tǒng)一步伐,這自然符合我們國家的現(xiàn)實情況。如今,我們邁步走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國家新征程上,我們已然進入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社會利益關系和社會結構在四十多年來的改革開放中發(fā)生大幅的變化,價值觀念從單一走向多元,個體主體的自主意識、創(chuàng)新意識日益提高。克爾凱郭爾的個體生存哲學雖然忽略了個體生存的社會現(xiàn)實,但卻以否定性的形式強調(diào)了個體的獨特性及其對于主體自由全面發(fā)展的重要性。當然,我們也要清醒地認識到克爾凱郭爾脫離社會現(xiàn)實的個人內(nèi)在精神性的信仰是軟弱無力的,而把個體的價值和自覺淹沒在社會性歷史性的宏觀規(guī)律之中也是片面的。馬克思關于個體內(nèi)在性和社會性的辯證統(tǒng)一關系告訴我們,只有根源于社會現(xiàn)實的,成長于社會公眾又承認個體獨立之主體意識的對人的本質(zhì)的界定,才能既在社會層面應對現(xiàn)實的危機,又在內(nèi)心筑牢主體自覺的意識以防范主體在馬克思主義信仰層面的退卻,如此方能進一步激發(fā)個體的主人翁意識,以更好的精神面貌投身到新時代特色社會主義的建設中來,以個體內(nèi)在精神的高昂來推進歷史必然性的平均化水平。
正如克爾凱郭爾強調(diào)時間或歷史并非等值的物理時刻,而是具有激情灌注的瞬間一樣,馬克思也認為歷史中某些階段或時期在必然規(guī)律的體現(xiàn)上具有特殊性。這種特殊性在主觀層面表現(xiàn)為主體革命熱情的高漲。物質(zhì)上革命條件的具備依然需要革命者內(nèi)在的精神狀態(tài)與之匹配才能真正使規(guī)律轉(zhuǎn)化為具體的社會歷史的進步。而這正是克爾凱郭爾強調(diào)個體及其內(nèi)在信仰給予我們這個時代的批判性啟示。
(三)實踐哲學:理性與信仰的現(xiàn)實統(tǒng)一
首先,從理性與信仰統(tǒng)一的落腳點來看,克爾凱郭爾強調(diào)理性與信仰的匯通是經(jīng)由內(nèi)在激情的迸發(fā)達成的。克爾凱郭爾在一定程度上承認理性的激情經(jīng)由冒犯和攀登,可以達成信仰的跳躍,從而將理性與信仰統(tǒng)一在個體主體內(nèi)在的激情之上。克爾凱郭爾認為主觀真理并不是要尋求主體對上帝的認識性把握,而是要在激情的情感實踐中建立個體與上帝的關聯(lián)。這種基于激情的關系抉擇在本質(zhì)上是主觀層面的神秘意識,表明克爾凱郭爾將理性與信仰的統(tǒng)一奠基于一種作為信仰的主觀性之上。從根本上來看,如果黑格爾代表的唯心主義是以理性統(tǒng)合信仰,那么克爾凱郭爾則是以信仰統(tǒng)合理性,二者雖然相反,但其實有統(tǒng)一的唯心主義的思維模式,都未找到理性與信仰統(tǒng)一的基石。馬克思認為這個統(tǒng)一的基礎并不是理性也不是信仰,而是人的現(xiàn)實的實踐。馬克思認為理性是人追尋真理的根本能力,啟蒙理性的目標是獲得對于世界和社會歷史發(fā)展規(guī)律的掌握,進而實現(xiàn)人的自由全面發(fā)展。對馬克思而言,理性能把握真理的根據(jù)并不是因為理性具有先天賦予的觀念,也不是來自于后天經(jīng)驗的客觀對象,而是來自于現(xiàn)實的社會實踐。因此理性是主體通過現(xiàn)實社會的實踐逐漸在主體思維領域形成的能力。而信仰作為一種在主觀上的社會意識,其來源只能是社會存在。西方傳統(tǒng)思想對信仰的探討幾乎都沒有看到信仰的現(xiàn)實根源,而只是在意識決定物質(zhì)的思維模式下片面地夸大宗教信仰的功能和作用。其中黑格爾哲學雖然清除了宗教信仰的非理性的盲目崇拜,但卻將信仰的根源奠基在脫離現(xiàn)實的抽象思辨之上。克爾凱郭爾則試圖清除信仰的理性化和世俗化傾向,將信仰重新帶回到主觀內(nèi)在的情感之上。兩種模式其實都是將信仰立基于唯心主義之上。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將信仰的基石奠立于現(xiàn)實的社會實踐,批判傳統(tǒng)唯心主義對信仰的主觀性認識,賦予信仰社會性、歷史性的物質(zhì)生產(chǎn)實踐的現(xiàn)實內(nèi)容。
其次,在理性與信仰統(tǒng)一的內(nèi)容上,對克爾凱郭爾認為理性與信仰的對象內(nèi)容本質(zhì)上是存在絕對差異的。盡管理性對信仰的達成可以起到功能性的作用,但理性與信仰的對象卻存在絕對差異,即理性無法把握上帝,而只能是在思辨的攀登中感受上帝這一對象的荒謬。這種在真理對象上的不一致,必然帶來信仰的主觀真理與理性的客觀真理之間矛盾。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克爾凱郭爾說:“信仰就是內(nèi)在性的無限激情與客觀不確定性之間的矛盾。如果我能客觀上把握上帝,我就不會信仰;但是因為我不能,所以我必須信仰。”①S.Kierkegaard,The Concluding Unscientific Postscript,p.204.克爾凱郭爾信仰觀對理性與信仰的統(tǒng)一性論證因此必然也是基于神秘主義的神秘解釋,其本質(zhì)是唯心主義。與此不同,馬克思則認為,理性與信仰統(tǒng)一于實踐。因為實踐賦予理性與信仰在對象內(nèi)容上的統(tǒng)一性,這個內(nèi)容的實質(zhì)就是歷史唯物主義所揭示的人類社會發(fā)展的規(guī)律,而共產(chǎn)主義社會既是基于理性所認識的人類歷史發(fā)展規(guī)律,即歷史唯物主義所揭示的科學理論。無產(chǎn)階級為了實現(xiàn)這一科學理論所揭示的共產(chǎn)主義社會,必須具備在觀念形態(tài)上對自身這個階級使命的確證。共產(chǎn)主義信仰就是這種確證最高形態(tài),它將馬克思主義所揭示的唯物史觀作為無產(chǎn)階級的意識形態(tài),成為無產(chǎn)階級共同的理想信念。因此,理性所揭示的社會歷史發(fā)展的規(guī)律與信仰所指向的對于共產(chǎn)主義社會的理想信念就形成了在內(nèi)容上的現(xiàn)實性統(tǒng)一。在馬克思的時代,為了譴責唯心主義和神學家對“信仰”一詞的濫用,他明確指出,“共產(chǎn)主義對我們來說不是應當確立的狀況,不是現(xiàn)實應當與之相適應的理想。我們所稱為共產(chǎn)主義的是那種消滅現(xiàn)存狀況的現(xiàn)實的運動。這個運動的條件是由現(xiàn)有的前提產(chǎn)生的。”②《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166頁。可見在馬克思看來,共產(chǎn)主義并不是某種主觀的信仰,而是在把握現(xiàn)代社會發(fā)展規(guī)律的基礎上形成的科學的理論和信念。
綜上,本文圍繞理性與信仰關系探討了克爾凱郭爾信仰觀的主要內(nèi)容及其時代價值。我們必須清楚地看到,由于克爾凱郭爾信仰觀的唯心主義立場,他對理性與信仰之間對立與融合的統(tǒng)一關系其實并沒有找到真正現(xiàn)實的物質(zhì)性基礎,但他關于真誠信仰的論述對于反抗虛無主義和抽象思辨的空洞卻依然具有重要的思想史價值。“文明因多樣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鑒,因互鑒而發(fā)展。”③《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468頁。我們并不是要全盤地接受克爾凱郭爾的信仰觀,而是在堅定馬克思主義理想信念,樹立馬克思主義信仰的基礎上批判地汲取和借鑒克爾凱郭爾信仰觀的積極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