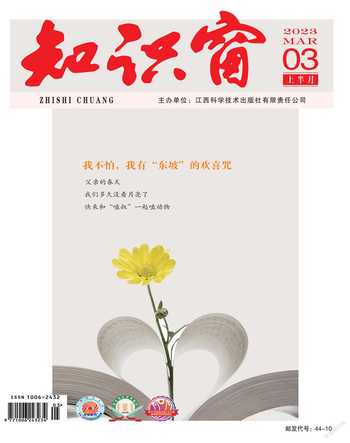我不怕,我有“東坡”的歡喜咒
余康妮

我的學生時代有過一個高光時刻,那是小學的一堂語文課,老師找同學背誦蘇東坡的詩。一時間,大家都被問住了。那一刻,我慶幸媽媽是位“東坡迷”。她告訴我,蘇東坡是個極可愛的人,也是極偉大的人。我大腦轉得飛快,心跳也倏地加快。最后,我舉手,流利地背出了《題西林壁》。
那天,我興高采烈地回家,心里生出莫名的興致。翻開外公的《蘇軾文集》,不多時便遇見了影響我一生的《定風波·莫聽穿林打葉聲》。我像個初嘗好茶的幼童,讀得并不明白,卻曉得其中有好味。夜里躺在床上,我分明看見鮮嫩的綠意,腮幫子一鼓一鼓的小蛙,還有那位沒帶雨具的先生。雨點打在他身上,打濕了他的衣衫,卻沒有打亂他的節奏。
第二天一早,我向媽媽提到《定風波·莫聽穿林打葉聲》,才得知寫這首詩時,蘇東坡被貶黃州,已遭遇寒徹骨的“烏臺詩案”。我的心湖泛起漣漪,我把“一蓑煙雨任平生”“也無風雨也無晴”寫在課本的扉頁。是的,蘇東坡的文字溫暖了他自己,溫暖了與他同時代的人,余熱還暖到我所處的時代,乃至我這個生命個體。了解蘇東坡越多,獲得的啟迪越深。后來,每當遭遇不如意,我都不由得憶起他“也無風雨也無晴”的氣度。有什么是值得害怕的呢?有何可怕?為何要怕?誰怕?路的盡頭,總是“也無風雨也無晴”的。如果說課堂上背誦的《題西林壁》似一陣不疾不徐的風從我心靈的湖面吹過,那么這首《定風波·莫聽穿林打葉聲》便是往我的心湖投下一顆石子。
雖然這顆石子悄無聲息地沉入平靜的湖底,但是起大波瀾時,黑云翻墨,這顆石子就會放出光來,照亮整片湖。
那時,父親在春月微冷的醫院里病成一頭盡完使命的老牛,又在灼人的猩紅火光中蜷成一堆殘破的紙錢。在父親的生命盡頭,東坡的話語又一次在我的心頭響起。這一次,它為我淡化了關于死別的恐懼。
歲歲清明,我蹲在清涼的風里。一片葳蕤之中,從前把我放在肩上的父親,問我晚上想吃什么的父親,一起擠著火車硬臥送我上大學的父親,永遠地縮在蔥蘢深處的一個盒子里。我記起蘇東坡也有過相似的沉痛。當把“料得年年腸斷處,明月夜,短松岡”流瀉于筆端的時候,他胸中的苦井想必也隨之涌出汩汩的水流,漫過心中的山林。雖然低落的情緒會將他淋濕,但是不會將他淹沒。憶起父親,我心中的田野不免被凄冷的苦雨再度浸濕。待到雨停風住,那便是我的自我開解之時。我又想起蘇東坡的輕吟:“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
我再次認識到文字的力量能強大至此,甚至能越過近千年的時間叩擊我的靈魂。受到這種神奇力量的鼓舞,我變得無比敬畏文字,信賴文字,生出學來他二分文采的心愿,也愿與文字終身為友,引領更多年輕一代與文字結伴。如今,我與學生講蘇東坡的故事,分享蘇東坡的智慧。學生不禁嘖嘖稱妙,既為他的可愛,又為他的偉大。
“老師,他做得真好!”一位學生樂呵呵地說道。他的臉上曾一度蒙著陰霾。
“老師,東坡先生這樣的人,應該算是苦中作樂吧?”
也許是吧,然究竟何為苦,何為樂?千人自有千解。也許如《題西林壁》所寫的那樣:“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不識廬山真面,只緣身在此山中。”在命運的波瀾面前,保持平和的心境是偉大的能力,這是蘇東坡教給我的。他時時引導我保持達觀,信步向前,一任生命的風雨從身邊打葉而過。感謝蘇東坡教會我以從容的心態與姿態應對人間萬事。生如逆旅,我幸得與這樣一位良師益友結緣。在風雨穿林之際,我早已習慣從心底掏出他的詞默念,仿佛喃喃著能召喚福分的歡喜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