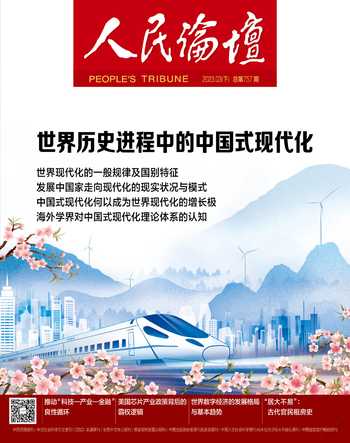海外學界對中國式現代化理論體系的認知
趙斌
【關鍵詞】海外中共學 中國式現代化理論體系 全球敘事 【中圖分類號】D61 【文獻標識碼】A

“中國式現代化”這一重要理念自正式提出以來,就得到國內外學界的廣泛關注和熱議。作為海外中國學領域的一大重要分支,海外中共學較為集中地反映了海外學界對中共黨史與黨建、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等重要理論或實踐相關研究的水準,而中國式現代化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因此注定會成為海外中共學敘事的一大焦點。
從發生學意義上看,中國式現代化敘事的出場與在場,可能被賦予了現代化理論體系及實踐的某些共有屬性。中國式現代化理論體系內生于中國土壤,且在(尤其新時代)中國與世界關系的相互建構中彰顯中國智慧。不論作為一種元敘事的理論體系,還是現代化之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踐衍生,當下及可見的將來,學界或可能從國際反饋層次對“中國式現代化”進行前沿追蹤。需要指出的是,“中國式現代化”作為近年(尤其國內)學界高度關注的理論議題,其國際反饋可能成為一個新的重要學術生長點:研究邊界可能觸及區域國別學、中共黨史黨建、國家安全學等新興學科,研究對象亦可能關涉政黨(交往)、政府(政策)、媒體(傳播)、企業(管理)等現代化政治與社會生活諸多向度。鑒于此,有必要通過高度聚焦的海外中共學視角,深入思考國際學界對中國式現代化理論體系的反饋,從“他者視鏡”理解中國式現代化的現實關切與全球關懷。
中國式現代化理論體系的海外中共學敘事
關于中國式現代化的國際/全球敘事衍生,所謂國際社會反映與評價必然紛繁復雜。即使我們將研究范圍限定為海外學界(如海外中國學),相關討論仍可能遭遇主題渙散等問題,因之或難以就中國式現代化理論體系展開跨越時空的高水平同行對話。對黨史、新中國史、改革開放史、社會主義發展史、中華民族發展史的全面深刻理解,離不開對中國共產黨這一領導核心的重點討論。海外中共學歷來關注中共黨史、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等重要歷史與現實,通過對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式現代化的持續觀察研究,較為準確地發現了認知中國式現代化何以可能的關鍵點:
其一,海外中共學對中國式現代化文明價值的闡釋和認同。海外中共學通過比較歷史分析發現,源自歐洲的社會主義得以在中國真正走向興盛,在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高度融合;中國具有深厚的文明土壤和社會主義發展的良好政治社會條件,并已邁上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2022年10月,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弘揚的“自信自強、守正創新、踔厲奮發、勇毅前行”的精神品質,體現出中國式現代化的精神內涵。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創造的人類文明新形態,兼具古今中外智慧,在傳統與現代、中國與世界的互動中,不僅維護全人類共同價值,還融合了農業、工業、數字經濟和生態文明,為世界繪就了新的文明愿景。
海外中共學通過世界近現代史和區域國別研究比較發現,西方大國崛起似難逃興衰周期,而中國式現代化卻具有可持續性。中國式現代化是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歸根結底,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式現代化的價值旨歸,在于以人民為中心。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黨沒有自己特殊的利益,黨在任何時候都把群眾利益放在第一位。這是我們黨作為馬克思主義政黨區別于其他政黨的顯著標志。”聯合國秘書長安東尼奧·古特雷斯(Antonio Guterres)曾評價,中國在減貧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是對全球減貧事業的重大貢獻。前巴西旅游部長和前巴西總統特別經濟顧問亞歷山德羅·戈隆別夫斯基·特謝拉(Alessandro Golombiewski Teixeira)認為,西方式現代化以生產資料私有制為核心,中國式現代化道路以公有制為核心,堅持以造福全體人民為目標。這并不意味著中國式現代化道路與資本隔絕,而是在社會主義公有制和共同富裕的前提下,準確調整資本與勞動關系,充分發揮和激活資本文明的一面,使之服務于現代化的目標。在這個意義上,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立足于人民群眾整體和切身利益,以人民群眾的主體愿望為動力。這種以人為本的思路從根本上區分了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和西方式現代化道路。
其二,海外中共學關注中國式現代化的全球關懷。社會主義中國“賢能政治”之成就,在消除絕對貧困之壯舉中得以充分體現,引發海外中共學乃至整個海外中國學界對西方“民主”理念的深刻反思;中國式現代化強調共享,這與謀求對發展中國家控制甚或壓迫的西方式現代化形成強烈反差,且中國式現代化崇尚人與自然和諧共生而非掠奪或破壞自然資源;“一帶一路”倡議、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全球文明倡議的提出,為合作共贏的全球議程設置提供了現實的經驗范本,說明中國式現代化關乎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對于全球多邊議程的推進具有重要意義。
二戰后,一些后發國家模仿甚至照搬西方式現代化,歷經一段時間中高速發展后,迅速陷入經濟停滯甚或衰退,墜入所謂“中等收入陷阱”,并遭遇政治失序、社會衰退、貧富差距拉大等發展難題。公允而言,國際社會理應容納不同的現代化路徑,也尊重各國人民對現代化道路的抉擇。美國共產黨秘書長克里斯托弗·赫拉利(Christopher Helali)認為,中國式現代化和可持續發展不僅提升了中國人民的生活水平,助益于中國社會發展,也促進了全球繁榮。中國帶動發展中國家群體促進經濟發展,實現互利共贏,而不是發展霸權或推行新殖民主義戰略。中國式現代化植根于以人為本的政治理念,中國共產黨愿同各國政黨分享現代化建設的經驗,以增進世界人民的福祉,豐富現代化理論與實踐,為世界現代化進程貢獻中國智慧。
海外中共學對中國式現代化理論體系的認知反饋
即使將研究視角和樣本限定于海外中共學這一看似狹小的專業視閾,其間亦可能存在一定的認知分歧甚或偏差。總體來看,西方學界的中國共產黨研究仍不乏一些傲慢偏見,而發展中國家及北歐國家的認知反饋則較為積極。海外中共學對中國式現代化理論體系的認知反饋可從如下五個方面探討:
第一,人口規模。海外中共學關注中國人口政策的變化,認為西方世界對中國人口政策存在誤讀,中國發展及其人口政策的調整,有助于縮小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關注“三孩”政策等新時代中國人口政策的新變化,認為“三孩”政策是中國緩解人口老齡化及低生育率的舉措,但也會受到高昂的教育成本、勞動力市場就業歧視等社會因素的干擾,其政策效果仍有待持續追蹤;①中國需要通過退休年齡延遲、養老金制度改革、城鄉結構調整、就業保障激勵、移民制度改革等途徑緩解養老和生育焦慮。
同時,中國人口政策與經濟增長之間的聯系,也成為海外中共學的關注焦點。比如,一些國際學者認為促進經濟增長的政策應更為行之有效,如鼓勵勞動力在本地創業就業等,由此連帶催生的激勵措施,推動經濟增長,并反過來有助于中國人口政策的優化。
第二,共同富裕。海外中共學關注中國城鎮化與脫貧事業。一些海外學者認為,中國城鎮化的遠景取決于國家與社會的長治久安,尤其是在世界經濟增長放緩之艱難時期,中國更需關照國內社會層面的焦慮情緒。雖然中國城鎮化進程受人口規模、城鄉收入分配差距、城市人口規模不均、城市間經濟結構差異、城市行政等級制度等因素影響,但中國宜居城市的經濟增長成就也舉世矚目。當然,此類對中國城鎮化進程的“審視”,無疑帶有某種西方中心主義色彩及公共政策分析偏好。
2022年,中國財政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與世界銀行共同發布了《中國減貧四十年:驅動力量、借鑒意義和未來政策方向》報告,報告顯示,過去40年來,中國貧困人口減少了近8億,占同期全球減貧人數的75%。中國的貧困治理成效具有劃時代意義,尤其是為發展中國家提供了重要的經驗啟迪。雖然海外中共學對中國貧困治理的認知不一,如有海外學者認為社會保障、教育和家庭補貼方面仍不夠完善等,但更多則贊賞中國貧困治理模式,認為中國為巴基斯坦等國利用有限資源消除多維貧困提供了范本,如對農村人口和城市人口施行有針對性的扶貧政策,進行試點推廣等。
第三,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除了物質文明的極大豐富,海外中共學同樣關注當代中國精神文明建設的進展,如通過城市個案分析,考察深圳的黨員發展情況和志愿服務活動的開展,進而分析公務員何以被激勵成為社區單元的社會行動者。②
青年是中國精神文明建設的主要群體和對象,也是中國精神文明建設的生力軍。在此過程中,新媒體發揮著重要媒介作用。有海外中共學者以上海青年對跨國流行影視劇的解讀為例,探討“向上流動”的當代中國青年,如何在集體主義價值觀內實現個人成長與商業、教育及社會發展目標的契合;同時,也有學者提出要重視中國社會文化環境變化,這將為新媒體條件下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的國家敘事形成提供新的內驅動力。
第四,人與自然和諧共生。關于中國經濟增長的環境代價分析,海外中共學高度評價了中國經濟增長之于全球經濟增長的引擎作用,以及中國農業發展對國家糧食安全的重要意義;同時也認為,高度依賴能源密集型重工業的經濟結構,導致中國將增長結構鎖定在高水平能源強度上,而農業經營和管理方式上也有著高額的環境成本,如過度使用化肥對土壤、空氣、水源造成污染。
關于中國環保承諾與行動,海外中共學認為,中國有能力在地方層面控制環境污染,并改善城市空氣和水的質量。具體到氣候治理與氣候行動,中國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扮演著重要角色,西方世界可以在空氣污染防治和碳排放交易體系方面與中國加強互動。一些海外學者認為,鑒于中國氣候政策在應對氣候危機、氣候治理與空氣污染防治等方面具有協同效應,中國國內氣候治理的政治和社會成本提高、減排成本下降,以及全球氣候談判與氣候行動激勵等制度化因素的轉變,因之在氣候變化議題上訴諸國家凈收益而非道義考慮,應當成為西方主要國家與中國互動時的優先項。海外中共學還進一步認可中國環境保護的獨特性與全球性。以林業為例,不同于西方某些草根環保運動,中國政府在生態環保進程中扮演著尤為關鍵的角色,且中國環境治理的經驗可能有助于環境社會學理論創新。③城市等次國家行為體在落實中央政策和氣候行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互聯網技術也增強了民間環保組織等非國家行為體參與中國環境治理的能力。至于“生態文明”“美麗中國”等典型的中國理念,也引發海外中共學關注,且將此類話語視作中國對“可持續發展”等相近理念的創新闡釋④,與“人類世”理念創設有異曲同工之妙,重構了知識與權力間的關系,中國學界也有望借此推動學科建設,并為全球可持續發展的科學進步貢獻新的知識。⑤
第五,和平發展。在看待中國發展壯大這一議題上,海外中共學與主流學界尤其是西方社會科學界保持著較高程度的一致。例如,認為中國的發展壯大將帶來一定的威脅;⑥西方媒體敘事引發普遍的對華焦慮,認為英文世界所謂“修昔底德陷阱”敘事反而可能導致局勢緊張甚或沖突惡化。
至于中國和平崛起與和平發展的可能性討論,英國國際關系學者巴里·布贊(Barry Buzan)認為,“和平崛起”比“和平發展”更適合于中國戰略研判,“和平崛起”是崛起中的大國得以在國際體系中與其他大國在物質能力、國際地位等方面獲得絕對或相對收益,且不會引發大規模的國際沖突,因而“和平崛起”可以看成是一個雙向進程,即新興大國適應國際社會規則與結構,同時其他大國也能適應新的權力和地位分配等新變化。
海外中共學對中國式現代化理論體系的認知歸因
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等更具未來政治色彩的中國(外交)新理念不同,中國式現代化(理論及其實踐)本身更多是以歷史進程和當代感來呈現的。海外中共學對中國式現代化理論體系的認知歸因,亦至少涉及如下三個層面:
其一,信息來源。盡管研究視角已然聚焦到小眾且專業的海外中共學領域,且假定海外科學研究者出于嚴謹學術分析的本能,必定會盡可能區分學術文獻和新聞媒體海量信息,然而學者仍很難實現研究數據來源完全客觀中立化。那么,中國的發展壯大本身可能被簡單化地視作經濟和軍事實力增長,因之時常被異化為全球和平與穩定的挑戰甚或威脅。同時,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海外學界關于美國霸權衰退的擔憂不絕于耳,英文世界習慣性將崛起大國對守成大國的挑戰稱為“某某陷阱”。一方面,中國努力通過對外宣傳等多渠道講好中國故事,傳遞中國聲音,但西方所謂主流媒體對中國的描述方式卻依然不乏主觀色彩甚至抹黑;另一方面,海外公眾的認知,至少部分受到其國內媒體敘事的影響。可見,這種理念沖突是社會建構的,我們需要關注國家身份、聯盟和戰略理論等何以在現有信息來源中進行社會建構。沖突分析框架的提出,可能超越學術研究的信息源本身,進而上升為國際政治問題。
相反,不妨再以上文提到的中國貧困治理和鄉村治理的成功經驗為例。這些案例之所以在發展中國家具有更廣泛的接受度,收獲積極反饋,本身也是發展中國家的海外中共學者對信息來源的篩選和“共情”決定的。出于相似的社會科學關懷,中國式現代化反映的中國之治,不論是宏觀經驗還是微觀經驗,都值得發展中國家借鑒。宏觀上,中國宏觀經濟增長軌跡反映了發展中國家持續高速增長的成功要素,如人力資本積累、外向型經濟、基礎設施公共投資、宏觀經濟穩定,以及符合比較優勢與支持競爭的結構性政策調整,激勵地方試點和創業來實現宏觀政策目標等,為有效治理提供了重要案例;微觀上,通過強大的電子商務和物流網絡,將農村地區納入城市供應鏈,以及用精準扶貧對貧困家庭和貧困地區進行有針對性的幫扶。⑦
其二,主體間認知。主體間認知差異長期存在且難以消弭,但又不能一概而論。換言之,剝離具體情境和信息來源的主體間認知,過多強調差異本身并無太多學理價值。具體到海外中共學對中國式現代化理論體系的解讀,其中的價值意涵及其背后的政治哲學基礎,值得比較和反思。以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為例,當涉及生態系統與生態文明話語時,中國國內學界較習慣于使用“建設”一詞,如“建設生態文明”“建設美麗中國”;但在海外中共學研究敘事里,西方更易接受的是“save/ preserve”,對應的是“nature, planet”——環保標語也成了“save the planet”“ nature needs half”,而不是“civilization”。在中文語境中,“生態環境”顯然是人類和自然過程的產物,法國哲學家拉圖爾所謂“現代人”的自然和社會政治(如氣候變化及其治理)是離散的,這是一種典型的西式二元認知,但這種二元認知或曰思維定勢已然被氣候變化等復合安全難題擾亂。從西方認知思維慣性看,人與自然是分開的,但“人類世”“地球史”等都超越了自然與社會間的二元性,迫使人們重新思考生態、氣候變化問題實際上是社會政治問題(如全球氣候政治)。因此,涉及生態文明“建設”時,其實關乎人與環境和諧共生,但在海外中共學敘事里,尚難以將植樹造林等行動視作保護“環境”,而偏向于將其劃歸為基礎設施(建設)范疇。
其三,敘事結構。海外中共學對中國式現代化理論體系的認知,反映了某種多線敘事結構。如上,海外中共學者獲取的信息來源較為單一(主要是英文信息源),敘事者往往又以非華裔的海外中共學者為主體(這不等于說華裔的海外中共學者的研究工作不重要),那么此時敘事結構就成了海外中共學突現于學界的直觀成品。換言之,盡管諸如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康燦雄(David Kang)、江憶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等海外學者對中國歷史與中國共產黨的認知不乏深刻洞見,但不論此類海外中共學(甚至包括更廣義的海外中國學)如何基于歷史詮釋或社會科學解釋框架,構筑起“精彩紛呈”的多線敘事,其背后或可能仍是一個“威斯特伐利亞束身衣”(Westphalian straightjacket)之下的“國際社會擴展”(the expans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進程邏輯。
中國式現代化理論體系的全球敘事路徑優化
與發展中的中國式現代化實踐幾近同步,中國式現代化理論體系也仍處于不斷完善和發展中,其全球敘事亦將隨之進一步展開。可以想見,凡涉及全球敘事,國內學界更多從國際傳播或中國理念對外宣傳的角度展開敘事路徑探析。于是,“國際傳播”“國際反饋”路徑分析,也成了近年來政治傳播研究當中的顯學(從“發出中國聲音”到“講好中國故事”)。不過,由上文認知歸因分析不難發現,傳播敘事路徑優化,或可能主要關涉大眾政治語言面向,且信息源往往關注廣義媒介,因之所及路徑探析,自然而然亦可能回落于政治話語之表征。換言之,有關政治傳播及其路徑優化的分析討論,既可能無處不在,又可能流于泛泛。鑒于此,有必要嘗試為中國式現代化理論體系的全球敘事開啟新的優化路徑。
第一,中國式現代化理論體系全球敘事的點面結合。所謂點面結合,至少包含兩層意思:一是以“海外中共學”研究為起點,以“海外中國學”研究為拓展面,從而較為科學、合理、漸進地延展關于中國式現代化理論體系全球敘事的學術分析。如此,方可能從研究設計和案例選取上精準把握中國式現代化理論體系全球敘事的問題點、議題面。試想,漫天撒網式的“國際反饋”研究,宛如游走于喧囂鬧市,所聞雜音往往可能更甚于研究者原本期待的理性思考。二是以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敘事為核心點,以當代中國尤其是新時代中國敘事為場域面,從而全面、深刻、動態理解中國式現代化理論體系的核心要義,而避免墜入海外中共學研究主題渙散之怪圈。以中國共產黨對外交往、中國外交為例,這些原本分屬于不同研究層次或范圍,倘若混為一談,不僅可能導致主題渙散,還可能被外界誤讀,滋生非中國世界的抵觸情緒和無謂焦慮。因此,何謂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新理念,何謂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所處的新時代場域,需要從全球敘事點、敘事面上清晰認知,并進一步優化敘事邏輯,以利于理論體系的整體完善。
第二,深化海外中共學視角下的中國式現代化理論體系研究,開展國際同行間高水平學術對話,推動全球知識界關于現代化理論與實踐的合作交流。如上文提到的不可避免且廣泛存在的主體間認知差異,不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還是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即使將研究視角聚焦為海外中共學,海外認知中的不同聲音仍不鮮見。研究層面小且專的海外中共學界同樣存在認知差異甚或誤解,更遑論“全球敘事”的無限拓寬。鑒于此,同樣不妨從兩個維度來尋求路徑優化:一是優化現有的學科布局和基礎研究條件,比如中國國內一些高校的全國重點馬克思主義學院,正嘗試或已經設立中共黨史黨建學一級學科。如何區別于這些單位原有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一級學科,如何就中國式現代化理論體系來從事前沿學術研究,回應時代和國家戰略需求,顯然是橫亙在新時代中國學者面前的新挑戰,但也是機遇所在。而“海外中共學”二級學科方向的設置,恰可能成為中國式現代化理論體系全球敘事建構的學術基地。二是國際同行間高水平學術對話的可能路徑探析,此處不妨仍以和平發展為例,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新理念,尤其是習近平外交思想中的新型國際關系理念,國際同行間的高水平對話似尚未開啟,而開展此類十分具體的理論對話勢在必行,因其事實上關系到合作共贏乃至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關于中國式現代化理論體系全球敘事的國際同行間對話亦概莫能外。鑒于此,可能的應對路徑,仍在于回歸學術研究本身,如可以嘗試借鑒理論經濟學、應用經濟學、政治社會學等社會科學中較為成型的話語體系,開展扎實的比較政治或歷史研究,從而真正意義上達到理論對話與爭鳴的短期目標,并最終邁向中國式現代化實踐之于新時代中國與世界關系良性互動意義上的全球敘事衍生等中長期目標。諸如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屢次載入聯合國決議,此類中國理念的實踐正能量,仍可能不斷涌現于國際平臺。
第三,推動中國式現代化理論體系的全球敘事結構優化。不論是直接尋求問題解決路徑的單線敘事,還是為打造更為立體的理論體系而構筑起來的多線敘事結構,一方面需要結合黨的二十大最新理論成果,繼續深化關于中國式現代化的學理闡釋,構建起符合中國式現代化理論體系豐富意涵的全球敘事;另一方面,以“中國式”敘事嵌入整個發展中國家世界現代化經驗分析討論,消解現有所謂現代化全球敘事的美歐中心主義,與國際社會共同實踐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全球文明倡議,或可能是中國式現代化理論體系全球敘事建構的必由之路。從中國式現代化理論體系的海外中共學敘事來看,中國式現代化理論體系的全球敘事結構優化,理應堅持以我為主,在此基礎上,博取眾家之長,為我所用。也就是說,不必刻意迎合所謂主流(尤其西方)現代化(理論與實踐)的標準,而仍以中國式探索、創造、追求為底色,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中國式現代化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
總而言之,中國式現代化并非完全形而上的抽象思想理論體系,而必定與具象化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有著深刻而現實的聯系。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指出:“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要求是: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高質量發展,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豐富人民精神世界,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海外中共學為中國式現代化理論體系的發展提供了“他者視鏡”,而中國式現代化理論體系的發展及其實踐進路,亦可能以海外中共學的他山之石為引,科學地、辯證地推進新時代中國與世界的良性互動。
(作者為西安交通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國際問題研究中心執行主任,西安交通大學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教授、博導)
【注: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新時代中國氣候外交的理論基礎與實踐路徑研究”(項目編號:19CGJ043)和第二批陜西省“高層次人才特殊支持計劃”(哲學社會科學、文化藝術類)青年拔尖人才支持計劃資助(項目編號:TZ0275)的研究成果】
【注釋】
①Isabelle Attané, “Chinas New Three-child Policy: What Effects Can We Expect?”, Population & Societies, Vol.596, No.1, 2022, pp.1-4.
②Deng Guosheng and Elaine Jeffreys, “Changing government in China through Philanthropy: On Socialist Spiritual Civilization, Civilized Cities and Good Communists”, Economy and Society, Vol.50, No.4, 2021, pp.517-541.
③Niklas Werner Weins et al.,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 the Making: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Climate-forestry Nexus”, Environmental Sociology, Vol.9, No.1, 2023, pp.6-19.
④Sam Geall and Adrian Ely, “Narratives and Pathways towards a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Vol.236, 2018, pp.1175-1196.
⑤Marinelli Maurizio, “How to Build a ‘Beautiful China in the Anthropocene: The Political Discourse and the Intellectual Debate 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Vol.23, No.3, 2018, pp.365-386.
⑥Timo Kivim?ki, “Finlandization and the Peaceful Development of China”,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8, No.2, 2015, pp.139-166.
⑦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世界銀行:《中國減貧四十年:驅動力量、借鑒意義和未來政策方向》,北京:中國發展出版社,2022年。
責編/周小梨 美編/楊玲玲
——評《中國現代化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