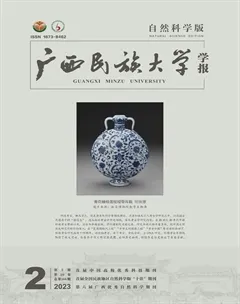科學史研究向何處去?
摘 要:科學史學科因學科內外各種不同的學術思想的碰撞而趨于撕裂,“萬花筒之喻”不足以告慰職業科學史家。文章致力于反思科學史與科學哲學、科學(知識)社會學、科學以及歷史學之間的學術互動進程,以揭示科學史學科從一開始就存在的、位于學科深層理論層面上的危機,指出欲維護學科完整性和學科自主性,科學史家須重返薩頓理想,發展長時段全球科學史。
關鍵詞:科學史理論;跨學科學術互動;薩頓理想;長時段全球科學史
中圖分類號: N09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3-8462(2023)02-0010-11
現代學術具有開放性,科學史亦然。每一領域皆有“不速之客”跨界而來,激起思想的碰撞和競爭,進而促使學術之花燦爛綻放。那么,在開放學術氛圍中,如何維護學術自主性?如何辨明職業科學史家所肩負的責任和使命?
喬治·薩頓(George Sarton,1884-1956)認定,構建科學史學科的意義在于可以溝通科學與人文。從一開始他就承認科學史研究的開放性,并且主張借助這種開放性來實現科學史的學術價值和社會-文化價值。因此,他在1913年Isis 雜志創刊號上宣稱,要將Isis 辦成“科學家的哲學雜志,哲學家的科學雜志;科學家的歷史雜志,歷史學家的科學雜志;科學家的社會學雜志,社會學家的科學雜志”。[1]然而,一個多世紀以來的科學史學科發展歷程并沒有如薩頓所構想的那樣,在科學與人文、理性與非理性、求真與求善之間真正搭起一座金色橋梁。時至今日,符合政治正確的意識形態已全面滲透于世界科學史研究之中,狹隘的民族主義在后現代的西方和古老的中國同樣盛行,科學與人文漸行漸遠,反科學的科學史和沒有科學的科學史登上了學術的大雅之堂。
在此,筆者對以往與科學史學科發展密切相關的跨學科思想互動作一番簡要的檢視,以幫助職業科學史研究者更好地理解科學史學科發展之格局,辨明學科發展之方向。
1 科學史與科學哲學之互動:一個悖論的產生
科學哲學家慣于從科學史案例中抽提科學哲學模型或理論,并將科學史視為其哲學模型或理論的應用領域。自邏輯經驗主義興起以來,莫不如此。然而,薩頓并不關注同時代的邏輯經驗主義的理論發展。作為科學史學科的重要奠基者,他對科學史的學科性質、價值、問題、主要方法、學科自主性及發展策略早已形成了系統的看法或信念。更重要的是,薩頓的科學觀導源于孔德實證主義,與邏輯經驗主義之間并不存在顯著的對立,其新人文主義史學信念與孔德式的科學信念之間雖然存在張力,但這種張力并不會導致整個系統信念的崩塌。
“ 二戰”結束后,邏輯經驗主義的整體理論,包括其科學觀與科學發展觀,均遭到越來越強烈的多方面的質疑和批判。一方面,如波普(Karl Popper,1902-1994)、庫恩(ThomasKuhn,1922-1996)、勞丹(Larry Laudan,1941-)等后邏輯經驗主義科學哲學家們無不急切地希望科學史家能夠用他們所提供的新的科學發展模型或理論替代邏輯經驗主義的舊模式,用科學史案例說明、支撐自己的模型或理論;期盼之余,科學哲學家也時常主動介入科學史研究。[2-3]另一方面,后現代主義者全盤否定邏輯經驗主義的基本理念,即使是真理概念和科學合理性概念,也無不遭到解構。
在此,我們首先要問的是,將科學哲學理論或社會學理論用作歷史理論——用作科學史的理論與方法,會出現何種結果?
在克勞的《科學編史學導論》出版之前,科學哲學家阿伽西(Joseph Agassi)先于職業科學史家寫出了一本題為《走向科學編史學》(Towards an Historiography of Science)的小冊子①。他不無天真地認定,科學史研究處于極不發達的狀態,之所以如此,是因為科學史家沿用了邏輯經驗主義的科學及科學積累進步概念,沒有采納他的老師卡爾·波普的“猜想-反駁”模型作為編史原則。因此,他號召科學史家在實踐中按照波普科學發展理論的指導展開科學史案例研究。[4]阿伽西甚至自己切入科學史研究,以法拉第《電學實驗研究》為對象,將法拉第的物理探索進程描繪成指向多種理論的猜想-反駁進程。[5]但是,在科學史家看來,這類研究充其量只是突出了歷史的某個側面,卻忽略了很多其他方面。
就結果來看,科學哲學理論或模型向科學史的滲透,已為大多數科學史家所拒斥,如薩頓拒斥了邏輯經驗主義。后來,科學史家又拒斥了阿伽西,拒斥了勞丹。原因在于,在歷史學家看來,為著哲學的目的而撰寫的歷史,有別于歷史學所內蘊的目標與價值,這種取向于某種科學哲學理論的歷史案例研究來說,或能清晰地呈現和解說哲學理論,但這種清晰的認知的涌現過程卻同時對歷史生動而復雜的完整畫卷構成某種遮蔽。
較為特殊的、須在此略加具體剖析的例子見諸庫恩和哈金(Ian Hacking,1936-)。庫恩于1962 年出版《科學革命的結構》(The Structure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以下簡稱《結構》),這本著作在科學史、技術史、科學哲學、科學社會學等多個領域,尤其在后兩個領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6]庫恩的第一身份,按他自己所述,是“科學史家”,而且《結構》也是以科學史家的口吻撰寫的,看起來很像是一本旨在沖擊和改變科學史家之科學史觀的科學編史學著作。在科學史方面,庫恩無疑曾深深地受惠于柯瓦雷(Alexandre Koyré,1892-1964)。在這本書中,他將柯瓦雷科學思想史版本的、大寫的、單數的科學革命概念(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升級為哲學版本的、小寫的、復數的科學革命概念(scientific revolutions),以“ 范式-科學共同體”這一成對概念為核心構建出成套的科學革命模型,以替代邏輯經驗主義關于科學發展的積累進步模型。庫恩以“ 范式轉換”(paradigmshift)解釋科學革命的本質,以急遽的思想革命甚至是心理學意義的格式塔轉換描述科學革命的機制。
庫恩關于范式-科學共同體成對概念的提出,恰恰構成了對康德“知識何以可能”的問題的再一次回答,盡管這一答案并不能算是一個全新的答案。庫恩像康德一樣關注人類的形而上學和智力底座,但他明確引入了新的分析視角,這一視角由共時歷史分析的視角和由“科學共同體”所隱含、所象征的社會學分析視角合并而成。庫恩的《結構》暗合了20 世紀初期物理學革命(以相對論和量子力學等的建立為標志)對現代人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所產生的全方位沖擊,但是庫恩沒有預料到的是,《結構》一書因其蘊藏社會學分析視角而在社會學界新興的社會建構論者那里贏得最強烈的共鳴,以至于我們今天完全有理由說,《結構》注定要被形形色色的后現代科學論者實行“強解讀”并被引作他們必讀的經典。
庫恩作為科學史家,于1978 年出版《黑體輻射理論和量子不連續:1894-1912》一書。[7]在此書中,他根本沒有采用他自己的哲學模型,也沒有討論相關的范式、科學共同體和革命,他似乎預知不宜按圖索驥地采用其范式-科學共同體概念和科學革命概念來書寫這段歷史。所以他回歸歷史學家本色,按照史學家查閱資料、采訪物理學家的通常做法而撰寫歷史,這曾讓因讀過《結構》而有所期待的讀者和評論者大跌眼鏡。更糟糕的是,庫恩的這本黑體輻射史研究著作在職業科學史家那里也未能得到一致好評。[8]在筆者看來,且不說他是否運用了自己的科學革命模型,僅從史學角度來評價,也只能說,其中大篇幅的艱深數學公式與涉及實驗探索的吝嗇文字形成鮮明對比,這一重思想而輕實驗的做法雖然暗合他的科學史觀,但很難說他真正把握了這一段物理學探索的輝煌歷史。
伊安·哈金也像庫恩一樣關注康德知識何以可能之問題,他不限于康德的純粹理性分析進路,而從歷史視角和社會視角汲取要素和營養。他說:“康德不把科學理性看作是歷史的、集體的產物,我們卻這樣看。”[9]178-199 如果說庫恩曾從柯瓦雷、弗立克(Ludwik Fleck,1896-1961)等主要探討科學主流話語且持理性主義立場的思想家那里獲得借鑒,[10]那么哈金則更多地從福軻(Michel Foucault,1926-1984)、費阿耶本德(Paul Feyerabend,1924-1994)等探討邊緣話語且持相對主義立場的思想家那里獲得借鑒。同時,區別于想要幫助或指導科學史研究的科學哲學家和科學知識社會學學者,哈金主動地、有些另類地從牛津科學史家克龍比(Alistair Cameron Crombie,1915-1996)處借用了styles 概念,構建其基于styles 研究的,既注重人類智力框架又注重經驗的,并且兼容歷史視角與社會學視角的科學哲學理論構架,其著名的《表征與干預:自然科學哲學主題導論》的出版奠定了他作為20 世紀后期一流科學哲學家的地位。[11-13]克龍比可以說是與柯瓦雷處于同一時代的,也是英國的第一位職業科學史家,其重要的代表作是他歷時40 年撰寫而成的三卷本《歐洲傳統中科學思維的式樣》(Styles of Sci?entific Thinking in the European Tradition)。[14]這是一部超長時段科學思想史著作。他對科學思想發展進程的理解與柯瓦雷有很大不同,克龍比認為科學思想是連續發展的。正因為存在著這種“連續論”與“斷裂論”之別,克龍比的長時段科學思想史研究長期居于邊緣地位,其學術影響一度湮滅于柯瓦雷科學革命敘事的洪流之中。克龍比所論之styles 是指古希臘以來的styles of scientific thinking and doing①,具有鮮明的長時段史學概念特征。他相信,這些styles 只發生發展于歐洲(包括古希臘在內)文明傳統之中,體現著歐洲科學思維和探索實踐所獨有的智力特征。希臘人創建了數學-演繹式樣、假定-模型式樣和實驗式樣,而13 世紀以后的歐洲人先后創建了概率-統計式樣、系統分類式樣以及歷史-進化式樣,這些式樣一旦產生,即持續存在并持續發揮作用,是它們引導新的學科或研究類型的產生。應該說,克龍比的研究進路是發人深省的,盡管它并不像柯瓦雷革命論綱領那樣振聾發聵,盡管它未能擺脫歐洲中心論立場。
關于哈金哲學性質的科學推理式樣概念(styles of scientific reasoning)與克龍比史學性質的科學思維與行動式樣概念之間的重要思想聯結和區別,筆者已有專門探討,此處不再復述。[15]在此,我們所關注的是,作為哲學家的哈金在《表征與干預:自然科學哲學主題導論》出版之前的1975 年和之后的1990 年,他分別撰寫了兩部“另類”著作,即《概率概念的發生:關于概率、歸納和統計推理概念的哲學探討》和《馴服偶然》。[16-17]這兩部著作分別探討了概率概念與非證明知識論在17 世紀的發生進程和概率論在19 世紀的發展進程,它們似哲學亦似歷史,似哲學史亦似數學史。然而,哈金本人對它們拒絕歸類。
哈金撰寫《概率概念的發生:關于概率、歸納和統計推理概念的哲學探討》時,應該是其哲學理論的初生期,其主、副標題顯示,他在開展關于概率-統計style 的發生學研究,其主要論題涉及三個方面:一是概率概念是17 世紀中期以后才有的概念,因為西方社會到此時才為這一概念的發生準備好條件,也就是說,概率概念的發生是西方社會與境中的一個突發現象。二是概率概念的發生,必然會導致休謨(David Hume, 1711-1776)歸納問題的發生,即未來必將出現一位休謨,他將提出歸納問題。三是要探討概率、歸納和統計推理概念的發生,須將視線集中于他所謂的“低科學”,如煉金術、化學乃至日常生活中的相關行為(如賭博、博彩)。
哲學家勞丹在《哲學評論》上發表書評,在肯定其研究主題的意義后,即從哲學史和科學史角度轉入一系列批評。他指出,休謨歸納不過是粗俗形式的歸納(plebeian induction),較之于后來的歸納研究,休謨形式的歸納在歸納思維史研究中并不像哈金設想的那么重要,不應占據核心地位;而且,他還指出,哈金認為概率和歸納思維的發生與他所謂的如天文學、光學、力學等高科學無關是完全錯誤的。[18]芝加哥大學統計學系的兩位數學家兼數學史家Daniel Garber 和Sandy Zabell 在《精密科學史檔案》上發表批評性論文。他們認為,哈金的概率發生論題是錯誤的,概率概念的產生并非源自一場突發性的革命,而是源自一個連續的發展過程,他們從連續論視角提出一套完全不同于哈金論題的歷史理解進路,并引用大量史料對哈金論題進行否證。[19]
我們將哈金的《概率概念的發生:關于概率、歸納和統計推理概念的哲學探討》《馴服偶然》以及他的科學推理式樣哲學理論合在一起看,可以發現,哈金挑選概率-統計式樣作為他的史學研究案例并借此闡發其科學哲學理論。后來,他在此基礎上提出,科學推理式樣的雛形經過半穩定的發生發展期后會步入“結晶”期。“結晶”是一個取自化學的隱喻,而科學推理式樣雛形發生“結晶”,就意味著發生了一種激劇變化,整個式樣到結晶時才真正形成,并由此全面開啟其社會化進程——干預或介入社會生活的進程。[9]至于他的概率概念研究著作如何歸類,相關論題是否獲得充足的史實支撐,是否為科學史家或科學哲學家接受,他都會像庫恩一樣對可能的批判有所預防,但說到底,他并不在意史學批判,因為他的根本目的不在于歷史,而在于借此思考并展現其哲學思想。
以上兩個例子展現了西方人文學術不斷批判、不斷走極端的特質,完全不同于中國傳統文化中的那種溫柔敦厚的詩教,這些批判本身即顯示,研究者的工作產生了跨學科的影響。跨學科的思想互動和學術實踐常常能給研究者帶來新的視角和意象,但是,就科學史研究而言,真正成功的跨界學術實踐是罕見的。跨學科的思想沖擊是一回事,而獲得完全的跨學科認可是另一回事。即使是像庫恩、哈金這樣具有跨學科影響力的學者,若將他們的哲學理論原封不動地當作史學理論或史學研究進路來用,也同樣是不適當的或難以取得圓滿成功的。
在審視科學史與科學哲學之間的學術互動進程時,平立克和蓋爾引出以下“悖論”:“敘事在歷史學中所發揮的中心作用必然牽涉更多的獨特性,同時,案例研究方法論在哲學中的規范性使用必然牽涉普遍性。”因此,“只要當代科學哲學還依靠歷史方法論來構建其個案研究,就會陷入一種自相矛盾的困境:歷史做得越好,哲學就做得越差”。[20]
2 科學史與默頓及后默頓科學社會學之互動:與境主義陷阱
薩頓時代的科學史與科學社會學之間存在兼容性。薩頓與默頓在科學觀上是一致的,而且默頓從身為導師組重要成員的薩頓那里傳承了許多重要的信念和方法,如科學自主性信念、薩頓算術(統計分析)。默頓認為:“特定的發現和發明屬于科學的內部史,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與那些純科學因素以外的因素無關。”[21]112 在他看來,科學社會學/史與科學內史并行不悖,科學社會學主要探討科學家的社會結構與功能,以及社會作為整體如何影響科學的整體格局和發展方向。默頓的追隨者,如本·戴維等人,也提出了社會學方法在科學史研究中的有效定義域,即謬誤社會學,認為社會學分析只適用于對科學錯誤的分析。后來,哲學家勞丹將之表述為“當且僅當信念不能用它們的合理性來說明時,知識社會學才可以插手對它們的說明”。[22]
隨著柯瓦雷科學思想史學派的興起,科學思想史家對于默頓科學社會學綱領提出了質疑。柯瓦雷像薩頓一樣,對科學進步論深信不疑。在柯瓦雷看來,與其說是人類社會促進了科學發展,不如倒過來說,是科學推動著人類社會進步。因此,柯瓦雷學派不認可默頓清教倫理促進科學進步之論題。關于默頓基于《國民傳記辭典》所載科學家傳記資料的統計分析來論證清教刺激17 世紀英格蘭科學技術進步的做法,霍爾對此嗤之以鼻。在他看來,統計科學家的宗教教派背景數據,并據之論證清教論題,就如同探討科學家的科學發現與他在作出重大科學發現時是穿著燈籠褲還是穿著馬桶褲的關系一樣,毫無意義。[23]
今天看來,柯瓦雷科學思想史學派與默頓學派之間的分歧或沖突遠沒有20 世紀60 年代的研究者們想象的那樣嚴重。盡管兩者在科學與社會誰驅動誰的問題上存在對峙,但從方法論上看,柯瓦雷傳統非常強調與境主義(con?textualism)和采用共時性質的與境分析,他要求研究者放下后見之明,回到歷史與境中理解當事人的思想和行動;[23]而默頓的結構-功能主義科學社會學同樣強調共時性質的社會結構分析。簡而言之,兩者在方法論上并無根本對立。
后現代取向的科學知識社會學學者,也如同后邏輯經驗主義科學哲學家一樣,從攻擊邏輯經驗主義科學觀入手,發展后現代旨趣的、解構論式的或建構論式的科學史話語。但是,與默頓學派有所區別的是,他們越出本·戴維的科學謬誤社會學的邊界來發展科學知識社會學/史,認定默頓所說的“特定的科學發現與發明”也服從且必須引入社會學分析。這些后現代學者淡化或否認科學合理性因素(科學理性思維和實驗探索)在科學發現中所起到的決定性影響,直至否認科學合理性和真理概念的價值,轉而強調理解“真科學”(指現實中以制度化形式存在的科學界),以利益追求、權力交換、談判協商解說“真科學”的本來面目。
然而,科學知識社會學/史所關注的科學發現案例都是基于短時段意義上的共時與境分析來完成,它們旨在解構科學進步或科學思想進步的宏大敘事,卻從未對科學史發展的整體進程給出新的理解。誠然,就薩頓實證主義式的科學進步敘事以及柯瓦雷關于科學革命的思想史敘事而言,后來的研究者可以從多個維度去批判、去解構,但是若批判者不能同時提供新的構建,則科學史作為一門學科就會失去其成立的理由。從薩頓時代起,綜合科學史研究就是科學史學科發展的命脈,如果丟掉了綜合科學史,就意味著將各門學科史交還給科學的各門學科,將科學思想史交給哲學,將科學-社會互動史交給社會學或政治學,那么,科學史這門學科就由此喪失其作為一門獨立學科而存在的價值。
科學知識社會學及相關后現代科學史話語缺乏長時段研究以及富于建設性的且行之有效的學術綱領,這種先天不足的話語體系只能依附于現代話語而存在,而且只能以反諷話語形式存在。因此,在奉行科技立國宗旨的當今時代(盡管他們稱之為“后現代”),這類學術難以在世界各國政府自主且充分地開啟其學術制度化發展道路,以至于不得不面向科學史、科學哲學、科學社會學等業已完成學科制度化的學科體制進行思想滲透和人才輸送。
較之于參與“哲學-史學”跨界研究實踐的科學哲學家們,后默頓時代的科學知識社會學/史學者以及科學的社會-文化研究者(so?cio-cultural studies of science)數十年來一直特別關注“社會學-史學”跨界研究,他們比薩頓、柯瓦雷的直系傳人們更熱心于更新和改造科學史學科的基本理論和學術織構,他們撰寫了多種科學史理論著作,其總數遠多于薩頓、柯瓦雷的傳人們所撰寫的史學理論著作。[24-27]事實上,他們以建構論和徹底的與境主義改造科學史和科學哲學原有的理論構架,不過是為了創造出一個更好的“寄生”環境。
從某種意義上說,后現代學者在科學史界的跨界行動中贏得很大成功,除了I.B. 柯恩(I. Bernard Cohen,1914-2003)等第一代職業科學史家,他們在更年輕的職業科學史家那里很少引起抵觸和抗拒,可以用作對照的是,后現代學者在向科學哲學界滲透時遭遇了理性主義哲學家們的強烈阻擊和批判。科學知識社會學學者曾自豪地宣稱,建構論綱領已在某種意義上控制了美國、英國以及歐洲科學史學術制度的“半壁江山”。
著名的社會建構論者,如皮克林(AndrewPickering)、加里森(Peter L. Galison)夏平(Steven Shapin)等人,他們往往在本科階段就接受過科學教育,接著在或有類似科學知識社會學學術取向的機構(如賓州大學科學史與科學社會學系)接受博士階段的訓練,然后順利步入科學史界,并通過他們語不驚人死不休式的判斷和雄辯贏得學術聲望和學術地位。如夏平,他在本科階段學習生物學,后于賓州大學科學史與科學社會學系取得博士學位,隨后加入布魯爾愛丁堡學派。1985 年,他與劍橋大學科學史系沙弗爾(Simon Schaffer)合作撰寫了《利維坦與空氣泵》,引入陌生人視角、相對主義視角、與境決定論視角,從科學-政治學或科學-權力論角度給出“全新”的解釋,給整個近代科學打上社會建構或政治建構的烙印或標簽,完全排斥科學家、科學思想史學派以及默頓科學社會學學派的傳統解釋。這些工作具有以下鮮明的特點:一是無視內史、外史之分。二是無視以波義耳(Robert Boyle,1627-1691)為代表的、新興的皇家學會實驗哲學研究與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79)唯理論知識論之分。三是無視實驗的具有普遍意義的客觀性質與在當時被附加于(演示)實驗之上的特殊的社會-文化性質之分。四是無視科學制度化進程的專業化要求。夏平還深入科學史理論與方法領域,主張科學史的社會建構論化,聲稱科學史與政治史具有完全重合的研究領域。[28]夏平的科學史理論重構以及他的科學史研究工作,雖然在當時已步入老年的科學思想史學派成員那里引來了嚴厲批評,[29-30]但在“ 二戰”以來逐漸在后現代風格的、強調自由民主至上和政治正確的西方人文學術氛圍中得到了熱烈贊揚。2004 年,夏平成功地進入哈佛大學科學史系——這一由薩頓親手開創的科學史研究重鎮,這曾讓國際科學史界的學者們一度瞠目結舌。夏平不但獲得過社會學方面的默頓獎和伊拉斯謨斯獎,而且獲得了科學史界的最高獎項——薩頓獎。
在此,我們須追問,為什么隨著科恩、吉利斯皮等第一代職業科學史家逐漸老去或逝去,國際科學史界會發生這種基旨性的變調?同時,我們須追問,以社會建構論為智力特征的后現代科學史理論與方法,能否真正替代薩頓的科學史傳統和柯瓦雷的科學思想史傳統,成為國際科學史研究的主流傳統?更重要的是,我們還須追問,若今天年輕的科學史家皆遵循這樣的傳統,科學史學科還有沒有未來?
早在20 世紀80 年代初,吉利斯皮就曾敏銳地注意到并深感痛楚地抱怨說,科學史正逐漸失去對科學的把握,正在遭受冒牌學問的戲弄。[31]時至今日,這些問題變得愈加嚴重。我們可以看到,當社會構建論視角被大量研究者采納以及科學知識社會史研究日趨興盛,科學史研究的問題及主題卻不斷變得碎片化,綜合性的、長時段的、連續論式的科學史研究越來越缺乏。例如,科學史著作常常被寫成沒有科學甚至是反科學的科學史,理性主義精神日漸失去,科學主義成為十足的貶義詞;當反科學主義興盛一時,真理概念本身也深受質疑時,科學發現過程被統一理解為利益驅動和協商解決的進程,科學合理性因素(如科學思維、科學方法和實驗)反而被一概漠視。概而言之,后現代形式的科學史研究似乎在宣稱:薩頓實證科學史研究毫無價值,需要徹底遺忘;而科學思想史學派所要揭示的科學進步論題和科學合理性概念,連同邏輯經驗主義所說的一切,皆與他們所描述的“真科學”相違背,皆為虛妄。
后現代論者對科學的非理性解說引起了科學家群體的高度反感和警惕。20 世紀末,物理學家索卡爾(Alan David Sokal,1955-)在后現代主流刊物《社會文本》上發表詐文《越界:走向量子引力的轉型詮釋學》,正式揭開了“科學戰”,他試圖以此呈現社會建構論的偽學術性質。[32]在詐文中,他一本正經地“胡說”道:物理世界的事實,如后現代主義所揭示的那樣,不過是純粹的社會或政治建構;量子引力,破壞了“存在”這個概念本身,為“得到解放的科學”(liberatory science)和“ 得到解放的數學”(emancipatory mathematics)開辟了道路。
索卡爾在某種意義上宣示了科學家群體對甚囂塵上的后現代學術的徹底否定態度①。在此,筆者不敢設想的是,若按照社會建構論的道路走下去,科學史事業與科學事業完全背離的那一天到底離我們還有多遠?
3 科學— 科學史— 歷史之互動:科學關切與歷史關切漸行漸遠
20 世紀60-70 年代,科學史家從科學家手中正式接過科學史的撰寫任務。在薩頓的科學-科學史-歷史互動模式中,科學史被視為一種需要科學本身參與其中的元科學研究,也就是說,科學家不但是科學史的主要讀者,而且兼為科學史的撰稿人。譬如,哈佛大學校長、化學家、教育家科南特(James Bryant Conant,1873-1978)于1940 年授予薩頓哈佛科學史教授的永久職位,并親自執筆撰寫《哈佛實驗科學案例史》以及其他科學史著作。[33]
時至2009 年,Peter Dear 在探討薩頓創辦Isis 的初衷以及該雜志出版100 卷的紀念文章中這樣寫道:“可以這樣說,在這一百卷出版過程中,已經出現了以下分流現象:Isis 已離科學家的專業關切越來越遠,與此同時,科學家也離職業化了的Isis的歷史關切越來越遠。”[ 34]
的確,職業形態的科學史正日益成為一般意義上的歷史研究,這與其說是因為科學史家有如霍爾所說的那樣采用了柯瓦雷式的研究方法,倒不如說是因為越來越多的科學史從業者不再像薩頓、柯瓦雷那樣將科學置于他們關注的焦點。
克龍比曾區分古文明中的實用知識與希臘意義上自然哲學的分支學科:天文歷法在古埃及、古巴比倫是實用知識,只有到了希臘,才可以說是自然哲學的一個分支學科。[14] 懷有強烈歷史關切的研究者將古埃及、古巴比倫天文歷法與古代文明的生產和政治運行關聯在一起加以探討,借以說明古代文明的知識構型與社會構型之間的關聯。同樣的,在歷史關切的引導下,研究者須將金字塔和木乃伊置于古埃及冥神教文化與境中加以研究。與之對照的是,在科學關切的引導下,一種簡單的做法是,拋開古埃及文化背景,參照今天的學科體制將金字塔和木乃伊研究當作是純粹的天文建筑史和醫學史對象來加以研究,但顯而易見的是,這類研究發生在年代錯置的前提下。要完整地展現科學史家應有的科學關切和歷史關切,還需要引入一種長時段全球史的研究視角,需要闡明古埃及的天文歷法、金字塔和木乃伊等實用知識體系如何傳入希臘,又如何在希臘發生演變并最終被納入自然哲學的知識框架之下的過程。可惜的是,長時段全球史的研究視角在當代科學史研究中少有問津。自柯瓦雷以降,科學革命論在科學史界壓倒了薩頓式的或是克龍比式的科學連續發展論,而后起的科學知識社會學/史研究專注于短時段案例研究,其研究綱領與長時段史學研究有著天然抵觸。
20 世紀以來的學術史研究表明,科學與人文的大分離已無可避免地降臨,而且分裂不僅發生在科學與人文之間,還發生在人類知識之所有領域的內部,或表現為理性與非理性之分,或表現為守護政治正確與守護真理之分,盡管早在20 世紀初薩頓和懷特海就預先察覺到這種文化分裂的信號并力圖防止或消解這種文化分裂現象。
在科學史界,上述分裂現象也表現得尤為突出:有歐洲科學史與非歐科學史之分(在中國表現為中西科學史之分,表現為研究對象相異),有意識形態陣營之分(即不同版本的政治正確之分),有民族主義陣營之分(表現為歐洲中心論與非歐文化的民族主義之對峙),有科學思想史與科學社會史之分(表現為方法論相異)。甚至,科學社會學/史圈內有默頓式科學社會學/史與科學知識社會學/史之分;科學思想史群體內部有柯瓦雷科學革命論與克龍比科學連續發展論之分;科學革命論內部還有大物理主義與反對大物理主義的兩種態度之分。所有這些分野不僅體現著學術分工之不同,而且體現著關于科學史的本體論和方法論之對峙,還體現著對話禁區的存在——持不同立場幾乎就意味著彼此之間無法完成對話。在此情形下,如何定義科學史?科學史還算得上是一個合法的專業領域或學科嗎?這些問題均不再像在薩頓和柯瓦雷時代那樣有著清晰而確定的答案。[35]
如果我們仍然堅持說科學史應該作為一門完整的學科而繼續存在下去,那么,科學史家還是要正視并回答這樣一個問題:科學家們所認定、所探索的科學事業是如何在歷史的長河中發生并發展至今的?
要回答這一問題,科學史家就必須站到長時段全球科學史的視角下反思科學史、反思科學史學史。
時至今日,科學史作為科學辯護或禮贊科學事業的日子已經成為過去,但這并不是說,沒有科學甚至是反科學的科學史就應該成為今日之科學史的主題。科學史家不能因為謀求自身理智的獨立性或學科獨立性,就必須踐踏科學并拒絕與科學家共享任何信念,譬如真理與科學合理性信念;也不能因為看到科學家群體內部的某些勾心斗角畫面而就此否認真理概念和科學合理性概念,其對科學家群體的行為仍然具有規范力和約束力;更不能因為看到現實中科學與政治之間的高度關聯以及科學背后常伴隨意識形態的作用和影響,而就此宣稱科學史與政治史具有完全重合的研究領域。
科學史家完全沒有必要冒充“陌生人”來觀察科學史,譬如,冒充既不懂科學也不懂哲學的門外漢來觀察波義耳與霍布斯之間的論戰,并且傻乎乎地為霍布斯嘲諷波義耳實驗哲學為“a philosophy of machine”而叫好。事實上,這樣做既不合乎歷史的方法論原則和評價準則,也不合乎科學發展的歷史進程。
福曼在探討科學史家的獨立性時曾經指出,20 世紀60 年代有不少科學史家曾錯把職業的獨立性與理智的獨立性混為一談。[36]在他看來,就科學史家而言,獨立性應當是指理智的獨立性。歷史之意義最終植根于史家的道德判斷,而科學家卻回避道德判斷,奉行“ 超越(Transcendence)”之宗旨,而“超越”不過是一種幻象和動機,它引導人們擺脫世俗生活或現實世界的紛擾,進入一個由理智的或美學的思想或理念所構成的超現實世界,一往無前地前進,并不斷地提升自己。因此,當一個科學史家追隨科學家進入這個超現實世界時,尤其是當他將視線過于狹窄地收縮于這個世界甚至只是關注其中的一部分,即知識世界或波普所說的“世界Ⅲ”時,他所能做的唯有“禮贊”(cele?bration)?然而,“ 禮贊”不可避免地導致“ 缺乏自我意識”的輝格史的產生,而對輝格史的反思又必然會要求研究者引入反輝格史的研究進路。但是,在不放棄“禮贊”的前提下,反輝格史的進路又必然是行不通的。福曼指出,科學內史研究者是在缺乏比“禮贊”更富于意義的道德動機的情形下轉而開始追求真相以反對輝格史,但這樣一來,他們便處于一種兩難境地:一方面試圖揭示歷史真相,另一方面卻遠離外史性的史料。歷史真相注定要與“禮贊”發生沖突。因此,福曼建議科學史家以“ 批判”(criticism)代替“禮贊”,與“超越”作別。從“批判”角度確立道德動機并付諸實踐,“科學史家就必須對現實中的不快與悲哀要有一種食欲,也必須樂于孑然佇立于世上、擺脫種種支撐性的意識形態,而不是與科學家一道愛神話勝于事實”。[36]他還強調說:“只有對科學知識施行徹底的歷史化——參照世俗因素與人的因素而非訴諸某種超現實的東西,解釋科學知識的種種特殊部分或結構——科學史家才能擺脫輝格史綱領,獲得理智上的獨立。”[36]
但是,福曼的論述系基于極不真切的前提,并且采用了類似于印度因明說中“ 難難”(故意曲解論敵,再加以駁斥)的駁難方式。必須看到的是:第一,科學家追求卓越,但絕非對道德問題漠不關心;第二,對于科學史家來說,“ 批判”與“ 禮贊”并非截然對立,只能二者擇一;第三,即使持“批判”立場,也并不意味著批判者就“擺脫種種支撐性的意識形態”;第四,科學史家欲尋求理智獨立,并非一定要與“超越”作別。在我看來,之所以說科學史家長期以來缺乏獨立的歷史意識,是因為他們未能自覺地上升到長時段全球科學史的高度深入思考科學史及科學史學史,并且由此找到自己獨立的見解。這正說明,今天我們尤為需要“超越”精神。“超越”,作為一種深層理念或動機,是絕不應該從科學史家的歷史意識的縱深處被清除出去的。事實上,任何一個真正的學者無不在追求著超越,當福曼提出“對科學知識施行徹底的歷史化”時,他不正是在試圖實現某種超越?
科學史家不能因為想要回避輝格史進路而生造歷史的復雜性,而就此否認科學進步,甚至斷言科學知識是任意的、相對的。
自巴特菲爾德在其《歷史的輝格詮釋》中定義并批判輝格史進路及宗旨以來,輝格禁忌赫然成為科學史界不容違背的一條重要規則,盡管歷史學界并不在意所謂的輝格禁忌。庫恩曾于1968 年描寫道:“內部編史學的新準則是什么呢?在可能的范圍內(永遠不是完全這樣,歷史也不可能是這樣寫出來的),科學史家應當撇開他所知道的科學。他的科學要從他所研究時期的教科書和刊物中學來,在革新家用他們的發現或發明改變科學的前進方向之前,他要熟悉當時的這些教科書和刊物及其所顯示的固有傳統。”[37]108
然而,霍爾在其發表于1983 年的《論輝格原則》一文中對所謂的輝格禁忌進行了清算。霍爾指出,巴特菲爾德并沒有在其《歷史的輝格詮釋》中給出任何反輝格史的研究進路。霍爾以伽利略“可是,它的確在運動”式的口吻宣稱科學的確在進步,并自信地論斷道:“所以,在我看來,輝格式的進步理念已然無可避免地被確立于科學史中。”[38]57 由此,我們就需要追問,庫恩所表述的“新準則”源于何處?其實,這種新準則完全導源于柯瓦雷的概念分析,與《歷史的輝格詮釋》并無本質關聯。
我們知道,自蘭克以來,記錄、描述真實的歷史,一直為許多史家引為自己的信念和使命。蘭克在其著作《回憶錄》中莊嚴宣稱:“歷史指定給本書的任務是:評判過去,教導現在,以利于未來。可是本書并不敢期望完成這樣崇高的任務。它的目的只不過是說明事情的真實情況而已。”[39]178但是,歷史學家們在史學實踐中已越來越清楚地意識到:一方面,“ 說明事情的真實情況”是極為困難的,沒有任何方法能夠保證實證史學一定能夠揭示真實的歷史;另一方面,歷史學家的使命也絕不僅僅在于“說明事情的真實情況”,歷史學的箭頭,在指向過去的同時,也真切地指向人類的現在與未來——換言之,過去的事件不但有其相對于“過去”而言的意義,而且有其相對于“過去與現在之間”以及“現在”或“未來”而言的意義。
4 結語
科學史這門學科從其學科制度化進程開啟之際便一直存在著深層次的理論危機,在薩頓時代,這表現為其新人文主義史學理念與實證史學編史綱領之間存在著難以化解的張力,也就是說,實證史學編史綱領不足以幫助他實現其科學-人文主義理想。當第一代職業科學史家轉而追隨柯瓦雷的科學思想史研究綱領,采納以“科學革命”學說為基調的歷史斷裂理解模式理解科學在全球發生發展的整體歷史進程之時,這種內在于科學史學科的理論危機又表現為對科學發展連續性的否認以及對共時性質的與境方法論的過度依賴,其結果是相關科學史研究由此染上了相對主義色彩,并為社會建構論綱領向科學史界的全面滲透打開了方便之門。但是,當科學知識社會史研究趁勢而起之時,科學史學科原有的、潛在的理論危機非但沒有消解,反而變得更加尖銳,建構論的科學編史學綱領染有鮮明的西方后現代社會政治色彩,非但不能為科學史學科完整性和獨立性提供有力的新辯護,反而促使科學史研究徹底地碎片化,甚至在其上打上了無視科學或反科學的烙印。
切斷了歷史,放棄了長時段研究,科學史家就放棄了對人類思想、社會和文化之深層結構的把握,也就放棄了對科學整體歷史的把握,就會成為真理的背棄者,其所書所寫,終將失去學術意義。而在長時段全球科學史的視界中,過去、現在與未來,是歷史時間的連續統一。歷史學家需要辨認過去,更需要“為歷史賦型”,科學史家亦然。[15]為此,科學史家須回到薩頓理想,回到薩頓的科學人文主義,回到科學國際主義,回到大歷史,回答長時段全球科學史問題。
[參考文獻]
[1] SARTON G.Historie de la science[J].Isis,1913,1(1):3-46.
[2] AGASSI A.Towards an Historiography of Science[M].Par?
is:Mouton amp; Co.,1963.
[3] LAUDAN L. The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C] ∥OLBYET R C. Companion to the History of
Modern Science.London: Routledge,1980: 47-59.
[4] AGASSI J. Towards an Historiography of Science[M].Paris:
Mouton amp; Co.,1963.
[5] AGASSI J. Faraday as a Natural Philosopher[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1.
[6] KUHN T.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M].Chica?
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2.
[7] KUHN T. Black-Body Theory and the Quantum Disconti?
nuity, 1894-1912[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8] KLEIN M, SHIMONY A, PINCH T. Paradigm Lost? A
Review Symposium[J].Isis,1979,70(3): 429-440.
[9] HACKING I.“Style” for Historians and Philosopher[C] ∥
HACKING I. Historical ontology. Cambridge: Harvard Uni?
versity Press,2002:178-199.
[10] FLECK L. Genesis and Development of a Scientific Fact
[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9.
[11] HACKING I. Language, Truth and Reason[C] ∥M. Hollis
amp; S. Lukes ed., Rationality and Relativism. Cambridge:
MIT Press,1982.
[12] HACKING I. Representing and Intervening: Introductory
Topics in the Philosophy of Natural Science[M]. Cam?
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
[13] 伊恩·哈金. 表征與干預:自然科學哲學主題導論[M]. 王
巍,孟強,譯. 北京:科學出版社,2011.
[14] CROMBIE A.Styles of Scientific Thinking in the Europe?
an Tradition:The History of Argument and Explanation Es?
pecially in the Mathematical and Biomedical Sciences and
Arts[M].London:Duckworth,1994.
[15] 袁江洋,佟藝辰. 回到歷史還是穿越歷史?—— 科學的歷
史哲學的反思[J]. 科學技術哲學研究,2021,38(2):20-26.
[16] HACKING I.The Emergence of Probability:A Philosophi?
cal Study of Early Ideas About Probability, Induction and
Statistical Inference[M].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
ss,1975.
[17] HACKING I. The Taming of Chance[M]. Cambridge Uni?
versity Press,1990.
[18] LAUDAN L.Ex-Huming Hacking[J].Erkenntnis,1978,13
(3):417-435.
[19] GARBER D, ZABELL S. On the Emergence of Pro babil?
ity[J]. Archive for History of Exact Sciences, 1979, 21(1):
33-53.
[20] PINNICK C, GALE G.Philosophy of Science and History
of Science:a troubling interaction[J].Journal for General Phi?
losophy of Science,2000,30(1):109-125.
[21] 默頓. 十七世紀英格蘭科學、技術與社會[M]. 范岱年,譯.
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
[22] 勞丹. 進步及其問題[M]. 方在慶,譯. 上海:上海譯文出版
社,1991.
[23] HALL R.Can the History of Science be History?[J].British
Journal for the History of Science,1969,4(15):207-220.
[24] SHAPIN S.History of Science and its Sociological Recon?
structions[J].History of Science,1982,20(3):157-211.
[25] SHAPIN S.Discipline and Bounding:The History and Soci?
ology of Science as Seen through the Externalism-Internal?
ism Debate[J]. History of Science,1992,30(4): 333-369.
[26] GOLINSKI J. Making Natural Knowledge: Constructivism
and the history of science[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27] CHATTOPADHYAYA D. Anthropology and Historiog?
raphy of Science[M].Athens:Ohio University Press,1990.
[28] SHAPIN S,SCHAFFER S.Leviathan and the Air-Pump:
Hobbes, Boyle, and the Experimental Life[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5.
[29] COHEN B. Book Review of Leviathan and the Air-Pump
[J].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1987,92(3):658-659.
[30] WESTFALL R. Book Review of Leviathan and the Air-
Pump[J].Philosophy of Science,1987,54(1):128-130.
[31] BROAD W. History of Science Losing Its Science[J]. Sci?
ence,1980,207:389.
[32] SOKAL A D. Transgressing the Boundaries: Towards a
Transformative Hermeneutics of Quantum Gravity[J]. So?
cial Text,1996,46/47:217-252.
[33] CONANT J B, L K (edLASH.).Harvard Case Histories in
Experimental Science[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7.
[34] DEAR P.The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he History of the Sci?
ences: George Sarton, Isis, and the Two Cultures[J].Isis,
2009,100(1):89-93.
[35] DEAR P. What Is the History of Science the History of?:
Early Modern Roots of the Ideology of Modern Science[J].
Isis,2005,96(3):390-406.
[36] FORMAN P. Independence, Not Transcendence, for the
Historian of Science[J].Isis,1991,82(1):71-86.
[37] 庫恩. 必要的張力—— 科學的傳統和變革論文選[M]. 紀
樹立,范岱年,譯.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
[38] HALL A R.On Whiggism[J].History of Science,1983,21:
57.
[39] 古奇. 十九世紀歷史學與歷史學家[M]. 耿淡如,譯. 北京:
商務印書館,1989.
[責任編輯 黃祖賓 楊小平]